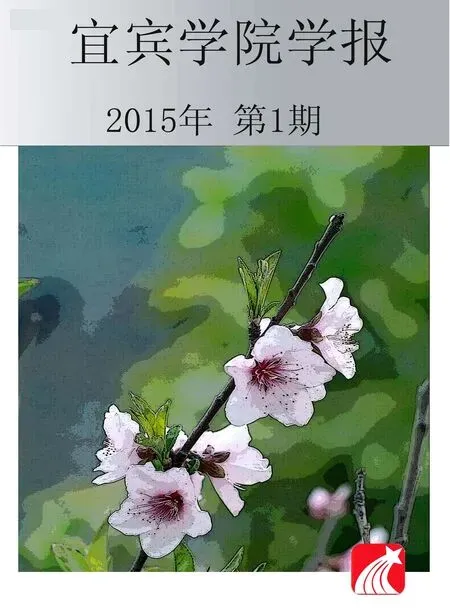从两份土地法文件看1946-1952年土改小说创作
彭冠龙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从两份土地法文件看1946-1952年土改小说创作
彭冠龙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主持人语:
突出文学研究的历史方法,是近年来学术的一大动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历史”也就是对“民国史”的尊重和挖掘。这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民国热”,而是对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降的“民国史”工程的借鉴,而这一工程本身就是我们国家政府主导的学术计划,得到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历史学的方法进入文学却只有短短几年,本刊从本期开始特辟“民国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学”专栏,发表国内外学界的相关论述,希望对这一研究有所贡献。
主持人简介:
李怡,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学术丛刊主编,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孙伟,南京大学博士,四川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土地改革小说创作潮流是一种特定时代与题材的文学书写思潮,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伴随着土地改革运动而起。党的土地法规和土改小说作品的关系并不能用“图解政策”简单概括:从作品内容方面看,小说对法规表现方式分为只选取很小部分予以表现和完全不表现两种类型,且在表现过程中充满了作者对法规的思考;从创作过程看,作者普遍坚持以自身亲历的事件为作品的基础和主要材料,同时,为了正确地反映土地改革而时刻考虑法规要求。实际上,1946-1952年土改小说创作是在一个由政策、艺术和生活三要素构成的场域环境中进行的。
土改小说;解放区文学;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社会运动,它使千百万农民“从封建剥削制度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第一次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1]404,从而极大地释放了他们的革命热情,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场运动从1946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52年,在此期间,大批知识分子作为“土改工作队员”,直接参与其中,并以小说形式反映着这一运动的过程,公开发表的作品数以百篇计。由于这场运动时间跨度长、过程复杂、意义重大,使得对其进行叙事的土改小说创作具有丰富性,其中,土改小说创作与土地法规的关系是历来被研究者关注的一点。
在土改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先后颁布了三份关于土地的法律文件。1946年,在老解放区已经进行过减租减息、新解放区进行了大规模反奸清算运动之后,解放区的阶级关系发生很大变化,但是封建土地关系依然存在,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关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支持前线的革命战争,中共中央于5月4日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土改运动兴起,这是中共中央在土改运动中颁布的第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发出不久,全面内战爆发,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使土改运动遇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另外,在执行《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这一文件的许多亟待解决的不足之处,中共中央决定于1947年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并于9月13日大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中共中央在土改运动中颁布的第二个土地法文件。新中国建立后,土改运动的直接目的由动员农民支持革命战争转变为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了顺应这一转变,1950年,中央政策研究室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经过一系列研究和修正,此文件在6月28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并于6月30日正式公布施行。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全国范围内出现参军参战的热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时代主题,使文学创作普遍以反映土改为手段为抗美援朝做宣传,因此,本文仅研究土改小说创作与前两份土地法文件的关系。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土改小说创作与土地法规的关系都以“图解政策”来简单概括。然而,仔细阅读《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后,再来看当时的土改小说作品,会发现二者关系并没有这么简单。
一 土改小说源于生活
《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有18项规定,在土改小说中被表现出来的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2]378这一项在每篇土改小说中都有所表现,因为这是土改运动的前提,没有这一项,土改运动不会发生,土改小说更无从谈起。
“(三)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如在清算、退租、土地改革时期,由于广大群众的要求,不能不有所侵犯时,亦不要打击得太重。”比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胡泰说的话:“像咱,他们只评成个富农,叫咱自动些出来,咱自动了六十亩地。咱两部车,他们全没要,牲口也留着,还让做买卖……”[3]223《旱》说得更直接:“现在的政策,富农的土地不动呀……刘少奇副主席在‘五一’劳动节大会上早讲过啦,这会毛主席也讲过了哩……”[4]
“(四)对于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的家属之属于豪绅地主成分者,对于在抗日期间,无论在解放区或在国民党区,与我们合作而不反共的开明绅士及其他人等,在运动中应谨慎处理,适当照顾,一般应采取调解仲裁方式。”这一项在土改小说中普遍被表现为地主经常利用的政策漏洞,如在《赵殿臣落网记》中,赵殿臣是个无恶不作的地主,“自从他知道他大儿子当了解放军的消息以后,他就披起‘光荣军属’的外衣来”[5]。《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的钱文贵也赶在土改前把二儿子钱义送去参军,当上了军属,因此在“密谋”那一章中说:“土地改革,咱不怕,要是闹得好,也许给分上二亩水地,咱钱义走时什么也没有要呢。”[3]17
“(六)集中注意于向汉奸、豪绅、恶霸作坚决的斗争,使他们完全孤立,并拿出土地来……对于汉奸、豪绅、恶霸所利用的走狗之属于中农、贫农及其他贫苦出身者,应采取争取分化政策,促其坦白反悔,不要侵犯其土地。在其坦白反悔后,须给以应得利益。”在这一项中,关于坚决斗争汉奸恶霸的内容在土改小说中有直接的展现,比如《拍碗图》对地主白吃鬼的斗争[6]、《暴风骤雨》对地主韩老六的斗争等。而关于分化中农、贫农及其他贫苦出身的走狗的内容,在土改小说中也有涉及,但是一般不写对走狗的劝说,而是一律将走狗塑造成投机分子、破坏分子和顽固分子等反面形象,比如在《暴风骤雨》中的韩长脖、李青山,在《邪不压正》中的小旦等。
“(八)除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及人民公敌为当地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处死者,应当赞成群众要求,经过法庭审判,正是判处死刑外,一般应施行宽大政策,不要杀人或打死人……”对这一项的表现多出现在斗争会场面中,比如《村仇》里写斗争地主赵文魁时,很多人冲上主席台打赵文魁,老刘“也过来劝解说:‘咱们不能乱打乱闹,他们有天大的罪恶,也要交法庭处理。’”[7]《邪不压正》写斗争地主刘锡元时,“不知道谁说了声打,大家一哄就把老家伙拖倒。小昌给他抹了一嘴屎,高工作员上去抱住他不让打,大家才算拉倒”[8]254。
970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early warning system in pre- and in-hospital connection of stroke patients
“(十二)在运动中所获得的果实,必须公平合理地分配给贫苦的烈士遗族、抗日战士、抗日干部及其家属和无地及少地的农民。”这一项在每篇土改小说中都有所表现,因为这是土改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土改小说中如果不表现这项政策,就无法准确反映土改运动的意义。
除以上6项之外,其余12项规定均未在土改小说中予以表现,也就是说,土改小说创作只反映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1/3的内容。若继续深究,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土改小说中有所表现的6项政策,有2项并非直接表现,而是在作品中被适当地加工了。
与《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情况类似,《中国土地法大纲》的16条规定也没有完全被土改小说创作所表现,在作品中能找到的仅有6条,即:“第一条,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第二条,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第五条,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第六条,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第八条,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第十三条,对于一切违抗或破坏本法的罪犯,应组织人民法庭予以审判及处分”。[9]3-8
另外,还有的土改小说作品与政策根本不沾边。比如孙犁的《村歌》,只用极小篇幅来写斗地主的情形,大量笔墨都放在干部群众之间、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之间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纠葛上;康濯的《买牛记》,通过买牛这件小事反映了土改之后农民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秦兆阳的《改造》,没有写对地主的残酷斗争,而是表现了在群众劝说和帮助下,一个游手好闲的地主变为普通劳动者的过程……
总之,土改小说的创作并不是原封不动地对党的土地政策完全予以表现,而是存在两种类型。第一种即是只选取很小一部分政策予以表现,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土改小说创作选取的这部分政策都是与“斗地主”“分土地”直接相关的,而那些被土改小说创作忽略的政策都与这两件事没有直接关系,比如团结知识分子、发展民兵组织及时开会总结经验等,在这类作品中,通常出现一种特殊情况,即有些政策被作者进行了加工修改,对这些政策规定的加工修改实际上也是更好地为“斗地主”和“分土地”服务的。第二种类型是完全不去表现政策,这一类作品与前一类正好相反,内容中没有“斗地主”和“分土地”,所写的要么是土改过程中的不良现象,要么是土改之后农民群众高涨的生产积极性。
结合作家创作过程来看,无论是那种类型的作品,所写内容实际都是作者自身亲历的事件。
在土改运动中,作家被“政策”驱赶着走进了农村,作为“土改工作队员”亲自参与土地改革工作,在参与过程中创作“土改”小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最早提出,要彻底明确“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就“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10]15。由于“为什么人”的问题被毛泽东定性为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一“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要求就被文艺界广泛宣传并认真践行了。在“土改”期间有关文艺工作的政策文件中,都能找到要求作家深入农村生活、参加土改运动的内容。比如,1950年的中南区文艺工作会议,就提出了这一年中南区的文艺工作方针和任务,其中指出:“一九五〇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生产建设和土地改革这两件大事。特别是土地改革……为了完成上述工作任务,必须要求每一个文艺工作者作艰苦的工作。所谓艰苦的工作,就是说,要有决心深入到工厂、农村中去,深入到群众运动中去,要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生产战线和土改战线上的斗争,要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做一个普通工人和普通农民的战斗伙伴。”[11]从《文艺报》刊载的来自南昌的一则通讯中可以看出当时江西省委宣传部和江西文联对作家参加“土改”的政策要求:“在省委宣传部的领导下,江西文联、文工团和广播电台合组了一个土地改革调查创作组,于六月底出发乡村……江西文联最近正计划吸收一部分在写作技巧和理论修养上有着一定水平的文艺工作者,摆脱原来的工作岗位,去参加土地改革去……”[12]在各地区这种政策的要求下,许多作家走进了农村,周立波去了松江省珠河县元宝区元宝镇,孙犁去了河北省饶阳县,沙汀去了四川华阳县石板滩,马烽去了晋绥根据地的崞县大牛堡村,等等。
这些作家在农村生活中不断发现素材,开始艺术构思。对于前文所述第一种类型的作品,以《暴风骤雨》的写作过程为例。在这部小说中,“人物和打胡子以及屯落的面貌,取材于尚志。斗争恶霸地主以及赵玉林牺牲的悲壮剧,取材于无常”[13]245。由此可见,这部小说的内容皆取材于作者的经历,而且在写作过程中,作者随时深入到实际斗争中寻找创作所需的现实原型,“初稿前后写了五十天,觉得材料不够用,又要求到五常周家岗去参与‘砍挖运动’。带了稿子到那儿,连修改,带添补,前后又是五十来天”[13]244-245。周立波始终认为“深深地感动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是第一等的文学材料”“所见所闻,是文学的第二位的材料”[13]246。因此,在《暴风骤雨》下卷的写作中,“写作的时间不算长,但是搜集和储备材料的时间却比较得多。宽一些说,从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八年春,除工作的时间外,都是下卷的积累材料的时间”“所用的材料,都是个人的经历和见闻”[14]249。除《暴风骤雨》外,田间的《拍碗图》、马烽的《村仇》、白苏林的《赵殿臣落网记》等作品的创作过程也都是很好的例子。
诸如此类的例子在每篇“土改”小说的创作中都存在,总体来看,在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作者都在亲身经历着土改运动,而且作者所重视的也正是“亲身经历”,而非“政策”,这种“亲身经历”就是“生活”。
二 重审政策与土改小说的关系
作家所重视的是“亲身经历”,是“生活”,那么,他们在创作过程中是否考虑了“政策”呢?答案是考虑了。不可否认,作为延安文艺理论指导下的文学创作潮流,土改小说的创作过程必然掺入了“政策”要素,这一点已经被研究者意识到了,但是,作家严格按照政策内容创作的真正目的以及作者对所反映的政策规定的思考却鲜有被注意到。
在创作过程中,作家确实是严格按照政策内容创作。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例,在创作这部小说之前,丁玲参加了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在怀来、涿鹿一带作了两个月的工作,在这期间,“卷入了复杂而又艰难的斗争热潮,忘我的工作了二十天”[16]125,《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根据这二十天的经历创作的。根据丁玲的回忆,在创作过程中,她为了不犯错误,“反复去,反复来,又读了些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材料”[16]126,也就是说,丁玲在创作时不断阅读关于土地改革的政策文件,其目的就是要保证作品中不出现政策问题,正因为如此,在塑造顾涌这个人物形象时,由于“当时任弼时同志的关于农村划成分的报告还没有出来。”“开始搞土改时根本没什么富裕中农这一说。”[17]141没有政策可依据,就“没敢给他定成分,只写他十四岁就给人家放羊,全家劳动,写出他对土地的渴望”[17]141。也正因为要保证作品中不出现政策问题,作品完成后,根据丁玲1948年6月16日的日记可知,在交给胡乔木审阅时,丁玲最关心的还是作品内容是否符合政策要求[18]。除这部作品之外,其他作品的创作过程无不存在这一现象,如孙犁的《秋千》、方纪的《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碧野《阿婵》等,就连周立波如前文所述那样重视亲身经历,也要在创作中考虑政策,对北满土改过程中违背政策的现象不予表现,并且指出“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写作,应该是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党性和阶级性的观点上所看到的一切真实之上的现实的再现”[14]250。
一旦作品内容不符合政策,就会招来“围攻”式的批判,比如秦兆阳的《改造》,作品发表六个月之后,《人民文学》第二卷第二期就刊出了有关这篇小说的两份评论文章,对这篇小说大加讨伐。徐国纶的《评〈改造〉》认为,《改造》采用劝说甚至帮助地主的方法在土改后是不适用的,对地主的改造应该实行强制劳动的方法[19];罗溟的《掩盖了阶级矛盾的本质》认为,这篇小说缺乏阶级分析,“爱”与“憎”是非常模糊的,无原则的歌颂了一个地主如何成了个“新人”[20]。从这些观点中可以看出,他们围绕的中心都是“不符合政策”。迫于压力,秦兆阳只得写检讨,承认自己没有写出地主阶级残酷地剥削农民阶级的本质,也没有写出正面人物对待王有德应具有的阶级立场和阶级觉悟[21]。
每一位作家都在创作中时刻考虑“政策”,一旦作品内容与政策有出入,就会被批评,这样看起来,土改小说创作似乎是在“图解政策”,而仔细观察他们对创作过程的自述以及他人的批判,会发现他们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正确地反映土地改革”。
在这里,所谓“正确地反映”不等于“如实地反映”,因为在“土改”过程中,自始至终都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错误,“查三代”“扫堂子”“搬石头”等现象都能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足以说明其普遍性,这些错误现象进入作品中之后不利于鼓舞和发动农民群众自发地参加斗争,与作家参与“土改”的主要工作——以文艺武器为土地改革服务——相矛盾。“正确”是指方向正确、与党中央的“土改”政策保持一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这就需要作者对政策有较深入理解,这一点几乎在每一份关于文艺工作者参加土地改革的政策文件和讨论文章中都明确提出了,如在1951年第2期《西南文艺》发表的刘仰桥的《参加土地改革,正确的反映土地改革》中明确指出:“要想正确地反映运动,表现新的人物,就必须熟悉运动的规律,熟悉新的人物,而熟悉政策则是真正熟悉运动熟悉人物必具的政治前提……”[22]杜润生在《在中南第二次文艺工作会议上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中也阐明了理解政策与正确反映土地改革的关系:“若不懂得土改政策,就是下乡去住上几年,也会茫然一无所知,发现不了问题,发现了问题无法正确反映。”[23]1950年9月《文艺报》发表的俞林的《我在土改中的一点经验》也着重说到这一问题:“我感到政策……是土改工作的重要环节,不理解这些问题就不能正确地了解这一运动,更不用说描写这一运动了”[24]。因为作家是作为“土改工作队员”参加土地改革的,所以“正确地反映土地改革”这一目的就成为了作家的工作任务,而熟悉政策、自觉地运用政策来表现土地改革运动就成为完成工作任务的必要手段。
在土改小说作品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对一些政策规定的反映,还能够看到作者对所反映的政策规定的思考。比如,在斗地主的时候,是否应该按群众的要求将地主就地打死,这就是对《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第八条的思考,反映到作品内容中,就出现了在斗争会场面里地主被打得半死时才会有干部上前保护的现象,如在《村仇》中群众斗争地主赵文魁时,群众已经开始打赵文魁,“赵拴拴……忽然又跳到了台下,一把扯住赵文魁的领口就打,他老婆也哭骂着扑过来了,用嘴咬赵文魁。田铁柱跳下台来去打田得胜……人们乱叫喊,有的也拥了过来”,在赵文魁被打了好久之后,老刘才劝解说“咱们不能乱打乱闹,他们有天大的罪恶,也要交法庭处理”[7]。类似的情节在田间的《拍碗图》、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邪不压正》等作品中都有呈现。地主作为统治阶级对农民长期以来的剥削,造成了尖锐的阶级对立,许多农民对地主产生了强烈的复仇情绪,这种情绪如果不能释放出来,可能会减弱群众斗争的积极性,而政策规定不能随意打死人,因此,作者在作品中总是先让地主挨打,再让干部来劝说,让读者把两方面都看到后自己再去评论。再如土地如何分配,这是对《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第十二条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第六条的思考,李伯钊的《桦树沟》就借群众之口探讨了这样几个问题:“把地都给了不会务育庄稼的傻子、懒汉,把咱生产给耽误了,咱八路军前方作战,还要不要吃公粮?”“按贫苦情形,按人口多少分地在理些。”“闺女分地是随婆家呢?还是随娘家?”[25]等,作者也是采取了把各种观点都摆出来,让读者自己去评论的办法。
三 在场域环境中进行的创作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土改小说的创作过程实际上存在着两组关系,即“艺术”——“生活”和“艺术”——“政策”,这两组关系并非彼此割裂,而是联系成了一个整体,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场域环境,见图1:

图1 艺术-生活-政策形成的场域环境
所谓“场域”,就是“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26]39,其中存在着力量和竞争。在这个三角形场域环境中,每两个要素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作家就在这样一个“场域环境”中进行创作,他们从“生活”中取材,经过艺术加工,创作出土改小说,这样一个原本很平常的创作过程被“政策”改变了。在这一过程中作家要时刻考虑“政策”,由此,“政策”影响到了土改小说创作,它甚至凌驾于“艺术”和“生活”之上,成为首要因素;作家的艺术创作在时刻考虑政策的同时,并没有对政策进行单纯的信息接收,他们首先在“政策”指导下用“艺术”正确地反映“生活”,并试图干预“生活”,即按照政策要求用土改小说正确地反映土地改革、指导土地改革;其次,他们用“艺术”思考“政策”、“政策”对“生活”的影响以及“生活”对“政策”影响的反映,试图通过这种思考对“政策”进行干预。
当然,以上只是建构了一个简单的模型,实际上,“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27],只有把这个模型放置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中去考察才有意义,对于土改小说创作来说,这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就是延安文艺理论所统治的文艺界,在民国时期仅仅局限于解放区文坛,新中国建立后则推广至整个中国文坛。在这样一个社会空间中,生活、政治和文学具有多重交叉的运动和互动效应,在这一效应的作用下,文学的政治化成为当时特定的“文学生态”,它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基础,后来经过周扬等人的不断阐释、发挥,以及建国后对《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等几次大的文学批判运动,其趋势不断加强。在这样一个文学生态中,土改小说仍然来源于生活,但要以党的文艺政策为标尺,不然就会被批判,《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邪不压正》《十年一别同口镇》《改造》等优秀作品都曾因此遭受指责,甚至受到严厉的政治批评;同时,在这样一个社会空间中,政策不仅仅是标尺,更是清规戒律,土改小说创作必须遵守党的文艺政策,由于“文艺为政治服务”是最根本的文艺政策,土改小说创作就必须同时遵守党的各项土地改革政策,在这两种政策的制约下担负起教育群众、宣传土改的重任,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这些作品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28]。当然,作家的创作会把土改运动中所存在的问题透露出来,只是要时刻警惕,以防触犯党的各项政策。
通过在一个具体社会空间中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一场域环境给土改小说的创作带来的影响。
首先是作家小心翼翼的创作心态。处在剧烈变化革命形势下的作家,往往缺乏准确把握政策的信心,加之不合理现象普遍存在的土改运动实际情况,使他们更加不知所措,在当时,阶级论已经作为统一的文学秩序逐步建立起来,“无产阶级立场”作为阶级论阐释体系的核心理念,其是否坚定可以从作品的政治倾向上反映出来,一旦作品的政治倾向出现偏差,就会被认定为作者的“无产阶级立场”不坚定,在这样一个“政治标准第一”的文艺界,如果对土改政策把握不准,并且在土改小说中透露出来,那么,作家将遭受难以想象的灾难,这种动辄得咎的恐惧令他们变得畏首畏尾。
其次,作家在场域环境中形成的小心翼翼的创作心态投射到作品中,就形成了一片光明的故事内容。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普遍存在,但政策要求作品必须“正确地反映土地改革”,作者试图以作品思考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但又不能让作品完全充斥着阴暗面,于是在小说内容中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无论土改过程有多么不合理,最终都会完美结束;无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有多么大,最终都会妥善解决;无论人物形象有多么落后,最终都会成为积极分子。这实际是在突显人民群众的“进步”过程,在“写进步东西是一种立场问题”[29]的时代,这种写法成了作家们唯一的选择,这种一片光明的故事内容绝对不会给作者带来麻烦,但是会给读者带来“虚假”的阅读感受。
不过读者的阅读感受并不重要,土改小说创作本身带有的革命功利主义倾向使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退居其次,这也是由场域创作环境造成的。在“政策”的影响下,文学创作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文学观所注重的是文学创作在宣传政治或教育人民方面的具体效果,要求文学创作树立阶级样板,而写新人物、光明面是塑造阶级样板的必要手段,由此可见,给读者带来“虚假”的阅读感受虽然降低了土改小说的审美意义,但是加强了作品必须具备的政治意义。
结语
总而言之,从作品内容方面看,小说对法律条文的表现方式分为两种类型,且在表现过程中充满了作者对土地法的思考;从创作过程看,作者普遍坚持以自身亲历的事件为作品的基础和主要材料,同时,作家为了正确反映土地改革而不断考虑法律政策要求。“土改小说”创作在一个由“政策”“生活”和“艺术”三要素构成的场域中小心翼翼地进行,作家把自己作为“齿轮和螺丝钉”,为“整个革命机器”的正常运作服务,由此可见,“土改小说”创作的背后隐藏着强烈的政治意图。
[1]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2]刘少奇.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M]//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4]祝向群.旱[J].人民文学,1950(5).
[5]白苏林.赵殿臣落网记[J].说说唱唱,1951(21).
[6]田间.拍碗图[J].文艺报,1950(1).
[7]马烽.村仇[J].人民文学,1949(创刊号).
[8]赵树理.邪不压正[M]//赵树理文集:第1卷.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
[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土地法大纲[M].渤海新华书店,1948.
[10]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1]熊复.中南区一九五〇年的文艺工作方针和任务[J].长江文艺,1950(2).
[12]王克浪.为土地改革进行准备:南昌通讯[J].文艺报,1950(12).
[13]周立波.《暴风骤雨》是怎样写的?[M]//周立波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14]周立波.现在想到的几点[M]//周立波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15]沙汀.在石板滩:一九五二年在四川华阳县石板滩参加土改日记片断[J].新文学史料,1991(3).
[16]丁玲.一点经验[M]//丁玲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17]丁玲.生活、思想与人物:在电影剧作讲习会上的讲话[M]//丁玲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18]丁玲.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J].新文学史料,1993 (2).
[19]徐国纶.评《改造》[J].人民文学,1950(2).
[20]罗溟.掩盖了阶级矛盾的本质[J].人民文学,1950 (2).
[21]秦兆阳.对“改造”的检讨[J].人民文学,1950(6).
[22]刘仰桥.参加土地改革,正确的反映土地改革[J].西南文艺,1951(2).
[23]杜润生.在中南第二次文艺工作会议上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J].长江文艺,1950(3).
[24]俞林.我在土改中的一点经验[J].文艺报,1950(12).
[25]李伯钊.桦树沟[J].说说唱唱,1952(26).
[26]Wacquant L.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A Workshop with Pierre Bourdieu[J].Sociological Theory,1989 (VII):9.
[27]毕天云.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论[J].学术探索,2004(1).
[28]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2001(2).
[29]何其芳.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论[J].文艺报,1949(4).
〔责任编辑:王 露〕
Analysis on“Land Reform Novel”Writing from 1946 to 1952 Based on Two Land Acts
PENG Guanl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5,Sichuan,China)
The trend of“land reform novel”writing is a form of literature expression characterized by a specific time and theme.It emerged in the 40s and 50s of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wake of the“land reform”movemen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cts issued by the Party and literature works can not be arbitrarily defined as“The Interpretation of Policy”.In terms of content,novels gave expression to the law in two differed forms,and were overflew with the authors’reflections on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in terms of the writing process,most authors wrote the works based on their own experiences while showing persisted concern for the specifications of the law with a view to give truthful account of the Land Reform.As a matter of fact,analyzed from the Field Theory,the“land reform novel”writing from 1946 to 1952 was defin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policy,art and life.
land reform novel;Liberated Area Literature;land reform movement
I207.42
A
1671-5365(2015)01-0016-09
2014-10-22
彭冠龙(1988-),男,山东泰安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