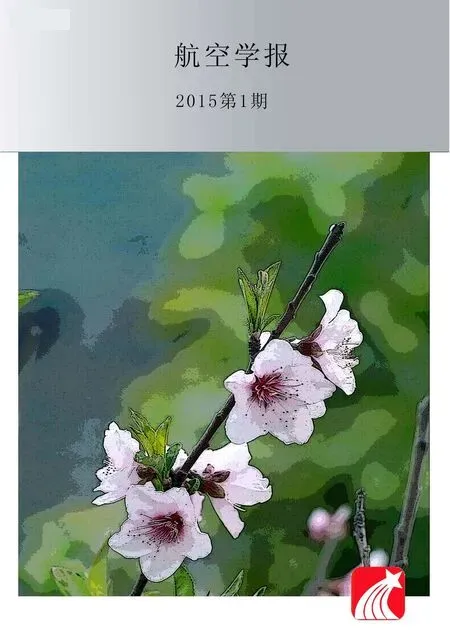高超声速飞行器流动特征分析
吴子牛, 白晨媛, 李娟, 陈梓钧, 汲世祥, 王聃, 王文斌, 徐艺哲, 姚瑶
清华大学 航天航空学院, 北京 100084
高超声速飞行器流动特征分析
吴子牛*, 白晨媛, 李娟, 陈梓钧, 汲世祥, 王聃, 王文斌, 徐艺哲, 姚瑶
清华大学 航天航空学院, 北京 100084
在非流线型构件或突起物的扰动效应、高马赫数和低雷诺数极限效应、低湍流度环境效应和由激波或摩擦导致的气动加热效应等4个方面的影响下,未来高超声速飞行器涉及的流动主要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典型流动结构强度高、尺度大,如强激波和厚边界层;局部流动结构数量多;激波、膨胀波和边界层结构之间相互干扰十分严重;转捩、压力脉动和一些流动结构对细微因素非常敏感;压力、摩擦应力和热流峰值现象普遍;升阻比屏障难以突破;流场同时依赖大量无量纲参数和有量纲参数,导致实验模拟难度大。本文在回顾传统高超声速流动主要流动现象的基础上,对上述7个方面涉及的典型流动现象的基础研究现状、问题本质和因果关系进行综合描述,讨论如何更有效地面对基础研究和工程实际问题。 该文既可为解决典型流动现象中尚未解决的基础研究提供帮助,也可为如何合理地利用有限的已知知识解决工程应用问题提供指导。
高超声速流动; 典型流动现象; 激波; 波系干扰; 因果关联度
高超声速流动的一些代表性经典理论足以让人们怀疑高超声速流动问题是一个简单且易于解决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Oswatitsch的马赫数无关原理[1]。依据实验和相似分析,Oswatitsch提出了基于无黏流动的高超声速马赫数无关原理,即当马赫数足够高(高于4~6,具体高于多少,与外形有关,越是钝头体起始马赫数越小)时,一些气动参数与流动形态与马赫数没有关系:①气动力系数和气动力矩系数;②压力系数、速度比及密度比;③脱体激波形状和脱体激波距离;④流线形态、声速面形态及超声速区的马赫波形态。
马赫数无关原理是基于无黏流动方程导出的,对于雷诺数足够大的钝体或者大迎角细长体绕流,由于压力远大于黏性力,这时马赫数无关原理是适用的。最近,Kliche等[2]考虑黏性流动,针对某轴对称钝头体数值模拟研究了马赫数无关原
理。他们的结论是:对于黏性绝热壁流动,马赫数无关原理仍然成立。但是,当壁面辐射热量时,即使马赫数大于16,增加马赫数会明显减小升力系数CL,增加力矩系数Cm,并略微增加阻力系数CD,减小升阻比L/D,如图1所示[2]。
该原理的价值在于可以由一个马赫数得到的气动参数反推其他马赫数下的气动参数。
另一个重要的经典知识就是牛顿的正弦平方定理。牛顿在其1687年出版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原理》中,把一般流动的流体看成由相互之间没有碰撞的粒子,与物体作用时切向动量保留而法向动量消失,从而利用其发现的动量定理,得出了平板受力正比于平板攻角的正弦平方的结论。牛顿的正弦平方定理虽然被认为阻碍了航空发展数百年(因为以此估算的气动力偏小,后来发现对于低速流动,气动力应该近似正比于攻角的正弦而不是正弦平方),但后来发现,对于高超声速流动,牛顿正弦平方定理以及后来修正的牛顿公式,如考虑了驻点压力修正的Lees修正,考虑了离心力的Busemann修正能合理地给出升力和波阻的近似值[3]。



图1 升力系数、阻力系数、力矩系数和升阻比随马赫数的变化(Re∞,u=50 000 m-1)[2]
基于这两个经典知识,人们可能得出结论,即高超声速流动是一般超声速流动结果将马赫数提高的简单定量延生,并且马赫数高到一定程度后,甚至都出现平台现象,即流动参数不再变化。
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否则,Bertin 和Cummings在2003年写综述论文时,不会以“高超声速50年了:我们过去在哪里,我们将往哪里去”作为标题[4]。原因如同他们后来在流体力学年鉴综述论文中所说的,高超声速流动存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气动以及气动热力学现象[5]。 整体气动加热与高温真实气体效应、多波系共存与干扰特征、低雷诺数环境下存在的黏性干扰和转捩不确定性、低密度空间的稀薄效应以及舵翼效率问题、激波附面层干扰等导致的局部热流峰值和压力脉动现象等,对飞行器外形设计、热防护设计、控制系统与动力系统设计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致实用的高超声速飞行器不是普通超声速飞行器的简单翻版,而是具有独特的外形、动力和控制机构。
虽然如此,传统的带翼再入和不带翼再入高超声速飞行器(如航天飞机和返回舱)已经发展成熟,或者说因为在大气层内过境时间短,气动约束不是特别严重; 而大气层内巡航类高超声速飞行器(或过境较长时间的大气层内滑翔的飞行器如CAV等)则由于需要长时间依赖气动力飞行,因此气动问题的特殊性会对高超声速飞行器的设计和应用起决定性作用。
因此,本文针对高超声速飞行器所面临的各种特殊流动现象进行归类综述,以期对基础研究、工程应用和二者的有机结合提供指导。
1 高超声速流动与飞行器特征
在本文中,用ρ、p、V、a、和γ分别表示密度、压力、速度、声速和比热比;α表示攻角;Cp表示压力系数;Ma表示马赫数;Re表示雷诺数;Kn表示努森数;θ表示气流偏转角;来流参数用下标∞表示;L、D表示升、阻力。
1.1 高超声速流动基本特征回顾
对于再入类高超声速飞行器,区别于其他流动的高超声速流动基本特征,在人们熟悉的图2中得到集中体现。这些流动特征包括:
1) 气动加热与高温效应,即经过激波减速加热或壁面摩擦减速加热,导致空气温度增加,引起分子振动能的激化、化学反应、电离和辐射(与马赫数的关系见2.6节)。这些化学反应,主要都是吸热反应,使得空气温度比单纯激波与摩擦加热引起的温度要低不少(例如,阿波罗宇宙飞船驻点最高温度实际为11 000K左右,而不考虑化学反应和辐射的理论值为60 000K)。化学反应改变了气体特性,如比热比和声速等,反过来影响流动规律。
2) 薄激波层效应,即脱体激波贴近物面,一方面与边界层外缘等可能直接接触,另一方面可能更容易打在飞行器突起物上或与下游突起物产生的激波膨胀波等结构发生强干扰。
3) 强黏性效应,即边界层由于其厚度近似正比于马赫数平方,因此对无黏流特性(如压力分布)的影响不是像低速流动一样只是一个小的位移厚度修正,而是有较大的影响。
4) 低密度和低雷诺数效应, 这导致可能产生稀薄效应(如飞行器整体在70km以上的高度,如果是小曲率半径的前缘,则在更低的高度),以及由于雷诺数较低,引起摩擦阻力太高(因为摩擦阻力随雷诺数降低而增加)或层流向湍流转捩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转捩不确定性中,还存在一个所谓的钝头体佯缪现象[6],即对于球形钝头体,转捩奇怪地出现在本应该为层流区的顺压梯度区域。

图2 高超声速飞行器流动特征[3]Fig.2 Flow characteristics for hypersonic vehicle[3]
在经典的高超声速教科书(如文献[3])中,这些高超声速流动内容是主要关注对象。然而,这些基本特征,主要反映了那些只是短时间穿越大气层的极高马赫数高超声速飞行器(如航天飞机再入、弹道洲际导弹)的流动,对于目前重点关注的在大气层有较长时间巡航或滑行的高超声速飞行,除这些流动现象可能存在外,还有许多更典型的流动现象。为此,本文先在1.2节简单介绍一下不同类型高超声速飞行器与流动特征的关联,接着在第2节介绍以第3类即巡航类飞行器为主的典型流动现象。
1.2 各类高超声速飞行器与流动
从Allen提出钝头体理论解决高超声速飞行器气动加热问题,到通过X-43验证超燃冲压发动机,人们主要见证了3类高超声速飞行器[7]:
1) 带翼再入飞行器(WingedRe-entryVehicles,RV-W):如航天飞机,Hermes,Hope-X,X-34,X-38,X-37B,Hopper/Phonex。
2) 不带翼再入飞行器(Non-WingedRe-entryVehicles,RV-NW): 如Huygens,Beagle2,Orex,APPOLO,ARD,SOYUZ,VIKING,AFE,CARINA,神州系列返回舱。
3) 基于吸气式发动机的巡航与加速飞行器(CruiseandAcceleratingVehicles,CAV)或上升再入飞行器(AscendingRe-entryVehicle,ARV):Sanger,X-43。
从Allen提出钝头体理论解决高超声速飞行器气动加热问题,到通过X-43验证超燃冲压发动机关键技术,前后经历了半过多世纪。人们已经对各类飞行器大致的流动特征有了总体性了解:
1) 再入或弹道类飞行器:压力效应主导,强真实气体效应,表面辐射,低密度效应,总体加热严重。采用钝头体减少物体加热,但钝头体可能存在转捩位置提前的问题(钝头体佯谬)。
2) 巡航飞行器:黏性效应主导,层流湍流转捩,表面辐射,弱真实气体效应,局部加热严重。对于这类飞行器,升阻比本来就存在屏障,因此很难采用钝头体,但局部非流线型构型或突起物的存在会导致严重的激波干扰线性和局部峰值热流。
从设计角度,各类飞行器的气动力和气动热现象, 在文献[7]中有了详细介绍,包括:
1) 各类飞行器不同部位的特殊流动现象,见图3~图5。
2) 各类飞行器升阻力参数和力矩参数随马赫数与攻角的变化曲线。
3) 各种因素的影响与各种部件的气动特性及其影响。
气动加热问题、升阻比屏障问题、动力问题和舵翼效率在各类高超声速飞行器的设计中都是可能需要考虑的因素。
气动加热是各类高超声速飞行器需要特别考虑的问题。再入飞行器不太关注升阻比之类的气动特性,可通过Allen的钝头体理论或烧蚀方式解决气动加热问题。钝头体理论设计的钝头体,采用脱体激波预先加热并通过外部流动带走主要热量,减轻了物面加热的负担。这是激波有效利用的方式之一,以增加波阻来解决极高马赫数的再入飞行器热障问题。但对于巡航类高超声速飞行器,飞行马赫数不是特别高,在稠密大气层的长时间巡航,要求波阻足够小,因此无法采用传统的大钝头体。但由此出现尖锐前缘局部高热流问题,而再入类飞行器只是总体加热严重。对于巡航类飞行器,尖锐前缘的高热流问题、激波边界层干扰导致的局部典型高热流问题将在2.1~2.5节中进一步介绍。

图3 带翼再入飞行器流动特征(钝头体,厚机身)Fig.3 Flow characteristics for winged re-entry vehicle (blunt nose,thick fuselage)
图4 不带翼再入飞行器流动特征 Fig.4 Flow characteristics for non-winged re-entry vehicle
图5 巡航类高超声速飞行器流动特征(乘波型)Fig.5 Flow characteristics for hypersonic cruise vehicle(waverider)
升阻比屏障是巡航类高超声速飞行器面临的一个困难(再入类并不追求高升阻比)。Kuchemann针对一些高超声速飞行器设计方案拟合了升阻比极限公式[8],Corda和Anderson针对优化的高超声速飞行器,给出了修正的升阻比极限公式[9]。具体而言,对于给定的马赫数Ma,升阻比L/D极限公式为
(1)
该公式表明,随着马赫数的增加,升阻比减小,很难超过6。其实考虑了吸气时发动机的高超声速飞行器,升阻比往往只有3以下(如图 6所示),哪怕提高0.1也很困难。升阻比极限往往被简单地归结为波阻的存在。其实,当马赫数增加时,升力系数、波阻力系数和摩阻系数都在减小(文献[2]指出,考虑有壁面辐射时,如果马赫数非常高,则摩阻系数可能是马赫数的增函数,见图1),因此马赫数的增加导致升阻比减小的原因并不那么直接。例如,以小扰动平板为例,假设(小)攻角给定,那么升力除以波阻(考虑参考温度修正)和层流摩阻后,升阻比在高马赫数下的极限为
(2)

图6 各种外形高超声速飞行器升阻比[10]Fig.6 Lift to drag ratio for various hypersonic vehicles[10]
采用Nonweiller提出的乘波体概念[11],可提高升阻比,使得升阻比极限由Corda和Anderson公式界定。巡航类飞行器可能更多采用乘波体外形。乘波体外形是激波的另一项有益利用,即利用驾驭激波产生升力。
无论如何,激波被认为是阻力产生的主要根源,因此人们试图用各种方式去减小激波带来的阻力[12]。
激波是否有益,主要取决于激波在什么位置(见2.1节)。文献[13]探讨了一种将可产生激波的物体倒扣在平板下方的升阻力解耦机制,以提高升阻比(如图 7所示)。

图7 升力面与阻力面独立的外形[13]Fig.7 Decoupled lifting and drag surfaces[13]

动力问题包括再入和滑翔类飞行器的姿控(见下面的舵翼效率问题)和巡航类高超声速飞行器中超燃冲压吸气式发动机(ARV之类的飞行器则在某些阶段采用吸气式发动机)。超燃冲压发动机主要由进气道、隔离段、燃烧室和喷管组成。前体激波、压缩面激波、唇口脱体激波及其与前体激波干扰、激波在进气道反射与激波之间相互干扰,激波边界层干扰、激波串、燃料射流激波、燃烧室凹腔激波与压力脉动等,这些是存在于发动机内的丰富多彩的流动结构(如图 8所示),对发动机性能与稳定性有重要影响, 在设计中需要充分考虑[14]。 发动机结构能否承受局部典型峰值热流和压力脉动,发动机本身能否在喷管处产生足够的推力,使得平衡前体阻力后,还能剩下足够的净推力,与进气道设计、内流道流场品质(均匀性、流量系数、压力畸变系数等)、隔离段的性能、燃料的有效混合、燃烧火焰的稳定性、多波系结构的相互干扰等密切相关,这些问题将在第2节的分析中进一步考虑。
图8 超燃冲压发动机示意图Fig.8 Schematic of scramjet
舵翼效率是高超声速飞行器飞行控制的重要问题。在动压较小的高度做高超声速飞行,依靠传统的舵面可能存在效率低、反应时间长等困难。 利用姿控发动机产生侧向喷流,具有高效率和响应快的特点,是高空姿态控制的有效方法。但侧喷流与外部来流会互相干扰,这种干扰会引起弓形激波、分离激波、桶形激波、马赫盘等激波结构以及流动分离(如图9所示)。弓形激波虽然由局部喷流引起,但其激波面可能会延生到喷管所在部位的另一侧,改变物体表面的压力分布,从而产生干扰气动力。干扰气动力与喷管设计推力叠加在一起,形成实际的侧向力。这种干扰有可能使侧向静推力放大或缩小,甚至导致推力反向而使喷流失效。研究表明,来流马赫数、喷流马赫数、喷流压力比、喷管构型、喷射角度、飞行攻角等因素均会对喷流侧向力带来影响[15-16],因此需要进行合理的设计。

图9 姿控发动机侧喷流场示意图[16]Fig.9 Flow phenomena for reaction control system16]
2 典型流动现象定性分析
由于再入类飞行器高超声速流动特点已经比较清楚,因此这里主要考虑巡航类高超声速飞行器典型流动现象,虽然某些现象在再入类中也会出现。
2.1 激波现象及其作用再分析
如图 10所示,高超声速飞行器各大部件和局部小物体(即非流线型构件或局部突起物)上均可能产生激波。如果采用超燃冲压发动机,那么发动机内还有激波(如图8所示,其中进气道内经过激波压缩、隔离段内通过激波调制上下游压力关系、燃烧室内还有射流和凹腔等引起的激波)。激波是高速流动中的常见结构,激波上下游流动参数满足清晰的激波关系式,但对其作用存在误解。最常见的误解就是认为激波引起激波阻力,因此总是有害的。以下是一些常识以外的有意义的结论。

图10 各种突起物导致流场加减速引起的激波[7]Fig.10 Shocks waves due to obstacles [7]
如果没有激波,那么驻点压力将大到结构无法承受。以驻点压力系数Cp0衡量, 假如高超声速来流不经过激波,而是等熵地滞止到驻点,那么,对应的“理想”驻点压力系数表达式为[17]
(3)
事实上,驻点前必然有一道脱体激波,由于激波的减压作用,使得实际驻点压力系数为
(4)
图11给出了理想驻点压力系数和实际驻点压力系数随马赫数的变化关系。由图可见,如果没有脱体激波,那么随着马赫数的增加,驻点压力系数会无限放大。正是由于激波的作用,才使得驻点压力系数小于1.84。

图11 驻点压力系数随马赫数的变化Fig.11 Stagnation pressure coefficient as a function of Mach number
激波对升阻力的贡献,与激波相对于物体的位置有关。图12给出了菱形翼自身产生的激波以及一道外来激波打在物面的情况。显然,激波只有作用在物体的迎风面,才会引起作用在该物体上的阻力。如果作用在背风面,则引起推力。对于升力以及对于膨胀波,也可以做类似分析。因此,既可以通过用针尖或射流破坏迎风面的激波减阻[12,18-19],也似乎可以通过在背风面产生激波增加推力。

图12 自身激波(上)与外来激波(下)的作用Fig.12 Self-induced shock waves (upper) and incident shock waves (below)
如图13所示,楔形压缩在O点引起的激波,可以在进气道内来回反射(图中A、B、G为激波反射点), 形成反射激波进一步在进气道内传播[20]。附录A对激波反射的类型、条件和激波隔开的各区流动参数的计算进行了描述。其中一个很重要现象就是存在正规反射与马赫反射两种类型的反射(如G点的反射)。正规反射由入射激波和反射激波构成,反射激波下游依然为均匀的超声速流。马赫反射由入射激波、反射激波和马赫杆(强激波)构成。马赫反射下游区域由滑移线下的亚声速区和滑移线上的超声速区(特殊条件下也可能是亚声速)构成,因此下游流动参数不再均匀,引起压力畸变,故应尽量避免。
另外一个重要性质是,存在这样的来流条件,两组反射均可能出现(见附录A有关双解区描述)。具体出现何种反射,与进入这一来流条件的历史有关,这就是所谓的滞后回线现象[21]。另外,两种类型还可能相互转换[22]。
双解区的存在以及滞后回线现象对吸气式发动机设计有重要意义,因为如果飞行条件正好导致双解区出现,那么激波反射类型与姿态变化历史有关。某些临近空间高超声速飞行器,如猎鹰计划HCV,Hypersoar采用低能耗低阻力的跳跃式飞行方式,飞行高度跨度大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由此导致的变来流条件改变了进气道内激波反射特性。 由于不同反射类型对应的压增和流场品质不一样,发动机性能也不一样,因此发动机设计时需要力求避免双解区的出现,否则经历不同姿态变化历史的巡航状态,发动机性能不一样。


图13 进气道内的激波反射Fig.13 Shock reflection in an inlet
还有一类重要的激波现象就是激波之间相交与干扰(如图14所示)。高超声速飞行器的各个部件均可能产生激波,激波之间相交会引起复杂的激波干扰结构[23-25](见附录A)。尤其当激波打在物面上时,会出现激波边界层干扰或其他干扰现象,引起局部热流放大。热流放大原因将在2.5节中介绍。 在3.7节中将用激波干扰的例子说明正确理解激波干扰结构对局部防热的重要性。

图14 激波干扰[24]Fig.14 Shock interaction[24]
激波的形状在应用中也是关注的问题之一。附体激波往往为直线,但脱体激波的形状则比较复杂, 工程上存在拟合公式[26]。激波反射中的马赫杆被证明是一段曲率极小的圆弧[27]。
2.2 高超声速边界层、转捩及湍流
高超声速边界层由于在飞行器本身所处的高度下对应的雷诺数较低(见3.3节),并且由于气动加热,降低了等效雷诺数,因此有较大的厚度,这导致其对无黏流区的作用不是简单的修正,而是有强烈的干扰。这种干扰导致的气动参数变化与下面定义的干扰因子有关:

(5)
式中:C为Chapman-Rubensen常数;Rex为当地雷诺数。沿边界层流向的压力分布是干扰因子的函数,而低速流动则近似为常数。边界层的增厚导致在附近有激波时,激波边界层干扰效应(见2.3节)更强。
阻力主要由摩阻和波阻两部分组成。等效雷诺数的减小导致摩阻比重增加。针对平板的波阻、摩阻平衡临界线和相对大小区域划分,如图15所示(文献来源以及有关高度-速度图上的其他气动环境,见3.3节进一步介绍)。根据攻角的确定方法分为给定攻角(攻角固定不变)和平衡攻角(攻角由升力与重力平衡得到)两种情况。飞行器若以固定攻角飞行,随着高度的增加或速度的增大,摩阻占总阻力的比重越来越大。若飞行器以平衡攻角飞行,在低空、高速区域摩阻大于波阻,在高空、低速区域波阻大于摩阻,在大部分能够平飞巡航的区域摩阻占总阻力的比重更大。高摩阻是高超声速飞行器升阻比瓶颈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减阻不能简单只考虑如何减少波阻。

图15 波阻与摩阻比随高度-速度的变化(K为翼载)Fig.15 Wave drag and friction drag ratio as a function of altitude-velocity map (K is wing load)
边界层转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转捩位置对壁面换热系数和摩擦系数以及其他边界层特性等均有重要影响。高超声速流动的转捩似乎也遵循低速流动转捩同样的物理机制,可将转捩过程简述为扰动的产生→扰动被边界层感知→流动不稳定与扰动增长→不稳定波的破碎与湍流结构的产生→充分发展湍流。详细介绍参见文献[28]和文献[29]。
1) 扰动的产生。转捩过程起因于物体发出的或者自由来流中的初始扰动(如自由来流的湍流度)的放大与发展。来流湍流度越大越容易转捩,因此处在具有高湍流度的低空大气层飞行器,边界层主要以湍流为主。但是对于高超声速飞行器,飞行高度一般在25 km高度以上,当地平流层环境的湍流度在万分之几以下(见3.3节)。因此飞行器层流段占的比重可能较大(如图16所示),转捩具体位置较为重要。另外由于实际飞行区域湍流度低,地面试验如果要比较好地再现飞行条件,需要采用静音风洞。

图16 某细长飞行器边界层(层流、转捩与湍流)Fig.16 Boundary layer for a slender body (laminar, transition and turbulent)
2) 扰动感知。这些扰动被边界层感知的程度(即扰动被送入边界层内部的程度)与物面的粗糙度、振动特性、钝度和曲率有关,也和来流马赫数等有关。扰动被感知的部分,才能进入下面的稳定性放大。
3) 流动稳定性与扰动放大。被边界层感知后扰动的增长与边界层稳定性有关。边界层稳定性与边界层速度分布有关,从而与来流马赫数、展向与流向曲率、压力梯度和温度等有关。作为边界层不稳定机制,常见的有凹形物面的Gortler不稳定性机制、Tollmien-Schlichiting第一模态和第二模态不稳定机制(后者称Mack不稳定机制)、三维横向流动不稳定机制。不稳定或稳定是边界层的内禀特性。注意,线性稳定性描述的是扰动的指数级增长放大,而非线性不稳定往往描述的是增长率低得多的不稳定性。
4) 破碎与湍流的产生。这些不稳定波在放大到一定程度后会出现一些自组织或相干结构(如发卡涡),并出现结构破碎形成局部湍流斑,破碎过程决定于多种形式的二次不稳定。在出现充分发展湍流前,在一个湍流间歇出现的区域,湍流斑不断增长,以完成层流向湍流的转捩。 这一过程的描述,包括相干结构的重要性及其演化,理论上一直无法做到完备。
5) 湍流边界层。转捩完成后,下游的边界层就是湍流边界层,或者叫充分发展湍流边界层。高超湍流边界层的结构与低速边界层存在相似之处(见3.5节),但由于密度变化和换热,相似解特性不会有低速流动那么明显。
对湍流的产生以及湍流形成后流场的物理认识和定量理论,构成了物理学重大的难题。尤其对于转捩,存在包括雷诺数和马赫数在内的数十个参数影响转捩位置以及转捩区长度。这对实验和模拟提出了挑战(进一步讨论见3.2节)。
另外,对于钝头体,还存在前面提到的钝头体佯谬现象[6]。该现象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既可能存在于飞行试验之中,也可能存在于风洞试验之中,由于没有合理的解释,因此被列为Morkovin未解决问题的清单之中。
作为对转捩复杂性的理解,图17给出了某尖锥转捩雷诺数Retr(即基于转捩点位置的雷诺数)与转捩点边界层外缘马赫数的关系[30]。首先,冷壁比热壁更难转捩(即转捩雷诺数更高),其次地面风洞试验结果给出的转捩雷诺数比飞行试验给出的低(因为地面风洞湍流度高)。

图17 某尖锥转捩雷诺数与马赫数的关系[30]Fig.17 Transition Reynolds number as a function of Mach number for a sharp cone flow[30]
文献[31]将已知的转捩雷诺数结果放在高度-速度图上(如图18所示)。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对于70 km以上的具有稀薄效应的高度,流动对于所有飞行器均为层流。因此,似乎不存在稀薄效应与湍流效应相互干扰的问题。如果单看边界层内的稀薄效应,那么用考虑了可压缩性效应修正的边界层厚度作为定义努森数的尺度,发现只有当基于距离前缘的坐标定义的雷诺数满足时,才可能存在稀薄效应。对于马赫数大于5的高超声速流动,当Rex<1 600时,显然不可能出现转捩。因此,对于高超声速流动问题,基本不可能出现稀薄效应与湍流转捩的干扰。
(6)
对于极高马赫数的情况,湍流边界层除了低速湍流边界层类似问题外,还存在湍流与高温真实气体效应的相互干扰问题。 高超飞行器所在的环境湍流度低,因此高超声速湍流边界层压力脉动主要表现为高频低振幅。但是,在出现激波边界层干扰时,还会引起其他脉动现象(见第2.3节)。

图18 不稳定与转捩临界线[31]Fig.18 Critical edges for instability and transition[31]
2.3 激波边界层干扰、其他干扰与压力脉动
高超声速流动中两类重要结构激波和边界层相交形成的激波边界层干扰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会引起与来流条件密切相关的局部流动形态,产生新的结构(激波、膨胀波和分离涡),引起压力与热流峰值,产生非定常脉动现象,虽然历经了60多年的研究,但定量规律依然需要进一步研究[32-36]。
2.1节介绍的激波在物面上的反射(图8所示的进气道内激波在物面上反射)和激波干扰(图14所示的入射激波/脱体激波干扰)产生激波打在物面上的现象,从边界层厚度的尺度看,都是激波边界层干扰问题。图19给出了另外一些激波边界层干扰产生的情况(主要有一个物体产生的激波与另一个物体的边界层相交;压缩拐角引起的激波与边界层干扰;喷流引起的激波与边界层干扰)[37]。
图20给出了一些典型的激波边界层干扰流动。以入射激波边界层干扰为例,穿越(入射)激波,压力增加,该压增传播到边界层内,导致逆压梯度,引起边界层增厚(甚至出现分离涡)。压增效应减弱后,边界层变薄,从而产生膨胀波、再压缩波。图21给出了有分离泡时壁面一些特征点及压力、摩擦系数和热流沿壁面的分布曲线。其中,I为干扰起始点(即边界层增厚引起的分离激波或压缩波的起始位置),从该点往下压力开始增加,边界层增厚导致摩阻系数下降;S为分离点,当地摩阻系数为0;O点接近涡心位置,压力出现第1个平台值(即经过了分离激波之后的无黏压力);R为再附点(摩阻系数为0),在分离点和再附点之间摩阻系数为负;再附点后的F点气流转平,经过了F点之前再压缩波的压力为第2平台压力,F点边界层最薄,当地摩擦系数和热流达到极大值。即使对于入射激波边界层干扰这一特例,还有一些其他情况(如没有分离泡、入射激波和分离激波出现马赫相交等,详细情况见文献[38])。对于其他情况,也可以做相应的分析,尤其是对于三维问题,舵面或埋入锥等引起的后掠激波与另外机体的边界层干扰,既有二维问题的干扰结构,还有流向结构[34]。对于三维问题,需要大量实验研究才能给出有用的结果,李素循[39]给出了大量有实用价值的数据。

图19 各种部件或射流引起的激波边界层干扰[37]Fig.19 Shock wave boundary layer interaction for obstacles and for jet flow[37]




图20 常见激波边界层干扰(二维)Fig.20 Various types of shock wave boundary layer interaction (two-dimensional)

图21 入射激波边界层干扰典型位置与压力、摩擦系数和热流沿壁面的分布示意图Fig.21 Schematic of typical points for incident shock wave/boundary layer interaction, pressure, friction coefficient and heat flux distribution
非定常现象是激波边界层干扰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反射激波左右移动、分离泡变大变小等复杂非定常现象。湍流边界层存在高频(10 kHz量级以上)低振幅脉动,激波位置的振动是低频(1 kHz量级以下)高振幅(接近边界层厚度或凸起物前缘半径)脉动、分离泡往往是高频高振幅脉动。这种脉动差异和联系,尤其是定量描述,目前仍然是空气动力学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36,40]。
高超声速飞行器在20~40 km高度范围内的压力脉动现象会导致飞行器表面出现局部大载荷,诱导抖振响应导致结构破坏,缩短飞行器使用寿命;同时脉动压力会造成严重的气动噪声。
首先,湍流流动脉动速度与平均流场的相互作用会导致脉动压力,湍流脉动压力大小与来流动压成正比,其特征是高频(102~104kHz)低幅值(0.001量级)。其次,飞行器表面转折处由于激波或膨胀波与边界层的干扰(细微的非定常结构在3.4节中有描述),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边界层分离。分离涡内的流动一般都有脉动,分离点和再附点具有不稳定性,这些均会导致脉动压力[41]。分离流脉动的特点是中频(1~102kHz)中振幅(0.001~0.01)。同时,对于激波边界层干扰,分离反作用于激波导致激波自己振荡,造成强烈低频(10~1 000 Hz)高幅值(0.01~0.1)脉动压力[42]。图22(a)给出了高超声速压力脉动的来源以及均方根脉动压力系数。由激波边界层干扰引起的大振幅脉动压力,声压可达到185 dB,且脉动压力频率与一般飞行器蒙皮材料典型频段(100~500 Hz)接近,因此这类脉动压力危害十分严重。
吸气式发动机在助推阶段,因进气道出口堵塞,会因压力波的传播在细长的空腔内形成压力脉动现象。激波和膨胀波反复在尾部壁面和头部开口处反射,进气道中气体的状态参数存在振荡现象,作用于后体上的压力在总压上下做大幅振荡,出现瞬时压力峰值,对结构强度带来不利影响。图22(b)给出了进气道入口压力和速度随时间的变化,图中:ux为轴向速度。


图22 压力脉动来源及均方根脉动压力系数[44]和吸气式进气道入口压力速度脉动现象[43]Fig.22 Source of pressure fluctuation, root mean square of pressure fluctuations[44] and pressure, velocity fluctuation for inlet of air-breathing engine[43]
吸气式发动机燃烧室的稳定凹腔,侧壁姿控发动机在熄火时,均构成凹腔流动问题,可能存在空腔共鸣现象,共鸣频率以及声压可以由Rossiter模型预测[45]。 例如,第n阶模态的频率为
(7)
式中:C1和C2为两个常数;W为凹腔的长度。
凹腔上游前缘因边界层结束,脱落形成的自由剪切层Kelvin-Helmholtz不稳定,产生一系列涡。这些涡以一定速度向下游运动并与凹腔后壁碰撞产生扰动波,扰动波以声速向上游传播,在空腔前缘处扰动波激发新的涡脱落,形成循环,导致共鸣与压力脉动。凹腔振荡引起的压力脉动可以高达170dB。所以振荡频率必须和结构共振频率错开,否则会引起结构破坏,另外凹腔流动还会导致附加阻力和力矩。
2.4 多波系、小扰动波的大影响
强可压缩性、强激波和厚边界层等,表面上只有这些才是高超声速流动的主要结构。实际上强度弱得多的小扰动波充斥在高超声速流场中,有时其作用非常大。
图23给出了激波边界层干扰示意图[34]。远端的反射激波和再附激波,在边界层附近看,则是一系列小扰动压缩波,大尺度分离涡周围还存在小尺度旋涡结构,多波系和多旋涡相互干扰,构成了2.3节中描述的3种不同频率的脉动现象,其机制依然是目前争论的焦点[36]。
在研究马赫反射时,早期忽略了小扰动波的存在。如图24所示,三叉点发出的滑移线(实际上也是一条流线)与反射平面存在夹角,因此在马赫杆下游,压力下降。这种压力下降,在滑移线上侧,需要通过产生小扰动膨胀波来平衡。考虑了这种小扰动膨胀波的影响后,马赫杆的高度预测才变得准确,否则误差超过50%。可见,表面上看不见的小扰动波,在与大尺度结构干扰时,会引起很大的尺度变化。

图23 激波边界层干扰引起的压力脉动[34]Fig.23 Pressure fluctuation due to shock wave boundary layer interaction [34]

图24 激波反射中马赫波的影响[46]Fig.24 Mach waves in shock reflection[46]
多波系结构在吸气式发动机的进气道流场中尤为典型,如图25所示。激波在多处与其他激波相交并与边界层干扰,因此多波系效应将非常复杂,对性能预测和设计构成挑战。
如果进一步将各处的流动现象提取出来,如图26所示,存在:激波与膨胀波、激波相交、激波反射、激波干扰、喷流干扰、激波边界层干扰、超声速混合层和凹腔共鸣等,因此吸气式发动机流场中几乎存在所有的高超声速流动特殊现象。

图25 吸气式发动机进气道复杂多波系结构Fig.25 Multiple waves for air-breathing engine

图26 吸气式发动机多种典型结构共存Fig.26 Multiple flow structure of air-breathing engine
2.5 气动加热:基本加热与加热放大
气动加热是气流减速、动能转换为热能的过程。对于来流动能较高的高超声速流动,气动加热尤其严重。气动加热一方面加热了空气本身,使得黏性系数增加、密度减小,在温度足够高的情况下,还会改变比热比和化学成分等。另一方面, 将热传入并加热物体,严重时会引起热气弹并烧坏物体,因此需要采用热防护措施。对气动加热的正确归类与理解,有利于气动加热的预测、防护和利用。
如图27所示,气动加热可恰当地分为基本加热[47]与干扰放大(或者二次加热)两个方面。基本气动加热包括激波加热和物面摩擦加热两个方面。二者均会加热空气本身,但激波加热的热流量主要被流动带走,摩擦加热的重要部分会传入物体。 传入物体的热量是有害的,前面提到的Allen的钝头体理论正是利用了钝头体产生的激波的预先加热能被带走这一事实,减少了摩擦加热量。除边界层摩擦加热,驻点加热也可以看成摩擦加热,只是驻点流动的摩擦是法向的,而边界层流动的摩擦是切向的,二者遵循相似的规律。


图27 基本气动加热[47]和局部干扰导致热流放大Fig.27 Basic aerodynamic heating[47] and amplification of heating due to shock interaction
边界层摩擦加热由于近似满足雷诺比拟(见3.5节的进一步介绍),因此与摩擦系数满足相似的规律:

(8)
式中:Cf为摩擦系数;St为反映加热量的Stanton数:Pr为普朗特数。驻点加热一方面满足与边界层相似的规律(驻点西门子相似解),另一方面受脱体激波减速的影响,加热量最终反比于前缘曲率半径的均方根[48]:
(9)
式中:下标s表示驻点。
除基本加热外,入射激波等与前缘脱体激波干扰、激波边界层干扰,引起的次生结构和穿越次生结构压力增加,将以温度梯度增加的形式反映在局部热流增加上,导致峰值热流现象(如图28所示[23-24, 49])。这种干扰可用压力比拟来描述[49]
(10)
式中:p3/p1为压力放大系数,即干扰导致的局部压力比(干扰点后的压力与干扰点前的压力比),可近似用无黏激波干扰与反射理论求解。另一个量qref为无干扰情况下,相同位置和相同来流条件对应的热流。激波干扰气动热的特点是影响范围小但局部峰值热流大,最大热流点的位置不断变化,这给热防护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美国的高超声速试验机X-15-2在30 km高度做马赫数为6.7的飞行试验时,外挂架和外挂发动机的激波发生干扰,引起严重的损毁事故,导致外挂架融化断裂,机身下方和发动机上的热防护材料严重烧蚀。

图28 激波边界层干扰[49]和激波/激波干扰[24]引起的局部峰值热流Fig.28 Peak heating due to shock wave boundary layer interaction[49] and shock/shock interaction [24]
图29给出了某高超声速飞行器一些典型位置的热流量级(热流值依据笔者团队经验,只给出具有参考意义的大致量级)。其中进气道前缘在有激波干扰情况下,峰值热流最大。

图29 不同部位的峰值热流示意图Fig.29 Schematic of peak heating at various positions
2.6 高温真实气体效应及低密度稀薄效应
为了得到不同马赫数下的高温真实气体效应,图30给出了飞行器在大气中以不同马赫数飞行时,加热的空气所具备的温度按理想状态计算(完全气体,无化学反应)和按实际状态计算,即考虑了空气在对应条件所发生的振动能激发和化学反应得到的激波后温度(与绝热壁恢复温度接近)。图中:实线为考虑高温真实气体效应影响的温度曲线;点划线为激波后的理想气体温度曲线;虚线为绝热壁理想气体恢复温度曲线。可见当马赫数介于3~8时,需要考虑振动能激发带来的气体比热比变化,在8~25之间,需要考虑离解等吸热反应。正是这些吸热反应,导致了实际温度低于理想温度。Ma>25以后,就得考虑电离和辐射了(这种马赫数可能只存在于再入飞行器问题中)。

图30 高温真实气体效应图Fig.30 High-temperature real gas effect
因此,在高马赫数下,出现如下效应:
1) 空气被加热。
2) 由于空气被加热,依据温度大小,会出现振动能激化、离解反应、复合反应和电离、辐射等。
3) 由于这些化学反应主要为吸热反应(辐射降低温度的效果也类似于吸热),因此,空气的实
际温度比理想加热要小。
4) 化学反应改变了组元构成(如图31所示)和气体特性,如气体常数R、定容比热cv、比热比γ和内能e等(如图32所示)。

图31 空气组元构成随温度的变化(一个大气压下)Fig.31 Composition of chemical species for air as a function of temperature ( 1 atm)




图32 气体特性随温度的变化(一个大气压下)

当飞行高度处在70 km以上时,稀薄效应会导致流场结构显著变化。图33(a)给出了某钝体马赫数云图。由图可见,随着稀薄程度增加(Kn增加), 与分子平均自由程成正比的激波厚度增加,激波脱体距离也增加。图33(b)给出了不同马赫数下马赫反射中马赫杆高度随Kn的变化。由图可见,随着稀薄程度增加,马赫杆高度线性下降。


图33 稀薄效应影响[52]Fig.33 Rarefied effect[52]
3 如何解决实际问题
这里从7个方面论述如何解决基础与应用中的实际问题。
3.1 因果关系的重要性,rP(F)-关联度
我们所关心的一些流动现象或者气动参数(以P表示),与另外一些现象或者研究手段(以F表示)存在因果关系,可用r-rP(F)来衡量,rP(F)为关联度参数。如果rP(F)→0,那么P和F之间毫无联系。如果rP(F)→1,那么二者之间有重要的因果关系。一般情况下,0 图34 前缘峰值热流关联度示意图Fig.34 Schematic of influence factors for nose aerodynamic heating 同理,在采用数值方法计算流场时,如果把湍流转捩模型的选取看成P,那么就不能依据算得的驻点压力正确来判断湍流转捩模型多么合理,因为此时rP(F)→0,即驻点压力与转捩模型毫无联系。反过来,如果把边界层看成F,把摩擦阻力看成P,那么rP(F)→1,即摩擦阻力决定于边界层性质。为了正确得到摩擦阻力,就得准确计算边界层。对于高超声速流动问题,在解决问题之前,或者研究P之前,正确找出满足rP(F)>0的那些F,是有效解决问题的关键。例如,改进了数值计算方法中的黏性项处理精度,就不能只用计算得到的压力分布来验证结果的合理性,必须以摩擦系数分布或热流分布来验证。针对所关心的气动特性,可以构造一个类似于图34所示的rP(F)图,或类似于表1的rP(F)关联度表,对指导学术研究与工程应用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2 相似参数问题 表1 部分气动参数的rP(F)关联度表 除数值模拟外(数值模拟也存在模型不确定性和精度不够等问题),任何地面模拟设备,包括常见的传统风洞、激波加热风洞、激波管、电弧加热风洞和自由飞弹射装置,都极难再现所有这些真实条件(即上面列举的11个参数)。因此,一种设备或一组实验往往只是研究高超声速气动的某个方面,如气动力、力矩、表面压力分布、热分布、激波/边界层干扰特性和进气道性能等。 除此之外,还需要考虑:①模型尺寸;②测量时间;③数据类型;④来流均匀度;⑤来流噪声;⑥来流清洁度;⑦来流稳定度。 如果需要模拟燃烧,还需要考虑Damköhler数。因此,气动问题的地面模拟是一门艺术,工程师需要知道哪些参数决定哪些性能,设计者需要用多种手段完成设计计划所需要了解的全部性能[4-5]。 总而言之,存在包括雷诺数和马赫数在内的数十个参数影响转捩位置以及转捩区长度。地面风洞试验存在湍流度较高,无法再现高空低湍流度环境问题。静音风洞的出现可以部分解决这一问题,但可能存在吹风时间过短,其他参数无法同时考虑等问题。 试图采用无量纲参数来总结或表述规律时,应该区分无量纲参数并不一定是相似参数。只有基于物理规律导出某些气动参数是某无量纲参数的确切函数时,该无量纲参数才可以看成相似参数。高超声速流动中常见的相似参数包括马赫数、雷诺数、干扰因子和努森数,但对于某具体流动现象,只有其中一部分可以看成是相似参数。 高超声速地面模拟包括飞行器外流和发动机内流模拟,涉及气动力、气动热和燃烧等复杂物理化学过程,要精确模拟所有过程非常困难。目前,主要模拟参数包括马赫数、雷诺数、Damköhler数、总温和总压、和飞行状态相同的纯净空气组分、实验时间及模型尺度。对气动力和气动热而言,正确模拟雷诺数才能正确地模拟边界层转捩。正确模拟Damköhler数才能正确模拟燃烧和空气离解和电离(Ma<7可忽略)基元反应,两组元和三组元基元反应的模拟相似准则是不同的。燃烧和空气离解模拟对来流组分和实验时间也是有要求的。对5 3.3 飞行环境 高超声速飞行器对飞行环境依赖很大,所处高度范围密度、压力和湍流度低(如图35所示),会出现许多临界状态(如航空航天的交界、层流湍流分界、连续稀薄分界、摩阻波阻比重分界等)。进行气动分析时,需要在图35、图36和图37所示高度-速度图上分辨相似参数范围、应用模式和流动类型(流转捩与稀薄效应、波系相互作用、非定常脉动、连续稀薄耦合)。图38则给出了一些典型临界高度。详细介绍和更多的高度-速度图可参考文献[53]和文献[54]。3.6节介绍的分析工具HAFF具备查看多种气动环境的功能。在进行一项具体气动分析之前,了解其飞行高度和速度,在高度-速度图上先期了解相似参数所处的范围以及有哪些主要流动现象,对正确开展分析和避免错误选用物理模型非常重要。 图35 高度-速度图上的大气参数分布与相似参数Fig.35 Air parameters and similarity parameters on altitude-velocity map 图36 航空、航天采用的空间划分Fig.36 Critical lines defining edges of space 图37 高度-速度图上的流动现象Fig.37 Flow phenomena on velocity-altitude map 图38 同高度的典型临界现象示意图Fig.38 Schematic of critical flow phenomena along altitude direction 3.4 正确识别、预测和考虑激波等结构的重要性 由于激波、膨胀波和其他小扰动波的重要性,在流场分析、计算和性能预测方面,需要对它们正确识别、捕获和考虑其作用。 激波与其他结构干扰以及激波在物面上的反射,会引起不同于膨胀波和滑移线的作用。因此,在复杂的空间流场结构(比如来自于CFD计算或PIV测量等)中,如何识别它们非常重要。文献[55]对现有识别技术进行了总结,图39给出了吸气时发动机中空间流场典型结构的识别结果。这种识别技术对高超声速流动这类具有复杂空间流场的分析十分重要(3.6节介绍的商业软件Apost提供这种功能)。例如,依据一个粗网格的CFD计算结果,如果能首先识别主要激波结构,就可能依据理论判断当地是否会发生(哪类)激波边界层干扰现象,从而引导进一步合理加密网格。 虽然进气道之类的流场多波系结构很复杂,CFD计算很难精细地捕获详细的多波系结构,但各种波及其相互干扰均满足已知的数学关系式,因此可以直接解析求解空间流场结构[56]。图40给出了平面进气道超声速流场解析分析工具预测的某进气道多波系结构。这种技术可以给出解析解的空间分布,需要的时间不到一秒,对进气道性能快速分析和评估有重要价值。另外,也可以添加边界层厚度修正,以及激波边界层干扰带来的修正(分离涡长度有工程估算公式,第1个平台压力用自由干扰流理论估算)。 图39 空间流场结构的智能识别Fig.39 Autonomous identification of various flow structures 图40 多波系结构的解析求解Fig.40 Analytical solution for multiple waves 人们在使用CFD和实验等研究激波边界层干扰带来的气动热问题时,往往得出精度很难满足要求的结论。其实使用工程估算方法往往能给出较合理的结果,在预估结果和正确理解当地流场结构(如分离涡大小、激波边界层干扰类型、当地边界层厚度)后,再通过适当网格加密和物理模型选取,往往能得出正确的数值模拟结果。在3.5节中,介绍了压力比拟,即热流峰值与无黏激波反射导致的压力增加比值是一个简单的指数关系。无黏反射压比预测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压力比拟也非常简练,因此这种方式可以把一个表面上复杂的问题变得十分简单。 3.5 湍流问题的模拟 转捩预测、转捩控制以及湍流模拟是解决工程应用问题的关键。高超声速飞行环境很难在地面模拟试验中再现(见3.2节),因此湍流预测模型的建立与校验,需要用到大量的试飞数据。这些数据大多是不公开的。 转捩预测问题:除前面介绍的钝头体佯谬,以及激波与层流边界层干扰导致提前转捩外,边界层的自然转捩预测也非常困难。文献[29]对一些公开的数据进行了详细描述,并介绍了数据与一些转捩预测模型(转捩预测手段主要有eN方法、抛物化稳定性分析和直接数值模拟等)的对比结果。其中一个对比见图17。现有湍流转捩模型很难不加校验地直接用到任何一个高超声速飞行器型号中。如何构造地面模拟设备(如静音风洞、精细测量设备),再现影响转捩位置的主要因素,是地面模拟试验面临的挑战,毕竟高空试飞代价高昂。反过来,如果能通过添加人为扰动,强制提前转捩,则可避免转捩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 湍流边界层特性与模拟:高超声速湍流边界层特性的预测,与低速流动相比,多出了一个特殊因素:气动加热导致温度场与速度场存在强烈耦合。二者是否存在雷诺相似,是基础研究和应用所关注的问题。目前针对马赫数一直到6的流动,人们已经得到了经过验证的普适雷诺比拟[57]。高超声速条件下的湍流边界层的平均速度型(包括混合长度、对数律与卡门常数)、雷诺应力和湍流统计特性也是工程应用关注的重要问题,通过某种变换,可以获得一些与马赫数无关的平均流特性[58]。这些结果目前只对马赫数不超过6的问题进行了验证, 对马赫数更高的流动存在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除了以上对湍流边界层的经典型描述外,高超声速湍流数值模拟(包括RANS, LES, DNS)对具有较复杂湍流边界层结构、混合层、激波边界层干扰区、凹腔流动等也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 基于稳定性理论的转捩模型与RANS模型也可以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高超声速流动统一的转捩与湍流预测方法[59]。 湍流模拟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①湍流数值模拟技术的发展与湍流的内禀结构特性研究目前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因此很难得到具有普适意义的湍流模型;②湍流模型的应用与数值计算技术是分不开的,因此对于绝大多数应用,很难区分湍流模型的误差、数值计算方法的误差和使用过程中的随机性(如网格不恰当加密、时间步长选取不正确及边界条件不恰当等)带来的误差。 早期湍流研究产生了混合长度概念、对数律、卡门常数和标度律等具有深远意义的简练结果(这些结果可以以代数模型形式用在工程中,看成湍流模拟第一阶段)。后来,人们对流体力学基本方程进行了某种形式的平均和脉动量模拟(如RANS、LES),但由于脉动量的模拟很难做到完全建立在流体物理上,因此湍流模拟经历了一个方法越来越分散、模型越来越复杂、程序实现越来越繁琐、数据处理越来越困难的阶段(湍流模型第二阶段)。近期,人们试图回溯到对早期湍流和流体力学内禀性质或者普适性质的重视,将这些特性或基于特性的模型(如雷诺应力模型和湍流热传导模型)逐步作为约束,添加到诸如大涡模拟技术中,形成约束性大涡模拟方法[60],这可以看成湍流模型第三阶段的开始。 3.6 气动力、气动热和压力脉动的快速估算 数值模拟包括外型适应性改造、网格生成、条件正确设置、物理模型选取、数值计算、结果后处理与结果验证等7个方面。这里无法全面涉及这些问题,但针对高超声速流动,有3个典型问题需要强调:①激波等多波系结构的正确捕获;②当有高温或低密度真实气体效应时,连续流场计算与具有刚性的化学反应模型或与稀薄流计算方法相结合;③整体流场与具有典型流动现象的局部流场的协同数值模拟。 首先,激波的正确与自动捕获,构成了现代计算流体力学方法研究的核心。这点对于高超声速流动尤其重要,因为前面已经看到,激波是高超声速流动中最典型、最丰富多彩甚至数目最多的流动结构。 高超声速流动中激波的一大特点是,除了非常强的激波,激波边界层干扰和高超混合层等也会导致一些非常弱的激波。因此,高超声速流动计算技术需要考虑发展既可以捕获强激波又可以以某种形式捕获弱激波的方法。其次,对于高超声速流动,空气的化学反应导致时间上的刚性,因此,对于像非平衡流动的计算,需要对化学反应模型的计算与流场计算进行有机耦合。如果飞行高度足够高,可能在某些区域需要进行连续流稀薄流耦合计算。最后,高超宏观流场除涉及大尺度激波和厚的边界层外, 还涉及局部激波相交、局部激波边界层干扰、射流与主流干扰等尺度较小但依然可以看成宏观流场的结构。对于局部典型热流之类的模拟,首先需要构造整体网格,进行计算,得到诸如入射激波等信息。确定干扰位置后,进一步需要将局部流场挖出,围绕局部流场构造小的计算区域和加密网格,以整体流场计算结果作为局部流场计算的边界条件。这种整体-局部计算方法对用有限的计算条件解决复杂的工程问题非常有效。 商业CFD软件被大量用在高超声速流动数值模拟中。人们常常询问各种软件的效果。其实商业软件的使用与使用者对问题的物理本质理解有很大关系。正确理解流动现象,在有典型流动结构的地方恰当加密网格、恰当选取物理模型等,往往能得到正确的结果。高超声速问题应用的空域高,不同高度存在不同的流动类别和相应的模拟方法,如图41所示。 图41 高超声速飞行区域的流动状态与数值模拟方法Fig.41 Flow types and methods of numerical modeling for hypersonic flow 如图42所示,目前,针对连续流区的CFD商业软件较多,如Ansys-CFX、Fastran、Fluent、CFD++等。针对稀薄流的DSMC软件有ESI-RARE。这些软件均具备并行计算功能。由于高超声速流动满足引言所说的存在诸如牛顿方法的快速理论,因此发展了基于快速估算的高超声速流动气动力、气动热和高超压力脉动软件(如ESI-HAFF)。后处理对于高超声速流动提取激波等信息非常重要。基于Tecplot、Ensight和CFD-Post等进行后处理,识别结构对使用者要求高。Apost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问题,可以自动识别激波、滑移线和膨胀波等典型结构。 图42 商业软件构成图Fig.42 Commercial code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基于牛顿类方法的高超声速气动力气动热以及用桥函数法将连续流区与自由分子流区的气动力气动热联系起来,对于卫星碎片再入等模拟十分有效[61]。 高超声速压力脉动问题很难通过求解气动声学问题来获得,因为局部效应太强,时间尺度很小。 目前最有效的办法是依据实验结果形成的工程估算公式来预测压力脉动[41-44]。 具体做法是,由牛顿类方法或CFD之类的给出指定外形的无黏平均流场(而不是脉动流场)计算结果。 在边界层、膨胀折转点、压缩折转点、舵翼干扰处等采用工程估算公式。这些公式直接将声压、功率谱和相关函数表述为当地马赫数的显式关系式,ESI-HAFF正是基于这种方式给出压力脉动的。 3.7 理论、数值计算和试验的有机结合 理论分析、数值计算和试验的有机结合表面上看是一个谁都认为重要且不值得在这里强调的问题,但一般情况下很难真正做到有效利用这种有机结合。这里依据笔者经验,举一个例子,表明三者有机结合会带来多大益处:第一,大幅度降低解决问题的成本;第二,对设计有重要价值。 图43给出了某类高超声速飞行器裙部示意图。裙部激波与前体激波在T处相交,除形成合并激波外,工程单位用模型试验得到的纹影中,观察到从T点产生另外一道波打在物面上。依据纹影图,工程单位特别关注打在物面上波的性质。因为,如果这道波是激波,那么会在物面反射点P上产生峰值热流。随着飞行姿态的改变,反射点位置也会改变,因此会对热防护设计带来巨大困难。 图43 局部激波与前体激波干扰形成的反射激波或膨胀波Fig.43 Interaction of a local shock wave with a forebody shock wave, forming reflected shock wave or an expansion wave 经过工程单位与理论分析工作者的结合,了解到前体激波与裙部激波相交这种类型的相交,除产生合并激波外,另一道波既可能是激波,也可能是膨胀波。具体属于哪一种,用无攻角时二维简化的激波干扰理论[17](具体计算方法见附录A)就可以得出结论。后来,针对工程单位使用的条件范围,发现另外一道波属于膨胀波,而不是激波。这样,打在物面上就不会产生热流放大。二维理论分析无法考虑到有攻角的情况。为此,补充了三维数值计算,最终发现在所考虑的条件范围内,针对所有攻角,只有膨胀波这种情况。这样,就不需要进行热防护考虑。 这一例子既说明了理论、数值计算和试验相结合的一种流程,也说明了对解决工程问题有多么重要。在结合得紧密的情况下,可以避免大量时间与经费的浪费,而且能得到正确结论。 高超声速飞行器飞行的区域具有低密度和低湍流度等环境特点。本文对高超声速飞行器尤其是巡航类飞行器高超声速流动的各种问题及其解决方法进行了回顾与综述,并对激波的作用和其他一些问题给出了一些笔者个人的理解,尤其强调了因果关系的重要性,并给出了因果关系示意图。以下是一些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针对弹道模式积累的高超声速流动知识,可以部分应用于巡航模式,但巡航模式面临的问题更多,尤其高升阻比要求是弹道模式不需要考虑的。如何提高巡航模式的升阻比,降低吸气发动机本身的阻力,需要投入更多的研究。 由于影响高超声速流动的因素很多(见3.2节),因此试验与试飞测量对获得一些定量数据(如转捩位置、热流峰值、压力脉动信息)非常关键。对于具体飞行器,许多有价值的数据不会公开,因此,建立自己的试验与试飞系统非常关键。这类定量问题数据(库)的获取更多属于内部研究。 激波边界层干扰、热流峰值问题、非定常现象和转捩等物理问题涉及到的是基础研究层面,基础研究形成的理论作为工程估算公式,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这方面的代表性工作有Wang等[12]的稀薄效应对局部气动热的解析理论研究,但整体上国内研究人员重视不够,尤其对马赫数高于7的情况研究不足。 湍流问题对高超声速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湍流中涉及增长与耗散现象,可能与其他增长耗散现象一样,存在一些更本质的规律,见附录B。 [1] Oswatitsch K. Similarity laws for hypersonic flow[J].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50, 2: 249-264. [2] Kliche D, Mundt C H, Hirschel E H. The hypersonic Mach number independence principle in the case of viscous flow[J]. Shock Waves, 2011, 21(4): 307-314. [3] Anderson J D. Hypersonic and high temperature gas dynamics[M].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89. [4] Bertin J J, Cummings R M. Fifty years of hypersonics: where we’ve been, where we’re going[J]. Progress in Aerospace Sciences, 2003, 39(6-7): 511-536. [5] Bertin J J, Cummings R M. Critical hypersonic aerothermodynamic phenomena[J]. Annual Review of Fluid Mechanics, 2006, 38: 129-157. [6] Reshotko E, Tumin A. The blunt body paradox—a case for transient growth[M]∥Fasel H F, Saric W S. Laminar-turbulent transition. Heidelberg: Springer, 2000: 403-408. [7] Hirschel E H, Weiland C. Selected aerothermodynamic design problems of hypersonic flight vehicles[M]. 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 2009. [8] Kuchemann D. The aerodynamic design of aircraft: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the current aerodynamic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guide to the solution of aircraft design problems[M].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78. [9] Corda S, Anderson J. Viscous optimized waveriders designed from axisymmetric flow fields, AIAA-1988-0369[R]. Reston: AIAA, 1998. [10] Stollery J L. Viscous interaction effects and re-entry aerothermodynamics: theory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M]∥Aerodynamic problems of hypersonic vehicles. 1972, 42: 191-1028. [11] Nonweiller T R F. Aerodynamic problems of manned space vehicles[J]. Journal of the Royal Aeronautical Society, 1959, 63(4): 521-528. [12] Bushnell D A. Shock wave drag reduction[J]. Annual Review of Fluid Mechanics, 2004, 36: 81-96. [13] Xu Y Z, Xu Z Q, Li S G, et al. A hypersonic lift mechanism with decoupled lift and drag surfaces[J]. Science China Physics, Mechanics and Astronomy, 2013, 56(5): 981-988. [14] Lockwood M K, Petley D H, Martin J G, et al. Airbreathing hypersonic vehicle design and analysis methods and interactions[J]. Progress in Aerospace Sciences, 1999, 35(1): 1-32. [15] Brandeis J, Gill J.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side-jet steering for supersonic and hypersonic missiles[J]. Journal of Spacecraft and Rockets, 1996, 33(3): 346-352. [16] Gulhan A, Schutte G, Stahl B. Experimental study on aerothermal heating caused by jet-hypersonic crossflow interaction[J]. Journal of Spacecraft and Rockets, 2008, 45(5): 891-899. [17] Tong B G, Kong X Y, Deng G H. Gasdynamics[M]. Beijing: High Education Press, 1989 (in Chinese). 童秉纲, 孔祥言, 邓国华. 气体动力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 [18] Josyula E, Pinney M, Blake W B. Applications of a counterflow drag reduction technique in high speed systems, AIAA-2001-2437[R]. Reston: AIAA, 2001. [19] Bracken R M, Hartley C S, Myrabo L N. Experimental and computational parametric drag study of an ‘airspike’ in hypersonic flow, AIAA-2002-3784[R]. Reston: AIAA, 2002. [20] Ben-dor G. Shock wave reflection phenomena[M]. Israel: Springer, 2007. [21] Ben-dor G, Ivanov M, Vasiliev E I, et al. Hysteresis processes in the regular reflection ↔ Mach reflection transition in steady flows[J]. Progress in Aerospace Science, 2002, 38(4-5): 347-387. [22] Li S G, Gao B, Wu Z N. Time history of regular to Mach reflection transition in steady supersonic flow[J]. 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 2011, 682: 160-184. [23] Edney B. Anomalous heat transfer and pressure distributions on blunt bodies at hypersonic speeds in the presence of an impinging shock, No. FFA-115[R]. 1968. [24] Hans F D, Keyes J W. Shock interference heating in hypersonic flows[J]. AIAA Journal, 1972, 10(11): 1441-1447. [25] Gaitonde D, Shang J S. On the structure of an unsteady type Ⅳ interaction at Mach 8[J]. Computer & Fluids, 1995, 24(4): 469-485. [26] George E K. A method for predicting shock shapes and pressure distributions for a wide variety of blunt bodies at zero angle of attack, NASA TN D4539[R]. Washington, D.C.: NASA, 1968. [27] Tan L H, Ren Y X, Wu Z N. Analytical and numerical study of the near flow field and shape of the Mach stem in steady flows[J]. 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 2006, 546(1): 341-362. [28] Maslov A A. Hypersonic boundary layer transition and control[M]. Netherlands: Springer, 2010. [29] Schneider S P. Flight data for boundary-layer transition at hypersonic and supersonic speeds[J]. Journal of Spacecraft and Rockets, 1999, 36(1): 8-20. [30] Malik M R. Prediction and control of transition in supersonic and hypersonic boundary layers[J]. AIAA Journal, 1989, 27(11): 1487-1493. [31] Hu R F, Wu Z N, Wu Z, et al. Aerodynamic map for soft and hard hypersonic level flight in near space[J]. Acta Mechanica Sinica, 2009, 25(4): 571-575. [32] Babinsky H, Harvey J K. Shock wave-boundary-layer inter-action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33] Gaitonde D V. Progress in shockwave/boundary layer interactions, AIAA-2013-2607[R]. Reston: AIAA, 2013. [34] Panaras A G. Review of the physics of swept-shock/boundary layer interactions[J]. Progress in Aerospace Sciences, 1996, 32(2-3): 173-244. [35] Dolling D S. Fifty years of shock-wave/boundary-layer interaction research: what next?[J]. AIAA Journal, 2001, 39(8): 1517-1531. [36] Clemens N T, Narayanaswamy V. Low-frequency unsteadiness of shock wave/turbulent boundary layer interactions[J]. Annual Review Fluid Mechanics, 2014, 46: 469-492. [37] Zheltovodov A A. Shockwaves/turbulent boundary-layer interactions-fundamental studies and applications, AIAA-1996-1977[R]. Reston: AIAA, 1996. [38] Délery J, Dussauge J P. Some physical aspects of shock wave/boundary layer interactions[J]. Shock Waves, 2009, 19(6): 453-468. [39] Li S X. Complex flow controlled by shock waves and boundary layers[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7 (in Chinese). 李素循. 激波与边界层主导的复杂流动[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40] Humble R A, Scarano F, van Oudheusden B W. Unsteady aspects of an incident shock wave/turbulent boundary layer interaction[J]. 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 2009, 635: 47-74. [41] Chen W F, Zhang Z C, Shi Y Z, et al. The prediction of fluctuating pressure on the surface of reentry vehicles[J]. Journal of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2001, 23(6): 20-23 (in Chinese). 陈伟芳, 张志成, 石于中, 等. 再入体表面脉动压力环境的预测[J]. 国防科技大学学报, 2001, 23(6): 20-23. [42] Plotkin K J, Roberson J E. Prediction of space shuttle fluctuating pressure environments, including rocket plume effects, NASA N73-29885, NASA-CR-124347[R]. Washington, D.C.: NASA, 1973. [43] Yu K H, Trouve A, Daily J W. Low frequency pressure oscillations in a model ramjet combustor[J]. 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 1991, 232: 47-72. [44] Tan C K W, Block P J W. On the tones and pressure oscillations induced by flow over rectangular cavities[J]. 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 1978, 89(2): 373-399. [45] Rossiter J E. Wind-tunnel experiments on the flow over rectangular cavities at subsonic and transonic speeds, RAE Technical Report No. 6403[R]. 1964. [46] Gao B,Wu Z N. A study of the flow structure for Mach reflection in steady supersonic flow[J]. 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 2010, 656: 29-50. [47] van Driest E R. The problem of aerodynamic heating[J].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Review, 1956, 15(10): 26-41. [48] Fay J A, Riddell F R. Theory of stagnation point heat transfer in dissociated air[J]. Journal of the Aeronautical Sciences, 1958, 25(2): 73-85. [49] Hung F T, Barnett D O. Shock wave/boundary layer interference heating analysis, AIAA-1973-0237[R]. Reston: AIAA, 1973. [50] Belouaggadia N, Olivier H, Brun R. Numerical and theoretical study of the shock stand-off distance in non-equilibrium flows[J]. 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 2008, 607: 167-197. [51] Belouaggadia N, Takayama K, Brun R, et al. Shock layers over blunt and conical bodies in hypersonic non-equilibrium flow[J]. Shock Waves, 2010, 20(4): 333-338. [52] Xu S S.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flows for vehicle flying in the transitional regime[D].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2008 (in Chinese). 徐珊姝. 过渡区飞行器流场的数值模拟和计算方法研究[D]. 北京: 清华大学, 2008. [53] Hu R F, Wu Z N, Wu Z, et al. Aerodynamic map for soft and hard hypersonic level flight in near space[J]. Acta Mechanica Sinica, 2009, 25(4): 571-575. [54] Wang X X, Hu R F, Wu Z N. Analysis of special aerodynamic phenomena[J]. Near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9, 1(1): 34-42 (in Chinese). 王晓欣, 胡锐锋, 吴子牛. 临近空间特殊气动问题分析[J]. 临近空间科学与工程, 2009, 1(1): 34-42. [55] Wu Z N, Xu Y Z, Wang W B, et al. Review of shock wave detection method in CFD post-processing[J]. Chinese Journal of Aeronautics, 2013, 26(3): 501-513. [56] Dalle D J, Fotia M L, Driscoll J F. Reduced-order modeling of two-dimensional supersonic flows with applications to scramjet inlets[J]. Journal of Propulsion and Power, 2010, 26(3): 545-555. [57] Zhang Y S, Bi W T, Hussain F, et al. A generalized Reynolds analogy for compressible wall-bounded turbulent flows[J]. 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 2014, 739: 392-420. [58] Zhang Y S, Bi W T, Hussain F, et al. Mach-number-invariant mean-velocity profile of compressible turbulent boundary layers[J].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2012, 109(5): 054502. [59] Fu S, Wang L. RANS modeling of high-speed aerodynamic flow transition with consideration of stability theory[J]. Progress in Aerospace Sciences, 2013, 58: 36-59. [60] Jiang Z, Xiao Z L, Shi Y P, et al. Constrained large-eddy simulation of wall-bounded compressible turbulent flows[J]. Physics of Fluids, 2013, 25(10): 106102. [61] Hu R F, Wu Z N, Qu X, et al. Debris reentry and ablation prediction and ground risk assessment software system[J]. Acta Aeronautica et Astronautica Sinica, 2011, 32(3): 390-399 (in Chinese). 胡锐锋, 吴子牛, 曲溪, 等. 空间碎片再入烧蚀预测与地面安全评估软件[J]. 航空学报, 2011, 32(3): 390-399. [62] Wang Z H, Bao L, Tong B G. Rarefaction criterion and non-Fourier heat transfer in hypersonic rarefied flows[J]. Physics of Fluids, 2010, 22(12): 126103. [63] Wu Z N. Prediction of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secondary ejected droplets by crown splashing of droplets impinging on a solid wall[J].Probabilistic Engineering Mechanics, 2003, 18(3): 241-249. [64] Wang W B, Wu Z N, Wang C F, et al. Modelling the spreading rate of controlled communicable epidemics through an entropy-based thermodynamic model[J]. Science China Physics, Mechanics and Astronomy, 2013, 56 (11): 2143-2150. [65] Wu Z N. The number e1/2is the ratio between the time of maximum value and the time of maximum growth rate for restricted growth phenomena? [EB/OL]. http://arxiv.org/abs/1401.2400.pdf. [66] Li J, Wu Z N. A note on restricted growth process with competitive production and dissipation mechanisms[J]. In preparation. [67] Trinh K T. On the Karman constant[EB/OL]. http:// arxiv.org/pdf/1007.0605.pdf. [68] Sreenivasan K R. On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Kolmogorov constant[J]. Physics of Fluids, 1995, 7(11): 2778-2784. Tel: 010-62784116 E-mail: ziniuwu@tsinghua.edu.cn 当一道由气流偏转角θw导致的斜激波(入射激波为i)在镜面上反射时(下面介绍的激波相交,类似于激波反射),根据反射激波r是否脱体,会出现正规反射与马赫反射两种基本类型[20]。正规反射相对简单,反射激波后的流动参数是之前参数经过气流偏转角为-θw形成的斜激波后的流动参数,可以用斜激波关系式求得。在马赫反射情况下,入射激波和反射激波在三叉点T相交,三叉点通过一个强激波(马赫杆m)与壁面G点相连。经过反射激波后的流动区域与经过马赫杆后的流动区域应该满足压力平衡和气流平行两个条件,由一道滑移线s隔开。依据这两个条件和斜激波关系式(见图A1),可以确定各区域的流动参数。 图A1 激波反射示意图Fig.A1 Schematic of shock wave reflections 属于正规反射还是马赫反射,与Ma和θw有关。图A2给出了激波反射的两条临界曲线:θw=θD(Ma),θw=θN(Ma)。 图A2中上面的曲线对应反射激波刚好脱体的条件,称为激波脱体准则,下面的曲线对应经过入射激波与反射激波的压力,正好等于经过一道正激波的压力,称为压力平衡准则。这两个准则均由vonNeumann给出,详细内容见文献[20]。高于脱体准则,一定是马赫反射,低于压力平衡准则,一定是正规反射。在两者之间(双解区),正规反射与马赫反射均可能出现,具体会出现哪种反射,这就与历史有关。如果飞行器姿态是从下方的纯马赫反射区(如通过增大θw)进入双解区,那么在双解区就是正规反射。如果从上方的纯马赫反射区进入双解区,那么就是马赫反射,形成所谓的滞后回线现象[21]。在双解区,一种形式的激波反射,也可以通过扰动转捩到另外一种形式的激波反射[22]。 图A2 激波反射临界曲线Fig.A2 Critical curves for shock wave reflection 如图A3所示,由两次压缩引起的两道斜激波最终必然相交。依据两道激波的强弱以及激波角大小,会出现如图A3(a)所示的弱相交情况和图A3(b)所示的强相交情况。 下面给出这两种情况下各区的计算方法。如果按一种情况的计算方法无解,那么另外一种情况一定有解。 两道较弱的斜激波交于一点C,产生透射激波CD(也称合并激波)。另外,还有一道指向物面的激波CE,根据条件,可能为压缩波(激波),也可能为膨胀波。由于气流偏转角θ1和θ2是给定的,(1)区参数可用斜激波关系式直接从(0)区得到,接着(2)区参数直接从(1)区得到。可是,穿越CD和CE的气流偏转角θ4和θ3是未知的,因此无法直接由(0)区和(2)区的参数得到(4)区和(3)区的参数,必须补充气流平行和压力平衡条件。原来,经过CD得到的(4)区流动和经过CE得到的(3)区流动,气流方向平行且压力相等,即 图A3 同侧激波相交Fig.A3 Intersection of shock waves from the same family (A1) 中间由一道滑移线隔开(这里,“+”对应CE为斜激波,“-”对应CE为膨胀波)。 这两个额外的条件,加上过CD的斜激波关系式以及过CE的斜激波关系式或膨胀波关系式,就可以定出(3)区和(4)区的流动参数。预估初始θ4和θ3,采用迭代方法求解,如果p3>p2,则CE为斜激波;如果p3 如果按照如上计算方法无解,那么为强相交情况。强相交是比较复杂的情况,两道入射斜激波都较强或者角度差别较大,则干扰处出现马赫杆BD。D点处流场结构类似于马赫反射,而在B点处,出现超声速射流。 如图A4所示,在上侧的相交点附近,BE之间含有一段弱斜激波Bb, 其下游为超声速,bE为强激波,下游为亚声速。二者的下游需经过一道斜激波bc提升压力,在bc的下游需要经历一道膨胀波降低压力,以与(4)区压力平衡。 如此交替,形成由滑移线BH和bG界定的超声速射流。 经过每道波均满足相应的关系式,如果当地气流偏转角未给定(如由(2)区到(3)区),则需要补充压力平衡条件和气流平行条件(如p3=p4,θ2±θ3=θ4) ,如此就可以构造完整的唯一确定各区气流参数的表达式。具体做法同弱相交情况类似,这里就不再详细介绍。 图A4 激波干扰点附近的超声速射流Fig.A4 Supersonic jet near interaction point 以上考虑了同侧激波情况,对于异侧激波相交(见图A5),也可以做类似分析。 图A5 异侧激波相交Fig.A5 Intersection of shock waves from different families 如图A6所示,飞机前体产生的一道斜激波IS,与下游某钝头体形成的脱体激波BS相交,那么根据相交位置与角度,会形成6种情形的激波干扰,即所谓的6类激波干扰[23-24]。 6类激波干扰可以按激波相交分析其出现6种类型的原因。对于第I、II、III和V类激波干扰,均有一道激波打在物面上,与物面上的边界层反射干扰,导致物面干扰点P处的局部热流分别增加10倍、5倍、10倍和5倍左右。第IV类干扰中,有超声速射流(产生原因见图A4)打在物面上,热流放大可达17倍量级。第VI类干扰打在物面上的是膨胀波,不引起热流增加。 图A6 入射激波与前缘弓形脱体激波相交,依据相交位置形成的6类激波干扰示意图Fig.A6 Six types of shock wave interaction due to intersection of an incident shock wave with a bow shock wave 在文献[63]~文献[66]中,笔者等针对耗散增长现象得到了一些普适规律。如文献[64],此类耗散增长规律对应的增长函数由对数正态分布规律给出(见文献[65]和文献[66]中引用的更多文献) (B1) 式中:f(t)为耗散增长函数(也可以是该函数的导数),t为函数增长相对的时间(也可以是空间);tD为f(t)出现极大值对应的时间,即f′(tD)=0;σ为某种类型的几何方差(反映了增 长函数围绕平均值的偏差)。对于此类现象,人们关注拐点tL的位置,即使f(t)增长率最大的时间,亦即f″(tL)=0。对式(B1)两次微分并令f″(tL)=0,便得到 (B2) 在文献[63]中,笔者对式(B1)定义熵,并利用耗散增长系统最大熵增率原理确定σ,得到普适常数 (B3) 在文献[64]~文献[66]中,将式(B3)代入式(B2)得 (B4) *Corresponding author. Tel.: 010-62784116 E-mail: ziniuwu@tsinghua.edu.cn Analysis of flow characteristics for hypersonic vehicle WU Ziniu*, BAI Chenyuan, LI Juan, CHEN Zijun, JI Shixiang, WANG Dan, WANG Wenbin, XU Yizhe, YAO Yao SchoolofAerospace,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Modern hypersonic vehicles have local non-streamlined obstacles, operate at lower turbulent environment with high Mach number and lower Reynolds number and cruise in air subjected to shock and friction heating. Due to these factors, hypersonic flows are full of strong local flow structures such as strong shock waves and thick boundary layers, with sever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m. Aerodynamic heating is strengthened locally by such interactions. A number of critical phenomena such as transition and pressure perturbations are quite sensitive and the competitive influences of wave and frictional drags make the lift to drag ratio have a barrier. All these are not simply dependent on the Mach number and Reynolds number, but also dependent on many dimensional parameters, so that modelling by ground facilities is difficult and a combined study of theory, numerical study and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 are necessary to solve an engineering problem. In this paper, we give an overview of the state-of-art knowledg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critical physics of hypersonic flow and discuss the methods to solve hypersonic flow problems in the most possible effective way.This review and discussion are hopefully useful for further fundamental studies and for providing a bridge between fundamental study and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hypersonic flow; critical phenomena; shock wave; multiple wave interaction; influence factor 2014-07-24; Revised: 2014-08-26; Accepted: 2014-09-30; Published online: 2014-12-04 11:30 s: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90716009); National Basic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a (2012CB720205) 2014-07-24; 退修日期: 2014-08-26; 录用日期: 2014-09-30; 网络出版时间: 2014-12-04 11:30 www.cnki.net/kcms/detail/10.7527/S1000-6893.2014.0228.html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0716009); 国家“973”计划 (2012CB720205) Wu Z N, Bai C Y, Li J, et al. Analysis of flow characteristics for hypersonic vehicle[J]. Acta Aeronautica et Astronautica Sinica, 2015, 36(1): 58-85. 吴子牛, 白晨媛, 李娟, 等. 高超声速飞行器流动特征分析[J]. 航空学报, 2015, 36(1): 58-85. http://hkxb.buaa.edu.cn hkxb@buaa.edu.cn 10.7527/S1000-6893.2014.0228 V221.3 A 1000-6893(2015)01-0058-28 吴子牛 男, 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高超声速流动的激波问题、气动热问题与多波系干扰问题。 *通讯作者.Tel.: 010-62784116 E-mail: ziniuwu@tsinghua.edu.cn URL: www.cnki.net/kcms/detail/10.7527/S1000-6893.2014.0228.html













4 存在的问题与发展前景
附录A: 激波反射与激波相交








附录B: 耗散增长现象的普适规律及与湍流规律的可能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