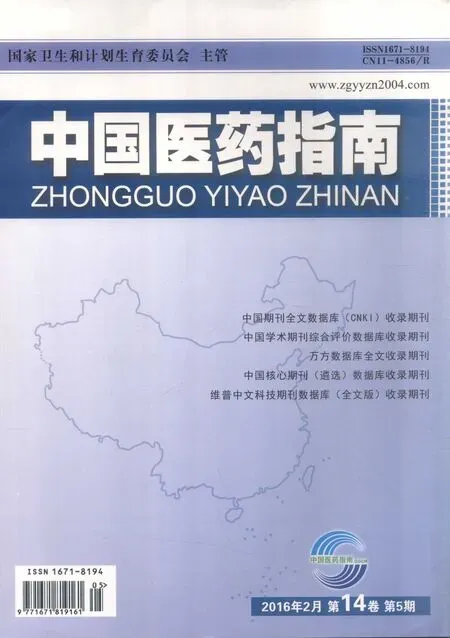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分子靶向治疗的新进展
王振亚 马长武
(内蒙古医科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110)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分子靶向治疗的新进展
王振亚 马长武*
(内蒙古医科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110)
【摘要】肺癌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病率和病死率都在逐年增加。其中非小细胞肺癌(NSCLC)占80%以上,我国肺癌5年生存率仅8%~10%。外科切除是可切除的NSCLC最重要的治疗手段,但即使是完全性切除后,仍有相当部分的患者最终死于肿瘤复发转移。目前第三代新药联合铂类两药化疗方案是治疗晚期NSCLC的标准方案,但疗效达到一个平台期,总生存率仅仅能提高约4.1%,患者似乎很难再从化疗中进一步获益。因此,寻找新的有效靶点和高效低毒的靶向药物成为了目前肺癌治疗的当务之急。本文综述了近几年来NSCLC分子靶向治疗的靶点和主要药物的进展情况。希望能为患者的治疗带来启示。
【关键词】靶向治疗;非小细胞肺癌;进展
肺癌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病率和病死率都在逐年增加。近30年来,肺癌已成为严重影响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常见肿瘤。据美国癌症协会公布的统计数据,美国在2014年出现224210例肺癌新发病例,在男女共患病中患病率居第二位,且159260例患者死于肺炎,占癌症致病死率的27.2%[1]。肺癌根据其生物学行为临床分为非小细胞肺癌(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和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其中NSCLC约占80%~85%。在我国,65%的肺癌患者在诊断明确时已为晚期,大多在Ⅲ~Ⅳ期,并且大部分诊断为早期的患者最终也将经历复发与转移。我国肺癌五年生存率仅在8%~10%[2-3]。
外科切除是可切除的NSCLC最重要的治疗手段,但即使是完全性切除后,仍有相当部分的患者最终死于肿瘤复发转移。目前传统化疗药物缺乏组织特异性,在发挥疗效的同时也带来严重的全身性不良反应。即便现在公认第三代新药联合铂类两药化疗方案是治疗晚期NSCLC的标准方案,但其疗效已经达到一个平台期,其总体有效率(RR)为25%~35%,至疾病进展时间(TTP)4~6个月,中位总生存期(mOS)8~10个月[4],总生存率仅仅能提高约4.1%[5]。而二线化疗有效率一般低于10%,患者似乎很难再从化疗中进一步获益。因此,寻找新的有效靶点和高效低毒的靶向药物成为了目前肺癌治疗的当务之急。
近年来,随着肿瘤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的发展,肺癌的有效靶点和高效低毒的靶向药物研究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包括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pidermal growth factorreceptor-tyrosine kinase inhibiter,EGFR-TKI)、棘皮动物微管相关蛋白样4-间变淋巴细胞瘤激酶融合基因(EML4-ALK)抑制剂、抑制肿瘤血管生成药物以及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单克隆抗体等。这些靶点的发现以及相应药物的陆续上市,给肺癌患者的治疗带来了希望。本文将重点介绍近几年来NSCLC分子靶向治疗的靶点和主要药物的进展情况。
1 EGFR-TKI
EGFR是一种跨膜受体,有研究表明,EGFR在早期NSCLC中过度表达。统计显示:高加索人种肺癌EGFR突变率大约10%,而亚裔人种EGFR突变率超过50%[6]。EGFR-TKI作用机制是通过与EGFR酪氨酸激酶区ATP结合位点特异性结合,能够有针对性地将磷酸根转移到蛋白质的酪氨酸残基上使其发生磷酸化,EGFR-TKI通过与ATP竞争性结合受体酪氨酸激酶区ATP结合位点,阻断了EGFR酪氨酸激酶活化和磷酸化,阻滞EGFR信号转导,最终导致瘤细胞增殖受抑、新生血管产生被抑制、肿瘤细胞迁徙转移能力减弱,启动细胞凋亡,从而达到抑制肿瘤的目的[7]。IPASS临床研究的结果显示,在EGFR基因敏感突变阳性的患者中,一线吉非替尼治疗组患者的疾病无进展生存时间(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明显长于化疗组,而在EGFR敏感突变阴性的患者中,化疗组患者的PFS明显长于吉非替尼组,由此确立了基于EGFR基因突变状态选择晚期NSCLC的原则。临床常用的吉非替尼(易瑞沙)和厄洛替尼(特罗凯)和我国自主研发的埃克替尼(凯美钠),目前常作为一线或二线方案治疗晚期NSCLC。
1.1自2003年5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吉非替尼作为首个口服的EGFR-TKI用于治疗常规化疗无效的晚期NSCLC患者以来,世界各国对吉非替尼对肺癌的治疗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经典的实验如Mok TS等[8]在Ⅲ期临床随机研究中,分为吉非替尼组和紫杉醇/卡铂组,一线治疗晚期NSCLC,结果显示吉非替尼组无论是PFS(24.9% vs 6.7%)还是有效率(71.2% vs 47.3%)均明显优于紫杉醇/卡铂组,而且不良反应反而明显减少。随后的WJTOG 3405、NEJGSG002、OPTIMAL、EURTAC、LUX-Lung 3、LUX-Lung 6等研究均证明了EGFR-TKI在PFS、生活质量以及耐受性方面都具有显著的优势,因此美国国家癌症综合网(NCCN)将EGFR-TKI列为EGFR基因敏感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的标准一线治疗。
1.2美国、欧洲及我国分别于2004年11月、2005年9月、2006年4月批准厄洛替尼作为一线化疗失败的NSCLC,是敏感基因突变肺癌患者的另一重要靶向治疗药物。厄洛替尼是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1(EGFR/ HER-1)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属小分子喹唑啉类衍生物,作用与吉非替尼部分相似,能与ATP竞争结合表皮生长因子受体(HER-1/ EGFR)酪氨酸激酶的细胞内催化区,抑制磷酸化,使阻断和抑制系统传送核内信息,而达到阻止肿瘤生长,控制细胞增殖、凋亡、新生血管生成和肿瘤转移。我国的一项多中心、非盲、随机Ⅲ期临床试验OPTIMAL比较厄洛替尼与标准化疗一线治疗具有EGFR突变的晚期NSCLC,结果显示PFS(13.1个月 vs 4.6个月)P<0.001和有效率(82.9% vs 36.1%)P<0.001[9]。
1.3我国自主研制的盐酸埃克替尼(凯美纳)是一种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小分子EGFR-TKI。通过对85种激酶的筛选,埃克替尼可以高效选择性抑制EGFR及其3个突变体,但对剩余81种激酶无明显抑制作用,具有特异性[10]。与外国生产的吉非替尼和厄洛替尼相比,其在化学结构、作用机制和疗效等方面相似,但安全性更好,皮疹等不良反应少且有显著的价格优势。ICOGEN研究结果表明埃克替尼与吉非替尼组相比,埃克替尼组的mPFS,中位疾病进展时间(mTTP)明显延长。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埃克替尼具有明显安全优势
2 EML4-ALK抑制剂
微管相关蛋白样4-间变淋巴细胞瘤激酶融合基因(EML4-ALK),在部分NSCLC患者中发现,染色体2P上发生的间质缺失以及插入导致部分N末端棘皮动物微管结合蛋白EML4与部分细胞内信号通路ALK受体酪氨酸激酶融合,形成EML4-ALK[11]。有研究发现NSCLC患者ALK基因重排比率国外为3%~6%[12],国内约为11%,多见于非吸烟的年轻男性。由辉瑞公司研发的克唑替尼(crizotinib)是一个选择性ATP竞争性小分子,为ALK阳性NSCLC的一线治疗药物。2010年ASCO报告了一项重要的Ⅱ期研究结果[13],Crizotinib治疗ALK阳性晚期NSCLC患者,客观反应率(ORR)为64%,疾病控制率(DCR)为90%,中位PFS未达到,且不良反应轻微,主要为胃肠道反应。由于有如此高的有效率和安全性,美国FDA批准Crizotinib直接进入Ⅲ期临床试验,并在缺乏Ⅲ期临床研究结果的情况下,该药于2011年8月被批准用于治疗ALK基因表达异常的晚期NSCLC患者[14]。克唑替尼常见的不良反应为视觉障碍、恶心、腹泻、便秘和肝酶升高[15]。克唑替尼是目前最早也是唯一一个进行Ⅲ期临床试验的ALK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3 抑制肿瘤血管生成药物
早在100多年前Goldman就观察到血管围绕肿瘤生成的现象,1971年美国Folkman[16]率先提出了肿瘤生长依赖血管形成的概念,并提出通过阻断肿瘤细胞营养供给达到抑制或消除肿瘤的学说。国内外诸多研究证明,新生血管对于肿瘤生长、浸润和转移具有重要意义,抑制新生血管的生成可使肿瘤细胞进入休眠状态,并可诱导其凋亡。1997 年Folkman等发表了一项抗血管生成剂内皮抑素(endostatin)治疗恶性肿瘤的动物试验结果,这种神奇的蛋白质可使原发肿瘤进展缓解,还可使微转移灶的生长停止。至此,这一理论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以切断肿瘤生长转移所依赖的“命脉”的抗血管生成治疗,成为重要的临床抗肿瘤治疗策略。1986年,又发现了导致血管生成的重要因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及其受体(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VEGFR),进一步揭示了肿瘤性血管生成的机制和意义。1997年,人们首次合成了针对VEGFR的抗体-贝伐单抗,由此研究使探索机制转化到临床治疗,此药也首次提高了晚期结直肠癌30%的总生存(OS)和晚期肺癌19%的总生存(OS)。继其之后,国内推出的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也在肺癌治疗中获得成功。于是,抗血管生成治疗被誉为继手术、化疗和放疗之后的“第四治疗模式。抗肿瘤血管生成药物大体可分为内皮细胞抑制剂、靶向VEGF和其他。
3.1血管生成剂内皮抑素(endostatin,恩度):肿瘤血管生成是一个多步骤的复杂过程,受血管生成促进因子和抗血管生成抑制因子的双重调控[17]。在促血管生成因子中,VEGF和血管生成素-1 (angiopoietin-1,Ang-1)及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ibroblast growth factors,FGF)共同诱导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血管生成抑制因子通过抑制形成血管的内皮细胞迁移和增殖,阻断血管生成,达到抑制肿瘤侵袭、复发和转移的目的。
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注射液商品名为恩度,采用大肠杆菌表达系统生产,是我国学者罗永章等自主创新研发的新型人血管内皮抑素。研究在天然内皮抑素序列N端添加了9个氨基酸,创造性地解决了重组蛋白质的复性问题,使规模化生产成为可能。研究表明,恩度能特异性强烈抑制血管内皮细胞增生和肿瘤生长,多靶点发挥抗血管生成作用,间接导致肿瘤休眠或退缩。Ⅰ、Ⅱ期临床研究证实,该药单药应用有效且安全性好。2003年4月至2004年6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组织了24家单位参与随机、双盲、多中心、对照Ⅲ期临床研究[18],试验组接受NP方案(长春瑞滨+顺铂)+恩度治疗,对照组接受NP方案+安慰剂治疗,结果显示,试验组较对照组有效率(RR),临床受益率(CBR),中位至疾病进展时间(TTP)均有显著优势。可见恩度与NP方案联合治疗晚期NSCLC能显著提高客观疗效,延长患者生存时间并改善生活质量。2005年9月恩度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批准为国家一类新药,2006年中国版NCCN非小细胞肺癌临床实践指南推荐恩度与化疗联合为治疗复发或转移性NSCLC一线用药。
3.2靶向VEGF:贝伐单抗(bevacizumab,Avastin)是目前NSCLC治疗的主要药物。其为重组人源化抗VEGF单克隆抗体,是首个获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的用于抑制血管生成的药物。2005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报道ECOG 4599的Ⅲ期临床试验[19],该研究将878例初治非鳞癌NSCLC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接受单纯化疗,另一组接受化疗联合贝伐单抗,一线化疗药物采用PC方案。结果显示,化疗联合贝伐单抗治疗组与单纯化疗组的有效率、患者的中位生存期(MST)明显提高,证实贝伐单抗联合化疗可改善晚期非鳞癌NSCLC的一线疗效。ECOG4599是第一项证明分子靶向药物与化疗药物联合可有效治疗肺癌的大型Ⅲ期临床研究,也是抗血管生成药物在肺癌治疗中与化疗联合成功的第一个范例,具有突破含铂一线化疗瓶颈的划时代意义。之后AVAiL研究[20]中,GP方案(吉西他滨+顺铂)联合贝伐单抗在治疗晚期NSCLC中获得类似的阳性结果,GP方案联合贝伐单抗较单纯GP方案化疗延长了患者的无疾病进展生存期(PFS)。鉴于此,美国FDA于2006年10月批准贝伐单抗联合泰素+卡铂用于NSCLC的一线治疗。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推荐贝伐单抗联合含铂两药方案用于中晚期NSCLC的一线治疗。
3.3其他:参一胶囊是国家一类单体抗癌中药,其主要成分人参皂甙Rg3可下调肿瘤的VEGF表达,破坏肿瘤细胞在血管壁着床,明显抑制肿瘤内皮细胞增殖生长和新生血管形成,是中国版NCCN指定的一线用药。
4 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单克隆抗体
单克隆抗体通过阻断胞外配体结合域,从而阻断EGFR的活化,其代表药物为西妥昔单抗(Cetuximab,IMC-C225)。
西妥昔单抗是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人/鼠嵌合型lgG1单克隆抗体,可以与内源性配体竞争结合EGFR从而阻断信号传导。此外,通过介导免疫学效应杀伤肿瘤细胞也是其重要的作用机制之一。临床研究显示[21],西妥昔单抗联合化疗一线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可提高患者对化疗的敏感度及患者的总体生存期,2009年已将西妥昔单抗纳入NCCN指南,并推荐作为晚期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该药的不良反应主要是痤疮样皮疹(发生率80%~86%)、斑丘疹、脂溢性皮炎、乏力及腹泻等。早发皮疹可能是西妥昔单抗治疗相关生存益处的独立预测因子。
5 结 语
随着分子靶向药物研究的不断发展,基于分子标志物的个体化治疗已成为NSCLC治疗的新方向。分子靶向药物以其高效低毒的特点为NSCLC的治疗开辟了新途径,利用最新的基因测序技术选择适合的多靶点抑制剂对患者进行个性化治疗,以及将作用于不同基因靶点的抑制剂进行联合用药,提高疗效和克服耐药性,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随着越来越多未知或不成熟的靶点被人们逐步深入了解,肺癌的靶向治疗必然会走向个体化,更多的癌症患者最终可以真正受益。
参考文献
[1] Siegel R,Ma J,Zou Z,et al.Cancer statistics,2014[J].CA Cancer J Clin,2014,64(1):9-29.
[2] 康倩,徐丹妮,余正.EGFR-TKIs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成本-效果分析[J].药物经济学研究,2013,30(6):377-380.
[3] Jemal A,Bray F,Center MM,et al.Global cancer statistics[J].CA Cancer J Clin,2011,61(2):69-90.
[4] Mendrola JM,Berger MB,King MC,et al.The single transmembrane domains of ErbB receptors self -associate in cell membranes[J].J Biol Chem,2002,277(7):4704-4712.
[5] Reed E.Platinum-DNA adduct nucleotide excision repair and platinum based anti-cancer chemotherapy [J].Cancer Treat Rev,1998,24(5):331-344.
[6] Hirsch FR,Bunn PA Jr.EGFR testing in lung cancer is ready for prim e time[J].Lancet Oncol,2009,361(10):432-433.
[7] Wakeling AE, Guy SP,Woodburn JR,et al.ZD1839 (Iressa): an orally active inhibitor of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signaling with potential for cancer therapy[J].Cancer Res,2002,62(20):5749-5754.
[8] Mok TS.Gefitinib or carboplatin-paclitaxel in pulmonary adenocarcinoma [J].Nengl J Med,2009,36(10):947-957.
[9] Zhou C,Wu YL,Chen G,et al.Erlotinib versus chemotherapy as fistline trea -t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advanced egfr mutationpositive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OPTIMAL,CTONG-0802): a multicenter,open-label,randomized,phase 3 study[J].Lancet Oncol,2011,12(8):735-742
[10] Zhou Q,Shentu J.A phase I/Ⅱ a study of icotinib hydrochloride,a ovel oral EGFR-TKI, to evaluate its safety,tolerance,and preliminary efficacy in advanced NSCLC patients in china [J].J Clin Oncol,2010,28,15s(Suppl l):7574.
[11] Soda M,Choi YL,Enomoto M,et al.Identification of the transforming EML4-ALK fusion gene in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J].Nature,2007,448(7153):561-566.
[12] Horn L,Pao W.EML4-ALK:horning in on a new target in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J].J Clin Oncol,2009,27(26):4232-4235.
[13] Bang Y.Clinical activity of the oral ALK inhibitor PF-023 41066 in ALK-positive patients with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SCLC)[J].ASCO,2010,28(18):143-146.
[14] 董江萍.FDA批准克唑替尼及其基因检测试法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J].药物评价研究,2011,34(5):402.
[15] Curan MP.Crizotinib in locally advanced or metastatic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J].Drugs,2012,72(1):99-107.
[16] Folkman J.Tumor angiogenesis : therapeutic implications[J].N Engl J Med,1971,285(21):1182-1186.
[17] JAIN RK.Normalization of tumor vascIllalure: an emerging concept in antiangiogenetic tfierapy[J].Science,2005,307(5706): 58-62.
[18] 王金万,孙燕,刘永煜,等.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联合NP方案治疗晚期NSCLC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Ⅲ期临床研究[J].中国肺癌杂志,2005,8(4):283-290.
[19] Sandler A,Gray R,Perry MC,et al.Paclitaxel-carboplatin alone or with bevacizumab for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J].N Engl J Med,2006,355(24):2542-2550.
[20] Manegold C,Pawel JV,Zatloukal P,et al.Randomized,doubleblind multicentre phase Ⅲ study of bevacizumab incombined with cisplatin and gemcitabine in chemotherapynaïve patients with advanced or recurrent non-squamous,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 BO17704[J].J Clin Oncol,2007,25(18S): LBA7514.
[21] Pirker R,Szccesna A,von Pawel J,et al.FLEX:a randomized,multicenter,phase Ⅲ study of cetuximab in combination with cisplatin/vinorelbine(CV)versus CV alone in the firstlin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NSCLC)[J].J Clin Oncol,2008,26(Suppl):8015.
中图分类号:R7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94(2016)05-0031-03
*通讯作者:E-mail: docmachangwu@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