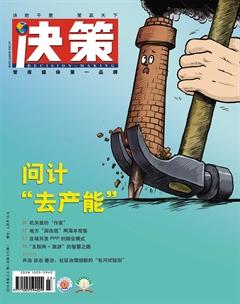机关里的“作家”
吴明华
在体制内,他们是不起眼的官员;而在体制外,他们却是人气十足的作家、专家或网络“大咖”。他们究竟是成功还是失意?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
在机关,人们往往会以升迁为仕途成功的标志。但却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并不热衷仕途和官场,而是醉心于写作,有的写官场小说畅销一时,有的在某一领域深入研究著书立说,有的寄情于文字著作颇丰,有的在网络和报刊上针砭时弊成为“意见领袖”。
在体制内,他们是不起眼的官员;而在体制外,他们却是人气十足的作家、专家或网络“大咖”。他们时常游走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边缘,有些人如鱼得水,也有人谨慎小心如“走钢丝”,而体制内外对他们的评价往往也反差极大。他们究竟是成功还是失意?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
“文坛中人说我是官人,官场中人说我是作家,用时髦话说,我是边缘人。其实,我什么都不算,只是个尴尬人。”著名官场小说作家王跃文曾这样评价自己。对于官员“作家”这个庞大的群体来说,他们是否真如王跃文所说,都是一群“尴尬人”?
“尴尬人”是如何炼成的
其实,初入官场的王跃文并不是“尴尬人”。相反,他还曾一度仕途通达。
1962年出生的王跃文,大学毕业后因为颇有才气,被分配到老家湖南溆浦县政府当秘书。“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却成天装着老于世故的样子。”王跃文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可笑,但当时却被认为是“谦虚谨慎,可成大器”。
果然工作没两年,王跃文便成了副科长,工作四五年,就升任正科长。此时,他不仅是机关的“笔杆子”,而且工作之余时常发表一些小说。“在偏僻的小地方,人们见我工作不错,又能写小说,越发认为我是个才子。因而,我在政府部门呆的机关就越来越大。”
30岁出头,王跃文便上调怀化市,两年后又上调省政府。从县里到省里,王跃文步步高升,官运一路享通,“在外人看来,这分明是个发达的迹象。”王跃文也承认自己当年是有政治抱负的,想通过自己的能力来有所作为。
然而此后,他似乎沉淀了下来,不仅级别没有得到提升,而且一直从事枯燥的文秘工作,这对他的仕途发展极为不利。在省政府办公厅工作5年后,当王跃文创作长篇官场小说《国画》时,他已经37岁,无论从年龄还是履历来看,他在仕途发展上已经没有了优势。
这期间,王跃文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大概从三十五岁开始,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官场讲究功夫在诗外,我没有任何诗外功夫。衙门越大,有些人越让人看不透。我慢慢意识到自己高看有些人了,觉得自己很幼稚。”
逐渐放弃抱负的王跃文,纯粹以就业的态度看待工作,并且更加专注地开始写小说,“我曾长期在官场工作,熟悉里面的人和事,对其中的世道人心有深刻的体察和感悟,有种不说不快的冲动,于是就借助小说来表达。”
“官场有自己的词典,什么叫成熟,什么叫能干,什么叫谦虚,什么叫涵养,同《现代汉语词典》上解释的并不一样。”一些潜规则在别人看来都是常识,人人都自觉而小心地遵循着,但王跃文却总是心生疑惑,拒不认同。
特别是作为秘书人员,身份很微妙,不是官员,却要用官员的脑子想问题,用官员的文笔写文章,有时候还得替官员办事情。“日子久了,心里有种别扭的感觉。我生性耿直,内心的真话不说出来就觉得闷得慌。”于是,他试着用小说的方式说真话。
《国画》出版后迅速热销,曾2个月内重印8次。但同时,小说对官场游戏规则逼真的描述,特别是对一些丑恶和腐败现象赤裸裸的揭示,触动了很多官员的神经。
有朋友曾向王跃文传递了一个信息,说某位很有身份的人看了《国画》,咬着牙根说,要是在那個特殊年代,可以枪毙他十次。一位领导甚至在一次副处以上的干部会议上,公开批判《国画》,而王跃文也写了一封公开信予以反驳。
尽管小说轰动一时,但也让王跃文处境尴尬,“人在官场而写官场题材的小说,怎能不尴尬呢?”小说出版一年后,王跃文即遭遇机构改革,分流下岗,“说白了,就是从现行体制中出局了。”
“如果以做多大官来衡量,我在官场混得非常不好,完全是一个失败者。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的人生失败。”在王跃文看来,有些官场中人,当他获得世俗成功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深层次的灵魂溃败。
离开官场,王跃文觉得是种解脱,不再是“边缘人”了,“但是,别的意义上的边缘人心态也时时存在。比如,我不太认同很多现实的金科玉律,却必须在某种场里过日子,心有尴尬而口不能言。”
“防范者”与“走钢丝”
因写小说而成为“尴尬人”,最终不见容于官场,像王跃文这样的似乎是特例,更多的人是在小心翼翼把握着官场与写作的平衡与界限。
“规则本来是封闭的,而官场小说作家试图以自己的文字,来打破这种封闭。这势必就会触及到不同阶层的利益,而作家不是真空中的存在。”在知名官员作家洪放看来,官场小说作家往往生存在一种无形的挤压之中。这种挤压,不仅仅来自于个体,更多的来自于群体。当作品与群体利益发生了冲突,官员作家就成了官场的“防范者”。
面对这种不可避免的尴尬,洪放一直试图找到平衡。他在创作时特别注意把握小说的尺度,不盲目地揭露与揭秘,而是坚持理想主义情怀和道德救赎。为了不让身边的人“对号入座”,他在创作中尽量不去单独地深入地剖析某个人物,而是采取融汇式的,消失特别的印记。
“也就是:像,又不尽像;不像,恰恰就是。”要精准把握这种尺度无疑很难,很多时候其实是在“走钢丝”。每次写完,洪放甚至会把整部小说里的人物名字拿出来,看有没有与当地官员名字相同的人,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在官员“作家”群体中,写小说的只是一小部分,还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们长期在基层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有深入研究,他们希望在本职工作之外自己的研究能经世济用。
相比写官物小说而言,做研究著书立说是工作之余的个人行为,与官场群体利益并没有冲突,但他们同样需要严守“界限”。
身为浙江某财经机关调研处副处长的傅白水,凭借多年来业余勤奋研究、笔耕不辍,如今已是浙江知名区域经济专家。他有一个“三不原则”:不参加各种论坛,不讲课不兼职,不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这些原则正是他对平衡与界限的严格把握。
1973年出生的傅白水,研究生毕业后进入财经机关工作,工作之余的爱好就是研究区域经济。他经常在国内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没两年便在浙江小有名气。
在机关,写一些工作以外的文章往往会被看作不务正业或是“出风头”,但傅白水却得到了单位领导的肯定和表扬。在他看来,这有几个前提:写的文章要有建设性,对工作有促进作用,而且内容跟本单位不相关,不涉及具体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做好本职工作,“首先工作要做好,要成为单位的核心骨干,这个度要把握好。”
“有些人在工作之外做得很好,慢慢和单位距离拉远,但我结合得很好,领导和同事相处得也很好。”在单位,傅白水是写材料的核心骨干,业余写文章,既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又能和单位工作相互结合、相得益彰。
“体制内就按体制内写,体制外就按体制外写,遵守各自的规则。这一点严格做到。”让他感到比较得意的是,有时候给机关写的材料和自己写的文章,都得到了省领导的批示,“两条线并行,没有交集过,带来的都是正影响”。
工作与写作相得益彰,源于对诸多“度”的严格把握。10年下来,尽管年纪不大,但傅白水头发几乎全白。
“体制内是安身立命的地方,个人研究写作可以在体制外实现个人价值。在机关工作一辈子,除了安身立命之外,人的一生要有一点情怀、一点理想。”傅白水告诉《决策》。
“特殊的风景线”
洪放、傅白水等官场中人之所以成为“作家”,主要因为工作之余的兴趣爱好,而有些人则是逃避现实、消磨时光的无奈之举。
河南省三门峡市交通局副局长尚柏仁,10多年来,每年都会用2个月的时间到农村进行调研,撰写了上百万字的调查报告和论文,成为知名的“三农”问题专家。在交通局工作却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三农”,一个在权力场中周旋有年的副局长还能潜心做研究,这让很多人感到不可理解。
“挥笔写时代,勤奋著人生。在写作事业精彩斑斓的天地里,努力做一片最美丽的叶子。”尚柏仁曾在一篇散文中这样写道。但他告诉《决策》,其实,这或许是冠冕堂皇的说辞,而真实的用意,只是自己不想学坏、不想辱没良心、不想在红尘中沉沦,“因此,从另一层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消磨时光的无奈之举罢。”
1963年出生的尚柏仁,凭借自己的勤奋努力,37岁即从乡长做到常务副区长,仕途前景颇为光明。然而2002年,他却被安排到交通局任副局长。这样的安排并不合官场常理。尚柏仁自己分析认为,可能是因为他生性耿直,说话直来直去,得罪了人的缘故。
“在常人眼里,做官、进步是不需要也不准有自己的思想的,而我偏是有个性之人。”这样的个性也让他在交通局遭遇了更大的挫折。
到交通局工作后,尚柏仁碰上前后两任局长相继腐败落马。交通局当时给他的印象是无序,很多事情都不按程序办,很多公正、公道,甚至正常的话都无人敢说。“我喜欢单刀直入,刚到局里时,依然心直口快,很快就惹了不少的告状信,诬告、诽谤、侮辱、谩骂等什么都有。”
特别是2005年交通局机构改革和干部竞争上岗中,改革牵动了系统内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上下意见很大,人际关系极其复杂。尚柏仁坚持讲实话,结果惹来告状信满天飞,“经过这场磨难,我思考了很多问题,也反思了很多东西。我重新给自己定了位:低调,做学问,多磕头少说话。”
贫寒农家出身的尚柏仁,对“三农”一直有一种情结。“雄气无处发泄”,他就把主要精力放到“三农”的调研和写作上,“这些年来,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便钻进书房里发奋地读书;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我便拼命地去写作;在我最无聊的时候,我就到农民朋友那里去调研。”
10多年下来,尚柏仁出版4部个人专著,成了专家型领导,“做学问的名气反而比做领导的名气大些”。
在当地官场,尽管也有人认为他是仕途不顺发牢骚,或是回避矛盾、不务正业,但更多人称赞他是在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他们这个群体,在机关也是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出世与入世
在复杂的官场生态里,尚伯仁们因避世写作、特立独行,而成为一道特殊的风景线。但同时,在官员“作家”群体中有一些人,他们心怀阳光、积极入世,用文字传播正能量,笔耕不辍、乐此不疲,他们也是机关里的一道风景。
2002年,49岁的张新民调任湖南省常德市政协副主席,尽管早早退居二线,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沉懈怠,反而精神焕发,重新找回了年轻时写作的激情与梦想。
“我们没有那种‘一无权、二无钱,无是无非度晚年’的失落感;没有那种‘无意义、无味道、无所谓’的倦怠状;也没有那种‘不出头、不找事、不争先’的无所作为思想。始终保持宠辱不惊、积极进取。”张新民说,当时书记找他谈话,原以为他会有情绪,没想到他爽快接受,不到一分钟就谈话结束。
秘书出身的张新民,过去几十年大部分都在办公室与文字打交道,以前写材料,没有多少是自己的东西,都是四平八稳的官样文章,“到政协后精神为之一振,写的东西都是自己的。”
到政协后,他坚持每天写作,已写出理论文章、时事评论、散文诗歌近一百多万字。他的文章文如其人,富含为官哲学与人生智慧。
2007年,张新民开办了实名博客,之后上网写文章就一发不可收拾。2013年,他还发动老干部成立了网络宣传协会,并因此而获得中组部的表彰。现在,他已经成为当地网络上的一面旗帜。
“我把网上发文章当作个人兴趣爱好,后来发现网上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什么观点、什么文章都有,我就自觉实现一个转变,把个人的兴趣转到社会责任上面,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张新民一直堅持一个观点,要像周总理提出的,学小蜜蜂采花酿蜜、传播香甜,而不要像苍蝇到处追腥逐臭,传播腐朽、病毒。
2013年,常德市新一任书记、市长到任后,开展城市改造“三改四化”。一开始,当地人不理解一片埋怨,甚至一片骂声。当时,张新民也有些不理解,但他并没有急着做出评论。
后来,常德连续下了7天雨,他就打着伞跑遍大街小巷,发现城内没有一处积水,于是写了篇文章,称赞良心工程得民心。文章在网上引起很大反响,迅速扭转了舆论走向,对市里的工作给予了强大的舆论支持。
“以前,我也喜欢写一些讽刺挖苦的杂文,后来我就感觉到这是人性的弱点,老是指桑骂槐自己又做得怎样呢?要给人信心、光明和希望。”在张新民看来,体制内的人心态更要阳光,那些愤世嫉俗的往往是不得志的人。
“有才的人为什么会不得志?很多时候也有他自己的弱点,要么不会为人处事,要么眼高手低。”张新民说,他曾遇到一些干部,文章写很好,但老是提拔不上去,因为平时一有怨言他就流露出来,人际关系必然会受到影响,“还有的人缺情商,总是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清高孤傲,即便领导想提拔他,但民主推荐时大家就不投他的票。”
张新民说,他曾经也有不得志的时候。他在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政府办主任时,8年内遇上三任书记市长闹不团结,“那就是在夹缝中为人,经常很为难,人生走入低谷”。
在他看来,人生走入低谷也不要气馁,失意不失态,失意不失志,失意不失言。后来,他还专门写了篇文章,总结面对党政一把手不团结怎么办。
“回过头来看,我感觉自己其实已经很得志了。什么时候都不要埋怨,怨天尤人没有任何作用,心里要怀着光明。我不愤世嫉俗。”张新民告诉《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