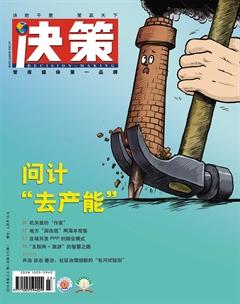地方“深改组”两周年观察
贺海峰
地方“深改组”是改革攻坚的前哨指挥部。通过呈现其运行的逻辑、取得的进展以及遭遇的困扰,更能洞察表象背后的中国政治密码与走向。
2014年1月22日,领衔新一轮改革的超级权力机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千呼万唤中闪亮登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设定的60项、336条改革由此拉开序幕。
紧随其后,所有省、市、县党委相继成立“深改组”,组长均由党委书记担任,行政首长和专职副书记担任副组长,规格和阵容与中央基本一致。同时,还公布了下一步改革的任务书、时间表和路线图。
两年时光倏忽而过。作为改革攻坚的前哨指挥部,地方“深改组”是怎样运转的?两年间取得了哪些进展,又遭遇到何种现实困扰?面对稍纵即逝的窗口期,中央和地方将如何出招?
释放出哪些信号
对于“深改组”,公众印象最深的当属不定期举行的领导小组会议。短短两年时间,中央“深改组”会议已召开了20次,差不多每月都有若干新方案出台,可谓紧锣密鼓、马不停蹄。而地方上也是动作频频,比如2016年2月14日,春节过后首个工作日,安徽省委“深改组”即召开会议,安排部署“十三五”开局之年的改革任务和具体举措。
这并不让人意外。实际上,自上而下的制度化会议,一直是中国特有的政治运作模式。当代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变化,往往都经由开会的形式发生。尤其是处于“众声喧哗”时代,“深改组”会议通过释放明确的改革信号,借助媒体全方位、强有力的传播,可以有效引导社会行为、思想和情感的制度化。
所有省级“深改组”会议,均由省委书记主持召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1月,会议总次数达到10次的省(市、自治区)至少有20个。其中,山东19次,贵州、吉林各18次,陕西、山西各17次,云南16次,广东、湖南、天津各15次,甘肃、江苏、福建、青海各14次,上海、辽宁、河北、黑龙江各12次,内蒙古、宁夏各11次,河南10次。
“深改组”会议频次的高低,能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地方党委改革紧迫感的强弱。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的“敲核桃”理论,就曾引起广泛共鸣:“显性问题容易发现,隐性问题往往包裹着一层硬壳。我们要敲开核桃,既看到挑战中的机遇、差距中的潜力,又找出先进中的落后、成功中的隐患。”在“深改组”的精准拿捏下,山东简政放权、金融、财税等改革都迈出较快步伐。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则多次提出:“要有改革的使命感、紧迫感,要积极行动起来,要成为改革的行家里手。不能慢慢腾腾地、晃晃悠悠地做到哪里算哪里。”在多重压力的倒逼下,贵州大数据、生态治理等改革一度轰动全国。
需要指出的是,“深改组”会议次数少,并不必然意味着改革含金量低、改革力度与成效小。只召开过8次会议的浙江,是毫无争议的改革样板省。2014年以来,仅在经济改革领域,就接连打出“五水共治”、“浙商回归”、创新驱动等“组合拳”,直击制约浙江转型发展的要害。只召开过6次会议的重庆,则主攻内陆开放和投融资、城镇化、国资国企改革。2015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影响下,重庆经济增速达到11%,较全国高出4.1个百分点,获得中央高层领导“点赞”。
从更深层面来看,“深改组”会议体现了主政者对改革大势的研判能力、对改革议程的把控能力。2015年,一位新上任的省委书记,在会议上特别谈到:“把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保稳定、防风险的改革举措往前排;突出抓好具有地方特色的先行先试重点改革;集中推出一批力度大、措施实、接地气的改革方案。”由此释放的信号是,通过差异化改革领跑,展现更多锐意和创新,为全国改革树立样板、提供经验。
低调而忙碌的改革办
与“深改组”的高调相比,作为其智囊和执行机构的改革办,则显得颇为低调而神秘。
这与改革办的职能定位密切相关。根据设计,“深改组”主要履行改革任务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的职责;各专项小组承担所负责领域改革推进的责任。而改革办作为常设性工作机构,则承担协调服务工作,负责日常运转、协调督促、上下沟通。
从组织架构看,各地改革办大多沿袭了中央的做法,即与党委政策研究室合署办公,同时新设立了秘书处、协调处。比如湖南省委改革办下设的两个处室,分别被冠名为改革调研处、改革推进处,其职能和事务与其他省份并无二致。2014年,中央改革办新增加了督察局,但地方改革办并未简单效仿,而是与省委督察室联合开展改革督察。
省级改革办主任的人选,主要分为两种任职模式:安徽、江苏、河南、北京等地,均由省委常委、秘书长兼任;陕西、湖北等地,则由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任。相对而言,甘肃、广东两省的配置较为独特,改革办主任分别由省委副书记欧阳坚、省委办公厅主任刘可为兼任。
作为改革办承上启下的协调者,专职副主任的角色相當吃重,必须兼备很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很强的实际操作能力。河北省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王晓桦,此前历任邯郸地委党校教师、成安县委书记、大名县委书记,一度是轰动全国的“改革派”官员。湖南省委改革办则配备了2名专职副主任。其中,秦国文曾任省社科院副院长、吉首市委书记,2015年初被明确为正厅级;罗云寿则一直供职于省委政策研究室,长于组织协调和文稿撰写。
从运作过程看,改革办大部分精力用于筹备会议、起草文稿、交流信息、督促检查、树立典型。“深改组”会议具有协商、决定、动员等多重功能,领导层、各部门和社会各界都极为关注。对改革办来说,必须提前一两个月筹备,反复征求各方意见,起草讲稿、形成方案。而往往一次会议结束,又要与各专项小组沟通,共同筹划下一次会议。其中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推倒重来、多次打磨,直到领导层和各部门达成共识。
分责、督察与考核,是改革办的核心职责。2015年底,安徽省委“深改组”首次对承担年度改革任务的省直牵头单位和16个省辖市进行督察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改革方案是否科学、改革举措是否有效、改革推进机制是否有力、改革效果是否符合预期。在考核指标设置上,“组织领导”“贯彻落实”“改革成效”分别占比10%、50%、40%,力促改革落地生根的导向十分鲜明,使得条与块的改革必须围绕“考核指挥棒”运转。由于需要多人全程参与督察考核,改革办有限的人手也就更加忙碌。
笔者在实地调研中发现,这种超负荷作业的状态,在各级改革办中普遍存在。一方面,“活多、人少”。广东、湖南省委改革办分别只有16人、12人,而相当数量的省委改革办仅有6-10人;市县改革办专职人员则更少,有的仅有1-2个编制,甚至尚未明确编制。另一方面,“体制内运行”。省市县改革办与党政机关联系频密,但对“外脑”的开发尚不够充分。广东、安徽遴选若干项重点改革,委托第三方开展绩效评估,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从县域看“最后一公里”
针对改革中的博弈状态,社会上流传着一个比喻:“上层踩油门,中层放空档,下层踩刹车。”此言尽管相当刺耳,却折射出一种普遍的担忧,即如何确保改革部署顺畅地推进到“最后一公里”。
县域是承上启下的“接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面深化改革,“成也在县,败也在县”。作为县委“深改组”组长,一位县委书记坦言:“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堆具体而微的改革难题要往前推。”如何在刀尖上跳出一支华美的舞蹈,无疑需要一批扮演“催化剂”角色的优秀操盘手。而如果县委书记不想动真格,改革试点成效必然难以彰显。
让人欣慰的是,在县委书记群体中,涌现出不少锐意改革者。2014年,浙江在德清县开展城乡体制改革试点。时任县委书记张晓强围绕破除城鄉二元结构,主导推进“三权到人(户)、权跟人(户)走”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推动农村新土改、新金改、新户改,有效实现了“死产变活权、活权生活钱”。湖北嘉鱼县委书记熊征宇,针对干部正常“下”的难题,实施“任期+实绩考核”改革,对县直76名副职干部集体卸职,经过任期考核、连任竞岗等流程,7名干部就地免职,搬掉干部“铁交椅”,激发干部队伍内生活力。
不过,也有部分县委书记反映,在改革中仍有诸多困惑,仅靠基层力量无法解决。一是对改革风险把握不准,担心对改革者产生不良影响;二是感到改革压力较大,担心改革实效与群众期盼还有较大落差;三是不清楚改革的边界在哪里,哪些领域直接执行,哪些领域尚需探索;四是有些改革虽有动力却没权力。有人担忧,长此以往,当基层发现问题时,不是考虑如何破除制度障碍,使生产活力得到及时解放,而是更寄希望于顶层设计。
实现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也是当务之急。从财政支出看,中央只花了15%,省级也花了15%,市县则花了70%。下一步,应当把部分事权的执行上移到中央,中央的事情中央干,地方的事情地方管。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真正形成改革合力。
此外,还要扩大改革的社会参与度。改革的本质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当前,个别改革方案制定过程仍由部门主导,变成部门内部操作、闭门谢客。作为利益相关方的公众却“被缺位”,作为超脱利益之外的学界也“被缺席”,无疑是改革方法论上的重大缺陷。而要突破这一困局,就必须扩大公众和学界的参与度,让改革红利真正抵达每个人的身边。
陈一新上调
中央改革办之后
2015年12月1日,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上调中央改革办担任专职副主任。
中央改革办领导大多出自中央部委,陈一新是唯一来自地方的官员。他是浙江省委、省政府核心智囊之一,先后出任金华、温州市委书记,具有丰富的政策调研经历和改革操作经验。11月19日,在离开温州前夕,他特意召集各县(市、区)党政“一把手”座谈,提出温州未来要做“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模范生”,还强调说,“底层创新与顶层设计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以底层创新成果赢得上级认可和支持,并为顶层设计提供更多经验”。
上调中央改革办以后,陈一新很快奔赴安徽、广东两省,督察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工作。在安徽定远县,他提出要让更多的群众知道改革成效,真正形成全社会理解改革、关心改革、参与改革、支持改革的氛围;要加大支持底层创新的力度,为顶层设计提供经验,同时检验顶层设计的科学性。
之前的10月13日,在中央“深改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中央通过的改革方案落地生根,必须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越重,越要重视基层探索实践。基层改革创新,要尽可能多听一听基层和一线的声音,要最大限度调动地方、基层以及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在这个背景下,陈一新上调中央改革办,其肩负的使命不言自明。特别是眼下,既得利益者不愿放手,改革出现“空转”的苗头,亟待择天下英才而用之。这样的英才未必局限于体制内,一方面要能洞悉地方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优劣势,另一方面又不存在与中央各部委之间的利益纠葛。未来两年,中央和地方能否起用更多“改革促进派”,将最终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成败。毕竟,距离2020年,时间越来越迫近了。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感谢安徽省委改革办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