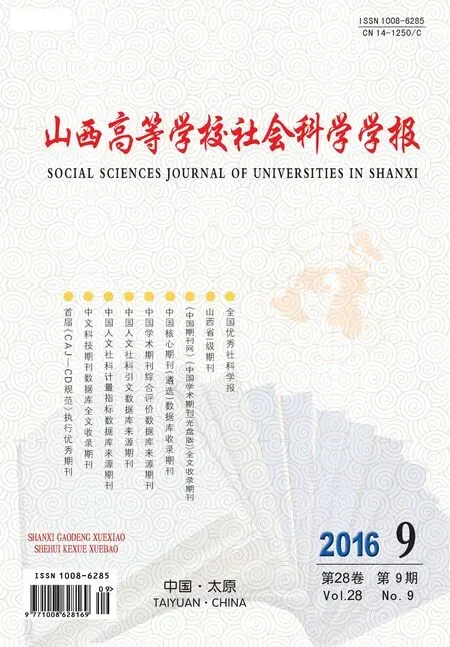社会暴力的起因、类型与再生产逻辑——以“吴妈事件”与麻城T村的调研为基础的讨论
刘 晨
(澳门大学 社会学系,澳门 999078)
社会暴力的起因、类型与再生产逻辑
——以“吴妈事件”与麻城T村的调研为基础的讨论
刘晨
(澳门大学 社会学系,澳门999078)
文章通过对底层暴力的起因分析得出,暴力与人性结构、人的原始性和生物性等因素有关。通过对底层暴力的理想型分类,得出了七种不同的暴力类型,进而对其再生产机制,以“吴妈事件”和“麻城T村”的调查为例,得出了底层暴力产生以后,政府的“不作为”或“乱作为”是引发“以暴制暴”的主因。尤其要注意的是,如何切断下一次暴力的发生是杜绝暴力的关键。并且,不仅仅是从制度上着手,还要从文化中自省,其是否对民众的人格塑造或人性结构的影响造成了暴力的隐藏。
暴力;理想类型;起因;再生产;文化
一、问题的提出
“谁要曾经思考过历史和政治,他就不可能会对暴力在人类事务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无所知。粗略一看,暴力一直以来很少受到特别关注,这实在令人吃惊*在最新版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暴力”一词甚至连个条目都算不上。。这表明,暴力及其任意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理所当然,并因而被人们忽视;没有人会质疑或者检验那些对所有人来说显而易见的事情。”[1]从中可以发现,人们对暴力还不是那么认真地对待,缺乏注意和反思。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暴力对于我们而言并不陌生,甚至在如今的一些新闻报道中时常可以见到。比如《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2015年8月27日,“中国留学生涉嫌绑架施虐同伴案”在美国再次开庭,虽然案件还没有最终判决,但有分析称,施暴的女生有可能被判终身监禁[2]。再比如,“昆明,某高校女生因怀疑舍友偷内衣,邀来同伙殴打舍友,强迫其脱下裤子暴露下身,并用手机拍下施暴与受辱的照片和视频。而在广东,开平某中七名女生结成‘七姐妹’,邀四个男生轮奸同班同学,并把殴打和轮奸场面录制下来传到网络上”[3]。还有,“7月12日凌晨,河南省平顶山市居民胡凯及其母亲麻伟玲,在绢纺厂家属院的家中熟睡时,遭多名社会人士闯入。母子二人被打昏后抬走,房屋遭到强拆”[4]。类似这样的社会暴力事件,其实还有很多。那么,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何有这么多的社会暴力?
但凡对暴力有一定研究和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些问题背后所蕴含的因素是比较复杂的,且全面地理顺和挖掘各个不同的暴力类型与原因所在,也比较有困难。基于此,本文重点从暴力的起因、暴力的类型和暴力的再生产机制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同时,本文还利用田野调查所得的一些一手资料进行比较性的分析,以试图去探求不同语境和场所中的暴力,发掘出我们是否还没有觉察到的引发暴力的潜在因素。
二、暴力的起因:人性结构、原始性与快感(或复仇)
有学者认为:“暴力潜藏在人性的深处,文明与文化使之幽暗或式微。暴力又是一种权利意志的极度张扬,但并未否定它的隐藏和策略能力。它普遍存在在人性之中,是侵略或者防御的瞬间力量的集合,是一种超限的工具。”[5]他的分析无疑是从人性结构的角度来定义暴力的,其是一种防御或反抗的工具。再从传统的古典犯罪学理论来看,他们又将暴力行为者视为理性的人,进而把暴力看作是一种工具性行动*特别是一些国家暴力的行为,可以参见阿伦特、索雷尔对暴力的论述,他们更多的是基于国家层面的。而本文论述的是非国家暴力的暴力,故而暂且不深入讨论这一问题。[6]。精神病学对暴力的诊断又是不同的,“暴力行为者是受魔症支配的‘非正常人’*这样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建构”或者“贴标签”的意味。,暴力行为是精神病和神经官能症的结果”[6]。而犯罪生物学认为,“犯罪人和那些施暴的人,和平常人有差异。犯罪人和施暴者是没有脱离野性的人,进化水平低于平常人。比如从颌骨,突出的颚骨等都可以看出”[6]。从这个层面说,暴力者的面貌或长相与平常人是不同的。再从社会学的角度说,“暴力是一种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或许我们再给暴力者下定义的时候,就已经用标签化的符号指涉那些施暴者,往往这些暴力行为的主体一旦被边缘化,成为异类,那么他们会在以后寻求同样是暴力者的情感支持,这样的一种循环就会导致暴力的层出不穷,周而复始”[7]。
可以发现,不同学科对暴力有不同的看法。从左春的研究发现,暴力与人性结构有一定的关系,再从犯罪学和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暴力与生物性、快感等有一定的关联;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是标签化了暴力者,应该不把他们看作是异类。值得强调的是,社会学的这一个观点,无疑与福柯的《疯癫与文明》所倡导的价值相同*福柯在该书中探讨了人们是如何对待疯子的,特别是对菲利普·皮埃尔和塞缪尔·图克的例子做出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详见《疯癫与文明》,福柯著,三联书店(北京),2007年版。。
接下来我们需要论述的是“人为什么有暴力?”首先,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以“猿人的政治”为例,猿作为进化之前的人类,同样也有政治行为,比如竞争权力(领导者或主导者)、厮打、搏斗等举动。这类的行为就构成了暴力的初始状态,也就是为了获得一定的利益,而采取了“拳头的逻辑”*笔者曾经在多个底层抗争的论述中,用到这一概念。通俗的说,就是中国的“权势社会”。其讲究的是,谁的拳头厉害,谁就是主宰者,那么被欺辱的一方,就需要服从或者是妥协。。甚至,为获得性交配权利,也会采取搏斗的方式,这在动物界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这样的“嗜好”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演进当中并未退却或消失,而是一并夹杂在现代文明之中。只不过,在“文明的进程”中,包括法制、道德、习俗、习惯等因素限制了人的生物性*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当中有更为深入的分析。同样,科技哲学对这一做法有更多的论述,如有兴趣,可以从这个方面入手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最终人的生物性、原始性、动物性等被框定在了一个范围之内,如果超过这个界限,那么就意味着犯了墨顿所说的“越轨”,而作为同样具有生物性、原始性的人群,就会对他者的越轨进行处罚和谴责等,以告知其暴力行为的“不合理”。
其次,获得快感、复仇等。前文已经谈到,复仇作为一种反击,或者防御等都是暴力的一种模式。而犯罪学的理论认为,“快感也是暴力起因的一种”。也就是说,采取暴力是可以获得把对方击倒或者伤害,这其中或许就有一种非常痛快的感觉。用俗话说就是“爽”。而有的人为了获得这种感觉,反复地采取暴力,以逼退、恐吓对方。总之,无论是快感、复仇还是恐吓,暴力都贯穿其中,成为最表面的一种现象,往往这类现象有时候不被人们太过于重视。人们更在意的是“看戏”*鲁迅笔下的群众——围着看“砍头”的群众就是这类。。
再次,作为人性结构中的暴力,其主要是文化造成的。在社会化的塑造下,形成了自我,“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智模式。比如,张娜的研究认为,“校园暴力中的孩子,往往会从电影、电视剧、游戏等东西中学习、内化和模仿暴力,进而自己也采取了暴力的举动来处理日常问题”[7]。恰好是这些习惯,从孩子的社会化的初始阶段就不断地影响、塑造和勾起人本身所蕴含的暴力性。或者,从父母的暴力中学习(家庭暴力等),从而在“有什么样的老子就有什么样的儿子”的逻辑下,让自己也成为了暴力者的一员。这种不经意间地环境渲染或传染,往往就把暴力沿袭了下来,最后再暴力地对待家庭中的她者或他者。
其实,人性结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本文所认为的是,善恶在人性中本就存在,关键是其在人性结构中占多大的比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善是上升而恶是下降的状态?还有就是恶被限制的如何?比如,受过教育的人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暴力实施概率就要少一些,因为有素养进行限制,还有法治、道德等也同样可以对其进行限制*但是在家庭暴力中,最新研究发现,高学历的夫妻之间更容易发生家庭暴力,多半都是男性对女性。。所以,在人性结构之中的暴力,如果被类如《水浒传》中的“好汉”匪气所引发,又没有什么限制条件和自觉的调整自我的可能性,那么暴力作为恶的一种就会“跑出来”。
通过以上三种不同起因的分析,我们看到了暴力的起因,特别是内在的因素是哪些。但是,暴力又不是单一型的存在,而是多种多样。接下来,我们就暴力的类型进行分类和阐述。
三、暴力的类型:一种理想型分类
“在由暴力建立的政治架构中,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利,用暴力征用的一切都视为政治正当。这种由暴力制造的斗争场域就弥漫了一种文化,对于暴力的辩护成为权力专政的政治正当。”[5]这段话所要表达的是暴力的政治。其实,暴力的政治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说体罚学生就是一种。老师与学生的权力关系(政治性)是不对等的,学生往往是处于弱势,无论是在体力还是在给分数的层面,作为弱势群体的学生,因为粗暴的教育而被体罚,服从或许会得到比较好的“谅解”;但是不服从,可能会遭受更加严重的处罚,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暴力的政治。这是第一种暴力类型。
第二种是校园暴力。我们所说的校园暴力,并非仅仅是上述我们所列举的例子,而是暴力在学生的斗殴、毒打中体现出来。比如上文所述的:昆明某高校女生因怀疑舍友偷内衣,邀来同伙殴打舍友案例。采取人格侮辱的方式进行暴力毒打,而行动主体仅仅是孩子,是学生,这是非常难以想象的。有心理学家认为,“把这样的毒打者,也就是施暴者理解为‘霸王花’,他们所需要获取的是‘征服’”[2],甚至有的女性还必须一边跪着,一边唱《征服》,最后让施暴者自己满意了,她者才不至于被继续毒打。
第三种是家庭暴力,包括夫妻间的暴力、亲密伴侣暴力和婚姻暴力等,有时候,还存在交叉的现象[8]。在中国,家庭暴力因为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才得以被公开讨论和研究。一般而言,女性研究者认为家庭暴力最终的根源是权力和性别,所谓权力的因素就是父权制。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父权社会所导致的家庭暴力产生的根本原因。但是,社会学家并不认同。他们更多关注的是社会中的大规模的普通人群,所以有的学者的研究结果是,“门当户对的婚姻,夫妻平权的家庭,夫妻间暴力发生的可能性最小*还需要考虑的是,夫妻间的资源获取能力、不同家庭背景的实力等左右暴力是否发生。[8]。其实,家庭暴力的研究还有很多,特别是对性别、性格、婚姻状态、学历背景、力量、资源的多少(包括收入的多少等)进行多方面的分析。但是总的来说,家庭暴力作为暴力的一种在日常生活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暴力类型,比起其他暴力类型,其或许被关注的最多。笔者认为,之所以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主要原因在于两次“女权运动”*关于女权运动,可以看波伏娃等人的一些论述。。
第四种是网络暴力。网络暴力更多的是采取发帖,微博暴力则主要在微博社区里所进行的网络围观行为,是微博用户在利用微博传播信息的时候,有意或者无意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通常网络暴力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等合法权益,给当事人造成心理伤害或精神伤害[9]。有学者认为:“网络暴力又有点像《盗梦空间》里的那句台词:‘适应性最强的寄生物是什么?细菌?病毒?还是蛔虫?是想法。适应性最强,感染度高,一旦一种想法在脑海里形成,便难以消除。一个完全成型的,领悟透彻的想法扎根在脑海,萦绕不开。’”[10]这里所说的“想法”,在本文看来,其实是说的“人肉搜索”。要知道,“人肉搜索”作为网络暴力的一种,可以非常迅速地把对方所有可以搜索出来的信息告于天下。比如“白衣32号”就是一个例子。在其打人视频被曝光以后,其被“强奸”的视频(其实是性爱视频)也被翻出,甚至跳艳舞的视频、家庭地址等都被翻出。这是一种典型的通过网络的技术和平台,构成“侵犯隐私”“道德侮辱”的暴力事件。
第五种是基层暴力或底层暴力。所谓基层暴力就是指基层社会中的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冲突,采取的拳头,权势逻辑的暴力,还有村民与村民之间的斗打。但凡这两种暴力,都存在不和谐、不合理之处。比如说,我们在调查麻城T村的时候,村妇就遭受村干部派出的黑社会的殴打*刘晨:《麻城T村:村民权益抗争中的困惑》,《南方都市报》,2015年1月25日。。黑社会的成员主要是村民,他们是暴力实施的一种主体,但是背后的主谋——那个撑腰的人却是村干部。另外,在《村庄内亲兄弟的“反兄弟行为”》一文当中,笔者列出了两个亲兄弟之间的暴力行为,他们本身也是村民,也是底层百姓,却因为利益关系,而采取道德侮辱与相互厮打,一方把另外一方的裤子都脱得干干净净,这是典型的道德侮辱的暴力做法。人格侮辱的背后,暴力所呈现出来的张扬状态把亲情等因素遮蔽得一干二净*刘晨:《村庄内亲兄弟的“反兄弟行为”》,《中国乡村发现网》,2015年7月27日。。其实,基层暴力的行为又何止于此,比如我们在调查山西的土改时发现,1947年左右,地主被批斗的现象其实也是一种暴力,有的甚至被割掉生殖器,被石头活活砸死,被游街示众,被扣“反革命”帽子等等。还有在“反右”“文革”当中的类似举动,可谓是把人性结构中的“恶”全部释放出来,最终导致底层伤害底层,惨绝人寰*这些事实,是我们在调查山西省平定的土改中得到的口述史。鉴于其他因素,本文不列举具体的口述事实,仅仅对一些情况做大致上的介绍。在另外一篇英文文章中,我们会将这些情况分析和研究出来。。再比如,储卉娟(2012)所研究的暴力在乡村秩序中的“豪强化”,也意在说明,“强力人士”,以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力和控制力,向下瓦解传统秩序,向上借助国家法与国家政权,进行管控和自我利益获取,瓦解国家法秩序的合法性。这也是一种基层暴力或底层的暴力*见储卉娟:《从暴力犯罪看乡村秩序及其“豪强化”危险:国家法/民间法视角反思》,《社会》,2012年第3期。。
第六种是媒介暴力。2007年12月29日,北京某公司31岁的白领姜某从24楼跳下身亡,她在生前的博客中将自杀的原因归咎为丈夫的不忠,并在博客里贴出了丈夫王某和第三者的照片。随后,王某及其家人将天涯社区、大旗网等告上法庭,最终以原告胜诉收场。这可谓是“中国媒介暴力第一案”[11]。这其中的媒介暴力主要表现是,媒体试图通过自己的优势(特别是技术优势和信息优势),在“人肉搜索”时,不但不立即删除资料,试图基于道德立场与同情正义的角度来“助纣为虐”,继而伤害他者的私人生活和依法享有的权利,故而构成媒介的暴力。这样的暴力,有时候是可以和网络暴力重合在一起的。
第七种是符号暴力。符号是布迪厄的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其位于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之间,即把既定的社会结构内化为个人的心智结构,同时形成个人新的心智结构,实现对社会结构的重建。进一步而言,符号会在这样的过程中建立不平等的秩序,能够把资本、资源转为自我的利益,并且作为文化资本的符号暴力与被支配者资源结合,掩饰了统治本身的暴力性质[12]。
以上七种暴力类型,是笔者基于现有的研究和调查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个“理想类型”,或者是对暴力的“理想型分类”。因为知识的有限性,肯定不可能概括完全,但是大部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看见的暴力类型*然而,有的暴力类型也可以合并起来进行分析,比如政治暴力与符号暴力。但是,因为有的暴力类型又不单单指涉的是政治,可能还有社会、文化等,故而将其单独列出。。
然而,这些暴力之所以存在,原因除了我们上述谈到的人类的原始性、生物性,犯罪学意义上的分析及其贴标签、获取情感支持等原因外,我们还应该去深刻地认识,暴力产生以后的再生产是如何的。
四、暴力的再生产逻辑:两个案例的分析
很多时候,暴力可以从两个线条去分析,一个是从下到上的暴力,我们将其称为革命、造反等。比如太平天国运动*见裴士锋:《天国之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王伦起义*见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年的王伦起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另外一种是从上到下的暴力,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政治暴力等。如果前面一种暴力对后面一种暴力进行反抗,那么就是“以暴制暴”。而这样的反抗过程,我们可以从田野调查的经验中获取。2015年4月,我们在湖北麻城访谈一位长期在上访的村民时,他告诉我们,“实在没办法,我就把村支书炸死算了”[13]。从这个角度来看,如以基层暴力的类型而言,正是因为村干部的胡作非为,而上级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拖拉”等,导致农民产生了这样的心态或心理*更多内容见刘晨:《商议型治理:农民集体上访的政治遭遇与同意困境——基于安徽池州市东至县DJ社区(城中村)的实地考察》,《宜宾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进一步说,语言暴力本就已经产生了,比如他们口中的毒骂等,反倒因为这些因素,导致如今面临是否要再生产一次,从而走向犯罪、越轨等。
这样的事情,在邢朝国调查的村庄也有发生,“吴妈案件”便是其中之一。吴妈的儿子不在家,而邻居仗着力量大,蛮不讲理地把吴妈屋子旁边的一棵树砍了,结果吴妈的二儿子从上海回来(请假回来办身份证),在两次说起此事都无效以后,将其邻居差点打死。仅仅为了一棵树,吴妈的儿子坐牢了。起初村内的人都去劝和,包括村干部在内,甚至要求吴的邻居去道歉,赔偿一下算了。但是,这位邻居不干。而吴妈也去找马书记,也不管用。故而,这样的暴力生产与再生产,就是作为本文所述的“基层暴力”(村民伤害村民)的一个典型案例[14]。
那么,我们有必要把我们的调查经验和这个案例结合起来论述,以基层暴力为例,进行暴力再生产的分析*本文提到的这两个案例都可以算作底层的暴力事件。故而,本节皆为底层暴力的分析。。首先,暴力的产生大多都是因为利益纠纷,而不是天生的情感仇恨。恰好是因为利益冲突,导致情感之间的不和。我们在调查麻城T村和安徽池州的D社区(城中村)的时候还发现,都是因为村委干部的“乱作为”伤害到了村民的利益,故而村民对村干部有了情感的仇恨。其次,情感仇恨与申诉无门结合,导致情绪发酵。在利益表达机制不通畅的时候,起初的情感不满就会升级,因为找不到地方发泄,最后要么是认命,要么是继续上访,要么是“以暴制暴”。对于大多数被伤害利益的村民而言,采取更多的是上访,而不是认命*认命或不认命与地方的文化也有关系。比如大别山区的农民就有一种固执、拗劲。而安徽池州的农民,这种拗劲就相对弱一些。。再次,当反复地申诉无门,上告无效,心理承受达到一定极限,那么就只能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来处理原先的利益纠纷。作为调节者和处理问题的政府干部,不作为和拖拉,是以暴制暴的催化剂,甚至有时候自己也会成了施暴对象,或命悬一线。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逻辑。而且,这样的案例,已经越来越多见。比如《大河报》报道的一则新闻:“鲁山县梁洼镇北店村发生一起因邻里矛盾纠纷引发的持刀杀人案,截至今天中午12点,该事件已造成8人死亡。”[2]此种惨烈的方式对待利益冲突,就是基层暴力的典型。同时,还有村干部之间的互相伤害,村支书把村主任或者后者把前者一刀毙命。可以理解的是,暴力的再生产的原因多半在于利益无法得到满足,或矛盾达到了难以调节的地步。
这是否与我们在开篇中所谈到的犯罪学、生物学或社会学对暴力的理解和分析有一定的关系,是否施暴者是因为颌骨比较突出,还是因为可以通过这类的举措,得到快感、复仇或者其他?不难想象的是,我们的基层暴力,多半都不是天生的“暴力”,而是后天一步步形成的。甚至,情感的纠缠所引发的暴力,也类同此理。如果这样说是假设,那么我们可以再回到吴妈的案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起初吴的邻居在打架时将其假发揪掉,就已经是暴力了。从口头上的语言暴力(第一次暴力)演变为第二次暴力的产生,随后村里的人去调解,村干部去调解,马书记“拖拉”*夏余才在《是什么导致了一起农村杀人惨剧?》中谈道:“可在过去真正是‘群众无小事’,一些村干部也是白天黑夜的跑,去给群众解决邻里之间的矛盾。时下的一些村干部则早已是脱离了群众,也早已是‘唯利是图’,一心一意只想着自己挣钱,他们也没有把群众的‘家长里短’放在眼里。更有甚者,还会中饱私囊,还会与民争利,还会欺骗群众,以此达到个人谋取私利的目的。到一些村子里,你也会看到村干部的房屋,会是当地盖的最好的房屋。”http://hlj.rednet.cn/c/2014/05/22/3356119.htm,导致其儿子回来以后,力量顿时被充实,而把邻居打伤,这是第三次暴力,最后儿子被抓坐牢,而吴的邻居还骂吴是活该,这是第四次暴力。无论是打,还是骂,在本文当中都是暴力的类型。却因为每一步基本上都是错误的,故而最后导致了暴力的一次次被生产出来,以两败俱伤的局面结束。另外,在媒介暴力中、网络暴力中,不也一样吗?如果天涯社区能够把一些内容删除,以免侵犯原告王某的隐私权,那么也不至于暴力会被情感推波助澜为“人肉”。所以,很多时候,暴力的再生产,都与一些后期的不当处理有关,而又夹杂了少许的人类生物性、原始性。如果想避免暴力的再生产,就必须在中间环节或节点中,以“作为”“办好事”来切断暴力再生产的可能性。
五、总结与反思
本文先是对暴力的起因进行了分析,得出三种不同的缘由;其次对暴力的类型进行了理想型分类,一共有七种不同的类型,但是有的类型是在有的时候可以重合或交叉来理解的;随后又对暴力的再生产机制或逻辑进行了分析,并通过案例和田野调查的经验进行了逐个的分析和比较。最终我们认为,切断暴力再生产的可能性,需要在必要的时候“作为”,而不是“拖拉”。
虽然我们所谈论更多的是底层暴力或基层暴力,但是我们有必要把如今比较严重的校园暴力事件等纳入到其中加以讨论。中国政法大学的某学者就曾经指出,中国校园暴力的受害人大多以沉默应对,报警的受害人很少,这和校方往往“大事化小”的处理方式有关[13]。面对暴力,我们应该用法治的思维去处理。这恰好是本文的一个结论所在,因为我们在上文中也看到,对于基层暴力(农村的暴力、土改中的暴力、文革中的暴力、校园里的暴力等等),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没有法治的引入,或者人们的法治意识淡薄所致,最后导致两败俱伤。
更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不同类型的暴力,我们应该有不同的应对策略。比如,对于乡村中的暴力,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权威出面调解——上级政府的作为,而不仅仅依靠法治的介入就能解决,可能法治的介入还会引起相反的效果。同理,对于校园的暴力,更应该是教育为主。特别是教育,要尤其重视文明素质的培养,而不能让孩子习得家暴中的一些不好的方面,诚然,更要杜绝家暴的发生。
在此,就不一一列出对于什么样的暴力用什么样的方式比较合适。本文所关注的是暴力的起因、暴力的类型和暴力的再生产,特别是一些基层中的暴力尤其值得人们深思,并非仅仅是因为人性结构、生物学中的一些因素导致。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什么塑造了这样的人性结构,或许是制度,或许更多的是文化。
我们的文化塑造的“好汉”“侠士”,通过小说、电影、电视剧、图画、游戏等方式,最后在人们心灵结构中深深刻上了印记,甚至“造反有理”的流毒,依然在我们的观念中阴魂不散。这是通过各种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批斗哲学等所引发的“历史惯性”对社会的影响,可是我们自觉地反思还不够。这些,仅仅从现在的日常话语就可以发觉。关键是,道德侮辱的流毒伴随着暴力的行使,导致的又不仅仅是肢体上的受伤,还有心灵、精神上的伤害。在“没有从肉体上消灭”的年代里,这些心灵上的伤害,可能伴随一生。所以,对暴力的反思也就亟须进行。
[1] 汉娜·阿伦特.共和的危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75.
[2] 暴力女生:一种带毒的花[N]. 中国青年报,2015-08-03(B3).
[3] 校园女生暴力事件,残酷青春谁之过?[EB/OL].[2016-03-01].http:∥news.qq.com/zt/2008/xynsbl/.
[4] 河南母子深夜被打昏遭强拆,多部门被追责[N].新京报,2016-08-04(A1).
[5] 左春和.暴力的由来[EB/OL].[2014-04-17].http:∥www.aisixiang.com/data/74022.html.
[6] 邢朝国.情景、情感与力:暴力产生的一个解释框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24.
[7] 张娜.莫让校园暴力成为“关注暴力”[N].中国青年报,2015-07-27(C7).
[8] 马春华.性别、权力、资源和夫妻间的暴力:丈夫受虐与妻子受虐的影响因素比较研究[J].学术研究,2013(9):45-47.
[9] 刘晨.杜绝网络暴力[J].求是,2013(11):89.
[10] 江南.“删帖门”背后网络暴力[J].社会观察,2012(9):36-38.
[11] 郝雨,王祎.媒介暴力的正负效应及社会控制[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12-15.
[12] 毕芙蓉.文化资本与符号暴力:论布迪厄的知识社会学[J].理论探讨,2015(1):54-55.
[13] 刘晨.暴力下的“弱者的武器”为何是失效的:答《青年学术评论》主编沙柳坡先生[EB/OL].[2015-06-23].http:∥www.cssn.cn/zm/zm_shkxzm/201506/t20150623_2043283.shtml.
[14] 夏余才.是什么导致了一起农村杀人惨剧?[EB/OL].[2015-05-22].http:∥hlj.rednet.cn/c/2014/05/22/3356119.htm.
Causes,Types of Social Violence and Logic of Its Reproduction——AdiscussionbasedoneventofWumaandinvestigationofTvillageinMacheng
LIU Chen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999078, China)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causes and types of social violence, and the logic of its reproduction. Through analyzing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violence, we found that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structure of human nature, primitiveness and biological nature of human being.Seven kinds of different types of violence are concluded through the ideal classification of underlying violence, and it is further concluded, by way of the mechanism of reproduction, with "WM event" and "T village of city of MC" as examples,that the government′s "inaction" or "wrong actions" after the underlying violence is the main reason led to "violence against violence". Therefore, we should notice that preventing next violence is the key to put an end to violence. And we should introspect if the influence of system and culture on the shaping of our personality or the structure of human nature has caused violence under disguise.
violence;ideal type;cause;reproduction;culture
2016-05-30
刘晨(1988-),男,湖北荆门人,澳门大学博士生;澳门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农村廉洁建设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知识分子社会学、网络政治学。
10.16396/j.cnki.sxgxskxb.2016.09.005
C913.8
A
1008-6285(2016)09-0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