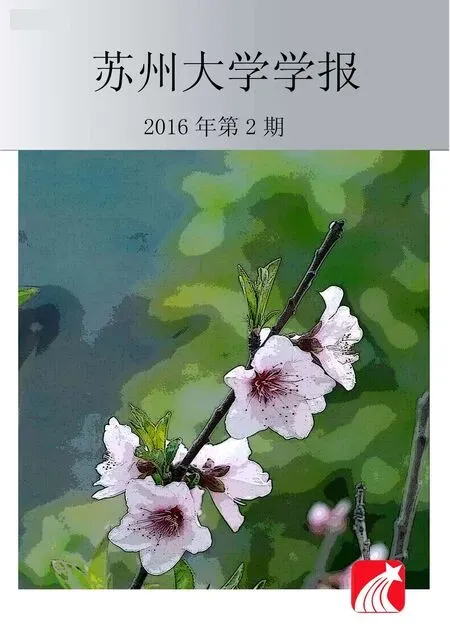健康型组织的概念、结构及其研究进展
时 勘周海明朱厚强时 雨
(1.中国科学院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 100190;2.中国人民大学 心理学系,北京 100872;3.北京联合大学 生物化学工程学院,北京 100023)
健康型组织的概念、结构及其研究进展
时 勘1,2⋆周海明2朱厚强1时 雨3
(1.中国科学院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 100190;2.中国人民大学 心理学系,北京 100872;3.北京联合大学 生物化学工程学院,北京 100023)
摘 要:健康型组织是国内外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的最新趋势之一,也在时勘博士承担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心理促进机制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本文首先回顾了从个人身心健康到组织健康的探索历程,回顾了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在组织健康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进展,特别是介绍了加拿大实施的健康场所的卓越框架,Salanova等人的HERO模型等内容,并重点介绍了时勘博士课题组基于我国新常态下组织变革的特殊要求,阐述了我国健康型组织研究的整体框架,并基于身心健康、胜任发展和变革创新的主要维度,提出了五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在此基础上,首先介绍了在健康型组织的概念和结构方面取得的一些实证研究进展。然后,根据健康型组织建设所涉及的胜任发展和变革创新方面的研究规划,分别提出了基于胜任特征模型的能力建设和职业发展研究、科学思想库、人才培养及科学普及的心理影响机制、基于网络媒体平台的社会心理行为的集成研究、社会心理促进模式示范性研究的中期进展及其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最后,讨论了健康型组织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健康型组织;HERO模型;健康场所的卓越框架;评估结构模型;社会心理促进机制
一、民族复兴的社会心理促进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并阐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高度关注,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也成为社会科学界的研究重点和热点。“中国梦”选题重大、内涵丰富,涉及多个学科领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心理促进机制,应该是从心理学、管理科学和信息科学学者进行跨学科合作探索的一个值得深化和拓展的专题研究。该项目定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心理促进机制”,拟以我国民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心理促进机制为主线,从历史、哲学和历代民众社会心理发展历程的视角,进行跨学科的联合探讨,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社会心理方面的影响机制,从而为社会和谐发展、经济发展和生态平衡提供有关人的社会行为的规律及管理决策依据,进而服务于国家的社会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科技创新与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一)民族复兴进程监测的评价指标体系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研究员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视角,提出了一个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监测评价指标体系。[1]该体系包含6大方面,每一方面赋予不同权重:经济发展(0.25)、社会发展(0.20)、国民素质(0.15)、科技创新(0.15)、资源环境(0.15)、国际影响(0.10)。在每一方面下,设置次一级的指标,例如经济发展下有“GDP与人口份额的匹配度”“人均GNI”“全球500强中国企业营业额”“上市公司市值占GDP比重”等4个方面的次级指标。他们运用该体系对不同年份的国家总体发展情况进行测算,得到相应的指数,以此作为民族复兴“进程”的监测指标。这套体系和测评方法具有综合、直观和量化的优点,将民族复兴具体到可见的指标和数字,通过这套指标体系,民族复兴在某一年份实现的程度,甚至速率都可以清晰地描绘出来。然而,它虽然也谈到国民素质等人的因素,但更多地是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对民族复兴进行分析,没有说明如何从社会心理角度出发看待问题,更没有从社会心理促进的角度来探索如何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需要被广大民众关注、参与和接纳的过程。如果将该体系的内容看作一种国民追求目标和动机的过程,那么它与社会心理历史变迁的考察具有更多的对应性。
(二)民族复兴的社会心理变迁
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民族在沧桑岁月中凝聚了56个民族13亿多人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共同创造美好家园所共有的民族精神及其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社会心理实际上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特定的社会存在决定了特定的社会意识,进而形成了特定的社会心理结构。[2]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孕育着中华文化和中华儿女,并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现阶段中国发展的历史现状和特殊国情也形成了目前中华民族独有的社会心理状态及其社会心理结构。它是凝聚一个国家或民族为整体利益而奋斗的精神纽带,因此探索社会心理结构的组成要素,并形成一个评估模型至关重要,对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中国梦的含义和民族复兴的历史渊源,可以从各个角度找到诸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研究。有从意识形态和政治理论角度出发的研究[3];有从思想史角度出发的研究,这方面汪晖的“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颇具代表性[4]15-22;有从民族性角度出发的研究,例如沙莲香所主持的中国民族性系列研究[5-7]1;有从本土心理学角度出发的研究,如朱永新对中国传统心理思想的梳理[8]41-54,不少港台学者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对中国人的心理变迁做了有益的探索[9]97-135。此外,从跨文化心理学角度,学界也对中国人心理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10-11]2-5我国2001年加入WTO、2008年举办奥运会,近年国家的GDP更是跃居世界第二。在三个阶段背后,很可能包含着社会心理的历史变迁,从民族的自卑到民族的自信,从艰苦自强到富足广交,从传统封闭到现代开放。沙莲香的“中国民族性”三部曲就是运用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分别立足于三个阶段去描绘国人的心理变迁历程,企图找到民族复兴在中国人本身人格中所蕴含的力量和发展的方向。[5-7]杨国枢等所倡导的华人心理学研究,更是从实证心理学的角度去系统地探讨中国人的传统心理及其面临社会变迁的适应机制,为团结中华儿女在社会心理促进上提供了有益的启发。[9]国内有影响的社会心态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末期。最初的研究因缺乏清晰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建构,成为对社会心态各个因素的调查研究的“拼盘”。进入21世纪中期,大型的相关项目相继展开,社会心态所具有的一些特性逐渐被研究者揭示出来。例如,杨宜音、马广海、王俊秀等针对社会心态概念界定、社会心态的心理结构、与社会心态相关的概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辨析。[11-14]进而,一些国家级、省市级社会心态项目的成果问世,跨学科、应用性的论文反映出社会心态概念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扩展性。如杨宜音、王俊秀主编的《当前我国社会心态研究》和王俊秀、杨宜音主编的《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较为系统地对社会心态的理论和一些专题领域进行了探讨,及时发布了相关调查报告,在国内外都形成了一定影响。[15]3-18社会心态研究在数量增加、领域扩展的同时,出现的问题是,冠以“社会心态”的研究数量不少,但各说各话、难以相互形成补充和对话。相形之下,具有理论意义和操作意义的成果却极为鲜见。
(三)民族复兴的社会心理促进模型
目前,从社会心理促进的角度,系统研讨分析民族复兴的研究还处于空白状态。遍查文献,除了前面提到的社会心理历史变迁、社会心态和个体幸福感之外,国内外有几方面研究可以为此提供启发性意见。中国梦不仅是个体层面的理想和幸福,更是社会和国家层面的整体民族复兴。中国梦不是美国梦,也不是其他任何国家的梦,具有独特的含义。从跨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中国人更加注重集体而不是个人,中国梦区别于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的梦的最核心区别是,中国梦不仅是个人主义的,还是集体主义的。早在30多年前,Hofstede通过不同国家价值观的广泛调查,提出“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核心文化差异,中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16]216-290后来,经过Triandis,Markus和Kitayama的发展,在价值、自我、思维方式、社会行为等多方面均证实了中国人以他人和集体为导向的文化基因。即使是旅居海外的华人,在长城、龙等文化符号的启动下,也会马上产生集体主义导向的心理和行为。[17-19]国内学者发现,甚至在有关记忆的脑激活和存储方面,中国人很自然地以母亲为参照,很明显地区别于美国人以自我为参照。[20]187-189来自港台的本土心理学研究反复地确认了一个共识,中国人是他人导向和社会导向的。[21]62-63因此,中国梦必然是包含了个人幸福、社会和谐和国家富强的非个人主义的民族复兴的宏伟梦想。然而,中国梦和民族复兴的社会心理究竟如何评价呢?它的具体内容和指标又有哪些呢?从组织行为的角度,探索从个人到组织、社会的健康水平的发展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二、从个人健康到组织健康
(一)组织健康的基本概念
关于健康的概念,世界卫生组织(WHO)1948年就在其成立宪章中有明确的阐述:“健康是一种在躯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美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状态。”[22]可见,健康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既包括身体健康,也包括心理健康;既有个人层面的健康,也有社会层面的健康。或者一个组织,一个国家,都有其健康的问题。类似这样的概念和研究近年已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近年来,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出现了组织健康(Organizational Health)的新概念。依据该概念,一个组织、社区和社会,如同人体健康一样,也有好坏之分。其衡量标准是,能正常地运作,注重内部发展能力的提升,有效、充分地应对环境变化,合理地变革与和谐发展。[23]此外,在组织行为学界,针对企业、社区、甚至社会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有关组织健康的标准,如关注目标、权利平等、资源利用、独立创新能力、适应力、解决问题、士气、凝聚力、充分交流等9项指标。这些指标不仅适用于企业,也适用于社区、甚至更大的社会范畴。时雨等将相关的理论运用到救援人员心理健康促进的实践当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4]综上所述,在宏观社会层面上研究社会心理促进的研究还比较少,已有的研究大多在概念上比较狭窄或者间接,不能涵盖并清楚揭示复杂社会互动的诸层面。尤其对于建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心理促进机制而言,可供借鉴的研究成果不多,但是,如果能够结合民族复兴的历史渊源、民族复兴进程监测评价体系、当前的社会心态评估,以及国民幸福指数几个方面,先行建立研究的基础,将更有利于建立综合的社会心理促进评价模型。
正如王兴琼所提出的,组织健康不仅仅涉及组织健康所涉猎的内容,而且还包括了组织外的利益相关者,比如社会责任以及客户忠诚等。[25]早期对组织健康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而第一个真正将组织健康进行定义的是Miles,他指出:“一个健康的组织,不仅在它所处的环境中生存,它更需要有长期的运行,并且能够持续发展和具有处理问题的能力。”[26]他是在分析学校这一组织的健康时提出来的,而在80年代前,研究的领域几乎都停留在对学校组织健康的研究上。而因此得出的组织健康的概念还具有很多局限性。到了80年代,组织健康在企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而此时对组织健康的关注,还主要是停留在强调企业短期的财务成功上,比如Clark等人认为:“组织健康是指组织成员自觉按照组织中未明确规定的潜意识行为进行工作,这些行为是能够确保组织维持现状以及促进其发展。”[27]这种对组织健康的提法只关注了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以及发展,员工在其中只是按照要求行事。虽然,在当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组织的发展,但是从长远来看,尤其是经济动荡和变革中,这种做法会阻碍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基于这样一种现实,Cooper和Cartwright将组织健康的概念向前推进了一步,认为组织健康的特征应该既包括财务上的成功(如利润),也应该包括健康的工作场所,在这里是指具有健康的和令人满意的工作氛围和组织文化。[28]从Copper等人对组织健康的理解来看,他们已经意识到健康的场所和组织文化与财务健康一样重要。因此,将组织健康的内涵进一步的扩大。后期的研究中,还是遵循这一理念,从两个方面来看待组织健康,只不过是在具体的细节因素上进行了区分,比如Ryff和Physical指出,组织健康既需要有公司的有效运行,同时还需要有生长和健康发展的能力。[29]
(二)组织健康结构的概念探索
组织健康的结构探讨源于20世纪末,当时由于对组织健康的概念和内涵缺乏统一的认识,还没有成熟和公认的组织健康的结构。Clark和Fairman试图将基于学校的组织健康的概念推广到企业等组织内,但是,由于测量上的问题以及组织之间的差异,结果不够理想。[30]此后Jaffe[31]对组织健康的结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包括组织绩效和员工健康的两维度结构。Bennett,Cook和Pelletiier等人根据生命周期论,将组织健康的结构扩大为四个方面,分别是肌体健康、情感健康、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32]另外,在结构上或者是有重合,或者是对组织健康的内部结构缺少内在的逻辑关系探索,很难对组织健康的成效进行检验。而在组织健康的结构探讨上,能总结以往研究的成果,并且以理论模型的形式进行呈现的要数加拿大的组织健康的卓越框架和Salanova的HERO模型。
(三)NQI有关组织健康的卓越框架
加拿大国家质量研究所(National Quality Institute,NQI)应用卓越框架来为组织的发展提供认证,这些认证内容包括了良好的企业指导和道德领导行为。组织采纳这个卓越计划后,会获得积极的成果,并且使组织变成健康型组织。在这样的组织里,他们的领导人能够理解在员工、客户和股东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组织为了承诺自身的责任会构建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这样的关系能够使组织在社会责任、员工健康和顾客满意度方面做得非常卓越。这一卓越计划实施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证实无论是在私立部门还是在公立组织当中,这一计划都使组织获得了成功。[33]该框架从三个维度出发,形成一条健康型组织建设的链条。在该结构中,组织通过自身的过程管理、有效领导,将焦点集中在员工、客户以及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身上,通过组织自身投入资源,进行健康环境建设,形成健康型的组织文化,培养出健康的员工和健康的客户以及供应商等群体,通过他们的满意程度进而不断地去提升自身的绩效水平。后来该模型接受了Moos的社会环境理论的观点,将事物看成是一个大的系统,系统与系统之间是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系统中的一部分的变化会影响到系统其他部分的变化。作为一个组织,要想使自身达到健康型组织的状态,必须将组织放在更大的系统或者结构中来看待。[34](见图1)

图1 NQI的健康场所的卓越框架
(四)Salanova有关组织健康的HERO模型
此外,HERO模型是有关组织健康的较为全面的结构模型[35],是一个启发性的理论模型,它整合了理论和实证的研究证据,包含了来自关于工作压力、组织行为学和积极职业健康心理学的研究成果。[36-38]这个模型被Salanova等定义为:“一个组织去做出系统性的、计划性的和积极的努力,进而去提高组织的以及包括他们的员工的实践过程,在此基础上获得积极的结果。”[39]根据HERO模型,一个健康、韧性的组织结合了三个主要的因素,它们之间相互作用:(1)健康的组织资源和实践(例如领导);(2)健康的员工(例如工作投入);(3)健康的组织结果(例如高绩效)。(见图2)。
总之,HERO模型整合了员工的健康和涉及的组织背景变量(例如工作要求、工具和技术以及社会环境)以及组织的绩效。这个模型告诉我们在理解组织的时候,组织是如何从实践层面上与员工的健康有关联;组织投资于员工的健康,会收获具有韧性的员工,高动机的员工;从结构和工作流程的角度来看,健康的员工会直接导向健康的和韧性的组织。最后,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看,HERO模型相较于以往,更为进步的一点是:考虑健康型组织的结果,它不仅包括了员工的健康,不仅仅是指他们所工作的工作环境,也包括了工作以外那些影响他们所在社区的健康这一结果要素。

图2 Salanova的组织健康HERO模型
三、健康型组织研究的整体构思
健康型组织研究的总体任务是,首先厘清影响民族复兴的社会心理因素,对健康型组织进行界定和操作性揭示,试图验证健康型组织是否包含身心健康、胜任发展和变革创新三方面,探讨民族复兴的社会心理机制,并探索基于智慧社会下社会网络媒体平台的民族复兴的社会心理行为的集成方法,试图在上述成果之基础上,通过健康型社区、职业智慧系统、危机应对的仿真模拟和科学普及梦幻基地等示范性平台,来验证本项目提出的社会心理促进机制的有效性,以达到促进健康型组织建设、促进民族复兴的目的。
四、健康型组织的研究进展
在健康型组织的研究当中,为了能够检验所建立的结构的有效性以及健康型组织建设的成效,采用科学的研究设计进行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从当前的健康型组织的科学研究上来看,大体遵循量化和质化两种研究思路。两种研究思路都将健康型组织的结构作为重要的变量来进行检验。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确立了健康型组织的有效性。

图3 健康型组织的结构探索的总体框架图
(一)健康型组织的结构及其评价有效性探索的研究进展
1.健康型组织的概念和结构假设
正如Newell所提出的,对组织健康的界定,必须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来进行。组织健康的内涵会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不同。[40]根据这样一种观点,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健康的考量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健康是身体、心理、精神和社会幸福感的一种完满状态,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健康的人能应对各种挑战,倾向于生活在幸福和建设性的生活中。正如健康的人所具有的活力、旺盛、稳健、兴盛、韧性和健壮一样,组织健康也是类似的。因此,健康型组织应该是一个包括身、心和灵三大维度的系统概念。在前已述及的民族复兴的评估指标的探索中,涉及国民素质、社会心态的概念均过于宽泛,因此,在已有组织健康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以把组织健康作为社会心态的切入点。目前,单纯检验组织健康就是没有疾病(生物医学的方法)的工作已经逐渐发展到工作场所的积极因素即员工健康、幸福感和绩效的影响。因而从身心灵全人健康的角度,来探索健康型组织建设的问题,应该是民族复兴事业社会心理促进机制的关键。2004年8月16日,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时勘研究员联合中智德慧、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美国、香港学者,在北京召开了《心的力量、新的成长:建设健康型组织论坛暨第二届中国EAP年会》,与会专家总结了国外员工援助计划(EmployeeAssissment Program)引入我国企业后开展组织健康研究的经验,并讨论了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组织兼并、重组、裁员、新管理手段的运用等带来的冲击等。时勘等人首次提出了健康型组织建设的新概念,倡导把我国的组织健康工作提升到“身心健康、胜任高效、创新发展”的健康型组织,以推动组织不断适应环境变化,达到创新发展之目的。经过十余年的系统探索,目前健康型组织建设的评价结构定位于身心健康、胜任高效和创新发展三大维度。[41]研究者认为,“健康型组织是指一个组织能正常运作、注重内部发展能力的提升,并且有效、充分地应付环境变化以及开展合理变革。”[9]在这一评价结构中,不能孤立地谈身心健康这一维度,其他两个维度是实现身心健康的重要保证。具体而言,胜任发展是实现企业发展和保证员工福利待遇的基础,而变革创新则是通过一种组织文化建设,即不断地追求创新,体现社会责任,来保证组织不断创新和长远发展。(见图3)
2.评估工具及方法的探索进展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在检验健康型组织的结构方面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共同方法偏差可能对健康型组织结构的影响。因此,在进行问卷调查等环节,采用了领导与下级匹配的方式来对各个变量进行测量。比如,在重庆渝中区以及广州东莞国税系统和中国铁路总公司的调查中,都采用了上下级配对的方式(结果见表1)。由表1可见,为了避免在调查中的共同方法偏差,上下级配对之后,针对上下级采用不同的量表来进行测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充分避免了统计结果对结构效度的影响。

图3 健康型组织评价结构模型

表1 健康型组织的结构量表
(二)“基于胜任特征模型的能力建设和职业发展”的研究进展
1.多重匹配性因素对职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试图从员工与环境的多重匹配性因素出发,探索员工与环境的多重匹配对新入职员工职业适应性的影响、对老员工组织的认同、工作投入和对组织满意度的影响,以及多重匹配因素对团队效能和团队凝聚力的影响,并基于多重匹配因素开发出能够提高P-O匹配、P-J匹配、P-G匹配和P-S匹配的干预方案。干预研究选取四川某职业学院即将入职(首次实习)的学生400人,四川某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实习生240人,山东、浙江两家企业的员工共计300人,作为干预对象。多重匹配因素对员工行为有效性影响的验证研究发现,员工获得与组织的匹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新员工培训体系中,应当比现在更加重视人际关系管理培训和沟通技能培训模块,提高初入职员工P-S匹配和P-G匹配水平。在入职半年后要加强企业文化培训,提升员工P-O匹配程度,从而进一步提高员工职业适应能力。此外,企业应该高度重视员工的职业适应和职业发展的问题,这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智能转型,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2.抗逆力结构及其组织与员工促进研究
本研究重点选取金融业信息化主管、医护人员、交通警察和科研人员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探索现代都市不同行业人员,在社会转型期的压力源及其社会心理(抗逆力和工作幸福感等)的结构要素,揭示了抗逆力对其工作心理与行为影响机制,形成不同行业人员的压力应对策略和方法及针对的组织与员工促进计划(OEAP),较好地解决工作压力导致的心身耗竭问题,提高其工作幸福感、工作投入和工作旺盛感水平。特别是项目组在上海静安区抽取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上海市儿童医院、静安区中心医院、静安区老年医院、静安区曹家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静安区南京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家不同等级医院380名医务人员参加多轮的心理学问卷调查之后,项目组设计了医务人员抗逆力提升项目,干预提升项目主要形式为心理学讲座、团体活动和讨论分享,每次活动后并布置相应的课后练习。“情绪管理”模块主要帮助学员体验积极情绪,塑造积极品质,让学员在习得发现快乐和调控负面情绪技能的基础上,发现自我价值,对工作和生命意义产生新的领悟;“自我效能”模块主要帮助学员改变不合理信念,增强自我接纳和提升自我效能感;“压力应对”模块则帮助学员正确认知和管理工作压力。“沟通合作”模块重在提高沟通能力、加深人际联结,体验换位思考、加强信任与合作意识,并培养协作能力。目前,干预研究已经持续1个月,得到了广大医务人员的支持和积极参与,项目组正采用实验组与控制组前后测的方式对方案的有效性进行验证,有关追踪研究有效性结果正在分析之中。
(三)“科学思想库、人才培养及科普的心理影响机制”的研究进展
1.领导行为和科研团队创新的关系探讨
本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试图通过系统科学的调查,比较全面、准确地了解科研团队创新管理的现状。研究内容包括科研人员的创新心理和行为特点,领导风格和团队氛围对科研人员创新行为的作用机理,建立影响科研人员创新行为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模型,并初步提出缓解科研人员工作压力和建设科研团队创新文化的管理建议。探索科研人员在创新活动中的心理和行为,了解科研人员对现状的满意度、对领导风格的匹配程度和对自主决策权力的需求,界定目前科研院所创新氛围的状态,有针对性地塑造领导风格和制定有效的管理措施,有助于促进科研人员在创新活动中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心态和行为。调查结果为进一步设计科研人员创新行为的激励机制提供数据支持,为改善管理提供现实依据,对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行为,提高科研院所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2.科学普及的心理促进机制研究
该研究正在设计“有效促进我国科学普及工作的社会心理机制研究”的方案。初步考虑从个体层面探究科学普及效果的社会心理促进机制,从群体层面探究情绪感染、群体规范等因素对科学普及效果的影响。最终,构建促进科学普及工作的社会心理机制多层模型,并提出了以学业情绪为切入点开展研究和以“最近发展区”为视角开展研究的策略,有关调研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最近的研究进展表明,科学普及教育需要加强学生的审辩式思维能力的培养,此外,权威的公信力与科学普及教育的信任构建的关系也正获得高度关注。对于科普教育的传授者和接受者,双方都缺乏一种运用理性的勇气,如果科普工作者能够认识到现阶段公众自身科学素养的局限以及公众接受信息的认知偏向性,用针对性的传播方法和诚恳真挚的态度进行科普;同时,如果公众能够摒弃在公共知识领域的逆反心理,遵循逻辑,克制情绪,信任关系的建立是指日可待的,科学普及工作的进程也能得到飞跃的发展。
(四)基于网络媒体平台的社会心理行为的集成研究进展
1.社交网络有效性的相关基础和方法研究
本研究探索如何从大量的用户评论中发现一个高质量的覆盖不同意见的代表性子集,并将该问题转换成集合覆盖问题。从理论上证明了ISP算法的计算时间成本总是小于全对SimRank的计算时间成本。研究人员在合成的和真实的数据集上进行了广泛的实验,证明了该方法准确性和效率。还为社交网络普通用户生成兴趣标签的方法,不需要利用用户发布的文本信息。即只要用户关注了少量的流行用户,就能够为其推荐标签。通过该方法,也可以为缺失信息的流行用户生成相应的标签。经比较实验发现,该方法生成标签的质量在准确率和召回率方面都优于现有的方法。
2.安全心智培训集成系统的示范型基地建设
安全心智培训集成系统是根据“情景—应对”的国家应急平台体系基础科学问题集成升华研究平台的对接要求,基于危险性识别、脆弱性分析和抗逆力评估等集成分析方法,建构客观环境指标和主观心理指标的融合模型,面向煤矿等生产性行业各岗位员工完善的抗逆力模型及其相关的评估问卷测评—培训系统。该研究在系统集成研究中提出了心理行为耦合模型的构思,在集成系统中,将获得的心理行为数据的挖掘、分析与心理测量的常模、心理行为实验获得的因果关系模型分析结合起来,从而使集成系统的分析功能得以增强,在此基础上,为社会心理促进的总集成平台提供了流程分析、数据挖掘和应急管理过程分析的集成方法软件的编制方案。安全心智培训集成系统主要分为需求分析系统与安全心智培训系统两大部分,其中,需求分析系统主要能识别生产过程中的风险源、发现生产环节中的脆弱性因素,并通过对个体的基本能力、人格特质、情绪心理、抗逆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以此确定特定岗位的胜任特征要求,进而制订个性化培训方案。在培训模式上,创造了安全心智培训七步法来达到受训者心智重塑的目的。安全心智培训主要包括目标定向、情境体验、心理疏导、规程对标、心智重塑、现场践行和评价反馈等七大环节,强调根据个体差异进行培训和效果评估,为制定和实施个性化培训方案提供依据,并且对于企业的安全管理提供全面、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支持。该项目已经获得1项山东省软科学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和1项省部级领导的批示。2015年9月22日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专门印发了关于山东能源集团肥城矿业公司安全心智培训经验材料的通知(煤安监司函办〔2015〕25号),要求全国各产煤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管部门,有关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有关中央企业学习和借鉴山东能源集团肥城矿业公司的安全心智培训模式,以提升安全管控水平。
(五)社会心理促进模式的示范型基地的研究进展
1.健康型城区建设的示范性基地研究进展
早在1900年,世界卫生组织针对全球范围内人口的老龄化问题提出了健康老龄化这一长远的战略目标。健康老龄化要求老年人四个层次的健康和各层次间的相互和谐,它们是老年人的单个个体,老年人所组成的群体,有老年人的家庭和整个老年社会。依赖于健康老龄化的推进,积极老龄化又有了更深的内涵,是指老年人在健康的基础上,积极地参加社会性的活动,从而提高其生活质量和强调生命质量,让老年人身心俱佳。而和谐老龄化则从关系和谐的角度来看待老龄化问题,只有老年人的家庭、人际以及整个社会关系融洽了,才能真正使老年人更幸福。由此先后开展了老年人社交网络和健康的关系研究、老年人认知障碍及社会交互作用机制研究,有关MPFC在社会交互过程中理解他人方面的作用的成果发表在2014年的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杂志上。此外,结合老人的社会需求,还开展了临终精神和心理关怀的研究、丧亲人群的社会支持研究。目前,实验基地上海市静安区卫计委课题组已经拍摄完成《担当》的记录片来迎接2016年在上海召开的世界健康城区大会。
2.职场排斥和融合的现场研究进展
截至2014年9月,广州市荔湾区辖内登记流动人员30.1万人,其中城镇户口9.5万人,占总人数的31.5%;农村户口20.6万人,占总人数的68.5%。主要来自广东、广西、湖南、四川四个省。目前,已登记在册的出租屋15.9万套,除居住在企事业单位、工厂的外,约有25万人居住在出租屋内。针对这一问题,民政局开展了一系列流动人口出租屋管理工作。正在进行的珠江三角洲社会融合促进模式研究,采取实地调研的方式对社区居民进行入户问卷调查,结果发现,职场排斥和社会融合的对立面,是阻碍社会融合的重要因素,并发现了影响社会融合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荔湾区民政局等部门采取了有效的应对措施:首先,建立了“党政领导,部门参与,保障有力,综合治理”的工作格局。全区组建了一支近550人的协管员队伍,协助有关职能部门做好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服务工作,形成“上面有人抓,中间有人管,下面有人干”的局面。其次,摸清情况,落实经常性管理措施。实行居住登记、办理居住证、建立流动人员和出租屋档案、通报协查、巡查走访、检查验证等措施,把出租屋分为重点户、一般户、放心户等层次进行分类管理,特别是对无业和有过不轨行为的重点户严加注视,管理效果较好。再次,对流动人员开展服务,对违法犯罪分子坚决打击,司法部门、工会提供法律援助,开展维权活动,计生部门为育龄妇女免费提供避孕药具,劳动部门帮助外来工工伤事故理赔、追讨欠薪、岗位培训和提供免费职介等。并据此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如该区对于流动人员与出租屋的管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行了有效维护,也有力地打击了违法犯罪分子,出租屋内刑事治安案件发案同比下降21.5%,这些管理工作对该区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和谐生活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民政局的举措不仅仅解决了外地人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改变了本地人对外地人的偏见。这些措施实行两个月后,项目组再一次对荔湾区的社会融合状况进行了调研,欣喜地发现大多数外地人都对这些举措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家参与社区工作的意愿更加高涨,工作时再也不用和城管“打游击”了,大家一致反映:“这里越来越有家的温暖了!”这些举措还得到了广州市委、政府的表彰,以及《南方日报》等新闻媒体的多次报道。
五、阶段性成果与研究展望
(一)阶段性成果
在对我国新常态下的健康型组织建设的探索中,共正式发表学术论文42篇,其中SCI或SSCI 9篇,核心期刊33篇;作为实践应用型成果,两次论坛《人力资源》增刊分别发表53篇(2015年,第390期)和48篇(2016年,第396期),出版学术专著或教程共5部,获得部委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全国管理学大会奖1项;还获得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同志批示1项,省部级领导批示1项,报送全国社科规划办《工作简报》2项,达到了预期目标。
(二)未来研究展望
将健康型组织的概念、结构及其评估反馈系统的系统研究作为承担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心理促进机制研究”这一课题的核心内容。由于该项研究涉及跨学科、多地区,理论探索和实践并行,整合难度较大。从目前的研究进展取得的初步结果来看,需要改进的问题主要是:
第一,关于健康型组织的概念和结构探索问题。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方面的研究结果还是不完善的,虽然已经被较为广泛地使用,但概念所包括的内容是否精确理解无误、测量方式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反馈模式是否有针对性而且持续开展,是亟待深入探索的问题。目前,组织的类型、文化和重视程度存在诸多差异,成为保证健康型组织建设的障碍之一。因此,需要通过较为系统的理论模型建构来规范目前的健康型组织的测量模型。此外,概念的不确定性也可能会导致研究者和企业管理者使用了不同的概念(如健康场所、健康工作组织,健康发起站,企业健康,健康型文化/氛围)。因此,界定健康型组织的概念和评价模型是今后本领域研究取得突破的关键,真正使之与其他概念得以稳定的区分。[42]30-37此外还需指出,目前采用的有关健康型组织各维度的关键概念多为描述性的,源于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对健康型组织结构的一些核心概念的修订如何考虑我国的社会文化背景、特别是目前高速变化的新常态背景、经济下行时期的独特情况,还需要更为系统的和扎实的探索工作。
第二,关于健康型组织建设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根据前面的讨论,很自然地考虑到要关注健康型组织所处的文化背景。从文献分析结果可以发现,西方发达国家一直秉承的是组织健康的视角,虽然在他们的假设模型中也涉及组织外的健康问题,如社会责任和客户忠诚等概念[43],但是,这些因素的外部环境影响机制探索的并不深入。此外,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劳动政策,特别是存在于民众心目中社会心理变迁因素,这些都是我们不得不关注的差异问题。此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幅员辽阔的大国,不仅仅是行业差异,地区差异同样不可忽视。从这个意义上讲,更应该从我国的文化特点和时代背景出发,继续深入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健康型组织结构。一个支持性的高效率的组织,增强环境因素的促进作用,以提升员工和组织的产出,是需要解决的刻不容缓的任务之一。
第三,关于健康型组织的数据模型检验问题。为了更有效地获得研究支持,特别需要解决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在前一个阶段采取的上—下级配对取样方法,经过对问卷的反复修订,力图保证数据获取的真实性问题。也就是说,在横断研究当中,要尽可能保证数据获得的多元性,即从多种来源的角度来收集数据,因此,健康型组织评价工具考虑将自评、他评的问卷配合使用。同时还尽可能获取来自客户的评价数据,以避免测量中的称许性问题。此外,在数据的分析层面上,应该尽可能地采用多层线性模型来探索跨层数据的影响机制,比如 除个体层面的数据分析外,更应该考虑在群组层面或者是组织层面的效应问题。总之,通过被试来源的多样性以及数据分析的跨层方面来保证避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但是,在获取有效性的数据当中,尤其是在检验健康型组织的成效当中,纵向研究设计是理想的选择。[44]正如Marisa Salanova所提出的,在检验HERO模型的时候,使用纵向研究设计来检验HORP(组织的投入,比如自主性和人际资源等),健康的员工和健康型组织的结果之间随时间推移所呈现出来的关系将是更为可靠的。
第四,关于数据的采集方式问题。有学者提出,建立好具有及时反馈功能的评价系统,可能对于有效提升组织管理水平也是至关重要的。[45]最近的研究在采用大数据和机器智能方面也开始做类似的探索,遇到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一方面,参与网络调查的人员未必能够完全代表所在组织的员工,可能会削弱调查数据的外部效度;另一方面,由于是在虚拟环境中对于调查问卷进行回答,能否更好地保证获取数据的真实性,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不过,目前由于AlphaGo相关的一些机器计算产品的问世,人们也更加倾向于在组织评价中采用更多的网络数据的收集方法,这些评估方法究竟孰优孰劣,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参考文献
[1]杨宜勇,谭永生. 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测算[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2,(16).
[2]许苏民. 论社会心理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J].中国社会科学,1983,(7).
[3]程美东,张学成. 当前“中国梦”研究述评[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2).
[4]汪晖. 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M].北京:三联书店,2004.
[5]沙莲香. 中国民族性(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6]沙莲香. 中国民族性(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7]沙莲香. 中国民族性(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8]朱永新. 心灵的轨迹:中国本土心理学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9]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 华人本土心理学[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10]Bond M H.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11]Chiu C,Hong Y. Social Psychology of Culture[M]. New York:Psychology Press,2006.
[12]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J].社会学研究,2006,(4).
[13]马广海.论社会心态: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J].社会科学,2008,(10).
[14]王俊秀,杨宜音,陈午晴. 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报告[J].调查与研究,2007,(2).
[15]王俊秀,杨宜音.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6]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inking and organizing[M]. Beverly Hills,Calif:Sage,1980.
[17]Triandis H C. The self and social behavior in differing cultural contexts[J]. Psychological Review,1989,96(3).
[18]Markus H R,Kitayama S. Culture and self: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emotion,and motiva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1991,98(2).
[19]Hong Y,Morries M W,Chiu C,et al. Multicultural minds:A dynam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culture and cognition [J]. American Psychologist,2000,55(7).
[20]朱滢.文化与自我[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1]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2]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reamble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s ado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Conference[J]. New York,1946,(6) .
[23]时勘,郑蕊. 健康型组织建设的思考[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49).
[24]时雨,时勘,王雁飞,等.救援人员心理健康促进系统的建构与实施[J].管理评论,2009,(19).
[25]王兴琼,陈维政.组织健康:概念、特征及维度[J].心理科学进展,2008,(16).
[26]Argyris C. The organization:What makes it healthy?[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59,1(3).
[27]Clark J V. A healthy organization[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wiew,1982,4(4).
[28]Cooper C L,Cartwright S. Healthy mind;Healthy organization-A proactive approach to occupational stress[J]. Human Relations,1994,47(4).
[29]Ryff C D,Singer B. The contours of positive human health[J]. Psychological Inquiry,1998,9(1).
[30]Shuck M B,Rocco T S,Albornoz C A. Exploring employee engagement from the employee perspective:Implications for HRD[J]. Journal of European Industrial Training,2011,35(4).
[31]Jaffe D. The healthy company:research paradigms for 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al health[J].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Washington,1995,(5).
[32]Bennett J B,Aden C A,Broome K,et al. Team resilience for young restaurant workers:Research-to-practice adaptation and assessment[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2003,15(3).
[33]Dan Corbett. Excellence in Canada:Healthy Organizations—Achieve Results by Acting Responsibly[J]. Jou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4,55(2).
[34]Moos R H. Context and coping:Toward a unifying conceptual framework[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1984,12(1).
[35]DeJoy D M,Wilson M G,Vandenberg R J,et al.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healthy work organization intervention[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2010,83(1).
[36]Llorens S,del Líbano M,Salanova M. Modelos teóricos de salud occupational[J]. Salanova M. Psicología de la Salud Ocupacional,2009.
[37]Salanova M,Llorens S,Cifre E,et al. We need a hero!Toward a Validation of the Healthy and Resilient Organization (HERO) Model[J]. 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2012,37(37).
[38]Vandenberg R J,Park K O,DeJoy D M,et al. The healthy work organization model:Expanding the view of individual health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kplace[G]// Perrewe P L,Ganster D C. Historical and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stress and health,2002.
[39]Salanova M,Llorens S,Acosta H,et al. Intervenciones Positivas en Organizaciones Positivas Positive interventions in positive organizations[J]. Terapia Psicológica,2013,31.
[40]Newell S. The Healthy Organization:Fairness,ethics and effective manage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lection & Assessment,1998,6(1).
[41]时勘,周海明,朱厚强,等.健康型组织的评价模型构建及研究展望[J].科研管理杂志专刊,2016,(S1).
[42]Halbesleben J R B. A meta-analysis of work engagement:Relationships with burnout,demands,resources and consequences[M]// Bakker A,Leiter M. Work engagement: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ory and research,2010.
[43]He Y,Li W,Lai K K. Service climate,employee commitment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2012,23(5).
[44]Salanova M,Agut S,Peiro J M. Linking organizational facilitators and work engagement to extra-role performance and customer loyalty:The mediation of service climate[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5,90(6).
[45]Torrente P,Salanova M,Llorens S,et al. Teams make it work:How team work engagement mediates between social resources and performance in teams[J]. Psicothema,2012,24(1).
[责任编辑:江 波]
作者简介:时勘(1949— ),男,湖北枝江人,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心理、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心理促进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3&ZD15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B849;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16)02-0015-12
收稿日期:2016-04-20
通讯作者:⋆时勘,E-mail:shik@psych.ac.cn。
The Healthy Organization:Concept, Dimensions and Research
SHI Kan1, 2ZHOU Hai-ming2ZHU Hou-qiang1SHI Yu3
( 1. School of Economical & Manage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3.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College,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3 , China)
Abstract:“The healthy organization” is a major research area of th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zational practice during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in China. The paper reviews the shift of focus of exploration from personal health to organizational health and major development of studies in this regard, especially Salanovas' HERO model, Excellence Framework for Healthy Place of Canada, and the Three-Dimensional-Nine-Factors model of the health organization of Shi et al. It introduces the latest development in positivistic studies of the structure and concept of the healthy organization,and proposes the gener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ies of the healthy organization in China as well as five research areas on the basis of personal health, competence and innovation. It discusses competence model-based capacity building and career development studies,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mechanism of think tanks, talent development and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tegrated studies of online mass media-based social-psychological behavior, and the demonstrative studies of social psychology promotion. It also points out some qu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regarding the healthy organization.
Key words:healthy organization; HERO model; excellence framework of a healthy place; evaluation model;promo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psych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