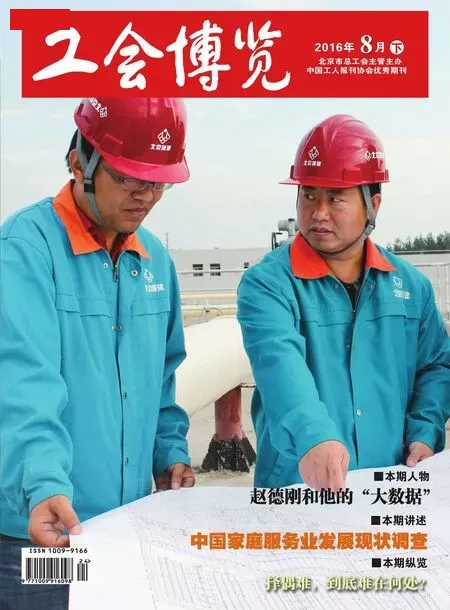唐山大地震:孤儿的艰难自我救赎
唐山大地震:孤儿的艰难自我救赎

1976年7月28日,里氏7.8级大地震在唐山爆发。40年前,这个真实故事的小主人公们在大地震之后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和灾后重建生活呢?这些年他们又是怎样生活的呢?
地震过后,唐山、石家庄和邢台等地立即在最短时间内建立了5所孤儿学校。其中,石家庄育红学校的故事最为大家所熟知,这所规模最大、设施和管理最好的特殊福利院,存在了8年之久,600多名孤儿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童年。
十天为孤儿建家:“那是个凭空创造的奇迹!”
1976年8月28日,唐山大地震刚刚过去1个月,时任石家庄第二中学党总支书记的董玉国接到了市领导布置的一项特殊任务:“筹建育红学校,为唐山地震孤儿们建个家。”第二天,作为育红学校党总支书记的董玉国奉命前去报到时,所谓“育红学校”还只是个概念,没有地址,也看不见任何东西。他唯一知道的是,10天之后,第一批唐山孤儿就要到来。
当务之急就是选址,“开始推荐的是救济院,但考虑到离市区较远,最终选择了位于长征街的工人政治学校。因为考虑到工人政治学校是个小二层楼,有25间房,还有一些平房,一个小礼堂,比较适合做封闭式的学校。”董玉国老人回忆说。
地址选好了,各类人员也需要很快配置起来。在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里,董玉国要与另外两名负责人从171个单位紧急抽调260多名有经验的优秀教职员工。
“我记得当时市领导有这样一句话:‘人员到位要快。谁不愿意被抽调,就带他去唐山看看,看看那里的废墟,看看那里的孩子们。然后,回来接着干!’”这句话董玉国老人记忆犹新。
9月6日,第一批孩子被褥还没有备齐。市里把一大批布拉到桥东区,让街道组织赶制。7日早上,几百条崭新的被子、褥子就送到了育红学校,有汽车拉来的、自行车驮来的、手推车推来的……与此同时,唐山孤儿要来的消息,震动了整个石家庄市。各行各业的人争相出人出力出钱,在短短十多天的时间里,桌椅、床铺、教学器具均已到位。“解放路商场,只要我们这里需要什么东西,打一个电话就立即送过来。”从新华区文教科临时抽调的刘俊琴说。粮店送来了最好的细粮,菜店送来了最新鲜的蔬菜,肉店送来了最好的肉。
“那时,市领导有这样的要求:孩子们进门应该要什么有什么,和家里没有任何区别。”董玉国说,“就连孩子们的小梳子、擦脸油什么的小物件,都一应俱全,摆放得井井有条。”房管局的人粉刷了房子,打扫卫生,学校老师、员工的调动,十天,全部到位!“那是个凭空创造的奇迹!”多年后,董玉国这样感叹。
面对欢迎人群,孤儿们异乎寻常的成熟
正在石家庄热火朝天准备之时,几百公里外的唐山,孤儿们怀着忐忑的心情踏上离家的路。9月8日清晨,天有点儿阴。火车站广场上人很密,所有的孩子都穿着蓝色的衣服,胸前挂着写上了姓名、年龄、籍贯的白布条。那么多孩子忽然聚集到一起,四处是尖细的叽喳声。不少孩子细细的手腕上有两只手表,那是父母的遗物;有的孩子坐在破行李卷上,守护着家里仅存的财产;还有许多孩子,脖子上挂着缝纫机头,重物压弯了他们的腰。他们每个人都背着一只鼓鼓囊囊的新书包,里面装着各个收养单位送的水果、点心、日用品。

火车开动了,带着这一路的祝福,孤儿专列驶进了石家庄火车站。为了拉近和孩子们的距离,接站的董玉国操着一口唐山话跟孩子们说话,这些孩子看着他一愣,一些很小的就争着喊他爸爸,董玉国搂着孩子们就掉下了眼泪,说:“我是你们的爸爸,我就是你们的爸
爸。”多年后,很多已经长大的孤儿们还是管董校长叫爸爸。
在育红学校里,绿豆粥和炸油条早已准备就绪,洗澡水也准备好了。但是孩子们没一个吃的,很多年纪小的哭着叫着要回家找妈妈。一位育红学校的老师回忆:“孩子们有的头砸伤了,有的胃膜砸伤了,还有出疹子发高烧的,还有急性肝炎的,状况都很不好。”孩子们洗完澡,服装厂和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就在那儿等着了,要给他们一个个量衣服鞋子的尺寸。衣服连夜赶制,第二天早上7点,每个孩子的枕头边都放了三套新衣服。唐山孤儿们坐着大轿车进入市里为他们举办的欢迎会会场。花环队、花束队、腰鼓队、老人、娃娃夹道欢迎,这些历经苦难的孩子们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成熟,没有哭闹,没有混乱,有的孩子甚至还在车上向欢迎的人们招手。
在欢迎大会上,一个13岁的男孩上台致辞,他一上台,台下就有人哭了。男孩却能控制住自己,一板一眼,讲得清清楚楚。只是说到“爸爸妈妈死了,是解放军叔叔救了我”时,他掏出手绢擦开了眼泪,但却咬着牙没哭出声,又接着讲下去。
石家庄和唐山两地的小朋友的同台演出,让会场上悲伤的气氛达到了顶点。观众哭,在后台的大人也哭,为孩子们伴奏的老师们哭成一片。坐在台下的市委书记情绪过于激动,突然冠心病发作,昏倒在地!

9月28日,第二批地震孤儿183人也从唐山来到石家庄育红学校。29日,第三批153人也来了。开办“育红学校”,使石家庄成为全国集中救助唐山地震孤儿最多的城市。有资料显示,从1976年9月7日首批接收,到1984年“育红学校”结束其历史使命,8年岁月中,共有650名唐山孤儿在“育红学校”生活、学习。这些孩子当时年龄最大的不到16岁,最小的仅仅6个月。
现实版孤儿“方登”: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
在电影中,大地震并没有让“孤儿”方登命丧黄泉,妈妈的一个撕心裂肺的选择却把她打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整整32年未曾走出。现实中,唐山孤儿的心理状况更加令人担忧。
一般情况下,70%有创伤经历的人即便没有经过任何心理辅导,也可以在半年或几年后自然痊愈;而另外的30%,则会在心理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可能从创伤发生的一瞬间一直延续到几十年之后,一部分会表现为抑郁、疲乏、惊恐、焦虑、酗酒、失眠、进食障碍等症状。最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国内的心理干预、心理救助领域还是空白。
“还是在孤儿院的时候,常梦见父母遇难时的样子。醒来,就会不知道自己在哪里。”那时候,唐山孤儿李宝霞脑海里总会看见母亲那张蜡黄的脸,然后是父亲的鼻子和嘴,上面都是血。还是小姑娘的宝霞离他们很近,能看到他们没有呼吸。福利院物质生活的充裕并不能弥补他们精神上所遭受的创伤。这些在异乡的孤儿过早地懂得了察言观色,如履薄冰地生活。其中,只有6个月大的唐山孤儿党育新的成长经历,是他们中尤为典型的一例。被解救后的党育新和500个唐山孤儿被送到石家庄育红学校。在这里,三个没名儿没姓的娃娃被重新起名党育红、党育新、党育苗,从此她们有了党氏三姐妹的称号。
育红学校的孩子们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定时睡觉、起床,一起玩耍,形影不离。有时这是一种快乐,有时这也是一种集体化的孤独。党育新记得,那时福利院的孩子特希望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才有人去慰问他们。党育新全家一共5口人遇难,惟有她活了下来。
34年来,党育新时刻都在幻想着自己有父母,但这仅停留在幻想。“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的概念,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我们孤儿就是这样。有人说我们孤儿没有教养就是因为这样。”党育新现在有时觉得自己很自私,觉得自己以前被亏欠的太多了,“工作后,我想买什么,不论多贵我都买给自己,变相地回报自己。”
党育新的梦想后来差点成为现实。有一对奥地利的夫妇来收养唐山遗孤,“党氏三姐妹”同时入选。福利院的阿姨说,谁乖,谁就有家。党育新觉得自己最乖,肯定讨人喜欢。最终,老大党育红被选去,因为她没有任何亲人。党育新不能去,是因为她终于找到了亲人,她还有个姥姥活着。后来,她被送到姥姥家。她和姥姥有亲情,生活却没保障。姥姥没有工作,生活很苦,需要舅母给生活费,每月20元,还要“看人脸色”,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孤儿院虽然孤独,但毕竟不用为生计发愁。党育新很想回育红学校。
她给福利院的阿姨写信,希望他们来接她。她不知道石家庄育红学校1984年已经解散。等了许久,也没有阿姨来接,她第一次真实地感觉到被集体“遗弃”了。
跟着姥姥的日子,没人告诉她长大会怎么样。来例假了,她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姥姥从来没有告诉她爸爸妈妈的事,连一张照片都没有。2004年姥姥去世,党育新从此失去了所有的亲人。
一边学会自立,一边忍受孤独
集体生活培养了孤儿们很强的社会适应能力,他们一边学会自立,一边忍受着孤独,福利院的童年时光对于他们来说,有得亦有失。1976年,2岁的杜明丽成为一名唐山孤儿,1984年,她告别育红学校回到唐山,“确切地说,我是回到唐山以后才明白了自己的身世,才知道自己是从小失去了父母的孤儿,脑子里边开始有了印象,以前朦胧地知道,但是不清晰,那种感觉很不一样。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后,当时并没有特别的感受。我虽然没了父母,可是,我从小在那样一个集体环境里长大,周围跟我一起玩的伙伴,都是这样的身世,老师对我们也特别好,所以对父母没有那么强烈,我说我挺幸运的,也不是特别悲伤。”
对于杜明丽的妹妹杜明艳来说,育红学校的这8年则对她的性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事领导常说,艳子是集体里长大的,走哪都能抱成团。“领导总说我有凝聚力,号召力,跟集体生活有很大关系,在那个环境里长大的孩子比较合群,能容忍别人,比较自立,从小锻炼出来了。”杜明艳现在在冶金矿山机械厂工作,还当上了销售科长,作为一个孤儿,她对家看得特别的重。有时候跟同事们开玩笑说,“我死也得抱着我老公死,你们一拍大腿散了,可以回妈家,我去哪啊?”这玩笑的背后是对家庭的深深依恋。
“她们身后没有家的支撑。”长期跟踪拍摄唐山孤儿成长的常青很能理解他们的孤独感。“那就是前后左右空无一片的感觉。”1981年,初中毕业的李宝霞也将被送回唐山,虽然她舍不得老师,但想到回去,还是感到高兴。“唐山毕竟是我的家。”她和哥哥弟弟三人都在冶金矿山机械厂的一个车间上班,彼此感情十分淡漠,“所以没感觉我们仨那样生活像个家”。“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没有父母,你只能靠自己。”对于生活中遇到的不顺利,李宝霞总是用这句话鼓励自己,相比较于常人,这些孤儿们更加成熟和自立。
对自己未来的丈夫,李宝霞没有过多的要求。“只要人好,能对我家人好。我就会嫁给他。”19岁时她经人介绍嫁给了比她大3岁的粮食局车队司机田福利。
“弟弟想要一个收音机。老田就花了150元给他买了一个。”那时候,每月工资都只有几十元。所以,老田向李宝霞提出订婚时,她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这些地震孤儿中普遍都有早婚的现象,他们一般在20岁就结婚。
党育新20岁时也早已在唐山参加工作,这一年“党氏三姐妹”再次见面。
党育新总说一句话,我姓党啊。于是大家都开玩笑,跟着“党”走。她善于察言观色,协调与众人的关系,然而很少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看上去光鲜亮丽,其实内心很苦闷。她自小就被灌输要坚强,要感谢党,久而久之她也这么想,只有在喝酒时,才能看出党育新的真性格,她喝得比谁都凶。
影片中的方登30多年无法释怀对母亲的怨恨,而现实中,过早失去亲人保护的孤儿,早早地便成为了一个社会人。他们来不及恨谁,来不及幽怨,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生存保卫战中,用时间,抹平一切伤痛。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像个正常人那样有尊严地活着,实现他们的自我救赎。
参考资料:《唐山大地震》,钱钢著;《唐山大地震经历者口述实录》,张军锋主编;《两代地震孤儿的心灵余震》,孙冉著
——小记者采访敬老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