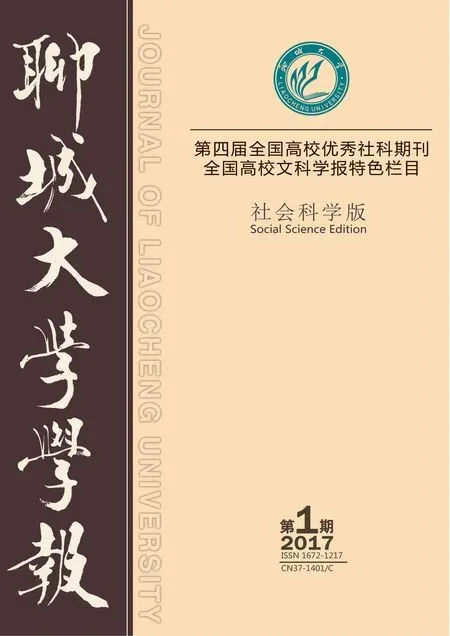朱乾《乐府正义》与乐府诗批评
王辉斌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朱乾《乐府正义》与乐府诗批评
王辉斌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在清代的乐府诗批评中,朱乾《乐府正义》一书既具“题解类批评”的特点,又兼“笺释类批评”之优长,二者相互作用,使《乐府正义》所“正”之“义”得以充分反映。《乐府正义》“题解类批评”的内核,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以“专论式”进行题解,注重对乐府“本事”的稽考,并重在对地名考察与旧说辨正。而上下求索以“正义”,指谬他说以“正义”,则为《乐府正义》“笺释类批评”的重点所在。
朱乾;《乐府正义》;法善戒恶;原乐论
在清代林林总总的乐府诗批评著作中,朱乾《乐府正义》是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乐府专书。全书15卷,共收唐以前乐府诗整900首,并将其分为10类,具体为:“郊庙歌辞”(卷一32首、卷二33首)、“燕射歌辞”(卷二29首)、“鼓吹歌辞”(卷三29首)、“横吹歌辞”(卷四57首)、“相和歌辞”(卷五36首、卷六25首、卷七34首、卷八74首、卷九24首)、“清商曲辞”(卷十192首)、“舞曲歌辞”(卷十一29首)、“杂曲歌辞”(卷十二61首,卷十三41首,卷十四79首)、“杂歌谣辞”(卷十五125首)①这一具体数量,为笔者据国家图书馆藏乾隆五十四年刻本《乐府正义》目录统计所得,其中的“一章”、“一曲”均以一首计,如《汉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即以17首计,特此说明。。就此10类而言,可知:一、《乐府正义》之分类,基本上是对郭茂倩《乐府诗集》分类的承袭,即只是去掉了其中的“近代曲辞”与“新乐府辞”。二、所选乐府诗以“相和歌辞”与“杂曲歌辞”为主,前者凡5卷193首,后者则有3卷181首,二者合计,其数量几占全书收诗总数的一半,这一实况的存在,亦与《乐府诗集》大体类似(《乐府诗集》所收之乐府诗也是以此二类为主的)。这两点表明,《乐府正义》与《乐府诗集》是颇具关联的,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从《乐府正义》之题解多为“《乐府诗集》曰”云云,即可准确获知。
但《乐府正义》所收之乐府诗,却又有与《乐府诗集》迥不相及者,如卷十四“杂曲歌辞”所收陶渊明《桃花源记》一篇,即为较典型的一例。此外,《乐府正义》还于《乐府诗集》的收诗之外,辑补了数以十计的乐府诗,如卷一司马相如《封禅颂》4章、班固《明堂诗》等5首,卷二王粲《太庙颂》3章、成公绥《晋中宫诗》2首、傅元(玄)《正旦大会行礼歌》4章、《上寿酒歌》等,即皆为《乐府诗集》所未收。由是而观,可知在乐府诗的“选择类批评”方面,朱乾与郭茂倩乃是存在着较大之差异的。这实际上涉及的是二人对于乐府诗的认识,以及对乐府诗如何定义的问题。据现所存见的乐府诗总集可知,于《乐府诗集》之外辑补乐府诗者,元人左克明《古乐府》乃率先而为,其后则代有继人,如明之徐献忠《乐府原》、梅鼎祚《古乐苑》等,即多有所辑补。这一实况表明,左克明等人对于郭茂倩关于乐府诗的认识(定义),或者说于《乐府诗集》所收之乐府诗,乃是并不满意的,而朱乾亦属如此。
《乐府正义》之于乐府诗的批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题解类批评”,一即“笺释类批评”,前者虽以引录《乐府诗集》的题解为主,却不乏新见,后者则以“笺评”最具代表性,故创获亦多。所以,这两种类型的批评,即成为了《乐府正义》之于乐府批评的内核,而其所“正”之“义”,亦皆因此而得以体现。此外,朱乾于《乐府正义》中还曾着眼于“专论类批评”的角度,对乐府与音乐的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亦进行了讨论。有鉴于此,本文特对朱乾编撰《乐府正义》的动机,于“原乐”方面的论述,以及《乐府正义》之“题解类批评”与“笺释类批评”之特点等,作一具体观照与论析。
一、朱乾编《乐府正义》的动机
朱乾,字秬堂,今浙江嘉兴人。其生平行止等均不详。据乾隆五十四年刻本《乐府正义》卷首所附朱珪《乐府正义序》一文,可知朱乾当卒于清高宗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是《序》有云:“丁酉,闻先生赴。庚子,珪视学于闽。”其中的“丁酉”,即乾隆四十二年,而“闻先生赴”者,实则为“闻先生卒”的另一种说法,盖因“赴”古通“讣”故也。但朱乾的生年与享年,以及交游、著述等,则皆因资料所限而无考。
朱乾《乐府正义》今传世者,主要有国家图书馆藏乾隆五十四年刻本。此刻本卷首附序二篇,即一为朱珪《乐府正义序》,一为朱乾《乐府正义序》,据朱珪《乐府正义序》之“受业大兴朱珪仅识”的落款,知其乃朱乾弟子。朱珪《序》主要记述了《乐府正义》的成书与板梓之况,以及对其之评价,朱乾序则述及了其对乐府诗的致用功能等多方面之认识,因此,二《序》之所言,对于具体把握朱乾的乐府认识观,以及弄清楚其编撰《乐府正义》的动机与目的等,均是颇具助益的。如朱珪《序》有云:
先生(此指朱乾—引者注)曰:“我于书无所不嗜,而尤有心得者,在古乐府,他日成一家之言无憾矣。”明年,先生归岁。庚辰,珪之官福建,过嘉兴谒先生。甲申,闻先大夫忧,奔丧返,再见先生,曰:“我《乐府正义》成矣,他日子能刻之,吾愿足矣。”……先生是书博综心契,其悟解或得之梦寐,其考证皆根之经史,真能自成一家言,足以传世而不惑者。原本各卷间附唐以后太白、子厚诸篇,而别为《新乐府》二卷,则唐宋后所作也。窃谓唐人全诗,各有注释,且其体离合不一,今断自隋而止,为卷十五,先授之梓。其唐人之沿古乐府体者,别钞为二卷,又新乐府二卷,还之其家,以待他日之续刻①朱珪:《乐府正义序》,《乐府正义》(卷首),国家图书馆藏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所引文字,包含了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记述了朱乾早年欲编撰一部“有心得”的“古乐府”,并欲使之“成一家之言”而传于世的构想;二是交待了《乐府正义》的成书时间,即“闻先大夫忧,奔丧返”而“再见先生”的甲子年,也即公元1764年;三是朱珪对《乐府正义》稿本的评价,认为“其悟解或得之梦寐,其考证皆根之经史,真能自成一家言,足以传世而不惑”;四是对《乐府正义》稿本编撰情况的介绍,即“原本各卷间附唐以后太白、子厚诸篇,而别为《新乐府》二卷,则唐宋后所作也”;五是记载了朱珪对《乐府正义》稿本进行编辑整理与刻印的情况,“今断自隋而止,为卷十五,先授之梓。其唐人之沿古乐府体者,别钞为二卷,又新乐府二卷,还之其家,以待他日之续刻”。其中,第四点最为重要,因为据此可知,《乐府正义》的原稿本不仅是“各卷间附唐以后太白、子厚诸篇”,而且还曾“别为《新乐府》二卷,则唐宋后所作也”。对唐人特别是宋人的新乐府进行编集,朱乾的“别为《新乐府》二卷”虽非首创,但却也并不多见①将宋人新乐府最早进行编集者,据现有材料可知,乃为宋无名氏所编《四家宫词》、《五家宫词》,后来明人多为之,如毛晋所编《十家宫词》等,即为其中之一,具体参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二章第三节,第85-100页,该书由黄山书社2010年出版。另据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五十一《古今诸家乐府序》一文可知,周紫芝在南宋初年曾编有《古今诸家乐府》三十卷,所收乐府诗乃由汉而宋,惜乎是书已佚亡,具体参见拙作《周紫芝新乐府观述论》一文,载《阅江学刊》2014年2期。,此则表明,朱乾之于乐府诗的认识,乃是“古”、“新”乐府并重的。
朱乾的《乐府正义序》,所述内容则较朱珪之《序》更为丰富,其中,既有朱乾对乐府诗与音乐关系的认识,也有其于乐器、乐律等之描述,更有对编撰《乐府正义》动机的表白等。所以,从乐府诗批评的角度言,朱乾《序》是较之朱珪《序》更值得注意的。如朱乾《序》有云:
乾以为既曰诗,未有不可被之弦歌者。……昔孔子正乐,亦曰正其礼义而己矣。故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自汉兴乐府,《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歌诗一章,卓然雅颂嗣音。建安继武,清泉奋迹,厥词炳焉。下逮齐梁,此道中绝。盖《三百》新声降而为乐府,乐府新声降而为唐人绝句,绝句新声降而为宋元词曲。新声愈盛,古调愈远,其去《三百篇》最近者,无如汉之乐府,所惜高祖乐楚声,而武帝又喜郑卫,声音之道缺焉。然文始五行,尤踵韶武,必有可观者,恨不传耳。今以《三百篇》例之,《郊祀》、《房中》如诗之颂,《鼓吹》、《铙歌》如诗之雅,《相和》、《杂曲》如诗之风,尚可以见其大概。明乎其义,则见其中美者,可以劝善恶者,可以惩尤,夫三百也。……义则本之经,事则案诸史。上自汉魏,下讫于唐,成书十□卷,必其善者可法,恶者可戒,然后敢登。若其善不足以法,恶不足以戒,而徒而淫靡之词,概从割弃,庶几乎。礼义明而声音亦可从此起矣②朱乾:《乐府正义序》,《乐府正义》(卷首),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这段《序》文,首先强调了诗与音乐的关系,认为在上古时期,只要是诗,“未有不可被之弦歌者”, 即皆可配乐而唱,其与汉代的乐府诗,乃并无多大之区别。正因此,“自汉兴乐府,《安世房中歌》十七章”等,即“卓然雅颂嗣音”,也即为《诗经》之馀响。这种“诗乐合一”的传统,中经建安时虽有所发扬,逮至齐梁之际,“此道中绝”,其最终的结果却是“新声愈盛,古调愈远”,以至于“声音之道缺焉”。这虽然是从音乐的角度对乐府诗的发展与流变之勾勒,但朱乾对于“声音之道”的“缺焉”,却是深感婉惜的。接下来,朱乾又着眼于风、雅、颂的角度,对汉、魏乐府诗进行了比拟,其所比拟者,与朱嘉徵《乐府广序》将乐府诗分为风、雅、颂乃如出一辙,所不同者,是《乐府广序》于“雅”之中又有“雅”与“变雅”之分。朱乾对于《乐府正义》之此举,显然是受到了朱嘉徵《乐府广序》之“乐府风雅颂”说影响的结果。《序》文的最后,是朱乾对自己编撰《乐府正义》之动机的夫子自道:“上自汉魏,下讫于唐,成书十□卷,必其善者可法,恶者可戒,然后敢登。若其善不足以法,恶不足以戒,而徒而淫靡之词,概从割弃。”这与皮日休在《正乐府十篇并序》所主张的“乐府美刺论”,乃有过之而无不及,则朱乾乐府观的致用性特点之鲜明,也就不言而喻。
欲通过编撰一部乐府诗总集,以试图达到“法善戒恶”之目的,这就是朱乾编撰《乐府正义》的动机所在。而在由汉至清数十家乐府诗总集编撰者中,持有如此之动机者,朱乾既是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人。
二、《乐府正义》之“原乐”论
《乐府正义》所收录之乐府作品,主要包含着两大类,即一为乐府论文,一为乐府诗,且前者皆为朱乾所撰著。乐府论文一类,又由“原乐”与“附论”所组成,“原乐”载于卷一之前,且标明为“卷首”(所以,《乐府正义》实际上有16卷),凡22篇;“附论”则有二,一为卷一“郊庙歌辞”之末的4篇,一为卷二“郊庙歌辞”之末的5篇,二者共计31篇。这31篇乐府论文,实际上就是朱乾的一部专论乐府诗的论文集,因之,其编入《乐府正义》者,即成为了《乐府正义》有别于其他乐府诗总集的一个明显特点。而且,在自西汉而清初的近两千年间,于乐府诗总集中收入如此之多的乐府论文者,也只有朱乾《乐府正义》一家,则《乐府正义》在清代乐府诗批评中所占地位之重要,也就不言而喻。
被朱乾编入《乐府正义》的31篇乐府论文,其依序为:《辨黄钟律尺》、《再者黍有大小》、《黄钟起度量衡再用倍数》、《申黄钟用倍数义》、《候气》、《两朝史乐志论辨》、《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戴氏论风雅颂以声别》、《郑氏三分七月》、《王氏一诗三用》、《礼乐沦亡之所由》、《礼乐有本》、《郑樵谓诗在于声不在于义》、《诗歌同异》、《歌曲所起》、《乐府之名》、《乐府诗源流》、《诗徵存亡辨得失》、《曲有解》、《音韵》、《情感》、《怨思之声》(以上卷首《原乐》);《五帝》、《马端临汉不郊祀论》、《朝日》、《社》(以上卷一《附论》);《汉有秦晋梁荆之巫》、《论原庙》、《汉郊庙二失》、《论太祖之位》、《论昭穆之位》(以上卷二《附论》)。这31篇文章,视野开阔,内容丰富,举凡乐器、乐律、礼乐、郊庙、诗歌、歌曲、乐府、音韵、情感等,乃均有所涉及,而成为研究朱乾乐府学思想的一份重要资料。就内容而言,这些文章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朱乾对前人关于律吕、乐府等认识之辨论,一为朱乾对自己认识乐府、歌曲等之所获的陈述,其中,又以“原乐”之《戴氏论风雅颂以声别》、《郑樵谓诗在于声不在于义》、《诗歌同异》、《歌曲所起》、《乐府诗源流》、《诗徵存亡辨得失》、《曲有解》、《音韵》、《情感》、《怨思之声》等文,最具乐府诗批评的特点。
朱乾对前人关于声、乐等认识的辨论,可以《郑樵谓诗在于声不在于义》一文为代表,在此文中,朱乾针对郑樵所提出的“诗在于声不在于义”说,进行了极严厉之批评。郑樵论诗,认为”得诗而得声者《三百篇》,其则系于风、雅、颂;得诗而不得声者,则置之,谓之逸诗”,此即《三百篇》与逸诗的区别。针对郑樵的这种认识,朱乾指出其乃全部为误,因而写道:“郑樵谓诗在于声不在于义,谬哉!”对于郑樵的这一认识,上引朱乾《乐府正义序》亦有所批评,这从《序》文开首引郑樵“理义之说胜,则声音之道微”云云,即略可获知。《序》文在“乾窃以为不然”之后,即以相当大的篇幅,对郑樵的“诗乐关系”说进行了辨驳,并提出了“既曰诗,未有不被于弦歌”的认识。此外,在《礼乐沦亡之所由》一文中,朱乾之于郑樵的“礼乐沦亡论”亦进行了批评,认为郑樵之说与礼乐沦亡的历史事实不符。凡此种种,均可见出朱乾对于郑樵有关诗、乐的种种认识,均是不予认同的。
《乐府诗源流》一文,则在对诗与乐之关系进行梳理的同时,还引王灼《碧鸡漫志》之所言考察了乐府诗的流变之况,以及“今曲子”盛行不衰的原因等,因而具有一定的“乐府史”意义。文章认为:
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今曲子,其本一也。后世风俗,盖不及古,故相悬也。王灼曰:“古人初不定声律,因所感发为歌,而声律从之,唐、虞禅代以来是也。馀波至西汉未始绝。西汉时,今之所谓古乐府者渐兴,魏、晋为盛。隋代取汉以来乐器、歌章、古调,并入清乐,馀波至李唐始绝。唐中叶虽有古乐府,而播在声律则甚少矣。士大夫作者,不过以诗一体自名耳。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①朱乾:《乐府正义序》,《乐府正义》(卷首,原乐),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这段文字虽然以引文为主,但从中可以看出,朱乾对于乐府诗的发展与流变,乃是极赞同王灼之认识的,特别是其中对“唐中叶”之“古乐府”的认识,历来言者极少,朱乾则只眼独具,将其进行了引录。除此文外,朱乾还在《诗歌同异》一文中,抄引了元稹《乐府古题序》对“古题乐府”(古乐府)予以称道的一段文字。合勘此二者,可知朱乾之于古乐府的认识,乃是情有独钟的。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引文字的开首两句:“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所表明的是,朱乾认为上古时的“古歌”与汉、魏时之“古乐府”,以及隋以后的“今曲子”,三者虽名不相同,实则为一。即在朱乾看来,乐府诗的源头,是“古歌”而不是汉武帝的“乃立乐府”。正因此,朱乾在《乐府之名》一文中即明确指出:“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即名之乐府,误矣,曰古乐府,尤误”。将“古歌”视之为乐府诗的源头,充分反映了朱乾对于“前乐府”①关于“前乐府”的定义,以及“前乐府”在西汉之前的创作概况,可具体参见拙作《论“前乐府”在先秦的创作》一文,载《西华大学学报》2013年2期,第29-33页。的高度重视。
总的说来,《乐府正义》卷首之“原乐”一卷,主要在于“原”上古时期“乐”之本意,这与徐献忠《乐府原》在于“原汉人乐府辞并后代之撰之异”、“各原其本意”者②徐献忠:《乐府原序》,《乐府原》(卷首),明诗话全编本,南京:凤凰出版社,1997年,第3032页。,乃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其所反映的,则是朱乾对于诗乐关系与乐府之源等方面的认识。如在《音韵》一文中,朱乾还曾如此认为:“乐府须识五韵通转,及三声回互之法,然后可读。”表明其于乐府诗的音韵等问题,也是相当重视的。而“附论”中的9篇文章,则主要是对上古时期郊祀等音乐文化活动的述论,以及对前人之说的辨驳,如辨“马端临汉不郊祀论”等。合二者而为一,即构成为了朱乾乐府认识观的一种具体反映。正因此,朱乾于《乐府正义》中所“正”乐府诗之“义”,或者说其于“题解类批评”与“笺释类批评”中之所获,即大都与此关系密切。
三、《乐府正义》的题解类批评
《乐府正义》中的15卷正文,主要由四者组成,其依序为:“歌辞”序文、题解、乐府诗、笺评。所谓“歌辞”序文,是指每一类“歌辞”之前的一篇小序,如《郊庙歌辞序》等,《乐府正义》凡10类“歌辞”、10篇序文,且皆于开首有“《乐府诗集》曰”五字,表明其均引录于《乐府诗集》的序文,经比对,且一字不易。而其题解,亦大抵如此,即其所引者,虽有他书,如《古今注》、《乐府解题》、《古今乐录》等,但《乐府诗集》则始终为其主要之引书。虽然如此,但《乐府正义》之题解,也是自有其特点的,如以“专论式”进行题解者,即为其一。
所谓“专论式”题解,是指题解的篇幅较大,所包含的内容亦较丰富,且所论大都为前人所不曾言及者,如卷九陆机《班婕妤》,便属于此类。陆机《班婕妤》一诗,凡12句,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三著录,其题解首引《汉书》,次引《乐府解题》,二者凡186字,无郭茂倩只字之认识。而《乐府正义》于《班婕妤》的题解,则多达522字,为《乐府诗集》字数的近三倍。《乐府正义》的这一题解,除开首全文引录了《乐府诗集》所引《汉书》的106字外,其馀的416字,全部乃朱乾所自为,且极具“专论式”之特点。为便于认识,兹将其抄录如下:
古乐府诗,题简而意赅。即如“怨诗”一门,起于卞和,汉魏继之《怨歌行》,已无所不备矣,至梁柳恽别出《长门怨》,而唐《阿娇怨》为赘矣。晋陆机别出《班婕妤》,而唐《长信怨》为赘矣。自此遇娇妒者拟《长门》,遇贤淑者拟《婕妤》,皆可用古题,顾此可指名者也。若泛而言之,则有《宫怨》一题,而《玉阶怨》、《娥眉怨》俱赘矣。若孟郊《征妇怨》,则已见于曹植之“明月照高楼”篇。总之,后世诸题,皆不出古辞《怨诗行》,及汉、魏《怨歌行》之三作。此古乐府题之所以拟之而不穷也。唯孟郊《湘弦怨》一题,非《怨歌行》可该,是为唐新乐府。元微之称“近代唯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旁”,不知《丽人行》已见刘向《别录》,郭氏采入“杂曲矣”。若《悲陈陶》、《悲晋坂》(当为《悲青坂》之误),则“铙歌”之《战城南》也,《哀江头》、《哀王孙》,则“杂曲”之伤歌行也,《兵车》,则“相和•平调”之《从军行》也。作书必有纲纪,然后可为法。《诗》止三百,《春秋》止二百四十二年,《周易》止六十四卦,以为天道备于上,人事决于下,则可以已矣。如必即事名篇,则是《易》必京房,《春秋》必纲目,文愈繁义愈乱矣。明乎《雁门太守》、《秦女休》、《云中白子高》诸行之例,类推之,古乐府之题无尽也。必古题所不能附,然后可为唐人新乐府,则亦寥寥无几矣①朱乾:《班婕妤题解》,《乐府正义》(卷九),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这完全是一篇关于《班婕妤》题解的小论文。全文之所言,虽然属于传统“四本”②乐府诗题解中的“四本”,所指为“本事”、“本题”、“本义”、“本文”。中之“本题”的范畴,但却又超出了《班婕妤》这一本题,而是由此及彼,涉及了如何制作古乐府之题与新乐府之题的大问题。在这一题解中,朱乾以《班婕妤》这一古乐府题为例,乃明确指出,凡拟古乐府者,必应以古乐府之题为题,而不得由其本题而“别出”他题,也即“必古题所不能附”,否则,便会导致“古乐府题之所以拟之而不穷也”的产生。而对于新乐府的命题,也应如此,即其题意不能与古乐府所写内容有所重复,而纵观由汉而唐的古乐府之题与新乐府之题,能如此者,实乃“寥寥无几矣”。并对元稹于《乐府古题序》所言之“即事名篇”提出了质疑,认为“如必即事名篇,则是《易》必京房,《春秋》必纲目,文愈繁义愈乱矣”。朱乾的这种认识是否正确,这里不作讨论,但从“题解类批评”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予以关注者,朱乾之前与之后则别无他人,这是颇值得注意的。
《乐府正义》题解的另一个特点,是注重对乐府“本事”的稽考,并补《乐府诗集》之所阙。“本事”之于汉、魏乐府,为其关键所在,故于乐府诗进行题解者,大都在对“本事”的探讨之中下功夫。《乐府正义》题解表现在这一方面的特点,可以卷十二傅玄《云中白子高行》之题解为其代表。《乐府诗集》卷六十三收录了傅玄《云中白子高行》一诗,但无题解,《乐府正义》之所撰,则正好补其阙。其题解为:
题曰“云中白子高”,而所咏者陵阳子明,犹《雁门太守行》之咏洛阳令也。按《山海经•内经》曰:“华山青水之东,有山名曰肇山,有人名曰柏高,柏高上下于此,至于天。”郭注云:“柏子高,仙者也。”《路史》:“尧治天下,有柏成子皋,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子皋辞为诸侯而耕。一作子高。”《列子•杨朱篇》:“杨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③朱乾:《云中白子高行题解》,《乐府正义》(卷十二),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这条题解,为了弄清楚诗题中的“云中白子高”为何人,以及《云中白子高行》一诗的“本事”,先后引了《山海经•内经》、郭璞注《山海经》、《路史》、《列子•杨朱篇》诸材料,以证实诗题中的“白子高”即柏高(又作柏子高、柏成子皋,伯成子高),为尧、舜时人,后“辞为诸侯而耕”、“舍国而隐”,以至于成为一位“仙者”。所以,《云中白子高行》一诗,无论是咏“云中白子高”抑或“陵阳子明”,其“本事”均与游仙相关。而尤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而所咏者陵阳子明,犹《雁门太守行》之咏洛阳令也”之所云,明确指出了是诗之题与文本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只眼独具。
《乐府正义》题解的第三个特点,是重在对地名的考察与旧说的辨正。先看对地名的考察。一般而言,《乐府正义》中的这类题解,主要考察的是诗题所标示之地名,且多属据材料以立论,因而所获令人首肯。如卷八于古辞《步出夏门行》的题解为:“《洛阳伽蓝记》云:洛阳北面有二门,西头曰大夏门,汉曰夏门,魏、晋曰大夏门,尝造三层楼,去地百尺,唯大夏门,甍栋干云。《文选》陆机《门有车马客行》注:古《步出夏门行》曰,市朝不易,千岁墓平。今此诗未见所出。”④朱乾:《步出夏门行题解》,《乐府正义》(卷八),乾隆五十四年刻本。以《洛阳伽蓝记》之所载而笺释诗题中的“夏门”,极具见地。《乐府诗集》卷三十七虽然收录了此诗,但却没有题解,此即可补其阙。再看对旧说的辨正。卷九陆机《泰山吟》之题解为:
按左思《齐都赋》注云:《东武》、《泰山》,皆齐之土风,弦歌讴吟之曲名也,其非丧歌亦明矣。士衡《泰山》,适感幽涂,武侯《梁甫》,偶悲三墓。自开三图有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甫主死之说。而《乐府解题》,遂谓《泰山吟》,亦《薤露》、《蒿里》之类,郭氏附会之,谓《梁甫吟》亦葬歌,不闻歌土风者,歌虞殡也。《解题》一书,但依样模形,不识古义类如此①朱乾:《泰山吟题解》,《乐府正义》(卷九),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这是对《泰山吟》“本义”的考辨。题解于开首引左思《齐都赋》之注而认为,《泰山吟》与《东武吟》一样,“皆齐之土风,弦歌讴吟之曲名也,其非丧歌亦明矣”。这其实是对《乐府解题》所持“丧歌”说②关于《乐府解题》所持《泰山吟》为“丧歌”说,具体参见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一《泰山吟》之题解,第6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的辨驳。正因此,故接下来即有“而《乐府解题》,遂谓《泰山吟》,亦《薤露》、《蒿里》之类,郭氏附会之,谓《梁甫吟》亦葬歌,不闻歌土风者,歌虞殡也”一段文字,其中的“郭氏附会之”云云,则是指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一于《泰山吟》题解引《乐府解题》之所言。所以,朱乾在这条题解中,主要是针对《乐府解题》与《乐府诗集》所持之“丧歌”说进行的辨正,并认为其说乃皆非。
四、《乐府正义》的笺释类批评
《乐府正义》中的“笺释类批评”,主要指的是附于每首乐府诗之后的一段“笺评”文字,因其篇幅一般都较长,而兼有“专论类批评”之特点,如卷一《郊庙歌辞•汉郊祀歌•练时日》之“笺评”,即有近300字之多。在这篇“笺评”中,既有对“本义”的陈述,又有于字词的注释,更有对旧说的匡谬,内容相当丰富,极便于读者对《练时日》之“义”的具体把握。《乐府正义》中的这种“笺释类批评”,实际上是受徐献忠《乐府原》、朱嘉徵《乐府广序》的影响所致,而后者的影响又尤为明显,这从朱乾在“笺评”中多引《乐府广序》者③关于朱乾《乐府正义》受徐献忠《乐府原》、朱嘉徵《乐府广序》之影响者,兹各举一例,以供参考:卷四《横吹曲辞•赤之扬》之“笺评”云:“徐献忠曰:汉以赤符兴业,至武帝扬威四远。”其中的“徐献忠曰”,实际上是对“徐献忠《乐府原》”的省称(徐献忠字伯臣,《乐府正义》所引又有“徐伯臣曰”云云,可具体参见卷一《唯泰元》之“笺评”等);又卷九曹植《怨诗行》二首之“笺评”有云:“《广序》曰:按《乐府》较《七哀诗》多十二句……”其中的“《广序》”,所指即《乐府广序》(同此者,另有卷六曹丕《燕歌行》“笺评”之所引等)。,即略可获知。但《乐府原》与《乐府正义》又是有所不同的,《乐府原》对“原其本意”的“意”之所“原”,主要是以“题解类批评”而为,《乐府正义》于“义”之所“正”,则属于“笺释类批评”的范畴。虽然如此,但《乐府原》所“原”之“意”,与《乐府正义》所“正”之“义”,却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即其都是为了弄清楚一首乐府诗的真实面目而在进行着“原”与“正”。这样看来,可知二者实际上是极具殊途同归之特点的。
综观《乐府正义》全书之“笺评”,朱乾于其中所“正”之“义”,除揭示题旨为其大端外,还重在对乐府诗中人名、地名、语词、历史事实,以及属于“题解类批评”范畴的“四本”(“本事”、“本题”、“本义”、“本辞”)等,都进行了程度不同之涉及。如果将这些“笺评”与其中的“题解类批评”合而观之,可知朱乾对于《乐府正义》“义”之所“正”,乃是着眼于立体多维的角度而为的,如此,则其之所获,自然是如上引朱珪《序》之所言,“真能自成一家言”的。而其之“正义”,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一为上下求索以“正义”,一为指谬他说以“正义”。为便于认识,兹各举数例以窥其一斑:
(一)上下求索以“正义”。《乐府正义》中的这类“正义”,主要是指朱乾通过各种材料、各种方法,以求得对乐府诗某一方面的确解,或者是就属于艺术范畴的作法、语词、声调等进行具体论析,如卷三曹操《度关山》之“正义”即属此类。此诗之“笺评”云:“魏武乐府诸题,必踞第一等议论,如《度关山》便想到陟方巡狩,考侯省农正刑等事,而归本于俭,意在简省舆从资粮之费,可谓有志于民事者,故能蔓刈群雄,几平海内。史称操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终无所赦。而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于用刑操俭,独惓惓言之。”①朱乾:《度关山笺评》,《乐府正义》(卷三),乾隆五十四年刻本。在这篇“笺评”中,朱乾由《度关山》之为“第一等议论”,联系到曹操的“有志于民事者”,因而认为,此诗之所写,是曹操对自己“用刑操俭”的“独惓惓”之言。这一“正义”,较之《乐府解题》认为“言人君当自勤苦,省方黜陟”云云②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91页。,乃是更具准确性与深刻性之特点的。又如卷十三宋子侯《董娇娆》之“正义”为:
董娇娆,人名。诗本一篇,而中含问答,竟似两体。“高秋八九月”一节,接蔟之妙,町畦化尽,此法唯汉诗有之,汉以后诗人不知也。此与《艳歌》、《白鹄行》作法同。若魏文《折杨柳行》,竟“西山”、“彭祖”两篇为一篇,上下自成唱和,体亦犹此。盖大曲有“艳”、有“趋”、合而成章,此当截“何为见损伤”以上为艳,“吾欲竟此曲”以下为趋,其有一诗未竟,则合以他诗,而声调始足,他可类推。③朱乾:《董娇娆笺评》,《乐府正义》(卷十三),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这一“笺评”所“正”之“义”,属于乐府诗艺术中的“作法论”。朱乾认为,《董娇娆》一诗的作法极具特点,因而乃以“接蔟之妙,町畦化尽此法”称道之,并着眼于“声调”的角度,对此诗之“艳”、“趋”之分合进行了点评。由是而观,可知朱乾之于乐府诗的诸种艺术,乃是深有研究的。其它如卷八古辞《折杨柳行》之“笺评”对《折杨柳行》这一诗题的史的勾勒,卷十二曹植《远游篇》之“笺评”对是诗题旨的重新认识等,亦均具特点,因限于篇幅,兹不具举。
(二)指谬他说以“正义”。质疑、考辨他人之说以“正义”,为《乐府正义》“笺评”之大端,如卷一开篇《汉郊祀歌•练时日》即为其一。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一著录《练时日》,无题解。《乐府正义》对《练时日》之“笺评”,所着眼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注音释词,一为笺释求意。对于前者,朱乾对此诗中的“侯”、“有”、“相”、“亿”、“青”等单音词,皆进行了笺释,如认为“有,又通望,望,祭也”等;而于后者,则对司马相如等人所持“用诸淫昏之鬼”的说法,藉材料以进行辨驳,认为其说“何其谬于礼也”。在此基础上,朱乾提出了《练时日》是一首“迎神辞也”的新见,而“迎神辞也”四字,即为朱乾对《练时日》一诗所“正”之“义”。两相比较,朱说自可信然。又如卷九于诸葛亮《梁甫吟》的“笺评”中,对黄庭坚之说的辩驳,亦颇具代表性。此“笺评”有近700字之多,为省篇幅,兹节录其中有关文字如下:
其(指诸葛亮—引者注)一生谋图之忠,悉见于此。抱膝隆中,兴怀往事,其梗固已先定矣。黄山谷曰:“陈寿叙武侯‘躬耕陇亩,好为《梁甫吟》’,语势既不尽其意,谓文失载此诗,此盖好简之过。余观武侯此诗,盖以曹公专国,杀杨修、孔融……耳,但云‘好为《梁甫吟》’,不知寿意所指,岂既作此诗,时时为客歌之,故云尔乎?”固哉!山谷之不知乐也。《太山》、《梁甫》、《幽州马客》、《行路难》等,皆曲调之名,陈武学之,学其声也,孔明为之,亦为其声也。孔明“好为《梁甫吟》”,犹曰“宜歌商宜歌齐”云尔。《步出齐南门》诗,乃是孔明之《梁甫吟》。其实前乎此者,《梁甫吟》之调,当不止一诗,故孔明好为之。……陈寿《志》,亦并非好简之过,失载此诗。渠既云“好为《梁甫吟》”,则自不当专载此诗矣。独其所称为杀杨修、孔融……而作,宜得其情④朱乾:《梁甫吟题解》,《乐府正义》(卷九),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黄庭坚(山谷)认为,《梁甫吟》为孔明因曹操杀杨修、孔融等人而作,朱乾认为其说“宜得其情”,即可以从之。但朱乾于“笺评”中,却针对黄庭坚认为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因“好简”而“失载此诗”,以及孔明“好为《梁甫吟》”者所指即此诗的认识,均进行了辩驳。综之则为:朱乾认为“陈《志》”未载《梁甫吟》者,绝非为“好简之过”,而是因为孔明“好为《梁甫吟》”者,乃为《梁甫吟》之曲调,而非《梁甫吟》之诗。并认为,“《梁甫吟》之调,当不止一诗,故孔明好为之”,“《步出齐南门》诗,乃是孔明之《梁甫吟》”。朱乾所“正”之“义”既是如此,故于“黄山谷曰”一段文字之后,即用了“固哉!山谷之不知乐也”九字,对黄庭坚进行了严厉批评。其它如卷一于《天马》之“笺评”对《汉书》“师古注曰”的非难,卷八于魏明帝《步出夏门行》之“笺评”对“《论语》注”的辩驳,卷十二于曹植《驱车行》之“笺评”对“王钦若曰”的考辨等,即皆属如此。
但《乐府正义》之“笺评”,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牵强附会即为其例,对此,王运熙《乐府诗述论》之《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书目提要》(第307页)已曾言及,兹罢论。
[责任编辑 唐音]
Mistakes Correcting of Yuefu(乐府) by Zhuqian and Yuefu Criticism
WANG Hui-bin
(School of Arts, Hubei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Xiangyang 441053, China)
Among all the Yuefu criticism in Qing Dynasty, Mistakes Correcting of Yuefu by Zhuqian fully manifests“mistakes”being“corrected”, with both advantages of title explanatory criticism”and“explanatory notes criticism”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The essence of“title explanatory criticism”in the book is mainly shown in three aspects, that is,“monograph”explanation, insight into“Benshi”and focus on study of place names and criticism of old sayings.“Correcting mistakes”by seeking truth everywhere and picking out mistakes of others is the focus of“explanatory notes criticism”in the book.
Zhu Qian, Mistakes Correcting of Yuefu, rewarding the goodies while publishing the baddies, original music theory
I206.2
A
1672-1217(2017)01-0019-09
2016-11-10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BZW072):中国乐府诗批评史。
王辉斌(1947-),男,湖北天门人,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