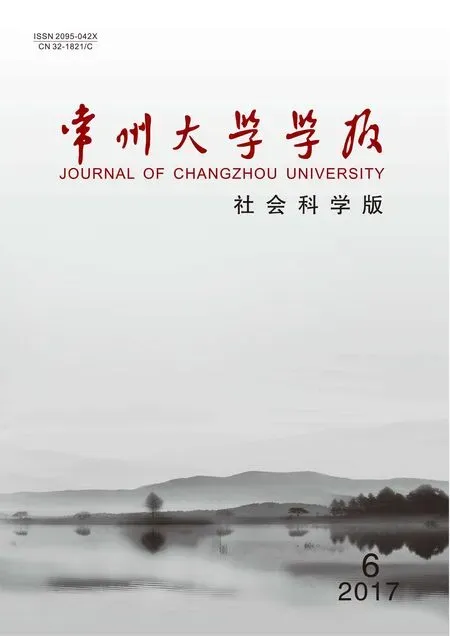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视域下江苏生态文明发展探究
张苏强,刘 魁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视域下江苏生态文明发展探究
张苏强,刘 魁
江苏既是经济强省,又是资源相对匮乏的省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亦面临前所未有的环境压力,而这已成为制约江苏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瓶颈。当前江苏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发展结构不均衡、生态环境制度供给质量低、城乡生态环境保护差异化明显、生态文明教育体系实效性不足等短板,都是对西方传统工业社会发展模式依赖的表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从有机整体论等视角呼吁转换发展形态,真正从理念和行动上实现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的协调,这为江苏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充分借鉴和重要参考。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
以小约翰·柯布、大卫·格里芬等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揭示现代主义机械论思维方式带来诸多弊端的基础上,克服了后现代主义对“发展”的单向度拒斥,主张以生态发展转向来实现对旧发展观的批判和超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强调转变现代主义思维,克服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虚无特性,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良性发展。反对发展主义、还原主义和增长主义的特征促使它成为研究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中的重要参考坐标。我们将这一理论坐标纳入江苏发展生态文明体系中,形成有利的认知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一直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排头兵,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但其依赖资源消耗和人口红利的传统发展模式亦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损害。尽管江苏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提出要率先建成全国生态文明示范省的战略规划,并明确划定生态红线,深入扎实开展绿色发展评估工作,但灰霾天气、水质污染、固废处置问题等仍在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有待提升。针对这一困境,无论是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还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都将现代主义生产方式视为江苏建设生态文明的障碍。尽管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抓住了问题要害,但其坚持完全放弃现代生产的态度略显矫枉过正。与之相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在坚守现代主义生产生活积极性的同时,逐步消弭现代主义弊端的主张更具现实意义。按照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江苏仍未能完全摆脱对西方传统工业社会发展模式的依赖,对生态文明建设认知缺乏长远和深刻的探索实践,都导致其在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上踌躇不前,陷入沉疴旧路。基于此,以反对西方工业社会发展模式、揭示西方现代性发展局限性而著称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为江苏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全新视角,为其走出一条富有本土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新路提供了参考。
一、江苏生态文明建设的四大短板亟待破局
坚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对江苏实现绿色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江苏以占全国1%的土地,养育了全国6%的人口,创造了全国10%的经济总量。但不容忽视的是,“人口密度大、人均环境容量小、单位面积污染负荷高”的特殊省情导致江苏在发展过程中较早遭遇资源环境的制约。尽管当前江苏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许多矛盾仍未能得到根本解决。伴随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资源消耗较快、环境污染较重等问题更是成为直接制约江苏生态文明建设的“拦路虎”。具体而言,江苏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经济发展结构不均衡、生态环境制度供给质量低、城乡生态环境保护差异化明显、生态文明教育体系实效性不足等四大短板,推进更高水平的生态文明建设刻不容缓。
(一)经济结构“短板”
经济结构“短板”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经济结构不合理,轻重比例不均衡;另一方面是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差、重量不重质、资源能源利用率低等。目前江苏经济社会结构中传统工业比重偏高,这种不均衡格局,在带来数量优势的同时,也存在能源消费比高和同质化发展的弊病。江苏地处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但其经济增长效益不高,仍存在依赖粗放型增长方式的迹象。2012年以来尽管江苏的资源能源利用率有了明显的提升,譬如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位列全国第七,但较之北京、上海、广东差距明显,而且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水平提高缓慢。
(二)管理制度“短板”
管理制度“短板”具体表现为生态社会管理局限性问题突出,生态环境制度供给质量低。就生态社会管理局限性问题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管理主体格局存在局限。尽管这有助于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但在架构生态社会管理体系过程中,公民和企业等相关利益者的生态权益如何体现,政府如何在生态文明社会中实现从管理者到治理者、引导者的身份角色转变,都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然,在这方面江苏也在不断鼓励公民、企业、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参与生态文明管理进程,但具体的监督权限和参与机制仍需要不断完善。例如水、电、天然气市场价格调整,生活垃圾处理等涉及民生环境的项目,如何更加公开、透明和高效地体现民众权益,就值得相关管理者精耕细作。二是以部门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存在结构性缺陷。众所周知,生态文明建设涉及多部门、多领域,但在现行管理体制下,相关部门机构更习惯从本部门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在协同配合的意愿和能力方面存有一定的惰性,在涉及资源整合和决策规划时易陷入九龙治水的怪圈,大量的复杂性研究和分散化、封闭性的管理运行都徒增生态管理成本,甚至出现管理缺位等管理失灵现象。
就生态环境制度供给质量而言,生态文明相关制度建设的短板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制度数量多,且制定标准复杂,出现制度内耗。生态文明建设涉及面广泛,多学科、多部门和多领域的特征十分突出,现有制度规范出台时标准不统一,缺少相互参照价值。如环保部门的规章制度和城管单位的规范存在重叠、交叉甚至相互抵触等冲突情形,这不但增加了制度制定成本,而且损毁了制度规范本身的约束效能。二是制度刚性不足,约束力欠佳,以至于出现守法成本高而违规成本低的现象,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反效应。这在根本上违背了立法的初衷,同时也为滋生腐败等违法行为创造了机会。例如,环保法中对排污企业的惩罚措施局限于小额罚款、关停整顿等手段,缺少财政、税收以及银行信贷等杀伤力更大的市场手段。
(三)城乡生态“短板”
城乡生态环境保护差异化明显,推进城镇化耗费了大量农村生态资源,同时又将生态废料返还农村,导致农村水污染、土壤污染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日益严重,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甚至有失控趋势。城乡生态“短板”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生态发展不均衡,水平差异明显,城乡生态环境治理缺少协调,局部出现污染向农村扩散转移的趋势。“从1978年到2014年,江苏省城镇化率由13.7%跃升至65.2%,远高于全国54.8%的平均水平。据专家估算,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58%~60%,而江苏省城镇化率将达到75%。”[1]。相较于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高歌猛进,江苏农业生态和农村环保却现状堪忧。“除去城镇化带来的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排放以外,乡镇企业废料排放、化肥农药滥用、畜禽粪便和稻麦秸秆等农业废弃资源也都成为农业的主要污染源。”[2]二是城乡之间生态循环出现裂缝。城市发展进步离不开农村各种资源的供给,同时农村又是城市各种废料排放分解的集散地,二者良性互动有助于形成完整的生态循环链条,但一旦污染物超出农村消化负荷能力,就很可能出现生态循环裂缝。近年来江苏水资源、土壤、大气等污染事件频发便是明证。如太湖水体富营养化;苏南地区城市地下水过量开采;生物多样性处于衰退状态;空气环境质量不容乐观,常规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新污染物又加剧了叠加效应,形成复合型污染。
(四)生态文明教育“短板”
生态文明教育“短板”具体表现为生态文明教育体系实效性不足,即生态文明教育主体不明确、教育方式不灵活和教育实效性不明显,生态文化、生态意识和生态道德建设缺位。江苏一直高度重视生态文明教育体系的培育,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生态文明教育主体多局限于党政媒体,影响受众更为广泛的社会媒体组织建设仍处于较低水平。就江苏而言,生态文明建设教育体系仍未脱离人类中心主义的轨道,有些文件和宣传手段只是更新了新词术语,迷恋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语词模式切换。对于生态环境我们所缺少的是整体和全局意义上的伦理精神、使命意识以及危机意识。令人遗憾的是,许多生态教育基地都是放放图片和视频等走马观花式的操作。在涉及生态意识、生态文化和生态道德等层面时,江苏作为较早明确生态文明工程建设的省份,虽一直重视处理生态环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但在实施过程中以GDP论英雄的现象仍屡见不鲜,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回避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社会公众更乐意将生态文明建设视为政府和企业的职责。社会舆论对生态文明教育的态度也处于实用主义的怪圈,超前消费、过度消费风气不减反盛。
上述这一系列生态短板相互影响,直接决定了江苏生态文明建设亟待改变。建设生态文明是对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的根本性替代,它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层面的深刻变革和调整。江苏作为中国改革发展的缩影,如何回避西方式现代化的破坏性陷阱而率先建成生态文明社会,这需要借鉴更加丰富多元的治理理念和认知方法,而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点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为我们开辟了一个较为合适的视角。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有很多理论维度,但关切和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始终是其聚焦中国问题研究的出发点。如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著名学者大卫·格里芬所言,关注人类现代物质文明与自然界之间整体和谐关系的驱动导向作用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维度[3]。另一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柯布更是一语中的:“占主流地位的‘增长癖’或‘GDP崇拜’才是带来生态危机的根源,也是生态文明建设亟待解决的最大障碍。”[4]他提出,要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共荣以及人民大众的幸福安康作为发展的根本内容。这一核心立场与江苏生态文明建设的初衷是不谋而合的。所谓“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柯布提出的有机整体论、人与自然关系的责任论、生态教育价值和共同体设想等关涉生态文明的创见都为实现江苏绿色发展提供了理论涵养和方法借鉴。
二、江苏发展生态文明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方案
从理论上说,江苏要走出不同于西方的创新发展道路,实现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摆脱西方发展路径依赖,需要对西方发展路径的特点、面临的危机及其根源有清醒的认识,否则就会陷入“迷途而不知返”的窘境。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关注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视角作出的深刻反思。
(一)以绿色GDP评价指标体系实现经济后现代转型
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成就及其生态文明理念与实践,以小约翰·柯布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学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对于当前中国的发展路径,他们也提出了善意的批评与警示。作为中国改革发展的典型,江苏同样需要重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与看法。
第一,在发展目标上,江苏要追求人与环境的共同福祉,走超越西方工业化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作为中国快速发展的第一梯队,江苏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缩影和写照。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一系列成绩有目共睹,制造强省和教育大省的地位也一直为其添彩,但在这些经济数字的背后则是无限制地扩大生产和刺激消费,由此获得较高的GDP增速。江苏人口基数大,地域面积少,资源短缺,但产业结构仍高度依赖重化工等高能耗产业,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生态文明建设还不够协调,环境治理任务依然严峻。2007年太湖蓝藻水污染事件就是一次严重警告,因此必须构建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发展方式。柯布认为,当前中国大力推行市场化的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完全的市场经济基础上,按照他的看法,“如果市场社会主义是对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种替代,那是值得期待的一种替代”[5],但是,“如果市场社会主义最终滑向成熟资本主义,政府被经济寡头控制,那就令人担忧了”[5]。中国目前虽然对经济寡头还具有一定的掌控力,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垄断资本在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仍存在滑向“成熟资本主义”的隐忧,对此江苏也需要有足够警惕。
第二,在发展标准上,江苏应重置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发展绿色生态经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要扭转以GDP为旨归的现行经济模式,向绿色生态经济转型。这正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学者所一直提倡的:发展一种以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为目标的后现代经济。推崇增长癖好的控制型经济模式不仅大量损耗我们的自然资源、能源,也对我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带来前所未有的危害,频发的雾霾、水污染等问题都反复揭示了经济范式的转变迫在眉睫。正如柯布所呼吁的:“以人类幸福为代价来提高世界生产总值的做法应该停止了。”1989年赫尔曼·戴利、小约翰·柯布和克利福德·柯布共同研究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即后来所称的“绿色GDP”,1995年克利福德·柯布则进一步研究出了“真实发展指数”。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排除GDP中的水分,扣除因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和人口数量失控等因素造成的经济损耗成本,从而得到真实有效的国民财富总值。一个经济繁荣、生态和谐的江苏既可为中国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又能为人民安居乐业、全社会拥有青山绿水创造有利条件。
(二)重视生态城市布局,推动农业永续发展和乡村共同体建设
首先,城市化建设确实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其前提是不能浪费土地和交通等资源,应科学地考虑城市生态结构与环境容量。柯布认为,城市建设选址要立足现有土地,反对因城市平面扩张延伸而占用良田。他提出“建设方便快捷的交通供应线,减少对长距离交通的依赖,达到节约能源减缓全球变暖趋势的目的。要走向生态文明,就要减少已经统治现代性的诸多趋势”[6]。在他看来,中国很多地方城市化的做法实际上正在加剧不可持续性问题,如占用耕地推进城市化的举动会进一步加大城乡差距。江苏人口、产业和城市高度密集,人均环境容量较小,生态环境比较脆弱,这都是需要面对的实情,如何在推进城市化建设中把握可持续性原则以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效,是一项长期的课题。
其次,反对农业工业化倾向,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柯布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学者对中国大规模推行西方工业化农业的举措表示担忧,他们更期待中国将对建设工业化农业的热情转换为关注生态农业的行动。他们指出:“西方的工业化农业大量使用化肥、杀虫剂和除草剂,不仅造成严重的农业污染,损害物种多样性,消耗大量的水,造成农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还会引起意想不到的生态灾难。”[7]。在他们看来,当前中国的农业决策和关于农村发展的决定,关系到亿万中国人民福祉,甚至会影响到世界未来格局,必须十分慎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学者始终坚持反对现代性的工业化生产,主张发展有机农业,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真正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扎根于城乡平等基础上。学者大卫·弗洛伊登博格直言不讳:“我们认为,中国别无选择,唯有发展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农业。”[8]学者王治河也指出:“‘可持续性农业’‘生态农业’‘有机农业’‘自然农业’等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后现代农业的不同表现形式。”[9]55柯布建议“鼓励农民多样化生产,杜绝工业化农业”[6]。中国传统的水稻种植业、渔业、副业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当今科技兴农的时代背景下,大量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确实有力地保证了农业产量,但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人为推动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也给农村环境带来巨大破坏,间接影响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事实上,在探索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方面,我国很多地方已经有了可贵的成果。如“江西、福建等地创造的‘猪-沼气-果树’生态农业模式,北京大留民营‘农产品加工、畜牧场、养鱼塘、大棚菜’相互依存多层次循环的‘农场农林复合生态模式’等,都是生态农业或者说后现代农业在我国的创新形态”[9]57。当然,我们需要明确,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是农业大国而非农业强国的认知是客观的,调整农业发展结构,超越西方工业化农业,走后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建议为江苏实现农业发展生态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最后,建立自力更生和相互尊重的乡村共同体。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学者格外强调滋养乡村文明、繁荣农村社区的重要性。小约翰·柯布主张大力发展低碳的生态农业,发展小型、高效和多样化的有机家庭农场。自近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许多村落逐步由传统的血缘、亲缘关系和宗法关系转向现代的行政管理关系、户籍关系。伴随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深入,社区和村落日渐形成“村社共同体”“工业村”等组织形态。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人们之间的交流方式、生活态度等社会关系,而且也影响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生存关系。柯布所提倡的自力更生和相互尊重的乡村共同体,是一种内生型的生成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重塑居民对社区和村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有利于构建和谐乡村社区,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三)推崇生态文明的有机整体教育
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引导绿色消费。教化之事,要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在王治河看来,“现代工业社会的教育是一种应试教育和碎化教育,更是一种竞争式的教育。对于当前弥漫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生态危机,实体主义的知识观以及由此产生的‘碎化教育’无疑是难辞其咎的”[9]85。菲利普·克莱顿的说法更加直白:“只有教育才能把个人和公共利益如此完美融合在一起”,“教育的功能在于交给学生与所有生命共生共荣及公正分配资源和机会的知识和价值观”,“如果生态文明的理念在学生时代没有扎下根,那么,这种理念此后也就不太可能树立和发展”[10]。为此,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学者提出要建设一种关注人自我内心和周围世界的有机教育。这是一种将量子力学、生物学和自组织理论作为科学依据的后现代教育。它强调自然与社会、人与他人、社会实践与传统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统一关联性,其核心是整合、和谐与创新的有机性思维。“教育如同大自然辅助万物生长一样,本身也是一种关注生态与人的创造性过程。这在生活上是与环境相通的,在生产上是与生态相连的。”[11]
(四)注重维护生态社会的公平正义
在保障人民生态权利和维护生态正义方面,江苏应该大有作为。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江苏不仅要吸取西方的经验教训,还要牢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宗旨,与时俱进,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受西方现代性路径依赖的影响,目前比较流行的是市场经济、科技创新、民主政治等发展路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带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颜色革命陷阱”以及“生态文明陷阱”,这就要求江苏在创新发展的同时,要注重社会发展的产业平衡与公平正义,强调分配公正、社会安全、道德提升、民众幸福、环境优美和生态和谐。在大力推动科技创新的同时,要警惕科技的双刃剑效应,提防其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还需要关注农业发展,发展可持续农业,为应对日益凸显的粮食危机做好准备。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过分迷信西方的高城镇化率,在当前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应该鼓励农民留在农村,发展可持续性农业,建设小规模农场,实现工业、农业与第三产业的协调发展。
三、结论
马克思说过,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始终立足于现实基础,无论是将现代性视为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抑或是把人的生态责任与自然的内在价值实现有机关联,都在印证自己清晰的逻辑线索。相较于生态马克思主义而言,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性,但并不反对现代主义。和生态哲学不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主张反对还原主义和实证主义,但不反对科学主义。与传统生态伦理学相比较,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反对传统生态伦理思维的机械主义倾向,主张突出人类的自为责任与自在可能,但并不反对东西方文化中的主观主义。他们反对发展主义,但并非反对发展。任何理论都有自己的不可周延之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亦概莫能外,譬如人文主义色彩浓厚,更重视形而上学建构等等,但其极具鲜明特色的某些思想理念,对于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江苏而言,毫无疑问是富有理论活力和实践价值的。
江苏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走在了时代前列,但是存在的诸多问题更值得我们反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视角为我们推动生态文明进程提供了借鉴与启示。无论是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评价体系向绿色经济转型,还是建设乡村共同体,形成城乡互动以符合生态容量的结构布局,抑或提倡有机整体教育夯实生态文明教育体系,保障人民的生态正义权利,都对江苏进一步探索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创设了理论契机和实践蓝本。例如对乡村共同体建设的重视和我国传统乡贤文化的契合,对生态正义的高扬与苏南发展模式中绿色贫困的解决都存在内在的关联性。然而,我们不能满足于此,更应该看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其理论土壤来自西方文化,作为一种批判工业化社会和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后现代思潮,其文化地域性我们不能忽视,也无法跨越。更重要的是,江苏生态文明建设的立足点和着眼点应该是在中国国情、江苏省情和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发掘社会主义本质与生态文明社会的契合点。生态文明社会中的“文明”一词,意义也应该在于文化的地域性与文明的交融性,创设一种新的发展状态,这首先应该是理论的自觉,其次是现实的自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江苏建成生态文明社会或许为期不远。
[1]刘若宇.基于一致性组合评价的江苏生态城市发展水平的比较分析[J].能源环境保护,2016(2):50-54.
[2]江苏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研究课题组.江苏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实践探索[J].江苏农村经济,2017(3):28-31.
[3]李惠斌,薛晓源,王治河.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7.
[4]赵成,姜德刚,王治河.中国过程研究:第4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42.
[5]柯布.论有机马克思主义[J].陈伟功,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1):68-73.
[6]柯布,刘昀献.中国是当今世界最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柯布教授访谈录[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0(3):5-10.
[7]小约翰·柯布.中国的独特机会:直接进入生态文明[J].王伟,译.江苏社会科学,2015(1):130-135.
[8]大卫·弗罗伊登博格.中国应走后现代农业之路[J].周邦宪,译.现代哲学,2009(1):68-71.
[9]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0]克莱顿.有机马克思主义与有机教育[J].孟献丽,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1):74-77.
[11]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M].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53.
OntheEcologicalCivilizationDevelopmentinJiangsufromthePerspectiveofConstructivePostmodernism
Zhang Suqiang,Liu Kui
Jiangsu is a major economic province, but also a province with relatively scarce resources. While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has brought great environmental pressure, the grim situation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has become a bottleneck restric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im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ucture, low quali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ystem, dispar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ineffectivenes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al system are reflections of dependence on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industrial society development model. 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 call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c holism so as to achieve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as well as people and society, which sheds ligh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Jiangsu.
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7-07-08;责任编辑:陈鸿)
张苏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刘魁,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研究”(15WTD005);东南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省级基地课题立项项目“小康社会、发展正义与中国发展的全球引领力提升研究”(2242017S30005);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格伦德曼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KYLX15-0201)。
B089;X32
A
10.3969/j.issn.2095-042X.2017.06.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