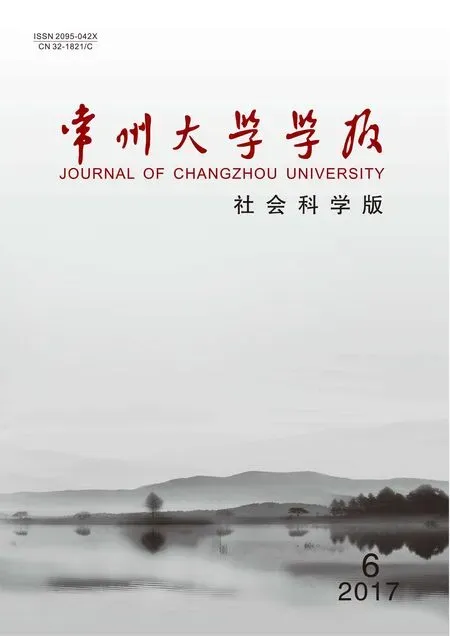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与未来
李 勇,陈艳艳
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与未来
李 勇,陈艳艳
分析马克思主义诞生于20世纪下半叶。它既是对分析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争论的超越,也是对20世纪下半叶学生工人运动的一种回应。分析马克思主义在追求马克思理论的确定性和科学性表述的同时,所展开的关于正义问题的探讨使其成功立足于英语世界的主流学术圈。时至今日,尽管作为学术流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沉寂了,但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式与精神已经渗透到了相关学科领域,并将持续影响这些学科的未来发展。
分析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正义;平等
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又被称为“不胡说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它发轫于1968—1978年间,1978年后的15年中由盛转衰。*与作为一种国际思潮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相较,英国分析马克思主义呈现出的特征稍有不同。首先,英国分析马克思主义虽然开始于哲学分析,但后期以科学理论建构为其内在特征,以塑造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为首要任务。其次,英国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要比国际分析马克思主义早,且时间层次划分比较明显。英国分析马克思主义前后共历三代。第一代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以康福斯(Maurice Cornforth)为代表,以将经验主义科学化为首要任务,同时开始科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是G.A.柯亨,柯亨在1978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成果。柯亨的工作不仅奠定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不模糊”策略,同时也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划定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重点研究领域。第三代以科林利克斯(Alex Callinicos)等人为代表,他们以各种现代科学理论为基础塑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参见ROBERTS A.E,The Anglo-Marxists:A Study in Ideology and Culture.MD:Rowman & Littlefield,1996.G.A.柯亨于1978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成果,也标志着分析马克思主义鼎盛时期的到来。同年,九月小组的成立标志着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正式形成。
一、分析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般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很难融入英语主流学术圈。以美国为例,至今未出现过重大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运动。究其原因,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与英语学术传统的对立。如逻辑实证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以及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等在美国都不受“待见”。因此,善于建构理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一直处于英语学术圈的边缘地位。分析哲学家往往以怀疑的态度审视重大理论成果,以怀疑主义态度回应其理论的深刻性与科学性。在英语世界中,任何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立足艰难,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很少对英语世界产生普遍性影响。但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缺席的情况下,英语世界产生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这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与经验哲学传统的一次伟大结合,也是历史的必然。换言之,分析马克思主义既是对分析哲学的超越,又是对20世纪下半叶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遇困境的回应。
第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的开创与引领作用。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英国出现了一批卓越的历史学家,如汤普森(E.P.Thompson)和希尔(Christopher Hill)等。他们将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与具体历史的阐述相结合,形成了享誉世界的新历史主义学派,并对英语世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但新历史主义在面对分析哲学与后现代理论“确定性”的质疑时,新历史主义陷入了困境。在对这种史学理论本身的确定性的追问中,分析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确定性”由此成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追求之一。
第二,英语世界左派政治与社会运动的需要。1956年后的英语世界新左派运动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拓展了学术与政治空间。1950—1960年代,英语哲学界的前沿仍然是语言分析学派。受这一学派的影响,人们认为大部分老生常谈的哲学问题都是语言歧义或模糊表述的结果,并且可以经由精密的语言分析得到彻底解决。新左派的兴起瓦解了日常语言哲学的统治局面,但分析的精神得以保留。新左派运动让人们知道了语言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政治依然重要。这不仅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打开了学术空间,也拓展了政治空间。
20世纪60年代末,英语世界的左派急需一种与当时政治形势相符的意识形态。这一时期,青年学生们反对大学教育,反对越南战争,为种族平等斗争等,这使得大学成了主要战场。于是,激进学生自然以斗争的方式反对机构性的学术文化。这种反对传统的结构性文化会出现两个后果:虚无主义和工人政治。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被学生中的激进分子接受。许多激进学生想把“批判的武器”纳入“武器的批判”中。他们认为长久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日常语言的学术训练,已是“清汤寡水”。因此新生的社会主义力量渴望马克思主义的完善。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了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其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清晰性”。在这场大争论之后,建立完整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被提上议事日程。人们通常认为,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偏向于政治关切,甚至阿尔都塞也不例外。实际上,分析马克思主义也同样有这种关切。这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动机有关。政治动机把大多数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召集在同一信仰之下,同时又赋予他们在各自的方向上以更广阔的空间。这些人认为自己的工作建立在光洁的石板之上。分析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特殊的文化现象,也是当时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的结构性表征。
第三,政治哲学在20世纪英语世界的复兴是分析马克思主义产生与走进主流学术圈的直接推动力与契机。20世纪60年代末,日常语言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开始衰退,政治哲学得以复兴。罗尔斯于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是这场复兴运动的标志。罗尔斯的政治哲学转向在一开始就影响了分析马克思主义,可以说,对正义问题的讨论是分析马克思主义进入英语学术文化圈的开始,也是分析马克思主义重建马克思主义并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辩护的最核心内容之一[2]128。 “正义”问题的讨论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契机。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正义”是评判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标准。正义的观念属于上层建筑,只与经济结构或生产模式有关。资本主义是滋生非正义的因素。机构性的安排与社会实践有悖于正义对资本主义的要求,但资本主义自身则无所谓正义或非正义。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探险中,他们努力证明正统观点是对的。如果失败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紧接着的任务就是要阐明“永恒正义”的概念怎样才能被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起初,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用辩护的方式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用理性的方式将研究对象表述清楚,因此研磨文本以及富于创造性的哲学重建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
这种最初的调和并没有收获良好的效果。当罗尔斯与自由主义思想在英语世界持续发酵时,马克思理论又一次遭到了质疑。于是,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不得不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内讨论“正义”问题。彼时,分析马克思主义刚刚兴起,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则是一个已然复兴的成熟学派,后者在学术界根深蒂固。相反,分析马克思主义却岌岌可危。于是,在这场学术交锋中,马克思主义关于正义问题的声音只是微乎其微。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对左派、至少对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构成了严重威胁。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成了学理上的一组悖论。面对这种困境,将马克思理论与“正义”问题打通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唯一出路。于是,他们选择了方法论的研究,并果断地抛弃了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与安德森结构主义的唯物史观),因为历史主义的论辩宏大而晦涩,导致了细节性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这种探索方式的优势也逐渐突显出来,对方法论的研究与成就最终促使分析马克思主义进入了英语世界的主流哲学圈。
总的来说,基于分析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学术和政治背景,分析马克思主义天然地具有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在其后期的发展中,学术维度得到了凸显,而实践维度日益萎缩。换言之,分析马克思主义借助科学的视角研究并超越了主流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保留了马克思关于社会秩序的观点。但随着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实践维度逐渐成了一个隐匿的维度。这使得分析马克思主义成了一种思维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在英语世界中,分析马克思主义似乎使马克思主义融入了主流的自由哲学与社会科学,但同时因为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维度,许多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只能被归于其他学派。
二、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
基于其分析方法与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在规范理论范围内为马克思主义辩护,这带来了两个结果。第一,分析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性。分析马克思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主义”的地位,这种观点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是独特的。这是一项重要的贡献,这也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者以自己希望的方式改变世界。在此基础上,分析马克思主义重提政治理论,并将其置于理论的核心位置。第二,以标准化方式为马克思主义正统命题辩护,在规范理论中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分析马克思主义在为马克思的某个命题辩护之前,通常会将其转换为哲学或社会科学标准所认可的表达形式[3]。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马克思主义成果在英语世界被视为主流思想之外的异类,这并不仅是出于政治原因和意识形态上的抵制,也由于理论预设的区别。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使马克思的观点被逐渐接受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成了英语世界学术讨论的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被普遍接受了的基础理论都很难被所谓的“规范科学”的规范过程改变。但在特殊情况下,基础理论的架构也可能通过彻底的“科学革命”发生改变,但理论却难以被推翻,历史唯物主义也不例外[4]。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直处于英语学术讨论的外围,但对于分析马克思主义而言,这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相较于社会主义理论更具有科学性。早期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给予历史唯物主义和正义问题以同等程度的关注。柯亨在1978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内部讨论的核心问题,也将历史唯物主义命题带入了英语世界的主流学术圈。柯亨将社会模式的变化置于历史内源性发展的环节上,从而完成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自然化过程[2]132-133。柯亨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观不同于黑格尔的目的论的历史观。目的论用现象的终点或目的解释现象。而马克思主义用因果律来解释历史的结构与方向。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获得一种信念:人类历史的结构与方向不是被植入的,而是本身所固有的。由于马克思认为历史事件本身并没有意义,所以他扬弃了黑格尔对历史的目的论解释。历史的意义就像自然的意义那样,有果必有因。历史与自然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历史独立于研究者的兴趣,其特征还有待被发现。在柯亨看来,马克思维护了黑格尔理论的正确性,没有屈服于现代史学的反理论潮流。因此,马克思让黑格尔站起来,并不是因为他把辩证法运用于解释实体、物质等概念,而是把黑格尔的理性直觉纳入与现代科学实践相一致的解释模式中。因此,历史的阐释完全可以建立在科学与分析的基础之上,这为分析马克思主义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提供了前提。
三、公正与平等的哲学追求与困境
20世纪下半叶,自由主义有罗尔斯的政治哲学转向,马克思主义有分析转向。有人认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只是把分析哲学用于马克思理论的阐释,其实作为原则的分析哲学对分析马克思主义之影响实则在经济领域。经济是社会科学中最具技术性的部分,也是对自我意识的明晰性要求最高的部分。就整体而言,分析马克思主义在经济理论的建构中收获颇丰。正因如此,分析马克思主义早期对公正与平等的追求并不是一种价值追求,而是一种哲学追求,同时也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内部要求[5]。
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平等”的理解一直是矛盾的。第一代自由主义者主要维护私有财产权,反对平等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再分配观点明显受到平等主义的影响,但也贬低了平等主义。这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把自己的目标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区别开来而远离平等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全新的社会模式。这种社会模式下的政治制度已经超越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视域。
对分析马克思主义而言,重要的是找出马克思理论中哪些是可以被规范化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常常会因为力求理论的简洁与精确,而牺牲了基本的洞察力与解释力,这使他们更多地关注平等而不是价值。马克思把价值贯穿于自我实现过程中,并置于共同体的自主性中。主流经济学着重研究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因此平等也落入了分配的领域中,而自我实现、共同体、自主性等观点乏人问津。经济学提升了理性选择的解释效用。理性的原则被用于解释普遍的经济交往,而经济分析最擅长解释的是私有财产领域中的市场制度。因此,在处理平等问题时,经济学家们自然会像自由的平等主义者那样认为对私有财产进行再分配有助于实现平等,资本市场实现了资源的初次分配后,政府会根据一种或多种平等主义理想实行再分配。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反对引进经济学家的这种解释框架。
分析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理论中所用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遭到了哲学维度上的抵制。然而,正是这种哲学维度上的抵制,使得分析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哲学维度上再塑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马克思曾抨击古典经济学家的个人主义,也批判政治哲学家以契约的形式把个人从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和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重要捍卫者。一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也接受了这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如埃尔斯特认为社会科学家当揭示社会现实的微观基础,但事实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仅是一种解释的视角,它在广泛的规范性评价系统中与规范性要求兼容。埃尔斯特做了大量的工作考察这种现象的哲学意义,比如在认识论方面的不协调与对立。他认为马克思的规范性与这里所描述的图景大致契合。埃尔斯特重建和维护马克思关于自我实现的承诺,也为自主性与共同体辩护。
四、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优势与未来
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在现代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内部发展出了三个学派:一个正统的继承者和两个“背叛者”。安德森“类型学”的马克思主义是它正统的继承者。阿尔都塞的“强结构主义”以社会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构来决定历史趋向,安德森将这种“强结构主义”发展为“弱结构主义”,即类型学的结构主义,认为历史与社会中存在着各种结构,而这些结构有强弱之分[6]。但在本质上,这一“类型学”的唯物史观的思维范式仍然内含有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以及本质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维特征。两个“背叛性的”继承者指的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基于蒙蔽主义,是阿尔都塞结构主义中混乱面的表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甚微[2]122。 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拒斥诸多基本前提假设,而这些前提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启蒙运动继承者的共识,这些共识包括:表象世界的意义与“散漫实践”所领会的意义并不一样等[2]122。因此,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文本以及马克思精神少有关联。而分析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严谨性,同时又否定了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对马克思辩证法来源于黑格尔的否定,也拒绝了结构主义的宏大叙事及其模糊不清的理论预设,并竭力论证与完善马克思辩证法体系的科学性。可以说,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未来举足轻重[2]122。
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崛起之前,很少有人仔细研究过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独特性。传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共识,那就是马克思从黑格尔发展出一套辩证的方法论,从而使其理论独立于资产阶级的科学与哲学。但阿尔都塞偏离了这个共识。阿尔都塞花了大量的精力去证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的理念辩证法是异质的方法论体系。换言之,他试图证明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论“不是什么”,从而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诠释科学的方法论应该具有的内涵。阿尔都塞的工作其实是在否定马克思辩证法的历史前提下来为马克思唯物辩证法辩护。卡尔·波普尔极力拥护这一观点[7]。分析马克思主义在阿尔都塞后举起了马克思方法论论证的大旗。
如果马克思关于社会运动规律等理论的解释模式大体上是符合现代科学目标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已经完成或者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实施科学的方法论证,即提出概念,构建理论,证实假设及其他。但是没有人将这一过程明确地呈现出来。如果马克思的方法论是符合现代科学的,承认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解释目标是揭示现实中因果律的确定性,那么马克思就必然会给他的解释设定一个目标。但是这个目标似乎在分析马克思主义之前无人知晓。以往关于辩证法的论证之所以没有说服力,主要是因为这些论证给出的证据存在于精心设计的论证中。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了辩证的解释方法并没有说明哪些内容必然会得到解释,也没有指出什么是无法解释的,即辩证的方法论没有明确自己的解释边界。如果辩证法的解释边界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那么它就只能算是在前理论水平上指导思想的途径。诚然,启发式的方法不会遭到鄙视,但是没有现代科学的中转,这种方法显然无法触及真理。在意识到马克思辩证方法论的独特性以及其独特性论证的缺失之后,分析马克思主义将最初重构马克思主义和为马克思主义传统辩护的目标,转换到了对辩证方法论的科学阐释与建构上。
分析马克思主义也与其他马克思主义流派命运不同。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仅仅在学术文化的边缘得到了保留,在结构主义与分析马克思主义之后,我们还看不到它重生的希望。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最强劲对手,如今已成为历史,甚至许多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投入到其他哲学流派之中。分析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尽管大多数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投入到其他学术流派,即使他们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还是分析哲学家。与此同时,他们也没有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事实上,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领地可能会被占领,但其掀起的第一波浪潮已经汇入了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科学中。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像自耕农那样精细地阐述和评价马克思的观点,在此过程中,他们中大部分人最终把马克思主义融入到自由的政治哲学与经验的社会科学。但正如上文所述,这种努力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不仅经得起分析哲学的考察,而且以更为有力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因此,尽管分析马克思主义已经离开了英语学术的前沿阵地,但他们的重建工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1]李勇.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研究视阈[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2):155-160.
[2]LEVINE A.A future for Marxism?[M].London:Pluto Press,2003.
[3]ROEMER E J.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an economic theor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73.
[4]KUHN S T.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15.
[5]李勇,张懿.柯亨论公正社会的可致性[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5(2):18-22.
[6]李瑞艳,乔瑞金.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思维范式探析[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6(3):34-38.
[7]POPPER K.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58:19.
OntheEarlyDevelopmentandFutureofAnalyticalMarxism
Li Yong, Chen Yanyan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nalytical Marxism emerged. It is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argument between the analy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western Marxism. It is also a response to the movement of students and worker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During the pursuit of certainty and the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theory, Analytical Marxism established its name in the English mainstream academic circle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n the issue of justice. At present, although Analytical Marxism is no longer popular as an academic genre, the analytical method and spirit of Analytical Marxism has penetrated into relevant disciplines, and will continue influenc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se disciplines.
Analytical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justice; equality
2017-09-26;责任编辑:陈鸿)
李勇,哲学博士,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陈艳艳,哲学博士,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讲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研究”(16BZJ007)。
B17
A
10.3969/j.issn.2095-042X.2017.06.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