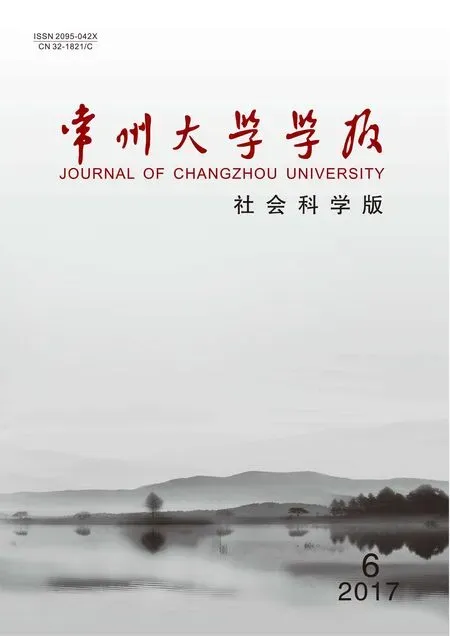“逸”:恽格绘画美学思想的核心观念
张 晶
“逸”:恽格绘画美学思想的核心观念
张 晶
“逸”是宋元以来文人画的重要价值观念。唐代朱景玄作《唐朝名画录》,最早以“神、妙、能、逸”四品评画,所指系“非画之本法”、不主故常的画法。宋代黄休复作《益州名画录》也以四品评画,却以“逸、神、妙、能”为评价等级,并以“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加以界定。“逸”成为最高评价品级。“逸”在“元四家”尤其是倪瓒的绘画思想中成为最为鲜明的旗帜。在清初六家之一的著名画家、画论家恽格(南田)的画论及创作中,“逸”成为核心的绘画美学观念及价值标准。而南田画论中的“逸格”“逸品”“逸气”,一方面是认同宋元以来的文人画“逸”的观念传统,一方面又从创作和评论的不同角度,为“逸”增添了新的内涵,使之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质。
“逸”;恽格;《南田画跋》;南北宗
作为清初杰出的画家与画论家,恽格(南田)对中国绘画美学的贡献是尤为突出的。他的画论,继承宋元文人画的传统并加以发展,代表了清初画坛的艺术精神。南田画论集中于《南田画跋》,同时还在其大量的题画诗中呈现出来。纵观南田非常丰富的画论文献,可以将其绘画美学思想概括在“逸”的范畴之中,同时,又可以见出对“逸”的充实与发展。因为《南田画跋》版本系统复杂,本文又并非是从文献角度切入对南田画论的研究,而是依据较为可靠的文献进行理论分析,故以卢辅圣主编之《中国书画全书》所收录之《南田画跋》及吕凤棠校点之《瓯香馆集》为文献依据,展开对南田画论的探究。
恽格(1633—1690),字寿平,号南田,常州武进人。入清之时,南田虽然才十几岁,却因其父忠于明朝的倾向而具有遗民心理。《清史稿》中的《恽格传》对其生平及思想的概括颇为客观,史载:“恽格,字寿平,后以字行,改字正叔,号南田,江南武进人。父日初,见《隐逸传》。格年十三,从父到闽。时王祈起兵建宁,日初依之。总督陈锦兵克建宁,格被掠,锦妻抚以为子。从游杭州灵隐寺,日初侦遇之,绐使出家为僧,乃得归。格以父忠于明,不应举,擅诗名。鬻画养父。画出天性,山水学元王蒙。既与王翚交,曰:‘君独步矣!吾不为第二手。’遂兼用徐熙、黄筌法作花鸟,天机物趣,毕集豪端,比之天仙化人。画成,辄自题咏书之,世号‘南田三绝’。虽自专意写生,间作山水,皆超逸,得元人冷淡幽隽之致。王时敏闻其名,招之,不时至。至,则时敏已病,榻前一握手而已。家酷贫,风雨常闭门饿,以金币乞画者,非其人不与。康熙二十九年,卒,年五十四。子不能具丧,王翚葬之。”[1]《清史稿》的记载说明了南田身世的曲折及君子固穷的高洁品性,同时,也指出南田的画风渊源,可以使我们较为全面地了解南田的画品与人品。
一
南田画学思想尤为丰富,倘要以一个核心观念统领之,那便是“逸”。这在《南田画跋》及其题画诗中有着普遍呈现。“逸”作为中国画论的审美范畴,有其久远的传统及变迁,当然并非南田首创;但南田在其绘画实践和画论中对“逸”的理解与表述,既是对“逸”的相关内涵的传承,又有其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义。在南田画论中,“逸”居于审美价值系统的顶端,从画家品格到画风笔墨,都是南田所标举的至高标准。我们可以从其画论中得见其对“逸”的推崇:
纯是天真非拟议可到乃为逸品。当其驰毫点墨,曲折生趣百变,千古不能加。即万壑千崖穷工极妍有所不屑。此正倪迂(按:即倪瓒)所谓写胸中逸气也。徐子有旷览人外之致,王山人因以此帧聊供卧游,笔墨神契遗象忘言当自得之。[2]233
不落畦径谓之士气,不入时趋谓之逸格。其创制风流昉于二米盛于元季泛滥明初。称其笔墨则以逸宕为上,咀其风味则以幽淡为工。虽离方遁圆而极妍尽态,故荡以孤弦和以太羹,憩于阆风之上。泳于泬寥之野。斯可想其神趣也。[2]233
逸品其意难言之矣。殆如卢敖之游太清,列子之御泠风也。其景则三闾大夫之江潭也,其笔墨如子龙之梨花枪公孙大娘之剑器。人见其梨花龙翔而不见其人与枪剑也。[2]236
郭恕先远山数峰胜小李将军寸马豆人千万,吴道子半日之力胜思训百日之功,皆以逸气取胜也。[2]236
高逸一种,盖欲脱尽纵横习气,淡然天真。所谓无意为文乃佳,故以逸品置神品之上。若用意模仿,去之愈远。倪高士云:“作画不过写胸中逸气耳。”此语最微,然可与知者道也。[3]242
以上仅是从《南田画跋》中摭举出南田正面论“逸”之几例,其他在《画跋》及其题画诗中尚有多例以“逸”评画。此处有“逸气”“逸格”“逸品”等几种说法,但其间并无明显的区别。尽管所指可能在画家主体层面和作品层面有所不同,却很难作出明确的分野。由南田对“逸”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一是画之“逸格”(“逸品”)在艺术上脱略笔墨畦径,不入时趋,这也是画品之“逸”的本来之义;二是绘画风格以幽淡为工,而远离世俗极妍尽态;三是“逸格”(“逸品”)更在于画作所体现出的精神气韵自由超拔,如“卢敖之游太清,列子之御泠风”;四是恽南田对于“逸”的理解,多是要直接绍述元代画家如倪瓒、黄公望等人的绘画观念。
南田在画风上师承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子久),而在绘画观念上最为推崇倪瓒(迂翁)。倪氏对于“逸气”的标举是稍有美术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的。倪瓒对“逸气”有这样的著名论述:
以中每爱余画竹。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之,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直没奈览者何。但不知以中视为何物耳。
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近迂游偶来城邑,索画者必欲依彼所指授。又欲应时而得,鄙辱怒骂,无所不有冤矣乎,讵可责寺人以不髯也。[4]
这两段话突出地表现了倪氏作画以“逸气”“逸笔”为其美学追求的特征。“逸”可被视作宋元文人画最具代表性的美学观念,在元代四大家这里也是绘画理论的焦点,其中又以倪瓒最为突出。不求形似,抒写主体情志,这是倪氏所云的“逸气”“逸笔”的内涵。
南田对倪瓒的推崇,更多的在于主体精神世界的契合。在他看来,倪瓒(云林)的境界是超脱凡俗的,而臻于“寂寞”。在南田的话语中,“寂寞”是世俗所无法理解的孤高境界。如他认为“云林通乎南宫(米芾),此真寂寞之境也,再著一点便俗”[2]230。这里所言之“寂寞”,是一种孤高难及的精神境界,这在南田画论中都是这种用法。这种境界,正是南田对艺术的追求所在。其《题雪中月季》:“冰鳞玉柯危干凝碧,真岁寒之丽宾,绝尘之畸客,吾将从之与元化游。盖亦挺其高标无惭皎洁矣。”[2]236所题雪中月季之品格,正是南田的精神世界之映像。心通造化,意侔真宰,南田对米芾、倪瓒、黄公望这一系画家,都是从这种精神境界来理解的,而且引为心灵的知己。如其题画云:“吾尝欲执鞭米老俎豆黄倪,横琴坐忘或得之于精神寂寞之表,残春高馆梦徘徊,风雨一交笔墨再乱,将与古人同室而溯游不必上有千载也。”[2]240可见南田对米芾、倪瓒、黄公望这一脉画家的认同,更为重要的是在于“精神寂寞之表”的层面。南田在题画诗中借题咏画作表露自己的精神世界。“薜荔山阿若有人,富春图里过残春。欲知迂老驱毫意,天海苍茫一问津。”[3]18“柳路溪风拂面寒,几枝晴雪傍檐端。暗香瘦影分明处,把酒山堂待月看。”[3]50“醉后闲呼鸾鹤群,北山何用著移文。知君高志轻轩冕,游戏真如出岫云。”[3]74精神境界的高远寂寞,也正是南田重“逸”的审美观念的一个主要内涵。
二
现在来看一下“逸”作为书画品评标准的含义及其地位变迁。
“逸”在中国书画发展史上是作为一个品级出现的,较早作为成熟的评价等级是在唐代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中。朱氏的《唐朝名画录》以“神、妙、能、逸”四个品级评定画家的成就地位,其高低次序亦以此为序,但“逸”的品位是有些特殊的,这也就为此后在黄休复的画评体系中,“逸”成为最高品级埋下了“伏笔”。“逸品”列在最后,共王墨、李灵省和张志和等三位画家。从景玄对这三位画家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列为“逸品”的画家都是不拘常法、不落畦径的,而且是以“墨戏”的态度与画法对文人画产生深刻影响的。我们分别看一下这三位画家的画风特征。一是王墨。“王墨者不知何许人,亦不知其名,善泼墨画山水,时人故谓之王墨。多游江湖间,常画山水、松石、杂树。性多疏野,好酒,凡欲画图嶂,先饮。醺酣之后,即以墨泼。或笑或吟,脚蹙手抹。或挥或扫,或淡或浓,随其形状,为山为石,为云为水。应手随意,倏若造化。图出云霞,染成风雨,宛若神巧,俯观不见其墨污之迹,皆谓奇异也。”[5]88王墨的形迹、为人及画风,可谓狂放不羁,不合常理,但又是士人画的代表。以此人为“逸品”,可以说是相当典型。第二位是李灵省。“李灵省落托不拘检,长爱画山水。每图一幛,非其所欲,不即强为也。但以酒生思,傲然自得,不知王公之尊重。若画山水、竹树,皆一点一抹,便得其象,物势皆出自然。或为峰岑云际,或为岛屿江边,得非常之体,符造化之功,不拘于品格,自得其趣尔。”[5]88李灵省之“逸”,侧重于“出于自然”,“不即强为”。第三位是张志和,也就是写了著名的《渔歌子》词的那位词人。“张志和或号曰烟波子,常渔钓于洞庭湖。初颜鲁公典吴兴,知其高节,以渔歌五首赠之。张乃为卷轴,随句赋象,人物、舟船、鸟兽、烟波、风月,皆依其文,曲尽其妙,为世之雅律,深得其态。”[5]88张志和被朱景玄定位为“逸品”,以其深契于文人情怀。《四库全书提要》述《唐朝名画录》之旨云:“所分凡神、妙、能、逸四品,神、妙、能又各别上中下三等,而逸品则无等次,盖尊之也。初庾肩吾、谢赫以来品书画者,多从班固古今人表分九等。《古画品录》陆探微条下称上上品之外,无他寄言,故屈标第一等,盖词穷而无以加也。李嗣真作《书品》后,始别以李斯等五人为逸品。张怀瓘作《书断》,始立神、妙、能三品之目。合两家之所论定,为四品,实始景玄。至今遂因之,不能易。”[5]65近人余绍宋撰《书画书录解题》,评述朱氏的《唐朝名画录》时说:“是编以神、妙、能、逸分品,前三品分三等,逸品则不分,盖既称逸,则无由更分等差也。”[6]363这段评述指出了“逸品”与其他三品的不同之处。朱景玄为是书所作自序尤能见其宗旨所在:“景玄窃好斯艺,寻其踪迹,不见者不录;见者必书。推之至心,不愧拙目。以张怀瓘《画品断》神、妙、能三品,定其等格上中下,又分为三。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以表其优劣也。”[5]68将“逸品”列入,并明确指“逸品”的涵义为“不拘常法”。
同样是以四品论画,迨及北宋黄休复,则将其顺序作了一个大翻转,即以“逸、神、妙、能”四品为序论画。如果说朱景玄敏锐地发现了逸品画家的存在,并予以充分表述,却仍将其作为另类进行品评的话,那么到黄休复则是名正言顺地将“逸品”置于至高地位,而以“神品”居于其后。《四库全书提要》评述此书说:“所记凡五十八人,起唐乾元,迄宋乾德,品以四格:曰逸,曰神,曰妙,曰能。其四格之目,虽因唐朱景玄之旧,而景玄置逸于三品外,示三品不能伍。休复此书又跻逸品于三品之上,明三品不能先。其次第又复小殊。逸格凡一人,神格凡二人,妙格上品凡七人,中品凡十人,下品凡十一人,而写真二十二处,无姓名者附焉。”[6]368黄氏所评“逸品”者只有一人,即孙位;“神品”二人,即赵公祐、范琼。《益州名画录》所品基本上是益州画家,有地域上的局限性,然黄休复的评品标准却是有着自觉的审美价值观的。黄氏对于“逸格”作了理论界定,其云:“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7]这个理论界定内涵准确而丰富,预示了此后中国文人画的审美取向。黄氏认为“逸格”之所以置于最高一层,罕有其匹。“逸格”之画,超越规矩方圆,不屑彩绘精研,得之自然,难以效仿。其画法颇为简率,其襟抱超然脱俗。
“逸”可以说是宋元迄清代文人画美学观念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能够绾合近古时期文人画思潮的基本脉络。从苏轼的“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到二米的墨戏云山,从董、巨到元四家,都可归在“逸”的旗帜之下。明代的董其昌在对文人画思潮的推波助澜中将这一脉系张皇使大,这也直接影响了清初六家的创作祈向。恽南田的绘画批评及自己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是这一脉系的承续与发展。
如人们所熟知,董氏的画论名著《画禅室随笔》,在画史中提出“南北宗”说,以禅之南北宗比拟画之南北宗,使这一脉系判然分明。其说曰:
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东坡赞吴道子、王维画壁亦云:吾于维也无间然。知言哉![8]143
董其昌提出的画史的“南北宗”,很显然,是以“南宗禅”拟之文人画一脉,其源在于王维。其后则有宋之董、巨、二米,至元代则有四大家。吴道子本为唐代第一位的大画家,朱景玄作《唐朝名画录》,以“神、妙、能、逸”四品评画,“神、妙、能”各品内又置上中下,“神品上”是最高品级是毫无悬念的。朱景玄仅以吴道子(道玄)一人为“神品上”,可见,吴道子在唐代画坛地位之尊。而苏轼的《王维吴道子画》中,虽也承认“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即王和吴)尊”,而实际上,却是扬王而抑吴:“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9]苏轼以非常明显的文人画立场对王维和吴道子进行轩轾,称吴为“犹以画工论”。
董源和巨然,也是这条脉系上的重要一环。董源生活在五代南唐时,因其曾任南唐的北苑副使,也称董北苑。巨然是其弟子。董、巨的成就主要在山水画上。米芾最为推崇董源,也兼及巨然。在《画史》中,米芾论述董源画时说:“董源平淡天真多,唐无此品,在毕宏上。近世神品格高无与比也。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色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10]看来董源多为江南山水。沈括论书画也是文人画的立场,其评董源:“江南中主时,有北苑使董源善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其后建业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体源及巨然画笔皆宜远观,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如源画《落照图》,近视无功,远观村落杳然深远,悉是晚景,远峰之顶,宛有返照之色,此妙处也。”[11]在对董巨作品的具体评价中,揭示其特征所在。董巨的地位,是米芾将之抬高的,米芾对董源的评价“格高无与比也”,可谓无以复加。元人汤垕也说:“元(源)在诸公之上”,又定巨然为董源正传,董巨并尊的观念就确立了。
作为宋代著名的书法家和画家,米芾的地位和影响更为广泛。米芾与其子米友仁,画坛称之为“二米”,在董其昌所描述的这条南宗的脉系中,更是举足轻重的环节。米氏父子善为“墨戏”。“墨戏”是即兴作画,信笔而为。《图绘宝鉴》述米芾、米友仁的画风:“米芾,字元章。天资高迈,书法入神。作画喜写古贤像,山水其源出董源。天真发露,怪怪奇奇,枯木松石,自有奇思。”[12]443又述米友仁:“米友仁字元晖,元章之子。能传家学,作山水清致可掬。略变其父所为成一家法。烟云变灭,林泉点缀,草草而成,不失天真。意在笔先正是古人作画妙处。每自题其画曰:墨戏。晚年多于纸上作之。”[12]449“墨戏”是米家父子的标志性画法,也是“逸”的美学观念下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现象。笔者曾有专文研究“墨戏”,曾经指出:“突出主体的意趣,随意所适,是‘墨戏’在创作主体方面的特征。既然以‘适意’为其旨归,就必然打破那种酷肖物象的摹仿式画法,而以画家的主体意趣恣意挥洒。离客观而趋主观,决不要求笔下形象的逼似物态,而是要在形象中寄托生发主体的意趣,‘写意不求形似’是‘墨戏’的技法上的特点。”[13]二米的“墨戏”,对于元代画风及画论有深刻影响,宜乎米芾成为元四家的追慕对象,同时,也成为董其昌所倡南宗画的主要关节。南田在题王翚仿“米山”画时曾指出其渊源:“米襄阳墨戏一正千古画家谬习。观其高自标置,谓无一点吴生习气。盖唐人画法,至宋乃畅。米家父子,又一变耳。石谷子(王翚)深得墨戏三昧,焕若神明,洗尽时人畦径。”[3]150南田于此指出了二米的“墨戏”在文人画流变中的地位,也可以看出“墨戏”与“逸”是同一机杼的。南田也认为倪瓒的画风也是源于米芾:“能与米颠相伯仲,古来还只数倪迂。应将尔雅鱼虫笔,为写荒林叠嶂图。”[3]167
元四家(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最能代表“逸”的美学观念,也是董其昌标举的南宗画的典型。“逸”是元代画坛上最为鲜明的旗帜,也包括了“墨戏”在内。倪云林力倡“逸笔草草”“胸中逸气”是人所共知的。董其昌评倪氏之语可见元四家所依之传统:“迂翁画在胜国时可称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历代唯张志和和卢鸿可无愧色。宋人中米襄阳(米芾)在蹊径之外,余皆从陶铸而来。元之能者虽多,然禀承宋法,稍加萧散耳。吴仲圭(吴镇)大有神气,黄子久特妙风格,王叔明奄有前规,而三家皆有纵横习气。独云林古淡天然。米痴(米芾)后一人而已。”[8]144吴镇论画也说:“墨戏之作,盖士大夫词翰之余,适一时之兴趣,与夫评画者流,大有寥廓。尝观陈简斋《墨梅》诗云:‘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此真知画者也。”[14]黄子久在创作实践上为后世取法者多,恽南田即以子久为宗师。他的画格主要是学董源、巨然而有所变化。清初“四王”之一王原祁评黄子久说:“大痴(黄公望)得董、巨三昧,平淡天真,不尚奇峭,意在富春、乌目间也。”[15]清初六家在画论上多从董其昌的“南北宗”说上来,师法元四家在其画论中比比皆是,画面上题写仿大痴倪迂者为数众多。实际上清初六家自有其个性风貌与时代品格,而在理论上却是张扬董其昌的南宗传统的。
三
恽南田的画论标举“逸格”“逸品”“逸气”,而且对于董、巨、米芾及“元四家”,在其题跋和诗作中都多所致意;而实际上,他的创作并不拘守于宋元以来文人画那种“逸笔草草”“笔简形具”的简率作风,而对“逸”的理解,也更多的是在精神境界上的超越与脱俗。南田对“逸”的理解与阐释有更为丰富、更具有时代意义的内涵。心灵与精神上的寂寞之境,这是其所主张的“逸格”的最为重要的内涵,而不一定以笔墨简率为“逸”的规定。事实上,观南田的画作,可以看出,都并非是“逸笔草草”、视竹为麻的。南田论“高简”一条:
高简一种不必以笔墨繁简论。如于越之六千君子、田横之五百人、东汉之顾厨俊岂厌其多?如披裘公不知其姓名,夷叔独行西山,维摩诘卧毗耶惟设一榻岂厌其少?双凫乘雁之集海滨,不可以笔墨繁简论也。然其命意大谛如应曜隐淮上,与四皓同征不出,挚峻在汧以书招之不从,魏邵入牛牢立志不与光武交,正所谓没踪迹处潜身,于此想其高逸庶几得之。[2]237
此处所说的“高简”即是“高逸”,其意旨在于精神世界的超迈高洁,如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南田所推崇的画作,如《为董十画松溪图》“以君丘壑心,发我林泉想。曲折入毫端,玲珑落指上。真宰无秘趣,空灵动新赏。烟滩翻层波,风谷藏秋响。沧洲如有求,梦与高云往”[3]7,笔墨曲折,细入毫芒,也无害于高逸之作,关键在于精神境界之高洁。 与“逸”相对的则是“俗”,能够脱俗方可谈“逸”。
由主体的寂寞精神境界而至画境之参乎造化,侔于真宰,这也是南田所谓“逸格”的重要内涵。南田有一段为人所熟知的话:“谛视斯境,一草一树,一丘一壑,皆洁庵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其意象在六合之表,荣落在四时之外。将以尻轮神马,御泠风以游无穷,真所谓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尘垢糠粃,绰约冰雪,时俗洁庵游心之所哉?”[3]101这里所描述的,与其说是洁庵先生的画境,勿宁说是南田所最为心仪的画境。它超乎尘滓,通于造化,非凡俗所可拟。南田论画又曾言:“出入风雨卷舒苍翠,走造化于笔端,可以哂洪谷笑范宽醉骂马远诸人矣。”2[239]在他看来,这种画境极为难能可贵,如他评价元代画家方从义的画境时说:“方壶泼墨,全不求似,自谓独参造化之权,使真宰欲泣也。宇宙之内,岂可无此种境界!”[3]248这是一种至高的境界,看似玄虚,却体现出中国画的根本精神。
南田所谓的“不落畦径”“不入时趋”,作为其所标举的“逸格”“逸品”的重要涵义,容易给人以忽略笔墨随意点染的误解,其实,南田之意是不为前人规矩所束缚,饱参古人后而自成一家,绚烂之极而达于自然。如其评黄公望《秋山图》时说:“董宗伯尝称子久秋山图为宇内奇丽巨观,予未得见也。暇日偶在阳羡与石谷共商一峰法,觉含毫渲点之间似有苍深浑古之色,倘所谓离形得似,绚烂之极仍归自然耶!”[2]239由法度入而臻于自在,南田借为石谷(王翚)临黄子久《富春图》以发其意:“石谷子凡三临富春图矣。前十余年曾为半园唐氏摹长卷,时犹为古人法度所束未得游行自在。最后为笪江上借唐氏本再摹遂为弹丸脱手之势。娄束王奉常闻而异之,属石谷再摹,予皆得见之。盖其运笔时精神与古人相洽,略借粉本而洗发自己胸中灵气,故信笔所之不滞于思、不戾于法,适合自然直可与之并传。”[2]235对于其所师法的宗匠,南田亦有所批判分析,如认为:“子久浮岚暖翠则太繁,沙碛图则太简。脱繁简之迹,出畦径之外,尽神明之运,发造化之秘,极淋漓飘渺而不可知之势者,其惟京口张氏所藏《秋山图》、阳羡吴光禄《富春卷》乎!学者规摹一峰,何可不一见也。暇时得小卷,经营布置略用《秋山》《富春》两图法,似犹拘于繁简畦径之间,未能与古人相遇于精神寂寞之表也。”[2]235在南田看来,“逸”不当以笔墨繁简论,而应视其能否得精神寂寞之表。
从绘画风格的角度讲,元人尤其是四大家的标志性画风,“荒寒”二字当之。而南田对元画的品鉴,则与此略有不同,他认为元画最能体现时代特征的应是幽淡、幽秀的风格。这种认知其实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南田作品的主导风格。南田论元人画风谓:“元人幽秀之笔,如燕舞花飞揣摸不得,又如美人横波微睇,光彩四射,观者神惊意丧,不知其所以然也。”[2]239又说:“元人幽淡之笔,予研思之久,而犹未得也。”[2]239“元人幽亭秀木,自在化工之外一种灵气。惟其品若天际冥鸿故出笔便如哀弦争管声情并集,非大地欢乐场中可得而拟议者也。”[2]240幽淡或幽秀也是与甜俗畦径相对的,且有一种神秘感在其中。南田题画诗多以幽淡之境为尚,如:“拂黛罗青山鬼知,春风不动岫云迟。藤花细落松声起,洗耳清泉独坐时。”[3]149“天机发静趣,灵境出无心。停弦听清籁,声不在瑶琴。”[3]152南田论画亦主“静气”,如题石谷画所云:“湿翠如烟出研池,此中静气有谁知?含毫得意应思我,烛跋西窗夜语时。”[3]149“静气”,也就是幽淡风格的要素。这些都可列诸南田论画主“逸”的核心观念之下。
南田画论集中在其《南田画跋》之中,而其题画诗里也有丰富的画学思想。“逸”可以作为总的概括,却又有着渊深的历史意蕴,同时,又注入前所未有的时代气息。南田的画论,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与玩味。
[1]赵尔巽.清史稿:卷五百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906.
[2]恽寿平.南田画跋[M]//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11册.2版.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
[3]恽寿平.瓯香馆集[M].吕凤棠,点校.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
[4]倪瓒.论画[M]//沈子丞.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205.
[5]朱景玄.唐朝名画录[M]//于安澜.画品丛书.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
[6]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M].江兴佑,点校.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
[7]黄休复.益州名画录[M]//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1册.2版.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188.
[8]董其昌.画禅室随笔[M]//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5册.2版.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
[9]苏轼.苏轼选集[M].王水照,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4.
[10]米芾.画史[M]//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2册.2版.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258.
[11]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七[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146.
[12]夏文彦.图绘宝鉴[M]//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3册.2版.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
[13]张晶.墨戏论[J].学术月刊,1992(7):61-66.
[14]吴镇.论画[M]//沈子丞.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206.
[15]王原祁.麓台题画稿[M]//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12册.2版.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282.
“Yi”:TheCoreConceptinYunGe’sPaintingAesthetics
Zhang Jing
“Yi” has been an important value in literati paintings since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Zhu Jingxuan in the Tang Dynasty took Shen, Miao, Neng and Yi as the four standards in painting criticism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n his bookFamousPaintingsoftheTangDynasty,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standards are “not the original law of painting”, but in an innovative way. Huang Xiufu in the Song Dynasty also used four standards in painting criticism in his bookFamousPaintingsofYiZhou, but in an order of Yi, Shen, Miao and Neng by defining that “limited by the established rules, and paying too much attention to color description. Using simple methods in painting, the shape is in a natural way. It doesn’t imitate but transcends the surface meaning, which is called the form of Yi”. Thus, “Yi” has become the highest standard. “Yi” became the most distinctive flag of “the four famous painters in the Yuan Dynasty”, especially in Ni Zan’s painting thoughts. “Yi” also became the core painting aesthetic concept and value of Yun Ge’s (Nantian) painting criticism and paintings, who was one of the six famous painters and painting critic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On the one hand, “Yi Ge”, “Yi Pin” and “Yi Qi” in Nantian’s painting criticism have been the approval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Yi” in literati paintings since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give “Yi” a new connotation and distinctive quality of the time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creation and comment.
Yi; Yun Ge;Nantian’sPostscriptofPaintings;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schools
2017-08-15;责任编辑:陈鸿)
张晶,中国传媒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美育与文明研究基地主任兼首席专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对文艺美学的建构意义”(10BZW019)。
J201
A
10.3969/j.issn.2095-042X.2017.06.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