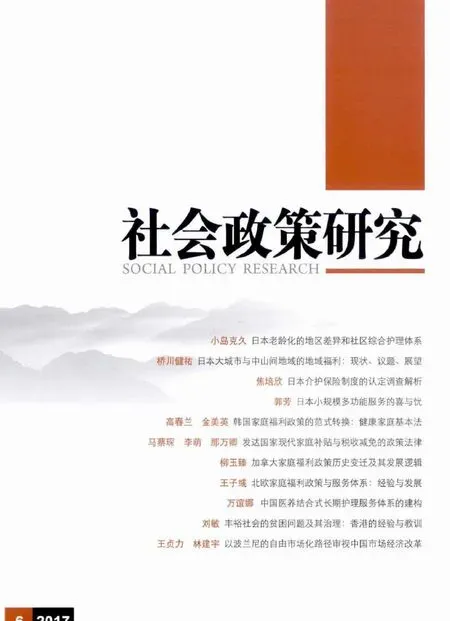丰裕社会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香港的经验与教训
刘 敏
一、丰裕社会的贫困问题
中国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前正处于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精准扶贫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扶贫政策要精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与贫困问题的演变。就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中国正在迈入丰裕社会。伴随丰裕社会的来临,中国的绝对性、分散性、发展性贫困问题得到有效克服,相对性、集中性、结构性贫困逐渐凸显,对于前者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对于后者我们在理论研究和政策应用上的经验尚不多。与欠发达社会相比,丰裕社会由于发展阶段和水平更高,其贫困问题的形式、性质、成因乃至扶贫策略都存在显著差异,国内学术界对此类问题的专门研究很少。因此,廓清丰裕社会贫困问题的性质,探究其贫困成因及其治理方案,对于新时期中国精准扶贫政策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的概念最早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是指经济发展程度和国民收入水平较高的富裕社会。当时处于经济发展“黄金期”的美国正面临丰裕社会的贫困问题,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促进空前的经济繁荣和“私人富足”的同时,也导致“少数人极端贫困”、财富分配严重不平等(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2009)。对此,加尔布雷思在其经典之作《丰裕社会》中进行了生动而深刻的揭示并开出了“药方”:发挥收入再分配和社会政策的调节作用,扩大教育、医疗、住房、社会福利等社会支出规模,通过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来遏制贫富悬殊。这些观点对后来美国乃至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在跨入丰裕社会后所遭遇的上述困扰,后来成为新兴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成长的烦恼”: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的同时,却遭受贫富悬殊扩大、社会矛盾恶化的“阵痛”;“先富者”尽情享受丰裕社会所带来的繁荣和富庶,贫弱者却在贫困的陷阱中苦苦挣扎(刘敏,2011)。
我国香港地区是丰裕社会贫困的一个典型案例:一方面,香港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商贸服务业中心及航运枢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另一方面,香港是一个贫富两重天的社会,是全球贫富差距严重的地区之一。香港社会丰裕与贫困的双重性,为中国内地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笔者曾经撰文探讨了香港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贫富差距问题①参见:刘敏,《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贫富差距问题——香港的经验启示》,《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被人大复印资料《台、港、澳研究》2011年第5期全文转载。,并以香港贫困问题为例分析了丰裕社会贫困问题的结构特征②参见:刘敏,《丰裕社会中的贫困:再论香港的贫困问题》,《兰州学刊》,2011年第6期,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1年第12期全文转载。。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继续以香港贫困问题为例,从表现形式、分布特点、主要成因、扶贫策略等方面进一步探讨丰裕社会贫困问题的性质与特点,希冀有助于增进对丰裕社会贫困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理论认识,推动丰裕社会精准扶贫模式的政策创新。
二、贫困的表现形式:相对性贫困
从表现形式上看,贫困有绝对性贫困与相对性贫困之分:前者是指贫困者的生活水平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一般采用绝对贫困线标准来度量,即以维持基本生存所需的收入或消费支出作为贫困线;后者是指贫困者的生活水平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这是丰裕社会贫困问题的主要形式,一般采用相对贫困线标准,以社会平均或中位收入的一定比例作为贫困线,常见方法是国际贫困线标准,即以社会平均或中位收入的50%为贫困线。
香港贫困问题建基于香港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收入水平,主要是一个相对性概念,更多是指收入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意义的相对贫困问题。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报告》,2015年我国香港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达到0.917,超过英国的0.909、日本的0.903,属于发展水平极高的地区(UNDP,2016:204)。2015年香港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万美元,位列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前列;家庭月收入中位数达到2.5万港元,社会总体收入水平较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2015:51)。但是,在香港整体社会丰裕的背后是长期存在的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表1显示,1986年,香港最高收入10%家庭所拥有的财富是最低收入10%家庭的22倍,2011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9倍,2011年最高收入10%的家庭占有社会总收入的41.0%,最低收入10%的家庭仅占社会总收入的0.7%(黄洪,2013:60)。2016年5月,彭博社根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GDP估值进行计算后发现,香港排名前十的亿万富豪的净财富总值相当于香港经济总值的35%(凤凰财经,2016)。根据莱坊(Knight Frank)发布的2017年《财富报告》,全球资产超过3000万美金的富翁,香港共有4080人,仅次于纽约、伦敦,名列全球城市第三、亚洲城市第一(Knight Frank,2017:18–20),香港的财富集中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表1: 最高及最低收入10%的家庭占香港总收入的比重
正是基于香港贫困问题的相对性,香港民间和官方都倾向于用相对贫困标准来制定贫困线。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和乐施会每年根据国际贫困线标准评估香港贫困状况。香港在2013年制定的首条官方贫困线,就是依据国际贫困线的方法,以家庭月收入中位数的50%作为贫困线。按照这个标准,2014年香港家庭月收入中位数为2.26万港元,贫困家庭数和贫困人口数分别为55.52万个、132.48万人,贫困率为19.6%。一方面,因为香港的贫困问题建基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收入水平,加之香港在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安全网,所以香港的穷人大体能够维持基本生活,一般不至于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另一方面,因为香港的贫困问题具有贫富悬殊和相对剥夺的特点,加之香港高收入、高物价、高消费的实际情况,所以收入水平低于看似标准较高的贫困线的港人日子并不一定好过,许多人面临生活窘迫、生计艰难的困境。根据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香港匮乏及社会排斥研究》,有110万港人生活于不同程度的匮乏状态,其中“综援家庭”特别是有儿童的“综援家庭”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存在严重匮乏的问题,32.7%的受访者表示“没有一件体面的衣服”,50.4%的受访者表示难以负担有需要时“打的士”往返医院就诊,54.7%的受访者不能负担“学生能够购买课外书、补充练习等”。
实际上,相比绝对贫困问题,相对贫困问题更加棘手、更难克服。这是因为,绝对贫困问题可以彻底解决,只要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广大赤贫者得以脱贫实现温饱乃至小康时,绝对贫困便迎刃而解;而相对贫困问题却无法根治,但凡根据社会平均生活水平来界定贫困,总会有一部分人生活在相对贫困线以下。相对贫困无法根治,却可以缓解,通过经济社会政策的有效调节,使相对贫困者能够同步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不断改善生活水平,进而把相对贫困控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反之,如果缺乏合理的经济社会政策和必要的收入再分配机制,发展成果无法惠及社会底层,那么相对贫困就会不断恶化,甚至向绝对贫困转化,最终走向贫富两极分化。对于香港存在的严重的相对贫困问题,香港社会有人提出“社会两极化”和“M型社会”的观点,认为香港社会结构正朝“中间收窄,上下两极扩大”的两极化方向转变,即中产阶级人数减少、上层阶级和底层阶级人数增加,社会结构由“橄榄型”向“漏斗型”转变,如果继续放任自流,很容易形成贫富对立的“双层社会”(刘兆佳等,2006:3–34)。

图1: 1971–2016年香港基尼系数
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相对贫困问题恶化不是香港独有的现象,香港相对贫困问题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贫富悬殊大、持续时间长,不仅是“亚洲四小龙”所独有,亦属全球发达经济体所罕见。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茨提出了著名的“倒U曲线”假设: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尔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Kuznets,S.,1955:18)。耐人寻味的是,香港的收入分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未出现“倒U曲线”所预测的“先恶化,后改进”,而是呈现“长时期持续恶化”的特点。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香港的贫富悬殊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不仅未得到有效缓解,反而不断恶化,这种情况在同等经济水平的地区极为罕见(刘敏,2011b)。从图1可见,40余年来,香港基尼系数始终居高不下,从1971年的0.430增至2016年的0.539,接近0.6的国际危险线。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布的《世界概况》,在全球基尼系数最大的10个国家和地区中,香港位列第九,是其中唯一的发达经济体①前八名分别为莱索托、南非、中非、密克罗尼西亚、海地、博茨瓦纳、纳米比亚、赞比亚,第十名为哥伦比亚,参见:CIA,The World Factbook,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根据联合国开发组织多次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香港是全球经济发达体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也是全球贫富悬殊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三、贫困的分布特点:集中性贫困
从贫困分布特点看,贫困有分散性贫困与集中性贫困之分:前者是指贫困大面积地分布于社会不同的群体、弥散在社会不同的地区,表现出大面积普遍性贫困的特点,例如改革开放前中国内地的贫困问题;后者是指贫困明显集中于少数特定的弱势群体、特定的贫困区域,客观上形成了贫困人口集中的贫困地带,表现出局部性集中化贫困的特点,例如美国的内城贫困问题,以及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国家存在的大规模贫民窟。香港的贫困问题具有明显的集中性特点,表现为人口与空间的双重集中性分布。
首先是人口的集中性分布。香港的贫困人口显著集中于两类群体:一是老人、病患和残疾人等生理性弱势群体,多具有高龄、多病、伤残的特征,其中尤以老人贫困问题突出。目前,老人综援(“综援”的全称是“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相当于内地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个案占综援个案总数的50%以上,老人的相对贫困率达70%以上。截至2013年3月底,香港约有26.8万宗综援个案,其中,老人个案15.3万件,占57.3%(香港社会福利署,2013:14)。从图2可见,2014年老人家庭初始贫困率(poverty rate before taxes and transfers,即不计算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调节前的贫困率)和实际贫困率(poverty rate after taxes and transfers,即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调节后的贫困率)分别达到72.2%、46.9%,是社会总体贫困率的3倍以上。二是失业、低收入、从事非经济活动者、单亲、新移民等社会性弱势群体,多具有低学历、低技术、低收入的特征,尤以失业贫困问题突出。图2表明,除综援家庭外,贫困率最高的是失业家庭,初始和实际贫困率分别高达81.4%、68.5%,实际贫困率远高于综援家庭;其次是非经济活动家庭,初始和实际贫困率分别达76.6%、57.6%;此外,单亲家庭、新移民家庭的初始贫困率分别达到49.5%、36.7%,实际贫困率分别为36.4%、32.4%,均远高于社会总体贫困率(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2015:35–36)。
其次是空间的集中性分布。香港的贫困人口明显集中于深水埗、葵青、观塘、黄大仙、北区、元朗、屯门,上述地区的初始贫困率分别达到 26.6%、25.7%、25.1%、24.3%、20.9%、20.6%、20.2%,初始贫困人口合计75.12万人,占全港18个地区初始贫困人口总数的56.7%。截至2016年底,香港共有公共租住房屋(以下简称“公租屋”)76.49万套,住户和人口总数分别为75.11万户、208.39万人,其中上述七个地区公租屋、公租屋住户、住户人口总数分别达51.78万套、50.76万户、139.74万人,分别占到香港公租屋、公租屋住户、住户人口总数的67.70%、67.58%、67.06%(香港房屋委员会,2016:1)。由于香港公租屋主要面向中低收入者,对申请家庭的收入和资产有严格限制,因此公租屋住户的集中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低收入者的集中分布。香港岛的太平山等地富豪云集,深水埗、葵青等地区穷人聚集,这也是香港贫富悬殊的真实写照。

图2: 2014年香港高贫困率家庭类别分布
美国著名学者威尔逊以美国内城贫困聚居区分析了贫困的集中化效应(Concentration Effects):伴随美国的经济转型和城市郊区化发展,制造业及其大量就业机会从中心城市外迁,内城区的中产阶级大量迁往郊区,城市内城区沦为贫困人口尤其是黑人贫困人口聚居区,最终产生了城市贫困在人口与空间上的“集中化效应”,不仅在地理空间上隔离了城市贫民,也在心理、社会和文化上孤立了他们,威尔逊称之为“社会孤立”(social isolation)——“缺乏与代表主流社会的个人和制度的联系或持续互动……强化了生活在高度集中的贫困区域的效应”(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2007:84–85)。由于历史发展、经济转型、产业转移等多重复杂的原因,香港的深水埗、葵青、观塘等地区成为贫困人口的聚集区,贫困率高、贫困群体规模大且分布广泛、脱贫难度大是这些地区贫困问题的基本特征。虽然香港贫困问题与美国内城区的贫困问题具有明显的差异,但二者在产生原因与表现形式等方面具有诸多相似之处:都属于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贫困,经济转型、产业转移、社会不平等是导致贫困问题积重难返的深层原因;都呈现集中性贫困,贫困人口在空间上的高度集中,客观上产生了底层阶级(Underclass),形成了贫困的集中化效应;都具有社会孤立的特点,贫困社群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遭受了不同程度上的社会排斥,仅靠贫困者个人努力很难实现可持续脱贫;都需要像威尔逊所说的普遍性“一揽子”改革计划,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策略、人力培训计划、收入再分配改革、社会福利制度等领域的综合改革,改革不平等的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从源头上铲除贫困滋生的土壤。
四、贫困的社会成因:结构性贫困
贫困的成因极其复杂,有贫困者个人原因,也有社会原因。从贫困的社会原因看,有发展性贫困和结构性贫困之分:前者是指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高、发展水平不足而导致的贫困问题,例如,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内地的大面积普遍性贫困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落后、社会发展程度低;后者是指由于不平等的经济社会结构或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导致的贫困问题。香港的贫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结构性贫困,是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社会转型以及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因经济落后或发展程度不高而出现的发展性贫困有根本的不同。结构性贫困是由于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不合理而导致的贫困,按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的观点,它不仅是“局部环境的个人困扰”,更是“社会结构中的公共问题”,个人困扰“产生于个体的性格之中——这些困扰与他自身有关”,公共问题反映了社会的共同命运,“往往还包含了制度安排中的某个危机”(米尔斯·赖特·米尔斯,2005:6–7)。
从一般原因看,香港的结构性贫困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的产物。从全球范围来看,贫富悬殊扩大似乎是全球化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西方发达国家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扩大的问题(钱志鸿、黄大志,2004)。新兴经济体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中也遭遇了贫富悬殊迅速扩大的困扰。伴随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经济结构从制造业到服务业再到知识经济的巨大转型,以及由此导致的制造业外迁、就业机会锐减、人力资源错配、产业结构失衡,香港的失业、低收入、在职贫困等新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刘敏,2011)。在此期间,受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离婚率上升等人口与家庭结构变迁的影响,香港的老人贫困、单亲家庭贫困不断恶化。美国学者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认为全球化促进了资本和财富的全球流动并创造了空前的经济繁荣,但也带来了资源集中、贫富悬殊、社会极化的问题。她提出了“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概念,在对伦敦、东京和纽约等全球城市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些全球城市在全球化和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都出现了收入分配和职业结构两极化的问题(Sassen ,S.,1991)。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全球城市,香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遭遇了收入分配和职业结构两极化的问题(Stephen W. K. Chiu &Tai–lok Lui,2004)。
从特殊原因看,香港的结构性贫困问题与香港不平等的经济社会制度有很大关系。在香港乐施会一项针对1001名受访者的电话调查中,68.3%的人将香港贫困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于经济社会环境,其中,36.3%的人认为是“缺乏完善的退休保障”,18.8%的人认为是“税制失去收入再分配的作用”,13.2%的人认为是“工资水平过低”(香港乐施会,2017:10)。例如,导致老人贫困问题极为严重的深层原因是香港缺乏完善的退休养老保障制度;在职和低收入贫困问题与香港缺乏完善的劳工政策以及对劳工权益的保护不够有很大关系;许多中老年劳工、妇女、少数族裔、新移民陷入贫困是由于香港就业及薪酬制度的不公平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香港低税制、低福利、低再分配的经济社会制度,是导致香港结构性贫困问题积患成疾的深层原因。自由经济体制是香港经济制度的鲜明特色,也是香港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原因。这种体制以自由贸易、低税率和少政府干预见称,表现为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剩余主义社会政策,具有低税制、低福利、低再分配的特点。卡尔·波兰尼指出,自由市场经济可以很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社会财富,却难以维护社会公平、减少不平等,因而需要自由市场和社会保护的“双重运动”来促进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动态平衡。国际经验表明,西方发达国家在自由市场创造丰裕之后更加重视社会保护,在获得经济效率之后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就是波兰尼所谓的“双重运动”。西方福利国家的诞生、东亚福利模式的出现,就是上述规律的体现。例如,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实现了向福利国家的起飞,日本在70年代中期实现了向福利社会的起飞,韩国在90年代后半期实现了福利快速增长(武川正吾,2011:211–218)。但是,我国香港地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进入丰裕社会之后,并未像西方福利国家一样,及时向社会保护模式切换,而是长期奉行“积极的不干预主义”,坚持“低税制、低福利、高发展”的发展道路,客观上造成“自由胜于平等,效率优于公平”的局面,这既培育了香港今日的繁荣和富庶,也为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埋下了祸根。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香港地区的初始贫困率并不高,但是由于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手段对贫困问题的调节作用严重不足,导致香港地区的实际贫困率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从表2可以看出,2012年,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甚至瑞典、丹麦等素以高福利、高平等性著称的北欧福利国家,初始贫困率也近30%,但是在计入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效应之后,实际贫困率不到10%。相比之下,香港的初始贫困率仅19.6%,但是在进过再分配调节效应之后,实际贫困率仍高达15.2%,远高于上述发达国家。由此可见,香港低再分配的经济社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放任和助长了相对贫困问题。对此,顾汝德(Leo Goodstadt)认为,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剩余主义社会政策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穷人的社会保护不足,是滋生香港丰裕背后严重贫困问题的深层原因(Leo Goodstadt,2013:281–282)。

表2: 2012年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贫困率(%)
五、扶贫的政策范式:存量式扶贫
根据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理论,国民经济福利多寡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增量发展和存量分配,即收入总量愈大、分配愈平等,经济福利就愈大(庇古,2007)。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政策范式上,扶贫有增量式扶贫和存量式扶贫之分:前者是指主要通过增量发展、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用好经济政策的方式进行扶贫开发,常见方式如招商引资、扩大投资、产业扶贫、落后地区开发、创造就业机会;后者是指主要通过存量分配、促进社会收入再分配、用好社会政策的方式进行扶贫开发,常见方式如完善扶贫、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社会政策。当然,增量式扶贫和存量式扶贫很难截然分开,但作为政策研究的一种“理想类型”,二者的区别显而易见。
大体而言,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以及发展中国家多采用增量式扶贫,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以及发达国家多采用存量式扶贫,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发展阶段的特点决定了扶贫策略,经济起飞阶段以及发展中国家因主要面临发展性贫困问题而需要增量式扶贫,经济成熟阶段以及发达国家主要面临结构性贫困问题而需要存量式扶贫;二是贫困问题的性质决定了扶贫策略,增量发展可以解决绝对性和发展性贫困,却无法解决相对性和结构性贫困,随着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增量式扶贫的边际效益会递减,存量式扶贫的边际效益会递增。香港历来重增量发展而轻存量分配、重经济效率而轻社会公平,这也是导致其贫富悬殊的深层原因。面对贫富分化的严峻现实,近年来香港社会开始反思传统政策的弊病,更加重视存量式扶贫和社会政策的调节作用,这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完善扶贫、教育、公屋、劳工、社会保障等社会政策,夯实社会安全网。加强社会救助,提高救助水平,2011年成立关爱基金,为尚未纳入社会安全网或已被纳入社会安全网但仍急需特殊照顾的经济困难人士提供社会救助;从2011年起,先后推出鼓励就业交通津贴、长者生活津贴、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扩大综援家庭津贴的覆盖范围,既夯实对老弱病残幼等丧失或缺乏劳动能力的贫困者的兜底性保障,也加强对适龄健全和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的开发式扶贫。健全扶贫组织机构,建立贫困线制度,2012年成立新的扶贫委员会,首次由政务司司长担任委员会主席,加强对扶贫工作的统筹协调。2013年首次制定官方贫困线,迄今为止每年发布《香港贫穷情况报告》,动态评估香港的贫困状况及扶贫政策成效。扩大教育资助范围,自2017年起对非营利幼儿园实施免费优质幼儿园教育政策,实现了15年免费教育。2012年启动公屋重建计划,2016年恢复“居者有其屋”计划,加强中低收入者住房保障。加强对劳工的权益保护,2010年通过了香港首部《最低工资条例》。不断完善“强制性公积金计划”、多次制定《强积金计划(修订)条例》,更好地保障参保人员的权益。
二是扩大教育、医疗、住房、社会福利等社会支出,发挥再分配的减贫效应。由图3可见,2009–2015年,香港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会福利等支出分别从582.40亿港元、383.87亿港元、162.58亿港元、404.18亿港元,增至791.22亿港元、607.74亿港元、320.92亿港元、650.01亿港元,以上社会支出合计年均增长9.10%,其中社会福利支出年均增长16.23%,远高于同期GDP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2015:247;2016:248)。这打破了香港在1987年确定的“公共支出增速不超过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速”准则,社会支出投入力度可见一斑。2015年,我国香港地区社会支出为4621.50亿港元,占公共支出的51.28%,这一比重达到了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刘敏,2014)①需要特别说明:1.OECD发达国家社会支出并不包括教育支出,考虑到在东亚国家和地区,教育是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之在国内大多数研究中教育支出也被列为社会支出,因此本文所说的社会支出是经过改进后的社会支出,其中包括教育支出;2.就社会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而言,我国香港地区基本上达到了OECD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就社会支出及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而言,我国香港地区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从一个方面体现了香港低税制、低再分配的自由经济体制的特色。。再分配的减贫效应已初显成效,在计入恒常现金等再分配效应之后,2009–2014年,香港的实际贫困率从16.0%降至14.3%,实际贫困人口从104.3万人降至96.2万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2016:16)。

图3: 2009–2015年香港教育、医疗、住房、社会福利支出(单位:亿港元)
三是创新社会政策模式,完善“政府+市场+社会”的大扶贫格局。近年来香港适应经济转型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新福利主义、社会投资、资产社会政策、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经验,在深化官商民三方合作、促进社会投资、扶持社会企业、发展社会资本、加强综合就业援助等方面大力创新政策模式与工具,旨在充分汇聚“政府+市场+社会”跨界别资源,更好地促进人力发展与社会投资,提升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例如,发展官商民三方合作,推行“携手扶弱基金”,加强公私伙伴关系,共同扶助弱势社群;大力扶持社会企业发展,推行“‘伙伴倡自强’社区协作计划”,鼓励社会企业为弱势社群提供社会服务、创造就业机会;推广社会资本发展计划,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跨界合作,推行“社区投资共享基金”,提升弱势社群参与经济、融入社会的能力;倡导“工作导向型福利”,完善“自力更生综合就业援助计划”,促进受助人重返劳动力市场;试行资产社会政策,设立儿童发展基金,通过建立个人账务、提供储蓄配额等方式,帮助困难家庭儿童积累资产。总之,新政策更加强调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公私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更加强调穷人的社会参与和能力建设,更加强调社会包容和社会团结,推动政策目标从事后补救到事前预防、从贫困救助到社会投资、从维持生计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转变。
六、结论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保持高速经济增长,迅速从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发展成为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内地也迅速从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变为一个贫富差距严重的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65,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水平。在迈入丰裕社会的过程中,中国内地绝对性、分散性、发展性的传统贫困问题得到有效克服,相对性、集中性、结构性等新型贫困问题却逐渐凸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对扶贫政策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精准扶贫政策。
香港社会在丰裕与贫困方面的双重性,为内地扶贫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一方面,香港在社会丰裕的背后长期饱受贫富悬殊问题的困扰,值得内地反思和警醒。香港长期重增量发展而轻存量分配、重经济效率而轻社会公平,由此导致香港成为全球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香港的教训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重增量发展轻存量分配、重初次分配轻再分配,经济发展不仅不能缓解贫困,反而可能催生不平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从而加剧相对性和结构性贫困问题。诚如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所言,如果政策处理不当,经济增长将促使社会不平等趋于扩大,因此公平正义的社会政策和机会均等的制度环境,对于可持续扶贫至关重要(冈纳·缪尔达尔,2001:21–22)。另一方面,香港扶贫模式创新的有益经验,值得内地学习和借鉴。面对严峻的贫富悬殊问题,近年来香港明显加大了扶贫开发及相关政策投入和创新力度,其中积累了不少值得内地借鉴的有益经验。
首先是坚持增量扶贫与存量扶贫相结合。香港历来注重增量扶贫,通过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高生产率的经济机会和就业机会,来提升穷人参与经济、融入社会的能力。这种以快速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增量扶贫策略,带来了绝对贫困的快速缓解,但也引起了相对贫困的不断恶化(John Page,2008:510–542)。因此,近年来香港日益重视存量扶贫的作用,不断完善扶贫、教育、公屋、劳工、社会保障等社会政策,扩大社会支出,强化再分配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与香港一样,内地亦存在绝对贫困快速缓解、相对贫困不断恶化的问题,也亟需增量扶贫与存量扶贫政策创新。国际经验表明,要同时缓解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问题,包容性经济增长(inclusive economic growth)和益贫式社会发展(pro–poor social development)至关重要:前者是普惠全民、照顾弱者的增长,后者是增进公平、减少贫困的发展。这方面,促进高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高生产率的经济机会和机会均等的制度环境,消除市场和制度歧视以及社会排斥,构建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都是行之有效的经验(庄巨忠,2012:10–15)。
其次是坚持政府扶贫与社会扶贫相结合。香港实行的是“政府+市场+社会”的大扶贫模式,在扶贫开发及社会服务领域,政府主要负责政策规划、资金支持和服务监管,社会组织负责具体策划和提供服务,企业积极参与慈善捐赠和创造就业机会,义工、社工、热心人士等公民力量广泛参与。这种扶贫模式常常引入政府购买服务、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运作方式,又被称为“官商民三方合作模式”“公私伙伴关系模式”。大扶贫体现了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优势,即“寻求把多种不同的社会机构(包括市场、社区和国家)动员起来”,将国家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与私营部门的高效率以及社会组织对社会公正的关注相结合,更好地发挥国家救助、社会互助与个人自助的协同作用(安东尼·哈尔、詹姆斯·梅志里,2006:191–193)。目前,虽然“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是内地扶贫开发的重要策略,但“社会参与”往往停留于动员热心人士捐款捐物,而未能形成公民参与和社会创新的可持续力量(刘敏,2013:227)。因此,深化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合作,更好地发挥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作用,依然是内地扶贫开发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最后是坚持外延扶贫与内涵扶贫相结合。外延扶贫重在加大扶贫开发投入力度,扩大扶贫、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支出规模。近年来香港社会支出年均增长近10%,社会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逾50%,这一比重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之下,内地的社会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不到30%,甚至落后于不少发展中国家,因此亟需加大以扶贫开发为重心的民生投入力度,增加社会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内涵扶贫重在深化扶贫政策创新,提高政策产出绩效。香港非常重视扶贫开发政策创新及其产出绩效:一方面汲取全球最新经验大胆创新社会政策模式,在社会服务运营、社会资本发展、社会企业扶持、发展型社会政策、社会工作队伍建设等领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验;另一方面重视结果导向,通过严格的监管、成熟的运营及科学的方法对政策产出进行综合评估,确保社会服务的覆盖面、可获得性及服务质素。例如,香港“社区投资共享基金”自2002年成立以来总投入4.32亿港元,资助项目323个,参与的伙伴机构达到8900个,建立互助网络2070个,支援家庭3.25万个,惠及60多万人,很好地发挥了“花小钱,办大事”的社会投资效果,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①数据截至2017年9月底,参见:香港特区政府社区投资共享基金,《计划成效及表现管理——计划成效小统计》,http://www.ciif.gov.hk/sc/about–ciif/ciif–achievements.html。。内地扶贫存在重外延轻内涵、重投入轻绩效的问题,在这个方面,香港注重政策创新与产出绩效的内涵扶贫模式值得内地借鉴。总之,内地可以借鉴香港就业援助、社会资本发展、社会企业扶持、资产社会政策、社会工作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有益经验,深化扶贫开发与社会政策创新,推动扶贫开发从事后补救到事前预防、从贫困救助到社会投资、从维持基本生计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更好地提升穷人参与经济、融入社会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哈尔、詹姆斯·梅志里,《发展型社会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庇古,《福利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7年。
[3]凤凰财经,《香港十大富豪家产占香港GDP的35%》,2016年5月25日。
[4]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
[5]黄洪,《“无穷”的盼望——香港贫困问题探析》,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
[6]刘敏,《丰裕社会中的贫困:再论香港的贫困问题》,《兰州学刊》,2011年,第6期。
[7]刘敏,《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贫富差距问题——香港的经验启示》,《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8]刘敏,《社会资本与多元化贫困治理——来自逢街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9]刘敏,《适度普惠理论视角下香港社会福利制度的经验与启示》,《澳门理工学报》2014年,第3期。
[10]刘敏,《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中国福利现代化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11]刘兆佳等,《社会发展的趋势与挑战∶香港与台湾的经验》,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06年。
[12]米尔斯·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13]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4]钱志鸿、黄大志,《城市贫困、社会排斥和社会极化——当代西方城市贫困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15]武川正吾,《福利国家的社会学:全球化、个体化与社会政策》,商务印书馆,2011年。
[16]香港房屋委员会,《公共租住房屋人口及住户报告》,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sc/about–us/publications–and–statistics/index.html,2016。
[17]香港乐施会,《香港贫穷问题的民意调查报告撮要》,http∶//www.oxfam.org.hk/content/98/content_31586sc.pdf,2017。
[18]香港社会福利署,《社会福利署回顾2011–12 及 2012–13》,http∶//www.swd.gov.hk/doc_sc/annualreport2013/SWD%20Review%20 2011–13–SC–text.pdf,2013。
[19]香港社会服务联会,《香港匮乏及社会排斥研究报告》,http∶//www.hkcss.org.hk/databank.asp,2012。
[20]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2014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https∶//www.povertyrelief.gov.hk/sim/archives.html,2015。
[21]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2015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https∶//www.povertyrelief.gov.hk/sim/archives.html,2016。
[22]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香港统计年刊(2015年版)》,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0100032015AN15B0100.pdf,2015。
[23]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香港统计年刊(2016年版)》,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0100032016AN16B0100.pdf,2016。
[24]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富裕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25]庄巨忠,《亚洲的贫困、收入差距与包容性经济增长——度量、政策问题与国别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年。
[26]John Page,“Strategies for Pro–Poor Growth∶ Pro–Poor, Pro–Growth or Both”,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2008 Vol.15,No.4.
[27]Knight Frank,The Wealth Report:The global perspective on prime property and investment,2017,http∶//www.knightfrank.com/wealthreport/2017/download.aspx.
[28]Leo F. Goodstadt,Poverty in the Midst of Affluence:How Hong Kong Mismanaged Its Prosperity,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3.
[29]Sassen ,S.,The Global City:New York, London ,Tokyo,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30]Stephen W. K. Chiu & Tai–lok Lui,“Testing the Global City–Social Polarisation Thesis:Hong Kong since the 1990s”,Urban Studies,2004 Vol. 41,No. 10.
[31]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6:Human Development for Everyone,http∶//report.hdr.undp.org/.
[32]Kuznets, S.,“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5 Vol.45,N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