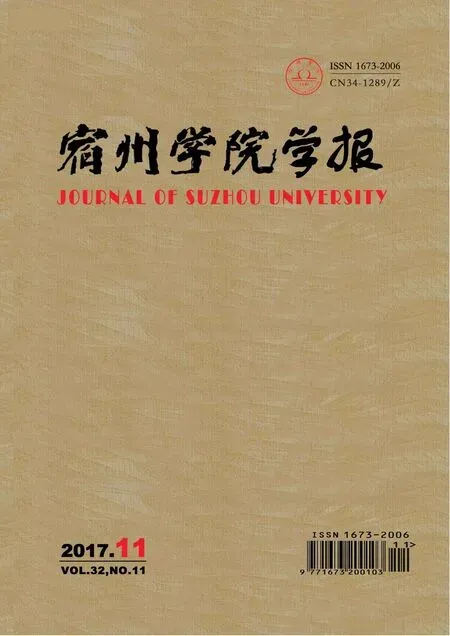花鼓灯男子群舞《瞧,这帮鼓架子》的音乐分析
陈宝利,晨 见
滁州学院音乐学院,滁州,239000
花鼓灯男子群舞《瞧,这帮鼓架子》的音乐分析
陈宝利,晨 见
滁州学院音乐学院,滁州,239000
从鼓架子舞蹈《瞧,这帮鼓架子》的音乐入手,了解作品中鼓架子的具体动作,凸显鼓架子挺拔、刚毅、豪爽、奔放、玩劲足的乐观精神。通过分析舞蹈音乐中具体的音乐结构及技术,如起、引、连、转、加强、填充等方面来阐释花鼓灯锣鼓在舞蹈音乐中的作用,说明锣鼓在整个舞蹈音乐中具有多样的结构和情绪意义。从《瞧,这帮鼓架子》的音乐发展手法看,民族民间音乐中典型的旋律发展手法是同头、合尾、加垛的运用;《瞧,这帮鼓架子》音乐的核心旋律语汇是321三个音,这三个花鼓灯旋律核心语汇贯穿于音乐始终,充分体现出花鼓灯音乐的地域特色。
花鼓灯;瞧,这帮鼓架子;锣鼓;核心语汇
花鼓灯作为安徽省最为常见的民间歌舞艺术,它集民间综合艺术之大成,融舞蹈、音乐、民歌与一炉,成为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花鼓灯的灯歌、舞蹈、锣鼓既可融为一体,也可以独立存在。安徽花鼓灯音乐包括花鼓灯歌和花鼓灯锣鼓以及花鼓灯后场小戏的小调三大部分。其自身的音乐结构包括音乐构成体系、曲调体系和技术体系。安徽花鼓灯音乐体系的构成过程中吸取了社会主流音乐以及艺术类音乐,更加离不开社会主流音乐和艺术类音乐的发展。因此,对花鼓灯的音乐分析,对研究主流社会音乐与艺术类音乐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以下从花鼓灯男子群舞《瞧,这帮鼓架子》的音乐结构及技术、音乐发展手法及核心旋律语汇等方面加以论述。
1 《瞧,这帮鼓架子》的创作背景
《瞧,这帮鼓架子》由安徽凤台花鼓灯艺术团演出,舞蹈编导:宋忠洋、岳颖,作曲:晨见、大雷。该作品参加第六届中国舞蹈“荷花杯”民族民间舞蹈大赛,获得安徽历史上参加“荷花奖”角逐以来的最高奖项——银奖,并获得唯一一个观众最喜爱的舞蹈作品奖“大地之舞奖”。本文所分析《瞧,这帮鼓架子》的乐谱源自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花鼓灯》第438至440页,全谱除去散板的引子外,一共有122小节(部分锣鼓有重复不重复计算)。
晨见先生多样的作品类型、丰富的创作经验以及对民族民间音乐独特的理解一直倍受关注。研究花鼓灯男子群舞《瞧,这帮鼓架子》也是为了更好地深入理解安徽民间音乐的特点,探寻晨见先生在民族民间音乐的理解和发展方面所做的具体工作。传统的花鼓灯表演一般不安排男子群舞,而《瞧,这帮鼓架子》编导在舞蹈设计上安排了男子群舞,特色鲜明,韵味十足,它以原生态的花鼓灯舞蹈语汇为主,通过合理地结构使之表现力更加丰富,艺术张力更加充分,借用创作者的话来说就是“要一火到底”,当然通过欣赏这个作品确实也是达到了这一创作要求。
2 花鼓灯锣鼓在舞蹈音乐中的作用
花鼓灯音乐专家汤兆麟先生在《花鼓灯音乐概论》绪言中说:“花鼓灯由花鼓灯歌、花鼓灯舞蹈以及花鼓灯锣鼓组成。”[1]花鼓灯锣鼓是花鼓灯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可以说玩花鼓灯,花鼓灯锣鼓必不可少[2]。花鼓灯舞蹈的伴奏也必然有锣鼓,正是锣鼓和舞蹈的配合才构成花鼓灯独特的民间风格,锣鼓音乐是花鼓灯艺术精髓的体现,花鼓灯锣鼓使用的打击乐器有花鼓、大锣、大镲、小镲以及狗锣等[3]。
花鼓灯舞蹈《瞧,这帮鼓架子》音乐中大量使用锣鼓。锣鼓在整个舞蹈音乐中具有多样的结构和情绪意义,以下讨论起、引、连、转、加强、填充六个方面。
2.1 起
起的作用是开始和引入,舞蹈由锣鼓开场,即谱子上标明的“开场锣”。由鼓单独演奏散板,速度由慢渐快,初步显示整个舞蹈的加快式情绪,同时伴随舞蹈以剪影散点造型亮相。然后,鼓架子和兰花表演由文伞把子或者丑鼓“走四门”后引出。大花场主要呈跑队并且以站肩的形势出场,一般队形构图为编篱笆、三钻子、两垛墙、满天星、跑乱场、里罗成外罗成等,以烘托出场气氛。大花场出场后舞台场面十分热闹,当舞蹈达到高潮时,全场的鼓架子和兰花在舞者吹响口哨时一起舞动起来。鼓架子遇到图形连接处时通常以最灵巧的身段随即进行表演,扭跳翻跌,取得全场观众的热烈追捧。
2.2 引
引的作用是引出,目的是为下一素材的出现做好铺垫[4]。在花鼓灯艺术中锣鼓音乐开始演奏时,多由鼓单独奏出一个或一段鼓点,然后加入锣与其他打击乐器。由鼓单独奏出的这一段被称为起鼓。起鼓之后,多先演奏花鼓灯的典型节奏——长流水节奏,这样就构成了音乐中1小节起鼓,2小节长流水锣鼓加2小节小煞锣与加锤锣的5小节引入节奏。此时锣鼓的演奏速度为174,快速的锣鼓引人入胜,使得音乐情绪爆发。
2.3 连
音乐旋律出现之前多演奏锣鼓点:匡匡 一龙 匡0,具体体现在第13、23、25小节处,此处的锣鼓既有乐句的连接作用,又有旋律之间的呼应作用,即前一句为旋律的上句,锣鼓作为具有应答关系的下句。
2.4 转
转的作用在音乐中主要体现在连接两个不同调性的乐段上,音乐中F调唢呐演奏完加入一句锣鼓后接上bB调大唢呐,在乐谱中为54和55小节。F调与bB调虽然为近关系调,但是如果不能合理地连接两个调性,过渡则显得生硬,在西方音乐中遇到这种情况通常使用共同和弦来连接,而这里作曲家直接使用锣鼓进行连接,既保持了音乐的整体情绪统一,又自然合理地引出具有对比音色的大唢呐。
音乐中唢呐演奏旋律,锣鼓加入则产生热烈、火爆的气氛。通过加入锣鼓烘托音乐的热烈情绪,是民族民间音乐鼓吹乐中典型的方式,如乐谱中第48至51小节。
填充主要体现在演奏长音。为了使持续的长音不产生单调感,在长音演奏时加入锣鼓,既可以起填充作用,又增加了热烈的气氛。
花鼓灯锣鼓与舞蹈动作在表演中融为一体,经验丰富的鼓手能够带领(引领)舞蹈者进行即兴的表演,不过二者需要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磨合,方能在表演中达成默契。在表演过程中,多样的舞蹈动作和灵活多变的锣鼓点子往往是民族民间音乐形成多样化艺术风格的重要催化剂[5]。
3 民族民间音乐中典型旋律发展手法的运用
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在旋律的发展方面上有很多经典而独特的手法,就花鼓灯舞蹈《瞧,这帮鼓架子》而言,其音乐发展的主要手法有同头、合尾和加垛。汤兆麟先生在《花鼓灯音乐概论》中将花鼓灯歌的典型曲式结构概括为合头式二段体、合尾式二段体和`头尾合式二段体,这是对大量花鼓灯灯歌旋律的分析与归纳,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这也充分说明要想保持花鼓灯浓郁的地域风格,则要从花鼓灯自身的灯歌旋律中汲取养料,充分体现其自身独特的音乐特征。
合头也可称为同头,指旋律的开头部分是相同的。使用合头来组织旋律,乐句之间既统一又有发展变化,这种表达方式非常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审美习惯:既讲究对称,又打破严格的对称。具体体现在音乐中的第14至21小节(图1),此处为铜管在C宫调上奏出的8小节旋律,此处8小节乐谱既可以看成由同头6引出的四个短句,也可以看成由两个4小节组成的同头换尾两乐句。

图1
音乐中F调唢呐演奏的旋律语法为“同头变尾三级跳”乐句,虽然旋律为4小节,但从句法上看应该为1+1+2结构,同头因素为321三个音[6]。
第41与43小节头相同,42和44小节尾部落音不同,前为2后为1,第45与46小节为完整、不可分割的一句,第46小节落在6上,而6这个音也是321这个三音组中前三小节都没有使用的落音,在第47小节出现既有新鲜感又不陌生,使得旋律妙趣横生。
合头同样在音乐开始和大唢呐演奏的旋律上使用,第1、2与3、4小节为典型的合头换尾。bB大唢呐演奏的第56至63小节旋律与前面1、2演奏的旋律仅是节奏上的变奏,其句式构成也是合头换尾。
合尾就是乐句结束时使用相同的素材,这种使用相同素材进行结尾的方式使乐段间联系更加紧密,使得音乐风格更加统一,具体表现在第21、38、63、79、122小节,它们都以宫调式主音作为结束。
加垛是民族民间音乐中特有的发展手法,而这一手法在花鼓灯艺术中有相同的体现。在花鼓灯锣鼓中有一锤锣,花鼓灯舞蹈动作中有凤凰三点头,所以在花鼓灯舞蹈《瞧,这帮鼓架子》音乐中也使用了这一技法,具体体现在48至51小节,此节奏为典型的花鼓灯舞蹈动作凤凰三点头的节奏型。
花鼓灯舞蹈《瞧,这帮鼓架子》音乐中的合头、合尾以及加垛是民间音乐旋律发展的典型手法,作曲家晨见先生从花鼓灯歌中提炼出具有可塑的、可发展的、具有男性特点的旋律语汇,通过典型的发展手法,变化出气势雄壮、触动内心深处的旋律语言。可见,合头、合尾以及加垛的应用在花鼓灯舞蹈音乐中是必不可少的。
4 花鼓灯核心旋律语汇的贯穿发展
花鼓灯舞蹈《瞧,这帮鼓架子》的音乐体现了花鼓灯音乐的独特韵味,为了做到既保持花鼓灯原有的风格特色,又具有新鲜的听觉感受,作曲家从花鼓灯音乐构成的本体中吸收、归纳出典型的核心旋律语汇,纵观整个舞蹈音乐,可以看出作曲家选择的核心语汇就是321三个音。在构成整个音乐时,作曲家紧紧抓住这个核心语汇,通过变化组织方式,运用模进、派生、变奏、扩大等专业作曲技术手段。创作出多个乐段,使整个音乐既紧紧统一在核心素材下,体现花鼓灯原始风格,同时通过多样的作曲技术使得音乐有了更好的衍生发展和情绪递进。
音乐在第1小节就以321这三个音组成变化的三个旋律素材进行展示,如谱例中用方框标记的123部分(图2)。

图2
音乐中由铜管演奏旋律的第15、17、19、21小节均以321三个音作为结束,只是排列不同,此段结束时以音乐开头的旋律变化组合结束,充分体现了花鼓灯旋律核心语汇的贯穿作用。
由F调唢呐演奏的旋律同样是以321三个音作为合头出现,引申出4小节的乐段,后面bB大唢呐演奏为前面铜管演奏旋律的加花变奏,其核心语汇还是由321三个音组成。音乐在最后达到高潮时以扩大一倍时值再现开始(97至103小节),乐曲结束如前文所说,画龙点睛般强调整个音乐的核心语汇(122小节)。
在民族民间音乐的多种表达方式中,为了使音乐整体统一又具有更多变化的可能,核心元素的重复与变异是十分常用的作曲技术。我国原生态的民族民间音乐不像西方音乐那样有严密的逻辑性,但它自然顺畅地表达语言思维就是在同一议题框架下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阐释。有位学者曾经提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艺术观点。男子群舞《瞧,这帮鼓架子》中核心语汇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符合这个艺术观点的,当然符合与否并不是创作者提前预谋的,而是作品间接体现出来的。
5 结 语
通过对花鼓灯舞蹈《瞧,这帮鼓架子》的音乐分析,对花鼓灯这一民族艺术瑰宝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对作曲家晨见先生如何保持浓郁的地域音乐文化特色,创作出具有特色鲜明且充满崭新音乐形象的艺术作品的高超作曲技术有了新的认识。音乐作品的分析过程就是音乐作品的解构过程,通过分析和解构能够充分了解音乐作品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体会作曲技术中统一与变化、对比的关系,凝练音乐作品的深层结构样态,从而发现作曲家具有的敏锐洞察力、深邃的智慧和独特语言是怎么汇聚产生的,后续还将继续研究晨见先生创作并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品,从而寻求民族民间音乐再升华的具体经验。
[1]汤兆麟.花鼓灯音乐概论[M].合肥:黄山书社,2005:20
[2]韩枫.中国花鼓灯艺术保护体系的创新与实践[J].中国科技纵横,2013(17):305-306
[3]李世军,杨传中. 凤台花鼓灯文化探源[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10(4):91-93
[4]潘志涛.中国民间舞教材与教法[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12
[5]谢克林.中国花鼓灯艺术[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9
[6]李吉提,王安潮.中国音乐结构分析概论[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1):132-135
(责任编辑:武艳芹)
10.3969/j.issn.1673-2006.2017.11.020
J722.212
A
1673-2006(2017)11-0084-03
2017-07-16
滁州学院校级科研启动经费项目“‘引’‘变’‘融’——淮河本土音乐作品中凤阳花鼓元素的有机运用”(2015qd29);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江淮丘陵地区名额的挖掘整理与形态学特征研究”(SK2017A0427)。
陈宝利(1982-),河北唐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计算机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