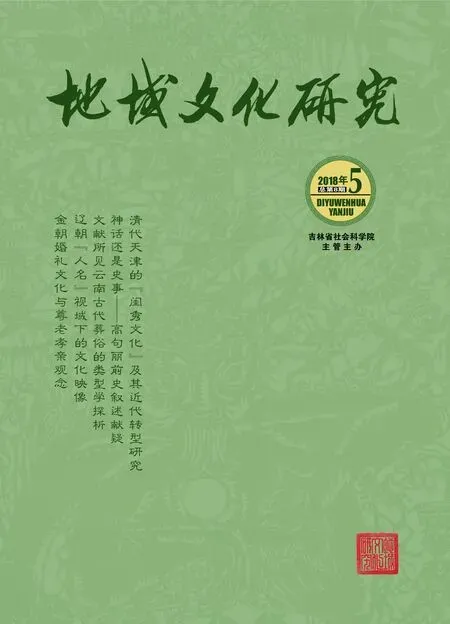清代天津的“闺秀文化”及其近代转型研究
——兼论长芦盐商对“江南女学”的传播与改造
高 鹏
美国学者高彦颐在其著作《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一书中提出一个疑问,“封建社会尽是祥林嫂吗?”①[美]高彦颐(Dorothy Ko):《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页。从晚清到五四新文化时期,“受害女性成了中华民族本身的象征……。受父权压迫的女性,成为旧中国落后的一个缩影,成了当时遭受屈辱的根源。受压迫的封建女性形象,被赋予了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至最终变成了一种无可置疑的历史真理”②[美]高彦颐(Dorothy Ko):《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页。。明清时代是“存天理、灭人欲”理学精神的鼎盛时期。但就在当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明清时代产生过更多的女诗人,仅仅在300年间,就有2,000多位出版过专集的女诗人。③[美]孙康宜:《明清文人的经典论和女性观》,《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来说,这些女诗人或许只是“少数”和“另类”,但就某些阶层和家族而言,她们的数量却不算少。
一、传统才德观与江南女学
在女子对家庭、家族、宗族和国家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上,古人的认识并不肤浅。早在周代,便出现了“妇学”的概念和定义,《周礼·天官》记载:“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一)女学内容与才德观
女学的内容与当时社会的才德观是分不开的。据考证,上古的女学不仅要求“妇德”,还要求一定的“女才”。“盖自家庭内则,以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莫不习于礼容。至于朝聘丧祭,后妃夫人内子命妇,皆有职事。平日讲求不预,临事何以成文。”①(清)章学诚:《妇学》,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74页。章学诚在考证上古妇学时说:“古之贤女,贵有才也”,“如女史、女祝、女巫,各以职业为学,略如男子之专艺而守官矣。至于通方之学,要于德言容功。……至其学之近于文者,言容之事,为最重也”。②(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9页。
两汉时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定型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专门的女学书籍,如西汉刘向的《列女传》和东汉班昭的《女诫》等。儒家思想“重德”的传统,开始影响到两汉时期的女子教育。不过,“重德”并不意味着“轻才”。《列女传》中“贞顺传”与“节义传”重点宣传“女德”,《通传》重点介绍“女才”,《母仪传》《贤明传》和《仁智传》则“德才兼有”,《孽嬖传》则是“女德”的反面教材。整体上,《列女传》并未表现出明显的“重德轻才”倾向。③张涛:《列女传译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2页。
后世的女子教育和女学书籍的内容确实存在“以德为主”的倾向。如唐代宋若华、宋若昭撰《女论语》、陈邈妻撰《女孝经》、武则天撰《列女传》《孝女传》《古今内范》《内范要略》等女学书籍;宋代司马光撰《家范》、袁采撰《世范》;明代明成祖徐皇后撰《内训》、吕坤撰《闺范图说》、温氏撰《母训》、黄尚文等撰《女范编》等;清代陆圻撰《新妇谱》、陈宏谋撰《教女遗规》、贺瑞麟撰《女儿经》等等。不过,这些书籍重视“德化”的现象在整个封建社会是带有普遍性的,不独针对女性。“大凡男女五六岁时,知觉渐开,聪明日启,便当养育良知良能。男则令其就塾,教以《小学》《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古人孝亲、悌长、敬身、明伦等行;女则令其不出闺门,亦教以《小学》《列女传》《内则》诸篇古人孝姑、敬夫、教子、贞烈、纺绩等事。务要使其朝夕讲诵,薰陶渐染,以成其德性,敦复古道,感动奋发,而见义勇为。”④(明)于镇僭:《于氏家训》,于树滋:《于氏十修家谱》卷2,清光绪十四年(1888)刻本。
究其根本,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指导思想,一直坚持“道德本位”原则。金观涛、刘青峰将其表述为“伦理中心主义”,就是“指把伦理道德看作高于知识价值之心态”。⑤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4页。韦政通称其为“泛道德主义”,“就是将道德意识越位扩张,侵犯到其他文化领域(如文学、政治、经济),去做它们的主人”。⑥韦政通:《儒家与现代化》,台北: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8年,第85页。女子教育“以德为主”是符合当时儒家思想的总体安排,而非特别要求。传统女子教育为历朝历代培养出许多“才女”。南朝徐陵编撰的《玉台新咏》,是一部东周至南朝梁代的诗歌总集,内容“全涉女性”⑦(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收录了班婕妤、鲍令晖、刘令娴等一批女作家的作品。清代康熙年间编纂的《全唐诗》690卷,专门为女诗人立有专卷13卷,上自后妃、公主,下至名媛、歌姬、尼姑、道士,均有作品入选。今人王延梯辑的《中国古代女作家集》,收录了上至先秦,下迄清末的1,400余位女作家的作品。①王延梯:《中国古代女作家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28页。社会整体上对“才女”持欣赏、尊重与包容态度。
(二)女学的局限性
在出人意料的数据背后,我们必须看到传统女子教育的局限性。首先,这种教育的受众面太小。“妇学古实有之,惟行于卿士大夫,而非齐民妇女皆知学也。”②顾廷龙:《顾廷龙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32页。艾伯特·奥哈拉将中国女性分为四个阶层,即奴隶和劳动女性,农民和商人之妻,学者和官员之妻,贵族和统治者之妻。在每个阶层内,女性的责任和特权是不同的。③顾廷龙:《顾廷龙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页。传统社会中,并不是每个阶层的女子都有学习的权利与条件。顾廷龙认为,“盖往昔妇女,井臼操劳,无才为德,相习安置;天才高隽者,或略经指示,便斐然成章;或观摩父兄,沾溉余艺,于针黻刀尺之间,为雪月风月之吟;至考订经史,及讲究经世之文,则犹凤毛麟角,此数千年来相承之风气也”。④胡文楷,张宏生:《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28页。纵观中国古代女作家,很少有人出身于平民百姓家。女子教育需要在家庭内完成,普通人家没有雄厚的物质条件支持女子读书,更重要的是,如果家族中缺少文化氛围,更会缺少教育女子的意愿。
其次,传统女子教育具有典型的非社会性。与男子可以进入私塾以及府、县、州学学习不同,女子不能走出家庭参加社会教育。女子受教育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幼承庭训”,这是传统女子教育最基本的形式,“庭训”可以是父母的亲自指导,也可以是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指点,还可以是家族中兄姊的教育;⑤郭英德:《明清女子文学启蒙教育述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二是延揽塾师到家坐馆,进行单独教育,时称“闺塾”。一般家庭谈不上“幼承庭训”,也无延揽塾师的想法和能力。古代的“才女”多出于书香门第和富贵家庭。按照“门第相当”的观念,她们也多会嫁入类似阶层。出于更好地为家族教育子女这一点考虑,她们进入夫家后一般仍可以继续接受教育,遇到开明人家,还可以与丈夫相与研习诗词歌赋,“琴瑟和鸣”。
最后,女子教育的地域特色明显。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得自汉魏以迄近代女作家“四千余家”,明清两朝即有3,750余人,尤以清代为多。这其中,绝大多数“才女”集中在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人称“江南才女”。这种现象与江南文化的中心地位不无关系,在文化风气浓厚的地区,女子教育和“才女”文化更容易被接受和尊重。在男子读书都困难的地区,谈不上“才女”风气。另外,“才女”风气的形成还得益于江南地区雄厚的经济基础。“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的发展,与这一地区因城市化和商品化而增殖的财富相辅相成。妇女受教育、读书、出版和旅行机会的不断增加,都是这一才女文化增长的必要条件”,“在帝国的其他地区,如著名的北京大都市地区和广东,……才女文化也曾出现,但只有在江南,它才达到了这样的高度”。⑥[美]高彦颐(Dorothy Ko):《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23页。?
二、江南才女文化的分支——天津的“闺秀文化”
因为天津建城与文化氛围形成的时间均较晚,清代以前未见津门闺秀的相关记载。《津门诗钞》中记载的第一位女诗人是程德辉,祖籍浙江绍兴。长芦盐商的到来,给城市带来了财富,吸引了大江南北的文人墨客,也将“女学”风气带到了天津。在他们的带动下,欣赏、尊重和鼓励“才女”的氛围慢慢养成。以盐商和士大夫家族为主的天津“闺秀”文化大放异彩,并形成一种传统,最终对近代女子教育的兴起、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长芦盐商对闺秀文化的推崇
对女子习诗词歌赋普遍抱有欣赏和宽容的态度,加上雄厚的物质实力,使长芦盐商成为推动天津女学繁荣的一股主要力量。张霖家族的重要人物张霔,著有《和小青诗》十首。小青姓甚名谁已不可考,但能与“津人诗三家”之首的帆斋先生相唱和并为其所推崇,其文化素养应该不低。实际上,张氏家族内部的酬唱应和向来不排除女眷,“父子兄弟逮于闺秀率解讴吟,时有唱和,故家遗韵,盖犹有存焉”①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中),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959页。。
张霔之后,查氏家族的查为仁对“才女”文化亦推崇备至。据查为仁《莲坡诗话》记载,查为仁有别业在曲周,庭前海棠于十月雪中盛开,曲周知县张若岩赋七律一首,和者甚多。查为仁认为,众多和诗中以津门闺秀许雪棠所作为最佳。许雪棠终生未嫁,工诗文,秘不示人,存世的仅《雪中海棠和韵》一诗。
“移从香国种无双,几见凌寒意不降。日映轻红娇带泪,风扶弱质笑迎窗。朱门旧许宜春睡,冷院新看伴玉缸。却恨杜公无好句,空教十月渡寒江。”②(清)梅成栋:《津门诗钞》(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08页。
汪西颢的《津门杂事诗》有云:“不栉书生不画眉,传来艳绝海棠诗。若教玉秤称才子,压倒楼头旧婉儿”。蒋诗的《沽河杂咏》也有云:“若无十月诗传播,闺秀谁知许海棠”。一百多年后,梅成栋在编撰《津门诗钞》时,将许雪棠比作东汉高士严光,非常钦佩其才华。
查为仁与津门闺秀之间的唱和多次见诸史料,有些带有相当浓重的“传奇”色彩。查为仁辑有《赏菊唱和诗》一卷,为《蔗塘外集》之一。查为仁系狱之时,“二三朋好时时慰问,或投以吟筒互相唱和”。③(清)查为仁:《莲坡诗话》(卷上),金钺:《屏庐丛刻》,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书,第18页。一次,查为仁偶得咏菊七律二首,和者甚众。津门闺秀赵琼英将其所和咏菊诗,属于纸扇之上,投给了查为仁。④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中),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968页。
宴赏诗传帝里秋,江流如线怅悠悠。海棠开后从凝望,篱菊逢时更惹愁。锦缆牵霞辞我去,金鞍踏月向谁留?浣花笺纸书频写,数尽飞鸿复一酬。
吴云燕树尽疑猜,耽入诗坛不省来。佳句空萦千里梦,仙葩谁徙树上栽。鹦哥帘底将伊唤,杜宇枝头向客催。莫负维扬好明月,琼花一朵未全开。⑤(清)梅成栋:《津门诗钞》(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19页。
查为仁虽身陷囹圄,但其才华仍然赢得了津门闺秀的钦佩和欣赏。康熙丙申年(1716)重九,查为仁作赏菊诗二律,与众人和韵,水仙杜丽春降卜和二律而去。⑥(清)梅成栋:《津门诗钞》(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19页。据载,杜丽春是明江西吉水县人(一说为庐陵人,据《津门杂事诗》),明万历年间随其父路过天津,船舶失事后,杜丽春谒见碧霞元君,摄天津水府事。①(清)梅成栋:《津门诗钞》(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19页。据说有人看到过她出水时的样子“华裾纤褂,如世所画洛神状”。②(清)华鼎元:《梓里联珠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1页。查为仁在《莲坡诗话》中录有其《海天词》一首,“每因封事到瑶池,池上桃花开几枝。俯瞰江河流影细,何人劈下两茎丝”。赵琼英、杜丽春两事虽“迹近荒诞”,但俱载于查为仁相关著作和方志中,从中可以看出作为盐商子弟、科场“解元”的查为仁,对“才女”和“女学”的欣赏与尊重,而这种态度会影响到盐商家族的女子教育。
(二)“不教谢女擅风流”的金至元、赵氏及艳雪
长芦盐商中,虽然张霖家族有“父子兄弟逮于闺秀率解讴吟”的传统,但张氏女眷所作的诗作未见留存,对“才女”的研究只能从查氏家族开始。
查氏家族出现的第一位“才女”是金至元。确切地讲,金至元是长芦盐商查氏和金氏共同的“才女”。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发生的“借帑案”中,查日乾和金大中都受到波及,查日乾还因此被投入监狱。查、金二人既“门当户对”,又是“生死之交”。金至元,字载振,又字含英,是金大中的独女。③(清)金恭寿:《金氏家集》,致远堂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书。金至元的才华离不开金氏家族的教育与熏陶,她“幼颖悟嗜学,闺秀中秉家传,已能诗”④(清)梅成栋:《津门诗钞》(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14页。。她“幼读书,通大义,颖慧绝人。女红之外,书算琴管,无不精妙如神。尤工于诗”⑤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中),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99页。。金至元的祖父金平(字子昇)、父亲金大中(字驭东)、族兄金玉冈(字芥舟)、金玉渊(字起潜)、金玉珽(字芳舟)等人都是天津文化史上著名的诗人,金至元可谓“幼承庭训”。金至元幼年便被许配给了查为仁,由于科场舞弊案发,查为仁入狱,9年后二人“始成婚礼”。嫁入查家后,金至元与查为仁“琴瑟綦谐”,唱和成帙,号《松陵集》。金至元诗作甚多,平时秘不示人,《津门诗钞》收其诗9首,《金氏家集》收其诗24首。她的诗作中有描写津门景物之作,如《重过水西园》。
一番雨过酿轻寒,七月南塘水半竿。最是重来好风景,秋光如染隔林看。⑥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中),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469页。
亦不乏开导、安慰查为仁之作,如《夜话和莲坡主人韵》:
人生大抵游仙枕,已出邯郸君莫疑。
世事浮沉无定著,流光劫活漫寻思。
试香午院宜煎茗,斗墨晴窗好赋诗。⑦(清)梅成栋:《津门诗钞》(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16页。
金至元“夙娴内则,不苟訾笑。性至孝,事父母及舅姑皆得欢心”。⑧(清)梅成栋:《津门诗钞》(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13页。但是嫁入查家后“仅十月而卒”。她的诗“清拔孤秀,不染粉黛习气”。⑨(清)梅成栋:《津门诗钞》(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14页。金至元殁后,查为仁不忍听诗作湮灭无传,搜集其诗稿若干首,托赵执信作序,刊成《芸书阁剩稿》留世。⑩(清)金至元:《芸书阁胜稿》,金钺:《金氏家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书。
佟锳遗孀赵氏,依夫兄佟鋐客居津门,“平生作诗最富,不轻示人,而绝无脂粉之态”,“所居曰残梦楼,因号残梦主人”。时人称赞金至元与赵氏“幽兰夕萎芸书阁,缺月秋寒残梦楼。留得玉台诗本在,不教谢女擅风流”。①(清)华鼎元:《梓里联珠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6页。佟鋐(字蔗村)家有姬妾名艳雪,“亦能诗,蔗村筑楼居之,名曰艳雪”。②(清)梅成栋:《津门诗钞》(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835页。金至元殁后,艳雪挽其云:“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③(清)袁枚:《随园诗话》,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2页。
(三)“兰房嗣响,率多咏絮之风”的查氏群英
金至元开启了金氏家族“才女”文化的先例,同时也为查氏家族做出了表率。“于斯堂查氏,一门风雅,累业缥缃。闺阁之秀,咸工文翰。自含英金夫人提唱于先,以后兰房嗣响,率多咏絮之风,他族罕有及者。”④(清)梅成栋:《津门诗钞》(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16页。李钦,查为仁的弟弟查礼之妻。李钦16岁的时候嫁给查礼,她好文学,《孝经》《尚书》《毛诗》俱能成诵。李钦颇解声韵,查礼每有诗作都要与其商榷,“一字之易虽精于诗者弗及也”。⑤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中),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822页。
查氏水西庄落成之日,查为仁携家眷前去游玩,命以此为题相唱和,女眷们巾帼不让须眉,查为仁的女儿查调凤、查容端、查绮文,儿媳严月瑶,侍女宋贞娘等人都作诗纪念,诗作均被载入《津门诗钞》中。⑥(清)梅成栋:《津门诗钞》(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16-619页。另外,查氏家族的女眷们几乎都有所著述留世,查调凤撰有《鸣祥诗钞》、查容端撰有《晓镜阁稿》、查绮文撰有《丽言诗草》、严月瑶撰有《阆娟诗草》、侍女宋贞娘撰有《草亭诗草》。
(四)“丈夫风格女儿身”的金沅
金沅,字芷汀,号问梅女史,是金至元的侄孙女。金沅深得家庭熏陶,“性婉顺,通礼则,奉尊嫜以孝,得先妣朱太君欢”,⑦(清)梅成栋:《津门诗钞》(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29页。“幼爱文史,在家尝诵四子书、孝经、朱子小学及唐宋人诗。嫁与同县孝廉梅成栋后,益读书,学为文,遂工吟咏,著《问梅小草》一卷”。⑧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中),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827页。梅家虽有门望,却属寒族,“梅氏、解氏,俱有门望,累世清芬,但无贵显,故天津旧有“寒梅瘦解”之称”。⑨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中),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717页。梅成栋与崔旭同出张问陶(船山)门下,同门先后腾达,梅成栋科场蹭蹬,终不得意。金沅曾作《梅花》诗四首,有“纷纷桃李休相妒,不借春风只自芳”之句,⑩(清)梅成栋:《津门诗钞》(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30-631页。一则明己志,亦含有对丈夫梅成栋的理解与慰藉之意,其“问梅女史”之号即有此意。
科场失意的梅成栋着意于诗,“尝就城西水西庄起梅花诗社,集诸名士觞咏其中。生平熟于乡邦掌故,所为诗文大率阐发幽光,表彰懿德,又非徒尚风雅已也”。⑪(清)梅成栋:《津门诗钞》(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013页。梅成栋辑的《津门诗钞》三十卷,其中专列“闺秀”一卷,上起程德辉,下迄金沅,共收录了18位津门闺秀的诗作,使我辈得睹“斯时芳华”。梅成栋能够成为天津文化史上承上启下、至关重要之一人,与金沅的理解、鼓励和影响是分不开的。金沅殁后,梅成栋悼之曰:“良友交情知己泪,丈夫风格女儿身”。①(清)梅成栋:《津门诗钞》(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30页。
三、才女文化向近代女子教育的转型
传统社会的女子教育不是普及教育、全民教育、平等教育和标准教育,它是一种“才女”教育,可有可无,可深可浅。女子能否得到良好的教育主要取决于是否出生在文化氛围和经济基础稍好一些的阶层,是否能够得到父家与夫家的支持与理解。盐商家族具备上述条件,女子教育基础较好。盐商家族的女子教育在查氏、金氏时期发展到顶峰,进入近代以后,严氏家族接过了继承和发扬女子教育的接力棒,实现了女子教育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一)“幼承庭训”是传统女子教育的主要形式
我们在看到封建社会不尽是祥林嫂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女子教育与男子教育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差别。在“德化”的共同基础上,男子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扬名科场”“光宗耀祖”。男子通过接受传统教育,参加科举考试,可以实现跨阶层向上流动,出身农家的男子通过读书可以进入士子阶层,如果科场得意,家族可以转变为官宦之家。女子受教育的目的就简单多了,“相夫教子”之外,陶冶一下情操,少了许多功利性。
“才女”出身的阶层几乎是固化的,能够接受“才女”的家族是有限的。“才女”通过嫁人实现的流动也主要是“平层流动”,农人、工匠家庭的女子很少有机会成为“才女”。无论江南还是天津的“才女”,她们或出身于诗书世家或出身于亦商亦儒的盐商家族。许雪棠是出身于世家的“津门闺秀”。金至元和金沅出身于文化素养很高的盐商家族,金至元嫁入了“门当户对”的查氏家族;金沅嫁入了非常有门望的梅氏家族。大盐商查为仁的女儿、儿媳们“咸工文翰”,侍女都可以吟诗作对。《津门诗钞》中记载的一些姓氏和家世都无考的“才女”,也并非出自诗书家庭之外。“滴滴青衫湿泪痕,不堪回首旧朱门”的丐妇显然遭遇了“门楣之变”。②(清)梅成栋:《津门诗钞》(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25页。“独负寒香过灞桥”的佛女出身于“津邑望族,以诗书世其家。父善画,笔墨为生”③(清)梅成栋:《津门诗钞》(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27页。。家族(包括夫家家族)文化风气的浸淫、文化氛围的宽松是造就“才女”的必要条件。
在教育方式方面,“男女授受不亲”之大防是不可以突破的,“幼承庭训”成为“才女”们接受教育的主要形式,“闺阁”是她们的主要活动范围。“才女”形成的首要条件是个人兴趣,然后是家庭的文化氛围,如果幸运的话,嫁入知书达理的书香门第后,她们爱好“诗词歌赋”的好习惯仍然可以继续下去。在讲究“门当户对”的传统婚姻中,这种“幸运”在一些阶层中或许并不少见,但对整个社会而言,这种对女性的教育方式局限性太大。
(二)北方现代女子教育的雏形——严氏“女塾”
“才女”不具有社会普遍性,在一个家族中也不具有太大普遍性,“才女”的形成离不开女子自身“好吟咏”“极闺房唱和之雅”的爱好和主观能动性。传统“女学”(即女子教育),是中国妇女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教育,除个别开明的家庭外,往往以礼教为重要内容,俗称‘女学’”①陈建武:《论古代“女学”》,《江汉论坛》2002年第6期。。传统“女学”一般围绕女性的三种角色(即父之女、夫之妻、子之母)展开,主要内容为“德、言、容、功”。教材也相对固定,如《女论语》《女孝经》《古今内范》等等。在礼教的基础上,士绅、儒商阶层对女子的“文学素养”会更重视一些。虽然士绅、盐商阶层女子的“幼承庭训”和聘请“闺塾师”还都属于传统女子教育的范畴,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推动近代女子教育出现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他们心底里“女子应该具有同样的受教育权”的潜意识。近代以来,普及女子教育的理念逐渐被人们所接受。长芦盐商家族——严氏家族在这个过程中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成为北方近代女学的“始作俑者”。亦儒亦商的严氏家族继承了长芦盐商家族重视女子教育的基因,加上严修的开放态度,使得近代女子教育的萌芽首先在严氏家族中萌发。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七日(1902年8月10日),严修偕长子智崇、次子智怡赴日本考察。②严修:《严修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90年,第132页。严修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日本的教育,严修特别留心了日本的女子教育。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严修先后参观了神户汎爱幼稚园、育英高等女学校、神户清水谷女学校、东京富士见小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华族女学校、常盘小学校等学校考察女子教育,并与相关人士进行了交流。③严修:《严修东游日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页。赴日本考察,令严修深受触动,日本近代女子教育取得的成就也使他的女子教育实践计划更加具体。严修回国后,在自己的家中办起了女塾,时称“严氏女塾”。严修“聘来日本人川本教日语、音乐,山口教手工艺,野崎教织布,从纺纱到织斜纹、直纹布,也织毛巾。还设有算术、缝纫各课”。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页。严修的次子严智怡任主任兼教国文课,三子严智钟教英文课,⑤赵宝琪、张凤民:《天津教育史》(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3页。严修亲自教授作文课,并编写了《放足歌》,教女塾学生演唱,宣传放足。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2页。女塾学生有严修女儿、侄女、儿媳、侄媳及其四姓近亲好友之女,年龄从十岁到二十几岁。严氏女塾虽然是一所家塾,但它是天津近代女子学堂的“根源”,也是我国近代创办最早的女子学堂之一,在天津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由女塾到女学堂——由封闭到开放
虽然教育范围已较家庭教育有所拓展,但严氏女塾从根本上还是一个半封闭的办学体系,教育对象仍以严氏以及“四姓”亲朋好友家的女眷为主。这种教育规模和方式,显然不能令严修满意。1904年4月,严修偕张伯岺等人再次赴日本考察,女子教育仍然是此次考察的重点之一。严修与张伯苓等人一行再次赴富士见小学校、参观幼稚园,发出“幼儿之教‘真可法也’”的感慨。⑦严修:《严修东游日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7页。6月21日,严修等人赴东京共立女子职业学校参观。⑧严修:《严修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90年,第156页。6月23日,严修在参观完日本早稻田大学之后,专门造访大隈伯邸,与大隈伯“谈教育事及维新前日本女学之大略,约一小时辞出”。①严修:《严修东游日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8页。6月25日,携张伯苓一行赴女子大学参观,听取校长成濑仁藏的介绍,参观家政、文学、教育、体育、美术、音乐、理科七部以及附设的高等女子学校,听取大久保介寿讲学校管理法,论赏罚之宜。②严修:《严修东游日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0页。6月29日,在高师附属小学观摩教学时,看到高等学校各女生舞蹈,“往来变换节之音乐,真运动之妙法。旷生大感动至泣下,盖为吾国女子悲也”。③严修:《严修东游日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7月16日,赴实践女学校,观我国留学生卒业式。考察过程中,严修下定了设立女学的决心。④严修:《严修东游日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7页。回国后,严修倡导开设学堂多处,其中便有天津公立女学堂,这在当时,堪称创举。1904年清政府颁定的“癸卯学制”还将女子教育排斥于教育制度外,在《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中规定“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或受保姆之教”。⑤赵宝琪、张凤民:《天津教育史》(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3页。
严修此时开设的女学堂,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学,而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分科教学的女学堂。1905年,严修改严氏女塾为严氏女学,设高小、初小两级,逐步设置国文、英文、日文、数学、理化、史地、音乐、图画各课,是为天津近代女学之发轫。⑥严修:《严修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90年,第179页。严修的妹妹严淑琳任学监。在校任教的教师有华海门、郑趾周、戴有三、张星六等津门文化界名流。⑦赵宝琪、张凤民:《天津教育史》(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3页。8月,严修在家中设保姆讲习所,聘请日本人大野铃子(女)为教员,张伯苓、胡玉孙及严智崇、严智惺(侄子)也在其中任课。课程有保育法、音乐、体育、游戏等,又设国文、英文、算术、生理、化学等科。另外还设有蒙养园,为保姆实习之所。这一年,严修在河西北窑洼建立高等女学堂及官立女子小学堂。
1905年冬,清廷设立学部,命荣庆为尚书,熙瑛、严修为侍郎。荣、熙为旗人,学部事务实际上大都由严修任之。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页。借此,严修得到了在全国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在这个位子上,他推动了中国第一个女学章程的制订与公布,推动设立京师女子师范学堂。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页。自严修创办女学以后,天津的女子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截至1911年,天津公立、私立女学堂已达20余所,成为当时全国女学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长芦盐商绵延二百余年的重视“女学”的基因在严修这里修成了正果,推动天津乃至我国传统的“闺秀文化”向近代女子教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