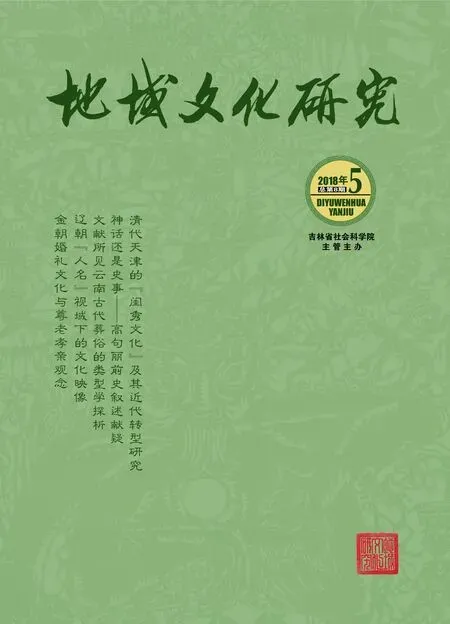高句丽族群形成与王国早期发展互动关系考察
祝立业
提 要:“沸流部”和朱蒙卒本夫余集团的整合,卒本夫余对古“句丽”的借壳,标志着新的高句丽族群共同体的初步建立,其突出表现便是朱蒙桂娄部取代沸流部(涓奴部)为王族,朱蒙死后,新老王族以联姻形式构建新的统治体系,这个体系可以称为高句丽政权和族群共同体发展历程中的“双核”时代,桂娄部和涓奴部共同主导着高句丽王国、部众的命运。此后,琉璃明王通过迁都、立东明王庙及设立大辅、左右辅制度,建立起王国的行政官僚体系,确立了王权的超然地位,高句丽王国和族群共同体由“双核”逐渐过渡到以王室为中心的“单核”。始祖庙、国社的建立和定期祭祀,是此一时期高句丽意识形态构建的重要内容,推动了高句丽族群共同体的进一步凝结。与中原王朝的接触,正史对高句丽的记叙,也进一步形塑出高句丽族群共同体的特质。
高句丽既是一个族称,也是一个王国政权名称。自西汉末期兴起到唐初消散,在7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其族、其国均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这就为后世研究族群聚合和政权建立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本文着眼于高句丽族群共同体形成与早期高句丽王国发展互动关系,旨在研究高句丽族群怎样最初形成,政权建立后,用何种方式促进了族群的进一步扩大,多族群又如何逐渐发展为大的族群共同体;在族群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其王国管理机制如何相应变化,这种变化反过来又如何影响了族群共体的构建。
一、桂娄部与涓奴部共治的“双核”时代
对高句丽早期历史发展的情况记载较多的史籍,首推《三国史记》。就《三国史记》记载看,高句丽建国伊始时,除了完成了对“沸流部”的兼并外,还对太白山东南的荇人国、北沃沮进行了攻占。高句丽向国都东南方向经营说明,随着“沸流部”的加入,王都附近的貊系小部族都已归化。朱蒙时代有一条值得注意的史料,朱蒙于其十四年(前24)为其亡母立神庙①《三国史记·东明王本纪》此条记事为:“十四年(前24)秋八月,王母柳花薨于东夫余。其王金蛙以太后礼葬之。遂立神庙”。,《三国史记》此后对高句丽的记载中,多次提到此神庙,朱蒙时代可明确为高句丽设神庙之始,其亡母为神庙祭祀对象。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高句丽王国的最初由五部组成,五部又称五族,分别为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五部当中以涓奴部和桂娄部为强,最初涓奴部为王,渐渐衰落后,桂娄部取而代之。关于高句丽早期权力更替及政权结构,《三国志·高句丽传》记为“其置官,有对卢则不置沛者,有沛者则不置对卢。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称古雏加。涓奴部本国主,今虽不为王,适统大人,得称古雏加,亦得立宗庙,祠灵星、社稷。绝奴部世与王婚,加古雏之号”②(晋)陈寿:《三国志·东夷·高句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3页。。这段记载的信息量很大,涓奴被可称“古雏加”,亦可“立宗庙,祠灵星、社稷”,说明虽然在国主层面被桂娄部取代,但实力已然超越其他诸部。以至于桂娄部需要与“绝奴部”联姻以巩固权力。看来,原来的五部之中,绝奴部应是比较弱小的,因为弱小才能有主动联姻王室的驱动,以期借王室自重。同样因为弱小而更被王室放心联姻,不必顾虑尾大不掉。绝奴部因世与王婚也取得了“加古雏之号”的特权。一国之内,有两部各立宗庙、“各祠灵星、社稷”,也意味着高句丽王国权力未归一统,王权并不强大。王国运转很可能处于“双核”驱动状态。
其实,高句丽王室最早的联姻对象是涓奴部。涓奴部就是沸流部,早期的卒本夫余也就是桂娄部,卒本夫余整合沸流部后,借壳沸流部古称“句骊”而成为后世意义的高句丽。
在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明王继位的次年,娶多勿侯松让之女。关于松让,在朱蒙时代,松让以国来降,封为多勿侯。也许其原名为“松”,因为“让国”才被称为“松让”。朱蒙之子娶松让之女,算得上门当户对,这其中也隐含了早期王室所在桂娄部需要以婚姻形式加强与涓奴部的联盟关系。松让之女生子无恤,也即后来的大武神王。生母死后,无恤在非长子的情况下得以最终继位,很可能是母亲所在部族拥立的结果,这也彰显出涓奴部在早期高句丽王国内的地位。
按《三国史记》记载,琉璃明王,名为类利,是朱蒙长子,“母礼氏。初,朱蒙在扶(夫)余,娶礼氏女有娠。朱蒙归后乃生,是为类利。幼年出游陌上弹雀,误破汲水妇人瓦器。妇人骂曰:‘此儿无父,故顽如此。’类利惭,归问母氏:‘我父何人,今在何处?’母曰:‘汝父非常人也,不见容于国,逃归南地,开国称王’归时谓予曰:‘汝若生男子,则言我有遗物,藏在七棱石上松下,若能得此者,乃吾子也。’类利闻之,乃往山谷,索之不得,倦而还。一旦在堂上,闻柱础间若有声。就而见之,础石有七棱。乃搜于柱下,得断剑一段,遂持之与屋智、句邹、都祖等三人行至卒本。见父王,以断剑奉之。王出己所有断剑合之,连为一剑。王悦之,立为太子,至是继位”③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一·琉璃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76页。。
这段记载的基本信息为:类利自幼随母长于夫余。联系到朱蒙之母柳花死后,夫余王金蛙葬之以太后礼的记载,朱蒙不为夫余所容,但其母、其妻、其子却都在夫余生活,且颇受礼遇,这也是比较奇怪的。
类利与其母自夫余到高句丽后半年,朱蒙去世。类利继位次年(前18)“秋七月,纳多勿侯松让之女为妃”,但过了一年,松妃就死去了。后面讲大武神王无恤是松氏所生,则无恤应该生于琉璃明王三年(前17),无恤为琉璃明王第三子,则另外二子都切、解明不知由何人生?
在《琉璃明王传》中,都切、解明死得都是莫名其妙的。
关于都切的记载只有两条“十四年(前6)春正月,扶(夫)余王带素遣使来聘,请交质子。王惮扶(夫)余强大,欲以太子都切为质。都切恐不行,带素恚之”“二十年(1)春正月,太子都切卒”①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一·琉璃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78页。。
关于解明,“二十三年(4)春二月,立王子解明为太子。大赦国内”。“二十七年(8)春正月,王太子解明在古都,有力而好勇。黄龙国王闻之,遣使以强弓为赠。解明对其使者挽而折之曰:‘非予有力。弓自不劲耳’。黄龙王惭。王闻之怒,告黄龙曰:‘解明为子不孝,请为寡人诛之。’三月,黄龙王遣使,请太子相见。太子欲行,人有谏者曰:‘今邻国无故请见,其意不可测也’。太子曰:‘天之不欲杀我,黄龙王其如我何。’遂行。黄龙王始谋杀之,及见,不敢加害,礼送之。二十八年(9)春三月,王遣人谓解明曰:‘吾迁都,欲安民以固邦业。汝不我随,而恃刚力,结怨于邻国,为子之道,其若是乎?’乃赐剑使自裁。太子即欲自杀,或止之曰:‘大王长子已卒,太子正当为后。今使者一至而自杀,安知其非诈乎’?太子曰:‘向黄龙王以强弓遗之,我恐其轻我国家,故挽折而报之,不意见责于父王。今父王以我为不孝,赐剑自裁,父之命其可逃乎?’乃往砺津东原,以枪插地,走马触之而死,时年二十一岁。以太子礼,葬于东原。立庙,号其地为枪原”②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一·琉璃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79页。。这段记载一方面显示解明是因反对迁都被琉璃明王逼死,另一方面又显示解明是至孝之人。而一个至孝之人又怎么可能可以反对父亲的军国大事呢?这里显然有矛盾之处。
该如何解释呢?恐怕是都切、解明得不到高句丽其他部族,尤其是沸流部的支持。反观无恤,其母并非琉璃明王首妻,但得享王妃之号,其人非琉璃明王长子,但终得王位,其母虽早死,而其继位却没有障碍。这只能归功于其母亲所在的涓奴部在高句丽王国内举足轻重。当时很可能流行的长子继位制,其兄都切、解明莫明其妙而死,很可能是无恤顺位继承的需要。从《三国史记》的记载看,琉璃明王除了都切、解明、无恤三个儿子外,还有如津、再思二子,如津于琉璃明王三十七年(18)溺水而死;另一子“再思”,也即大祖大王宫的父亲,无恤可能排行第三,前两个兄长死后,其序在前,继位顺理成章。
涓奴部的超然地位还体现在大武神王无恤十五年(32)发生的一件事例中,其大意为大王神王时期,仇都、逸苟、焚求三人为沸流部长,骄横不法、鱼肉民众。因为是朱蒙时代的老臣,虽然罪大恶极,但也只是废为庶人而已,后来派南部使者邹壳代为部长,最后也是以恩服之。作为沸流部首领的仇都、逸苟、焚求罪大恶极,但只受薄惩,说明其所在之部实力雄厚,高句丽王不敢有太大动作。能将一部首领免为庶人同时也说明大武神王时期,以桂娄部为依托的王权也在逐步加强中,也许与绝奴部联姻制衡的效果,已在此时显现。似乎可以做这样一个推断,高句丽王国“双核”驱动时代结束于大武神王统治末期,自大武神王统治末期开始,王权日益加强,高句丽政权和族群共同体由此进入“单核”时代。
二、由迁都、立始祖庙开启的王权渐强时代
高句丽王国发展到琉璃明王时期,有一个重大的举措,王都由纥升骨城迁往国内。关于迁都的序曲,《三国史记·琉璃王传》的记载颇为有趣:公元2年,用于郊祀的猪跑掉了,管牲口的官员遵王令循迹找寻,最后在国内地区的尉那岩找到了,并将其寄养在当地人家。回来后报告高句丽王,极言国内地区适合迁都,即拥有可供防御的山水之险,又有丰饶的物产。琉璃明王被其打动,亲自视察后,决定迁都。过了一年,迁都完成,修筑了尉那岩城。
看起来,过程很简单,决定很迅速。国内地区适宜为都的原因是即拥有可供防御的山水之险,又有丰饶的物产。琉璃明王在逼解明自杀时,自述迁都原因为:“吾迁都,欲安民以固邦业”。
中国正史中也有关于高句丽都城的记载,但迁都时间上不够明确,如《三国志·高句丽传》载:“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秽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都于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户三万。多大山深谷,无原泽”①(晋)陈寿:《三国志·高句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3页。;《三国志·毌丘俭传》记载:正始五年(244)“俭以高句丽数侵叛,督诸军步骑万人出玄菟,从诸道讨之。句丽王宫将步骑二万人,进军沸流水上,大战梁口,宫连破走。俭逐束马悬车,以登丸都,屠句丽所都,斩获首虏以千数。……六年,复征之,宫遂奔买沟。俭遣玄菟太守王颀追之,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南界,刻石纪功,刊丸都之山,铭不耐之城”②(晋)陈寿:《三国志·毌丘俭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62页。;《周书·高丽传》载:高句丽“治平壤城,其城东西六里,南临浿水……其外有国内城及汉城,亦别都也”;《隋书·高丽传》《新唐书·高丽传》亦载:“高句丽都平壤之时,亦曰长安城,东西六里,随山屈曲,南临浿水。复有国内城、汉城,并其都会之所,其国中呼为三京”③(唐)令狐德芬:《周书·高(句)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884页。。
今天集安国内城和丸都山城在当时曾共同构成高句丽的中期国都。
集安市区附近目前发现有两座城址,一为今集安市区所在的平原城,目前称为国内城,一座是距离市区不远的山城子山城,现称丸都山城。
无论是从自然资源角度还是军事防御角度看,国内地区都要优于卒本地区。自然条件上,国内地区是一个小盆地,气候温润,适宜五谷。从守备安全看,国内地区远离汉郡,沿途山水险要,易守难攻。就当时情况看,高句丽迁都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对于日后南进战略影响巨大。
就此次迁都而言,除了上面谈到的原因,恐怕也还要从加强王权的角度考量。一般来讲,打破固有部族势力格局,最好的办法便是将首领和其民众分开,卒本地区是涓奴部的传统势力范围,其影响根深蒂固。桂娄部属后期进入者,虽然被尊为王,但其实权力空间有限。通过打破原有部际利益格局应该也是迁都的内在驱动。
琉璃明王迁都以后,曾发生王子解明自杀一事。表面上看,解明之死是因为没有维护旧都周边稳定而被赐死。从琉璃明王守新都、解明守旧都的格局看,琉璃明王的迁都并不是很顺利,事实上这种情况也是可以想见的,迁都一定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必然会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解明被赐死,除了因为没有很好贯彻琉璃明王意图外,很可能是因为和旧都卒本地区守旧贵族走得过近,甚至为他们利益代言,而招致琉璃明王疑虑,进而逼其自杀,未必不是以此震慑反对派。
迁都国内以后,高句丽的王权确实得到了加强。一个例证是,琉璃明王肆行田猎,五日不返,面对大辅陕父的劝谏,琉璃明王非但不听,反而一怒之下将陕父解职。轻易黩黜大臣,显然昭示着王权已然强化。此外,琉璃明王立无恤为太子时,明确委以军国之事。既然军国之事悉由王出,则此后,见诸史籍的委将率兵西伐梁貊、袭取汉县也都是王权进一步强化的表征。
琉璃明王死后,大武神王无恤继位,“三年(20)春三月,立东明王庙”①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二·大武神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83页。。东明王庙的设立具有重大意义,“这是高句丽王国、高句丽族群共同体历史发展的一件大事。从《三国史记》记载看‘东明王庙’最迟在新大伯固三年改称‘始祖庙’,这意味着其王系及族群共同体始祖构建更进一步,同时也是王权进一步加强的表现,桂娄部之始祖已成为整个高句丽的始祖”②祝立业:《高句丽族群共同体的早期演进》,《学问》2017年第1期。。此后,见于记载的高句丽王祭拜始祖庙的史料如下:
1.(新大王)“三年(167)秋九月,王如卒本,祀始祖庙。”③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四·新大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98页。
2.(故国川王)“二年(180)秋九月,王如卒本,祀始祖庙。”④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四·故国川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01页
3.(东川王)“二年(228)春二月,王如卒本,祀始祖庙。”⑤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东川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08页。
4.(中川王)“十三年(260)秋七月,王如卒本,祀始祖庙。”⑥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中川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11页。
5.(故国原王)“二年(332)春二月,王如卒本,祀始祖庙。”⑦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六·故国原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18页。
6.(安臧王)“三年(521)夏四月,王幸卒本,祀始祖庙。”⑧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七·安臧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36页。
7.(荣留王)“二年(619)夏四月,王幸卒本,祀始祖庙。”⑨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八·容留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51页。
以上史料说明,在高句丽时代,新王继位后到旧都朝拜始祖庙是一个必然履行的程序,这既是宣示敬天法祖、承位有序的方式,同时也是团结部众、凝聚共识的手段。高句丽还有国社和宗庙,很可能始祖庙单设一处,宗庙另立别地,供奉除始祖以外的其他故去的高句丽王。“神庙、国社、宗庙是高句丽王权的表征,也是高句丽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⑩祝立业:《高句丽族群共同体的早期演进》,《学问》2017年第1期。。
三、由军事扩张促成的多族群聚居情况
自朱蒙立国至美川王时期,高句丽历代王均有所开拓,中间虽然遭受了毌丘俭、慕容皝两次严重打击,但总体上领土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多,各代王时期的开拓如下:
高句丽建国伊始时,除了完成了对“沸流部”的兼并外,还对太白山东南的荇人国、北沃沮进行了攻占。高句丽向国都东南方向经营说明,随着“沸流部”的加入,王都附近的貊系小部族都已归化。
琉璃明王时期主要是与夫余的缠斗,双方各有胜负。此外西伐梁貊、袭取汉县,高句丽依托迁都后的国内之险,尝试攻击汉郡,掳掠人口财富。
大武神王时代:二年(19)“百济民一千余户来投”①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二·大武神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82页。;四年(21)冬十二月,“王出师伐扶(夫)余……执扶(夫)余王斩头”②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二·大武神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83页。,大获全胜;五年(22)“秋七月,扶(夫)余王从弟谓国人曰:“我先王身亡国灭,民无所依。王弟逃窜,都于曷思。吾亦不肖,无以兴复。”乃与万余人来投。王封为王,安置掾那部。以其背有络文,赐姓络氏”③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二·大武神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84页。;“九年(26)冬十月,王亲征盖马国,杀其王,慰安百姓,毋掳掠,但以其地为郡县”④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二·大武神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84页。;“(九年)十二月,句茶国王闻盖马灭,惧害及己,举国来降。由是,拓地浸广”⑤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二·大武神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84页。;“十三年(30)秋七月,买沟谷人尚须,与其弟尉须及堂弟于刀等来投”⑥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二·大武神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85页。;“二十年(37)王袭乐浪,灭之”⑦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二·大武神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87页。。
闵中王时代:“四年(47)冬十月,蚕友落部大家戴升等一万余家,诣乐浪投汉。《后汉书》云:大加戴升等万余口”⑧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二·慕本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88页。。
慕本王时代:“二年(49)春,遣将袭汉北平、渔阳、上谷、太原”⑨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三·太祖大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91页。。
太祖大王时代:“四年(56)秋七月,伐东沃沮,取其土地为城邑,拓境东至沧海,南至萨水”⑩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三·太祖大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91页。;“十六年(68)秋八月,曷思王孙都头以国来降。以都头为于台”⑪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二·太祖大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91页。;“二十年(72)春二月,遣贯那部沛者达贾伐藻那,虏其王”⑫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三·太祖大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92页。;“二十二年(74)冬十月,王遣桓那部沛者薛儒伐朱那,虏其王子乙音为古邹加”⑬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三·太祖大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93页。;“五十三年(105)春正月,扶余使来,献虎,长丈二,毛色甚明而无尾。王遣将入汉辽东,夺掠六县。太守耿夔出兵拒之,王军大败”⑭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三·太祖大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93页。;“六十六年(118)夏六月,王与貊袭汉玄菟,攻华丽城”⑮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三·太祖大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91页。;“六十九年(121)春,遂成因据险以遮大军。潜遣三千人,攻玄菟、辽东二郡,焚其城郭,杀获二千余人。夏四月,王与鲜卑八千人,往攻辽队县。辽东太守蔡讽,将兵出于新昌,战没。功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以身捍讽,俱没于阵,死者百余人”⑯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三·太祖大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91页。;“六十九年(121)十二月,王率马韩、貊一万余骑,进围玄菟城”①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三·太祖大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91页。;“七十年(122)王与马韩、貊侵辽东”②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三·太祖大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91页。;“九十四年(146)秋八月,王遣将,袭汉辽东西安平县,杀带方令,掠得乐浪太守妻子”③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三·太祖大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95页。。
新大王时代:“五年(169)王遣大加优居、主簿然人等,将兵助玄菟太守公孙度,讨富山贼”④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四·新大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99页。;“八年(172)冬十一月,汉以大兵向我……汉人攻之不克、士卒饥饿,引还。答夫帅数千骑追之,战于坐原,汉军大败匹马不反。王大悦,赐答夫坐原及质山为食邑”⑤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四·新大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99页。。
故国川王时代:“六年(184)汉辽东太守兴师伐我。王遣王子罽须拒之,不克。王亲帅精骑往与汉军战于坐原,败之,斩首山积”⑥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四·故国川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01页。;“十九年(197)中国大乱,汉人避乱来投者甚多,是汉献帝建安二年也”⑦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四·故国川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02页。。
山上王时代:“二十一年(217)秋八月,汉平州人夏瑶以百姓一千余家来投,王纳之,安置栅城”⑧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四·山上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05页。。
东川王时代:“十六年(242)王遣将袭破辽东西安平”⑨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东川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08页。;“十九年(245)春三月,东海人献美女,王纳之后宫。冬十月,出师侵新罗北边”⑩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东川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09页。;“二十年(246)秋八月,魏遣幽州刺史丘俭,将万人,出玄菟来侵。王将步骑二万人,逆战于沸流水上败之,斩首三千余级。又引兵再战于梁貊之谷,又败之,斩获三千余人。王谓诸将曰:‘魏之大兵,反不如我之小兵。丘俭者,魏之名将,今日命在我掌握之中乎!’乃领铁骑五千,进而击之。俭为方阵,决死而战,我军大溃,死者一万八千余人。王以一千余骑,奔鸭渌原。冬十月,俭攻陷丸都城屠之。乃遣将军王颀追王,王奔南沃沮,至于竹岭。”⑪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东川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09页。
中川王时代:“十二年(259)冬十二月,王畋于杜讷之谷。魏将尉迟楷名犯长,陵讳将兵来伐。王简精骑五千,战于梁貊之谷败之,斩首八千余级”⑫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中川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11页。。
西川王时代:“十一年(280)冬十月,肃慎来侵,屠害边民……王于是遣达买往伐之。达买出奇掩击,拔檀卢城,杀酋长,迁六百余家于扶(夫)余南乌川,降部落六七所,以为附庸。王大悦,拜达买为安国君,知内外兵马事,兼统梁貊、肃慎诸部落”⑬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中川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12页。。
美川王时代:“三年(302)秋九月,王率兵三万侵玄菟郡,虏获八千人,移之平壤”⑭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美川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16页。;“十二年(311)秋八月,遣将袭取辽东西安平”①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美川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16页。;“十四年(313)冬十月,侵乐浪郡,虏获男女二千余口”②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美川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16页。;“十五年(314)秋九月,南侵带方郡”③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美川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16页。;“十六年(315)春二月,攻破玄菟城,杀获甚众”④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美川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16页。;“二十一年(320)冬十二月,遣兵寇辽东,慕容仁拒战,破之”⑤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美川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17页。。
从上述史料可以基本看出,至美川王时期,除原有五部部众外,此一时期,高句丽人口构成中至少还包括辽东汉人、东海人、马韩人、带方郡汉人、北沃沮人、梁貊人、新罗人、夫余人、乐浪土著、乐浪汉人、荇人国人、夫余人、玄菟郡汉人、百济人、平州汉人、肃慎人、南沃沮人、带方郡土著。当时已然是族属庞杂,人口众多。
在《三国志》完成的年代,约公元297年前后,高句丽王国已成为方可二千里、户三万的一个边疆政权。广袤的领土,众多的人口,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事实上,高句丽自琉璃明王时期开始就在不断调整自己的统治机制。
高句丽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除了与汉族、夫余族有密切关联外,与周边的肃慎、靺鞨、鲜卑、沃沮也有很大的关系,肃慎、靺鞨一度供其驱使,沃沮被其蚕食、兼并,与慕容鲜卑长期在辽东争雄,及拓跋鲜卑兴起,北魏王朝建立,又臣附于北魏。
肃慎是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殷商至西汉时称肃慎,东汉至晋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称靺鞨。
高句丽与肃慎一族的关系,史料多见于《三国史记》,在《三国史记》的记述中,未区分不同时期肃慎族系的族称变化,一概以隋唐时期“靺鞨”的称谓,追述前代史事,事实上并不科学。但今天叙述两者关系,不得不依据《三国史记》,所以也只能姑妄从之。
靺鞨最早见载于《三国史记》,是在《东明圣王记》中,“其地连靺鞨部落,恐侵盗为害,遂攘斥之,靺鞨畏服,不敢犯焉”,其实,当时并无“靺鞨”称谓,实为肃慎。
史称靺鞨先人,“多勇力,处山险,又善射,发能入人目”,“便乘船,好寇盗,邻国畏患,而卒不能服”,“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不相总一,“处于山林之间”,“常为穴居”,“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夏则裸袒,以尺布蔽其后”⑥(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挹娄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12页。。这基本描述的是西汉末年肃慎人的生产生活状况。部落林立,无强力组织,所以一开始就受到已初具王国形态的高句丽的“攘斥”,且面对“攘斥”,也只能“畏服”。
从太祖王六十九年(121),“肃慎使来,献紫狐裘及白鹰白马,王宴劳以遣之”的记载看,东明王以来,肃慎一直势力不张,屈服于高句丽。
西川王十一年(280),肃慎侵袭高句丽,“屠害边民”,西川王命王弟达贾率兵伐之。“达贾出奇掩击,拔檀卢城,杀酋长”,并因此被封为“为安国君,知内外兵马事,兼统梁貊、肃慎诸部落”⑦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西川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12页。。
南北朝时期,肃慎改称勿吉,已发展成7个较大的部落,其中白山部因为临近高句丽,故为高句丽所控制,甚至要承担为高句丽作战的义务,如长寿王五十六年(468),“以靺鞨兵一万,攻取新罗悉直州城”①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六·长寿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27页。;文咨明王十六年(507),高句丽“王遣将高老与靺鞨谋,欲攻百济汉城”②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七·文咨明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34页。;婴阳王九年(598),率靺鞨之众万余,侵犯隋之辽西,招致隋发水陆六军讨之③(唐)魏征:《隋书·靺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22页。;故《旧唐书·靺鞨传》称:“白山部,素附于高丽”。而粟末部则时常构成高句丽的边患,史载“粟末部,与高(句)丽接,胜兵数千,多骁勇,每寇高(句)丽”④(唐)李延寿:《北史·勿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24页。。
唐丽战争期间,唐军进攻高句丽安市城,高句丽大将高惠贞曾率靺鞨兵往救,被唐太宗击败,战后,唐太宗下令,收靺鞨兵三千三百人,尽坑之。高句丽宝藏王十三年(654)、二十年(661),仍有高句丽率靺鞨兵进攻契丹、新罗的记载,说明终高句丽一世,白山靺鞨都受高句丽驱使,直到高句丽灭亡,这些靺鞨人才得以摆脱高句丽控制,《新唐书·黑水靺鞨传》:“白山本臣高(句)丽,王师取平壤,其众多入唐”反映的就是这种状况。
鲜卑也是东北大地上一个古老民族,兴起于大兴安岭。为先秦时期东胡族的分支,秦汉之际,东胡被匈奴所败,分为两部,退保乌桓山和鲜卑山,均以山名作为族名,形成乌桓族和鲜卑族,受匈奴奴役。大约在2世纪中叶,檀石槐率部统一鲜卑各部,檀石槐死后,鲜卑陷入分裂。3世纪前叶,轲比能重新统一东部和中部鲜卑,但轲比能死后,各部落又开始独立发展。五胡十六国时期,鲜卑各部落趁中原大乱,先后建立政权。385年,拓跋部建立起强大的北魏政权,并在439年统一北方。北魏后来分裂为东魏和西魏。557年,北周取代西魏。隋朝在北周基础上建立。《三国志·魏书·鲜卑传》注引《魏略》称:“鲜卑,亦东胡之余也。其地东接辽水”,“自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高句丽兴起于辽东山地,与鲜卑相邻,彼此战争不断。高句丽第二代琉璃明王时期,即曾受到鲜卑侵扰,琉璃明王采纳扶芬奴计策,迫使鲜卑“计穷力屈,降为属国”⑤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3《高句丽本纪第一·琉璃明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77页。。太祖王六十九年(121),高句丽寇抄辽队县,曾裹挟“鲜卑八千人,往攻辽队县”⑥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5《高句丽本纪第三·太祖大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93页。。
晋武帝太康年间,以慕容廆为首的慕容鲜卑崛起于辽西,建立了前燕政权,一改往日受高句丽欺凌的历史,转而进攻高句丽。烽上王二年(293)、五年(296),高句丽连续两次遭到慕容廆攻击,致使峰上王哀叹:“慕容氏兵马精强,屡犯我疆场,为之奈何!”⑦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7《高句丽本纪第五·峰上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14页。故国原王时,面对慕容鲜卑侵削不已,高句丽纳质修贡,拱手称臣。
高句丽与慕容鲜卑争夺辽东之地,始于慕容廆时代,高句丽烽上王期间,慕容廆即曾派大军进攻晋成帝咸康三年(337)十一月,辽东公慕容皝自立为燕王,建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史称前燕。慕容皝继承了其父开创的事业,并有所拓展。前燕有争夺天下之志,故巩固辽东为其首要选择。当时高句丽也在积极谋取西向拓展。这样前燕和高句丽的矛盾,较慕容廆时代更为剧烈,争夺的对象就是辽东。
391年,高句丽广开土王即位。公元396年,燕王慕容宝继位后,授广开土王为平州牧封辽东、带方二国王,承认了高句丽在辽东的势力范围。398年,慕容盛继位,公元400年春,慕容盛以广开土王礼慢为由,亲率大军征讨高句丽,一举攻克高句丽新城、南苏两邑,深入高句丽境内七百余里,掠得五千余户而还。此战虽然极大地削弱了高句丽的实力,但未伤根本。经历了两年休养生息、厉兵秣马,公元402年、404年,高句丽两次对燕用兵,最终迫使慕容氏退出辽东,全面占领争夺了100余年的辽东之地。次年,燕王慕容熙进行反击,但终因指挥失当,被高句丽逆转,史载春“燕王熙来攻辽东。城且陷,熙命将士毋得先登,俟铲平其城,朕与皇后乘辇而入。由是,城中得严备,卒不克而还”①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8《高句丽本纪第六·广开土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24页。。至此,高句丽在与慕容鲜卑的争锋中,最终胜出。
公元385年,拓跋鲜卑建立北魏,北魏建立不久,横扫周边诸政权,迅速成为北方霸主。北魏的强大存在,杜绝了高句丽的西向觊觎之心。面对可能的军事打击,保住既有土地和人口成为当时高句丽的首要任务。讨好北魏统治者也就成了当时高句丽王的必然选项,具体途径就是不断朝贡、恭敬有加。高句丽的恭顺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回报,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遣员外散骑侍郎李敖拜高句丽长寿王为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赋予了其守护辽海安宁的重任。
契丹为宇文鲜卑的后裔,因为地近高句丽,历史上与高句丽也多有交集。小兽林王八年(378),“契丹犯北边,陷八部落”。好太王即位元年(391),“北伐契丹,虏男女五百口,又招谕本国陷没民口一万”②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8《高句丽本纪第六·广开土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23页。,其五年(395),又躬率往讨,攻破契丹稗丽部的“三部落六七百营,牛马群羊,不可称数”③好太王碑第一面碑文。见耿铁华、李乐营《通化师范学院藏好太王碑拓本——纪念好太王碑建立1600年》,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页。。
北魏孝文帝太和三年(479),即长寿王六十九年,“高句丽窃与蠕蠕谋,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惧其侵轶,其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止于白狼水东”④(唐)李延寿:《北史》卷94《契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27页。。北齐天保四年(553),即高句丽阳原王九年,契丹遭北齐文讨伐,“其后复为突厥所逼,又以万家寄于高丽”⑤(唐)李延寿:《北史》卷94《契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29页。。
隋文帝开皇年间,“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内附,高祖纳之”⑥(唐)魏征:《隋书》卷84《契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81页。。唐王朝建立后,契丹随即附唐,岁常朝贡。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时,悉发契丹酋长从军,契丹部众积极配合唐军,在唐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沃沮因其地在东,故又称为东沃沮,复分为南沃沮和北沃沮。《后汉书·东夷传》称:“东沃沮在高句丽盖马大山之东,东滨大海;北与挹娄、扶(夫)余,南与秽貊接。其地东西狭,南北长,可折方千里。”一般认为。沃沮居于今中国延边及朝鲜咸镜道的靠海区域。《后汉书·东夷传》“东沃沮在高句骊盖马大山之东,东滨大海,武帝灭朝鲜,以沃沮地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佧郡于高句骊西北,更以沃沮为县,属乐浪东部都尉,至光武罢都尉官,后皆以封其渠帅,为沃沮侯,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去南沃沮八百里”,《三国志》载:“其言语与句丽大同,时时小异。”“沃沮……其俗南北皆同,与挹娄接。挹娄喜乘船寇钞,北沃沮畏之”。
沃沮“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谷,善种田”,地理位置远胜于“多大山深谷”,“无良田,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①(晋)陈寿:《三国志》》卷30《东夷·高句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3页。的高句丽,自然成为高句丽的扩张对象。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初,在东明王王十年(前28),即“命扶尉猒伐北沃沮,灭之,以其地为城邑”②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3《高句丽本纪第一·始祖东明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76页。。太祖王四年(56),高句丽进一步向朝鲜半岛扩张,“伐东沃沮,取其地为城邑,拓境到沧海,南至萨水”③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5《高句丽本纪第三·太祖大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91页。。萨水为今之清川江,此处的沃沮应为南沃沮。这表明,大致在高句丽大祖大王期间,沃沮全境具为高句丽所兼并。
高句丽对沃沮的具体统治政策为:“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使相主领,又使大加统责其租税,貊布、鱼、盐、海中食物,千里担负致之,又送其美女以为婢妾,遇之如奴仆”④(晋)陈寿:《三国志》卷30《东夷·高句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6页。。曹魏之后,史书不见沃沮记载,说明沃沮被高句丽所并后,原有族群渐渐融入高句丽。
四、多元族群并存背景下五部向一体的演变
自朱蒙立国一直到美川王时期,高句丽的王权一直处于不断加强的进程中。立国之初,王室出于桂娄部,王权对于其他各部而言,是盟主而非君主,经过两代王的努力,尤其是经过迁都以后,王权日益扩大,自大武神王起,君主专制色彩日益浓厚。
从《三国志·高句丽传》的记载看,高句丽最初是一个五部联合体,五部各置僚属,以“使者”为号,内部实行家臣制,只向高句丽王备案而已。这意味着早期高句丽无独立于五部之外的政权组织体系,换言之,五部各自为政,高句丽王国只是松散联盟,王室更多起的是协调作用,其角色类于诸侯长。五部之间,涓奴部是曾经的国主,桂娄部是外来的雄强,绝奴部与桂娄部世代联姻,表明桂娄部取代涓奴部为国主,采用的是联合一个本地族群进而压服其他族群的方式。涓奴部虽然失去国主地位,但其部并未被拆散,仍具有强大实力,仍然可以单立宗庙,拥有“古雏加”称号。桂娄部作为外来的征服者,从人员组成上可能比较复杂,并因此而更具开放性、更具地缘性。其他四部则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基于血缘、亲缘而凝结起来的部落,部众成分相对简单,表现为一定的封闭性。
能否根据自己的判断对臣下进行赏赐和惩罚,是衡量王权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准。琉璃明王因扶芬奴立有战功,先欲赐给食邑,在扶芬奴推迟不受后,又赐黄金良马。而对于伤害祭牲的官员,则毫不犹豫地坑杀。一赏一罚,显示出琉璃明王时期王权已进一步加强。到了大武神王时期,已能够将沸流部长废为庶人,次大王时更已随意诛戮大臣,这些都是王权强化的表征,王权越强化,意味着高句丽王国形态越发育。琉璃明王立太子时,明确委之以军国之事,昭示五部之外,更有军国,这也是政权组织紧密的体现。这一时期,高句丽还出现了暴君和暴政,暴君也罢、暴政也好,背后反映的都是王权加强的事实。美川王是被群臣捧着玺绶迎立的,似乎昭示着,此一时期服御制度已然建立。上文提到的暴君烽上王,在位时期大修宫殿,其理由为“君者,百姓之所瞻望也。宫室不壮丽,无以示威重”①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7《高句丽本记第五·峰上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14页。,在当时其实也是一种潮流,是王权强化需要外在体现的反映。
和王权加强相一致的是,王位继承方式也有序可循。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是这一时期王权继承的主要模式。太祖大王时期,“承袭必嫡”被认为是“天下之常道也”。而“以弟之贤,承兄之后”也是“古亦有之、子其勿疑”②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5《高句丽本纪第三·太祖大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94页。。就模式而言,“嫡长子继承制”来源于西周,“兄死弟及”传统则能追溯到商代。
和王权加强相对应,此一时期的高句丽出现了辅臣制。琉璃明王时期有了大辅一职,后来又出现了职责更为明确的“左、右辅”。从史料看,右辅出现的时间更早,似乎专职军事。乙豆智是第一个见诸史籍的右辅,在大武神王八年明确被委以军事③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4《高句丽本纪第二·太武神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84页。。乙豆智在大武神王十年(27)又被任命为左辅,与此同时,松屋句被任命为右辅。大武神王十年也被认为是高句丽左右辅制建立之年,脱胎于大辅的左右辅制标着高句丽王国中央权力架构进入新的时期。左右辅有点类似于中原王朝的左右相。
在高句丽政权早期,左、右辅一职十分显要,具有统领内政、军事的大权。而早期担任这一职务的都是各部的实力人物,如大武神王七十一年(123)冬十月任命的左辅穆度娄,之前的官爵为沛者;次大王讳遂成二年(147)春二月任命的左辅弥儒,之前为贯那沛者。
这种变化的出现与高句丽此一时期土境拓广、人口日多有关。继左右辅之后,高句丽又出现了国相一职,从名称上与中原王朝更趋一致。此时,似乎官职和爵位也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比如首见于史籍的国相答夫,在拜相的同时,被加爵为沛者,其具体权力为“知内外兵马,兼领梁貊部落”④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6《高句丽本纪第四·新大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99页。。左右辅体系变为国相体系,发生在高句丽新大王二年(166),这项改革可能也是新大王之所以被称为“新”大王的原因之一。从答夫的职掌看,“知内外兵马”显示出统领王国所有军事力量的权力,而“梁貊部落”又显示出具有地方管理权的特征。故国川王时代,国相被赋予更大的权力,当然这种权力背后是王权的更加强大,故国川王有“无贵贱,苟不从国相者,族之”⑤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6《高句丽本纪第四·故国川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02页。之语,显示了此一时期王权的自信。山上王曾“以高优娄为国相”⑥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6《高句丽本纪第四·山上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04页。,东川王以“于台明临于漱为国相”⑦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7《高句丽本纪第五·东川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08页。,中川王时期又“命相明临于漱兼知内外兵马事”⑧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7《高句丽本纪第五·东川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10页。,“七年(254)夏四月,国相明临于漱卒,以沸流沛者阴友为国相”⑨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7《高句丽本纪第五·中川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10页。,西川王二年(271)“国相阴友卒。以尚娄为国相。尚娄,阴友子也”⑩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7《高句丽本纪第五·西川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10页。,尚娄死后,烽上王“以南部大使者仓助利为国相,进爵为大主簿”⑪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7《高句丽本纪第五·烽上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13页。。
此一时期,更多的官爵出现在史书中,从名称看既有中原风格的官爵,如中畏大夫、大主簿、太守、驸马都尉,也有高句丽自己特色的,如皂衣、优居、沛者、于台等,显示出高句丽王国政治形态的发展印记。总体上,一套混合内外的官爵体制被逐渐建立起来,地方官制出现了“太守”,显示出高句丽王国占领汉人地区后,在管理上一仍其旧,按照郡县化模式管理。从《三国史记》记载看,早期高句丽官和爵的区分不明显,同一名号,经常此段显示为官职,而下段则显示为爵位,不知是本身的混乱,还是后世记录者的混乱。
鉴于“沛者”和“于台”总是伴随各部出现,基本可推定是专属于各部的高级爵号,如太祖大王时期出现的遣贯那部沛者达贾①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5《高句丽本纪第三·太祖大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91页。、桓那部沛者薛儒伐朱那②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5《高句丽本纪第三·太祖大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96页。、贯那于台弥儒、桓那于台菸支留③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5《高句丽本纪第三·太祖大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95页。。由太祖大王时期的贯那于台弥儒在次大王时期成为贯那沛者的情况看,沛者应该是一部之中最高的爵位,大概是某部之主的意思,于台次之。次大王时期的桓那于台菸支留被任命为左辅时,被加爵为大主簿的事实显示,在中原为官职的“大主簿”在高句丽为高于“于台”的爵号,烽上王“以南部大使者仓助利为国相,进爵为大主簿”④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7《高句丽本纪第五·烽上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13页。条记事,也说明“大主簿”是一种爵号。当然也有可能“大主簿”属于担任王国行政官员后的爵号,而“于台”属于未在王国任职的各部部主之爵号。
左右辅、国相人选的出身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此一时期高句丽王国内部权力结构的一些特征。如左右辅来自不同的部,显然是着眼于权力制衡和部际均衡,国相人选既有自平民间拔擢者,又有在各部贵族间选立,说明不同时期,王权和相权博弈程度不同。大致上,王国危乱时,用人重才不重出身,王权彰显、政由己出。一旦进入平稳时期,相权往往被各部贵族把握,甚至父死子继,说明五部依然实力强大,并且通过掌握相权的方式进一步扩张权力,对王权而言,这是一种消解和制衡。慕本王被杀后,国人以“太子不肖,不足以主社稷”为理由,迎立太祖大王,实际上就是部权强大,甚至参与废立的表现。五部对于王国内部重要官员的遴选甚至高句丽王位继承人的选定都具有重要的发言权。比如在故国川王时期,评者左可虑等与四椽那谋叛,“王征畿内兵马平之。遂下令曰:‘近者官以宠授,位非德进,毒流百姓,动我王家,此寡人不明所致也。令汝四部,各举贤良在下者。”于是,四部共举东部晏留。王征之,委以国政。’”⑤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记第四·故国川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01页。
《三国史记》中,不乏高句丽王被推举继位的事例:“闵中王讳解色朱,大武神王之弟也。大武神王薨,太子幼少,不克即政,于是,国人推戴以立之”⑥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记第三·次大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96页。。“慕本王薨,太子不肖,不足以主社稷,国人迎宫继立”⑦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记第二·慕本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88页。。
普通百姓显然难以左右王位继承人的人选,因而此处的“国人”,我们只能将其理解为各部居住在国都里的贵族,因为他们才具有干政、涉政的可能,而确定王位继承人时,各部贵族必须考虑本部族的利益,只有那些能被普遍接受的具有王位继承资格的人选,才能够在时局混乱,前王不足以掌控局面或者猝死的情况下被推选出来。
美川王之后,“国相”不见于史书记载,“这也许跟美川王本身的即位方式有关:峰上王无道,国相仓助利‘知王之不悛,且畏及害,退与群臣同谋废之,迎乙弗为王。王知不免,自经,二子亦从而死。’①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7《高句丽本纪第五·烽上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15页。乙弗既是美川王,也许他从峰上王的经历中,感觉到了相权对王权的威胁,此后不再设立国相一职”②祝立业:《以王权为中心的高句丽政治制度考察》,《东北史地》2007年第1期。。
因为国相承上启下、总揽一切,被王室和各部所看重,对于国相人选,高句丽王和五部贵族不时进行着博弈,因为国相大多选自各部贵族首领,王权、相博弈其实是为王权与部权博弈的变种。这种博弈在相当的范围和程度上决定了高句丽王国历史发展的走向。
关于地方官职。高句丽的五部是以卒本夫余为中心,依据地理方位划分的五个部族联合体。居中的桂楼部实力较强,被称为中部成为王族。其他四部因分别位于桂娄部的四方,而分别称为东、南、西、北部。早期的高句丽王权便是建立在依靠本部统御四部的基础上。
从《三国志》的记载看,似乎高句丽一开始就有五部,但我们考察一下高句丽的建国神话就知道,其实作为高句丽意义上的五部,是在朱蒙一行逃达今天辽宁省桓仁县城附近后,经过一系列对土著部族的征服后实现的。之前作为部族的五个部落是五个互不统属的部落,只有他们联结在一起时,才作为高句丽的五部存在,也只有五部联结在一起后,才出现高句丽这一民族共同体。
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都贯之以“奴”字,似乎暗含了《三国志》撰写者认为桂娄部和其他四部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按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高句丽民族已经形成,陈寿似乎失于详察,而本末倒置的以为高句丽民族一开始就有五部,事实则是五部的统一,形成了早期的高句丽民族。
关于高句丽的建国传说,在诸史中,《三国史记·高句丽本记》的记载最为详尽:
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一云邹牟,一云象解(象解恐当作“众牟”)……金蛙有七子,常与朱蒙游戏,其技能皆不及朱蒙。其长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非人所生,其为人也勇,若不早图,恐有后患,请除之。”……王子及诸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之,告曰:“国人将害汝,以汝才略,何往而不可。与其迟留而受辱,不若远适以有为。”朱蒙乃与鸟伊、摩离、陕父等三人为友,行至淹水一名盖斯水,在今鸭绿东北,欲渡无梁……朱蒙行至毛屯谷魏书云至音普述水,遇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朱蒙问曰:“子等何许人也,何姓何名乎?”麻衣者曰:“名再思”;衲衣者曰:“名武骨”;水藻衣者曰:“名默居”,而不言姓。朱蒙赐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乃告于众曰:“我方承景命,欲启元基,而适遇此三贤,岂非天赐乎?”遂揆其能,各任以事,与之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一云:朱蒙至卒本扶余,王无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其女妻之。王薨,朱蒙嗣位。时朱蒙年二十二岁,是汉孝元帝建昭二年,新罗始祖赫居世二十一年甲申岁也。四方闻之,来附者众。其地连貊鞨部落,恐侵盗为害,遂攘斥之,貊鞨畏服,不敢犯焉。王见沸流水中有菜叶逐流下,知有人在上流者,因以猎往寻,至沸流国。其国王松让出见曰:“寡人僻在海隅,未尝得见君子,今日邂逅相遇,不亦幸乎!然不识吾子自何而来。”答曰:“我是天帝子,来都于某所。”松让曰:“我累世为王,地小不足容两主,君立都日浅,为我附庸可乎?”王忿其言,因与之斗辩,亦相射以校艺,松让不能抗。二年(前36)夏六月,松让以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都,封松让为主。丽语谓复旧土为多勿,故以名焉。①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一》,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74-175页。
《三国史记》的这段记载,事实上是对《三国志·高句丽传》“今桂娄部代之”的注解。现实的历史场景或许是,庶出的北夫余王子朱蒙一行,因王室内部的迫害被迫出逃,最终在今天的辽宁省桓仁县城附近(卒本夫余)落脚,与当地一支土著部族,以联姻的形式结合组成了最初的桂娄部。此后朱蒙以桂娄部为依托,展开对周边小部族的吞并。“松让以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都,封松让为主”正是早期朱蒙政权的吞并模式。因为朱蒙所在部落并不完全具备“占其地,治其民”的实力,因此采取了“因其豪酋治其民”的统治方式,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这显然是最为有效、成本最低的统治形式。
早期高句丽王对五部臣民的统御是通过各部贵族间接实现的,对各部而言,直接效忠对象首先是各部的大加,而后才是高句丽王。桂娄部高于其他各部的军事经济实力则是保证这种统治模式有效进行的基础。对于高句丽政权的上述统治模式,笔者称之为“王国的五部化”。
终高句丽700余年历史,五部始终没有消亡,即便到了唐丽战争时期,五部作为实体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说明高句丽事实上最终也没有完全建立中央集权体制,高句丽是以五部为基本单位对外扩张的,很可能是谁出兵、谁受益。
中原王朝自秦始皇以来,一直处于不断加强君权的历程中,历代君主都强调“威柄自操、政由己出”。在推行郡县制的过程中,旧贵族的权力渐渐被新的官僚阶层取代,没有贵族头衔的文人和原本属于吏的阶层以及新的军功阶层,渐渐成为帝国行政的主体,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需要建立贵族体系之外的新的行政体系,去实现君权独尊的愿望。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历史趋势,自然也影响着处于这一历史洪流中的高句丽政权。
在高句丽的不断对外扩张中,五部土地、人口都在增加,实力不断增强,甚至尾大不掉。如何有效的统御五部、贯彻政令,也日渐成为高句丽王面对的问题。解决五部利益与王国利益冲突的方法,对高句丽王而言只有“五部一体化”一个选项,也就是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国中有国、政出多门。抑制各部权力对于王国权力的侵蚀。这集中表现在仿效中原王朝更改王国权力架构和推行郡县制的举措上。
其实早在大武神王处理沸流部长的仇都、逸苟、焚求三人犯法事件上,高句丽王就在进行“五部一体化”的尝试,被派去代理沸流部长的官员本为南部使者,这实际是一种“异部管理”的思维,即用彼部之官管理此部之事,从而消除部内的袒护。就高句丽内部管理而言,这是对低级别官员任用方式的一次变革。这种变革即使没有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下来,却至少是一种新的尝试。
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句丽迎来发展良机,辽东、乐浪、带方等传统汉郡陆续被收入版图,汉人的大量融入以及汉地先进的生产方式,使得高句丽王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其统治机制也相应进行了调整,地方建置上出现了郡、县、村之制,相应有了邑长、仟长、佰长的官职,行政、军事合为一体,和后世猛安谋克相似。
在唐代之前,也曾散乱见到类似于中原地方官职的记载,如高句丽太祖王曾“赐栅城守吏物段有差”,太祖王五十年时“东海谷守献朱豹”,西川王十九年时“海谷太守献鲸鱼目”,峰上王在位时高奴子被提升为“新城太守”。此外还有“新城宰”“鸭绿宰”“三品栅城都督”等明显具有地域性的官职。
从《三国史记》的记载看,高句丽王国之内还有更小的“封君”的存在,这种封君很可能只具备荣誉性质,并无实际领地和权力,如据《三国史记》载,新大王伯固曾封遂成之子为“让国君”,西川王曾“拜达贾为安国君”。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管理机构及官职的设立,都反映了多族群加入后高句丽王国管理的内在需要。高句丽“五部王国化”进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推行郡县制,唐丽战争时期,地方上出现了褥萨和道使等明显带有郡县化标识的官职。有理由相信这些郡县不依附于五部而直接听命于高句丽王。高句丽的郡县化显然并不彻底,高句丽灭亡时,有城一百七十六座,只有三分之一看起来实行了郡县化管理。其余三分之二应该还在五部控制之下。
自美川王开始,高句丽王国出现了“相位虚悬”的局面。我们知道,当一种权力出现真空时,必然有另一种权力或者权力的另一种形式去填补这种空缺,比如明朝罢相不设后,出现了内阁,建立了辅臣制度,进而首辅又成为实际的“相”,而清代则出现了军机处。
五部在扩张战争中分别得到了壮大,对权力和利益的争夺也日益加强。攫取最高的权力的欲望也随之不断增强。在这种形势下,“王国五部化”的倾向表面上看似乎愈演愈烈了,但其实却涌动着“五部一体化”因素。正是在这种争夺中,各部力量的发展渐渐失衡,资源、权力逐步走向一部。这一政策可能催生出新的能够取代王族的力量,也可能因各部都得到削弱,而使王权更加占有优势。无论出现何种局面,历史发展的趋势都是渐渐的走向“五部的一体化”。
结 语
“沸流部”和朱蒙卒本夫余集团的整合,卒本夫余对古“句丽”的借壳,标志着新的高句丽族群共同体的初步建立,其突出表现便是朱蒙桂娄部取代沸流部(涓奴部)为王族,朱蒙死后,新老王族以联姻形式构建新的统治体系,这个体系可以称为高句丽政权和族群共同体发展历程中的“双核”时代,桂娄部和涓奴部共同主导着高句丽王国、部众的命运。此后,琉璃明王通过迁都、立东明王庙及设立大辅、左右辅制度,建立起王国的行政官僚体系,确立了王权的超然地位,高句丽王国和族群共同体由“双核”逐渐过渡到以王室为中心的“单核”。始祖庙、国社的建立和定期祭祀,是此一时期高句丽意识形态构建的重要内容,推动了高句丽族群共同体的进一步凝结。与中原王朝的接触,正史对高句丽的记叙,也进一步形塑出高句丽族群共同体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