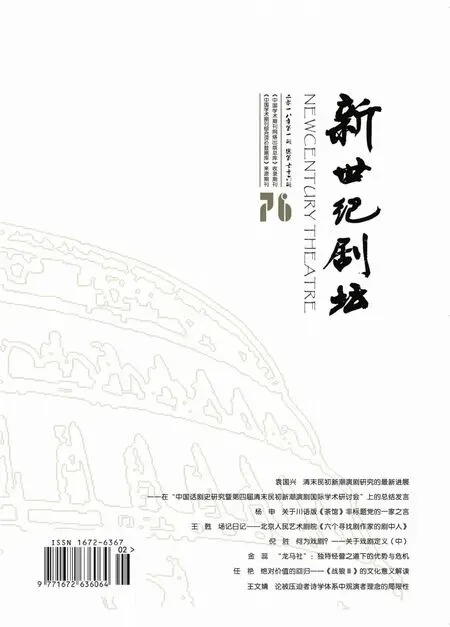剧评二则
好听好看的歌剧《玛纳斯》
我不懂歌剧,只凭个人感觉好听好看就好。
中央歌剧院演出的歌剧《玛纳斯》就是我感觉好听好看的歌剧。
《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的史诗。既是史诗,那就很长。中国现在有记载的《玛纳斯》有8部,20多万行。吉尔吉斯斯坦的《玛纳斯》更多更长。《玛纳斯》讲述的是柯尔克孜民族英雄玛纳斯家族的传奇。史诗是人类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支柱,有史诗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把史诗改为表演艺术是世界最通常的做法。史诗很长,看起来和听起来要花费很长时间,把史诗改编成表演艺术,能让史诗得以更广泛的流传。
改编史诗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就是取舍。成功的取舍应该是突出自身艺术形式的特点又不失史诗精神和精华。古往今来,世界上成功的史诗改编有许多。中国的,好像不多。
歌剧《玛纳史》向成功改编史诗前进了一大步。
歌剧,首先是听音乐。
《玛纳斯》的音乐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不懂音乐,但是从小在歌剧院长大,几乎天天就是听音乐。我个人认为歌剧音乐的关键是旋律叙事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唱段和唱段之间的音乐要流畅,唱段要能推进剧情发展,典型唱段可以独立成歌,歌剧的高潮也是音乐的高潮,咏叹调要能流传。
歌剧不是话剧加唱,歌剧也不是歌曲连唱。歌剧是一个完整的音乐作品,音乐的风格既要统一完整,又要有鲜明的个人主题音乐,个人主题音乐要互相辉映,相得益彰,彼此推进。这些说起来有点儿模糊,总之,就是听起来好听,不别扭、不“咯楞”就好。
《玛纳斯》的作曲许舒亚先生有20年在法国留学和工作的积累,他作为一位中国音乐家,对西洋歌剧的规则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他又是一个对中国音乐有着深厚感情的音乐家,为了写好《玛纳斯》,他多次深入到新疆柯尔克孜民族生活的地区,采集了大量的柯尔克孜民歌。他能把柯尔克孜民族音乐和西洋正统的歌剧创作方式很好地结合起来,找到了史诗《玛纳斯》丰富的音乐形象,只有大量占有原始音乐素材,才能从容地加工提炼,才有了《玛纳斯》这样好听的歌剧。
我是第一次看杨洋指挥的中央歌剧院的乐队,这让我对中央歌剧院乐队刮耳相听了。
歌剧好听靠作曲,歌剧好看靠导演。
我对王延松的导演作品一直比较看好。他是一个有思想、有追求、有品味、有创新的导演。他的舞台美学观念求新求美求品味。这一版《玛纳斯》再一次展示了王延松的导演追求。
我看王延松的戏有一个感觉:他总是先在舞台美术上做戏剧表达的整体大格局。当年看他给总政话剧团导演的《日出》就吓了我一跳。他居然把上海交际花陈白露的豪华公馆设计成一个鸟笼子,这样的暗喻实在是深刻又准确。去年看他导演的小剧场话剧《独自温暖》,那冷峻、多变、无常的家居准确表达了一个变态又心地善良的老女人的状态,又让我由心敬佩。这一版《玛纳斯》,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可以时开时合的巨大地块,这让我想起《三国演义》的开篇“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玛纳斯》是史诗,被认为最早流传在公元3世纪。1000多年来,人类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西北更是如此。合也好,分也好,总是人类的选择,是当时的人群为了更好地生活。就是这样一个时分时合的舞台,寓意着英雄玛纳斯带着柯尔克孜人民艰苦卓绝、生生不息的精神。除了这个巨大的土地版块,舞台中间时常升起一个巨大的生动的马头,骏马是草原民族的依靠,骏马也是草原英雄的象征。当玛纳斯站在这巨大的马头身后时,一个神一样的英雄就屹立在观众面前。还有天幕上一直出现的飞翔的雄鹰,鹰是柯尔克斯民族最好的朋友,一只好的猎鹰可以养活一家人。雄鹰又是柯尔克孜英雄的象征。玛纳斯就是柯尔克孜人心中最勇敢的雄鹰。盘旋在天上的雄鹰,就是玛纳斯,就是柯尔克孜。这样的场景,很好看。我觉得王延松导演总是能和舞台美术部门达到最佳的创作状态,所以,他的戏在整体视觉上就让观众进入戏剧环境。有了一个成功的舞台美术设计,戏就可以在这样典型的环境中纵横驰骋了。
曲子写得好,歌剧就好听。导演有水平,歌剧就好看。可是要把好歌儿唱好听,要把好戏演好,还得靠演员。中央歌剧院的演员确实是中国国家队,实力不凡,尽管有的角色是特邀演出,但这是国际惯例,是允许的。袁晨野和幺红都是成熟的歌剧表演艺术家,他们饰演的玛纳斯和卜妮亚非常出色。王传越饰演的赛麦台依男高音非常漂亮。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饰演阿依曲莱克的郭橙橙。她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花腔女高音,她的演唱为阿依曲莱克增色不少。这台演出的所有演员的音色都非常漂亮。在大乐队伴奏、大剧场演出不用戴麦,这真是值得中国的话剧团体、戏曲团体好好学学。人家能做到,你们为什么做不到?
如果说我对这部戏有些什么建议,我觉得剧本还是弱了一点儿。王晓岭老师是中国著名的诗人和歌词作者。他能完成《玛纳斯》这样的由史诗改编的歌剧实属不易。但是,《玛纳斯》作为史诗,本身的史诗语言对歌剧的编剧而言,无疑是可以借鉴同时又带来禁锢。我觉得这部戏的编剧太过于拘泥于史诗《玛纳斯》的语言,没有把史诗语言大胆地放到歌剧里去进行再创作。歌剧也是剧,是剧就有戏剧的逻辑,戏剧逻辑和史诗逻辑是不一样的。史诗可以有游离于人物和故事情节之外的大段的抒情,这些抒情一定很美,但是拿到舞台上来不一定有戏剧性,而戏剧性不强是影响观剧人的审美兴趣的。歌剧的唱段和一首单独的歌曲也不是一个写法。好的歌曲是个人感情的抒发,可以没有故事情节,而歌剧的主要唱段是要唱故事的。歌剧情节要靠唱词推进,过于热衷一段唱词本身的完整,忽视了主要唱段对剧情的推进作用,唱词和唱词之间的逻辑联系不紧,就会影响戏剧的整体艺术感染力。玛纳斯和赛买台依两代英雄一个死法,都死在叛将手里,这不能拘于史诗原来的结构,在戏剧结构上是应该变化的。如果赛麦台依在紧急关头,玛纳斯来托梦,使赛麦台依躲过了这一劫,则会使两英雄更增加了传奇色彩,也符合史诗精神,岂不更好?
我还是觉得这是中国近年来不多见的真歌剧。说它是真歌剧是因为它具备歌剧欣赏美学的主要要素,好听,好看,舞台画面美,音乐旋律有激情。这是大歌剧必备的。如果把剧本改得再好一些,《玛纳斯》可以成为中国歌剧的保留剧目。
我开始就说过,对歌剧我是外行。权当胡说。
隐瞒真相往下混——看淮剧《小镇》
2017年3月在北京长安大戏院看了由江苏省淮剧团演出徐新华编剧、卢昂导演的淮剧《小镇》。这是根据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改编的。《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是马克·吐温写于19世纪90年代的小说。那时,马克·吐温看不惯美国社会一些假斯文、假崇高的坏现象。他让一个人来到被称为美国道德优秀楷模的赫德莱堡小镇上,宣称自己多年前曾经在这个小镇被一个人相救,但是他没有看清救他的人的相貌,现在他要找到这个人,并送给这个人一袋金币。一时间,有19个人声明是自己救了那个人。可是这19个人被一一揭穿并不是救人的人,文明小镇的道德底线被撕开。马克·吐温通过这样一个故事,抨击了美国社会的虚假文明和在金钱诱惑下,人的道德底线的失守,对推动美国的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把一部100多年前的外国小说改编成中国戏曲在舞台上表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故事要中国化,要现代化,要为今天的中国观众接受。徐新华对《小镇》的改编很成功。不知道这是根据美国小说改编的观众,会相信这是发生在中国南方一个小镇的故事。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逻辑,都对。边文彤老师的舞美设计,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南方水乡小镇的风貌。就是我这个事先知道这是根据马克·吐温小说改编的人,也被舞台上表现出来的纯正中国南方风味所吸引。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中国各个地方都被金钱至上的思想影响着,小镇也不例外,故事就是在这样的中国现实背景下开始的,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义。
戏是围绕小镇上的老师朱文轩展开的,朱文轩是市级模范教师,不但课教得好,而且一生助人为乐,经他帮助的人无计其数,他是小镇的精神文明楷模。可是,当他家中遇到危难,儿子经商破产将被追究法律责任时,他动摇了那颗正直的心,想冒领无人认领的五百万,以救儿子一条命。戏在朱老师当年救没救人、没人认领救人的钱时他要不要领钱救儿子、冒领并没有被揭穿后要不要自己主动向公众说出真相、要不要为了保护小镇人的文明形象而一直隐瞒真相中纠葛,这一系列矛盾层层深入,入情入理,扣人心弦。这是一出写人的戏,写人的内心冲突的戏,写人在真诚与虚伪中间挣扎的戏。写得好,演得好。
一个地方剧种,如何让其它地方的观众喜爱,一直是我没想明白的问题。早年间,地方戏主要在本地演出,为本地老百姓服务,本地百姓的语言、民歌、民调,和地方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年间没有音响也没有字幕,老百姓也没文化,不认字,但听得懂戏,看得懂戏,主要原因就是语言相通,曲调相通,对戏里的故事有共识。京剧等一些较大的剧种得以在全国流行,靠的是“玩艺儿”。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看戏就是看“玩艺儿”。“玩艺儿”主要是“念、唱、做、舞”。没有“玩艺儿”的戏就不“叫座儿”。“玩艺儿”就是绝活儿,就是做的地道。地方戏的“玩艺儿”我看首先是唱功。唱得好,老百姓爱听,戏就受欢迎,所以过去看戏也叫“听戏”。可是对不熟悉地方戏语言的外地观众,如何欣赏地方戏就有一定的难度了。不用回避,现在有“玩艺儿”的演员越来越少了,地方戏如何让更多的观众欣赏呢?
我看不少地方戏剧团都走了话剧的路子——请导演排戏。
在西方戏剧中,导演是一门学问,甚至是戏剧中最重要的人物。戏,是导演排出来的。应该说,这些年,导演对地方戏曲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前一段时间,有人发文章说话剧导演毁了戏曲。这话不妥。没有话剧导演,戏曲更难度日。
《小镇》的导演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卢昂教授。这出戏,看出了导演的功力。
前面说过,戏曲首先靠唱。《小镇》的主演陈明矿唱得好。我不懂淮剧,但我听得出来陈明矿的嗓子好,音厚音宽,这是一个演唱者的本钱。陈明矿的行腔委婉自如,对戏词理解深刻。所以,他塑造的朱老师撑起了舞台,撑起了故事。这是一个剧团,一出戏成功最重要的条件。有了优秀的主演,其它演员就可以向主要演员靠拢了,“一棵菜”就可以形成了。光有演员的唱还不够,戏曲的节奏,要靠音乐来衬托。《小镇》的音乐写得好,导演利用戏曲音乐调整戏剧节奏手段纯熟。每当关键时刻,锣鼓点紧敲慢打,音乐抑扬有度。人物的心理节奏、剧情的快慢进展,在音乐的烘托下,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这是这出戏好看的关键。我不知道淮剧有没有程式化的表演方式,但我认为我看出来《小镇》中从舞台调度到演员间配合中的程式化表现方式的舞台美。这也是这台戏好看、耐看的重要方面。
《小镇》好看,和戏中要表现的思想有重要关系。马克·吐温的原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揭露、嘲讽了小镇人在金钱面前的全面败溃。而《小镇》则反其意而用之,在败溃之际,小镇人对金钱的冲击做了全面的反省。
这真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马克·吐温在100年前,揭露美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的道德水准的下降是有意义的,当时美国只有100年的历史,国家没有根基,民族没有传统,美国的文明是靠这样的不断揭露丑恶而建立起来的。今天的中国,面临和美国当年差不多的情况。但是,《小镇》的作者没有忘记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中华民族有着“仁、义、礼、智、信”的优秀文明。小镇中心那口大钟上刻着“清白自重”四个大字,就代表着中华传统文明的源远流长。《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中,止于对小镇人的虚假道德揭露。而《小镇》则没有停留在那个层面上。它让小镇人对道德失误做了反省。这个反省是分两次进行的。一次是朱老爹对40年前一次偶尔失误的反省,为了不败坏小镇文明的名声,朱老爹对自己的一次小失误掩盖了40年,40年中,他用无私的奉献来为自己赎罪。而40年后,朱老师则对自己的失误当众认错,他不怕丢脸面,不怕丢了小镇的好名声,他不愿意用维护自己模范的名声、小镇清白的名声来掩盖一个失德的真相。朱老师的当众认错,是朱老爹默默赎罪的道德升华。
真相再丑,揭出来才能给世人以警示。揭出来才能重新做人。这一点,是《小镇》这部淮剧最高的价值。
真相掩盖越久,包袱就越背越重。隐瞒真相往下混,会走入无底深渊。
一个人不能生活在虚假中,不能生活在精神包袱下。
一个小镇觉醒了,古镇重回文明。
一个县城也应该觉醒,一个城市应该觉醒,一个国家更应该觉醒!把真相告诉公众,才能正常往前走。“灵魂的拷问与自我救赎,是我们这个民族当下最为缺失的,也是最应召唤的。”——这是导演卢昂写在演出说明书前页的话。我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