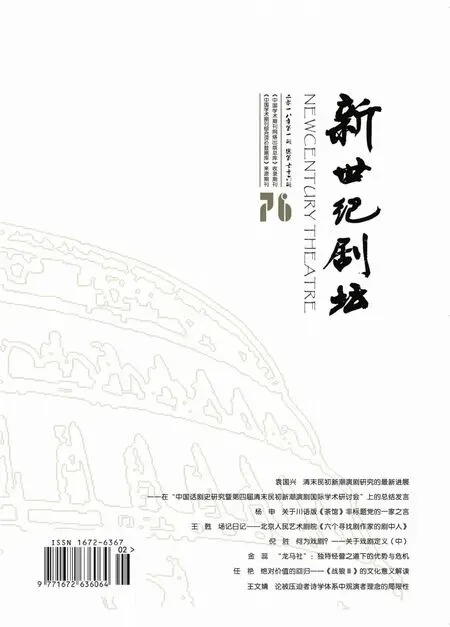叫醒戏剧的魂儿
有个固执的美国老头,阿尔比,裹挟着心灵的风暴,用戏剧的武器摧毁了一座座精神奴性和惯性的堡垒,在人类的艺术陷入娱乐至死或者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操控一切不能自拔的时候,他从那泥潭中迈出了艰难探索的步履,走向人性没有灯光的荒蛮幽暗地带。他要用自己的创作叫醒戏剧的魂儿。
没有魂儿的戏剧注定失魂落魄。戏剧要么是无家可归浪子的出游,抑或是朝着灵魂故土的归航和跋涉,要么是针对社会现实的X光片一样的病灶扫描……概而言之,戏剧可以是心灵守望、聚焦、探索的所有层次上的收获,但关键一点在于,它不能少了筋骨、血脉、气质和精神。
阅读阿尔比,你会获取一颗跟着骚动的戏剧而激荡、畅游、对撞的心。
“我恋爱了!她叫西尔维娅。她是只山羊!”阿尔比想干什么?这老头莫非疯了!像晚年的尼采,抑或日落时分的托尔斯泰,他们的痴迷、癫狂和执拗,触及到了人类思想最痛苦、最深沉、最麻木、也最荒凉的边界。阿尔比,你已经是炉火纯青的大师了。可以安度晚年,在荣誉、地位、声望的光环里,坐享其成,说些无关痛痒的废话、蠢话、啰嗦话,没有人会和你抬杠较真。但你偏不,你还是带着从前的犀利、叛逆、固执、清醒还有魔法,用那出名为《山羊或谁是西尔维娅?》的戏剧,对着已经黯淡甚至消失的人类良知敲击、追寻、叩问。是的,你不能不那样。真正的戏剧人的心愿应该那样。
“剧中的男主人翁马丁·格雷是一位美国社会中典型的体面、正直、事业辉煌的建筑师。他与他深爱的妻子和儿子过着理想的幸福生活。在他的幸运之周里,他三喜临门。除了五十岁的生日晚会外,他还荣获国际最高荣誉的建筑设计奖和一项地标建筑设计的巨资合同。然而,当他惶恐不安地向友人袒露自己难以启齿的隐秘——他与一头山羊(西尔维娅)之间发鞥了难以割舍的性爱时,他四周的一切——家庭、亲情、生活和事业在瞬间崩裂了。”
这是译者胡开奇对该剧的引言介绍。我阅读的《山羊:阿尔比戏剧集》[1]就出自胡先生之手。是他在中文读者和原作之间搭建起了一座值得光顾、领会和欣赏的艺术之桥。
《山羊或谁是西尔维娅?》称得上惊世骇俗的作品,它对生命本相的洞察、烛照和揭示几乎触及了人类情感与思维的底线。马丁·格雷的最大难题是他爱上了一只山羊。身不由己、情不自禁地,跟它发生了关系。戏剧的张力就是要营造一个有魅力的纽带,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但是人与一只山羊,大概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鲜有的,属于个案吧。阿尔比,你这是在文明的伤口上撒盐呢。你曾说,“所有的文明对其宽容度都有着专断的限制”。于是,你渴望用自己的、异端的、非比寻常的方式来给独断专行的文明松绑解压。你这老顽童似乎在得意洋洋地跟我们说,让人跟其他生灵谈个恋爱,过瘾吧。是的,你这一过瘾,却给那对夫妻酿造了平生最苦涩的酒,你把荒诞引向了家庭伦理的深水区,进而引向了人类挑战自我极限的临界点,结果你也毁掉了那只无辜而可爱的山羊。你究竟图个啥?!
说句心里话,阅读阿尔比,曾经是一种折磨。他早年的代表作《动物园故事》,是我大学时代看到的最令人头疼的荒诞派作品。《等待戈多》让我闷闷地枯想枯坐,然后越看越有意思越有滋味,“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戈多,永远的人生话题,不老的追问。《犀牛》则是挖到了人类异化的病根——从众性,即昆德拉常讲的媚俗,尤涅斯库如果见到昆德拉,当引为知己。《女仆》的主仆游戏,假戏真做,应了作者让·热奈的那句一语成谶的格言,“我自由了,我迷路了。”女仆反仆为主,没想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看来,自由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而《动物园故事》演绎的穷汉杰瑞和绅士彼得由于话不投机最后导向凶杀的结局,我琢磨不出这里面埋藏的人性逻辑。那会儿,年轻,不懂得两个彼此隔离错位的生命,会由于一个奇妙的场,在那公园的长凳上,命运之神已经瞄准了他们,让他们身不由己地进入戏剧的圈套。及至年长一些,才稍微悟出了点什么。阿尔比就是阿尔比。荒诞本来就是反常规,反逻辑,反理性的。而人类意识的崩溃,常常就出自荒诞的背反。不可理喻有时候比情理之中更值得我们探寻剖析。那是更强大的宿命和悖论。如果说,“隔绝”带来了“异化”,是《动物园故事》的主题,那么,幸福感带来了麻木,而精神和肉体渴望突围,就是“山羊”故事的最原始的推动力。马丁·格雷看起来什么都不缺,人家是成功人士嘛。美国梦,其实求的不就是成功,不就是幸福嘛。然而,美国的戏剧大师们却不这样看。无论尤金·奥尼尔,还是田纳西·威廉斯,也包括阿瑟·米勒在内,他们把成功和幸福视为人性的陷阱,在心灵的天平上,虚无感、幻灭感可能分量更重。母爱的温情,在奥尼尔眼里却是漫漫长夜(《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威廉斯把欲望的底座压在了文明的秤砣上(《欲望号街车》)。米勒懂得美国梦的实质就是良心的抽空,功利主义的凯歌高奏(《推销员之死》)。到了阿尔比,这个硕果仅存的美国戏剧翘楚,这个古怪爱剑走偏锋的精神探险者,他却发现人的性爱可以越界。在阿尔比眼里,文明体制就是枷锁。爱可以是多向度的吗?马丁当然爱他的妻子斯蒂薇(戏里的一言一行神态举止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后来他又爱上了西尔维娅,那只山羊。他的命运由此得以更改或曰逆转。
斯蒂薇不能容忍他的丈夫爱西尔维娅“爱得跟我一样深”。马丁把心里的秘密都告诉给了那位知心好友罗斯,而后者也无法容忍和理解“你在和一只山羊发生关系!”的事实。所以他给斯蒂薇写了一封告密信。如果把山羊换成另一位女士,或许斯蒂薇会容忍默许,也难说,至少她在心灵的失衡程度上会有所缓解。罗斯大概会觉得那是男人再正常不过的情感出轨。但是有了山羊介入的纠纷,性质就变得严重了。斯蒂薇用的词语叫兽交。人和动物发生了性行为,碰触到了人类伦理道德的分界线,当然她要怒不可遏了。
全剧一共三幕。第一幕马丁和妻子等罗斯前来采访,他们聊着家常。期间,马丁向妻子遮遮掩掩地袒露了他爱上一只山羊的事。妻子误以为他在开玩笑,是恶作剧。阿尔比在此铺垫得很妙。将人物命运转换给了先在的心理预期。后来是罗斯采访过程中,他们由斗嘴转到了对内心真实的揭发,马丁于是向挚友摊牌。在对方的认知观念上掀起了惊涛骇浪。
第二幕是三个人的戏。夫妻加上他们的孩子比利。比利同性恋,这一身份加强了故事的有机和打破常规的情理。当然,在母亲眼里,儿子的恋爱可以接受。其实,这个接受也是社会经过相当长历史时期的煎熬而得以理解和认可的。现在谁能说同性恋是不正常的呢。性取向因人而异嘛。可是,丈夫爱上了山羊,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十恶不赦了。比利也认为爸爸是个性变态狂。但作为孩子,他还是不希望父母为此闹个你死我活,因此在下场时他几乎是哭着退出。接着多半场的戏让给了一对夫妻的心理较量。就编剧法来说,人物动作的性质比动作的强度更能激发戏剧本身的生命力和感染力。从契诃夫开始,描写人物内心的冲突和焦虑,就成为经典戏剧作家们最擅长的地方。在阿尔比的戏里,妻子是唇枪舌剑,刀刀见血。丈夫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可他根深蒂固地觉得自己是无辜的,值得同情和理解。他的辩护里,提到不同人跟猪、跟狗,还有跟鹅发生的恋情。这仿佛是传奇,也仿佛是神话故事。以此,也有研究者认为阿尔比的这只山羊只是一个象征,一种隐喻,剧中的兽交不过是剧作家对一种社会理念的文学性思考与探索(参阅胡开奇《一个悲剧定义的注解》)。其实,打开人类浩瀚无尽的精神画卷,我们会轻而易举地找到人与其他物种缠绵爱恋的篇章。就说《聊斋》里的,人跟狐狸做成了夫妻,《白蛇传》更是人蛇之恋。当然它们作为故事被接受和认同,是艺术幻化的结果,狐狸和蛇毕竟成了精,有了人形方可。而同样是人和兽之恋,阿尔比的戏,大概更自然,更本性,更赤裸裸,没有为这种畸恋披上一层幻觉美感的外装。
西方戏剧传统从古希腊以来,就有着质疑、拷问、追寻、探求的无边界的特征,人对神、上帝、命运等等都可以设身处地给予怀疑、抨击、嘲弄和鞭笞,由此戏剧之魂通向终极的自由造访、释疑、解答和追问。
归根到底,人的本性存在与制约性的人类文明构成了对峙和碰撞,阿尔比以他不可更改的愿力试图承接西方戏剧传统对人生难题的不懈思考、回眸与眷顾。他要探索文明的宽容度到底可以宽容到哪个限度。其实,阿尔比在《山羊或谁是西尔维娅?》写作范式里所构筑的本能与道德、感性和理性、内驱力和外在约束力之间的对抗,就哲学意味来讲,并没有超出赫伯特·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所触及的最敏感的人性边缘地带。马尔库塞曾经公允地指出,“文明陷入破坏性的辩证法之中,因为对爱欲的持久约束最终将削弱生命本能,从而强化并释放那些要求对它们进行约束的力量,即破坏力量。”这样文明无形中就以虚伪的道德律令的镣铐来捆绑住人对爱欲的真实渴望和诉求的手脚。就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阿尔比的那只山羊是使得他的男主人公从程式化的日常庸碌之中得以咸鱼翻身的解放者。
必须看到,是西尔维娅让马丁获得了新生。“我把买的蔬菜放在车后,关上后车盖——(停顿)就在那时我看到了她……她用她那双眼睛看着我……我觉得我融化了。我觉得我当时的感受:我融化了。”人可以融化在大自然中,融化在母亲的怀抱里,也可以融化在恋人的眼睛里。在马丁的感觉深处,那融化是美的默契,真诚的投奔,热烈的许诺,忘我的交流。但是,他忘记了,他的恋人可是一只山羊。
古希腊的戏剧中,有替罪羊的说法。俄狄浦斯是替罪羊,杀父娶母,触犯了神的旨意,不知不觉是在替盲目的命运受过。西尔维娅的命运如何?
阿尔比的戏到此即将往高潮推进。马丁的妻子斯蒂薇会接受丈夫那口口声声的诗意浪漫吗?谙熟戏剧规律的人,或者扩而言之,懂得人类理智的人,都会在心里说,绝对没有那个可能。戏剧要走弧线,人性善恶交织才有意思,最有看头的场面总是两个人物的背反和逆反。正如我们预感到的,斯蒂薇不由分说地撕碎了丈夫马丁的浪漫和温情。在第二幕的结尾处,她断然高呼,“我让你跟我一起毁掉!”
在这部阿尔比戏剧集中,荒诞和毁灭仿佛构成了无法逆转的、永恒的人性二重奏。《欲望花园》中,清醒的旁观者杰克被枕头闷死,其实他是该剧唯一的罪证证人。《在家在动物园》,杰瑞猛扑在锐利的刀锋上自杀,看似小题大做,实际上是渴望交流而无法获得后的报复式冲动。在荒诞和罪孽中,人是活不好的,甚至活不下去。
实际上,如果把阿尔比的《山羊或谁是西尔维娅?》看成是作者与现代文明的一次冒犯性的对话,一次恶作剧式的挞伐,一次关乎人性和道德伦理的二律背反式的探讨,我们或许已经把到了这出戏的脉。精神一脉相承,文脉自古相沿,谁说阿尔比的人物身上没有投射古希腊悲剧形象的倒影。譬如说,斯蒂薇怎么看都延续着美狄亚的魂魄和行迹。美狄亚要惩罚变心的丈夫伊阿宋,走的是“曲线自卫”,拿两个孩子开刀。斯蒂薇扬言毁掉丈夫,则是拿老公的情人下手,也不是直接复仇。这里的情感逻辑在于,把你最爱的对象,毁掉,不是对你本人最大的惩处吗?嫉妒,往往是致命的。受到嫉妒伤害的一方,会祭出疯狂的理智做代价,寻求心理上的平衡。
阿尔比的第三幕,注定惊心动魄。暴风雨的高潮即将来临。生命激情爆发的制高点,没有宽恕,没有理解,没有悲悯,更没有原宥。女主人公终于走上了精神复仇的不归路。先是儿子比利上场,发现满地狼藉,母亲不见了。接着父子间展开了一番心灵上的交谈。从青春期的困惑,到“生活有悲有喜”的不堪和无奈,从下坠的沉沦到没顶之灾前的恐慌,从救赎到幻灭……父亲的烦恼是“我不知道我们的处境有什么规则”,儿子的洞察是“一切都没啥意思,都在你的意料之中”。也许是文明的程序设计本身出了差错,让比利是同性恋,甚至跟他父亲接了吻,让他的父亲爱上了山羊。如果我们承认,比利是正常的,那么马丁的人兽之交也是正常的。文明当然需要禁忌。但禁忌是对不由自主的情感的蔑视和取消吗?
而告密者罗斯的再次登场,带来了一次小高潮。设想,如果不是他写检举信,马丁还会过着和睦而其乐融融的生活。家庭风暴也不至于瞬息蔓延。马丁直呼罗斯为叛徒犹大。这个角色当然是这个戏里最令人讨厌的了。在此剧中,罗斯是线索人物。没有他的所作所为,也就没有作为动力型人物马丁和阻力型人物斯蒂薇的对抗与扭结。罗斯显然是以公众道德和社会法庭的代言人和审判者身份出现的。他不关心一个人灵魂的孤独、痛苦和绝望的程度,而是在乎理性的文明规则与程序对人的看管、监视和制约。他对马丁慷慨陈词的威吓听起来绝非耸人听闻,“你知道他们怎么判这种刑吗?你知道他们会怎么对付你?新闻媒体?所有的人?随后一切全完蛋——你的事业,你的生命……”
阿尔比是谙熟戏剧之魂的老戏骨了,他对马丁性格的处理非常有分寸、有张力、有层次。跟儿子,跟妻子,跟出卖者罗斯,马丁的口吻截然不同。对儿子的口气是软中带硬,一方面给自己留点面子和尊严,另外父亲的慈爱也不能丢下。和妻子,是商量,妥协,让步,但还有几分顽固的坚持。那最后的心灵空隙任谁都不能剥夺。而在第三幕他与罗斯的据理力争,大声呵斥,像是终于等到了前面两场心理焦虑无法投射和释放的一个出口,“我的灵魂当然是我的事情,但你根本就没有灵魂。”在整个剧的展开过程中,马丁的情感诉求,就是想找到一个理解他的人,懂得他和西尔维娅的关系是可以的人。“就没人理解这事吗!?”他顿足捶胸也依然无济于事。更可怕的场面在马丁的绝望之后如风暴一样席卷,“斯蒂薇拖着一只死羊上。羊的喉颈被割开;斯蒂薇的衣裙,手臂上流满鲜血”。阿尔比的场景提示,写得一目了然,令我们感叹无语。用羊来替罪,完成人的救赎,高级的荒诞,幽默,讽刺。让无罪的人(生灵)无辜地死去,用这种最不可接受的戏剧境遇,来强化人性本身的脆弱和盲目,构成了阿尔比三个作品共同的结局,并且暗示了其精神主题,即人类的异化和隔绝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用其极的致命性和有效性。
叫醒戏剧之魂,就是唤醒人对自己在文明境况中的尴尬际遇的觉知、反省和体悟。不必讳言,阿尔比对美国精神中强调的幸福成功之梦,早就看到了那骨子里的危机、羸弱和贫血。幸福成功,如果无节制无限度地追求,说到底不过是物质满足和物欲横流的代名词。几乎不关涉人的心灵的痛痒和精神状态的欠佳。《欲望花园》里几乎出场的所有人物,都心怀鬼胎,或者道貌岸然,只有那个图丝太太,光明正大地干着老鸨子的勾当,因为她有恃无恐,依仗着“我们做有利于我们的事,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而清醒的见证者杰克面对由图丝太太操控的那些为了金钱什么都可以干的拜金主义狂热信徒,就只得落得个被枕头闷死的必然结局。阿尔比的戏几乎不会为主流社会的正统道德和秩序做任何辩护和掩饰,心腐烂了,拥有再多冠冕堂皇的点缀,精神世界也是苍白的,贫瘠的,无助的。他想让失魂落魄的人走出欲望花园。而你要知道,那个欲望花园的诱惑该有多大!
在阿尔比的戏剧作品中,不正常的死,大概构成了对盲目麻木的生之挞伐、暗讽与揭露。其实,古往今来,经典的戏剧总是要站到文明体制的对立面展开独立思想的宣告和独立艺术的呈现。承接这一传统,《在家在动物园》展示了人被物质异化后人际关系也同样异化的不争事实。肤浅的温情脉脉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几乎俘虏了整个世界,但是阿尔比,偏偏要用自己的嘴、自己的笔当然还有自己的冷嘲热讽,对浮华拜金庸俗势力冷漠残忍的西方社会文明给予最有力的剖析、挖掘和对抗。彼得在家,似乎没有什么问题的夫妻关系,实际上早就暗流涌动千疮百孔,他们的爱情名存实亡。走出家门,到了中央公园,却意外遇到了杰瑞。他们坐在一条长凳上,却是分属不同世界的两个人,是彼此的过客,幽灵,直到互相隔膜,鄙视,唾弃。直到闹出了人命案。阿尔比是残酷的天才,较真的恶作剧者,人类精神的幽默分析师。戏剧不写死,不足以惊魂。写死,如果触及不到爱欲的本质,文明的症结,人的绝望中的渴望救赎,那么即便写了,也是同样地无济于事,属于黔驴技穷的招数而已。
或许在阿尔比的内心,平庸构成维持世界的力量,极端则是创造世界的力量。按照戏剧艺术的情境激化、人物性格发展乃至对高潮的预期抵达,极端肯定比平庸化设计,具有更彻底的张力和弹性。而死亡是打破正常和平静的生活惯性的最佳方式与手段。当然对于死者,阿尔比区分了死的状态和意义。杰瑞故意撞在彼得的刀口上,是自己寻找解脱。他活累了活够了。最后他是微笑赴死。而杰克的死于非命,原因在于他有可能揭露图丝太太的底牌,会影响到那个“欲望花园”的茂盛滋长和正规运转,阿尔比想说的是在生活中没有绝对的旁观者。人会不知不觉地掉进各式各样的网里,欲罢不能,难以安生。当然在这三部作品中,西尔维娅的死是最悲凉的,首先在于它不是人类,无法理解人类的嫉妒仇恨的程度该有多么恐怖与致命。其次,这个死本身是被动的,不可变更的,它代替马丁赎罪,成为人类爱情危机的祭品。再次,西尔维娅为了惩罚马丁而用另一个无辜生灵的命作为抵押和支付,这种毁灭的代价等于同时毁掉了三个生命的存在感。这就构成了罪孽本身的多重循环。人啊人,你理应为血腥的不义承担罪责!
”超凡的社会批判者”,这是阿尔比的自况。“人们在百老汇看到的那些东西,根本就不是戏剧,只是一些批量生产的产品,它们只会使人沉睡或沉醉,无法叫人惊醒和清醒。”而他的致力于让人惊醒和清醒的戏剧,是捅向文明痼疾和伤口的一把刀子。晚年的阿尔比,依旧锐不可当,锋利无比,这想来是令许许多多中国戏剧人为之赞佩、感叹和青睐的地方。斗胆而言,我们的戏剧越来越套路化、大众化、程式化、体制化了,几乎听不到面向旷野和星空的发自灵魂深处的战栗般的呼喊。用阿尔比的台词来说,“我们安全吗?我们太……文明了?”而真正的戏剧是飞升的,野性的,是心灵的风暴,精神的浪涛,以及思想的号角。希望我们本土的戏剧家也能拥有阿尔比式的大胆、炽烈、执著和自信,唤醒属于自己的戏剧的魂魄。
注释:
[1](美)爱德华·阿尔比著.山羊:阿尔比戏剧集[C].胡开奇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