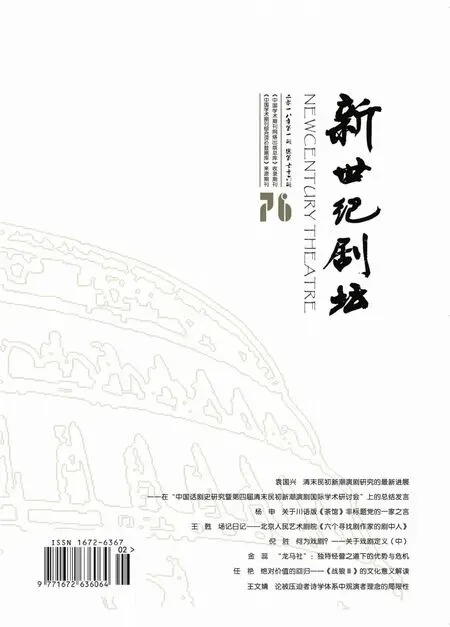何为戏剧?
——关于戏剧定义(中)
戏剧作为综合艺术
前已述及,20世纪以前,西方戏剧学界一般比较偏向于从文学角度来讨论戏剧,表演被认为只是将文字具体化、形象化的工具,人们比较忽视表演自身的独立价值。到20世纪初,出现了戏剧表演的自我觉醒,产生出一些重要的表演理论,比如著名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验说。不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主张在不脱离剧本、不违背戏剧的文学性的情况下发展出表演理论体系,因此他只是强调或补充了戏剧传统理论里比较被忽视的表演性的一面,却并未试图去打破戏剧传统理论。
关于戏剧,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比如戏剧属于综合艺术等。关于戏剧的综合性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已经描绘得很清楚了——
戏剧的力量在于,它是集体的艺术家,它把诗人、演员、导演、音乐家、舞蹈家、群众演员、制景师、电工技师、服装师以及其他舞台工作人员的创造性劳动结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而且,戏剧艺术是综合的艺术,它的力量也就在这里。戏剧同时利用一切艺术的创造,没有一种艺术除外,它把文学、舞台、绘画、建筑、雕塑、音乐、舞蹈的创造全都集中在自己的屋顶之下。
这是一支强大的、团结一致的、装备精良的军队,它要以同时发起友好的总攻击来影响剧场里的全体观众,使成千人的心脏立刻一起跳动。[1]
戏剧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由多种艺术形式集聚并存而成,这些形式相互扶助相互协作,完美的配合才能造就一场完美的演出。需要指出的是,各种成分在戏剧里的权重并非等同。不同的戏剧作品对戏剧诸元素会有各自的偏重,比如我们常听人说有些戏是导演戏,有些戏则依赖演员,而在百老汇的音乐剧里演员却不是那么重要,可以经常更换,即兴剧、幕表戏则没有详细剧本等等。
最理想的是,舞台呈现拥有最终决定权。由此,编剧、导演等等的地位都应该服从整个舞台艺术的创造。然而舞台呈现却又是由具体的人来决定,这个人可以是导演,也可以是编剧,更可以是制作人,因此,实际上戏剧里的各种成分一开始往往各自为政,从排练开始冲突不断,经过不断的磨合才有可能达成最优效果。
“无论怎样精细,没有一个文本,也没有一个演出计划,能明确决定在演出中与表现或者效果相关的每一个特征。总是会有一些问题未能为文本或演出计划所解答,诸如角色的长相,她如何说话,演出空间如何造型,是什么激发了一句台词的念白,又是怎样的姿势配合这句台词,等等之类的问题。不同的演出对这些问题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为了制作一台演出,执行者们必须超越剧本或演出计划中给定的内容。”[2]
不少剧作家同时也是小说家,小说写作可以事无巨细,在电视电影发明之前,小说描写如雨果、果戈里甚至繁琐到令人厌烦的程度,可以说小说为读者提供了全方位的信息。然而剧本写作却不然,它是一种让渡,将小说里用文字描述的一些信息让渡给演员、导演和舞台美术设计,让他们来补充创造(比如人物的高矮胖瘦),剧本则仅剩下对话。当然,剧作家也要写舞台指示,然而与小说相比,这些指示太过简略,更何况剧本里基本无法描写出人物的内在心理。到后现代戏剧,大多数剧本都取消了舞台指示。
因此,创造一台戏剧,是各种艺术形式综合运用的结果。演员对剧本的关系,绝对不是一切遵从,他当然也应该向剧作家请教,如果剧作家还在世。但演员也有他自己的创造性,他必得从自身出发来揣摩剧本,比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要求演员写剧中人小传,就是希望演员用自己的全部生活经历来丰富人物,显然,不同的演员由于自身生活经验的差异,写出来的小传也千差万别,这就是不同演员扮演同一个人物会各有特色的原因。
导演排戏,目标之一在于激发和监督演员对剧中人的认同,其二则是将自己的艺术理解交付给全体演员,让他们在大致统一的理解上各自发挥且相互配合,从而达成一出艺术趣味统一的作品。
当然,演员和导演之间也是相互让渡的关系。
狄德罗说:“舞台好比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每个人都要为了整体和全剧的利益牺牲自己的某些权利。”[3]
尽管不少人都理解戏剧的综合性质,但在每次具体排戏过程中却不得不经历各种磨合,甚至争吵,才能真正完成,这一过程甚至是排戏的必经阶段,很少能避省。
最终,戏剧艺术的呈现必须有所偏重,主导,比如偏向于以导演为主或以演员为主或以编剧为主或舞美设计为主,比如百老汇音乐剧就追求舞台美术和编剧,而多少忽视演员和导演的作用,因此能保证同一个剧演上100年,更换过多个导演和演员,仍能保持原汁原味。
布莱希特却强调戏剧各元素的独立性。认为它们相互之间是冲突的,并且主张保留这种冲突,而不是要求相互牺牲和成全。
叙事戏剧以及互动
第一个打破亚里士多德戏剧观念的应该是皮斯卡托和布莱希特。
皮斯卡托指出,戏剧(Theater)有两种形式:叙事性的(或史诗式的)和戏剧文学性的(epische und dramatische Form)。[4]
叙事性的(epische)或译叙述性的,原文是希腊语,即史诗的。史诗的演唱采用叙事方式,类似我国的说唱艺术,而与代言体的戏剧有相当差异。由于作为文学体裁的史诗具有不少特点,而皮斯卡托和布莱希特重点强调的只是史诗那种叙述特点,以与戏剧文学相区分,因此不少中国学者都采取叙事性这个译法。史诗的多义性,使得史诗剧这个译法让人困惑。然而,史诗这个译法的确是布莱希特和皮斯卡托的原意,因为史诗的表演并非只是叙述性的,偶尔也会有扮演,因此,episch并非只是叙事,本文遵从大部分中国学者的做法,保留叙事译法,是想强调史诗剧的叙事特点,但希望读者能理解这个词的复杂内涵。
皮斯卡托提出所谓的叙事戏剧,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戏剧文学(drama)传统。亚里士多德说史诗、悲剧、喜剧和音乐诗都是诗歌,因此史诗仍是在诗歌的大概念下,也就是说,从字面上看皮斯卡托的叙事剧并未完全脱离诗歌,而只是从悲剧、喜剧挪到了史诗上面。
然而,戏剧文学(drama)是代言体格式,而叙事剧则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这个差别导致戏剧表演上也必须做出改变。因此,叙事剧的出现,不单对戏剧文学有冲击,在表演上也有创新,实际上对戏剧(Theatre)原有的内涵和外延都进行了扩大和改变。
布莱希特在《戏剧小工具篇》里说:“‘戏剧’(Theater)就是,为了消遣娱乐,对人们之间流传的或假想的故事做活生生的反映。这就是我们随后要讨论的戏剧的意思,无论它是新的或老的。”[5]我们说,艺术有两个功用,娱神和娱人。王国维曾引用过郑氏《诗谱》:“是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6]布莱希特在《戏剧小工具篇》里不断否定戏剧的娱神功能,而强调戏剧的娱人功能,这是对传统戏剧功能的缩小。
布莱希特明显受到中国戏剧的影响。他否定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移情式的戏剧演出方式,反对共鸣,主张冷静反思,这一点与皮斯卡托的实践是一致的。
从政治戏剧的目标出发,皮斯卡托试图在戏剧里清除第四堵墙。皮斯卡托说:“如果我们想要那种不为娱乐来看戏的理智观众,我们就必须拆除第四堵墙。”[7]这里皮斯卡托明确表示,戏剧不是娱乐,可见他的戏剧观与布莱希特还是存在一定差别的。
由此他发展出一些新的戏剧手段和技术。“皮斯卡托成功地打开了第四堵墙,成功地将合法的政治内容植入戏剧,成功地使用有效的技术手段将舞台变成充满活力的有机体而不是一张‘图片’。”[8]在他的戏剧里,“将观众与舞台分开的墙被扫除;整个建筑变成了议事厅。观众被拉上了舞台”。[9]
皮斯卡托在1942年发表的《戏剧的未来》中说:“戏剧的目标是将观众卷进行动里来,戏剧的历史简单地说就是在观众参与度方面……取得或多或寡的胜利。”[10]著名的包豪斯艺术家,曾设计皮斯卡托整体剧院的格罗皮乌斯说:“我们试图,通过技术手段(投影,脚手架,可移动的构件,等等)逼迫观众与场景行动紧密接触,使得他们参与游戏,不允许他们躲藏在幕布后面。”[11]
皮斯卡托将这种表演方法叫做客观表演。详情请参见拙著《早期德国文献戏剧的阐释与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
前面提到,戏剧具有两重性。皮斯卡托的做法,强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人较少关注的表演和观众的关系,尤其注意了观众的感受。
戏剧是什么?戏剧最要紧的任务,是去讲好一个虚构的故事?还是令观众得到享受和思考?这是布莱希特和皮斯卡托留给我们的问题。
身体戏剧:阿尔托、格洛托夫斯基等
身体戏剧(Physical Theatre)是后现代戏剧的一个潮流形式,国内也有翻译成形体戏剧或肢体戏剧的。考虑这种戏剧形式主要是东方戏剧训练方式,尤其是融合了瑜伽等宗教身体训练方式,它与西方体育的纯肢体动作不同,具有身心合一的、内在的修炼,因此我们将它译为身体戏剧。
当然,身体戏剧,准确地讲应该译成身心戏剧或身心合一戏剧。然而东方思想史上的心与西方所谓的mind也有差别,它不是指亚里士多德《工具篇》所陈述的,理性推理的思考方式。
我们当然可以捕风捉影地追溯身体戏剧的起源一直到古希腊,然后谈起哑剧、即兴喜剧和舞蹈传统等等。然而,如果考虑到身体戏剧里有着东方神秘主义修炼方法的因素,我们不得不说,身体戏剧的主要发起人应当是法国戏剧家阿尔托,他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皮斯卡托的同代人,他明确提出了身体戏剧这个名称。“从梅耶荷德和阿尔托,中经朱利安·贝克和朱迪斯·马连娜的‘生活剧团’以及彼得·布鲁克等人在60年代的残酷戏剧实验,直到DV8、劳埃德·纽森(Lloyd Newson)、维姆·范·德凯布斯(Wim Van derKeybus)、弗兰士·B(Franco B)和布里什·高夫(Brith Goff),戏剧期望从内脏和感官上进行沟通,这种沟通是建立在演员活的身体之上的。”[12]
法国戏剧大师阿尔托全名Antonin Artaud (1896-1948),他是“诗人、剧作家、杂文家、小说家、演员、制作人、戏剧理论家以及画家。他也被视为精神病患者、瘾君子和囚犯,他去世后,下一代人则将他视为文化偶像或承受痛苦的、失败以及有着伟大的文学智慧而变成疯子的例证。”[13]其戏剧主张是残酷戏剧(The Theater of Cruelty)。他对后世戏剧家影响颇深,其主要的追随者有格洛托夫斯基、巴尔巴等人。
残酷戏剧,“从一个层面看,其目的是否定,通过摧毁过去无可置疑的那些道德假定而令社会陷入沮丧。然而它也有积极的方面,通过用暴行击垮惯常的反应,它打开了观众的心灵——这就是阿尔托在《曾契》(The Cenci)一剧中所运用的策略。”[14]
阿尔托否定戏剧文学(drama)在戏剧里的崇高地位,他说:“将戏剧固化在某一种语言上——写定的文字、音乐、灯光、噪声——就意味着它即将毁灭,选定任何语言都背叛了对那种语言的特殊效果的趣味;并且语言的干枯就与其局限相伴。”[15]阿尔托所说的语言(language),是指包括音乐、身体动作等在内的人类表达自己的方式,而并非仅限于说话写字的语言。
阿尔托希望打破旧的戏剧传统,“冲破语言接触生活就是创造或再造戏剧;本质的东西不是去相信这个行动必然会保留神圣,也就是说,令其独特——本质的东西就是去相信不只是任何人能创造它,而且必然会有所准备。”[16]
这种冲破是与瘟疫类似的,“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戏剧,就像瘟疫,是一种精神错乱,是癔语。”[17]
“如果戏剧就像瘟疫,那不仅因为它严重影响了群众而且因为它用同一种方式令他们精神混乱。在戏剧里就像在瘟疫里,有某些东西既是胜利的又是复仇性的:我们知道无法预知的、瘟疫扫过的地方所形成的灾难就是巨大的杀戮。”[18]
“和瘟疫一样,戏剧是对各种力量的可怕的召唤,这些力量通过事例驱赶心灵进入冲突的园地。”[19]
“如果本质的戏剧(essential theater)如同瘟疫,那不是因为它是传染性的,而是因为像瘟疫一样,通过那些能将所有心灵(不管是个人的还是人类的)的怪异的可能性进行定位的手段,它揭露、产生、外化那些深藏的潜在残酷性。”[20]
“戏剧的行动,就像瘟疫,是有益的,因为它驱使人们去看他们自己是如何,它令面具脱落,显露出我们这个世界的谎言、懈怠、卑鄙和伪善。”[21]
从这样一种戏剧观出发,阿尔托当然要批评文学对舞台的独占。
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这种情况是如何出现的?在戏剧里,至少在我们所熟悉的欧洲戏剧里,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西方,全部戏剧的东西明确地,即,不能由话语由字词,或者如果你愿意这样表述,不能由对话所涵盖(并且对话自身被视为一种起着令舞台上的“声音”成为可能的作用,被视为对这种配音的急迫需求的作用)的东西,被当作是背景。
更进一步说,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西方戏剧(我说西方戏剧因为有幸存在着其他的戏剧,比如东方戏剧,它们保留了完整的戏剧理念,而在西方这种类似的理念都遭到了滥用),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除了戏剧的对话,西方戏剧没法看到戏剧的任何其他方面。
对话——一种写定的和能说出来的而并不必然从属于舞台的东西,它属于书本,这一点由这个事实所证明,在所有关于文学史的手册里都会为以戏剧作为说话的语言史的一个下属分支而保留一个位置。
我说,舞台是一个具体的物理场所,它召唤人们去充实它,去给予它自己的具体语言来讲述点什么。
我说,这个具体的语言,为着诸感官和说话的独立性,第一次满足诸感官,令其有着感官的诗意和语言的诗意。我所说的这种具体的物理语言是指真正的戏剧的,它所表达的思想要超越说话的语言能达到的程度。[22]
需要说明的是,物理的,也译作身体的。对西方人来说,人的身体和大自然一样都是物质的,都可以用physics来表示,在这个词里这两个意思是合一的,是一个东西。
再多说几句,为什么在东方戏剧的某个作品里身体能影响心灵,为什么这种作品里行动的直接意象具有力量,就像在巴厘戏剧里,其原因就在于这种戏剧以完整保留了古老传统使用身姿、音调以及与诸感官和所有可能的东西的和谐的秘密为基础——这并不是指责东方戏剧,而是指责我们,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伴随着我们的事物的状况应该被摧毁,要在所有方面所有阻碍自由思想的操练的地方迅速并且带着恶意地摧毁它。[23]
由此,阿尔托从东方戏剧里悟出身体戏剧的路向。
巴厘戏剧给我们揭示出一种身体的和非说话式的戏剧理念,这种戏剧被舞台上能出现的东西所限定,除了写定的文本之外,然而我们在西方所构想的戏剧则宣布自己与文本结盟并被文本所局限。对西方戏剧来说字词是一切,缺少字词就无法表达;戏剧是文学的分支,一类能发出洪亮声响的语言,即便我们承认在舞台上说出来的文本和用眼睛阅读的文本之间存在着不同,如果我们严格限制戏剧为在角色之间发生的东西,我们就无法将其与表演文本的理念相分离。[24]
阿尔托的继承者,格洛托夫斯基也同样受到了东方戏剧的影响。格洛托夫斯基力求抛弃戏剧的综合因素,令戏剧简化也纯粹起来,他称之为质朴戏剧(Poor Theatre),也有人翻译为贫穷戏剧、穷干戏剧。
戏剧这个字的涵义是什么?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有许多可能的回答。学术点讲,戏剧(the Theatre)就是这样一个处所(place),演员在其中背诵写成的文本(text),用一系列的动作来图解文本,使其更容易为人所理解。[25]
格洛托夫斯基对戏剧定义的探索尤其见于下面的谈话:
没有服装和舞台设计戏剧能存在吗?是的,它能。
没有音乐与情节相伴,戏剧能存在吗?能。
没有灯光效果戏剧能存在吗?当然。
没有文本呢?能;戏剧的历史确证了这个。戏剧艺术的进化中文本是最后一个加入的元素。如果我们将一些人放到一个有剧本情节的舞台上,把他们集中在一起令他们像在艺术喜剧里那样即兴扮演他们的角色,演出将同样的好甚至台词不被朗诵出来而只是喃喃自语。
但没有演员,戏剧能存在吗?我找不出任何例证。有人可能会提到木偶戏。即便是那儿,也能看到一个演员躲在布景背后,尽管他是另一种类型的演员。
没有观众,戏剧能存在吗?至少有一个观众才能成就一个演出。于是我们留下了演员和观众。因此我们可以定义戏剧为‘发生在观众和演员之间的事’。所以其他事物都是附加的——也许有必要,但是是附加的。[26]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格洛托夫斯基认为最重要的戏剧训练是演员的身体训练。于是他在东西方戏剧艺术中寻找被淹没的,各种身体训练的方式。
目前在世的著名戏剧家巴尔巴和铃木忠志,也是身体戏剧的代表人物。巴尔巴主要接受的是格洛托夫斯基的影响。而铃木忠志从日本能剧的表演训练中发展出一套所谓铃木训练法。这些训练非常大的程度上受到了东方传统戏剧艺术训练方式的影响。
铃木忠志说:“如果我们把戏剧视为演员和文本之间的关系,那么戏剧的定义特征就会由说着台词的演员的身体里所体验到的自发的感受显露出来,这个身体接着就孵化出一种想象力的、丰富的语言遗产的再生,其中含蕴着全体人类的身体上的集体无意识。”[27]
“另有一些理论将演员视为向观众解释或传递事先写好的文本内容或亲密地分享口头叙述的中介。这时,演员的存在只是为了传递表达在叙述里的作者或社会的理念或哲学,这种信息转达的精确程度成为判断一个表演(a performance)的适当性的一个标准。我批评这种定义,我不否认有些人的确接受的就是这种训练,但我不相信这就是演员工作的本质。”[28]
身体戏剧的问题在于,受到东方神秘主义修炼方式的影响,它最终也会走向神秘主义,戏剧表演逐渐被看作是身体训练的副产品。住在隐秘的处所,不与俗世交道,成为修炼的最高境界。信徒们的终极目标不再是舞台表现,戏剧被他们抛弃。而到那时,他们的训练也已经不是戏剧了。
阿尔托在他那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其身影被各种大师的光环掩盖,其主张影响不大。身体戏剧这个名称在1970年代第一次引起公众注意,在80年代风靡一时。代表性的剧团有,英国的DV8身体剧团、哑剧行动同仁团(Mime Action Group,MAG),法国的同心剧团(Théâtre de Complicité)等。尽管身体戏剧终于繁荣起来,然而立即就出现了泛化(overuse),实际上多少已经背离了阿尔托等人的原意。[29]
不过,阿尔托等人的影响并不限于身体戏剧。“当代导演们几乎没有不受过阿尔托影响的,然而仅有一次有人尝试将阿尔托的理论在实践里试用。那些有自己风格的信徒,如谢克纳或贝克和马连娜,他们都采取借用的方式以形成自己的混合形式,彼得·布鲁克和查尔斯·马洛维茨(Charles Marowitz)则不同,他们将阿尔托的文字当作他们在1964年作品的基础。他们的‘残酷戏剧’实验被设计成对演员的训练,并在一系列的表演中达到高潮,其中包括阿尔托的超现实主义短剧《血的喷涌》(The Spurt of Blood)。这些成果被吸收进了热奈的《银屏》(The Screens)以及布鲁克对魏斯《马拉/萨德》令人震惊的阐释之中。有趣的是,布鲁克得出的这个结果并不明确:‘你们应该将阿尔托看作纯粹的生活道路,换句话说阿尔托的生活里有一些东西与戏剧的风格相关。’这个‘有一些’是指存在着‘某种有限的、特殊的——几乎是技术上的——东西,使用瑜伽和呼吸练习,用想象处于身体不同部分的一定位置的特殊情感来进行情绪表达’(换句话说那些东西是包括在阿尔托的论文里的、与形而上学或西方文化状态几乎完全无关的东西)。”[30]
(未完待续)
注释:
[1]郑雪来选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论导演与表演[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91
[2]Carroll.Philosophy and Drama[A].(David Krasner and David Z. Saltz ed. Staging Philosophy[C]).U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6:107-108
[3](法)狄德罗.狄德罗美学论文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93
[4]Zeittheater(ed).Das politische Theater und weitere Schriften von 1915 bis 1966[M].Berlin:Row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1986: s.267
[5]Bertolt Brecht.Bertolt Brecht Ausgewählte Werke In sechs Bänden[A](Sechter Band[C]).Berlin:Suhrkamp Verlag,1997: s.521
[6]王国维撰,马美信疏证.宋元戏曲史疏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
[7]Judith Malina. The Piscator Notebook[M].New York:Routledge,2012:151
[8]Judith Malina. The Piscator Notebook[M].US:Routledge,2012:159
[9]Judith Malina. The Piscator Notebook[M].US:Routledge,2012:6
[10]Judith Malina. The Piscator Notebook[M].US:Routledge,2012:126
[11]Judith Malina. The Piscator Notebook[M].US:Routledge,2012:126
[12]Simon Murray and John Keefe ed.Physical Theatres:An Introduction[M]. New York:Routledge Inc. 2007: 25
[13]Adrian Morfee.Antonin Artaud's Writing Bodies[M]. 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1
[14]Christopher Innes.Avant Garde Theatre[M]. New York: Routledge Inc.1993:51
[15]Antonin Artaud.The Theatre and Its Double[M].Translated by Mary Caroline Richards.New York:Grove Press.Inc. 1958:12
[16]Antonin Artaud.The Theatre and Its Double[M].Translated by Mary Caroline Richards.New York:Grove Press Inc.1958:13
[17]Antonin Artaud.The Theatre and Its Double[M].Translated by Mary Caroline Richards.New York:Grove Press Inc. 1958:27
[18]Antonin Artaud.The Theatre and Its Double[M].Translated by Mary Caroline Richards.New York:Grove Press Inc.1958:27
[19]Antonin Artaud.The Theatre and Its Double[M].Translated by Mary Caroline Richards.New York:Grove Press Inc.1958:30
[20]Antonin Artaud.The Theatre and Its Double[M].Translated by Mary Caroline Richards.New York:Grove Press Inc.1958:30
[21]Antonin Artaud.The Theatre and Its Double[M].Translated by Mary Caroline Richards.New York:Grove Press Inc.1958:31
[22]Antonin Artaud.The Theatre and Its Double[M].Translated by Mary Caroline Richards.New York:Grove Press Inc.1958:37
[23]Antonin Artaud.The Theatre and Its Double[M].Translated by Mary Caroline Richards.New York:Grove Press Inc.1958:47
[24]Antonin Artaud.The Theatre and Its Double[M].Translated by Mary Caroline Richards.New York:Grove Press Inc.1958:68
[25]Jerzy Grotowski.Towards a Poor Theater,A Clarion Book[M]. US:Simon and Schuster,1968:28
[26]Jerzy Grotowski.Towards a Poor Theater,A Clarion Book[M]. US:Simon and Schuster,1968:32-33
[27]Kameron H. Steele Trans.Culture is The Body: The Theatre Writings of Tadashi Suzuki . New York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Inc. 2015:4
[28]Kameron H. Steele Trans.Culture is The Body: The Theatre Writings of Tadashi Suzuki . New York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Inc. 2015:4-5
[29]Simon Murray and John Keefe ed.Physical Theatres:An Introduction[M]. New York:Routledge Inc. 2007:14-17
[30]Christopher Innes.Avant Garde Theatre[M]. New York: Routledge Inc.1993:6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