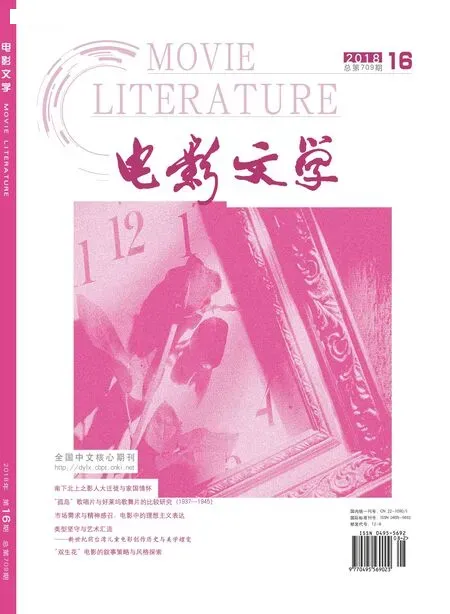“孤岛”歌唱片与好莱坞歌舞片的比较研究(1937—1945)
许海燕
(中央戏剧学院,北京 100710)
1927年10月6日,华纳兄弟影片公司推出世界电影史第一部有声片《爵士歌王》(当时中国译名《爵士歌者》The
Jazz
Singer
)。时隔一年半《爵士歌者》登陆中国,《申报》1929年4月的增刊中曾报道其在垄断西方电影首轮放映的夏令配克影戏院首轮播出,“今日起日夜三次开映”,时间分别为“第一次下午二时半、第二次下午五时半、第三次晚间九时一刻”。当时在上海可以放映有声片的电影院相对较少,大部分还停留在默片放映或现场配音的阶段。默片配音片在当时的上海十分盛行,比较成功的有在中央大戏院上映的1926年12月22日“明星”公司根据托尔斯泰的《复活》改编的影片《良心复活》,导演卜万苍就采取了现场演唱“带戏登台”的方式。“特制了一套与影片中唱‘乳娘曲’时完全相同的布景,搭在银幕后面。在乐师、京剧青衣冯子和的配合下,当放映到杨耐梅坐在客厅唱‘乳娘曲’时,银幕升起,舞台灯光大亮,杨耐梅带妆入戏,唱出了‘秋雨滴梧桐,秋花漫地红……’的苏州风味曲调。”新颖的配音方式引来了中央大戏院长达20天爆满的放映状态。而从《爵士歌者》开始,大光明大戏院、夏令配克影戏院、卡尔登大戏院、平安影院等规模较大、实力雄厚的影院开逐渐重视有声片的放映设备。平安影院在11月间登过一个广告说“完全之有声电影,今年以内,不但本埠各院,无其设备……”,岂知平安居然宣布,从本年除夕这一天起,专演有声电影。平安属于华北公司,资本雄厚,而且十分努力,所以赶早一天把有声电影奉献给大家。其筹备了不止一两天,机器早已安装好。11月27日记者承约往观(往听),觉得十二分有趣,且老友陈霁堂君在旁说明,更觉获益匪浅。原来现今有声电影分两种,那天平安却两种都演过了。第一种是“莫非通”(Movietone),就是将声音摄入片中,成一种光带,映时利用光学方法,借无线电机及播音机,将所摄的声音还原出来。第二种是“伟大风”(Vitaphone),是用话匣方法,听说那唱片总有女人的脚盆那般大小;话匣上是有两个转盘,这个完了,那个上来,不致间断。影片与话匣的媒介,自然也自电力,不过要是片子断了,那可就要产生麻烦,所以人家比较还是喜欢玩“莫非通”,但片子旧了,莫非通也会有不通的时候。声音比较起来,还是“伟大风”响亮得多。所以可说各有其好处与坏处了。此次平安试演的两种片,声音都十分清脆,观者简直等于置身于舞台中,丝毫不生不快之感。一切应有之声音尽有之,无用的声音,都未曾摄入片内,实在是最近进步的制品,不比以前其他各片之瞎凑。第一片歌舞升平,描写纽约舞场中之一故事,取舞剧为其主体,精彩部分都加着五色,声色俱备,洵为大观。至于剧中歌乐之优美,化装之浪漫,则其余事耳。该片并无字幕,第二片(伟大风式)则有之,闻平安之后全演有声影片,至同一公司之光明等院,则将视上海华人对于西语有声影片之情感如何,然后始定装机映演否。本埠他院闻亦有继起者。
无论是“伟大风”还是“莫非通”,有声片技术的推广使得从1929年开始引进的好莱坞歌舞片风靡上海。《沙漠情歌》(The
Desert
Song
)、《璇宫艳史》(The
Love
Parade
)、《百老汇之歌舞》(The
Broadway
Melody
)、《鸾凤和鸣》(Naughty
Marietta
)、《凤凰于飞》(Rose
-Marie
)、《华清春暖》(Footlight
Parade
)等均创造了票房奇观。中国第一部蜡盘发音的有声片《歌女红牡丹》(胡蝶主演)来自“明星”公司1931年3月张石川的创作;同年10月“天一”公司斥巨资租借美国录音设备、聘用美国有声片制作人员,创作出第一部片上发音的有声片《歌场春色》(宣景琳主演);“联华”公司则由于资金问题仅依靠“明月社”演员拍摄了两部有声短片。
图1 上海平安大戏院(后更名为平安电影院)及其上映好莱坞歌舞片的宣传册

图2 1938年上海中央大戏院照片
中国歌唱片的初次尝试便体现出与好莱坞歌舞片的巨大差异。1939年2月春节期间,当时“孤岛”最著名的三家影院分别上映歌唱片:沪光影院推出新华公司的《木兰从军》,新光影院推出艺华公司的《楚霸王》,金城大戏院推出国华的《孟姜女》。从花木兰、虞姬到孟姜女,歌唱片的取材呈现出与中国传统戏曲所偏爱的历史、传奇题材相类似的特征。而1939年好莱坞上演的《百老汇小夜曲》(Broadway
Serenade
)、《让自由歌唱》(Let
Freedom
Ring
)、《华盛顿广场的玫瑰》(Rose
of
Washington
Square
)等歌舞片,大都与百老汇音乐剧相关联或直接改编自音乐剧。题材上的互文本性,使得中国传统戏曲的“悲苦”内核暗含于“孤岛”歌唱片之中;而百老汇音乐剧的“狂欢”机制同样烙印于好莱坞歌舞片内部。深层次的互文本性呈现出“孤岛”歌唱片与好莱坞的歌舞片的本质差异,一方面,中国传统戏曲母题与战时环境背景相结合,孕育出“才子佳人”共同反抗压迫的叙事轴心;另一方面,好莱坞在20世纪30年代进入黄金时期,观众的注意力由百老汇的话剧舞台转向银幕。百老汇的歌舞盛宴随即转移至画框之中,形成“万花筒式”的歌舞奇观。强大的视觉冲击与观影快感机制的建立,使得30年代中国歌唱片呈现出外喜内悲的核心观念。由于1937年七七事变后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电影格局,因而在武汉、重庆等大后方,歌唱片失去了生长的条件。但在“孤岛”好莱坞歌舞片仍然大行其道,中国歌唱片也形成了其成长的土壤。本文将从母题与母题链入手,通过观众的认同机制与主题狂欢,进而得出“悲情”“孤岛”与“纵情”好莱坞的结论。
一、母题与母题链的重构
维谢洛夫斯基认为母题是“最简单的叙事单位,它形象地回答了原始思维或日常生活观察所提出的各种不同问题。在人类发展的初级阶段,在人们生活习俗和心理条件相似或相同的情况下,这些母题能够自主地产生,并表现出相似的特点”。作为一种“类型化的结构”,母题呈现出反复性与不可分性的特点。作为非情节化的、有别于主题色彩的程序单元,母题是根植于作品中的最小分子,它的生成与当时的流行文化、心理状态、精神内涵有着深层次的共振关系。而它的重构则成为包括电影、文学、音乐、戏剧等艺术形式的流变所无法逃避的核心内涵。母题往往是以“群落”的方式聚集,并最终形成母题链。如图3所示,“花木兰”作为母题,它的周围不可避免地围绕着替父从军、女扮男装、北魏时期、巾帼英雄、忠孝仁义、皇帝嘉奖、军营生活等子母题。“花木兰”母题与周围的子母题所形成的母题链才成为构成文学、电影、戏剧等艺术作品的基本叙事的核心框架。差异化的母题的重构与母题链的生成展示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歌唱片与好莱坞歌舞片的本质区别。

图3 “花木兰”母题与子母题
一方面,母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作者身份、作品状态以及时代要求中,展现出不同的拼合形态与所指。在母题的演变中,存在着跨时代造就的内部横向裂变,与跨民族、跨地域形成的纵向延伸。以“花木兰”母题为例。其一,横向裂变表现为:在北朝民歌《木兰辞》中,花木兰是替父从军的“孝”的代表——“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而在1939年陈云裳主演的歌唱片《木兰从军》中,花木兰则演变成了保家卫国、驱除外敌的“忠”的化身——“青天白日满天下,快把功夫练好它。强盗贼来都不怕,一起送他们回老家”;到1956年常香玉主演的豫剧电影《花木兰》,则突出了花木兰作为女性这一形象与男性之间的差异,责任心、坚定的信念成为花木兰这一“女性”形象的重新建构之基点——“若都是恋家乡不肯出战,怕战火早烧到咱的门前”。其二,纵向延展为:在1998年迪士尼动画电影《花木兰》的叙事中,“花木兰”成为为了花家荣耀而战的巾帼英雄,个人主义色彩充斥了花木兰的形象内涵。插科打诨的风格特点消解了战争、苦难和家国情怀传承的思维模式。另一方面,母题链的结构序列与环套模式的差异,成为不同叙事模式的产生基石:线性叙事、环形叙事、倒叙叙事、重复性叙事等模式的生成均来自不同的子母题的排列次序。线性叙事、倒叙叙事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歌唱片与好莱坞歌舞片中占据主导地位。《天涯歌女》中,采用“英雄救美”的母题。围绕母题周围的是系列子母题——年幼受骗、妹妹茶楼卖唱、姐姐做暗娼、偶遇少年、恶霸欺凌、施计逃跑,按照因果逻辑顺序线性排列形成母题链,并最终生成“英雄救美”式的程式化表达。
母题的运用、子母题的筛选以及母题链的编排,成为1937—1945年好莱坞歌舞片与“孤岛”歌唱片的本质区别。其差异化的母题阐述分别来自两种不同的艺术形态,即中国传统戏曲与百老汇音乐剧。
二、认知博弈:大众审美与联动机制
母题链的组合、选取与表达方式直接导致电影作品的主题意蕴以及视听符码的差异,究其本源,与当时社会的大众审美认知以及文学、戏曲、戏剧的互相联动作用相关,尤其以戏曲艺术为主。1937—1945年期间,“孤岛”上映的歌唱片数以百计,其中包括《马路天使》(1937)、《三星伴月》(1938)、《木兰从军》(1939)、《天涯歌女》(1940)、《夜深沉》(1941)、《鸾凤和鸣》(1944)等。在母题的呈现上,中国歌唱片受到中国传统戏曲的影响,保留了诸如“花木兰”“英雄救美”“受难歌女”“才子佳人”等传统意象。而在子母题的筛选中,导演有意识地选择了与“抗争”“悲悯”情感诉求相关联的情节。在满足当下政治、时代潮流的同时,更深层次地与中国戏曲的悲苦内核共振。中国观众长期的戏曲审美影响了电影审美方式的形成,在中国电影产生之初便呈现出与戏曲艺术的联动模式,中国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学术界对此有异议,这里仅作为探讨戏曲艺术与电影艺术的关系,区别于电影史的定论)应当属于戏曲电影或古装电影的类型。“影戏”也成为电影最初的称谓。虽然以程式化的服装、化装、布景和表演为特点的中国戏曲的写意功能与相对写实的电影艺术之间存在艺术表达方式的冲突,以及20世纪30年代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的传播,加速了“影戏”的消亡,“电影”这一名词逐渐取代了“影戏”的称谓。但是,电影之中仍然渗透着戏曲艺术的某种意识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将“悲”“苦”作为最完美型人格。经历过大“悲”大“苦”方能大“慈”大“善”的人谓之“仁者”。只有“仁者”才能精神不朽,“力量”永存。在此过程中,人们为了寻求自我“力量”的传承,选择“自我牺牲”,进而得到“自我保存”。这才成为传统文化所宣扬的“悲苦”人格。而传统的“悲苦”精神早就孕育在盘古开天辟地之中:“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理),肌肉为田土,发须为星辰,皮肤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这是三国时徐整的《五运历年纪》(《绎史》卷一引文)中最早对于盘古在混沌之中开天地的情形的描写。盘古孕育之时,天地混沌不堪,历经一万八千年,盘古忽然醒来用手中板斧劈开混沌,形成天地。天地形成后,他害怕天地再次合拢,于是盘古顶天立地,遗世独立。终于天地稳定,盘古功成身退,身体化为宇宙。作为创世者,盘古的魅力在于追逐光明的过程中虽然艰难,但其亲历辛劳,最终化生万物。“悲”于功成却孤独,“苦”于力竭而创造,最终将其身体牺牲而成为人类的始祖“盘古”。盘古的魅力即传统文化之魅力——人在混沌的“悲苦”环境之中依然保持坚定的信念,从而进入“悲苦”的人生状态,得到内心的宁静与泰然,最终获得自我救赎的“悲剧性毁灭”。中国传统文化是“悲苦”的而非“悲剧”的。其原因在于“悲苦”是体悟生命本身的过程,“悲剧”是“悲苦”的结局。在传统观念之中,更加强调前者的主动性,如“士为知己者死”,我们更加强调“士”与“知己者”之间的侠义的、惺惺相惜的精神状态,这种状态可以促使“士”为“知己者”做任何“悲苦”之事,而“死”表示可以为了“知己者”牺牲而成为“悲剧”的决心。因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文艺作品中对“悲苦”的表达,像戏曲之中的《窦娥冤》《牡丹亭》,小说之中的《红楼梦》《水浒传》等,到了电影《太太万岁》之中,这种“悲苦”更加通过视听表演的方式经由女主人公的隐忍、顺从、妥协而表达出来。
1941年费穆对于戏曲与电影之间的关系做过较为深刻的理论批评。作为导演出身的费穆,对于戏曲尤其是京剧在电影中如何表现有其独特的认知。探讨京剧与电影的关系,既是对20世纪30年代的“孤岛”电影的繁荣背后的担忧——前文论述过当时“新华”“国华”“艺华”这三家影业公司为了争夺观众,不惜进行拍片竞赛,同质化、低质量的古装片、歌唱片和戏曲片大量涌入市场,使得电影的艺术性停滞不前,商业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同时,又是为了寻求戏曲与电影之间的出路的探索和尝试。费穆认为,“‘京剧’电影化有一条路可走。第一,制作者认清‘京剧’是一种乐剧,而决定用歌舞片的拍法处理剧本。第二,尽量吸收京剧的表现方法而加以巧妙地运用,使电影艺术有一些新格调。第三,拍‘京剧’时,导演人心中常存一种写中国画的创作心情——这是最难的一点——那么这一部电影的‘京剧’,大概不会完全要不得。”在费穆的论述中,京剧/戏曲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音乐剧,在导演技法上需要采取歌舞片的处理方法,这种观点必然受到了当时好莱坞歌舞片的影响。但是他所强调的歌舞片的表现技巧大都沉浸在外部的表达手段,对于内部核心机制的构建,则更加强调传统叙事思维以及艺术表现力——戏曲母题与大众传统审美的联动模式。
在母题的选择上,被“孤岛”歌唱片引用最多的则是“奇女子”母题与“拟男”母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母题存在意向上的相关性:一则由于两者均以女性形象为其侧重点;二则这两种女性形象均有别于封建传统的女性形象,即带有不同程度的“男性”特质。首先,作为侠肝义胆与才华横溢的“奇女子”母题。传统女性审美之中标榜的大家闺秀形象——“女子无才便是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消解在奇女子的叙事模式之中,这类女子或是如李清照、柳如是般才思敏捷,或是如杨排风、窦娥般节烈忠义,属于戏曲叙事中女性的叛逆者。“孤岛”歌唱片将奇女子母题引入电影之中,形成其独特的女性形象群体,其中出现最多的则是载歌载舞的歌女、深陷泥淖之中的妓女以及具有独立思想的下层女性形象。《马路天使》中的歌女小红,李丽华、周璇两个版本《三笑》中的侍女秋香,《西厢记》中的侍女红娘,《新茶花女》中的卖花姑娘,这些形象往往成为电影的核心叙事动力,也成为女性观众模仿、男性观众满足的观看动因。其次“拟男”即女扮男装,作为“奇女子”的极端表述。由严敦易先生首先提出,在他看来“虽然‘拟男’的动机和抒写,与弹词中的主人公不同,她们并不出将入相,到头来依然是贤妻良母。她们只是发发牢骚,揣摩悬想一些男人们有的、能做的、快意的事”。表征形象的男性化并没有改变传统女性叙事的内核,因而《花木兰》中作为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木兰,其被观看的女性命运并没有改变,反而更加深了被窥视的欲望:女性观众在女扮男装的身份替代中、替父受苦的孝道中得到内心满足;而由于现实中传统女性仍然占据绝对优势,女扮男装的反叛者形象引发了新一轮男性观众的窥视快感。一方面作为女性观众,身份替代纾解了被男性挤压的痛苦,掌握“我即男性”的主动权。因而《花木兰》中,木兰在军营中大肆行使其领导权;另一方面作为男性观众,反叛的魅力激发了其征服的欲望,影片最终还是以木兰嫁作他人妇从此过上相夫教子的生活作为结尾。女性幻想后重新回归传统家庭,男性最终依然成为权力的中心,既满足了女性的想象,又承担了男性叙事视角。
母题的选择决定了影片的叙事核心,由母题引发的一连串的子母题相互连接,构成影片的核心叙事动力。因而“孤岛”歌唱片的母题选择往往形成与大众审美联动的模式。
三、诱导共融:认同心理与主体狂欢
中国传统戏曲母题传承造就了“孤岛”歌唱片悲苦的内核。其母题建构主要依托于传统戏曲审美,其建构与发展呈现出与观众接受审美变迁的趋同,而好莱坞歌舞片的母题传承则来自舶来艺术——戏剧审美以及观众的认同机制。起源于欧洲的戏剧从其内容层次、美学体系以及表达方式上进行划分,大致可以分为悲剧、喜剧、正剧等。尼采在其《悲剧的诞生》中曾经对艺术,尤其是古希腊的戏剧艺术进行了论证,提出阿波罗式的日神精神以及狄奥尼索斯式的酒神精神。所谓日神精神来自古希腊神话之中的太阳神阿波罗,他既是光明的指代,又是预言与造型艺术之神。其精神的实质呈现出冷静、隐忍、肃穆与纯净,在他的光芒下,一切艺术变成确定的、完美的、虚幻的存在。而作为酒神的狄奥尼索斯是颠覆日夜的狂欢之神,他热爱音乐、热爱艺术,代表着艺术本体。因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而使得认知主体麻痹后自然回归子宫,形成不自知的狂欢与躁动,这种深层次的悸动背后是无法遏制的生存的痛苦与幸存的快感,在短暂的麻痹后使个体充满了自我满足的幻想。尼采认为艺术尤其是悲剧艺术起源于酒神的迷醉,冷静于日神的幻境,最终抵达快感的永恒彼岸。“狂欢”“肃穆”成为戏剧的两个重要的母题形式。
作为表现崇高、恐惧、正义的悲剧代表了古希腊、古罗马戏剧艺术的最高成就,早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便引进了这一戏剧样式。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舞台艺术中出现了百老汇音乐剧——“一种艺术表现的方式或模式,也是商业运作的机制,是那个圈子里的一些艺人,也是渗透在美国生活方方面面的一种精神和风格”——这一视觉化的、奇观化的区别于传统戏剧模式的舞台形式。其呈现出的整齐划一的舞蹈、女性身体符号化的构图以及弱化情节而强化节奏动作的表现形式与尼采提出的酒神狂欢相一致。一方面,自1929年“黑色星期二”开启的大萧条以来,美国有大量失去收入、生存困难的居民,他们长期处于无法果腹、极度痛苦的生存环境之中,为了寻求出路,一部分人走上犯罪、滥用暴力的道路,而更多人的则是沉迷于醉酒状态——解除生活困顿的束缚,回归本真的幻想;另一方面,百老汇作为美国文化消费的寄托品,为了迎合观众醉酒的需求强力推出歌舞音乐剧,在身体、精神极度疯狂、快速的舞蹈中消磨时光。因而,狂欢成为当时美国民众面对生存压力被迫做出的选择,“狂欢”也成为百老汇音乐剧深层次的母题选择。
同样,好莱坞电影在20世纪30年代日臻成熟,大制片厂制度达到全盛时期。高度商业化、类型化、系统化的电影工业体系的完备,使得好莱坞电影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类型片的高潮,其中拥有百老汇歌舞剧观众基础的歌舞片成为制片人重要的盈利类型。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音乐剧的黄金时期诞生了百部歌舞片:《风流浪子》(The
Beloved
Vagabond
)(1936)、《画舫璇宫》(Show
Boat
)(1936)、《淘金者1937》(Gold
Diggers
of
1937)(1936)、《风流水兵》(The
Singing
Marine
)(1937)、《好莱坞旅馆》(Hollywood
Hotel
)(1937)、《大学艺游会》(Varsity
Show
)(1937)、《巴黎的淘金者》(Gold
Diggers
in
Paris
)(1938)、《百老汇小夜曲》(Broadway
Serenade
)(1939)、《让自由歌唱》(Let
Freedom
Ring
)(1939)、《华盛顿广场的玫瑰》(Rose
of
Washington
Square
)(1939)、《百老汇旋律1940'》(Broadway
Melody
of
1940)(1940)、《笙歌喧腾》(Strike
Up
the
Band
)(1940)、《百老汇的小鬼》(Babes
on
Broadway
)(1941)、《月宫宝盒》(Cabin
in
the
Sky
)(1943)、《疯狂的女孩》(Girl
Crazy
)(1943)、《俄克拉荷马》(Oklahoma
!)(1943)、《歌剧魅影》(Phantom
of
the
Opera
)(1943)、《嫦娥幻梦》(Lady
in
the
Dark
)(1944)、《出水芙蓉》(Bathing
Beauty
)(1944)等。一是,区别于百老汇音乐剧的“贵族化”(高昂的票价),电影票价在经济萧条的年代更易于被观众所接受,加之电影本身强大的记录现实、表现细节、蒙太奇重构的优势,使得好莱坞歌舞片在挣扎、痛苦的年代风靡一时。二是,相对于音乐剧演员的在场性,电影复刻传播的优势随即展现,直接导致音乐剧、歌舞片两种艺术形式相互交融,如20世纪30年代百老汇著名演员齐格菲尔德便辗转于戏剧、电影之中,成为百老汇、好莱坞的“双栖明星”。两方面的相互作用下,好莱坞歌舞片生成了后台歌舞片的类型模式,将百老汇的舞台空间以及歌舞表演融合后台叙事情节,最终生成奇观化的“狂欢”母题。围绕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歌舞片“狂欢”的母题,形成了浪漫爱情、大腿、灰姑娘与王子、公主与平民、舞女郎等子母题。在母题链的选择中,好莱坞歌舞片通过极尽疯狂的集体张扬,将音乐、舞蹈、杂耍、情节剧等因素聚合在一起,围绕母题,形成外部诉说个人情感、身体观赏、群落化表演的母题链整合。
四、催化建构:“悲情”“孤岛”与“纵情”好莱坞
中国传统戏曲母题的演变转移催生出“孤岛”歌唱片的“悲情”格调;百老汇的“狂欢”母题同样移植到好莱坞歌舞片之中并最终生成纵情歌舞的外部表征。两种类型相似、时间相同的类型电影,由于各自不同的政治背景、时代特征以及深层次的母题差异,形成悲情与纵情的总体情绪力量。母题概念的对立直接导致影片母题链选择、表述状态的差别:从主题内容到女性形象、从演员表演到音乐舞蹈,一方沉迷于家国、另一方寄情于享乐。两种差异化的类型电影同时上映于上海,建构出“孤岛”特有的文化碰撞奇观。
碰撞之一表现为:差异化的情感困境——家国罹难与个人苦难。先有国家才有个人,“孤岛”首先面临的现实困境是国破家亡,而好莱坞则是沉浸在经济萧条所造成的个人苦难之中。因而造就了观众审美体验的深沉苦难与狂欢激情碰撞。“孤岛”歌唱片的悲情色彩包含两个层次:其一,作为国家受难、流离失所的外部大环境的苦难;其二,作为抵抗渺茫、民众麻木的现实困境。从个人到家国,破碎低沉情绪充斥的“孤岛”以及严酷的电影审查制度影响了艺术家的创作。导演既要表现出与现实环境的割裂,又要充分展现自我觉醒的思想,因而他们被迫选择以歌咏志。“自《渔光曲》以后,影片插入歌曲的很多,同时,便产生了所谓电影的主题歌,如《渔光曲》的主题歌《渔光曲》,《飞花村》的《飞花村歌》,《大路》的《大路歌》,《新女性》的《新女性歌》,在原则上我们不反对影片和音乐的联系,在电影的效果上,音乐有很大的力量。”因而在《木兰从军》中出现了“强盗贼来都不怕,一起送他们回老家”的自信;在《马路天使》中吟唱“家山呀北望,泪呀泪沾襟”的悲悯。国家危亡之于个人困境如同经济基础之于上层建筑,考虑上层建筑要以经济基础为其先决条件。显然,好莱坞并没有存在经济基础的瓦解,因而好莱坞歌舞片的情感背景则是远离政治生活的个人情绪的宣泄。“爱情至上”成为好莱坞歌舞片十分重要的主题,其过程呈现出偶遇、相爱、挫折、结合的叙事特征:首先,主人公在群体化的歌舞演出中相遇,而后迅速坠入爱河;其次,情节突转,男主人公往往遭到爱情抑或是理想的挫折,与女主人公产生情感危机;最终,通过歌舞欢唱以及英雄主义的视角达成主人公爱情与理想的圆满结局。而女性在这四个步骤中呈现出性格“缺席”甚至是角色“缺席”的特征,集群化的表演模式遏制了个体尤其是女性个体的生长,使得女性角色沦为好莱坞歌舞片华丽的背景。“孤岛”歌唱片中女性形象的符号化与好莱坞女明星群体的背景化形成了“孤岛”歌唱片与好莱坞歌舞片的第二个差异。
碰撞之二表现为:个人化吟咏苦难与群落化纵情高歌。好莱坞歌舞片/后台歌舞片中主要依托于华丽的歌舞段落,主人公往往是剧中舞台演员本身,在套层文本中形成群体表演与后台叙事相呼应的表现手段;而“孤岛”歌唱片则主要集中于叙事文本的讲述,以情节线索为主要依托,着力展示主人公受困与解救的过程,声音符号作为次要表现手段镶嵌于叙事文本之中。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歌舞片/后台歌舞片受到百老汇音乐剧的影响,导演十分注重歌舞的重要性,而忽视电影文本的叙事作用。因而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歌舞片均呈现出超越现实的、奇观化的舞台表演,对于个人困境的展示则相对削弱,酒神的狂欢制造出纵情歌舞的银幕群体沉迷状态。焦雄屏对好莱坞歌舞片的幻想机制做出了两个方面的论述:“1.整体结构上,所有的冲突障碍均因末了推出一个完美无瑕的歌舞秀而克服。2.不同的小段歌舞中,发挥叙事功能,演员彼此间的冲突关系透过歌舞表达。”20世纪30年代著名歌舞片导演巴斯比·伯克利的《华清春暖》(Footlight
Parade
)就制造了三台歌舞幻境。影片主要讲述即将面临失业的切斯特·肯特导演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制片人给予的让他导演百老汇开场前的贴剧广告这一赚钱机会,他需要同一天晚上在三个不同的剧场分别上映不同的广告短剧。面对高强度的压力与抄袭的困扰,肯特历经三天疯狂的排演最终取得成功。影片主要用于表现男主公肯特在失业面前临危不惧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为了赚取金钱而不辞千辛万苦的功利主义,对于其女秘书的爱慕与暗恋,肯特表现得十分冷漠甚至根本就没有发现。女性在影片中隐藏,沦为肯特成功的背景。片中最出彩的部分则是三场歌舞秀的展示,从“蜜月旅馆”(Honeymoon Hotel)到“瀑布芙蓉图”(By a Waterfall)再到具有异域风情的“上海莉莉”(Shanghai Lili),女性以其群体化奇观印象构成了身体符号化的表达。在“瀑布芙蓉图”中,簇拥着女主角的女舞蹈演员群体在瀑布旁纵情高歌,而后跳入池中又跃出水面,一连串动作与歌声伴随着水中狂欢的结束而逐渐隐去。然而观众注意力仅集中在香艳的外部身体表演中,对于影片个人形象的印象则十分模糊。较之于好莱坞歌舞片中女性角色的缺失,“孤岛”歌唱片则呈现出女性形象的受困。由于技术与传统的差异,好莱坞歌舞片集群式的歌舞场景并没有出现在“孤岛”歌唱片之中,取而代之的是主题歌的演唱与戏曲程式的模仿,在个体诉求上更加倾向于戏剧化情节的构建。由于中国歌唱片并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类型模式,因而笔者探讨三四十年代“孤岛”歌唱片时,所倚重的是这一时期集群式出现的、主人公在剧中演唱主题歌的影片,同样涵盖具有歌舞片性质的影片。如《斩经堂》《水淹七军》《马路天使》《三笑》《木兰从军》等影片均有主题歌演唱的段落,因而将其归为歌唱片。在广义的“孤岛”歌唱片维度下,影片的侧重点在个人、舞台、情节、突转。如在周璇主演的歌唱片《西厢记》中,以元代王实甫的戏曲剧本为蓝本,讲述张生、莺莺“才子佳人”的母题。从红娘牵线到两人西厢夜访以及最终私订终身,影片突出表现了红娘作为功能性中间人的性格特征,其自身的爱恨情仇、家国离恨淹没于影片之中,个人化的情感表达最终消解。好莱坞歌舞片中群体化的表述淹没了个人性格,而“孤岛”歌唱片同样将重点放在情节线上。无论是视觉化的幻想,抑或是隐匿的个人性格,最终成就了“悲情”“孤岛”与“纵情”“好莱坞”的表述形态。
注释:
① 夏令配克影戏院:今名新华电影院,遗址位于上海静安寺路127号(今南京西路石门二路路口)。由西班牙人雷玛斯创建于1914年9月8日,是集影院、戏院、剧院功能于一体的影戏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控制好莱坞电影的首轮播放权。
② 中央大戏院:徐颂创办,前身为1923年2月16日成立的申江大戏院,专门的电影院。1924年由湖北路汉口路路口迁至上海市北海路25号。1925年更名为中央大戏院,以演沪剧为主,电影放映为辅。1966年更名为革命剧场、北海剧场。1970年改为工人文化宫剧场。1984年改名为工人文化宫影视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