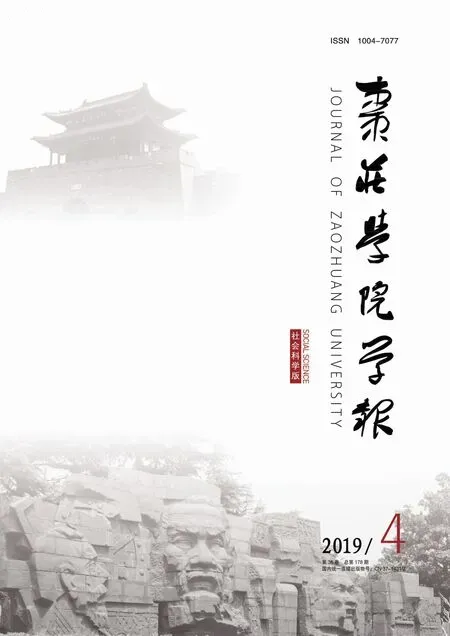论魏晋时代的审美范式
——以《世说新语》为例
陈福盛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世说新语》这一独特的传世经典文本在传统文化中具有多重内涵,有时它被视作那个时代文人逸事的真实记载,其中很多故事甚至被作为正史堂而皇之地写进历史;有时它又被视作特定时期文人情趣的表达,李泽厚认为:“《世说新语》重点展示的是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漂亮的风貌;而所谓漂亮,就是以美如自然景物的外观,体现出人的内在的智慧和品格。”[1](P85)于是又成为独特文人精神品格的汇集;进入现代文学分科之后,它又被树立为早期小说的典范样式,成为中国早期小说叙事的代表。虽然魏晋风流在后世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风范,然而却一直没有人将《世说新语》作为一部美学文本进行系统解读。从形式上来看,《世说新语》并不是理论性的美学著作,然而它却具有鲜明的审美目的,刘义庆之所以编撰此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个人及当时社会对魏晋士人的一种浓厚的追慕情结。可以说,《世说新语》记录了那个时代独特的审美追求与文化情趣,通过简明生动的笔墨勾勒出一幅幅审美风尚图卷。所以,此书虽然不是典型的理论性美学著作,但却是最具有活性因子的感性审美活动的历史文献。对于这样一部著作,如何从理论上提炼其审美范式,重建那个时代的审美文化规范,并且启迪当下人们建构现实美好生活,无疑具有较大的学术和实践意义。
一、人格审美范式的见证
《世说新语》是魏晋士人生命情态的诗意化表达,它所展现出来的审美理想首先表现为鲜明的人格范式。人物品藻发源于汉末、流行于魏晋,尽管这与个体的政治前途密切相关,但却已经不再是纯政治行为的记录,甚至在很多时候为了突出个体的自我风采,政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有意地被个性所遮掩。例如谢安虽然是著名政治人物,但在《世说新语》中描写谢安时最突出的并非他挽时局于既倒的政治功业,而是他虽经营事物但却托心玄远的个性与意趣,政治功业只是他超然人格的衬托。品藻是对个体自身价值的衡量,它所折射的是个体的自我风采。对此,前辈学者多有论述,如鲁迅指出,“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2](P55)。个体的价值取决于自我的语言建构能力,个体需要通过语言(也包括部分行为举止)充分显示出自身存在的独特性,这样就将个体自我从政治功利的目的中解放出来了。董晔认为,人物品藻一旦脱离实际的政治需要,必须推动个体审美人格的建立,对个性主义的张扬,对人物风度神韵的崇尚,正构成那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3](P43)。当人自身的个性行为可以作为欣赏对象时,围绕“人”本身的审美规范就开始建立起来,而《世说新语》恰恰是中国关于“人”的审美范式建立过程的见证。
对《世说新语》进行审美解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自我的重新构建,即以“我”为本的高自标置。自我构建是个体确立自身价值的关键,只有独立自主的“自我”意识才能使人格审美成为可能,也才能树立起真正的审美范式。当个体意识到“我”本身即可以具有充足的独立价值,并且能够自我欣赏这种独立价值时,个体才能真正把生命看作是一段充满审美体验的经历,并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相应的审美规范。从此方面来看,《世说新语》对“我”的标置就体现在这样一种自我认同上,即每个人都有优势和不足,这并无足羞,更重要的是彰显个性,展现出自己的优势。当个体意识到自我的真实较之其它附加的名利、权势、功业等外在内容更珍贵时,“真”就成为一个根本性的人格范式。
摆脱现实中各种有形无形的规范化束缚,将自我放置到一个超脱于现实规则之外的层面,自我本身的情趣就会自然地跃入到审美者的眼帘。当然,这种超脱并不是完全背离现实中的人生规则,因为如果仅仅是与现实规则相对而行那又会陷入到另一种束缚之内,所以名士乐广对一味求旷求达的废礼行为才会发出“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世说新语·德行》)的嘲笑。追求自我之“真”并不是逆行悖德,而是遵循现实世界的运转方式自然而处,在现实的行为活动中展现自我真趣,做人如若过于做作矜持,则只能对自然天成本质造成损害。人性之“真”便源于一种天然的本性,这是魏晋士人为后世所确立的一种人格典范,也是一种审美标准,对后世文人的行为性格具有深刻的影响,也是后世文人审美情趣的重要文化资源。
当“真”成为个体自我风采的核心要素之后,对人的欣赏就以个体的内在精神气质为主。当个体能够以自己本然面目行事时,个体的内在性情风采就成了能为他者所直接体验欣赏的对象。所以在《世说新语·赏誉》中记载了谢安称颂王述“掇皮皆真”,毫不掩饰对其个性风采的欣赏。这种人物自我的力量有时甚至能超越名利势位带来的世俗自豪感,书中多处记载凭借强烈个性魅力折服对方的故事就是明证。因此,在对《世说新语》的美学研究中,将“真”作为人格之美的基础,并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衍生出“清”“神”“简”“远”“朗”等一系列的审美范畴,它们作为次级审美范畴不仅进一步扩大了“真”的内涵,而且将“真”所蕴含的审美意味形象化,这就抓住了魏晋人格审美范式的核心问题,形成了一个有核心有层次的人格审美体系。
人的个性风采只有在现实的行为活动中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因而围绕人的审美活动最终还要体现在个体在特定境遇中的行为方式上。“魏晋士人从未把生活仅仅作为人的自然的或世俗的日常活动,而是使生活本身成为诗意的存在,把个体的行为化作精神的、审美的对象,然后咀嚼再三、细细品味。”[3](P95)魏晋士人不仅用传神的语言创造出独特的审美范式,而且还通过自己的切身践行树立起一种行为的典范,使诗意的生存不仅是一种理论的宣扬,更是一种现实的存在。
二、山水审美范式的确立
宗白华先生曾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4](P215)《世说新语》对中国传统审美范式的建构不仅体现在个体人格方面,而且体现在对自然山水的欣赏方面。在这一时代,山水已经不再是与人相对立的外在客观世界,而是人类主体情感所浸染后的审美世界。东晋南渡之后,山明水秀的江南自然世界迅速激起了人们的审美热情,山水自然逐渐成为彼时士人展现个性风采的绝佳场域,也是寄托自身审美情趣的最好对象。
然而,山水也并非在魏晋时期突然跃入人们眼帘成为独立审美对象的。在魏晋之前,“庄老”和“山水”是长期并存的,从东汉末年开始,士人们就由于对时局的失望,纷纷转向了田园山水,从中寻找精神的慰藉,并以此发泄内心的苦闷。的确,士人对山水的亲近由来已久,自东汉末年,寄情山水就已经成为一种风尚,经过魏晋的充分发育之后,才在刘宋时期正式揭下那层面纱。
当然,山水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被视为审美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它首先是体玄悟道的场域。早在庄子那里,山水自然就一再被看作体悟至道的载体。魏晋玄学盛行之后,山水更是被视作启迪玄远幽心的媒介。自然山水的四季变化同时也蕴含着时间的变迁,在物的空间中隐藏着时间的内涵,而伤时感乱恰恰又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太多的战乱与死亡让士人对时间的交替格外敏感,因而山水自然的时序变化其实也蕴含了更深的生命主旨。
然而,随着体悟的深入,玄思开始让位于审美。正如董晔所说,大概由于那时的山川景色更易使人想起时光流逝和人生短促,所以物之变迁与生之匆匆就在这自然审美的过程中完全融为一体了[3](P131)。生命与山水融为一体之后,山水才真正成为个体意义世界中的一部分,才真正明亮起来。山水意识觉醒的标志就是文人雅士不再把山水仅仅当作玄思的对象,而是当作自我意义世界的一部分。山水之所以是“我”的山水,是因为它的可居性,它能成为个体自我存在的意义性空间。
这种自我与山水的意义共融就是山水审美独立的开始,用当时世人的话语表达就是“会心处不必在远”。山水只有成为“我”的意义世界的一部分,才能显示出它独特的审美价值。因而,之前道家所追求的离群索居,在人迹罕至的名山大川中独自悟道的方式并不能显示山水与人的共在特性,也无法体现出山水与个体意义世界的审美关系。只有当山水成为“我”的意义世界的一部分,“我”与外在山水的关系才能够转化为审美性的存在。在这样一种审美共在中,山水自然就成为一种可亲可感的对象,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都以它们各自的方式自由地存在,草长莺飞、花开月落、万木葱茏、霜天鹤唳,任何一种自然画卷都是个体的感性审美对象,也是个体与这个世界相交融的图景。他们不需要走到人迹罕至的深山绝谷,只要心中有自然山水的意念,那么处处山水都向人生成,成为宜人的对象。
当山水自然的审美地位确立之后,山水游乐就成为魏晋士人的主流审美活动。从金谷集会到兰亭禊集,魏晋士人把游乐山水作为人生意义的重要指标,也愿意将这种活动作为一种集体共在搭建起的价值平台。金谷之会标志着山水自然进入了士人的日常生活,显示出文人共同的山水审美情趣,使山水正式成为文人生活的一部分。即使个体化的行为如隐逸,在这个时代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离群式的隐姓埋名,而是在自然山水欣赏中建构起的一种名士风度,在自然山水体悟中建构的一种特殊审美关系。这一点绝然不同于以修道求仙为目的的早期隐逸,它是真正的与自然山水相共融。
三、文本审美价值的追求
《世说新语》不仅向内建立起真纯任性的人格审美范式,向外建立起自然可亲的山水审美范式,而且它本身的表达方式也同样为后世文学书写树立起典范。《世说新语》的话语表达方式已经形成为一种独特体例被后世称为“世说体”“即按照内容把作品中的故事分成若干门类,每一门类中以不同人物的故事表现大致相同的主题。所以其描述中心是移动的,而故事则是并列的。”[3](P164)这种书写体例并不仅仅是一种文本处理形式,它本身就是一个包含着丰富文化信息和广阔阐释空间的场域,不仅对后世小说的分类影响深远,甚至还波及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人格心理的深层结构,蕴含着丰富的审美文化信息。的确,在漫长的历史传承中,《世说新语》的文本早已超越了作品本身的意义,而具有了更深刻的文化内容。
从表达对象上看,《世说新语》的志人方式树立了一种典范。它并没有对人物进行全面细致的刻画,没有像西方叙述文本那样着眼于人物命运的全景式展示并且追求故事情节的完整性。甚至它也与史传体的中国史学作品相背离,不追求全面展示人物的一生功业事迹。《世说新语》的志人方式在很多时候近乎白描,通过三言两语的对话或者超常规的行为来展现人物内在的精神气质。它所呈现的往往只是某一特定细节,然而正是这种细节展现出生动感人的个性风采。
当个体的行为被压缩到一个局部的行为动作或偶尔的只言片语时,关于人物思想道德以及伦理意识方面的束缚就基本被剥离出去了。在有限的叙述空间内,整体的社会价值规范对叙述本身没有太大意义,而个体的独特生存方式则影响到叙事的效果。因而,《世说新语》尤其重视对个体情感的描绘,因为无论是相亲相爱还是相憎相厌甚至是相生相杀,都能在特定情境中展现出人物的内在个性气质。这种独特的叙事理念与全书的重情倾向是一致的,也是《世说新语》能够不断被文化重构的关键。
《世说新语》的语言风格同样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极大地凸现了语言本身的审美价值,并且创造出一系列有关汉语审美的语言典范。当语言被推向显处直接作为审美体悟的对象时,语言本身的经济性就成为一个衡量其审美意蕴的重要指标。从理论上说,在有限的文字符号之内承载的意蕴越多,该话语的审美空间及审美层次就越复杂,也就越容易吸引欣赏者的注意力。因而,《世说新语》发展出一种极简约的语言审美规则,它要求在有限的话语中寄托无限的审美韵味。
《世说新语》中经常出现诸如“简”“约”之类的术语,它们不仅是对人物个性的描述,往往也意味着描写对象的生活或者语言表达风格。简约本是玄学的目标,老子的“大音希声”观念就已经蕴含了对简约风格的要求。然而,只有在魏晋士人这里,简约才成为一种审美的风致,是从行为到语言的去繁缛化。当语言被压缩到最简的状态时,语言在某种意义上也就触及到了存在的本真,因为不加任何装饰的语言表达其实就是存在的外现。魏晋士人就是借助于这样一种极度简约的表达方式,传达出他们对生命的真实体验。
当然,对语言的极致性审美追求最后会演化为语言游戏,《世说新语》中已经充分表现出这种对语言的热爱。生于动乱之世,此身之外皆为不可安顿之物,只有语言常存心底,是展现自身生命价值的根本。魏晋士人所热衷的清谈活动,最终转化为语言的审美体验,参与者固然以玄理为鹄的,然而其寻绎搜索之处、面争口折之际恰恰体现了对语言的深刻感受力,往往这种感受本身超越了所探索的玄理,成为给参与者印象最深的存在。一场辩论结束之后,辩论者的观点或许早已经不复记忆,然而辩论者的语言之美往往引得旁观者如醉如痴、回味无穷。
总之,从审美的角度对《世说新语》进行系统的理论重构,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与研究价值。通过对这一重要的文化原典所体现出来的人格范式、自然情趣以及文学意蕴的多重解读,还原出那个时代独特的审美风貌,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魏晋时期审美观念的形成对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重大意义,将突破文本与学科的双重限制,将《世说新语》研究推上一个崭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