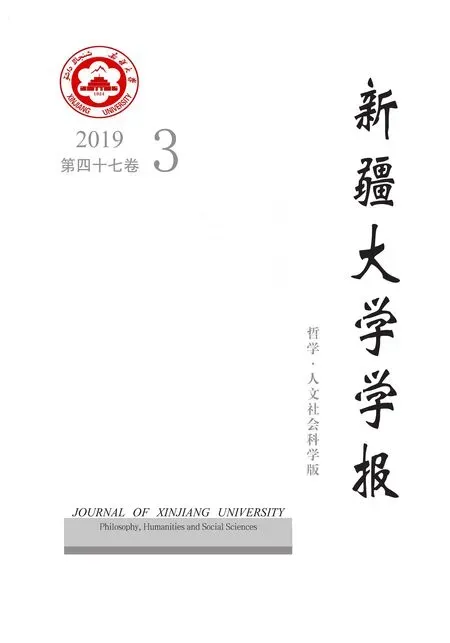论陈子龙与七子诗学*
姜克滨
(1.枣庄学院文学院,山东 枣庄 277160;2.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又字人中,晚年号大樽,松江华亭人,是明末重要诗人。陈子龙诗歌创作成就很高,被公认为“明诗殿军”,朱庭珍在《筱园诗话》中曾说道:“末年诗人,惟陈子龙雄丽有骨,国变后诗尤哀壮,足殿一代矣。”[1]2363学术界对陈子龙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对其诗学思想,多数研究者认为他是继承七子诗学复古派的代表人物,如朱则杰《明诗的光辉终结—略论陈子龙的诗》一文中认为:“陈子龙对前后七子极为推崇。……在整个明代来说,陈子龙是复古派的最后一个大家。”[2]朱则杰虽认为陈子龙对七子诗学的继承乃是“旧瓶装新酒”,但未深入论述陈子龙的诗学创新。再如刘勇刚在《论陈子龙诗歌》一文中也认为:“陈子龙执云间派之牛耳,是明末成就最大的复古派诗人。”[3]陈子龙的拟古、复古,似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我们的疑问由此而来。如果陈子龙对七子诗学全盘接受,以因袭模仿为能事,又怎能超越七子,又怎能成就斐然,取得“明诗殿军”之称号?通过对陈子龙诗集、文集的细读,我们不难发现陈子龙诗歌成就主要来源于创新,而不是复古。陈子龙在继承“复古”诗学的基础上,融汇创新,有自己的诗学主张。陈子龙一方面重倡七子诗学,改变了当时诗坛尚奇求异的不良创作风气,对诗歌风雅传统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他有着自觉的诗学批判意识,秉承何景明“力主创造”之精神,以现实主义手法写时事政治、民生疾苦,取法盛唐诸家,使其叙事诗堪称“诗史”,抒情诗则具高华雄浑之风格。陈子龙也有着自觉的诗歌文体创新意识,大力提倡歌行诗创作,对“云间派”歌行的形成和清初歌行的兴盛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陈子龙对七子诗学的崇尚
陈子龙在崇祯初年,参加了以张溥、张采为首的复社,又与夏允彝、徐孚远等结几社,与复社相呼应。他是明末清初江南的风云人物,诗词俱佳,为云间派领袖,在当时声名远播。陈子龙诗学思想远追六朝、盛唐,近法明七子,陈子龙对七子诗学的崇尚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与明末清初诗坛诗风转换有密切关系。
陈子龙诗歌受七子影响较深,他多方面学习继承了七子的诗学主张,倾向于复古。陈子龙奉七子,法盛唐,在当时的诗坛影响很大。钟、谭“幽深孤峭”诗风流行一时,陈子龙对七子诗学的推崇与钱谦益对“宋诗”的倡导具有同样的意义,使当时诗坛风气为之一变。《明史·文苑》列传173 中论道:
王、李之持论,大率与梦阳、景明相倡和也。归有光颇后出,以司马、欧阳自命,力排李、何、王、李,而徐渭、汤显祖、袁宏道、钟惺之属,亦各争鸣一时,于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至启、祯时,钱谦益、艾南英准北宋之矩矱,张溥、陈子龙撷东汉之芳华,又一变矣。[4]7307-7308
宋犖在《漫堂说诗》中说:“此后诗派总杂,一变于袁宏道、钟惺、谭元春,再变于陈子龙;本朝又变于钱谦益。”[5]朱彝尊《明诗综》中引钱瞻百云:“大樽当诗学榛芜之余,力辟正始,一时宗尚。遂使群才蔚起,与弘正比隆,摧廓振兴之功,斯为极矣。”[6]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一中说:
王李教衰,公安之派浸广,竟陵之焰顿兴,一时好异者,诪张为幻。……卧子张以太阴之弓,射以枉矢,腰鼓百面,破尽苍蝇蟋蟀之声,其功不可泯也。[7]642
在公安末流、竟陵诗风的影响下,诗人“好异”“为幻”,作“离奇之言”,以轻浮险怪、俚俗率直为尚,将诗歌引入了歧途。陈子龙重倡七子诗学,对于改变当时诗坛尚奇求异的不良创作风气,恢复诗歌风雅传统,功不可没。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诗派,诗学汉魏、盛唐,在七子诗学旗帜下,酬唱吟诵,声势浩大,引起了一场诗风变革。许多学者、诗人都肯定了陈子龙的诗学贡献,如宋琬在《周釜山诗序》中说:
明诗一盛于弘治,而李空同、何大复为之冠。再盛于嘉靖,而李于鳞、王元美为之冠。……云间之学,始于几社。陈卧子、李舒章有廓清摧陷之功。于是北地、信阳、济南、娄东之言,复为天下所信从。[8]374
在《尚木兄诗序》中也说:
三十年来海内言文章者,必归云间。方是时,陈、夏、徐、李诸君子,实主齐盟,而皆以予兄尚木为质的。复有子建、直方为之羽翼,于是诗学大昌,一洗公安、竟陵之陋,而复见黄初、建安、开元、大历之风。所谓云间几社者,皆朋友倡和、鸡鸣风雨之作,何其盛也![8]379
宋琬在诗序中高度评价了云间派诗人对七子诗学的提倡之功,正是云间诗人的努力使诗坛风气大变,挣脱了公安派、竟陵派的束缚,诗歌创作重新走上健康之路,得以兴盛起来。
七子诗学,虽然有其缺憾,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能促使诗人摆脱公安、竟陵派的不良创作倾向。以陈子龙、李雯、宋征舆为代表的云间诗派对七子的推崇,对盛唐诗的倡导,都有其特定的时代因素。汪辟疆曾说:
有清康乾之初,承明代前后七子之后,流风余韵,至此犹存。观于复社、几社诸贤如陈子龙、李雯之伦,罔不奇情盛藻、声律铿锵,当时号为七子中兴。流风所播,乃在明末遗民,下逮清朝,仍未歇绝,不过稍益以悯时念乱之思,麦秀黍离之感,故读者罔觉为七子余波耳。语其至者,如顾炎武、杜濬、陈恭尹、侯方域、陈维崧、吴兆骞、夏完淳等诸家,皆此风会中所孕育者也。[9]
汪辟疆此段话表明,七子诗学影响深远,从明中叶到清康乾年间几近二百年。不仅陈子龙继承了七子诗学,而且顾炎武、陈恭尹、陈维崧、吴兆骞等人,也深受七子诗风影响。在学步七子之中,他们也纠正了七子诗学的一些弊端,能增添时代精神,有自己的风格。清初诗坛,对七子诗学,不少著名诗人多加肯定,诗学七子者不在少数。沈德潜认为七子诗歌皆有可采之处,并非一无是处,他在《说诗晬语》中说:“李献吉雄浑悲壮,鼓荡飞扬;何仲默秀朗俊逸,迴翔驰骋。同是宪章少陵,而所造各异,骎骎乎一代之盛矣。钱牧斋信口掎摭,谓其摹拟剽贼,同于婴儿学语。”[10]李梦阳、何景明同样是诗学杜甫,但两人诗歌都有自己的特点,沈德潜对此多有肯定,同时对钱谦益的“全面否定七子”作法略有微词。
陈子龙对七子诗学的崇尚,在其早年的经历中就可以看到。《陈子龙自撰年谱》中曾经记叙过这样一件事:
崇祯元年戊辰秋,豫章孝廉艾千子有时名,甚矜诞,挟谖诈以恫喝时流,人多畏之。与予晤于娄江之弇园,妄谓秦、汉文不足学,而曹、刘、李、杜之诗,皆无可取。其詈北地、济南诸公尤甚,众皆唯唯。予年少在末座,摄衣与争,颇折其角。彝仲辈稍稍助之,艾子诎矣。然犹作书往返,辩难不休。[11]642
陈子龙对艾南英诋毁七子非常不满,以致与之争论不休,从中可以看出陈子龙对七子的崇拜。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在诗学方面有着较一致的追求,云间派的诗学主张,五言诗学汉魏,近体诗法盛唐,继承了七子诗学的衣钵。吴伟业在《致孚社诸子书》中说:“弇州先生专主盛唐,力还大雅,其诗学之雄乎!云间诸子,继弇州而作者也;龙眠、西陵,继云间而作者也。风雅一道,舍开元、大历其将谁归?”[12]云间派对七子的推崇,从他们编选的《皇明诗选》一书就可以看出来。《皇明诗选》选录明代诗人诗作,前后七子作品多达七百六十首,而全部诗选作品不过一千余首。在诗序和诗评中,云间诗人对“七子”多加赞赏。陈子龙在《皇明诗选·序》中说:“自弘治以后,俶傥瑰伟之才,间出继起,莫不以风雅自任,考钟伐鼓,以振竦天下。而博依之士,如聚沙而雨之,作者斐然矣。”[13]1李雯在《皇明诗选·序》中说:
至于弘正之间,北地、信阳,起而扫荒芜,追正始,其于风人之旨,以为有大禹决百川,周公驱猛兽之功……又三四十年,然后济南、娄东出,而通两家之邮,息异同之论,运材博而构会精,譬荆棘之既除,又益之以涂茨。此后七子之所以扬盛烈也。[13]8-9
徐孚远在《陈李倡和集序》中说:“明兴几三百年,能诗之家,何、李振其风规,七子挺其秀实,斯既斌斌矣。……北地、琅琊数子,生当其世,建旗撞鼓,高风绝尘,偃盖前后,所谓遭时也。”[11]760宋征璧在《平露堂集序》中说:“国朝前有何、李,后有七子,固已追建安之遗风,俪开元之殊轨矣。”[11]765由此可见,云间派诗人对七子诗学顶礼膜拜,佩服至极,这不能不影响他们的创作。陈子龙早期诗作也深受七子诗学影响,多摹拟古人之作,模仿汉魏、盛唐诗歌,例如《拟古诗十九首》《拟公宴诗》等。其乐府诗,复古、拟古的调子很浓,大量创作了许多古乐府,如《步出夏门行》《秋胡行》《董逃行》等。这些作品大都未脱古人之樊篱,艺术性不高。
二、陈子龙的诗学批判与创新
陈子龙并非单纯效法前人,重走七子老路,他对七子诗学更多的是一种扬弃,吸收了七子诗学中的积极因素,在多方面能自出机杼。沈德潜为清初著名诗论家,他认为陈子龙有裨诗教,创作方面也超出七子。他在《明诗别裁集》卷十中评曰:“诗教之衰,至于钟、谭,剥极将复之候也。黄门力辟榛芜,上追先哲,厥功甚伟。而责备无已者谓仍不离七子面目,将蜩螗齐鸣,不必有钧绍之响耶?”[14]143严迪昌在《清诗史》中认为:“陈子龙是晚明时期绍承‘七子’派最称得法,从而深孚名望者,也可以说,是‘七子’诗风得以历晚明而入清延续不断的一个关键中介。”[15]43陈子龙对七子诗学的扬弃,明显体现于他后期的创作中,他的诗歌往往能反映社会现实,民生疾苦,诗风也更为沉郁悲凉。他摒弃了七子诗学的消极因素,增添了新的时代精神,这是陈子龙学七子而得以成功的一大关键。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实际上对七子诗学进行了多方面的革新,不只限于内容方面,在诗歌文体方面也有革新,严迪昌先生认为:“云间派的成功在于承沿‘七子’诗体形式美的外壳,既加以丽泽,又充实以实情真气,从而使诗的本体获得活力。”[15]43
陈子龙对七子诗学方面的缺点也有明确的认识,有着自觉的诗学批判意识。在《六子诗序》中他说:“献吉、仲默、于鳞、元美才气要亦大过人,规摹昔制,不遗余力,苦加椎驳,可议甚多。今人之才,又不如诸子而放乎规矩,猥云超乘后世,可尽欺耶。”[16]374“可议甚多”表明陈子龙对七子诗学有着清醒的认识,并非全盘接受,而是对其批判性的继承。陈子龙在《仿佛楼诗稿序》中也说:
诗衰于宋,而明兴尚沿余习,北地、信阳力返风雅,历下、琅琊复长坛坫,其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也。特数君子者,摹拟之功多,而天然之资少,意主博大,差减风逸,气极沉雄,未能深永。空同壮矣,而每多累句;沧溟精矣,而好袭陈华;弇州大矣,而时见卑词。惟大复奕奕颇能洁秀,而弱篇靡响,概乎不免。后人自矜其能,欲矫斯弊者,惟宜盛其才情,不必废此简格,发其幽渺,岂得荡然律吕,不意一时师心诡貌,惟求自别于前人,不顾见笑于来祀。[16]378—379
陈子龙在此诗序中首先对七子的文坛贡献做了肯定,认为他们“功不可掩”,诗学宗尚也不能否定。随后他对七子创作方面的不足逐一点评,如他认为七子“摹拟之功多,而天然之资少”,见解十分精辟,抓住了七子诗学的理论软肋。而“意主博大,差减风逸,气极沉雄,未能深永”则说出七子诗歌风格方面的缺憾。陈子龙还对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的诗歌作了评点,评点准确概括了他们诗歌的优点与缺点,反映了他自觉的批判意识和深博的诗学修养。陈子龙对何景明的诗歌十分赞赏,认为“颇能洁秀”,这也是他诗歌多学何景明的原因。陈子龙的创新意识也十分强烈,“惟求自别于前人,不顾见笑于来祀”,反映了他自主创造,追求个性的诗歌创造精神。
陈子龙的创新精神其实多学何景明,在七子中,他的歌行学步何景明,受其影响最大。同样是“诗必盛唐”,李梦阳与何景明有很大的不同,《明史·文苑》列传174中说:“梦阳主摹仿,景明则主创造,各树坚垒不相下,两人交游亦遂分左右袒。说者谓景明之才本逊梦阳,而其诗秀逸稳称,视梦阳反为过之。”[4]7350七子诗学的弊端一是多剽窃模拟,第二则是创作雷同。七子诗学对诗人才思束缚太多,学习古人,却丢失了诗人个性风格,难免出现东施效颦的结果。叶燮在《原诗》中曾对七子诗学有一段评价:
昔李攀龙袭汉、魏古诗乐府,易一、二字便居为己作……五十年前,诗家群宗嘉隆七子之学,其学五古必汉、魏,七古及诸体必盛唐。於是以体裁、声调、气象、格力诸法,著为定则,作诗者动以数者律之,勿许稍越乎此。又凡使事、用句、用字,亦皆有一成之规,不可以或出入。其所以绳诗者,可谓严矣。[17]571-590
在诸多规则的限制下,七子的创作如同背负着沉重的枷锁,难以自由驰骋,在诗歌创作方面,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对古人诗模仿改易,雕词琢句,并且不可避免带来千人一面的弊病。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曾说道:“追昔为诗,空同子刻意古范,铸形宿镆,而独守尺寸。仆则欲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18]575从此段话可以看出,同为学古,李梦阳以古为范,追求相似,手法死板僵化;何景明则领会神情,有变化,有创造。朱庭珍《筱园诗话》中曾说道:“有明前七子中,以何信阳为最。以信阳秀骨天成,笔意俊爽,其雅洁圆健处,非李空同所及。且持论力主创造,较空同议论,专宗摹仿,谓临帖以相似为贵,作诗亦然者,高下相去远矣。”[1]2359正是在创新精神方面,陈子龙与何景明有比较一致的追求,陈子龙才对何景明十分推崇。在《皇明诗选》中,陈子龙等选了何景明150 首诗,仅次于李攀龙(155 首),是前七子中最多的一位。在《皇明诗选》卷十“何景明”条下有以下评语:
卧子曰:“暇日与辕文论诗,辕文曰:‘李何七言律皆本于杜,李得其雄壮,何得其雅练’,此论诚知言哉。余以为李以浑直之气,行其雄壮,何以婉丽之致,追其雅练,故人见李之袭,以何为脱耳。”[13]687
陈子龙正是秉承何景明“力主创造”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摆脱古人的束缚,创作出富有时代精神和自我个性的诗篇。陈子龙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这种创作理念也深受何景明诗歌的影响。何景明的诗歌中有很多反映社会现实、民生疾苦的作品,如《玄明宫行》《元日》等讽刺统治者的奢侈和荒淫,《官仓行》《岁晏行》等诗揭露了豪强地主横征暴敛以致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何景明的此类诗歌直接来源于现实生活,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与模仿古人有了本质区别。
陈子龙学古而不拟古,不以似古为高,而主张诗歌要有个性风貌。其创作继承了现实主义精神,他的不少作品感慨时事,关心民生,沉雄豪迈,七律与歌行尤其出色。陈子龙在《仿佛楼诗稿序》中说:
盖诗之道,不必专意为同,亦不必强求其异。既生古人之后,其体格之雅,音调之美,此前哲之所已备,无可独造也。至于色彩之鲜萎,丰姿之妍拙,寄寓之有浅深,此天致人工,各不相借也。[16]378-379
陈子龙认为在诗歌的体格、音调方面,古人已经做得相当完善。诗歌风尚也不必强求一致,后代诗人可在以辞藻、内容方面再加以开拓,融冶自我性情,形成自己的风格。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三中说:“(吴兆骞与)陈卧子之黄门集,俱能原本七子,而自出精神者”[19]80,对陈子龙诗歌创新精神赞赏有加。陈子龙也主张诗歌要反映社会现实,要抒发内心的真实感情。他对诗歌的情感与文采同样重视,学习古诗十九首的“感时哀世”“清新醇厚”,也注重学习曹植“辞采华茂”的华丽。他在《佩月堂诗稿序》中说道:
予读之而叹曰:思深哉!其有情也,晔乎其有文也。……盖词非意则无所动,汤而盼倩不生意,非词则无所附丽,而姿制不立。此如形神既离,则一为游气,一为腐材,均不可用。夫三代以后之作者,情莫深于十九首,文莫盛于陈思王。[16]380-381
陈子龙极为赞叹“民间之诗”,认为它们来源于现实的劳动生活,抒发“劳苦怨慕”之情,文辞“婉丽而隽永”,是诗歌创作的典范。而后世之诗,由于作者缺乏丰富的生活体验,诗歌往往在内容与文采方面呈现“形神分离”的状态,不能与古诗相提并论。陈子龙早期创作的大量诗歌,例如《小车行》《卖儿行》等作品,还创作了《拟古诗十九首》,虽然走的是复古路线,但仍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陈子龙生活在一个充满灾荒与战乱的时代,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他对政局时事格外关心,对普通民众的生活也十分关注。他用诗歌来表现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真实感受,在诗歌内容上较之七子的模拟翻新已经有了一个质变,所以其诗歌中多爱国思想、英雄之气。他在《三子诗选序》说:
当五六年之间,天下兵大起,破军杀将,无日不见告,故其诗多忧愤念乱之言焉。然以先朝躬秉大德,天下归仁,以为庶几可销阳九之阨,故又多恻隐望治之旨焉。念乱,则其言切而多思;望治,故其辞深而不迫,斯则三子之所为诗也。[16]424
正是社会的沧桑巨变,以及陈子龙对国家、对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腔热血,使陈子龙诗歌既有丰富深刻的内容,又有悲壮慷慨的风格。陈子龙的诗歌题材广泛涉及了社会的各个层面,朝廷政治,民生疾苦都有涉及,如《今年行》《辽事杂诗八首》《群盗》等诗,写明末的宦官专权,明清战事,明末的农民起义等,从多侧面反映了明清之际的社会面貌。
陈子龙的创新精神还体现在他对诗歌文体的自觉认识,特别是在歌行方面。陈子龙认为在七子效法的各种诗体中,五律、七律等诗体已经比较完备,后人难有创新,只有七言长篇(即歌行)还有发挥的空间。陈维崧之子陈履端在《湖海楼诗集序》中说:“曾记卷首有云间蒋大鸿先生序文,又有先生蝇头细楷朱评云:‘忆昔陈黄门先生语余,自嘉靖七子以来,诗家各体变态略尽,独七言长篇,尚多境地,将来才人差足自展,窃以望之子辈。’”[20]4-5从此段话可以看出,陈子龙对诗体的演变有着清醒的认识,力求在歌行创作方面能超越前人,提倡歌行诗创作,希望能够自成一家。在歌行的宗尚方面,不同于何景明主学初唐四杰,陈子龙转益多师,广泛学习前代(主要是唐代)歌行诗人的艺术手法,并且要在学习模仿之中,形成自己的风格。陈子龙在《六子诗序》中曾说:
七言古诗,初唐四家,极为靡沓。元和而后,亦无足观。所可法者,少陵之雄健低昂,供奉之轻扬飘举,李颀之隽逸婉妍。然学甫者近拙,学白者近俗,学颀者近弱,要之体兼风雅,意主深劲是为工耳。[16]373
陈子龙对唐代的歌行诗人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初唐四杰和元、白不太欣赏,推崇杜甫、李白、李颀,以“体兼风雅,意主深劲”为美学宗旨,反映了他在歌行艺术方面的不懈探索。陈子龙在以后的创作中,就创作了很多歌行,在前人较少涉足的领域,开始拓展新的创作空间。正因为陈子龙在歌行诗方面的努力,他的歌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朱笠亭在《明诗钞》中说:“七言古诗,杜诗出以沉郁,故善为顿挫;李诗出以飘逸,故善为纵横。卧子兼而有之,其章法意境似杜,其色泽才气似李。”[11]782李雯在《属玉堂集序》中说:“以乐府古诗论之,曹孟德雄而不英,曹子桓英而不雄,而子建独兼之。以唐诗言之,则高达夫雄而不英,李颀英而不雄,王右丞则英中之雄,王龙标则雄中之英,而子美独兼之。此卧子之才,纵横间出,凡此诸家,命意即合,而独于二子深有宗尚也。”[11]763李雯所说古诗,绝大多数即歌行,陈子龙乐府诗学曹植,而歌行取法高适、李颀、王维、王昌龄、杜甫诸家,主学杜甫。朱彝尊在《明诗综》中说:“卧子五古初尚汉魏,中学三谢,近相见,辄讽太白诸篇。其才性故与相近。七古直兼高、岑、李颀之风轨,视长安、帝京更进一格。”[6]3697陈子龙歌行兼采众家之长,一方面多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另一方面也注重诗歌的辞采与格律,因此他的歌行既有“诗史”特征,又有“沉雄瑰丽”特色。
陈子龙不仅在诗歌理论方面,倡导歌行创作,而且身体力行,以富有成就的创作引领了诗坛歌行创作的风气。陈子龙的叙事诗有“诗史”之誉,施蜇存、马祖熙在《陈子龙诗集》前言中评论道:
在崇祯、弘光两朝中,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都在他的诗歌中有所反映,现存的诗歌,虽然是经过兵燹和长期禁锢后幸存的部分,但仅就这些诗来看,称之为史诗,也并未过誉。[11]2
陈子龙的叙事诗多数为歌行体,诗歌多反映了明朝的军国大事,特别是明清之间的战事,如《登州行》《收登行》《悲济南》《大梁行》《檀州乐》等。如《登州行》反映了崇祯四年孔有德叛乱的始末,《悲济南》写崇祯十二年清军攻陷济南。陈子龙的歌行诗除了写军国大事,明清战争,还揭露了当时朝廷内部宦官专权、勾心斗角的黑幕。陈子龙早年参加复社,坚持同魏忠贤阉党作斗争,对黑暗腐败的朝政非常愤慨。陈子龙表现天启、崇祯朝政治黑暗的歌行作品,如《白靴校尉行》《策勋府行》等。这些歌行作品从不同角度批判了明朝贤良不分、黑白颠倒的官场现实。陈子龙的“诗史”创作,以史书的“实录”精神,反映了众多历史事件,在叙事中,采用了多种叙事手法,有时在叙事中穿插议论成分,具有“史评”倾向。特别是他的歌行体叙事诗,别具一格,在叙事之中贯穿忧国忧民的深厚情感,格调雄浑悲壮。此方面的研究论文可参考拙文《“诗史”中的雄浑之笔—论陈子龙歌行体叙事诗》。①姜克滨《“诗史”中的雄浑之笔——论陈子龙歌行体叙事诗》,《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43-49页。
陈子龙歌行也有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他秉承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在模仿古诗之中,自出新意,取得了较高成就,此方面的代表作品如《小车行》:
小车班班黄尘晚,夫为推,妇为輓。出门茫然何所之?青青者榆疗我饥。愿得乐土共哺糜。风吹黄蒿,望见垣堵,中有主人当饲汝。叩门无人室无釜,踯躅空巷泪如雨。[11]85
《小车行》作于崇祯十年,饥民因大早四处流亡,诗歌反映了当时民不聊生的图景。诗歌展示了一个灾荒场景,在黄昏的路上,尘土飞扬,一对夫妇在逃难途中。“空巷”之描写,言近旨远,含蓄写出了崇祯年间饥荒遍野,饿殍成群的悲惨景象。作者亲睹饥民流离失所之状,以极简省的笔墨描绘了当时人民的悲惨处境。沈德潜《明诗别裁集》评曰:“写流人情事,恐郑监门亦不能绘。”[14]144
陈子龙对七子诗学的扬弃,对盛唐诸诗人多方面的借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对歌行诗的倡导,影响了云间诗人,对歌行诗体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王士禛在《香祖笔记》卷二中评曰:“然余观其(陈子龙)七言,殊不止此……沉雄瑰丽,近代作者,未见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时瑜、亮,独有梅村耳。”[21]陈子龙作为“云间派”的领军人物,他的歌行创作带动了歌行诗的创作风潮,陈子龙所代表的“云间派”歌行创作,与吴伟业的“梅村体”歌行并驾齐驱,对清初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