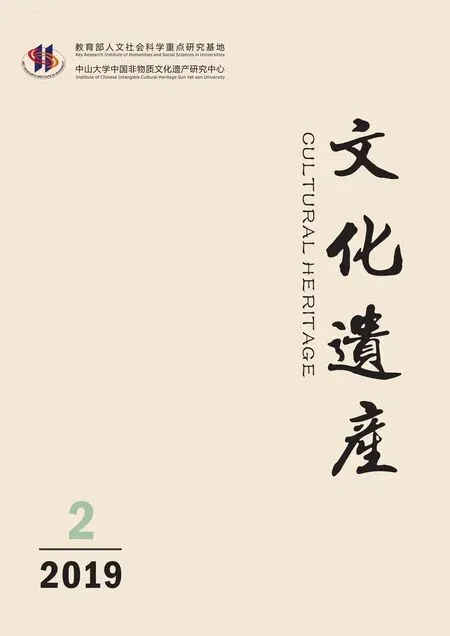中华工匠精神的渊源与流变*
石 琳
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工匠精神”,一时间“工匠精神”成为社会和学界热议的话题。截至2019年2月17日以“工匠精神”为主题词在知网搜索,文章总量已达14600余篇(见表1)。人们对工匠精神研究和认识已经进入一个历史新阶段。
目前学界对我国工匠精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匠精神本体含义,中外工匠精神对比评价,及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等,这些研究丰富了工匠精神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推动了其传播与发展。然而,目前一部分学者在研究中,一味推崇古代工匠在精美绝伦器物设计制造技艺中表现出的工匠精神,呼吁当代应回归传统工匠精神。相反,也有些学者则对中华传统工匠精神持否定态度,以任大刚为代表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古代并没有工匠精神。事实上,在浩瀚且历史久远的工匠文化世界中,我国工匠精神的流变具有系统性与复杂性,绝不能一概而论。基于此,本文将系统梳理我国工匠精神的历史背景及流变,对比古今工匠精神异同及成因,对传统与现代工匠精神进行解读。
表1截止2019年2月17日,在知网数据库以“工匠精神”为主题词检索到的论文年度数量分布
一、古代工匠社会地位的优越性与工匠精神的溯源
(一)“圣人创物”工匠精神的起源
中国上古燧人氏钻木取火,皇帝作釜甑,伏羲氏作宫室,轩辕氏造车,史黄作图等皆体现出“圣人创物”的基本观念。从创物的层面看,这些圣人都是“匠人”。创物的“物”不仅仅指物质层面的建筑、器具、车等,还包括精神层面的文字、图等。[注]邹其昌:《工匠文化与人类文明》,《上海文化》2018年第10期。更值得注意的是上古神话中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娲,在汉代落实到具体形象时,他们除了繁衍子孙外,“女娲持规,伏羲规矩”,他们手中所握制图工具,象征着为子孙立规矩,建制度。[注]张良皋:《匠学七说》,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第192页。“东方太皞,执规而治春,南方炎帝执衡而治夏,中央皇帝执绳而治四方,西方少昊执矩而治秋,北方颛顼执权而治冬。”[注]刘 安:《淮南子》,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9页。上古圣人对工具的崇拜,关注的是国民生计,本质上是一种圣人创物、救世的工匠精神。正如《周礼·考工记》载“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这种精神在工匠文化的历史沿革中,演变成一种圣人创物之道,并赋予具体圣人偶像,诸如造物精湛的偶像——“鲁班”,文化教化的偶像——“仓颉”等。
(二)“工商食官”制度与系官工匠社会地位的保障
夏代手工业主要由王室、部落或氏族、私人手工业三种类型。其中,王室手工业设置“司工”来管理各部落手工业[注]常淑敏:《殷墟的手工业遗存与卜辞“司工”“多工”及“百工”释义》,《江汉考古》2017年第3期。,司工下设专门管理工匠的官员,如车正、陶正等;部落手工业以家庭工匠生产模式为主,工匠劳动所得大部分交给部落,再由部落将一部分上交王室,一部分留作本部落贵族使用[注]魏明孔:《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先秦秦汉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页。。这种产品分配制度与夏代推行的“贡赋制度”相一致[注]曾宪年:《〈尚书·禹贡〉:我国远古时期赋税制度的萌芽》,《武陵学刊》2011年第5期。。从史料《夏书·胤征》“工执艺事以谏”与《考工记》中“夏后氏上匠”等可以看出,当时工匠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一定的发言权。随着考古发掘推进,一些新石器后期墓葬出土了大量手工工具,从随葬品的种类、数量及等级可以判定,墓主人生前为手工业者,并且社会地位要比普通氏族成员要高[注]李友谋:《我国的原始手工业》,《史学月刊》1983年第1期。。
通过墓葬考古发掘分析,发现商代已经形成工匠世袭制度[注]肖 楠: 《试论卜辞中的“工”与“百工”》,《考古》1981年第3期。。学者在商代的工匠等级、工种研究中多有争辩。根据甲骨文、金文的考古,我们发现“司工、百工、多工”等“工”字词汇多次出现,许多学者认为这些工匠指代工匠的管理者[注]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519页。;也有学者认为“司工”为工匠管理者,“百工”“多工”为普通工匠[注]常淑敏:《殷墟的手工业遗存与卜辞“司工”“多工”及“百工”释义》,《江汉考古》2017年第3期。;“多工、我工”为奴隶主所拥有的工奴[注]肖 楠:《试论卜辞中的“工”与“百工”》,《考古》1981年第3期。;根据甲骨文中“取工、丧工、执工”逃亡或被用来祭祀的记载,他们很有可能就是当时的工奴等[注]韩香花:《史前至夏商时期中原地区手工业研究》,郑州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99页。。甲骨文和《易·卦爻》中记载了关于宫阙、衣服、皮革、车、兵器制造等工种的存在[注]祝慈寿:《中国古代工业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年,第105-106页。。结合考古和众多学者的研究,目前学者普遍认为商代除了王室贵族所奴役的工奴外,大多数工匠仍具有人身自由[注]魏明孔:《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先秦秦汉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33页。。
西周为了进一步规范手工业管理,设置“司市”官职监管手工产品的质量[注]侯家驹:《中国经济史》上册,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84-89页。,设立“司空”总领“百工”,“百工”由“车人、玉人、梓师……”等组成,负责具体手工作坊。工匠要居于官府,生产贵族所需要的手工产品,即“工商食官”[注]邱树森、陈振江:《新编中国通史》第1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2页。。这种制度奠定了官府手工工匠地位。“工部族居,不足以给官”[注](晋)皇甫谧撰,(清)宋翔凤、钱宝塘辑,刘晓东校点:《逸周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2页。。“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注](春秋)左丘明著,罗家湘注译:《国语》,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7-138页。。此时工匠职业世袭已经明确。
春秋中后期“井田制”“工商食官”制度相继瓦解,越来越多人从事私田的耕种和手工业生产[注]刘东升:《试论井田制的瓦解》,《科教文汇》(上半月)2006年第4期。,官府手工业与家庭手工业并存局面开始形成。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统治者担心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会威胁到自身经济和政治地位,诸如齐桓公思考“吾欲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为此有道乎?”[注](春秋)管仲撰,吴文涛、张善良编著:《管子》,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541页。,采取“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注](战国)商鞅著,(战国)韩非著,张党点校:《商君书》,长沙:岳麓书社1990年,第47页。措施,以达到“重农抑商”的目的。基于此,为了更好的管理私营手工业者,各国设置了“市籍”对手工业者登记来进行监督管理[注]中华书局编辑部:《云梦秦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年,第226页。。整个周代官府手工业专业手工工匠、雇佣手工工匠在依附于官府的同时,仍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甚至没有徭役、兵役。
二、古代工匠社会地位的跌落与工匠精神流变
(一)“重农抑末”的推行与工匠人身地位的转变
秦统一六国后,将大手工业主“迁”或“谪戌”,即没收手工业经营者大部分财产,或将他们迁移到外地。并对手工业经营者“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注](汉)桓宽:《盐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5页。,用沉重的赋税来抑制手工业发展,致使整个秦代官府手工业发展比私营手工业发展强劲。秦代官府手工业生产采取“物勒工名”制度,已经以律法的形式在秦《工律》《司空律》等律例中出现[注]梁安和:《试议秦的“物勒工名”制度》,《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而且秦代手工业生产管理机构已具备上层服务王室的内史、少府、将作少府等,中层负责官府管理的考工室、左右司空等,下到负责具体生产的百工、隶徒工匠编制系统[注](东汉)班固:《汉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91-295页。。这一系统中除刑徒、官府奴婢社会地位低下、无偿劳动之外,工师及工匠仍有一定的收入和人身自由,但在秦代严苛的律例下,对工匠整体管理及产品质量、数量都受到严格控制,这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自由[注]高敏:《秦汉时期的官私手工业》,《南都学坛》1991年第2期。。
汉初工匠的管理制度一改秦代重税政策,实行“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汉惠帝实行“驰商贾之律”[注](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51页。,使汉代工商业发展环境得到改善。汉武帝时,工商业经济发展与封建政权之间的矛盾再一次加剧。统治者推行禁榷政策来垄断盐、铁、酒等行业,实施“算缗钱”的税收政策,控制工商业发展,并且要求商人加入“市籍”。官府这一系列“重农抑末”经济措施直接导致了工匠收入减少及社会地位降低[注]刘国良:《中国工业史》古代卷,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215-234页。。民间工匠中有一部分被大私营手工业主雇佣,这些工匠往往出身贫苦,靠出卖手工技艺来维持生计,从“潜谴贫人能缝者,佣作贼衣”[注](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867页。,蕲县人施延“家贫母老,周流佣赁”[注](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第1558页。,及申屠蟠“家贫,庸为漆工”[注](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第1751页。可见一斑。此外,私营手工业工场中工场主还通过买奴婢来为其劳作,这些奴婢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且始终作为主人的私有财产[注]郝春文:《关于汉代奴婢问题的一些看法—与林剑鸣先生商榷》,《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7年第3期。。
(二)番役、匠籍的雏形与工匠社会地位的跌落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争灾祸不断,各个时期官府对手工业采取严格管理与控制,工匠社会地位极其卑微。如三国时,工匠不能与庶民等阶层在一块居住,《魏书·韩麒麟传附韩显宗传》道“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沽,各有攸处”[注](北齐)魏收撰,许嘉璐主编,周国林分史主编:《二十四史全译·魏书》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1110页。,甚至直接被排除良民之列。西晋通过法律形式规定“百工”为卑贱职业,对工匠出行、服装等皆有严格限制[注](清)严可均:《全晋文》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570-1571页。。东晋时期,工匠除了承受沉重徭役,服役期间若死亡,要其家人代役,即便无家人,须用刑徒代役[注](唐)房乔:《二十四史·晋书》,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南朝“番役”及南齐“番假”制度[注](梁)萧子显撰,许嘉璐主编,杨忠分史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南齐书》,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67页。,要求工匠按时间定期服役。发展到北周“番役”制度规定“役丁为十二番,匠则六番”[注]王咨臣等译:《历代食货志今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4页。,即普通劳役者12个月需要在官府服役1个月,而工匠要6个月在官府服役1个月,工匠服役时间要比普通劳役者服役时间更长。民间手工工匠在大手工业地主的奴役下,“耕当问奴,织当访婢”的现象普遍存在[注](梁)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99页。。
唐代系官工匠主要由奴婢、番匠、和雇工匠三种类型组成。其中,官奴婢劳作基本没有经济回报,人身自由受到很大限制,并且身份地位低下;而番匠仍延续隋代每年两月服役惯例,并通过“团貌”制度保证工匠按时服役;中唐后“和雇工匠”制度、“以资代役”制度流行,和雇工匠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好转[注]魏明孔:《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5-383页。。工匠实际生产中“造弓矢长刀,官为立样,仍题工人姓名,然后听鬻之;诸器物亦如之。以伪滥之物交易者,没官;短狭不中量者,还主。”[注](唐)张九龄等原著,袁文兴、潘寅生主编:《唐六典全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41页。“立样”和“物勒工名”等方式监督产品质量进一步完善。隋代“工商不得仕进”[注](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5550页。,唐太宗时“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注]许嘉璐主编,黄永年分史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3953页。,从仕途上遏制工匠社会地位改变。此外,官府只供给奴婢、刑徒工匠衣食物,而短番匠在上番期间没有报酬,只有雇匠雇佣期间才有一定的报酬,但受雇仍是义务,并不具有自由选择权[注]祝慈寿:《中国古代工业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年,第356页。。两朝工匠社会地位极其卑微,并且工匠过着“通计工匠,率多贫窭,朝驱暮役,劳筋苦骨,箪食瓢饮,晨炊星饭,饥渴所致,疾疹交集”的困苦生活[注]许嘉璐主编,黄永年分史主编:《二十四史全译 ·旧唐书》,第2600页。。
(三)匠籍制度的演化与工匠受剥削的加剧
宋代官府对工匠施行“雇募制”,即雇募期间官府给予工匠一定的雇值。但在实际操作中应募者的雇值远远低于市场,并且人身境况恶劣至极。“若依市价,即费钱多,那得许钱给与”[注](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441页。,“和雇工匠,雇值多不时给”[注](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第11746页。,并且强制、虐待层出不穷,致使北宋“以和雇为名,强役工匠,非法残害,死者甚众”[注](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第8502页。。而南宋工匠遭受压榨、奴役更甚。因此,工匠“逃走、疾病、死亡,殆无虚日”[注](清)徐松加:《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726页。。民间手工业虽然形成了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业组织——“行会”,但官府以估价、征役的形式对其管理,强制从业者加入行会,才能获得经营本行业[注](宋)郑侠原著,郑宛华重刊:《西塘集》,郑州:郑氏文化研究会1993年,第5页。。总之,总体上看,宋代工匠管理制度在对工匠的生活和人身自由管理上,较前朝有一定改进。但是实际操作上工匠却面临着沉重剥削,以南宋为例,工匠在现实生活中仅能达到温饱水平。[注]侯家驹:《中国经济史》下册,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510-512页。
元代将全国人口通过户籍的形式进行管理,规定工匠划入匠籍不能脱籍,并且世袭,元代户名多达上百种,而手工业工匠主要分布在军户、民户、匠户之中。官府工匠在服役期间,政府给予工值和衣食,课余时间允许私造私营,较前朝工匠待遇有很大改善。但元代工匠在服役中仍然面临严酷压榨,“不时之需,谓之横造”的额外任务,所属匠官“每影占者匠人每”,“又科要钱有”,更有“一局之内,不下一二百人,并无俸给,止是捕风捉影,蚕食匠户”,致使“匠户贫窭尤甚”,“计无所出,必至逃亡,今已十亡二三,延之数年,逃亡殆尽矣”[注](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37页。。相比系官工匠,民户工匠则相对自由,并且可以自由流动,凭借手艺自由受雇,以获取雇值。然而,官府工匠在不够用情况下,民匠也要面临“轮番斟酌勾唤”[注]《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紫山大全集》,第841页,网站http://skqs.guoxuedashi.com/3206s/1897843.html。。由于蒙元少数民族政权的特殊性,工匠在收入和地位得到暂时提升,但“匠籍”的实施确立了对工匠人身禁锢的开端。
明代初期对匠籍进行了“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等进一步细分,工匠服役“轮班制”与“住坐制”相继出现,从形式上来看,明代工匠人身自由及待遇比前朝有所改善。但据史料记载,轮班服役工匠疲于上工路途来回奔波,路费、食宿费用自理。工匠遭受上工之外的额外压榨、克扣雇值等较元代有过之而不及。导致大量工匠通过逃亡、消极怠工的方式来抵抗服役。(见表2)为防止工匠逃亡官府屡出律例,诸如逮问罚班、家人补班、没收田产、发配充军、处死等措施。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清代“纳银代役”工匠制度的进一步实施,清顺治年间匠籍制度实际已经名存实亡[注]清史简编编写组:《清史简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9-151页。,匠籍制度的废除,转而官府向民间召募赴工代役,代之以雇募制、计工给值的匠役制度。随着官营手工业官员腐败、工匠在服役期间受剥削严重,官营手工业发展缺乏动力,最终走向没落。

时间宣德元年(1426)正统三年(1438)正统十年(1445)景泰元年(1450)天顺四年(1460)成化元年(1465)工匠逃亡人数(万)0.50.4513.483.841.85
表2 (数据摘自《手工业经济史·明代卷》107页)
(四)工匠人身境况与工匠精神关系
通过对工匠人身境况梳理可看出先秦时期工匠不但具有人身自由,并且还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与《考工记》中记载的“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注](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114页。,不谋而合。而秦汉至明清工匠长期属于社会的弱势阶层。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在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社会中,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而采取的“重农抑末”经济政策,手工业长期处于统治者打压的环境中;“士”(贵族、知识分子等)与“匠”(工匠),“学”(科举考试相关的诗文、辞赋等知识)与“术”(技术、技巧等)的分离等。致使工匠始终被排斥在政治权利和知识权利之外。由秦汉到明清,古代“工匠精神”本质上来说是由两种路径共同促成的:一是由官府、行会、作坊等社会环境和传承方式所形成的“外化”路径;二是工匠这一职业群体对上古“圣人创物”之道的内省心理而造就的“内化”路径。抑或说,传统工匠在阶级社会政治、经济、人身等外部环境压迫与工匠自省心理等相互作用下,不断重复实践中产生了稳定的工作态度和价值观。这种态度和价值观就是传统工匠精神。这种“工匠精神”既有为满足王公贵族需求所表现出的对造物精益求精,巧夺天工的“工匠精神”;也有为完成政府赋税、徭役所秉持的恪尽职守,吃苦耐劳的“工匠精神”;还有为维持生计、养家糊口,表现出的追求实用、求真务实的“工匠精神”。
三、古今工匠精神的对比与重生
不管是传统手工工匠,还是当代“机械工匠”“数字工匠”,他们都是人类物质与精神文明的缔造者,也是工匠精神最直接的代表。时代发展中由于宏观层面中社会分层、社会组织形式变化,以及微观层面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传统与现代工匠所呈现出的工匠精神存在明显差异。工匠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定义主要是指“具有专业技艺特长的手工业劳动者”[注]余同元:《中国传统工匠现代转型问题研究》,复旦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8页。。而当代工匠定义更具广泛性,美国学者理查德·桑纳特认为“匠艺活动其实是一种持久的、基本的人性冲动,是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欲望”[注][美]理查德·桑内特:《匠人》,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12页。。 因此,人们将任何工作或活动当做一门手艺,主动努力的去实现目标的人,都可以称之为“工匠”。古今工匠所表现出的工匠精神,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其传承及成因上却大相径庭。
(一)古今工匠服务群体差异——贵族与民众
我国古代官营手工业生产,大多是不计成本、材料、工时的生产活动。“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注]王利器:《盐铁论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6页。。“时内府供用日繁,守备分守中官布列天下,率以进奉为名,糜帑纳贿,动以巨万计。而江西浮梁之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尤多,且久费不赀。”[注](清)夏燮:《明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17页。。官府手工业的匠艺活动主要以满足统治阶级享受为第一要务,这种背景下的工匠精神,并不是以节约资源、工时下的精益求精,而是任务式的执行命令。
18世纪工业革命后,机器批量生产得以实现,人的双手得到解放,手工工匠为主的时代逐渐示弱。1919年德国包豪斯的成立,一股带有民主性、社会性的设计实践、设计教育活动迅速推广开来。设计服务由向专有贵族服务,转变为向大众服务。设计制造活动既要考虑成本,又要在考虑人机工学、艺术、技术、生态环境、用户体验等等前提下,努力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以服务大众为宗旨。民主、文明环境下的工匠精神具有明显的使命感。
(二)古今工匠人身自由、社会地位变化——被动与主动
秦代的“迁” “谪戌”,汉、魏晋时期的市籍、匠籍,唐代“番匠”,宋代工匠的“按籍轮转”,元代的“匠籍”及明代“轮班制”“住坐制”,目的是为了使工匠更好地服务统治者。而魏晋对工匠人身地位的贬低,隋唐限制工匠入仕等,工匠始终远离政治、文化权利中心。以及宋、元、明、清四代工匠遭受的盘剥,古代工匠在二千年来始终处于社会底层。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变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成为了我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在法律层面,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摒弃了旧社会将人民划分为三教九流的陋习,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职工拥有的各项权利和义务。政府层面上,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对建设“大国工匠”给予肯定和指导。《我在故宫修文物》《大国工匠》《了不起的匠人》《留着手艺》《上海工匠》《手艺》《指尖上的传承》等节目的陆续录播,推动了工匠精神在民间的推广和传播。
古代工匠一直在被压迫、被奴役的环境中从事匠艺活动,这种环境下所逐渐形成的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在统治阶级逼迫下产生的,带有明显的被动性。而在当代平等、民主社会的工作环境中,工匠精神是作为一种职业态度或价值追求,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精神驱动力,来为社会服务。
(三)古今匠艺活动中监督考核流变——匠人内省与职业信仰
古代匠艺活动的考核体系中,匠人自身的职业素养上,要遵守的“由圣人而是崇”和“体圣明之所作”,其体现的是“依于法而游于艺”,即工匠在劳作中要做到“重道、求道与体道”,学习先人的匠艺哲学宗旨。同时,也要遵循“按乃度程”“毋作淫巧”的生产技术准则和要求[注]余同元:《中国传统工匠现代转型问题研究》,复旦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8页。。在生产实践活动环节,工匠须“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工师效工”要求工师作为监工,按照技术标准对工匠制作的产品进行监督管理;“物勒工名”制度要求工匠在器物上铭刻自己的姓名,以备工师检查,如若发现产品存在问题,工匠将受到相应的处罚。这种考核体系可以概括为:以圣人之道为匠人自省,人(工师)与法(物勒工铭)为主制度监督体制,共同建构的古代工匠的监督考核体系。
在当今设计、生产等实践各个环节中,根据行业特点,设置了不同层次的系统性监督管理机制,如企业内部的技术、质量、销售、服务监督制度,市场流通层面的销售监督管理政策,以及服务跟踪机制。总之,现代造物活动监督考核体系以科学为依据,以政策、法规为保障,集全面系统的监督、管理、服务为一体的考核体系,这是对古代依靠人与法监督体制的进一步推进。面对当今频发的产品质量、工匠职业道德等,推行更加严格的科学、系统的考核措施之余,古代工匠的自我考核和内省,亟待我们学习和借鉴。
(四)古今工匠精神的培育路径——保守与兼容
工匠精神的形成和传承,从文化心理学分析看,主要由“外化”与“内化”两种路径相互作用产生的。古代工匠精神的“外化”,主要是以家族、官府、行会为载体来展开工匠精神培育与传承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师徒传承,口传心授,亲身实践”方式,带有“秘而不宣”的民俗约定,这主要是因为工匠自身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会,也不能将视作“看家绝活”的技术知识文本化,这关乎自身在行业内的竞争力和生存。
古代工匠精神的“内化”,是在工匠持续的匠艺活动中,通过不断的造物经验与工匠知识的积累,构建起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工作态度、信仰。古代工匠精神传承路径上的几世一业,很大程度上是由官府行为(匠籍、匠户、徭役等)来强制实现,从人的社会发展角度看,是对人的压迫和约束,带有明显的局限性。然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强制对工匠技艺的传承,对实现古代工匠遵从圣人创物之道,为对匠人自省的心理内化与体验,实现工匠精神内化,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抑或说传统工匠精神的培育,本质上是由内化路径:工匠自我心理机制——圣人之道的匠人自省;外化路径:官府、行会、家族等环境下——家传式和学徒式,相互作用的产物。
而当今不管是“手工工匠”“机械工匠”还是“数字工匠”,其工匠精神的培育,需要其成长的工匠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是工匠精神确立的基础和生长的生态环境。当代工匠文化生态环境营造更多强调文化性、开放性、创新性,推崇理论与实践结合,将工匠文化根植于家庭、学校、企业、社会等。工匠人才培育由传统经验型、技术型工匠向知识型、科学型工匠转变,由迫于生计向个人职业追求转变,由作坊传播向学校、企业传播转变。我国工匠精神由外在逼迫和内在自省结合下的传统“工匠精神”,向兼容并包、民主文明的现代化教育和主动追求精益求精、求实创新的工作学习态度、信仰相结合下的现代“工匠精神”转变。
结 语
我国传统工匠在古代重农抑商的自然经济社会中,处于下层阶级,其人身处境差,社会地位低;军户、匠户、灶户等户籍制度的实施与徭役、赋税的征发,使工匠人身自由和职业变动受到很大限制,且长期受到统治者的严酷剥削。传统工匠精神的产生、传承和发展,是在统治者压迫下,匠人不得不依靠匠艺活动维持自身生计,同时背负家族荣誉、国家任务等众多层面的背景下被逼迫的产物,或者说传统工匠精神是在历史时代环境下倒逼产生的。
传统工匠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强调的是“现实层”,抑或说“一种工匠本位的精神,而不是其他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本位是内在于工匠的性质、领域或世界之中的”;而当今工匠精神更多的是强调“工匠精神”的“超越层”,“这个超越性层面已不再落实到具体的工匠活动领域,而是一种人生价值信仰、一种生存方式、一种工作态度,也就是马克思所说‘一种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认’境界。”[注]邹其昌:《论中华工匠文化体系—中华工匠文化体系研究系列之一》,《艺术探索》2016年第5期。所以说我们对传统工匠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并不是单单针对传统工匠精神“现实层”所体现出来的工匠本位状态下的工匠精神,或者说其制作过程、器物文化所体现出来的工匠精神。“以万人之功”的旧有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已不适合当代社会发展。当今我们所传承和发扬的是工匠精神更多的是“超越层”所体现出来的工匠精神,作为一种信仰、生存方式、工作态度,所强调的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恪尽职守、求真务实、精益求精、求实创新的方式或原则,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新时代“中国精神”的表现[注]陈国平:《价值与意义:中国道路自信生成之源》,《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为了把事情做好而好好工作的欲望”的工匠精神及其所推动的匠艺活动,是建立在积极主动的行为之上,这与古代工匠精神形成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说我们在认识和发扬传统工匠精神要区别开来,不应当机械、盲目地鼓吹借鉴古代工匠精神。
总之,面对当今学界热议的我国工匠精神缺失的问题,我们需要头脑冷静,要清晰认识工匠精神的两个层面;要看到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各项事业正在逐步完善,尤其是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过渡期;也要看到中国从“手工工匠时代”向“机器工匠时代”、“数字工匠时代”跨越期短,当前国家物质文化水平、精神文化水平仍需要长时间积累的现状;更要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工匠精神培育路径中的精髓和糟粕,尤其是当今社会各项事业中“超越层”工匠精神缺失的问题,及传统工匠精神的历史演变与现代化转型的特质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掌握工匠精神培育外化路径的系统化创设,也要学会内化路径建构,两者不断地相互融合才能实现当今工匠精神的培育与传承,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立足实际,正确传承和发扬本国工匠文化,向“中国制造2025”迈进,向“美好生活”建设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