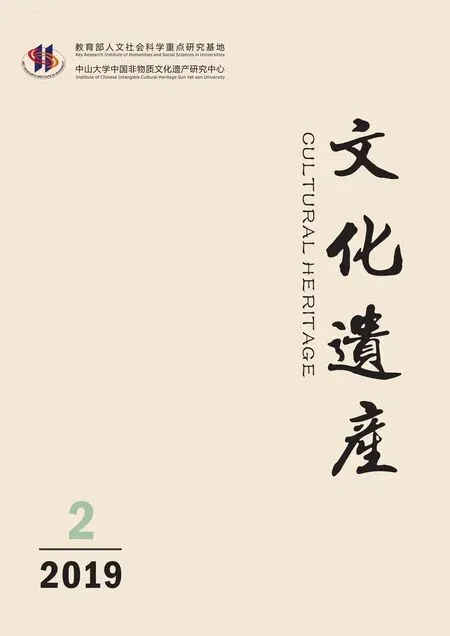《西游记》杂剧作者献疑
杜治伟 王进驹
今见《西游记》杂剧凡六本二十四出,系盐谷温先生1928年在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发现。这本杂剧,由于在原本上署有“元吴昌龄撰”的字样,而《录鬼簿》中吴昌龄名下恰录有《西天取经》,因此学界最初认定其为吴昌龄的作品。后孙楷第先生于1939年撰文,对吴昌龄与《西游记》杂剧的关系进行辨正,根据(1)天一阁抄本《录鬼簿》,吴昌龄所作《西天取经》杂剧有“回回叫佛”事,而今本《西游记》杂剧没有;(2)《录鬼簿》后附录《录鬼簿续编》,载有杨景贤《西游记》杂剧;(3)传是楼本《词谑》第二篇“词套”引杨景夏《玄奘取经》第四出,内容与今本《西游记》杂剧同;(4)杨景贤一名杨景言,“杨景夏”系“杨景言”之误。遂将此剧的作者判归元末明初的杨景贤[注]详见孙楷第《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现在所见的杨东来评本西游记杂剧不是吴昌龄作的》,《沧州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44-265页。。孙先生的考证结果很快得到了学界的普遍接受,自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游记》杂剧都与杨景贤捆绑在一起。不过,新中国成立以来,仍有不少学者陆陆续续对杨作杂剧提出了质疑。如,50年代,严敦易先生通过对文献记载及剧作内容的分析,认为《西游记》杂剧系拼凑而成的可能性较大(甚至还受到百回本《西游记》的影响)[注]严敦易:《“西游记”和古典戏曲的关系》,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西游记研究论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145-152页。。70年代,日本学者太田辰夫先生在对杂剧进行新的考辨基础上,认为其“可能是假托为吴昌龄所作,为了和当时通行的《西游记》剧乃至小说《西游记》对抗而别立一家的作品。”[注][日]太田辰夫:《西游记研究·戏曲〈西游记〉考》,王言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2页。80年代,李时人先生在追溯唐僧出身故事的渊源时,认为《西游记》杂剧原本于元代民间艺人的演出底本,杨景贤可能对之进行了加工、整理[注]李时人:《略论吴承恩〈西游记〉中的唐僧出世故事》,《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90年代,熊发恕先生专门就孙楷第先生的考证结果进行商榷,认为今存《西游记》杂剧是经过增饰的元代无名氏作品[注]熊发恕:《〈西游记杂剧〉作者及时代考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大约与此同时,在王季思先生主编的《全元戏曲》中,对杨作、吴作也表示不同程度的怀疑[注]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404-405页。。严、太田、李、熊等先生的论述虽然没有完全动摇孙先生的结论,却足以引发《西游记》杂剧写定时间及作者问题的再探讨。近年来,田同旭[注]田同旭:《〈西游记〉杂剧作者应归吴昌龄》,《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李小龙[注]李小龙:《〈西游记〉命名的来源——兼谈〈西游记〉杂剧的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等先生又分别立足于作家艺术能力、社会文化条件以及作品命名来源,认为《西游记》杂剧的作者,仍应该是吴昌龄。本文拟在前人的基础上,从故事演化的角度并结合戏曲选本,对《西游记》杂剧是否为杨景贤所作,也提供一些个人浅见。
一、取经出发前的求雨活动
在《西游记》杂剧中,玄奘取经之所以获得世俗社会的支持和认可,乃是在于他于京都求雨有验,而根据《永乐大典》所引《西游记》片段,既然明代平话本中出现了梦斩泾河龙故事,那么在取经出发前便不太可能有玄奘求雨的描写。百回本《西游记》中玄奘自白“我却不会祈雨”,这大抵表明,随着取经故事的演化,入明以后,玄奘便丧失了求雨的神通。既然如此,元本中是否存在求雨活动呢?根据《朴通事谚解》所述取经故事,观音显像之时,唐太宗正聚天下僧尼设无遮大会,此时是否是为了祈雨,不敢妄下结论,但就无遮大会的本意而言,似乎也应该与求雨活动无涉。不过元代之前的取经故事,的确应该包含求雨的内容,王振鹏《唐僧取经图册》缺题的上1,所表现的便极有可能就是揭求雨皇榜事,而其他如密宗不空、善无畏等法师,在历史上均曾有过求雨之举。这似乎说明杂剧描写的取经故事并非独立的存在,而是对某一时期取经故事的反映。《唐僧取经图册》是元代以前取经故事的结集,密宗法师的求雨活动,在唐宋时期已经广为流传,《西游记》杂剧中出现求雨的描写,是否是受到元前取经故事的影响?其与平话本相比,取经缘起部分缺少无遮大会或太宗入冥、梦斩泾河龙故事,是否又是因为其未受到平话本故事的影响所致,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二、沙和尚先于猪八戒的排序
取经队伍有一个不断壮大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取经五圣因融入取经故事的时间存在先后,因此在排序上也呈现出差异。就猪八戒和沙和尚二者而言,沙和尚本先于猪八戒加入取经队伍,故而在早期的取经故事表现中,沙和尚都排在猪八戒之前[注]甘肃天水甘谷县华盖寺释迦洞唐僧取经壁画中,无论是去程(图像从左到右依次为孙、唐、沙、马、猪)还是返程(图像从左到右依次为孙、沙、马、唐、猪),猪八戒都处在壁画的最后位置,虽然图像的绘制要考虑到布局、结构等问题,并不完全等同于取经人物的出现顺序,但一来一往的人物安排,却也足以说明在取经团队最初形成四众一马布局时,猪八戒的确处于四众的末端,居于沙和尚之后。。但根据各西游宝卷以及队戏《礼节传簿·唐三藏西天取经》可知,基本上入明之后,猪八戒便稳居沙和尚前面了。以此反观《西游记》杂剧(沙和尚先于猪八戒),这便说明,杂剧所反映的取经故事一定是元乃至元前的面貌。《朴通事谚解》所引《西游记》注释中,有“与沙和尚及黑猪精朱八戒偕往”[注]《老乞大谚解 朴通事谚解》,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第294页。的句子,似乎意在表明元代平话本中沙和尚排在猪八戒前面。常为学界所忽略的韩国敬天寺(敬天寺系由中国匠人于1348年修建,则其石塔上的浮雕应该是对元顺帝及其以前西游故事的最直接反映)“西游”故事浮雕[注]关于20幅“西游”故事浮雕的内容和研究介绍,详请参见谢明勋《西游记考论:从域外文献到文本诠释》,台北:里仁书局2015年,第3-82页。中,在石塔的东侧北面,有一幅收降沙和尚的图像(从项挂骷髅头,可以断定双手合十屈膝者为沙和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幅图像的右半部分绘有三人一马,而20幅浮雕中这也是唯一一幅涉及收降的故事,或许意在借此表明取经团队组建的完成,在此故事图谱中沙和尚最后加入取经队伍。如果敬天寺故事解读无误,那么至少说明元末已经五圣齐备,且猪八戒已经后来者居上,跃居在沙和尚之前[注]平话本《西游记》(“谚解”本)和敬天寺取经石雕时间相近,表现内容相悖,这应该与不同载体的特殊性有关。元代刊刻的平话,多是来源于说书底本,这只要翻阅《三国志平话》等就可以发现。因此,它必然是对先前取经故事的汇集,就其描写而言,多是以今之笔,记录过去演说之故事。但石雕则具有现实性,是对时代故事的直切反映。把听到的取经故事以图像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形式而言是艺术的创作,就内容而言则是跨载体的平行转移。因而,相近的时间,反映的故事内容却仍旧可能存有一定的时间差。。根据演化的规律,则必然是先“沙-猪”后“猪-沙”,如是,则《西游记》杂剧便不太可能是元末明初的产物。否则当“猪-沙”已经为人所普遍接受(雕刻匠人总是根据自己的听闻而进行创作,他们的接受正具有普遍性)的情况下,杂剧作者何以会反其道而行之,且作品中不时出现“猪-沙”“沙-猪”的混淆。合理的解释似乎只能是,杂剧是元代的产物,它体现了从“沙-猪”到“猪-沙”的过渡。又,广东省博物馆藏有元代磁州窑“取经故事”瓷枕,该瓷枕中取经五圣的排序,也是猪八戒在前,沙和尚在后。因此,杨光熙先生认为《西游记》杂剧的创作时代要早于“唐僧取经瓷枕”[注]杨光熙:《论〈西游记杂剧〉和“唐僧取经瓷枕”创作时代先后》,《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3期。。于硕又从瓷枕和杂剧插图中均有华盖这一特殊物饰,认为瓷枕与杂剧的创作时间较近,不过他本身对瓷枕的年代是否为元代,却表示怀疑[注]于硕:《唐僧取经图像研究——以寺窟图像为中心》,首都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3-74页、第38-40页。。按,于硕立论的前提是认为《西游记》杂剧为杨景贤的作品从而以之为参照,事实上这种立论依据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并没有理由否定取经瓷枕为元代的论断。现将元明不同作品中有关猪八戒、沙和尚的排序总结对比如下(见表一)[注]朱德熙先生在《‘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书后》(《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8年第2期)中认为“朴通事”当作于至正六年(1346)以后、元亡(1368)以前,则其中所引的平话本《西游记》最晚也应该写定于元代。而徐晓望先生《论〈西游记〉传播源流的南北系统——兼答蔡铁鹰先生》(《东南学术》2007年第5期)一文认为《西游记》平话诞生于福建地区,考虑到建阳地区至治间曾刊刻“讲史平话”五种,则《西游记》平话的产生甚至可以提前到元前中期。:

表一 元明不同作品中猪八戒、沙和尚先后顺序表
总之,基本可以确定为元代的作品,猪八戒出现在沙和尚后面,可以确定为元末乃至明初的作品,猪八戒排在沙和尚前面。这样看来,《西游记》杂剧倒真的可能为元代中前期的作品,其作者是否为元末明初的杨景贤便很值得怀疑了。
三、杂剧内容多取宋元旧事
不管《西游记》杂剧的作者是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杂剧故事并非作家个人的独创,而是在前人基础上的综合和删改。《西游记》杂剧共六本二十四出,包含大约十多个故事单元,且这些故事单元,多数都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系统(见表二):

表二 杂剧故事与宋元以来相关故事对应表
在这简单分列的十二个故事单元中,很少有《西游记》杂剧作者的独创,有的只是部分内容的微调,如将取经时间从元代常态的六年[注]《朴通事谚解》所引《唐僧西游记》,民间宝卷《取经道场》《西游道场》等反映平话取经故事的文本中,都明确提到取经时间为六年,因此笔者认为就取经时间而言存在一个“六年”的演化阶段。改为符合历史事实的十七年,将“朱八戒”改为“猪八戒”等等,但有些改动无伤大雅,有些则是为了切合杂剧所反映的向佛宗旨。且若将前后的取经故事作品与杂剧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便又可以发现一些端倪。以孙行者闹天宫故事为例,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简称《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西游记》杂剧、百回本《西游记》的描述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以明代百回本作为参照,《西游记》平话显然 比《西游记》杂剧在情节上更为接近。这或许与杂剧、平话两种文体的不同属性有关,但也不能排除平话在时间上更近百回本的可能。然而若以《取经诗话》作为参照,就孙悟空的居住地而言,紫云罗洞显然更近于紫云洞。并且杂剧中有鬼子母故事,平话中没有,百回本中没有,但《取经诗话》有《入鬼子母国处第九》(王振鹏《唐僧取经图册》也有鬼子母故事)。此外,杂剧中“通天大圣”的命名以及孙行者掠金鼎国女人为妻,可能受到《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的影响,而杂剧中出现的十大保人,太田辰夫先生认为开元寺雕像猴行者、东海火龙太子,六菩萨、六神将等是其前身[注][日]太田辰夫:《西游记研究》,王言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82页。。因此,就杂剧的内容而言,其在时间上当更接近于宋元故事,较少见出元以后作品的痕迹。
四、杂剧的命名和文献选录
在钟嗣成《录鬼簿》、朱权《太和正音谱》、臧晋叔《元曲选》、赵琦美《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钱曾《也是园书目》等明确记录吴昌龄及其杂剧的文献中,其杂剧都名《西天取经》或《唐三藏西天取经》。万历四十二年勾吴蕴空居士的刻本,较早的将吴昌龄与《西游记》之名联系起来。此后,关于吴昌龄所作杂剧的称谓才出现《西天取经》和《西游记》的混淆,但《西天取经》多指有回回迎僧的杂剧,《西游记》系指《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的简称。而取经故事演化的过程中,先后出现过以《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新镌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等命名的作品,就这些作品的名称而言,唐宋之时,往往出现“三藏法师”+“取经”的字眼,这既肯定故事的主人公是“三藏”法师,又强调西行取经之事。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的命名,正是对这种命名法的一种承袭。《朴通事谚解》最早出现《唐僧西游记》《西游记》(《唐僧西游记》是全称,《西游记》是简称)的名称,并且以“取经”命名,强调的是取经本身的重要意义,而以“西游记”命名,则更注重对沿途历难的描写。从这点看,《西游记》平话和《唐三藏西天取经》似乎各有侧重。《录鬼簿续编》首次在杨景贤的名下录有杂剧《西游记》(其后以《西游记》命名的剧作才开始多了起来),这至少表明杨本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西行故事,而非取经中单个片段的展示。徐渭《南词叙录》有本朝戏文《唐僧西游记》(所指不明),《宝文堂书目》乐府类下也录有《西游记》(所指不明),这说明“西游记”取代“西天取经”作为取经故事的命名愈来愈为多数人所接受。传是楼抄本《词谑》所引题名“杨景夏”的《玄奘取经》第四出,相当于现存《西游记》杂剧第一本第四出,但文字并不全同。从文字的差异可以认为今本得到过修补[注]之所以这样认为,一者今本的曲词更雅致;二者今本卷前有一首七言四句颂圣类诗,卷尾有“愿祝吾皇万万年”“祝皇图永固宁”等类颂语,显示出其内府承应本特征。,不过这种修改是杨东来先生的手笔还是此前的他人不得而知。又天启四年,止云居士《万壑清音》录存有《西游记》四出,其中《回回迎僧》《诸侯饯别》二出,根据孙楷第先生披露的天一阁抄本《录鬼簿》所录吴昌龄《西天取经》剧目有题目和正名“老回回东楼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经”,学者们普遍认为属于亡佚的吴本(部分内容);而另二出《擒贼雪仇》《收服行者》,出于今本《西游记》杂剧。这种杂烩或不符合选录者初衷。那么是否存在“擒贼雪仇-诸侯饯别-收服行者-回回迎僧”,这四出构成一本杂剧的可能呢?首先,孙先生将其中二出判为吴本有些轻率。这是因为,一者,《万壑清音》所录杂剧为《西游记》,而吴昌龄杂剧名为《唐三藏西天取经》,除了杨东来批评本《西游记》杂剧,其他收藏者很少将两名故意混淆;二者,吴本有“回回叫佛”事,但有“回回叫佛”事的未必就一定是吴本,不能排除他本有“回回叫佛”事的可能;三者,《万壑清音》的凡例云:“今则元人所作,多不选入,大都取我国朝名家最善者辑而刻之”[注](明)止云居士编:《万壑清音》(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本影印),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第四辑,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第25页。,吴本的杂剧明显与选录标准相矛盾。若果凡例之语可信,那么证明《西游记》杂剧也当是明朝的本子,至少选录者将其判断为明朝的本子。万历四十二年,《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刚问世,情钟戏曲而编辑曲选的止云居士似乎不太可能没有听闻(臧晋叔所编《元曲选》在吴昌龄《西天取经》下标注“六本”,显然是受到《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的影响,而根据《万壑清音》的凡例,可知止云居士对《元曲选》十分熟悉[注]《万壑清音》凡例的最后一条为“北曲吴兴臧先生有元人百种之刻,已专美于前矣,兹所选者,悉不敢蹈袭。然其中若一卷《渔樵问话》四折,则又大同而小异;若《拷问承玉》略稍相同,余皆迥别矣。”详见(明)止云居士编:《万壑清音》,第28-29页。)。既然听闻而又拼凑选录,这便不可理解。况且就明代剧作家而言,杨景贤、陈龙光、夏均正等均有《西游记》的戏剧作品,很难说不存在某一戏剧家在继承前面西游戏的基础上改编创作。因此, 纵然无法确定四出戏曲是否出自同一杂剧,但在选录者看来,它们必然不会出自明显不同的杂剧,或是此前被某一(些)剧作家传抄在一起,以至误认,或者本身就是某一戏曲家的删改之作。若果如此,以《西游记》杂剧的松散结构,甚至让人怀疑它是拼凑了元明以来的剧作而成,只是在其基础上又进行了艺术加工。其次,孙先生所谓“杨景言”(杨景贤)等同于“杨景夏”之说,细思之后,发现《词谑》本身并不足以证明二者为同一作家,况无论是字音还是字形,“言”“夏”讹误的可能性都不是很大。在古代不同作者撰有同名作品,同名作家而撰有不同作品本是司空见惯的常事,如唐有诗人子美(杜甫,字子美),宋有诗人子美(苏舜钦,字子美),单以诗人子美而论,焉知是唐是宋?明有江苏吴承恩、四川吴承恩、安徽吴承恩,仅以吴承恩而言,又焉知定是小说作者?在去古较远的今天,即便作品所署之名相同,尚要进行文本内容的考量,更何况作者署名本不全同,又无直接的证据,怎么能够遽然断为一人?且杨景贤作品名《西游记》,杨景夏作品名《玄奘取经》,仅因其残存的一出相似而断为一作,忽略了有同源异本或前后借鉴的可能。孙先生考论精密,自足垂范后世,只是笔者以为在证据链上尚待补充,非是牢不可破的定谳。
就杂剧所呈现的特点而论,其似非成于一手。《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谓吴昌龄意欲和王实甫《西厢记》相争雄,因有是作[注]“昌龄尝拟作《西厢记》,已而王实甫先成,昌龄见之,知无以胜也,遂作是编以敌之。”详见(明)勾吴蕴空居士:《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总论》,黄仕忠等合编《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第二辑第二十三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1页。,这无异于扯虎皮做大旗,单不说《西游记》《西厢记》二者的命名法并不相同[注]李小龙以为二者命名体现出一种因袭借鉴,但笔者以为“西游记”三字中,“西”是表示方位的名词,“游”是动词,“记”是文体的表征,若说“东游记”“北游记”等是对“西游记”的仿拟,自然没有疑问。但“西厢记”中,“记”表文体,“西厢”指西厢房,这是如《破窑记》等典型的以居所命名,“西游记”的命名与其相比仅是形似,命名的艺术构造并不一致。另,元代已经明确出现“西游记”作为平话的名称(全称《唐僧西游记》),戏曲“西游记”的命名,似应来自平话的渗透,至于平话的命名来源,或是本于传记体文学(如《长春真人西游记》等)的影响。,未必是因袭的结果,仅流传过程中直到万历四十二年才以《西游记》代替《西天取经》就足以说明问题。明人作伪之风盛行,小说中诸多假托之作便是最有力的例证,因此,这里不过是借吴昌龄的名声来为眼前的作品装点。伪托在无声中恰又反向证明了此本非吴昌龄所作,不过在拼凑中对其作品可能进行了部分的承袭。肯定了此剧的拼凑特征,自然便让人怀疑它是否也融入了杨景贤的作品。如果《词谑》所引杨景夏《玄奘取经》与杨景贤《西游记》的确并非同一作品的话,那么杨景贤作品的全貌似至今无法窥知。倒是今本《西游记》杂剧应该是同时拼凑了杨景夏以及其他一些被历史湮没作家的作品,这种拼凑,使得作品体现出复杂的艺术特征。
结 语
孙楷第先生将《西游记》杂剧的作者定为杨景贤,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成定谳,但因证据链上的缺陷,仍陆续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笔者在接踵前人的基础上立足文本文献,试图从几个方面对《西游记》杂剧的作者是否为杨景贤提出疑问。首先,《西游记》杂剧中存在的出发前求雨活动,显示出较早的时代特征;而沙和尚早于猪八戒加入取经队伍的描写,也为元代及其以前的取经故事所特有。其次,就文本内容而言,《西游记》杂剧可以拆成十二个单元故事,且这些故事基本都有其相对独立的元前来源。最后,通过对《西游记》杂剧命名及文献载录的考察,可以确定《西天取经》与《西游记》杂剧是不同文本,吴昌龄并非《西游记》杂剧的作者。《词谑》所引《玄奘取经》第四出与《西游记》杂剧存在异文,且题名“杨景夏”而非“杨景贤”;《万壑清音》选录的四出西游戏,涵盖了《西天取经》和《西游记》杂剧,与选录标准相违背,杨景贤之说也值得怀疑。因此,笔者比较同意严敦易先生的观点,《西游记》杂剧可能是拼凑包括吴昌龄、杨景夏等前人作品的产物,属于集体智慧。《西游记》杂剧的时代和作者问题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