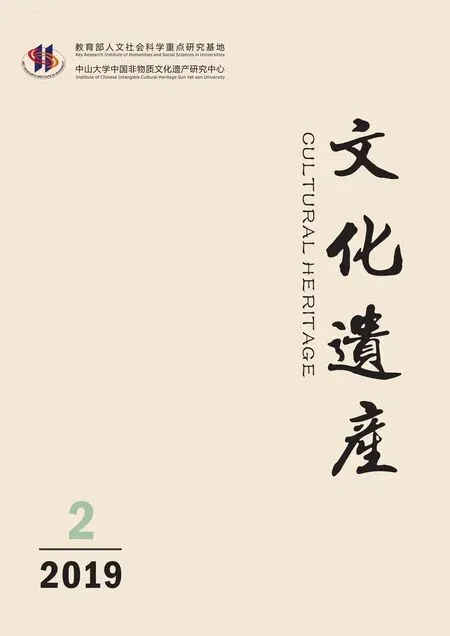富连成藏《长生殿》(时剧)初探*
康保成
孙萍、叶金森主编之《富连成藏戏曲文献汇刊》(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第11册收有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长生殿》(时剧)。这一剧本,无论对于解决《长生殿》(时剧)的文本性质,还是界定“时剧”究竟属于昆唱抑或弦索变体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剧本还提供了晚清北京剧坛的一些史料线索。
一

按《探究》的标点,“时剧”二字在书名号之内,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点。其次,《探究》所提到的傅惜华《皮黄剧本作者草目》一文,先连载于1935年4、5月间天津《大公报·剧坛》,后收录于《傅惜华戏曲论丛》(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据傅文云,《草目》所著录诸剧,均为“余历年目睹,及个人所藏,皮黄剧本之作家可考知者。”《草目》著录云:“《长生殿》,清四乐斋主人撰。主人姓氏里居不详,清末人。一名《定中原》。自《听政》起,至《刺逆》止,共八出。演唐玄宗朝安禄山之变,以郭子仪为主。有光绪二十三年排印本。”[注]傅惜华:《皮黄剧本作者草目》,《傅惜华戏曲论丛》,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355、359页。这个著录的特点是:第一,“时剧”二字并未出现,也就是说,傅文并不把“时剧”当做剧名。第二,傅文的确是把《长生殿》(时剧)当做皮黄剧本的。
《探究》所引王永健《长生殿节选本》一文,提到《长生殿》(时剧)时云:
值得一提的是,光绪十一年(1885),四乐斋主人著有《长生殿》时剧八折:《听政》《洗儿》《平番》(应为《平蕃》,引者注)《演猎》《逼反》《劝行》《誓师》和《刺逆》,全剧本采用七字、十字句,其中以《逼反》最精彩。此剧于光绪二十三年(1987)排印出版。(参见周明泰《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中国艺术中心1985年内部资料)这本八折的《长生殿》虽系时剧,而非昆剧,却同样说明直到清末,《长生殿》仍为观众和作家所喜爱。[注]王永健:《长生殿节选本》,谢柏梁、高福民主编:《千古情缘:〈长生殿〉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27页。
这里也未把“时剧”当做剧名。作者指出:“四乐斋主人”所著《长生殿》是“时剧”,并非“昆剧”。但什么是“时剧”?则语焉不详。且从上文引用《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来看,作者似未获亲见这个剧本。按周明泰《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以下简称《小录》)在“光绪十一年乙酉”下著录:
退庵居士藏《长生殿》时剧一册,系光绪十一年乙酉九月四乐斋主人著。至二十三年丁酉四月,亦嚣嚣斋主人排印并校字。内分八折:《听政》《洗儿》《平蕃》《演猎》《逼反》《劝行》《誓师》《刺逆》。以第六折为最精彩。全剧七字、十字句皆有。[注]周明泰:《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北京:学苑出版社,《民国京昆史料丛书》 第十四辑,影印民国二十一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2013年,第317-318页。本文引《小录》均据此版本,以下不再注出。
两相对照,王文显然从《小录》而来。所不同的是,《小录》除指出本剧的作者之外,还明确指出剧本的收藏者为“退庵居士”。巧合的是,富连成藏本很可能就是“退庵居士”收藏的本子,这一点容后叙。
除《探究》提到的傅、王二文之外,阿英编《晚清戏曲小说目》对此剧有著录,并引录了该剧作者的“短序”[注]阿英编:《晚清戏曲小说目》,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第55页。,蔡毅编《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则把“短序”当做“跋文”予以收录[注]蔡毅编:《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2545页。。那么,作者的自述究竟是“序”文还是“跋”文?“时剧”为什么被当成了剧名?如果不是剧名,那作者为什么刻意标明“时剧”?此剧的作者“四乐斋主人”是谁?收藏者“退庵居士”是谁?刊刻者“亦嚣嚣斋主人”是谁?这个剧本究竟是否属于皮黄剧本?随着《富连成藏戏曲文献汇刊》影印出版,研究者得以亲见这一剧本,上述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问题应当基本上可以得到解决了。
二
《长生殿》(时剧)收录于《富连成藏戏曲文献汇刊》第11册第333-376页,惟《汇刊》“目录”谓其为“钞本”,非是。经与周明泰《小录》 相对照,《汇刊》影印本之底本与北大图书馆藏光绪二十三年(1897)亦嚣嚣斋主人排印本为同一版本。此剧封面,在长方形双线框内竖排“长生殿时剧”五字,“时剧”与“长生殿”三字连排且字号字体均相同。背面单线框内分两行标明“光绪丁酉三月排印”。目录页首行大字竖排“长生殿时剧目录”,并有小字注云:“俗名定中原”。目录页背面有题署如下:
《长生殿》八折,原系游戏之笔,于一切时剧腔调或多未谐。倘有演唱者,不妨随意更改,但不可为俗笔所误耳。时在光绪十一年乙酉秋九月,四乐斋主人识。
原刊本的封面、目录及作者题署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了结不少疑问。首先,刊本将“长生殿”与“时剧”连排,这大概就是某些学者将“时剧”当作剧名,写成《长生殿时剧》的原因。但从作者题署来看,“时剧”非但不是剧名,而且也与当时的“时剧腔调”并不协调。其次,序文通常置于剧前,跋文则置于剧末。但这个题署,放在全剧正文之前,其内容却更像跋文。这大概就是有人把它当作“短序”,有人把它当作“跋”的原因。
根据作者题署,此剧作者为“四乐斋主人”。傅惜华《皮黄剧本作者草目》云此人“姓氏里居不详,清末人。”迄今未见有人考出“四乐斋主人”是何许人。我推测,此人即大清道光皇帝的亲孙子、敦郡王奕誴的第四子爱新觉罗·载瀛。李治亭编《爱新觉罗家族全书》第八册《书画揽胜》有《载瀛小传》如下:
载瀛(1859-1930),惇勤亲王奕誴(道光帝旻宁第五子)第四子。镶白旗。生于咸丰九年(1859),封不入八分辅国公,承袭多罗贝勒,历任宗人府宗正、内廷行走、御前行走、镶黄旗汉军副都统、正蓝旗护军统领、东陵守护大臣、马兰镇总兵、镶黄旗汉军都统等职。长于古琴演奏;工绘画,善作走兽、鞍马,尤以画马名扬于世,所作造型准确、体态生动、立体感强,马匹侧后多配以山水、林石,其笔法受宫廷画家郎世宁画风影响颇深。一生热爱丹青,对子女专事书画艺术有极大影响和熏陶,其子溥伒、溥僩、溥佺、溥佐等均为中国现代著名书画家。[注]李治亭编:《爱新觉罗家族全书》第八册《书画揽胜》,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8页。
在金哲主编之《中国近现代绘画精选集》上,我们看到了两幅载瀛的画作,并以此坐实了载瀛号“四乐斋主人”及“春园居士”。第一幅是载瀛和他儿子溥伒合作的《幽兰仙蝶图》,此图右上题字“已巳初冬春园载瀛写生,时年七十有一”,题字下钤有“春园居士”“四乐斋印”两枚印章。图的右下方题“溥伒写石”四字,旁钤有“雪斋”印章(溥伒号“雪斋”)。可知此画的花草、飞蝶为载瀛所画,而山石则出自其子溥伒手笔。虽为二人合作,但父子间心有灵犀,使此画天衣无缝,堪称精品。第二幅为载瀛所画的《骏马图》,此图左上题字“庚午仲春四乐斋主人写真”,题字下钤有“春园居士”“心正笔正”两枚印章。[注]金哲主编:《中国近现代绘画精选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0页、121页。我推测,号“四乐斋主人”的载瀛,即《长生殿》(时剧)的作者。此剧作于光绪十一年(1885),时载瀛26岁,若按虚岁是27岁。
《小录》谓此剧收藏者为“退庵居士”。富连成藏本在题署末行下钤有四字藏书印章一枚,右半边阴文为“退庵”,左半边阳文为“文麟”,合称应是“退庵文麟”。毫无疑问,富连成藏本,应该就是周明泰《小录》中所说的“退庵居士”收藏的本子。这未免也太巧了!
晚清号“退庵居士”的名士有好几位,收藏《长生殿》(时剧)的,应该是著名京剧票友老生文瑞图。此人在清末北京剧坛上赫赫有名。周明泰《小录》多处提到此人,且在“咸丰九年巳未”下有此人《小传》:
票友老生文瑞图生,姓田原名文麒,号瑞图,京旗内务府人。由内务府堂笔帖式出身,历升主事员外郎郎中,及候补三院卿护军,参领衔管理颐和园造办处、昇平署事务。父名师曾,总管内务府大臣、兵部尚书。瑞图以事革职,永不叙用。遂改名文麟,唱学奎派,晚年别号退庵居士。[注]周明泰:《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第260页。
又,《小录》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孙菊仙小传》下记,四喜班班主梅巧玲去世后,“其徒余紫云、李砚侬接充班主,以营业不佳报散。该班值事人姚增禄、汪立中、玉五等邀退庵居士接倒该班,由时小福充班主,仍赔累不堪。四十三岁(指孙菊仙年龄,引者注)癸未,遂由退庵居士要求菊仙由嵩祝成班改搭四喜班,与王九龄、张胜奎、杨贵云、罗寿山、叶中定、杨隆寿、庆春圃等原有角色,并添约谭鑫培、吴燕芳、穆凤山、余玉琴、朱桂元、吴顺林等同演。[注]周明泰:《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第222页。”刘绍唐主编之《民国人物小传》在《孙菊仙小传》中提到此事,并增添了“退庵居士”被刺的情节:
巧玲殁后,其徒余紫云、李砚侬接充班主,以营业不佳报散。值事人姚增禄、汪立中等,邀票友老生退庵居士文瑞图接办“四喜班”,由时小福充班主,仍赔累不堪。九年,退庵居士要求菊仙由“嵩祝成班”改搭“四喜班”,允之。由于菊仙离去,“嵩祝成班”竟因此报散。孙加入“四喜班”后,初演于“康乐园”第一日,“嵩祝成班”管事因生计所关,纠众怀利刃,谋入园刺退庵居士,不果。[注]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7册,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第221页。
“嵩祝成班”原由宫中庞太监、刘太监等组班,由于班中角色病故而请孙菊仙入班帮忙,“退庵居士”劝菊仙改搭“四喜班”而造成“嵩祝成班”散班,因此才发生了他本人被刺事件。以此可见“退庵居士”在梨园行的影响。
光绪十五年(1889),左都御史许应骙、副都御使杨颐的手下在庆和园寻衅滋事,官府“欲将庆和园封门并饬革该园”,“孙菊仙会同杨月楼、余润仙暨各园园主、班主,与退庵居士商议,罢业七日,零碎角色糊口无资,由退庵居士集款四千八百吊,散放各班。后孝钦后闻知,特赏九千六百吊,命退庵居士会同各班主,分给贫苦角色,每班约得一千二百吊。并奉懿旨,令许应骙、杨颐将滋事六人交出,在庆和园门前枷号十日示众。”[注]周明泰:《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第323-324页。于此可见,退庵居士文瑞图,这个曾经管理过“昇平署事务”的京剧票友竟然可以通天,他虽被朝廷革职,但依然可以游走于戏班与王府乃至皇宫之间。顺便提及,退庵居士文瑞图与《小录》作者周明泰是相识的。《小录》在谈及光绪十五年梨园行罢业事件时,用的是“退庵居士述”的口吻,可见此事是“退庵居士”讲述给周明泰的。
又,王芷章《清代伶官传》在“姚阿本小传”下记光绪九年八月:“恭亲王府中堂会,用四喜班底加外串,阿奔与朱素云尝合演《雅观楼》一出,事见退庵居士所藏四喜戏单。[注]王芷章:《清代伶官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64页。”以此可知,“退庵居士”好收藏,他收藏贝勒载瀛的剧作完全在情理之中。富连成科班成立后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和前清诸王府的京剧迷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看来,“退庵居士”收藏的本子后来流入富连成科班,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长生殿》(时剧)在作者题署的下一行,又有如下文字:“二十三年丁酉四月,亦嚣嚣斋主人排印并校字。”这个“亦嚣嚣斋主人”是谁?目前难以确考。孟子曰:“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孟子·尽心上》)意思是:别人理解我,轻松而快乐;别人不理解我,也轻松而快乐。晚清通州雷学淇以“亦嚣嚣斋”为室名号[注]陈乃乾编:《室名别号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1页。,但他主要活动在道光时期,比载瀛的时代要早。光绪间河南永城人吕遐绎、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吴仪的外祖父喻肖溪(1868-1925)均著有《亦嚣嚣斋诗文集》,但似均与《长生殿》(时剧)的刊刻无关。清末湖北拔贡生谢庭书撰有《亦嚣嚣馆诗集四卷》》,此人能画(见清李放《画家知稀录》),是否与载瀛有关待考。
三
《长生殿》(时剧)共八出,出目已见上文所引周明泰《小录》。显而易见,此剧虽剧名沿袭了洪昇的《长生殿》原著,但实际上作了大量删改,五十出戏被删得只剩下八出,李杨爱情主线完全不见了。即使仅剩下的以郭子仪平息叛乱为主线的八出戏,也把原著改得面目全非。
“时剧”第一出《听政》,大致相当于洪昇原著第十三出《权讧》,写杨国忠和安禄山一同“面圣”,却又把原著在第十出《疑谶》出现的郭子仪扯进来。
第二出《洗儿》,写杨贵妃为义子安禄山“洗儿”,原著无,为“时剧”所加。本来,这件事是有史料和前人戏曲作品为依据的。《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载:“上闻后宫欢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三日洗禄儿对。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并因此引出了“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等记述[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662页。。元白朴的《梧桐雨》杂剧在“楔子”部分有如下描写:
(正末云)不知后宫中为什么这般喧笑?左右,可去看来回话。(宫娥云)是贵妃娘娘与安禄山做洗儿会哩。(正末云)既做洗儿会,取金钱百文,赐他做贺礼。就与我宣禄山来,封他官职。[注]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489页。
然而,洪昇却没有理会这些史料,而是毫不迟疑地把它们丢弃了,因为他要写一个“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杨贵妃,因此“凡史家秽语,概削不书。[注]洪昇:《〈长生殿〉自序》,引自竹村则行、康保成:《〈长生殿〉笺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页。”“时剧”有意把原著丢弃的部分添加进来,并不符合原著主旨。这一出还把虢国夫人、秦国夫人也扯进来,与安禄山打情骂俏,更显无聊。
第三出《平蕃》,写郭子仪帅军平息并收伏西羌叶护,既与史料不合,也是原著中根本未予提及的。
第四出《演猎》,大致上相当于原著第十七出《合围》,但把安禄山手下的史思明等四将改成了子虚乌有的参军“庄严”,并让原著第三十四出《刺逆》才上场的李猪儿提前上场,意在为后来的《刺逆》做铺垫。
第五出《逼反》,截取原著第二十出《侦报》、第二十三出《陷关》,把原著中郭子仪、安禄山等人口述的部分改为明场演出。
第六出《劝行》,大致相当于原著第二十四出《惊变》和第二十五出《埋玉》。
第七出《誓师》,大致相当于原著第三十一出《剿寇》。
第八出《刺逆》,大致相当于原著第三十四出《刺逆》、第三十五出《收京》。
总之,在“时剧”的八出戏中,有两出是洪昇原著中所根本没有的,其余六出利用了原著的一些情节,或删削,或缀合,或增添,改动相当大。所谓“大致相当”者,仅指主要情节而言,其细节以及唱、白、科范提示等均重新写过,与原著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那么这个剧本用的是何种声腔呢?正如周明泰《小录》所言,此剧采用的是七字句、十字句,很明显不是昆曲,而是乱弹的句法。以下略举数例。第一出《听政》唐明皇(小生扮)上场唱:
红光起日东升景阳锺响,想当年遭国乱重整朝纲。
到如今才落得太平有象,多亏了众文武扶保孤王。
这是典型的十字句唱词。同出末尾杨国忠(净扮)唱七字句:
听一言来心好恼,大骂无知小儿曹。
低下头来生计谋,教你难防笑里刀。
以上是皮黄或梆子剧本常用的齐言体的十字句、七字句唱词,这类唱词在全剧中占绝大多数,可见傅惜华把《长生殿》“时剧”定位为皮黄剧本是不错的。但剧本第二出杨贵妃(旦扮)出场,唱的却是六句不够整齐的歌词:
独坐在皇宫院闷悠悠,清晨起巧梳妆才下朱楼。
御园中牡丹开香风透,说不尽皇家富贵风流。
宫蛾女搀扶俺漫漫行走,等候了驾还宫携手同游。
同出还有“杂唱昆曲”的提示,唱词是:“郎当郎当,福寿绵长,红绫被裹之个大骚羊。谁敢说荒唐,谁敢说荒唐。”又提示:“二私坊扮连相上演毕叩首下,二私坊艳妆上合唱昆曲一支叩首下,武旦短衣上对舞双剑毕叩首下,象奴牵象上跪献酒杯叩首下,二武士牵二马上相对舞毕叩首下。”光绪年间,皮黄已经稳居于京师剧坛之首,但昆曲和其它声腔并未完全退出舞台,这种描写看似无心,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宫中演戏的实情。
另从古典戏曲的刊刻习惯来看,一般唱词用大字,念白和科范提示用小字。但这个剧本的唱词、念白同用大字,少数科介一般用小字,有的也混入大字行列。这显然与一般的刊刻规范不合,或反映出从传统的杂剧、传奇向皮黄剧本刊刻风格靠拢的某种转向。
四
这个剧本标明《长生殿》(时剧),但作者自己又说此剧“于一切时剧腔调或多未谐。”那么,这个剧本究竟是不是“时剧”呢?那得先看什么是“时剧”。
徐扶明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时剧的‘时’,就是时兴、时尚的意思。”“在当时,也有把时剧称为‘杂剧’。《缀白裘》就是把《花鼓》《借靴》《卖胭脂》《打面缸》 等,列入‘杂剧’”。“当时时剧,包括着多种戏曲声腔的剧目,有梆子腔、高腔、罗罗腔、柳枝腔、弦索腔等。”[注]徐扶明:《昆剧中“时剧”新探》,《艺术百家》1990年第1期。武俊达指出:
昆曲所用曲牌除南北曲外,还有一部份“时剧”所用曲牌颇为混杂,就成书于乾隆末年叶堂编《纳书楹曲谱》所收时剧十四出及标名时剧实为散曲的九部散套来看,所用曲牌近五十种,其中有些是从昆剧南、北曲变化而来,如【山坡羊】【梧桐树】【新水令】【点绛唇】等等;有些是从明清民歌发展而来,如【驻云飞】【锁南枝】【挂枝儿】【寨儿令】等等;有些则是引用其它声腔,如《借靴》所用“延索调”实为“弦索调”的讹记,《罗梦》所用“弋阳调”引自“弋阳腔”。[注]武俊达:《昆曲唱腔研究》,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第30页。
吴新雷主编的《中国昆剧大辞典》“时剧”条(本条作者为顾聆森)云:
时剧,昆班艺人俗创或从花部中吸收时兴流行的小戏,“时”就是时兴、时尚的意思。因地方戏中有些生动活泼的短剧,通俗易懂,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昆班便加以吸取、溶化、俗创为昆戏。如乾隆十四年(1749)编刊的《弦索调时剧新谱》中,收录了《思凡》《罗梦》《借靴》《磨斧》《夏得海》等二十个折子戏,就是从弋腔、高腔、梆子腔、弦索调中移植过来的。苏州叶堂编刊的昆曲范本《纳书楹曲谱》也在《外集》中收录了流行的《僧尼会》《王昭君》《花鼓》等时剧。宣鼎画的《三十六声粉铎图咏》中也记载了《过关》《拿妖》等昆腔丑角戏中的时剧。这些戏码为昆腔注入了新鲜血液,增强了新的活力。[注]吴新雷主编:《中国昆剧大辞典》,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7页。
那么“时剧”究竟算不算昆曲或者昆曲的变种呢?徐文武、刘崇德《清代弦索时剧与昆曲》一文认为:“清代时剧不是昆曲之变,而是昆曲与其他声腔剧种交融并流的一个例子,是昆曲与其他声腔交流融合的一个侧面反映。昆曲在定型之后的近两三百年发展流传过程中,不断地吸收新的时调,与其他声腔交流与融合。在保持相对独立的前提下,增加自身的艺术创新。”[注]徐文武、刘崇德:《清代弦索时剧与昆曲》,高福民、周秦主编:《中国昆曲论坛2005》,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3页。
其实,讨论“时剧”的归属问题,还要看它的来源。我大体上同意徐文武、刘崇德的看法,现将本人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太古传宗》《纳书楹曲谱》中的“时剧”,来自“弦索腔”。中国戏曲自宋金、宋元时期便有北曲杂剧、南曲戏文之分。其中北曲用三弦、琵琶一类的弦乐器伴奏,又称“弦索腔”。弦索不仅用于戏曲,更早是用于讲唱文学,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就是最早的弦索讲唱。明中叶以降,北方产生了大量俗曲,就是“弦索腔”的延伸。所谓“俗曲”,亦即明清两代民间流行的时尚小曲,也称“俚曲”或“小曲”。李开先、顾起元、沈德符等记录的俗曲曲牌有【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泥揑人】【鞋打卦】【耍孩儿】【驻云飞】【醉太平】【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打枣竿】【挂枝儿】等数十种。这些曲牌,虽然名称与南北曲曲牌相同,但实际上词格和唱法却与南北曲迥异。俗曲在当时影响巨大,沈德符谓其“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其谱不知从何来,真可骇叹!”[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47页。俗曲不仅用于清唱,而且还进入到北方宣卷和道情讲唱之中。到明末,俗曲进入戏曲。清康熙年间,蒲松龄的《禳妒咒》通篇采用俗曲,成为俗曲体戏曲的代表作。康熙至乾隆初流行的俗曲体戏曲,被称为“时剧”,其剧目有《思凡》《僧尼会》《大王昭君》《小王昭君》《花子拾金》《芦林》《夏得海》《罗和做梦》《醉杨妃》《红梅算命》《金盆捞月》《旷野奇逢》《临湖》《踢球》《花鼓》《唐二别妻》《借靴》《磨斧》等。这些剧目所使用的俗曲曲牌有【山坡羊】【玉娇枝】【驻云飞】【四边静】【挂真儿】【竹马儿】【诵子】【耍孩儿】等。早期南戏本是我国最早的俗曲体戏曲,但由于它被传奇所使用的规范的曲牌联套体制所替代所遮蔽,故阻断了它对明末清初新一轮俗曲体戏曲的直接影响。于是,明中叶以来产生的俗曲,经与弦索清唱和宣卷、道情的结合,萌生出了俗曲体戏曲亦即“时剧”,并开始了它先由北向南,再由南及北的传播过程,并在传播中不断壮大。[注]参拙文:《试论俗曲体戏曲及其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以蒲松龄〈禳妒咒〉为中心》,《文史》2018年第4辑。
简言之,按照我们的理解,所谓“时剧”,就是用明中叶以来的时尚俗曲连成的戏曲。所以,判断一个剧本是否属于“时剧”,要看它是否使用了俗曲曲牌。《长生殿》(时剧)基本使用齐言体唱词,只不过上引第二出杨贵妃所唱的六句不够整齐的歌词,或者留下了俗曲的痕迹(从长短句向齐言过渡)亦未可知。总的来看,该剧本虽未标出板式,但仍旧是一个乱弹本子,不符合“时剧”的标准。
这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刊本将剧名与“时剧”连排成“长生殿时剧”,而作者却声明:此剧“于一切时剧腔调或多未谐”。标出“时剧”的用意,其一是为了区别于洪昇的《长生殿》原著,其二是为了区别于昆曲。而作者的声明,才将此剧排除在真正的“时剧”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