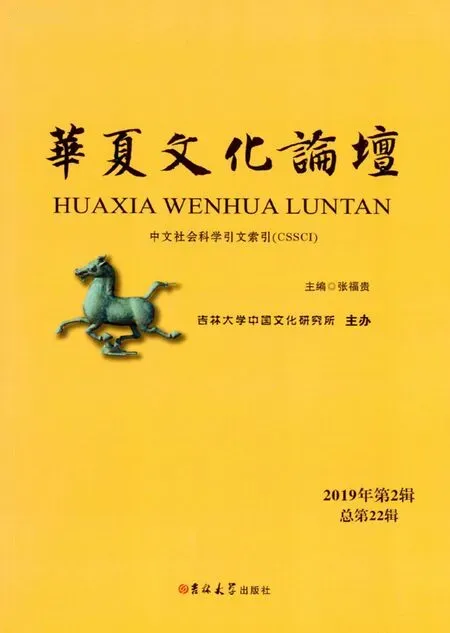曲径通幽话“禅”、“空”
——从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诗说起
易佳妮
【内容提要】唐代诗人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诗构思巧妙,匠心独运。“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历来为人称道,“幽”、“深”二字实为妙笔生花,“曲径通幽”一语也含义深邃;但其后两联的“空”、“寂”二字方为点睛之笔,这里道出了诗人的禅心和妙悟。“空”是佛教哲学领域最为重要的术语,“寂”亦与之密切相关。若想真正领悟这首诗的深层含义,就得理解诗中“禅”和 “空”的意义。理解这类佛教专业词汇,无论对于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的训释,还是对于古典文学欣赏和中国文化史研究都将大有裨益。
一、引言
人教版(古诗文背诵部分)和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均选录了唐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以下简称《题禅院》)这是诗人游览名山古刹、寻幽探胜而作的一首题壁诗(下文简称“《题禅院》”)。全诗匠心独运,构思巧妙,围绕破山寺后禅院,描写了特定境界中的静趣,折射出诗人的禅心和妙悟。然而要想深入领会“曲径通幽”的思想内涵,领悟“禅”和 “空”的真正内涵,却须知道一些佛学知识。联系这首诗的写作背景以及唐朝的社会文化环境,我们就可以推广开来说,这个话题既牵涉到语言文字问题,也关涉到文学欣赏和文化研究的问题。
关于《题禅院》诗的艺术性,宋洪驹父誉之“全篇皆工”(见《宋诗话辑佚》)其颔联和颈联尤为千古传诵的佳句。欧阳修曾感慨称道:“我常喜诵常建诗云‘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欲效其语作一联,久不可得,乃知造意者为难工也……兹为终身之恨尔。”此联之美,堪称巧夺天工,不唯因写景之传神,亦因其思想之深邃。佛教提倡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净心修行,方得妙悟。观此禅院,花木繁茂,沁人心脾,清幽静谧,令人心旷神怡。诗人勾勒出这个美妙的修行道场,曲折地表现了僧侣们对理想境界的热切向往。山光、水色、幽林、静刹,观之令人杂念烟消、冥尘雾散。但若仅仅理解到如此分寸,似乎仍未得其三昧。这里,诗人是否蕴含了几分“禅悟”的理趣呢?颔联的“幽”、“深”二字乃生花妙笔,但其颈联方为点睛之笔。如果联系社会环境和诗的内容仔细考量,进而认识“禅”和“空”的真义,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领会此诗的精髓。
二、关于《题禅院》中几个关键词语的释义
(一)“禅”
佛教为什么把为修行者所建的房舍叫做“禅房”呢?其中的“禅”原来是梵语dhyāna、巴利语jhāna省译,全译禅那、持阿那等;意译则为静虑,指专心致志、别无旁骛的心境。本来dhyāna(禅)在印度是佛教、外道和凡夫共修之法,唯其目的及思维对象不同而已,因此dhyāna和jhāna本来是通用词。“禅”及其他各种定意之法泛称为禅定,“禅定”是音译加意译的译词。佛教传入中国后,“禅”和“禅定”均用来指专心致志思维佛法的精神状态,演变为佛教专用词语。因此,佛教就把为修行者所建的房舍叫做“禅房”或“禅堂”。唐萧至忠《荐福寺应制》诗:“香塔鱼山下,禅堂雁水滨。”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五回:“施主辛苦了。这里不洁浄,污辱众位罢咧。请到禅堂里歇罢。”
佛法抽象深邃,道人心中有“般若”(智慧),方可参悟佛法。若想获得真智,即需专心致志,进入“禅定”之境。此为修心之本,甚为重要。
次谈“禅者”和“禅心”。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选录了李汉荣的《山中访友》一文。其中一句话是:“你好,悬崖爷爷!高高的额头,刻着玄奥的智慧;深深的峡谷,荡着清澈的禅心;你是一位无言的禅者,云雾携来一卷卷天书,可是出自你的手笔?”教材对句中的“禅心”的注释为:“佛教指清净、无杂念的心境。”但“禅者”一词却未予注解。根据课文对“禅心”的注释,那么“禅者”似乎可以注释为“佛教指清净、心无杂念的人”吧。这样解释并不为错,但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本,给人一种隔靴挠痒的感觉。学生若问:人是有思想的,所谓“佛教指清净、无杂念的心境”,到底心里应该念什么呢?应该明确,佛教所谓“正念”与“杂念”是相对的,“正念”指如实思想“诸法”(万事万物)的本质。佛教净土宗认为,面临诸种遭遇,能心不错乱颠倒,一心念佛,这也叫“正念”。其实所谓“念佛”有时指口念佛陀,但更多情況下是指思虑佛说的“真理”,或曰“真谛”。
这样解释,答案就清晰了。“禅心”应解释为:佛教指思虑清净、没有杂念、专心思考佛法的心境。“禅者”应该解释为:佛教指心地清净,专心思考佛法的修道者。文章写“悬崖爷爷!高高的额头,刻着玄奥的智慧;深深的峡谷,荡着清澈的禅心……。”这句话禅趣深邃,文思隽永。佛教确实充满了“玄奥的智慧”,但只有对佛教术语解释到位,方可引导学生去学习,进而深入领会国学的奥妙。
(二)“曲径通幽”与“禅”和“空”
现代汉语的“曲径通幽”早已俨然是成语了。但查检《辞源》、《汉语大词典》等辞书,均无收载,令人遗憾。这个成语的表层含义指弯弯曲曲的小路通往风景幽美的境地,语源即常诗的颔联。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常诗的“曲径通幽”语含禅机,隐喻了一个佛家的哲理:若欲参悟佛法妙道,会有诸多法门,走一段曲折幽深之路,亦可进入令人心驰神往的胜境。此联的铺垫妙不可言,颈联“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方为点睛之笔。在旭日东升、光照山林的美景中,诗人流露出对佛宇的礼赞。有人说,诗人仕途坎坷,临赏此佳境,寄托了遁世情怀,恐未中肯。人教版语文教材将“潭影空人心”释为:“潭影澄澈清明,使人在尘世杂念顿时消除。”亦恐失之肤浅。
这个“空”不是消极的“空无”或“虚无”,应以佛教“缘起性空”说解释之,方可得其三昧。佛教认为,众生与诸法均由因缘和合而成,因此它们都是没有“自性”(本质)的,以此观“空”,方为“真谛”。佛教强调从“事相”体悟“空观”之深义。后秦鸠摩罗什译《大品般若经》曰:“一切法自性空……一切法如幻、如梦、如响、如影、如焰、如化。”大乘佛教认为“诸法无我”,一切法如梦如幻、如影如响,“潭”和“影”即属诸法,岂有本质可言?“空”是最为重要的佛教哲学术语,“空观”是世界哲学史上的重要思想。诗中的“潭影”不就是慧眼观空的方便法门吗?正如唐李嘉佑《题道虔上人竹房》诗所言:“诗思禅心共竹闲,任他流水向人间。”亦如唐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舂茶会》诗所说:“虚室昼常掩,心源知悟空……不知方便理,何路出樊笼?”认识这一点,不仅对于我们学习古汉语词汇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我们学习中国文学史和哲学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常建大约生活在唐中宗至开元、天宝年间,他一生仕途不顺,但是否信佛,史料未载。据其诗可知,他曾游历过不少山川寺观,而且与僧人交往甚深。其诗《潭州留别》:“贤达不相识,偶然交已深。宿帆谒郡佐,怅别依禅林。”其《题法院》诗:“皓月殿中三度磬,水晶宫里一僧禅。”在与僧人交往过程中,他的生活和思想很可能受了佛教的影响。其《燕居》诗:“啸傲转无欲,不知成陆沉。”诗人与禅僧互动之风,晋代已行,其后诗禅交涉,相得益彰。唐宋时期,诗人与禅僧交往,已成时尚。唐代的韦应物、刘禹锡、颜真卿、权德舆等人,不仅与禅僧交游甚密,而且以禅入诗,王维(字摩诘)连名字都取自佛教人物“维摩诘居士”,更不用说其诗的禅韵了。这种风尚使唐诗更加含蓄雅致,韵味盎然。据此而言,将《题禅院》诗归入“禅诗”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作为成语,“曲径通幽”之妙即源于其禅意。“幽处”乃美妙之境;“曲径”隐喻法门,亦有美学价值。“幽”有幽雅、玄妙、深邃之美;“曲”乃达到幽雅、美妙之境的径路和法门。“曲”字古含曲折、宛转、回环之美,亦有周遍、详尽等义。《荀子·非相》:“曲得所谓焉,然而不折伤。”梁启雄释:“荀卿书‘曲’字多有周徧之义。”唐韩愈《为裴相公让官表》:“圣君所厚,凶逆所雠,阙于防,几至毙踣,恩私曲被,性命获全。”“曲”还有深邃义。“曲悟”即深刻的领会。南朝梁何逊《哭吴兴柳恽》诗:“曲悟同神解,龟谋信有知。”“曲尽其妙”即全面深入地将其奥妙表达出来。《文选·陆机〈文赋〉》:“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可见,颔联“曲”“幽”“禅”“深”等字均推敲高妙,一字千钧。理解此联对于体悟“潭影空人心”的“空”字,至为重要。
“曲径通幽”新解。现代人未必都能禅悟,也无须追求佛教的“般若”,但今人却从其隐喻义得到启发,用它来隐喻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处理问题、应对事务或完成事业时采用的态度和方法。金庸《天龙八部》第十三回:“姜老者正要抢上攻他后路,万万想不到他这一锥竟会在这时候从这方位刺到。曲径通幽这一招是青城派的武功,姜老者熟知于胸,如此刺法全然不合本派武功的基本道理。”曹天元《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序》:“这个故事更像一个传奇,由一个不起眼的线索开始,曲径通幽,渐渐地落英缤纷,乱花迷眼。正在没个头绪处,突然间峰回路转,天地开阔,如河出伏流,一泄汪洋。”翁绍军《从存在主义的定义谈起》:“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那位哲学教员的定义,我并非想抬出华尔来贬低他,相反,这个定义从根本上说也许并不错。问题在于对西方哲学思想的评述是不是仅此而已,还有没有曲径通幽之胜境。”冯建兵先生的一篇论文,题目是“曲径通幽深几许,别有洞天——谈“提示”在物理习题教学中的作用”,其“曲径”即指导学生应对难题的“法门”之一。张燕凤的论文《曲径通幽处,柳暗花明时——浅谈初中古诗词题鉴赏方略》,其“曲径”也取此义。
三、诗文中的禅意与文学欣赏及其他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喜诵常建诗,并感慨《题禅院》颔联之美,这恐怕与其深邃的禅意不无关系。赏析此诗,我们应有感悟佛道的情致,方可体味出比“幽境”还妙的“禅意”。这需要我们具备基本的佛教修养。佛学是比较深邃的理论体系,道人需要“般若”(智慧),方可参悟真如。真智之获得,须入“禅定”之境,“须知不动念,照出万重源”(唐皎然《禅诗》)。定心、定力之获得,即须戒除贪欲。“若问无心法,莲花隔淤泥。”(唐李端《同苗发慈恩寺避暑》诗)佛教禅宗所以名“禅”,乃因其强调“直指心性”的顿悟。禅定乃智慧之门;获取般若真智,方可“明心见性”。因此“禅定”为修心之本,甚为重要。
诗思和禅意的水乳交融,为古代汉语词汇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为中国古典文学、古典哲学等平添了几分深邃的韵致。理解这一点,不仅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佛教专业词汇和一般词汇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我们认识佛教、正确欣赏文学作品,甚至学习中国文学史和哲学史都具有积极的意义。这里我们不妨以苏轼的两首诗为例,谈一点简单看法。
苏轼也是同时期将佛教思想诗化的杰出代表。唐宋时期,不少文人深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他们辛勤阅读佛经、积累佛禅事典,使得他能将佛理和禅意融会贯通,并将个人的领悟写入诗中,这大大改变了中国诗词以抒情和描摹山水田园为主的风格。苏轼诗词中涉及佛教内容者概有两类:第一类是阐释其学修佛法的体悟,申明见地。苏轼诗词中有时流露出来的对人生本质的思索,可以看出他受佛教人生观的影响。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 》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上人困蹇驴嘶。”细玩首颈两联,读者约略可见其句源自宋代的灯录。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十四:“僧问:‘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还端的也无?’师曰:‘芦花两岸雪,江水一天秋。’”苏诗感慨人生无常,流露出无限惆怅,体现了佛教“有漏皆苦”“诸行无常”的人生观。联想到苏轼才高志远,却命途多舛的一生,我们就不难领悟,这些看似随手拈来的词句,原来却饱含了浓厚的禅意和深邃的人生哲理。
《红楼梦》第七十六回写史湘云和林黛玉最后一次对诗,湘云出了上联“寒塘渡鹤影”,黛玉对的下联是“冷月葬花魂”。有学者指出此联取意于明代洪应明《菜根谭》中的名句:“雁渡寒潭,雁过而潭不留影;风吹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倘若深究,即不难发现《菜根谭》之句亦源自古代佛教名僧的语录。
第二类是苏轼经过累年佛法的修学,于写景抒情中,将内证深切的现实感受,加以提炼升华,辅以文学手法的润饰,透露出深邃的禅意。许多禅师认为,东坡不少诗词之内容,乃直呈悟后之境界。苏轼《题西林壁》诗是他游庐山时,夜宿东林寺,与两位禅师,彻夜讨论佛法,有所醒悟,于次日早起所作:“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诗大意是说,佛法与世间万象不二不离,万象有别不过是表象而已。众生观见诸法之差别,乃因其观察角度不同。在这里“庐山”隐喻了“诸法”。其深层的涵义是:众生不识庐山真实之面目,乃是由于自身智慧开显不足,也就难以观见“缘起性空”的真谛;洞悟佛法,最需要般若智慧。智慧具足了,方可彻悟:佛法本在心中,何须南辕北辙,孜孜求法于心外?
于苏轼的研究,学者们有从苏轼人生仕途、思想发展方面展开的研究,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从其诗词散文等文学艺术方面展开的研究。我们认为,鉴于佛教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大影响,而苏轼作为一位受到佛学思想影响较深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若是能将佛教专业词汇与苏轼的文学语言结合起来,尤其是将佛学和词汇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立体的研究,这无论是对佛教术语的通用化研究,还是常用词的术语化的研究,都将有着莫大的助力。
迄今为止,对佛禅思想和艺术的研究已遍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领域。在现代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面对佛教文化,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当代莘莘学子,唯科学是骛,专心致志,方可获得菩提心性,进入深邃美妙的科学之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