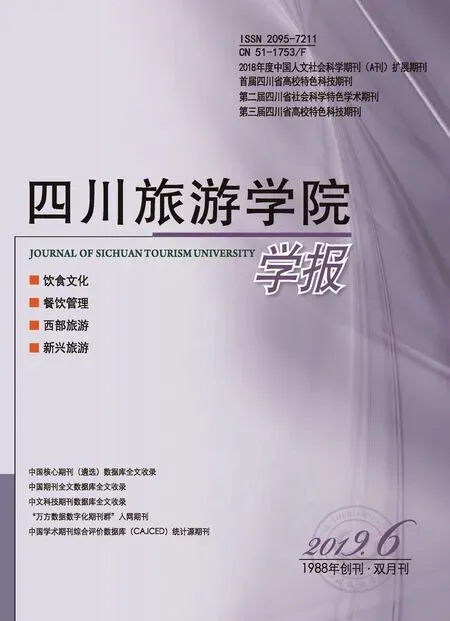汉代漆器餐具艺术特征探究※
覃曼琳
(玉林师范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汉代餐具在我国的器皿设计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尤以汉代漆器餐具为代表,堪称中国漆器的巅峰时代[1]。迄今出土的汉代餐具已有上千件之多,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汉代真实生活的映射,体现了当时的审美价值以及文化内涵。为了发掘现代餐具设计源文化的优秀资源,本文针对汉代餐具的整体造型与纹样造型进行分析,了解其文化背景,结合汉代考古发现,分析社会与经济发展对餐具造型艺术的影响。从根源找到其设计的初始,更深入地探究其艺术价值。
1 汉代漆器餐具出土状况
汉代餐具的发展经历了400年的漫长历程,尤以汉代漆器为代表,在中国的历史上独树一帜,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与艺术成果,许多出土的汉代餐具依然光亮如新,可见当时的高超技艺。
从目前汉代漆器的考古资料分析,安徽、江苏、湖南、湖北等地区较多,陕西、云南、广西、贵州、甘肃、新疆等中西部地区也有不少数量,整体比东部地区多,而东部地区以江苏最多。
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出土的漆器汉墓有六十余处,每一座汉墓件数有几件、十几件、几十件甚至几百件之多,由于年代久远,有些已经残破。而汉墓出土的漆器最多且保存最好、极具代表性的当属湖南长沙的马王堆,发掘于1972至1974年,包括了一号、二号、三号共三座汉墓,是汉代初期长沙丞相百官之首轪侯——利苍及其妻儿之墓,出土的漆器共500余件,其中的漆器有鼎、圆盒、勺、笥、耳杯、耳杯盒、圆平盘、食盘等。
其次,在西汉中晚期,扬州为中心的江淮地区的汉墓出土居多,据《汉广陵国漆器》记载:“汉广陵所在的扬州及周边地区,西汉时期的墓葬极多,据不完全统计,只扬州地区1949年以来发掘的墓葬就有500余座,随葬品、漆木器的比重很大,出土漆器共有数千件之多”。在扬州的考古中发现,随葬的漆器不但品种丰富,而且其装饰工艺采用了多种技巧,包括贴金银箔、针刻、雕刻、彩绘等。虽数量庞大,但风格自成一派。
此外,在西汉中期,漆器被皇家青睐,出现了官营作坊专门生产漆器,其中以四川成都漆器最为出名,其做工精美,款式变化多样,成都成为漆器艺术品的集散中心,各地漆匠公推“蜀工”技艺为最。1992年,四川的绵阳永兴双包山M2汉墓出土了近五百件西汉中期的漆器,其中有大量的漆碗、漆盘、耳杯等食用器具。可惜的是,由于受到自然界的侵蚀,器物受到严重的损害。
汉墓漆器餐具在东汉时期,明显少于西汉时期,多见于江苏、安徽、甘肃等地。有江苏扬州东风砖瓦厂汉代木椁墓群、江苏盐城三羊墩汉墓、江苏省邗江甘泉二号汉墓、安徽天长市汉墓、安徽寿县茶庵马家古堆、甘肃武威雷台汉墓等,每个汉墓出土仅寥寥几件,还有一些是残片。东汉时期,官方慢慢不再控制漆器生产,漆器亦从皇家“错彩镂金”与“银扣黄耳”风格走向民众致用追求[2]。漆器餐具也已逐渐减少,中晚期逐渐出现了瓷器器具。这一时期,瓷器餐具初现,工艺与设计还不成熟,有待完善。
由此可见,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漆器餐具,展现了整个汉代的发展历程,极具代表性。我们应保护起来,更深层次地挖掘其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结合现代设计进行转化、传承与发展。
2 汉代漆器餐具艺术价值分析
2.1 汉代漆器餐具的设计思想分析
2.1.1 初期浑朴而静穆的造型艺术
鉴于前朝秦国因“法治”而亡国的教训,汉代初期的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阶级的地位,实行“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黄老政策。因此,黄老思想中的“无为”对当时的艺术创作产生非常大影响,同时在“汉承秦制”的理念下,器皿设计艺术继承了先秦的道家简约美学思想,形成了简约无为的审美原则,餐具的造型设计简单大方,以功能设计为主,趋于生活化、平民化。当时,统治阶级的一些元老深受楚文化的影响,其审美还局限于恭谨与规范,设计作品在满足其审美基础上,结合当时社会发展新元素,形成了其设计作品不仅恭谨与规范,还充满了浪漫与神秘。这一时期作品基本延续该种融汇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浑朴而静穆的造型艺术。[3]
2.1.2 中期阔大沉雄的造型艺术
汉武帝继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当时文化主流,汉代漆器餐具设计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大美”的审美思想将传统平民艺术升华为贵族艺术、神权艺术,打破了传统的简朴实用,在表现形式上更趋于艺术化发展,涌现出一批精美的漆器餐具。受当时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影响,漆器图案元素也随之丰富,增加了映射国家权力威严的设计,形成了“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气势,彰显漆器餐具阔大沉雄的造型艺术。
2.1.3 晚期典雅庄重的造型艺术
汉代漆器艺术经历早期的浑朴而静穆、中期的阔大沉雄发展,在晚期形成了典雅庄重的造型艺术。从孝元帝开始到东汉,汉代文化发展进入到鼎盛时期,儒教神学、美学思想发展迅猛,形成了装饰之“美”是体现“天”的意志的观点,通过设计形式展现严格的等级制度,通过纹络图案表达区分不同等级。皇权与贵族对漆器餐具的喜爱,加速了漆器艺术的升华,融权贵、神学崇拜、美学于一体,成为皇权与贵族气息展现、彰显身份显赫的载体,将美学实践推到顶峰时期。
到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及神学崇拜受到新思维的批判,融权贵、神学崇拜、美学于一体的设计思想受到一定影响,当时权贵威严、神学崇拜与追求世俗之美两种设计理念并存,从表现“山神海灵”的唯心主义美学向“鞍马人物”的唯物主义美学转变。随着王朝的衰落,奢华的漆器艺术发展进入萧条期,数量骤减,加之受“致用为本”的美学思想的影响,逐渐失去了装饰之风,趋向实用化与世俗化发展,回归民众。
2.2 汉代漆器餐具的整体造型设计分析
2.2.1 造型具有简约实用、形态写实
通过对汉墓中出土的漆器餐具整体造型设计的分析,其造型具有简约实用、形态写实等特点。如:汉代初期的马王堆汉墓的内装七件小耳杯漆耳杯套盒(如图1)就非常简约实用。这是一个套装式的食盘套盒,盒身由上下两部分合扣而成,盒内的空间刚好能容下整齐叠放的七个大小相同的食盘,其中六个顺叠和一个反扣。盒子和盘子的造型都是以方中带圆的椭圆形为主,盘子的长边两侧边各有一耳,耳的形状延伸了盘子的方中带圆的月牙造型,沿着盘身是弧度微微上翘,设计线条流畅而统一,耳的设计便于拿取,在功能性的造型设计下,又富于装饰的艺术美感。马王堆汉墓的漆绘盥洗器(如图2),整体依然采用了方中带圆的造型设计,一边延伸出一个凹槽式的把手,把手设计不但有利于抓拿,把手设计成凹槽造型还有利于倒水引流。这两件作品无论是从圆润饱满的整体造型设计,还是空间设计的合理安排,都呈现出一种平衡而稳重、恭谨而静穆的视觉效果。

图1 马王堆汉墓内装七件小耳杯漆耳杯套盒

图2 马王堆汉墓漆绘盥洗器
2.2.2 增加动物元素,丰富趣味性
在西汉时期,设计元素增加了动物的造型,丰富了汉代漆器餐具的趣味性。如江苏的扬州市西湖乡胡场二号西汉墓出土的“彩绘马头形柄漆勺”、十四号西汉墓出土的“银扣彩绘鸭形漆勺”,整体则为鸭子挺胸抬头的造型,鸭身部分为勺体,鸭头和颈部为勺柄,这种勺子的造型生动写实,将实用性与装饰性巧妙地融为一体。可以看出汉代餐具设计工匠匠心独运的设计理念和对器物实用性以及功能性设计的思考,在发展中,还融入了一些生活的情趣,增强了餐具的亲和力、美观性与趣味性。
2.3 汉代漆器餐具的纹样造型分析
2.3.1 纹样造型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汉墓出土的餐具造型设计的美学思想与审美原则不但表现在它的整体造型上,在纹样造型的设计也充分体现了出来[4]。在秦楚文化以及儒道思想的影响下而发展出来的汉代漆器的纹样造型艺术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汉代餐具上的纹样造型有自然景象、动物形象、几何纹样等[5]。马王堆汉墓的内装七件小耳杯漆耳杯套盒(如图1),盒身接近底部的下半部分用云气纹装饰,接近边缘的上半部分以几何纹样装饰,盒内的七个盘子都以几何纹样装饰上半部分,与盒身形成呼应,其余部分单色无纹,整体呈现出简约大气、和谐统一的美感。
动物纹与云气纹结合的纹样造型设计也极具艺术魅力。马王堆汉墓凤鸟云纹漆盒,盒身由对称的上下两部分组成,盖顶中心纹样造型运用了三足鼎立的构图方式,使三只凤鸟回首顾盼神飞的姿态组合成平衡式纹样,凤鸟身上的羽毛细如发丝,其间以云气纹搭配,使整个图案组织严密对称,线条流畅,达到对称中有变化的艺术效果。盒身的外壁以较粗的线圈形进行疏密变化的装饰,与纤细的纹样造型形成鲜明的对比,无形地产生了节奏感与韵律感。粗线圈之间形成的空间,一部分用云气纹和几何纹样进行装饰,另一部分则留白,形成空气的流动感与艺术设计的呼吸感。
2.3.2 纹样造型的功能性
除了图案纹样的装饰,漆器上还出现了一些标识性文字,标明容量和用途,进一步体现汉代对于功能性的审美要求。马王堆汉墓“君幸酒”云纹漆耳杯和马王堆汉墓“君幸食”漆耳杯,整体造型相同,但前者内壁中间书“君幸酒”三个字,为“请君饮酒”的意思,耳背书有“一升”二字,表示容量,内壁有云气纹装饰;后者内壁中间书“君幸食”三个字,为“请君吃食”的意思,耳背书有“一升半升”四字,内壁无纹样单色装饰。两者一个是盛酒的,一个是盛食物的,盛酒水时可以看见耳杯内壁的底部,其耳杯内壁则有纹样装饰;盛食物时看不见耳杯内壁则无纹样装饰,体现了纹样装饰与功能设计的密切关系。在马王堆出土的每件耳杯都写有“君幸食”或“君幸酒”的字样,可见,当时对器物的要求分工明确。这些都说明纹样造型设计对功能性中合理分配的要求。
2.4 汉代漆器餐具的色彩分析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对色彩的崇拜,“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楚人尚红”等等描述散见于各种古代文献资料中。汉墓餐具的色彩以红和黑为主,基本沿承了楚国的色彩审美观念,大面积采用红与黑互为底色、相互置换,使色彩更加和谐、丰富,运用金、白、绿、灰等其他颜色,小面积点缀在红与黑之间,增强色彩的节奏感、韵律感。[6]
马王堆出土的耳杯器形多为外壁施黑漆,以红漆在黑漆底上绘图或写字;内壁施红漆,以黑漆在红漆底上绘图或写字。内红外黑的色彩搭配形成内外区别的空间感。此外,为了使整体的装饰具有对比性,时常在动物头部、翅膀及器物其他某些部位的结构线上,使用小面积金色加以点缀,让整个画面产生具有活力的跳跃感,赋予了很强的生命力。[7]沉稳的红色很好地包容了金色的热烈,使整个器物显得活泼、可爱。漆器上的红色与黑色相互映衬、相得益彰,在稳重的黑色衬托下,炙热的红色达到了完美的色彩呈现。
2.5 汉代漆器餐具的工艺分析
汉代漆器餐具的工艺已经非常成熟,新材料的出现与更新,使得工艺不断朝新的方向发展,衍生出更多的装饰手法与工艺。在延续战国的彩绘、锥画等装饰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出新的技法,如金银箔贴、镶嵌、堆漆等,使汉代餐具独具特色。[8]其中彩绘装饰是汉代漆制餐具的主要装饰形式,彩绘包括了漆绘和油彩,结合新的技法使得装饰纹样更丰富多彩,更具层次感,展现出汉代丰富的文化内涵。
2.5.1 漆绘
漆绘是用生漆制成半透明的漆液,以色入漆调和成不同色彩的颜料,描绘在已上漆的器物之上,色泽光亮,且不易脱落,大部分的漆器纹饰都采用这种绘描技法。汉代之前采用平涂为主,汉代时期则以线描为基本手法之一。纹饰细腻流畅,毫无滞涩感,是刚与柔的完美呈现。
2.5.2 油彩
由于漆器上的白色、浅黄、天蓝、灰绿等一些浅淡的颜色用漆无法调出,所以出现了用桐油调制这些浅淡的颜料,绘描于已涂漆的器物上的油彩;但油彩描绘有一个缺点,就是所绘纹饰会年久老化,变得易于脱落。
2.5.3 锥画
锥画,也称为“针刻”,这种技法源于战国时期的针刻文字,用针或锥子尖在已上漆的器物之上刻出线条的纹样;有的将刻出来的线条缝隙内填入金彩,产生了金银错纹饰的视觉效果,且细若游丝、飘动流畅。马王堆的三号墓中就有部分漆器是用这种技法做的雕饰。
2.5.4 金银箔贴
金银箔贴是汉代出现的新技法,它是用金箔或银箔锤制成各种薄片图纹,用漆液贴在器物上,涂漆,打磨至光亮,最终使金箔或银箔与漆面形成一个平面,整体呈现剪影的效果。
2.5.5 堆漆
堆漆是西汉时期的新工艺,是利用漆液黏稠而不易流动的特性,层层堆起,使得图纹产生立体感,可形成一种浮雕的效果。
除了以上介绍的常见的工艺技法外,还有刻灰、雕漆、刮绘、镶嵌等技法,每一种技法都各具特色,倾注了当时人们的智慧,展现了汉代时期的审美与文化。同时,汉代漆器餐具还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文化内涵。
3 结语
餐具,是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最直接、最真实的映射,是中国特有的手工艺制品,汉代的餐具设计是中国发展史的巅峰时期,无论是设计造型还是工艺制作,都达到了超高的水准,出土的汉墓漆器就证明了这一点。从战国时期发展到汉代,其无论是在制作技艺还是文化内涵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从汉代的漆器餐具看其简约、静穆而古朴的设计艺术特色,再从其实用、美观与趣味兼具的设计特点可见,与现代的审美趋向非常契合,为现代艺术设计提供了优秀的源文化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