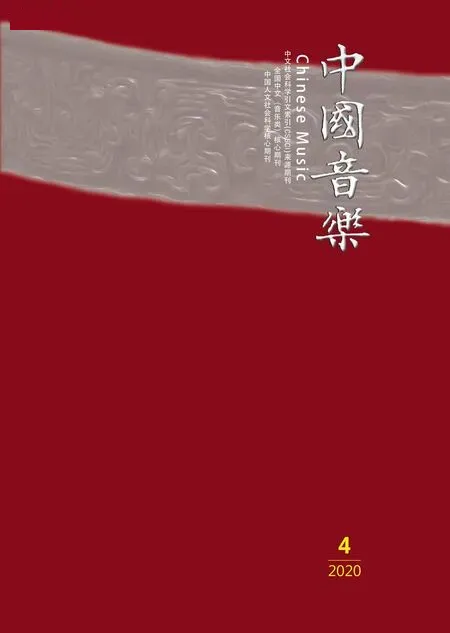从乐器研究到表演研究
——丝绸之路上的抱弹类鲁特及其演奏传统
○徐 欣
从20世纪中期迄今,中外学者的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丝路”)音乐研究在对象和视野上呈现出了不同层次。其一是以丝路沿线不同音乐品种、地区、民族、国家等为单位开展的微观与中观研究,其二则是将丝路音乐作为整体线索展开的宏观思考。从不同路线而产生的研究分野上来说,体现在对绿洲、草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区别探讨。此外,以时代与方法为限,还可以分为以史料为基础的古代丝路音乐研究(包括乐谱、乐律、乐人、乐队、乐像、乐器)以及以活态存见为基础的当代丝路音乐研究,本题所涉及的抱弹类鲁特便以此为理论背景展开。
广义的丝路沿线地区广泛分布着不同类型的抱弹类鲁特,其脉络多样,数量丰富,仅中国各民族所拥有的就有五十种以上。如果从其器名词源出发来辨识,或可将其分为七大系统,即塔尔类(如北印度、西亚西塔尔,维吾尔族都塔尔等);弹拨尔类(如土耳其弹拨尔、维吾尔族弹拨尔等);热瓦普类(如新疆各少数民族热瓦普、西亚喇巴卜等);火不思类(如柯尔克孜族考姆孜、蒙古族火不思等);冬不拉类(如哈萨克族冬不拉、锡伯族东布尔等);琵琶类(如汉族北方说书中的琵琶、福建南音琵琶、日本琵琶等);三弦类(如汉族民间曲种中的三弦、蒙古三弦、日本三味线)。诚然,如此划分只是基于初步的脉络梳理,并不是具有唯一合理性的分类,但其中体现出的对于源流关系,或者说对于一件乐器在历史和不同文明之间如何互动的问题意识,实际上呼应了诸多音乐历史学家和民族音乐学者长期以来的思考。丝绸之路作为一条通道,它所呈现的复杂性与种种“走廊型”或“中间型”地带的文化层叠与复合有所不同,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带状的流动(mobility),不但为物质形态(从丝绸、皮毛、金属到乐器等等)和非物质形态(从思想、语言、制度、技术到曲调等等)提供了互通有无的基础,其自身也成为了一种交流的象征。基于这种历史的空间流动性及其互相影响,丝绸之路音乐研究在诞生之初便携带着一种“关系主义”视角,不论是史学领域的源流考辨,还是以当代存见为依据的现象研究,都存在一种将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化、整体化的取向。本文要讨论的是,如果把丝路上的音乐作为一个可以贯通探讨的区域,除了将抱弹类鲁特作为“乐器”而从其物质层面加以考察之外,是否可以从“器乐”的表演实践角度进行再度探讨;在研究手段上,除了借助实物、图像与文本等史学材料,是否可以从活态抱弹类鲁特表演的田野资料中寻找新问题,建立新联系。
一、乐器学视角:基于物质与文本的丝路抱弹类鲁特研究
从研究方向来看,相关的史学研究是非常活跃的领域,其考察的重点是具有中外音乐交流史意义的历史关系研究。早期成果如日本学者林谦三集中讨论的三弦、火不思、阮咸、琵琶几样乐器与波斯、阿拉伯、新疆以及中亚类似乐器的脉络(1956年)①参见〔日〕林谦三:《东亚乐器考》,钱稻孙译,曾维德、张思睿校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比较晚近的则有梁秋丽、周菁葆对丝绸之路各个国家和地区弹拨尔历史记载的整理(2015年)②⑪参见张欢:《丝绸之路与中外乐器交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中亚音乐研究”结项成果文集(内部资料),2016年。,吉娅·贾妮珍(Gisa Jähnichen)从图像学的观察中探讨丝路沿线的横码鲁特与演奏家性别之间的关系(2019年)③参见〔德〕吉娅·贾妮珍:《迁徙的鲁特:丝弦和性别意识》,邓晓斌、尹翔译,载〔美〕韦慈朋、萧梅主编:《丝绸之路上的抱弹类鲁特: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从古代到当代表演》,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9年,第378–399页。该文最早发表于2016年“丝绸之路上的抱弹类鲁特”(上海音乐学院)专题研讨会。,亚历山大·朱马耶夫(Alexander Djumaev)对近年来在粟特、安息、石国、费尔干纳、巴克特里亚——吐火罗斯坦、花剌子模等地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器物与壁画上的弹拨鲁特图像做了研究,并对“陶俑的表演目的”等问题做了探讨(2016年)④参见〔乌兹别克斯坦〕亚历山大·朱马耶夫:《中亚抱弹类鲁特:从图像、描写到音乐实践》,发表于2016年“丝绸之路上的抱弹类鲁特”(上海音乐学院)专题研讨会。,等等。同时,以琵琶为主线,牛龙菲(1985年)⑤参见牛龙菲:《古乐发隐》,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岸边成雄(1988年)⑥参见〔日〕岸边成雄:《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王耀华、陈以章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年。、陈应时(2003年)⑦参见陈应时:《龟兹五弦琵琶东传日本考》,《丝绸之路》,2013年,第4期。、赵维平(2006年)⑧参见赵维平:《中国与东亚诸国的音乐文化流动:赵维平音乐文集》,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等学者的研究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丝路抱弹类鲁特的互动与源流。音乐考古方面则有对于乐器出土实物的考察,如《新疆丝路沿线出土琵琶类乐器及其音响复原构想》(2016年)⑨参见吴春艳、张寅:《新疆丝路沿线出土琵琶类乐器及其音响复原构想》,《音乐研究》,2016年,第3期。,历史与当代实践相贯通的综合研究则有索依达什(Soydas)对土耳其库普兹历史与当下流布的梳理(2019年)⑩参见〔土耳其〕M.埃敏·索依达什:《史实、传说与当下关联:以土耳其古代乐器库普兹为例》,黄建清译,载〔美〕韦慈朋、萧梅主编:《丝绸之路上的抱弹类鲁特: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从古代到当代表演》,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9年,第355页。该文最早发表于2016年“丝绸之路上的抱弹类鲁特”(上海音乐学院)专题研讨会。,以及张欢在丝路与中外乐器交流的主题之下,对热瓦普(喇巴卜)、弹布尔的历史源流和当代存见的分别论述(2016年)⑪等等。
丝绸之路的流动性不仅仅局限在历史,也通过时间之河流动到了当代,这使得它们既是历史遗产,也是当代各个音乐文化传统中的传承。因此,基于实地考察的共时探索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萧梅曾提出,丝路上的抱弹类鲁特需要得到史学和人类学的共同关注,并组织召开了“丝绸之路上的抱弹类鲁特”专题研讨会(2016年10月,上海音乐学院)。在这次会议上,凯瑟琳·弗瑞泽(Katherine E.Freeze)的《丝绸之路从中亚到印度和西藏的弹拨鲁特Ko-phongs》从三个地区Ko-phongs的外形到三类不同的音乐家通过对这件乐器的演奏风格来建构其文化身份上的认同问题,展现出器物——乐人——音乐之间的关系;而詹妮弗·C.珀斯特(Jennifer C.Post)的《声音材质、皮和骨:欧亚商贸之路上的鲁特与生态》则重点强调丝路传播地点与鲁特琴物质性变迁的关系,讨论了乐器材质的地理文化内涵⑫参见〔美〕詹妮弗·C.珀斯特:《声音材质、皮和骨:欧亚商贸之路上的鲁特与生态》,邓晓彬译,载〔美〕韦慈朋、萧梅主编:《丝绸之路上的抱弹类鲁特: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从古代到当代表演》,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9年。该文最早发表于2016年“丝绸之路上的抱弹类鲁特”(上海音乐学院)专题研讨会。。
通过以上概述不难看出,已有研究在范畴上均将视野置于相对广泛的历史空间里,从而呈现出丝路抱弹类鲁特的差异与同质性,而在研究材料上大多还是以文献、图像与实物为主,方法上侧重特征描述、律调分析,以及源流考证与古今流变。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发现,已有的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在空间视野上有其特定倾向,史学领域对丝路抱弹类鲁特关系的探讨,多将汉地乃至东亚的琵琶、三弦等包括在内,而在共时研究(或是综合研究)方面其线索的最东端则止步于新疆。这同时也体现出第三个问题——丝绸之路不同线路在研究中的分离,即以新疆为界,向西、北方向的陆上丝路与中原汉地以东的海上丝路东海航线之间仍缺乏贯通的普遍观照。
此外,仅仅从历史探索的角度而言,将抱弹类鲁特视为一件乐器而考察其名称、材质、形制只是一个方面,若想让乐器发声而成为音乐的一部分,则必定与人的表演实践相关。然而,如何考察历史性的表演实践?相对于观看乐器实物,我们似乎难以用同样的清晰明确来观察已经走入历史的乐器表演,但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陷入困境的命题。我们可以通过或变形、或写实的再现来观察图像学信息,从而做出相对可信的判断。从敦煌音乐图像到波斯细密画,再到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油画中的音乐场景,丰富的视觉描写为观看音乐表演提供了可能;我们也可以以乐器的物质形态为基础,建立其与身体行为的关系,例如琵琶,有拨子和无拨子时的右手奏法不同,音色各异;卧弹与竖弹时,左手在持琴感觉和按弦空间上不同,音效乃至功能也各异;骑行、步行、站与坐、边舞边奏的姿态也会带来差异,等等。此外也可以通过文献释读的方式,例如:从孙该《琵琶赋》中“抑扬按捻,拰搦催藏”之“下按”“上抬”“揉弦”“吟弦”技法分析出常态乐音、韵音等几种典型的微观手法和乐音变化,又可从“仪蔡氏之繁弦,放庄公之倍簧”来判断琵琶演奏中既有连续发声的动作,也有左右手配合中多弦并用的多音奏法和音乐声⑬陈岸汀:《弹法——音效——情态:魏晋三篇〈琵琶赋〉典型演奏手法及音乐风格情态研究》,《中国音乐》,2019年,第4期,第84、86页。。真正的困境在于,实物、图像与文字都是静态的,与切实的活态表演之间依然存在距离。首先,无论是对身体姿态的观察,还是对音响形态的拟构,都必须在实际操演中才能真正地将其关联起来;其次,这些可以被观看的字与像,在某些程度上,也不免陷入匠人工艺的不求甚解或是艺术再现的二次创造,从而带来误读的可能。事实上,一些从静态的观看中得到的历史疑问,譬如敦煌壁画上的反弹琵琶是否真的存在,花边阮是否可以发响并被演奏,鼓吹的喧闹与丝竹的清雅是否真的可以合乐⑭上述对敦煌图像是否能够还原为真实表演的讨论,源自李玫、张振涛、萧梅等人在2018年9月12日上海音乐学院首届邀访学者之一、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朱晓峰之讲座《解读敦煌音乐——以图像和文字为手段》上的相关发言。等等,都可以将其还原至表演实践当中加以重新考量。最后,历史语境中的乐器、图像与文字都是孤立的,只有当代的人的活动才能将它们之间勾连起来从而呈现其流动,从学术研究直到仍在延续的表演实践皆是如此。当然,以上讨论并非在质疑围绕实物、图像与文献展开研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与此相反,上述材料是叙述历史的基本维度,亦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只需要连接起另外一环,即通过活跃在丝绸之路沿线的抱弹类鲁特类乐器及其表演传统(包括独奏传统与弹唱传统),在与已有研究成果彼此参照的过程中窥见一种基于经验的历史想象,是为历史与当代的互相阐释。
二、表演实践视角:基于弦功能活态考察的丝路抱弹类鲁特研究
所谓表演的活态特性,在激活身体感觉和声音体验之外,还表现出既基于物质性,又超越物质性的特征。因此,在演奏观念和身体能动性的作用下,会带来多样的演绎方式与声音结果。比如,陕北说唱琵琶书所使用的琵琶,虽为四弦但实调两音,即两根老弦定C,两根子弦定G,在伴唱中使用旋律加持续低音的演奏模式,形成了富有特点的定弦法与用弦法,这一现象曾在萧梅等⑮参见萧梅、孔崇景、张真瑞:《内亚视角下的陕北琵琶书》,《中国音乐》,2018年,第1期。与孔崇景的分析⑯参见孔崇景:《陕北说书琵琶的“多样性”调查研究》,2018年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中得到了相对充分的阐发。但实际上,中国学者观察抱弹类鲁特用弦的地理起始点并不是中原汉地,而是作为“中国内亚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的新疆与内蒙古。
(一)从“中国内亚边疆”到丝路东西两端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在记录新疆民族弦乐器时,对“其琴弦在演奏中如何扮演不同角色”这一问题便开始了认知与描写。其中有对维吾尔族萨塔尔“共鸣弦”概念的提出,如简其华(1957年)⑰参见简其华:《新疆的民族乐器说明》,1957年,油印本。、万桐书(1986年)⑱参见万桐书:《维吾尔族乐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等通过记写萨塔尔的定弦而区分出其中的共鸣弦;段蔷(2009年)⑲参见段蔷:《中国·新疆民族乐器制作图鉴》,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09年。则详细记录了新疆各民族共47种乐器的用弦,经萧梅、孔崇景整理归纳,发现可将其分为“主奏弦+演奏弦”“主奏弦+伴奏弦”“主奏弦+共鸣弦”等六种弦功能类型。近期,肖振新(2016年)⑳参见肖振新:《新疆维吾尔萨塔尔研究》,2016年中国音乐学院硕士论文。针对萨塔尔共鸣弦,从弦鸣原理、产生因素、声学分析、审美等多角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并延伸讨论了北印度萨塔尔、维吾尔族热瓦普等带共鸣弦的乐器。在国外学者的著述中,也能发现对西亚与中亚地区相关问题的认识,如约翰·贝利(John Baily)在对阿富汗都塔尔的研究中曾提及“持续低音弦”(drone string)与持续高音弦的区别(1977年)㉑John Baily.Movement patterns in playing the Herati dutar.The Anthropology of the Body.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7.;阿卜杜拉施多夫(Abduvali Abdurashidov)也指出塔吉克斯坦弹布尔声音系统中主弦和辅弦的存在(2019年)㉒阿卜杜瓦里·阿卜杜拉施多夫:《弹布尔声音系统的基本结构》,康妮译,载〔美〕韦慈朋、萧梅主编:《丝绸之路上的抱弹类鲁特: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从古代到当代表演》,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9年。该文最早发表于2016年“丝绸之路上的抱弹类鲁特”(上海音乐学院)专题研讨会。。
学者们把新疆作为地理出发点之一,是直接以乐器弦制的类型化差异切入的。而内蒙古方面,以萧梅的系列文章为代表,则是从内亚地区多种双声音乐体裁的形态出发,回溯并聚焦至弦乐器的弦制问题。萧梅将内蒙古双声音乐(如“潮尔”“呼麦”等)置于境内外蒙古语族与突厥语族地区同类音乐现象当中,并在提出“弦功能”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把讨论以抱弹类鲁特为主的“主——辅”弦制的地理范围最终定义在一个具有空间开放性的欧亚大陆㉓参见萧梅:《文明与文化之间:由“呼麦”现象引申的草原音乐之思》,《音乐艺术》,2014年,第1期。㉔参见萧梅:《从“弦功能”再看亚欧草原的“双声结构”》,《音乐艺术》,2018年,第2期。。可以说,萧梅与肖振新等人以新疆为出发点的空间布局一方面有所重叠,即同时涵盖了新疆以及西亚与南亚,但又有所突破,即向中亚、蒙古乃至中国西北汉族地区做了延伸(2018年)㉕参见孔崇景:《陕北说书琵琶的“多样性”调查研究》,2018年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本文沿用萧梅提出的“弦功能”这一概念,并进一步将其理解为以“主——辅相协”的定弦法为物质基础,以实际演奏中“旋律——伴奏”的用弦法为动态展现的一种“弦制度”。可以说,丝路抱弹类鲁特在“弦数多样”与“弦制接近”上体现出的一致性,不仅仅存在于中国西北部少数民族、西亚、南亚与中亚、蒙古,同时也囊括了汉地民间说唱中的琵琶与三弦,并远及日本。以往并不显见的弦功能问题,恰恰是表演实践中最为突出的、能够将欧亚大陆抱弹类鲁特有机关联的重要线索。
(二)汉地琵琶的华化及其他
音乐史学领域对于丝路音乐传播流向的问题一向多有讨论,无论是西乐东渐还是华乐西传,亦多从物质的角度入手,尚未展开对表演技法源流的关注,而这恰是反观音乐文化之历史流动的重要方面。对于琵琶华化问题,我们已知琵琶弦材在唐宋时期经历了由鹍鸡筋弦到蚕丝弦的演化㉖参见曹川:《从琵琶用弦的演变看唐宋时期的胡乐华化现象》,《中国音乐》,2014年,第4期。,在演奏法上则废拨用手,从“横抱运拨”过渡到“竖抱摘阮”㉗参见陈岸汀:《华化与分型:汉唐琵琶的类型特征、演奏方式及其人文存在研究》,2015年中国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胡乐琵琶至此逐渐融入华乐传统。但这并不是我们可以考察琵琶华化问题的全部,从弦功能的角度,仍可以对演奏观念和演奏技法的“存与变”进行再度追溯与思考,这是因为在汉地抱弹类鲁特身上,既能体现出这种渐进的、历时的形/材制与奏法转换,实则还有空间性的当代弦功能留存。在汉地说唱(弹唱)音乐中的陕北琵琶书、江南弹词琵琶、南音琵琶当中,均存在外侧高音弦奏旋律,低音弦作为和音的情况,其中反映出两个问题:首先,当代汉族专业性琵琶的发展已经远离了主——辅弦制,表现出“器”与“技术”的分离,但在民间音乐品种,尤其是弹唱类音乐品种中却能找回这种演奏传统。这一方面可令我们重审“礼失求诸野”的民间对于历时源流研究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追问,是什么造就了民间琵琶与专业琵琶这种差异?论其本质,维持了弦功能的民间琵琶均为伴奏,而专业琵琶早已成为高度器乐化的独奏乐器,在审美和功能上既远离了“胡乐”,也远离了民间。从伴奏到独奏,从弦功能的普遍存在到专业和民间的分层,这种变迁应被视为琵琶华化的特点之一而得到更为深入的讨论。
从弦功能角度展开的抱弹类鲁特研究,其意义还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乐器”和“器乐”研究有时在研究中会处于彼此分离的状态。从演奏中的弦功能切入,以乐器弦制为基础,观察其在实际演奏中如何用弦,将为乐器和器乐研究的统一提供不可或缺的观察点。
第二,弦功能既是微观的,也是宏观的。通过微观层面的细致分析,可以厘清弦功能类型与乐器形制(插入柄式、颈柄式)、表演形式(弹唱、独奏)、乐器词源系统(塔尔系、弹拨尔系、热瓦普系、火不思系、冬不拉系、琵琶系、三弦系)等的关系,建立丝绸之路抱弹类鲁特弦功能类型学,继而通过弦功能的线索从宏观层面辨识几大区域文化圈、几大历史族系(波斯、突厥、蒙古、汉等等)和不同文明板块(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关系。
第三,从学科角度来说,弦功能研究从实质上补充了丝路沿线整体音乐研究的活态视野,弥合以往“重历时、轻共时,重史料、轻活态”的状态,从而推动整体丝路音乐研究、欧亚大陆区域音乐研究的实质性发展和丝绸之路文化传播、交流、变迁等研究的深入。
结语
在涉及历史和空间的关系研究当中,可作为基本单位的文化区域概念并不是单一的。就本文所探讨的对象而言,它既存在于“欧亚大陆”这个广袤的地理范畴,又隶属于丹尼斯·赛诺笔下所含甚广的“内亚”,而本文之所以以“丝绸之路”作为空间线索则出于两点考虑,其一是由于丝绸之路本身的历史延续性,其二是其中所象征的文化与文明的交流与互动。从这两点出发,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代研究,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既是研究对象,更是一种研究思路,为我们面对历史性的流动提供了当代视角的阐释,并最终将这种阐释回归于历史的长河。
本文虽然在时间范畴上强调当代,但更为首要的意图则在于研究视角上对表演实践的关注,以其“活”的内涵进一步理解以下两种动态关系。其一,尽管有其局限性,但历史性的表演实践也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被认识和分析。古今东西,无论在哪个时空维度上,我们皆可通过表演实践重新认识历史进程与空间流布之间的纵横延展。其二,表演以乐器的物质性作为前提,但同时又通过人的能动性完成了对物质性的超越。本文以“弦功能”及其制度性用弦为例展开探讨,强调了对结合乐器定弦与演奏用弦的丝绸之路抱弹类鲁特“弦功能”问题的观察,希望能够从一首首乐曲的弹奏,或一支支歌曲的伴唱中,来深入理解“器——乐——人”的连续统一。回到本文最初的论述,丝绸之路作为一条通道,在其间历史性流动并传承着的,不仅是有形之物,也有无形的、刻写在观念与身体之上的表演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