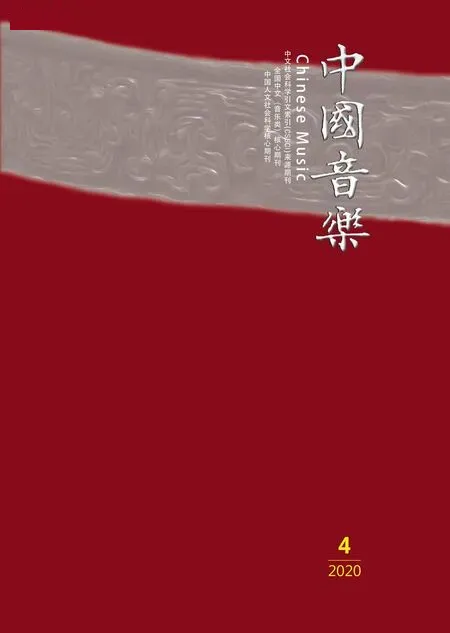口头传统的“逆时态”传承
——布仁初古拉“十八部蟒古思因·乌力格尔”到七山“北斗七星神灵”系列史诗的“传承”过程闻录及阐释
○李佳音
一直以来,“活态传承”是衡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合理与否的基本准则。从时间形态上来说,这种“活态传承”往往是“顺时流”的:通过活着的人的活态传承,推进文化的生命活力,并在传承过程中发展、演进。科学上,人们运用基因工程等科技手段进行逆向回溯、复原解析。那么,文化上我们可否利用现在的技术或科研手段,进行“逆时态”的恢复重建,保护文化的原始基因呢?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于2003年9月29日至10月17日在巴黎举行的第32届会议上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为“保护”下了如下定义,原译文是:“‘保护’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http://www.ihchina.cn/zhengce_details/11668.html),2003年12月8日。按照这一理念,“保护”应当是囊括了这九大方面的所有举措,而非其中某些措施的组合。那么我们以往的搜集、整理工作是否为保护工作本身?延伸地看,对逐渐消逝的文化进行“恢复重建”是否为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理念中“振兴”民间艺术的一种新形式?
从比较音乐学时代开始,无论出于猎奇还是实验的角度,人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对身边发生的传统进行保护。不同的时代,人们从保存、保护、抢救、复兴等不同的视角,建设了大量的传统资源数据库,以便后人量化传统文化基因。朝戈金提出通过学术机构、地方政府和民众,以及其他社会力量的合作建立“文化基地”,来保护培育类似生物基因的、极具生命力的、多样化的“文化因子”,进而提出了“文化因子”与“文化基地”好比“鱼”和“水”,通过提取鲜活的“鱼”的文化基因,让其在“文化基地”中生存,而非简单地对丧失文化活力的“鱼”进行标本式保留,②参见朝戈金:《“文化因子保护”与“文化基地建设”——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断想》,中国社会科学院IEL民族文学研究所(http://iel.cass.cn/2006/xscz/whyz_cgj.htm),2004年9月13日。这是文化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音乐学界,杨玉成提出:如果将传统音乐看成是一条鱼,这条鱼本应在原生的环境中生存,假使原生的河干枯了,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另外一条河;在另外一条河里如果仍然不能生存,我们可以将它放进鱼缸里使其继续存活;鱼缸里面还是无法生存,我们就把它捞出来当成标本保存。进而他将传统音乐的保护分成四种形态,即原生环境传承、次生环境保护、实验室保留、“标本”保存。这是一个从“原生环境”到“实验室”语境置换的过程。③引自杨玉成教授2016年对笔者的指导。萧梅曾将文明的价值比作基因,饱含着学者的文化自觉和对传统文化的担忧:“物种的基因库就是要有效地保存这些类型的基因,以备万一 ……而一个人类学者的责任亦如同基因库的建设者,一座人类的文化基因库。”④萧梅:《田野的回声——音乐人类学笔记》,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0–211页。几位学者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延续提出了一种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确保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恒久性的思路,即如何发挥富有生命力的、具有内在联系的遗传密码和核心元素——文化基因的作用,同时指出学者的责任担当。但是,按照民间文化“活鱼要在水中看”的原则,成为“标本的鱼”已失去了其鲜活性,它们经过风干等技术处理,看上去光鲜亮丽,可事实上生命已逝,即便放在鱼缸中维持其生命,但失去了它的“原生性”,其生命的“功能性”已然丧失。语境置换后的生存“虽然保留着其风格的原生性,但生存方式已经不再是原生形式,如要做到真正保护,尚需将它再放回到河里——虽然这条河也许不是它原来生活的河,但能保证它的自然生存”。⑤博特乐图、哈斯巴特尔:《蒙古族英雄史诗音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69页。河枯则鱼死,那么东西坏了是不是可以修,究竟失去的东西我们能否复原?枯鱼之肆又可否挽救?
近年来,应用民族音乐学逐渐在国内兴起。这“是一种受到社会责任引领的方法,把越来越广博的和深入的知识和理解从一般的学术目的引向解决具体的问题,可在特殊的学术语境中,或特殊的学术语境之外进行工作”。⑥张伯瑜:《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介绍和个人认识》,载〔加〕克里萨拉·哈瑞森、张伯瑜主编:《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理论与实践》“前言”,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7页。作为一个应用民族音乐学的科研类目,“科尔沁英雄史诗活化演唱”的恢复重建工作在内蒙古艺术学院民族音乐传承驿站⑦内蒙古民族音乐传承驿站于2011年7月挂牌成立,是文化部民族民间文化发展中心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研究与传承基地所属民族音乐“传承——研究——应用”综合平台。总站设在内蒙古艺术学院,目前已成立科尔沁史诗传承驿站等8个分驿站。驿站采取“流动站”的工作模式,一方面不断把具有精绝技艺的民间艺术家请进驿站,进行传承和研究,另一方面则与课题研究相结合,关注濒危乐种、珍奇乐种的传承人,将他们直接请进“驿站”,及时进行抢救、保护、传承。至2019年已有200余名艺术家进站工作。展开。本文意在选择其中一个与民间艺人合作的个案,描述这一工作过程,基于学者的研究和学术思考,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探讨这种非传统社会中面对面师徒传授,借助现代媒体,如何使科尔沁英雄史诗这一失传传统恢复演唱,进而探讨我们能否逆转“民间——实验室”这一思路:用“标本”在“实验室”里孕育,再将它还原到生态环境中去,让传统文化“反客为主”重新焕发活力,并在新技术与当下文化表达的符码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一、科尔沁英雄史诗的发现与遗失
在蒙古族文化长河中,英雄史诗以其宏大的叙事风格和独特的演述形式,经过一代代的说唱艺人不断编创和广泛传唱,形成了规模浩大、内涵深刻的史诗演述传统。在中国境内,不同地区也形成了不同的史诗演述风格。科尔沁英雄史诗,当地称“蟒古思因·乌力格尔”(manggus un üliger),流传于内蒙古科尔沁。⑧参见博特乐图、哈斯巴特尔:《蒙古族英雄史诗音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蟒古思”意为“恶魔”,“乌力格尔”意为“故事”,蟒古思因·乌力格尔便是“恶魔的故事”,讲述天神下凡脱胎人间的英雄迅速成长,在众神的帮助下消灭恶魔蟒古思,保卫家园,捍卫和平的故事。有无伴奏的讲述形式和有伴奏的演述形式两种。其中,有伴奏演述形式有潮尔伴奏和胡尔伴奏两种传统,均为自拉自唱形式。与此相应,学界又分别称之为“潮尔史诗”和“胡尔史诗”。潮尔史诗和胡尔史诗的区别,不仅是伴奏乐器的不同,二者演述系统和艺术风格迥异。“潮尔史诗”的演述艺人统称“潮尔奇”(cogurci),民间称“蟒古思奇”(manggusici),在潮尔的伴奏下以韵文体形式进行演述,其曲调自成体系,唱腔风格亦诗亦吟,同时具有很强的音乐性,与伴奏乐器之间形成纵向声部叠合的呼应关系。“胡尔史诗”的演述艺人统称“胡尔奇”(hugurci),他们是一群在胡琴的伴奏下既述史诗,又说书(乌力格尔üliger),也唱歌(叙事民歌 üligertü daguu),还能即兴说唱好来宝(holboga)的口头艺人。⑨参见博特乐图:《胡尔奇:科尔沁地方传统中的说唱艺人及其音乐》“绪论”,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胡尔史诗,受近代蒙古族说唱音乐胡仁·乌力格尔、叙事民歌、好来宝的影响,唱词散韵结合,表演说唱兼具,其音乐曲调多来自胡仁·乌力格尔曲调。
过去,科尔沁史诗的演述传统曾经作为科尔沁地区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活跃于民间。科尔沁地区有记载的史诗艺人有:琶杰(1902-1962年)、毛依罕(1906-1979年)、包·那木吉拉(1920-1990年)、那顺特木尔(1880-1945年)、巴拉吉尼玛(1900-1966年)、根敦(1857-1922年)、朝鲁(1881-1966年)、敖力道(1936- )家族等。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学界虽然亦展开了搜集整理,但由于科尔沁史诗本身特征不易融入当代中国社会生活,随着老艺人相继去世,这一流传千年的传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世界。
21世纪以来,科尔沁史诗重新进入学术视野。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的蒙古族青年学者陈岗龙,2002年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发现了一个叫齐宝德(1945-2010年)的胡尔奇。这位时年五十多岁的说书艺人,在胡琴的伴奏下,演唱了一部叫《铁木尔·森德尔·巴图尔》的史诗。陈岗龙对这部史诗的文本以及齐宝德的演述方式进行了研究,作为他撰写博士论文《蟒古思故事论》⑩参见陈岗龙:《蟒古思故事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的重要依据。陈岗龙对齐宝德及其蟒古思因·乌力格尔的发现和研究,使学界对胡尔系统的科尔沁史诗演述有了初步认识。然而,学界中所说的“潮尔史诗”却像一个尘封的谜,学者们只是从零星的记载中了解到它过去的点滴,却从未见过其现世的活态存承,尤其是民间传说中的“十八部蟒古思因·乌力格尔”,成为学界“可望而不可及”的文化悬案。
根据陈岗龙提供的线索,当时正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的杨玉成⑪杨玉成(博特乐图)(1973- ),男,蒙古族,内蒙古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找到了齐宝德。当时,中国音乐学院正在实施“中华传统音乐文化资源库”项目,于是杨玉成把齐宝德带到中国音乐学院,录制了这部科尔沁英雄史诗《铁木尔·森德尔·巴图尔》,共13小时。在博士论文的调查与研究中杨玉成发现,这些以说唱乌力格尔、叙事民歌和好来宝为主的胡尔奇,早期像琶杰、毛依罕等艺人与今天的齐宝德一样会唱史诗。然而让他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这个承载了蒙古族古老文化和宗教渊源,具有千年历史并广泛流传于几乎蒙古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却在近一个世纪以来以惊人的速度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销声匿迹了?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于是杨玉成申请到了全国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蒙古族英雄史诗音乐的抢救、保护及研究”,并从2005年开始在内蒙古各地展开了田野调查。然而,虽然发现了一些有关史诗的碎片信息,但除了上述齐宝德及其《铁木尔·森德尔·巴图尔》外,再没有找到其他活态存承的史诗。
2006年的一天,杨玉成偶然从电视上看见有个叫布仁初古拉的艺人在潮尔的伴奏下说唱《十二个头的阿尔扎克蟒古思》。这是一个他从未看过和听过的形式:只见这位身材高大的艺人,在潮尔低沉浑厚的伴奏下,用极具气魄的旋律吟唱勇士与恶魔蟒古思战斗的情节——同样是“蟒古思的故事”,但其演述风格与齐宝德的《铁木尔·森德尔·巴图尔》完全不同!让他兴奋的是,布仁初古拉的伴奏乐器潮尔被认为是一件濒临失传的古老乐器,且用其伴奏的英雄史诗演唱传统被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断流。于是他顺着线索多方打探,最终与布仁初古拉取得了联系,邀请他到呼和浩特进行交流。
2006年8月,布仁初古拉从家乡科左中旗来到内蒙古师范大学。简短的交流之后,更让杨玉成欣喜的是布仁初古拉能够完整地演唱被学界认为早已失传了的“十八部蟒古思因·乌力格尔”,而且还掌握另外五部史诗,共计一千余小时!⑫参见博特乐图:《远去的绝唱——记布仁初古拉及其史诗的发现与保护》,《草原歌声》,2011年,第4期。重要的是,布仁初古拉完整地掌握着科尔沁潮尔史诗演唱所用的9套21首曲调——这是一套自成系统的曲调库,与他的史诗演述融为一体,形成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杨玉成将这位史诗艺人请到学校,对其进行录音录像、口述访谈、专题研究以及安排学生传承他的史诗演唱,同时聘请布仁初古拉为特聘教授,并为他举办音乐会……
2008年6月,布仁初古拉录制完成十八部蟒古思因·乌力格尔中的《宝迪嘎拉巴可汗》《阿斯尔查干海青把秃儿》《道希把拉图把秃儿》等前三部史诗,共46小时;录制了10首叙事民歌,1个多小时;期间,他还向内蒙古师范大学和内蒙古艺术学院一些教师、学生传授了潮尔和史诗演唱技艺;同时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的积极努力下,2007年科尔沁潮尔史诗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布仁初古拉的发现,科尔沁潮尔史诗当下的活态样貌渐渐浮出水面。试想,21世纪,如果将十八部蟒古思因·乌力格尔整理出来,那么这将是人类口头艺术史诗学领域里的一个奇迹。我们整理出来的科尔沁英雄史诗有几个以活态的形式存在?但是这份珍贵遗产恰恰由布仁初古拉承载着。
然而,正当布仁初古拉和项目组成员沉浸在这个好消息所带来的喜悦中,并准备进行下一步录制和传承工作时,布仁初古拉被查出罹患胃癌晚期,突如其来的病魔瞬间将其击垮,高大的身躯也迅速瘫倒在床,在病榻上挣扎数月后,于2008年8月28日与世长辞。
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德国著名蒙古学家瓦尔特·海希西⑬瓦尔特·海希西教授(Walther Heissig 1913——2005),波恩大学教授,德国著名蒙古学家,曾在中国境内科尔沁地区进行调查时打听到关于科尔沁“十八部蟒古思因·乌力格尔”的消息,并且找到了著名潮尔奇那顺特木尔的外孙色楞,记录下了他口述的两部史诗。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找到完整的“十八部蟒古思因·乌力格尔”。到21世纪的陈岗龙、杨玉成等学者,在长达三十多年的科尔沁英雄史诗找寻过程中,布仁初古拉的出现成了科尔沁英雄史诗活态呈现的最后一次邂逅。而布仁初古拉的逝世,昭示着一个潮尔史诗说唱艺术的活态传统,再次消失在公众视野。至此,科尔沁潮尔史诗的活态传承似乎也随着布仁初古拉的离世戛然而止。收录布仁初古拉6首潮尔史诗唱段和10首叙事民歌的CD光盘《远去的绝唱——穆·布仁初古拉科尔沁潮尔史诗、叙事民歌演唱专辑》是项目组应布仁初古拉最后的夙愿赶制出版的专辑。没能等到这部专辑的出版,成了布仁初古拉短暂史诗演唱生涯中最大的遗憾。正如杨玉成在该专辑的后记中写下的那样:“失而复得的千古绝唱,我们难道无法挽留你远去的脚步吗?”⑭穆·布仁初古拉:《远去的绝唱——穆·布仁初古拉科尔沁潮尔史诗、叙事民歌演唱专辑》“后记”,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音像出版社,2008年。
二、口传史诗恢复重建的学理思考
布仁初古拉承载着完整的十八部蟒古思因·乌力格尔大型串联史诗以及其余五部史诗,同时他用潮尔这一濒临失传的乐器伴奏,演唱技法别具一格;他的科尔沁潮尔史诗演述,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蕴含着高超的口头艺术思维方式和精绝的口头艺术技艺,以音乐为例,布仁初古拉运用史诗曲调的奥妙不在于其曲调本身,而是在具体的演述当中,即如何相互灵活组合以及变换使用等;他所用的音乐曲调共9套21首,在具体的口头演述当中能够自由变化,衍生出无数变体……的确,布仁初古拉不仅让学者们了解到了与科尔沁史诗共生的古老乐器潮尔,更重要的是发现了科尔沁潮尔史诗极为宝贵的音乐风格、演唱技艺和源远流长且自成体系的演述传统,这是有别于任何一种蒙古族传统音乐的独特样式。然而,布仁初古拉的逝世,使本来按部就班的录制工作和传承规划不得不停下来。但项目组对此并不甘心,开始大胆地想象:有没有可能让断裂的传承链重新接续起来,我们能否实现失传史诗的活化演唱?其实,在发现布仁初古拉之前,杨玉成便与著名胡尔奇扎拉森⑮扎拉森(1950- ),男,奈曼旗人,蒙古族说唱艺术家,自治区级传承人。合作,试图继续让扎拉森学习布仁初古拉的套路,并凭借他出色的口头演述能力,将史诗以即兴演述的形式呈现。然而,结果并不令人满意。⑯同注⑧。其原因,一是学术准备不足,对史诗的演述传统了解不深,另一方面,扎拉森根深蒂固的胡仁·乌力格尔演述惯习,使得他无法转换成潮尔史诗演述思维,演述出来的是用胡仁·乌力格尔套路完成的史诗。
2010年,随着杨玉成调离工作单位,科尔沁英雄史诗的恢复演唱工作再度中断。
2012年12月21日,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来到内蒙古艺术学院民族音乐传承驿站找到杨玉成教授。这位名叫七山⑰七山(白其山)(1978- ),男,蒙古族,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人。的牧民说,在电视中看到一期杨玉成教授关于乌力格尔的访谈节目,自己酷爱胡仁·乌力格尔,但始终没有机会学习。此次从内蒙古东部的兴安盟科右中旗千里迢迢来呼和浩特,就是想得到杨玉成教授的帮助,圆自己学习乌力格尔的梦想。
交谈中,七山的经历和文化背景,引起了杨玉成的兴趣:这位不会拉胡琴、不会说书,甚至没见过潮尔的年轻艺人,小时候听同村一位叫伐喇嘛的老人给他详细讲述过一套由七部组成的“北斗七星神灵”系列史诗故事;他虽然高中都没读完,但自幼喜爱阅读,而且养成了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下来的习惯——他不仅将伐喇嘛讲述给他的史诗故事熟记于心,而且记录了下来。这使项目组兴奋不已,一个大胆的想法迅速呈现在眼前——与七山合作,将他掌握的七部史诗激活并恢复演唱!
可是难题也随之而来:七山对史诗等口头演述技艺丝毫不了解,他不认识布仁初古拉,不识乐器,甚至没见过潮尔,更谈不上演述史诗了。然而,这位年轻人对学习史诗有着强烈的愿望,他的执着和决心让团队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启动了科尔沁潮尔史诗恢复演唱的试验。
基于对以往实践中经验教训的反思,团队为此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思考和周密的工作规划。杨玉成曾经对蒙古族说唱音乐、史诗、叙事民歌及艺人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研究,发现口传音乐的传承有几个核心特点:“首先,口头艺人掌握的是套路,而不是文本本身。一名艺人只要掌握了套路,就能把新的故事‘装入’到已有的‘套路’当中进行新的故事的演述。这里所说的‘套路’包括故事、音乐曲调、语词程式、风格、技艺、演唱技法、表演形式等,学习者通过‘学’与‘习’来掌握别人(包括师傅等任何模式对象)的‘套路’,最终形成自己的‘套路’。那么对于七山掌握的“北斗七星神灵”这套系列史诗的重建工作过程不应仅停留在史诗故事文本意义上的思考,而是将套路与既有故事如何进行对接,即将布仁初古拉史诗的演述套路和七山的故事文本相结合,把新的故事‘装入’‘旧套路’中,便能够完成一部书的演述。其次,口传音乐传承的关键在于‘学’与‘承’,非‘教’与‘传’,而且‘模仿’是民间最普遍、最有效的学习方式。所以,有了‘模仿对象’,便能实现学承。他发现,民间艺人学艺过程中,模仿对象不一定是师傅,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模仿对象’。口头传统的‘模仿’学承方法以及‘受者’的‘学’与‘承’在传承过程中位于核心性、主动性。而‘授——受’主体之间面对面互动的缺位,仍可实现技艺的传递”。⑱引自杨玉成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应用民族音乐学第六次国际研讨会”(2018年7月7-10日)上的发言。这里,“我们需要理解遗产建设中出现的交流技术所带来的广泛影响”。⑲〔美〕约瑟林·摩恩:《马特佩琴音乐在线化——津巴布韦东北部的在线学习、可持续发展和遗产回归》,殷石译,载〔加〕克里萨拉·哈瑞森、张伯瑜主编:《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208页。为了实现这种理解,我们就需要在已有的声像资料与文化传承人之间建立一个重要的联系媒介,去弥合这条断裂的鸿沟。那么我们拥有布仁初古拉的声像资料、已知“套路”,再针对艺人个体差异,同时借助数字声像资料和现代媒体技术,是否可以实现“模仿对象”的“镜像性在场”和模拟化的传承链建构,最终升华到艺人在“表演中进行创作”呢?这一切简单来说,口头艺人只要形成了某种“套路”,便能将新的故事“装入”这一旧的“套路”当中,通过演述进行融合,实现“表演中的创作”,新的演述就能够完成,史诗文本也能够生成。这是史诗从文本到表演意义上的飞跃。
那么,能不能让七山掌握布仁初古拉的“套路”,并把自己的“北斗七星神灵”“装入”其中,完成活态史诗的演述呢?
三、七山“北斗七星神灵”系列史诗恢复重建过程
基于以上学术思考,传承驿站与七山合作,开始了科尔沁潮尔史诗的恢复演唱计划:把布仁初古拉的技艺“附于”七山身上,将布仁初古拉的史诗演述“套路”与七山掌握的史诗故事融合起来,完成史诗演述。我们采取的方法是:教——根据布仁初古拉的潮尔伴奏辅助七山学习演奏潮尔;学——通过视频,模仿布仁初古拉的演述,掌握主题、典型场景、曲调变换、用词、演述风格等;习——通过录音,不断进行实践、练习。整个重建实验,也是杨玉成教授及其团队与七山进行合作、磨合、尝试、探讨及实践的过程。
从2013年12月至2018年2月间,七山一共六次到内蒙古民族音乐传承驿站,通过驿站项目组成员与艺人的协作,采取团队小组工作模式,利用布仁初古拉留下的音视频资料,对“北斗七星神灵”系列史诗进行恢复演唱工作。2012年12月,七山第一次进站,共7天。根据他的个人情况,传承驿站为七山配备了一些学习资料——布仁初古拉留下的演唱专辑,当年采访布仁初古拉时的音频以及一些英雄史诗蒙文书籍,驿站项目组成员与七山共同观看布仁初古拉演述视频,同时伊丹扎布老师为他制作了一把潮尔。提供的视频、音频主要是想让七山对蟒古思因·乌力格尔演述模式、基本风格、曲调运用等有所了解,提供的英雄史诗书籍是想让七山学习史诗的书写规范。在学习之初,七山由于没有唱和奏的基础,人声和乐器潮尔配合起来非常生涩,他不能准确地根据潮尔伴奏的提示音找到人声的音位,对潮尔伴奏也摸不清头绪。驿站项目组成员一边与七山观摩布仁初古拉演述视频,一边辅助他的潮尔伴奏学习。此次七山进站时间虽然较短,但是对科尔沁潮尔史诗有了初步认识。此后,七山回到老家,开始一边练习潮尔、学曲目,一边根据伐喇嘛爷爷的讲述,按照史诗演述规范整理、书写七部史诗中的第一部。
七山用了一年的时间练习潮尔伴奏,整理并书写了七部“北斗七星神灵”系列史诗中的第一部——《阿日本宝音图可汗》。2014年12月期间,他第二次来到传承驿站。这一次,七山开始尝试第一部史诗《阿日本宝音图可汗》的录制和口述史采访。这次七山运用了布仁初古拉的五支曲调,结合《阿日本宝音图可汗》故事场景看着书写文本进行录制,共计16小时。经过一年时间的学习,七山虽然初步掌握了潮尔史诗的基本风格、书写规范,具备了一定的潮尔伴奏能力,但是,由于没有说唱和演奏潮尔的基础,他对于伴奏与唱腔的配合、曲调与不同主题之间的转换上,仍不够熟练。例如,他对于曲调的使用很有限,在唱腔技巧的运用上相对单一,且找不到唱腔与伴奏对应的音位等。基于“模仿是民间技艺最直接有效的学习方式”的认识,我们和七山再次对照布仁初古拉的视频进行深入观摩,而观摩的关键在于探讨布仁初古拉演述的科尔沁潮尔史诗风格,包括语言,潮尔伴奏方式以及如何在不同故事场景中变换曲调等等。这种模仿与在民间不同,是一种离开语境、虚拟化景象似的表演,缺少民间场合的互动,也是一种相对静态的观摩模仿,从而在时间流中看到比较固定化的文本,而非民间瞬时流的表演。为了更方便在老家闲暇时观看视频,驿站为七山配备了相应的多媒体设备:一台便携式音视频播放器,两个32GU盘。七山利用在老家农闲或放羊的时候,随时随地观看和聆听“移动电视”中的视频和音频。
布仁初古拉的发现是整个科尔沁潮尔史诗保护传承的基础,他留给了我们一个潮尔史诗的演述“蓝本”,然而,这一“蓝本”并非一个“权威的精校本”⑳朝戈金:《“回到声音”的口头诗学:以口传史诗的文本研究为起点》,《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第8页。,我们不能仅仅将其作为文学样本来研究,或者套用研究书面文学的方式来研究民间口头传统。正如朝戈金所说:“口头诗歌是与文人诗歌有着很大差异的作品形式,不可以简单套用研究文人书面作品的方法来研究这些口头创作、口头传播的作品。忽视了它的特殊性,所得出的结论就难免是隔靴搔痒,似是而非。那么同样,以书面文学的诗学去阐释口传史诗的特质,也会影响到学者的正确评价和科学判断。”㉑〔美〕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译者导言”,朝戈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页。格物致知,是由于口头传统的口头性和变异性等固有特质,它时刻处于流动中,我们只能通过对布仁初古拉所演述的潮尔史诗的套路进行本质性的把握,将现有传统进行分析解构,再借鉴这种演述传统,结合不同艺人、不同技艺,将残缺的传统进行重构。而在重构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考虑到民间传统的口头性与变异性特质,同时也要观察到艺人们在表演中的创编过程。对于史诗的学习,七山并不是对布仁初古拉史诗文本从头到尾地背诵记忆,而是学习了布仁初古拉史诗演述文本中的“部件”。“部件”是无数个主题和主题链接,主题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特性修饰语,比如蟒古思的长相、战斗场景、勇士、行走等主题在唱词中的表述,是相对固定的单元,是需要背诵的基本元素,这些程式必须通过死记硬背。只有积累了一定的程式和主题,才能达到文本上的即兴,即在程式的基础上展开或者压缩,同时与特定的描述性、叙述性、抒情性等曲调结合,进行新故事的创编。正如杨玉成所说,“在口头演述当中,艺人用程式的手法按照主题所提示的叙事路线建构他们既传统又独特的演述文本”。另一方面,七山的主动性学习。七山利用在民间接触艺人的机会,走访多位艺人,用录音笔录下了不同艺人为他讲述的民间知识。
之后,七山分别于2015年4月、2015年12月录制了第二部《阿斯布日、塔斯布日把秃儿》(长13小时)、第三部《高娃乌兰哈屯》(长40小时)。模式与第一部相同,均为看着书写文本进行录制。直至第三部录制完成之时,七山经过与驿站团队合作结合自身练习,已熟知潮尔史诗演唱的基本风格、书写特定程式,对结构单元、主题、程式、曲调、典型场景等演述因素有了规范把握,潮尔伴奏与人声的配合日趋熟练。
仅从表演的角度来看,七山的“北斗七星神灵”系列史诗是从布仁初古拉的“十八部蟒古思因·乌力格尔”所“孕生”出来的。在“新瓶”中装入“老酒”,将布仁初古拉的蟒古思因·乌力格尔的表演套路附载于七山的蟒古思因·乌力格尔之上。但如果是完全“文本化的技艺模仿”,是依靠记忆去演述,这并没有自己的创作;而表演中的创作是在时间流中依靠程式、主题来创作。根据七山本人多年来对于蒙古族民间文学的积淀,以及持续5年的潮尔史诗学习,在他2017年3至4月第五次进站期间,我们鼓励他尝试脱稿即兴演述。于是,七山在录制第四部《杜勒根东扎萨克》的时候,他只写出了第四部史诗故事的叙事路线,沿着路线框架进行即兴发挥。在背诵了大量的史诗唱词程式和主题后,结合他个人对民间文学的阅读、听赏与书写经验,在没有舞台灯光和观众的他所熟悉的驿站录音棚里,七山尽情驰骋在口头史诗世界,基本上摆脱了唱词的束缚,录制第四部约60小时。
七山是内蒙古民族音乐传承驿站展开的科尔沁史诗恢复重建工作中的个案之一。如今,他已完整地录制四部史诗,能够在潮尔的伴奏下熟练地自拉自唱,完整、规范地运用布仁初古拉的5首史诗曲调和各种程式、主题、典型场景以及风格,来即兴演述“北斗七星神灵”系列史诗,且逐渐体悟到了史诗唱词规范,潮尔史诗演述传统中的潮尔伴奏方式,潮尔史诗的演述曲调及说唱套路中的“固定”和“自由”、“弹性伸缩”与“随机变调”等问题。布仁初古拉及其史诗,这一持续了十余年的研究,其应用成果目前已经展现,如今,他的传承者们跨越时空地继承他的衣钵,随心所欲地穿行于远古与当下,昨天与今天。
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到实践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在田野与实验室之间、资料积累与理论研究之上、学术资源与民间资源的双向互动中,传统史诗经历了从“文化基因重组”到“合成”的过程。这项传统史诗的恢复与重建工程融通了学者的学术思维与艺人的口传思维,接通了口传音乐理论研究与传承实践,并通过研究成果反哺传统音乐文化,历时之久,学理复杂。继2006年杨玉成发现科尔沁史诗艺人布仁初古拉和他所掌握的十八部科尔沁系列史诗后,科尔沁英雄史诗完全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新的命名过程。其中既有像扎拉森、七山、史诗驿站成员等人的传承,又引起了学术界、“非遗”界、地方政府的关注。尽管每个艺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一些不足,掌握的技艺也有所残缺,但是立足于“乡土社会口耳相传——艺人的文化自觉——学者的科学研究”三个基本环节的重建探索,已使科尔沁英雄史诗的传承以活态形式呈现。“逆时态”的史诗重建工作来自于前人的经验得失以及对传统的认知,在当前“非遗”保护实践工作中具有全局性的探索和参考意义,同时也为科尔沁英雄史诗的保护工作建构了一个可持续性的发展空间。从中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的是:在史诗的学术研究中应该面对的文本是什么?史诗传统的文本真实和语境真实是什么?我们该怎样在缺失的本土文化的语境中去理解文本背后的活形态的史诗演唱传统?这种实验室语境中的恢复重建最终是否能与语境变化的民间相契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恢复与重建究竟能否回到它过去自然的环境中,在实验室中“复活的鱼”还能否回到它原有的“河流”中,这些对史诗传承问题进行重建的背后,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又应当如何重建?
诚然,这个实验只是从“标本”到“活化”的一个过程,如果全面复盘包括语境在内的科尔沁史诗演述传统,也就是“基因活化”再还归到活水中,要说的还有很多。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传统在当下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继续呈现,学者有心重建,却无力回天逆转旧时语境。“河流”已不再是以前的河流,民间的生活环境在变,过去流行于科尔沁民间专治妇女癔病的“安代”,现在已变成广场舞和课间操,但它仍然是“非遗”;过去承载民众信仰的史诗说唱,如今也只能实现在舞台和实验室。虽然我们不能完全重建仪式场景,但是这种史诗传统的核心本质却始终如一,它的本质在于其所传递的知识、技巧及其所承载的思想,以及如何用这些思想去塑造生活在现代语境中的艺人,艺人又如何继续发挥个人创造力等问题。传统文化在当下需要一种新的“打开方式”与“输出方式”,正如吉登斯所说:“传统可能完全以一种非传统的方式而受到保护,而且这种非传统的方式可能就是它的未来……由于传统被有效地证明是合理的,传统就将继续被坚持。”㉒〔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页。这也许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一种宿命。
学者们预言:“当亘古而又常新的史诗演述与现代科技相遇时,一扇崭新的窗口为我们打开了……作为语词艺术的史诗传统将会以新旧并存的形式不断延续和发展,在大数据时代证明人类的创造力之所在。”㉓巴莫曲布嫫、朝戈金、毕传龙、李刚:《蒙古英雄史诗的数字化建档实践》,《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6期,第11页。失传曲目的恢复重建,失传体裁的活化演唱,究竟是不是当代民族音乐遗产保护与重建值得我们去尝试的又一条路?我们拭目以待。
附言: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杨玉成教授的指导,顺致谢忱!
———走进去,就感到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