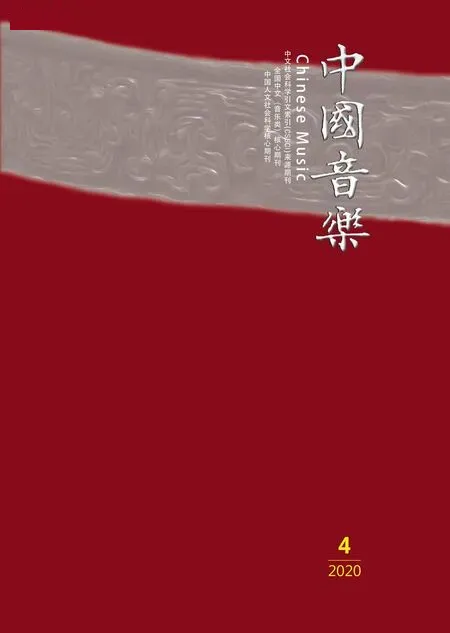中国古代童蒙读物中的琴乐内涵及其乐教精神
○白 英
古琴,也称为七弦琴,在古代的文献中古琴曾有许多别名,如瑶琴、绿绮、焦尾、丝桐、焦桐等等。这些别名也出现在中国古代蒙学读物中,例如《声律启蒙》中有“尘虑萦心,懒抚七弦绿绮”①张圣洁主编:《蒙学十三经·声律启蒙》,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第9;169页。,“锦瑟对瑶琴”②张圣洁主编:《蒙学十三经·声律启蒙》,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第9;169页。;《幼学琼林》中“琴名绿绮焦桐”③邓启铜、诸泉点校:《幼学琼林》,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3;251页。。
传说俞伯牙向成连习琴,在蓬莱仙境伯牙领悟到师傅的一片苦心,体会到古琴与人的性情、心胸、情操的关系,最终将琴曲中蕴含着的人生境界通过缓缓流淌的琴声表现出来。关于古琴的典故、人物、作品等内容大量存在于中国古代童蒙读物中,通过琴乐对童蒙进行文化、艺术教育是蒙学读物中十分突出的内容,其中既包含有关琴学的技法,也蕴含着古人对琴文化的理解、人生追求和审美意识,古琴在童蒙教育中所承担的不仅是对于琴技教育的精益求精,更包含了古人对琴学中的琴德、琴韵的意境追求。
一、中国古代童蒙读物中的琴乐内容
中国古代童蒙读物中涉及古琴的相关内容主要包含古琴的由来、琴人、琴曲以及与古琴相关的故事与典故。古代童蒙读物的写作注重词汇的精炼和诗韵的对仗,其文字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也便于儿童记忆,由于古琴所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与童蒙教育中的道德、艺术观念紧密联系,因此,对蒙学读物中琴乐内容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古代儿童艺术教育的观念以及其深层的文化内涵。
1.古琴的由来
对于古琴的由来,明代程登吉编著的蒙学读物《幼学琼林》中言:“造琴瑟,教嫁娶,乃是伏羲。”④邓启铜、诸泉点校:《幼学琼林》,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3;251页。《龙文鞭影》中曰“太昊制琴”⑤张圣洁主编:《蒙学十三经·龙文鞭影》,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第259页。,对于太昊,《汉书·古今人表》中有“太昊帝宓羲氏”,而王利器、王贞珉先生著的《汉书古今人表疏证》中颜师古曰“宓音伏,其音同”⑥王利器、王贞珉著,乔仁诚索引:《汉书古今人表疏证》,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11页。。对于古琴乃伏羲所造的传说也在琴学著作中得到体现,蔡邕《琴操》中曰:“昔伏羲氏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返其天真也。”
虽然在其他文献中对于古琴的由来有不同记述,例如桓谭《新论·琴道》中记载神农氏“削桐为琴,绳丝为弦”⑦易存国:《中国古琴艺术》,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第113;113–114页。,《礼记·乐记》中记载“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⑧《礼记》,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512页。,但是,无论是伏羲氏、神农氏还是舜帝造琴,古琴都出现在中华文化诞生之初,这一乐器都被赋予了“御邪僻,防心淫”、“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⑨易存国:《中国古琴艺术》,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第113;113–114页。的作用。因此,在童蒙读物中对古琴的关注远远超越了其他乐器,古琴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极具象征意义,它也成为童蒙教育中最具人格教育意义的乐教内容。
2.琴人、琴曲
不同于多数乐器中以乐师、乐工为主要人员构成,中国古代琴人不仅包含琴师,也包含大量的帝王、圣人与文人,而古代蒙学读物中所涉及到的琴人大多出自文士阶层且具有较高琴学造诣。为何在蒙学读物中较少涉及琴艺精湛的乐人,而以文士阶层中的琴家为主,其中深层的原因也许与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中的“人”体系与“艺”体系的区别相关。
自西周礼乐制度创立以来,音乐教育既有对于国子的教育,即乐教的部分,也有对于乐工、乐师的培养,主要在音乐行为的操作技术层面。《尚书》中记录了乐教的对象是“胄子”,通过乐教将胄子培养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⑩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8页。的国家栋梁。琴乐中的人文色彩从西周就已形成,虽然经历了“礼崩乐坏”,官学中的音乐教育逐渐衰微,但是在文士阶层中以突出文化修养、人格情操培养的琴乐传习却延续了下来。“在此意义上,琴学亦可归于音乐教育中的‘人’体系,由于音乐行为方式的不同,单纯学艺以供娱乐的琴艺训练属于‘艺’体系。”⑪修海林:《“人”与“艺”:中国传统音乐教育两种体系的存在与启示》,《音乐研究》,1994年,第2期,第18页。
在南北朝时期,学者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中可以明确看出古代文人对于古琴中“人”体系与“艺”体系的态度差异,其中言“不知琴者,号有所阙”,但不可“处于下坐,以取残杯冷炙之辱”⑫檀作文译注:《颜氏家训》,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14页。,认为如果不懂弹琴,人生就会有缺憾,这体现了音乐教育中对古琴的重视,但是《颜氏家训》中也告诫后人不要像伶人一般坐在宴席下面,将精湛的演奏用于娱乐他人。这种态度的差异造成了古代童蒙读物在列举琴人时,多以突出人物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情操为主,例如孔子、俞伯牙、钟子期、蔡琰、嵇康等历史人物。
《幼学琼林》中曰“尼父试弹琴,发泗水坛前之杏”⑬同注③,第309;94页。,提到孔子鼓琴的内容,在《庄子·渔父》中也有所记录:“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⑭方勇译注:《庄子》,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37页。在童蒙读物中未对《庄子》中的思想进行更为深入的阐述,而是突出了孔子弹琴时所追求的人生境界,这与《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学琴于师襄的故事不谋而合。
中国古代蒙学读物中涉及到俞伯牙与钟子期以及琴曲《高山》《流水》的典故较多,例如《名贤集》中曰“高山流水向古今”⑮张圣洁主编:《蒙学十三经·小儿语 弟子规 朱子家训 名贤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第151页。;《龙文鞭影》中曰“钟子聆音”⑯同注⑤,第265页。;《幼学琼林》中曰“伯牙绝弦失子期,更无知音之辈”⑰同注③,第309;94页。,这一琴乐典故也在《吕氏春秋·本味》篇中有所记载。古人操琴一方面表现了其审美情趣,另一方面也将琴乐与对待贤者之礼相对应,即“非独鼓琴若此也,贤者亦然。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⑱陆玖译注:《吕氏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16;148页。有贤德的人要以礼相待,正如同钟子期作为聆听者不仅有极高的音乐修养,更在琴乐中听出了伯牙的人生志趣,所谓“知音难觅”,贤德的人更需要能够与自己在精神上相契合的知音。
蔡文姬是东汉蔡邕之女,“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⑲许健:《琴史新编》,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9页。。古代蒙学读物中包含蔡文姬故事,例如《三字经》中曰“蔡文姬,能辨琴”⑳李逸安、张立敏译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千家诗》,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4;165页。,引导男儿也要向有才学的女子学习;《龙文鞭影》中曰“蔡琰《胡笳》”㉑同注⑤,第191页。涉及到她以胡笳的音调编写成的琴曲《胡笳十八拍》,作品表达了她回乡后对子女深深的思念之情。
在古代蒙学读物中还包含许多琴人、琴曲。例如《声律启蒙》中“离曲听阳关”㉒同注①,第98;137页。,《幼学琼林》中“王维折柳赠行人,随唱《阳关三叠》曲”㉓同注③,第93页。都涉及到琴曲《阳关三叠》。《千字文》中曰“嵇琴阮啸”㉔李逸安、张立敏译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千家诗》,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4;165页。,涉及到同为竹林七贤的嵇康和阮籍,嵇康以善弹琴曲《广陵散》而闻名,阮籍创作古琴曲《酒狂》表现了其醉后的狂态,在古琴曲中极为独特。甚至在《百家姓》中也包含“琴”姓,《汉书古今人表疏证》中列举了清代梁玉绳、王引之等人对琴牢、琴张身份的注疏。梁玉绳指出:“牢始见论语,即琴张。琴,姓,牢,名。”王引之曰:“牢本作张,云子张善鼓琴,号曰琴张。”㉕同注⑥,第305页。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古代世代相承的琴师子孙中以琴为姓。
二、中国古代童蒙读物中琴乐内容的文化内涵
桓谭在《新论·琴道》中言“八音广博,琴德最优”㉖同注⑦,第114;7页。,古琴作为众器之首,它不仅是修养性情、表达情感的乐器,同时它也承载了“琴以载道”的历史重任,同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蒙学读物中“琴与剑”总保持着特殊的联系,并在儿童的心性培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1.琴以载道与童蒙教育观念
“道”在中国哲学中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它往往以消解具象的“无”体现其无限性,“道”与“技”之间的关系体现为“道”超越了各种具体的“技”,它是“技”的理想境界㉗王前:《“道”“技”之间: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同时对于“道”的领悟需要借助于操作者的亲身体验,所以“悟道”需要在“技”的活动中进行体验和感悟。古人对于古琴的学习正是强调由“技”的层次逐渐上升到“道”的层次,悟道的过程需要避免心浮气躁和急功近利。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录了孔子从“习其曲”到“习其数”再到“习其志”最后“得其为人”的习琴过程,它是孔子“体悟”的经历,而《文王操》这一琴曲中所体现的正是孔子对文王的精神认同,他也借助古琴的“技”寄托和抒发了对于其精神世界中“道”的追寻。
《周易·蒙卦》中有“蒙以养正,圣之功也”之说,蒙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儿童具有正直品格,在儿童还处在蒙昧幼稚的阶段时就施以教育,使其形成良好的品性。除了进行“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的教育以外,更重要的是“为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㉘[宋]朱熹辑,[清]高愈注,沈元起译:《言文对照小学集注》,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第2页。。琴乐的习得以心平德和、修身正己为目的,因此在童蒙教育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清代人汪绂在《立雪斋琴谱·小引》中曾说:“士无故不撤琴瑟,所以养性怡情。”㉙同注⑦,第114;7页。《声律启蒙》中言“书箧琴囊,乃士流活计”㉚同注①,第98;137页。,古琴成为中国古代文士阶层传达心性、情志的主要途径。
2.琴与剑——古代儿童心性的培养
剑在中国文化中是侠客形象的代表,它象征着中国武侠精神中锄强扶弱、行侠仗义的侠士精神。中国古代童蒙读物中将琴与剑相对应培养儿童“剑胆琴心”的心性也十分多见,例如《幼学琼林》中言“看舞剑而工书字,必是心灵;听弹琴而辨绝弦,无非性敏”㉛同注③,第112页。,《声律启蒙》中言“丝对竹,剑对琴,素志对丹心”㉜同注①,第173页。等等。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往往具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观念,“剑”代表着为国家效力的“治国平天下”理想,是侠士精神的外在体现;而“琴”则代表了文人雅士内心的向往与追求,成为其道德修养、人格境界提升的内在力量。古琴作为文人的雅好,以琴的“文”对剑的“武”,儿童心性培养的过程中一方面注重对于武学精神的理解与阐释,另一方面也注重用“琴”所特有的精神境界中和“剑”中的杀戮,使之具有更多的审美价值以及人文关怀。
3.琴乐中的意境——以琴诉情
黄奭在《乐纬》中言“鼓琴者,当知四海”,“琴音调,则四海合”㉝同注⑦,第62页。,古人弹琴虽在技艺层面,但琴韵则与自然万物相通,将宇宙的宏大与心灵的沟通通过深沉的琴声表现出来。中国古代童蒙读物中许多都涉及到俞伯牙的琴曲《高山》《流水》,而钟子期从琴音中聆听到的“高山”和“流水”,正是两位艺术家运用直觉体悟的方式将古琴的琴韵与宇宙万物建立联系,从而使琴曲超越了技艺的局限。
琴乐中的意境还体现了文人的志趣所在,童蒙读物中的许多古诗都展现了悠然的情趣以及以琴诉情的情怀。蒙学读物《千家诗》㉞参见张立敏编注:《千家诗》,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中收录了王维的古诗《竹里馆》,其中“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展现了诗人的情趣所在,它也与陶渊明的名句“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相互呼应,将琴乐的意境以及诗人的人生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琴歌《阳关三叠》是唐代流传下来的琴曲,表现了诗人在送友人时的真挚情谊,而《幼学琼林》《声律启蒙》中也有关于《阳关三叠》的内容。可见以琴诉情是文人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那些无法言说的情感都在琴中,随琴声的流淌而缓缓诉说。
三、中国古代童蒙读物中的乐教精神
古琴在“器”的层面是娱乐身心的工具,但是在“道”的层面它体现了中国古代的乐教精神,这一乐教精神又通过蒙学的教育内容渗透在古代儿童的身心成长过程中。
从人的成长发展来看,儿童期所接受的教育观念将会深刻地影响人的一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许多有成就的人物都具有较高的音乐修养,其中不乏有诗人、文学家、历史学家,甚至医学家和政治家,例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王”和“诗魔”之称,同时他好音乐、能鼓琴,有十分丰富的音乐生活和音乐实践。在他的诗词中也经常描述弹琴作诗的场景,《琵琶行》中他对琵琶演奏的诗意描写已经成为中国古诗词描写音乐情境的佳作,白居易还撰写了专门研究音乐的论著,如《沿革礼乐》《复乐古器古曲》。再如,东汉历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其撰写的《汉书》许多章节都包含有“乐”的成分,如《律历制》《礼乐志》《艺文志》等。清代医学家、词曲学家徐大椿,号回溪老人,他精通医学,有多部医学著作,不仅通晓音律,而且著有《乐府传声》,其中讨论了北曲的特点,并提出了唱曲时情感的重要性。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作为古代王朝的统治者和政治家,也拥有较高的音乐修养,在《贞观政要·礼乐》以及《旧唐书·音乐志》中都有李世民音乐思想的记载,而唐玄宗所作《霓裳羽衣曲》也充分说明其具有十分深厚的音乐修养。
中国古代文人、政客、诗人、思想家中许多人都具有较高音乐修养,甚至他们其中一些人在音乐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是因为在对国子或贵族进行的教育中,必然包含“乐”的成分。《尚书·尧典》中有关实施乐教的记载明确包含“乐”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对象等方面,“乐”的教育是古代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孔子“六艺”的教育中“乐”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与乐人、乐工的娱乐音乐教育所不同的“乐教”是古代追求人格完善、精神气节以及艺术实践的重要方法。而“乐教”的艺术教育内容也在中国古代蒙学读物中大量存在,其“乐教”精神体现在蒙学读物中“大其心”的教育理想、“潜其心”的教育内涵以及“游于艺”的教育实践当中。
1.古代蒙学“乐教”中渗透了古人“大其心”的教育理想
中国古代对于“音”“乐”有不同的认识,《乐记》开篇将“声”“音”“乐”进行区分。西周时期“乐教”中的“乐”包含乐德、乐语和乐舞三个部分,它的教育对象是贵族子弟,通过“乐”的教育使贵族获得道德、文学和音乐、舞蹈的共同发展。因此,古代“乐”的内涵与当代的“音乐”有巨大差异,它不仅包含了当代音乐中所提倡的对于美的追求,也更多地包含对于人格、道德、礼仪,甚至政治的理解,古代的“乐”是一个融合了天文、历法、政治、审美等内容的复合体。
古人言“大其心,容天下之物”,人的心胸开阔就会更加包容。在许多童蒙读物的字里行间中就体现了这种“大其心”的恢弘气象,例如《千字文》开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㉟同注⑳,第129页。,古人在童蒙教育中希望培养儿童豁达的心胸以及容纳天地的气度,在这段朗朗上口的文字中,为儿童展现了何等宏大的气象,将“天地”“宇宙”“日月”“星辰”都融入其中。再如,《声律启蒙》中言“男儿气壮,胸中吐万丈长虹”㊱同注①,第11;173;169页。,用形象的比喻展示了男子胸中伟壮的气魄。虽然儿童在诵读中未必能够深刻地理解某些语词的内在含义,但是这种“大其心”的教育思想却渗透在儿童洒扫应对、吟诗作画中。
2.古代蒙学“乐教”中包含了古人“潜其心”的教育内涵
“潜其心,观天下之理”㊲韩作珍:《吕坤的人生智慧》,2004年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第29页。即鼓励学子们潜心钻研,纵观天下事理。蒙学“乐教”内容中“潜其心”的教育观念体现在“乐”与天文、历史、政治、艺术等相关知识内容中,儿童通过“乐”的学习积累起对这些知识的初步认知。
(1)蒙学读物中“乐”与天文
天人关系的哲学问题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的艺术世界,童蒙读物中的“乐教”也经常涉及有关天文的内容,例如《幼学琼林》中言“旱年潦年之占,雷辨雌雄”,涉及到“师旷占”。古代以“善听”著称的音乐家师旷听出雷的雌雄,即“雷初发,其音恪恪霹雳者,乃雄雷,旱气也;其依依不大霹雳者,乃雌雷,水气也。”㊳同注③,第9;17页。再如,《声律启蒙》中“天寒邹吹律”㊴同注①,第11;173;169页。描述了战国时期的邹衍吹律管而使天气转暖,以致庄稼生长的故事。虽然这些与天文相关的内容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但是在蒙学读物“乐教”内容中引导儿童对“乐”与天文的关注,拓展了儿童的视野。
(2)蒙学读物中“乐”与历史
蒙学读物中“乐”的内容往往与历史紧密相连,儿童在诵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触到鲜活的历史故事与历史人物。例如《幼学琼林》中言“击壤而歌,尧帝黎民之自得”㊵同注③,第9;17页。讲述了尧帝游于康衢,老人击壤而歌的故事;《龙文鞭影》中“老婢吹篪”㊶同注⑤,第55页。讲述了后魏河间王元琛的婢女善吹篪,遇羌叛乱在阵前吹篪而使得敌人归降的故事;《声律启蒙》中“秦王亲击缶”㊷同注①,第11;173;169页。讲述了秦王在渑池羞辱赵王,蔺相如以死相争,迫使秦王为赵王击缶的故事。这样的历史故事在童蒙读物的“乐教”内容中大量存在,在“乐”中学习历史也是蒙学教育中十分重要的教育内容。
(3)蒙学教育中“乐”与政治
作为蒙学教材的《论语》包含了许多“乐”与政治的相关内容,例如,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㊸张圣洁主编:《蒙学十三经·论语》,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第291;38;111页。周公创立了礼乐制度并“制礼作乐”,此后,礼乐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制度被确立下来。由于“礼”与“乐”之间相辅相成,孔子十分强调“乐”与政治的关系,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㊹张圣洁主编:《蒙学十三经·论语》,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第291;38;111页。表达了孔子对季氏逾越了礼乐制度后的愤怒。“乐与政通”的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对音乐的理解,这样一种独特的“乐教”观念也作为蒙学教育内容被中国古代的儿童所学习。
(4)蒙学教育中“乐”与艺术修养
古代童蒙教育中的“乐教”不是培养乐工或乐伎,许多当代作为音乐专业学习的知识,在古代童蒙教育中是最普遍的常识。例如,《三字经》中包含了古代八音的分类方式,即“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再如,《千字文》“闰余成岁,律吕调阳”㊺同注⑳,第130页。以及《龙文鞭影》中“凤凰律吕,鹦鹉琵琶”㊻同注⑤,第191页。都涉及“六律”与“六吕”的乐律学知识,《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乐官伶伦以“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㊼同注⑱,第148页。,这些十分专业的乐律学知识在当代属于专家学问,而在古代童蒙的“乐教”中却十分平常,蒙学教育中的“乐教”内容为儿童获得较高的艺术修养奠定了基础。
3.古代蒙学“乐教”中体现了古人“游于艺”的教育实践
《论语·述而》中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㊽张圣洁主编:《蒙学十三经·论语》,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第291;38;111页。古代童蒙教育中重视将“游于艺”的艺术审美体验活动作为儿童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这种学习方式符合儿童“游戏”的审美体验特征,儿童在“艺”的精进过程中逐渐超越了单纯“技”的层面,在孔子“游于艺”的状态中达到心灵的愉悦与自由。
古代童蒙教育中的艺术审美体验活动体现在习琴的过程中。古琴具有极其独特的记谱方法,因此需要通过“打谱”来获得确定的乐谱,这一方法受到打谱者的文化修养、琴艺修养和想象力等诸多条件的限制,通过打谱显示出同一乐曲不同的风格,也传递出打谱者个人的风韵,这一极富创造性的艺术实践就是古代乐教中所强调的学习方式之一。
《论语·泰伯》中“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㊾同注㊸,第139页。描绘了孔子在聆听师挚演奏时的内心感受。古人注重琴德对童蒙教育的意义,刘向在《说苑·修文》中将琴学作为乐教的重要内容,即听琴时“乐之动于内,使人易道而好良;乐之动于外,使人温恭而文雅”㊿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69页。。通过琴乐中所蕴含的精神意蕴去除那些粗厉的气息,而以清淡平和之性启发孩童的心智。无论是琴乐的听觉体验还是习琴中的动觉体验,在古琴的艺术实践中学习和欣赏“乐”是古人所倡导的学习方式,儿童也只有沉浸在音乐的活动与创作中才能感受到音乐的独特意义。
古琴是古代文人用于抒发心志、寄托情思的主要乐器,同时也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研究中的重要的内容。琴德、琴韵中蕴含了中国古代独特的音乐文化观念,这一乐器不仅在文人中广为流传,同时帝王、侠士中也不乏有技艺精湛的琴者。由于古琴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因此古代蒙学读物中大量涉及与古琴相关的内容,中国古代童蒙读物中琴乐内容的文化内涵体现在“琴以载道”的琴乐精神、“剑胆琴心”的心性追求以及“以琴诉情”的意境营造等方面。
通过对古代蒙学读物独特文化内涵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童蒙读物中的“乐教”传承不仅体现在琴学方面,而在许多古代蒙学读物中都贯穿了对于“乐教”精神的传承,在其中不仅渗透了古人“大其心”的教育理想、“潜其心”的教育内涵,而且也将其“乐教”精神贯穿在“游于艺”的教育实践中。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不断推进音乐课程改革,在当代的艺术人才培养中,我们不仅需要借鉴国内外优秀的教育理念,更需要从历史的积淀中汲取营养。古代童蒙读物由于其文字优美、声律押韵、内容丰富等特点也经常作为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中的内容,其中大量的琴乐内容不仅体现了古人的乐器观念,更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人文情怀,同时,对于中国古代童蒙读物中“乐教”精神的研究与思考也为当代音乐教育改革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与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