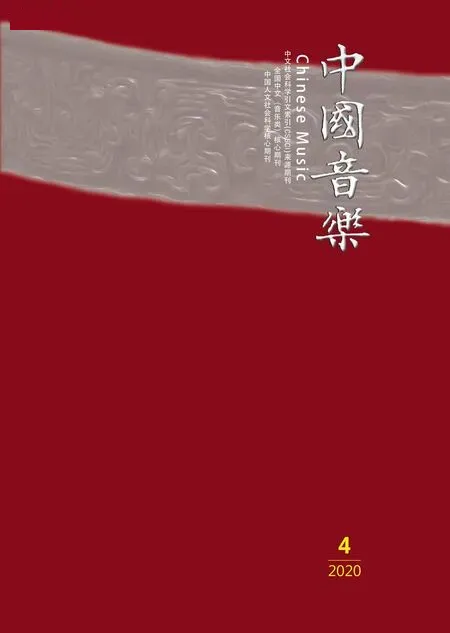基础教育音乐课程目标的历史回顾与当代文化立场
○彭 珂
引言
十九大之后,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如何实现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以及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当前摆在我国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增强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立志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①新华社:《习近平出席全国教育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2018年9月10日),http://www.gov.cn/xinwen/2018-09/10/content_5320835.htm,2018年11月26日。据此,我国音乐教育也理应顺应历史潮流,坚定正确的文化立场,在新时代背景下不断探索音乐教育的育人价值。
一、基础教育音乐课程目标的历史回顾
音乐育人价值的实现,有赖于音乐课程目标的达成度,而音乐课程目标的达成,基础教育是关键。要想厘清中国当代的基础教育音乐课程目标应该体现怎样的文化立场,需要遵循历史发展的逻辑,以史为鉴,必须从中国基础音乐教育的历史背景中寻找智慧。所以,笔者通过简要梳理我国近现代基础音乐教育的发展史,并以“音乐课程标准”为切入点,大致厘清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的发展脉络,便可从中看出音乐课程目标的历史演变。纵观近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基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笔者将其划分为了三个时期,即以中表西时期、以西表中时期和中西互表时期。
(一)以中表西时期
1861年,近代教育的开创者冯桂芬在其《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最早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主张。②参见熊月之:《略论冯桂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27、28页。随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地阐述了“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主张各级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应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放在首位”,同时“可接纳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和技术”。③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721页。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明确将“中体西用”定为其办学宗旨。④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第29页。此时,我国的音乐教育虽尚未独立分支,但教育的总目标可理解为以中国纲常名教为本,辅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达救国救民之目的。
1904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张百熙、张之洞和荣庆等人于1903年奏拟的《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课程标准”性质且在全国实行的教育法令文件,其中明确规定了中小学的具体学习要求。虽未独立开设音乐课,但将中国古代诗歌列入了课程学习的范畴。文中提到:“外国中小学堂皆有唱歌音乐一门功课,本古人弦歌学道之意;惟中国雅乐久微,势难仿照……以诗歌为涵养大方,学中每日轮班歌诗……以读有益风化之古诗歌列入功课。”⑤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音乐·美术·劳技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3页。除此之外,兴学者也认识到了诗歌与音乐的相通之处:“七言绝句词义兼美者、皆协律可歌,亦可授读,皆有合于古人诗言志,律和声之旨,即可通于外国学堂唱歌作乐、和性忘劳之用。”⑥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音乐·美术·劳技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3页。按章程之意,学习古代诗歌的目的在于陶冶身心、涵养德性,从而培养德行兼备的人。音乐课程内容要以“中国雅乐”为主,对于西方音乐的接纳仅为借鉴其课程形式而已。
1907年3月8日,清政府颁布了《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正式将音乐课纳入课堂。并在《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要学习“平易雅正之乐歌”,音乐学习要符合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⑦参见林翰羽:《近现代我国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的历史演进》,《音乐天地》,2018年,第8期,第28页。课程目标中的以中表西立场不言而喻。
1912年9月和1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相继公布了《小学校令》和《中学校令施行规则》,“最先将唱歌和乐歌分别列为小学和中学必修学科”⑧同注③,第4515;4088;345页。。同年11月公布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提纲挈领地指出,在“教授各科时,常宜指示本国固有之特色,启发儿童之爱国心、自觉心,并引起其审美观念”⑨同注③,第4515;4088;345页。,同时明确了音乐课程的目标:“唱歌要旨,在使儿童唱平易歌曲,以涵养美感,陶冶德性。”⑩同注③,第4515;4088;345页。
这些课程教授文件一以贯之体现了以中表西的文化立场,且德育和美育思想初显,说明在19世纪中叶至五四运动前期这段历史时期内,国人对本国文化的固守和自信,以及对西方文化采取相对抵制的思想态度。这从晚清大学士倭仁反对京师同文馆试图聘请西人教学的态度中可见一斑:“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尤以西人为教习不可。”⑪周勇:《中国教育改革的世纪难题与历史教训》,《教育发展研究》,2017年,第2期,第42页。这种自信,现在看来虽有些“盲目”的意味,但坚守中国文化底线的立场值得肯定。随着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的涌入,中国人在这种复杂的文化撞击中逐渐失去了自信,从而在文化立场的选择上转为了强烈的文化自卑,这种对于中国文化的否定以及对于西方文化的推崇,至五四运动时期达到了顶峰。⑫徐祖胜、杨兆山:《多元文化背景下教育改革的文化立场分析》,《理论月刊》,2019年,第8期,第148页。“这种文化自卑心理在‘五四’时期就集中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否定,甚至产生了对民族文化的罪恶感和‘赎罪’意识。”⑬封海清:《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文化走向的转变》,《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34页。这种意识反映在基础音乐教育领域,在课程目标中也体现出了明显的以西表中立场。
(二)以西表中时期
随着五四运动的开展,西方的乐理知识、体裁、作曲技法等开始大量涌入中国。由于这种思想意识以及文化立场的转变,音乐课程标准也随之进行了一系列的修订。
1923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先后颁布了《小学音乐课程纲要》和《初级中学音乐课程纲要》,在教授歌唱的基础上加入了乐理、识谱和器乐等技能性课程。这一阶段基础音乐教育课程的主要特点和目的就是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音乐技能和技法。⑭张穗宁:《历史视域下“新课标”的解读与思考》,《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第140页。笔者认为,这也是我国音乐教育在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下“重技法”而“轻文化”的开端。
193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三篇音乐课程标准,分别为《小学课程标准音乐》《初级中学音乐课程标准》《高级中学音乐课程标准》。较之以往,本次修订在小学部分加入了乐器构造与维修的相关内容,中学部分则进一步向专业化和技能性发展,要求学生了解复杂的乐理与和声知识、知晓西方音乐历史的发展、学会鉴赏歌剧和交响乐,掌握固定唱名法和非固定唱名法等。⑮刘昭:《析二十世纪以来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课程标准的发展沿革》,2014年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1–12页。
1936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对当时现行的音乐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将小学段的课程标准按学生年龄段进行了细化,分别颁布了《小学低年级唱游课程标准》和《小学中高年级音乐课程标准》;而中学段则变化不大,名称上仍为《初级中学音乐课程标准》和《高级中学音乐课程标准》。从小学段的情况来看,在名称上将“音乐课程”改为了“唱游课程”,体现了当时小学段的课程目标由“专业性”向“生活性”的转变。正如课标中所说:“顺应儿童爱好游戏的兴趣……训练互助、团结、协作、服从等精神”⑯同注⑤,第36;68页。,音乐的美育功能稍以展现。然而,本次修订对中学段的教育目标却只作出了细微调整,仅略微降低了技巧性的要求,但总体上仍旧偏向专业化和技能化发展。⑰沈菡:《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普通学校音乐课程标准研究》,2007年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第16–17;26;27页。
1940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对1936年版中学音乐课标进行了修正,颁布了《修正初级中学音乐课程标准》和《修正高级中学音乐课程标准》。其中对初中段的课程教学目标进行了修改,在上一版的基础上增加了“灌输音乐知识,训练读谱能力”一条,同时将“训练听觉,使有欣赏名歌曲之能力”改为了“训练听觉,养成其辨别音质、音高、强弱、节奏等能力”。⑱沈菡:《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普通学校音乐课程标准研究》,2007年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第16–17;26;27页。而高中段的变化则主要是教学时间和频率有所增加。总体来说,1940年版课程标准仍主要强调音乐技能的专业化。
1941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门根据1939年4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之精神,将原有的初高中合并,实行中学“六年一贯制”。⑲解亚:《中国近代普通中小学科学教育(1922–1949)》,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50页。遂连同小学在内重新制定并颁布了新的音乐课程标准,即《小学音乐科课程标准》和《六年制中学音乐课程标准草案》。仅从课程目标上来看,小学段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培养识谱能力……鼓励其进取团结的精神,以完成乐教的功能”⑳沈菡:《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普通学校音乐课程标准研究》,2007年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第16–17;26;27页。,中学段则无较大改进,依旧以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为主。
194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对全国中小学学制进行了改革,将小学分为了低、高年级,中学则取消“六年一贯制”,重新恢复为初中和高中。同时相应地颁布了各学段的音乐课程标准,即《小学低年级唱歌游戏课程标准》《小学中高年级音乐课程标准》《修订初级中学音乐课程标准》和《修订高级中学音乐课程标准》。就小学段而言,对低年级的教育理念回归至“唱游”,课程目标中有了寓教于乐的思想,同时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亦有所提及,如文中所述:“促进儿童身体适当的发育……培养儿童康乐活泼的习惯和互助团结等精神。”就中学段而言,除了在学时上对初中和高中有所区别之外,教育目标上则强调乐理的重要性,以及通过音乐的学习而增强集体荣誉感和爱国精神。此版课标对音乐的德育功能有了些许侧重,但是对于技能的要求仍显得过于专业,与基础音乐教育的实际状况不符。㉑同注⑤,第36;68页。
从上述音乐课程标准所反映的事实来看,随着“西化”思潮的不断深入,中国人从固守本国文化传统转向了全面向西方学习。音乐教育领域从最初向日本学习,到全面效仿欧美,中国学人的文化立场从以中表西转变为了以西表中。㉒同注⑫,第148页。所以导致了“重技法”而“轻文化”的现象,音乐课程目标中对培养怎样的人却较少提及。究其原因,显然是受到了以汉斯立克为代表的西方自律美学的影响。这种陈旧的观点,即便是在今天的欧美国家,也已被艺术教育界的理论和实践所反思、更替。在此观点的影响之下,也许会导致音乐和艺术脱离特定国家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实际。反映在音乐教学中,就会导致师生对“音乐”只关注声音,而忽略其内涵。因为西方观念的“入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音乐教育就变成了“为音乐而音乐”。虽然如此,但同时也应看到的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在本阶段后期,我国基础音乐课程中渗入了美育和德育的内容,虽为泛泛而谈,但至少是有所关注了,预示着文化立场上的中西互表时期的到来。
(三)中西互表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文化领域开始全面复苏,同时也出现了对西方文化的批判。音乐教育中的德育美育功能凸显,从关注“声音”逐步转向了关注“人”的发展,开始逐步走向了中西互表的时代,基础音乐教育目标的确立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教育部门便颁布了进入新时期后的第一个音乐课程标准,即《中小学音乐课程暂行标准(草案)》。其中,教学目标明确规定了音乐课程的开设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基本音乐技能,还要在教学过程中传递乐观向上的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原文如是说:“培养儿童正确的听音、发声、歌唱、简单演奏等初步的音乐知识和技能……培养儿童活泼、愉快、热情、勇敢及‘五爱’国民公德和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感情。”㉓同注③,第4516页。除此之外,教学内容中也重申了歌唱教学所选用的歌曲须在歌词上反映出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正确的审美情趣。㉔同注⑮,第17页。此版本课程标准无论是课程目标还是教学内容,均与旧版存在根本性变化,一方面降低了音乐技能的要求,另一方面加大了德育和美育的比重。教育目标中更进一步地体现出新中国的教育思想,即以德育为主,培养新中国的建设者。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音乐教育思想也随之体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此时,教育部先后颁布了《小学唱歌教学大纲(草案)》和《初级中学音乐教学大纲(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初级中学音乐课程标准)。小学部分的主要变化在于加大了歌唱教学的比重,约提高至整个教学时间的三分之二,且认为歌唱乃解放儿童天性的主要手段,是美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学部分仍然以歌唱教学为主,同时辅以音乐理论和中西方音乐欣赏的学习,并强调了与中学与小学的有效衔接,认为音乐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本次课标的修订注重了学生的天性和音乐教育的一体化发展,“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成为音乐课程目标的一部分。
1979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停滞期后,我国又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随着《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试行草案)》的颁布,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再一次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契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音乐的美育功能再一次得到了肯定。教育目标的重中之重便是培养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在音乐的潜移默化中实现人格的提升。但可惜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残留问题,本课标在落实到各地教育机构的过程中,并未得到良好的贯彻,音乐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中仅占有极小的比重。㉕马达:《二十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研究》,2001年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191–192页。
当然,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音乐教育的发展以及新目标的确立也并非是一蹴即至的。因此,1982年,教育部分别颁布了《全日制五年制小学音乐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和《全日制初级中学音乐教学大纲(试行草案)》。课程目标正如大纲中所述:“音乐教育是进行美育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㉖姚思源主编:《中国当代学校音乐教育文献(1949——1995)》,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41页。
1992年,在之前的基础上,教育部相继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音乐教学大纲(试用)》和《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音乐教学大纲(试用)》。其中首次有了“音乐课是九年义务教育小学阶段的必修课”的提法,音乐教育的学科地位得到了肯定。㉗同注⑮,第24页。虽然仍在强调美育的重要性,但说法上已经从“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变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实际上对于美育的要求有所降低,可看成是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小插曲。
进入新世纪以后,教育部于2001年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这是在以往基础上的实质性转变,旗帜鲜明地树立起了“以审美教育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真正成为音乐教育的主题。此外,在教学内容上也有所更新,其尤为明显的是将教学内容清晰地分为了感受与鉴赏、表现、创造和音乐与相关文化四个领域。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不仅注重了音乐技法的传授,而且提出了跨学科的学习理念,更重要的是强调了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
2001年版课程标准实施了十年以后,为适应我国教育改革深化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发展要求,教育部于2011年正式颁布了《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年版)》。其中“前言”部分开篇便点明了音乐课程的价值在于“为学生提供审美体验,陶冶情操,启迪智慧;开发创造性发展潜能,提升创造力;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增进对世界音乐文化丰富性和多样性的认识和理解;促进人际交往、情感沟通及和谐社会的构建”。㉙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年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页。“课程目标”中则进一步明确了要通过音乐教育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审美能力,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树立终身学习的愿望,并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标志着我国基础音乐教育事业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
通过对上述文件的整理,不难发现,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的理念与目标已从盲目崇拜西方的思想中解脱出来,逐步迈向了立足中国文化本位的中西融合阶段。音乐课程目标中所反映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随着我国经济、文化事业的稳步前进和国际地位的明显提升,教育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音乐的德育和美育功能贯穿了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并随着历史的推进不断强化。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素质教育大讨论,也是人们重新认识到音乐育人价值的又一明证。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中国人对于文化立场的选择也逐步走向了中西互表的时代。虽然仍存在些许受自律美学影响的痕迹,但毕竟已不再是主流。
二、当代文化立场的确立
我国基础教育音乐课程目标中所体现的文化立场问题,一方面需要在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寻根溯源,以史为鉴,扬长避短;另一方面也需要结合当今中国音乐教育的实际加以考量。基于对我国基础教育音乐课程目标的历史回顾以及对当前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在当代文化立场的选择中,必须做到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立场。中国近代百余年的音乐教育发展,始终在以中表西和以西表中的过程中艰难前进,首先是对本国文化传统的坚守心态,而后是受到西方音乐文化的冲击后的“全盘西化”心态。人们逐渐在中国音乐“落后”与西方音乐“先进”的矛盾中陷入两难,一方面认识到西方音乐文化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又想要维持传统文化的尊严,在两者之间飘摇不定。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和传播,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指导思想上的可能性。但是,以中国历史的发展实际来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实践探索的过程中出现过教条主义的错误经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才有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停滞期。改革开放后的实际经验告诉我们,“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把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形态,从而为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中西文化冲撞交汇引出的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文化话题提供了正确的答案和实践的典范”㉚林默彪:《中西文化百年激荡的检讨与反思》,《理论学习月刊》,1998年,第5期,第55页。。所以,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对于中国基础音乐教育而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立场不动摇。
其次是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地位的文化立场。如上文所述,以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出发,中国基础音乐教育的发展历程,总体经历了以中表西、以西表中向中西互表的转变过程。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仍然占据主体地位,人们在固有的文化传统中表现出了强烈的自信心态,以中表西思想深入人心。然而,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在对传统文化的普遍的“鄙夷”声中,我国的音乐文化开始走向了“西乐东渐”之路,音乐教育体系也在以西方模式为蓝本的参照下纷纷建立,实际上就是以西表中思想的体现。不容忽视的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五四运动也有其进步的一面,至少推动了古老的中国向前迈进的步伐,其历史功绩不容否定,但其最大的弊端却在于将“五四”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统统称为“旧文化”,而将此之后的文化看作是“新文化”,这种二元对立的新旧文化观阻挡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㉛陈先达:《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9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如今文化自信的提出,经过了上百年的发展,这个过程也可看作是中国文化主体性地位的重立过程。当今文化领域的中西互表,实际上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另一种表述。借用方克立先生的总结,在当代背景下,所谓“中学为体”,即“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为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而“西学为用”则是“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为学习、借鉴的对象”。㉜方克立:《关于文化体用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第17页。这种具有时代意义的解释,与张之洞等人的“中体西用”思想是显然不同的。这种解释,也就是笔者所说的中西互表。这种立场,就是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地位的文化立场,是具有新时代意义的文化自信的立场,也就是“中国立场”。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我国近现代基础教育音乐课程标准的历史梳理,笔者发现,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的目标和理念大致经历了从“片面育人”到“全面育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不管是“采西学”,还是当今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音乐教育活动始终围绕着“培养什么样的人”而展开,并一步步地走向完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经仔细分析并反思过后,发现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始终或多或少地存在“重技法”而“轻文化”的现象。其中有历史的原因(参考前文所提及的1923年版音乐课程标准),也有现实的因素(受西方自律美学的影响较深)。总而言之,在当今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基础音乐教育的有效实施,根本的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立场,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地位的文化立场,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扎根中国大地办学”是当前及今后我国音乐教育发展的不变宗旨,教育工作者们也应将此要求贯彻到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及领域,“结合现实考虑我国的文化背景及发展状况和民族传统对音乐教育的要求,就必然要关注到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文化传统,要顾及这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要体现渗透其中的丰富的民族特色,并将这些要求贯穿在教育过程中,通过教育造就有利于我国音乐文化健康发展的新一代”,㉝刘沛:《音乐教育的目标》,《中国音乐》,1987年,第4期,第4页。进而真正实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的目标。
——依托《课程标准》的二轮复习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