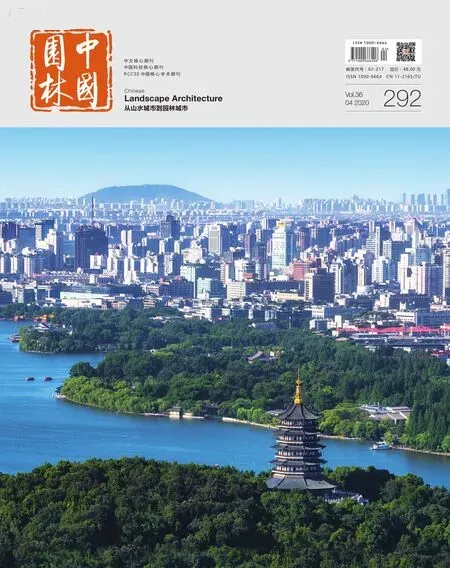基于生态安全的城市绿色廊道系统规划研究
——以南昌市为例
刘华斌
杨 梅
李宝勇
过仕云
古新仁*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城市的快速发展,城乡环境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1],城镇建成区规模扩大的同时生态用地规模受到挤压与分割,城市绿色斑块破碎, 生物多样性降低,各类绿地呈现生态“孤岛”[2],导致城市生态调控力下降,生物栖息地难以获得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城市景观效果、人居环境质量和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影响[3-4]。目前,许多国家把绿色廊道建设作为破解城乡生态问题的有效途径[5-6]。
绿色廊道(green corridor)是指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过滤污染物、防止水土流失、防风固沙、调控洪水等生态服务功能的廊道类型[7]。它促进生物因素运动,调节气候,为野生动物提供迁徙植被通道。内涵上与生态廊道(ecological corridor)等同。生态安全是指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情况。结合本研究特征,将生态安全定义为城市具备健康、稳定、可持续的生态活力和状态,具有维护生物多样性、恢复和调控环境的能力。城市土地的紧缺,导致依赖增加绿地数量面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传统方式已成困境,通过绿色廊道将栖息地、保护区等分散的生态斑块连接起来,增强城市绿地景观空间单元之间的连接度,能高效促进物种迁移、能量交换和信息流通[8-10],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景观安全格局优化,从而以有限的城市用地保障区域生态安全。
国内外学者在城市绿色廊道系统方面进行了多角度探索研究,如对城市或区域等不同尺度的生态廊道或绿地生态网络的构建[11-13]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城市绿色廊道的生态规划方法[14]或功能类型设计重点[15];或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绿色廊道构建方法[16];并对土地或景观类型进行多种生态安全评价[17],包括PSR评价方法等[18];也有学者就廊道的研究进展[19-20]、价值研究[21]、廊道不同类别[22-23]等进行了多领域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相关研究在选择确定生态用地具有一定主观性,且依据单一物种确定相关模型参数、计算连通性指标显得片面和科学性不足,构建的廊道体系也多为无宽度的概念廊道,不利于指导实际的生态建设。
“源-汇”理论基于生态学中的生态平衡理论,通过分析源汇景观在空间上的变换及生态效应,探讨调控生态过程发展的途径和方法[24],有助于识别区域生态源地,理解区域生态格局与过程的关系,克服在确定生态用地时的主观性。辨识生态廊道广泛采用的是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 model,MCR)的方法,它基于生物因素克服空间的不同土地景观类型需克服不同阻力过程的原理,其阻力之和最小的路径就是生态源地之间连接的最小累积阻力通道[25-26]。因此,以南昌市为例,运用“源-汇”理论,借助GIS空间分析技术,以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构建城市绿色廊道系统。在构建的廊道基础上以引力模型进行廊道系统优化,分析确定城市绿色廊道建设尺度并进行生态连通度安全评价,从而规划科学可行的南昌市绿色廊道系统。研究结果可以为其他城市及区域生态规划建设的实际操作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南昌市地处江西中部偏北,赣江与抚河下游,鄱阳-湖西南岸,东经115°27′~116°35′、北纬28°10′~29°11′之间。梅岭国家级森林公园主峰为全境最高点,海拔841.4m。地形以鄱阳湖平原为主,东北因濒临鄱阳湖,地势较平坦,西南则多丘陵,河流湖泊丰富,水域面积达2 204.37km2,占市域面积29.78%。南昌市西含梅岭,东临鄱阳湖,域内有赣江、抚河等主要河流,植被丰富,湖泊众多,形成“西山东水”的基本景观格局。市域内现有绿色廊道较为单一,主要为农田或道路防护林带、河流水系防护绿地等形式,如新建区象山镇新增圩农田防护林、环城快速路绿带、赣江沿岸景观绿地等,起到了防风固土、改善城乡小气候、丰富生物多样性的作用。但绿色廊道数量、长宽度、连续性都显不足,分布也十分有限,尚未形成协同维护城市生态安全的绿色廊道系统。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南昌市域全境为研究对象,基于30m空间分辨率的2017年6月Landsat-8卫星遥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2017DLTB市级缩编)、30m分辨率的南昌市域DEM数据以及南昌市总体规划(2005—2020)、南昌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修编(2015—2020)数据。相关数据还取自南昌市统计局、水利局、林业局、园林局等。
2.2 绿色廊道系统构建
2.2.1 源的确定与景观重分类
“源-汇”是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有效途径,对城市绿色廊道规划具有基础作用。从景观生态学角度,源是维护和促进生态要素和过程、有利于物种多样性发展的生境。汇则是阻止和拟制生态要素和过程的类型。对促进物种、能量、信息等生物多样性扩展,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用地来说,发育良好的林地、草地、湿地、田地、水体景观类型,起到了“源”的作用,对阻止物种、能量、信息等生物多样性扩展,制约生态发展的城镇居民点、道路交通、坡度、高程等,则起到了“汇”的作用。
依据南昌市卫星遥感影像及土地景观类型现状图,并根据自然资源分布及物种多样性丰富程度,本文在市域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城市绿地等重要生境中选取10个动植物种族群落完整的区域作为“源”斑块(图1),分别是1梅岭、2八角岭、3象山、4葛家山、5龙头山、6麻山、7洪背垄、8艾溪湖公园、9象湖公园、10黄家湖。源斑块面积共366.5km2(表1),约占南昌市域总面积(7 400km2)的5%。
2.2.2 构建景观阻力面形成绿色廊道
生物物种、能量、信息的流通与交换需要克服土地景观类型造成的阻力才能得以实现,但这种阻力呈现显著的非均一性。景观类型、土地地形是影响景观阻力的主要因素,其差异导致景观阻力在空间分布上的巨大变化。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表明生态流在“源”地之间流通所应付出的最小代价和路径,由Knaapen提出[27]并经俞孔坚等人优化得到。ArcGIS软件中的成本路径工具的算法原理是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公式如下:

图1 南昌市土地利用现状分类(2017)及源斑块分布

图2 土地利用阻力值分析

图3 高程阻力值分析

图4 坡度阻力值分析

图5 综合阻力值分布

图6 南昌市绿色廊道系统

图7 完整廊道系统

图8 优化廊道系统

图9 对比廊道系统

式中,MCR表示生态源地斑块间生态流动的最小累计阻力值;Dij及表示源斑块i、j之间的空间距离;Ri表示斑块i、j之间生态流动需克服景观类型的阻力值;n、m表示两景观斑块各自的数目。
景观类型划分、阻力赋值与绿地斑块选择的合理性影响到绿色廊道空间分布。为简化数据分析过程,研究对2017DLTB市级缩编中土地景观类型进行重分类。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28]及结合南昌市特点,将土地景观类型划分为林地、耕地、草地、水体、建设用地、道路用地6类,并结合地形坡度、高程等2个方面,共同构成阻力类型。为了便于不同类型阻力因素的比较和统一计算,对各类景观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1~100 的分值,以此得到各类景观阻力值(表2)。
选用土地利用类型、高程、坡度3个方面作为生态扩张阻力的影响类型,并以它们在影响的重要程度方面确定不同权重,分别为:土地利用0.7、高程0.2、坡度0.1。借助ArcGIS软件,通过多次模拟阻力面,最终确定南昌市土地利用类型、高程、坡度的阻力值分析结果(图2~4)。在ArcGIS中运用Raster Calculate工具进行计算,取得符合实际的拟合结果(图5)。
通过该模型得到南昌市生态功能的潜在廊道结构,10个绿地源斑块可生成共45条廊道。得到一个累积景观阻力最小的南昌市绿色廊道系统(图6)。
2.2.3 吸引力模型辨识重要绿色廊道
生成的南昌市绿色廊道系统具备了理论意义上最充分完整的生物流通线路(图7)。但由于廊道数量过于庞大,并且各条绿色廊道在整个城市生态网络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有差异的,因此既可行又有必要进一步的选择、提炼与优化。
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表明自然界中任何两物体间引力与质量成正比,与距离成反比。该定律可借鉴用于度量和判断生态源斑块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强度和绿色廊道的相对重要性,为优化绿色廊道系统提供依据。本文将重力模型进行改进,将物体质量用生态源斑块面积代替,即以面积的标准化值作为其权重值。得到绿色廊道吸引力模型:

表1 各类源斑块面积

表2 不同景观类型与地形因子级别的阻力值

表3 基于重力模型计算的斑块间的相互作用矩阵

式中,Gab指源斑块a与b之间的相互作用力,Na与Nb指源斑块a与b的权重值,Dab指源斑块a中心与源b中心间的空间路径距离。得到各源斑块间绿色廊道相互作用强度值(表3)。
在南昌市完整绿色廊道的基础上,选取吸引力大于1.0的路径,构建出一个由21条廊道构成的优化绿色廊道系统(图8)。该系统中廊道数量依然较多,且分布极为不均衡。作为对比,再去掉吸引力相对较小的廊道,保留吸引力大的主干廊道,但保留主城区的2条廊道,连接构建对比绿色廊道系统(图9)。
2.3 生态安全评价
2.3.1 绿色廊道安全宽度
城市廊道系统结构的确定,但也只是缺乏尺度的概念系统。虽然廊道长度随构建路径的生成而确定,但是却没有宽度。只有具备宽度的绿色廊道才能进行实际建设,并发挥其生态功能,维护物种多样性,确保城市生态安全。绿色廊道宽度的变化,其内部景观生态异质性、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性也随之变化[29]。根据前文分析结果,选择以优化的绿色廊道系统为基础,以50、100、200、500、1 500m为廊道宽度,借助ArcGIS中的缓冲区分析及叠加运算等过程,分别得到的各缓冲带内林地、草地、耕地、水体、建设用地、道路的景观利用构成的面积比例数据(表4)和相对变化比例图(图10)。
通过表格数据结果表明:对于南昌市,一定范围内随着廊道建设宽度的变化,已构建的廊道系统占用道路、草地、建设用地的比例基本保持在3%以内的,占用水体比例也在10%左右,基本保持稳定状态(该结果也印证本文规划绿色廊道的合理性)。林地、耕地是构建的绿色廊道系统主要用地类型,在廊道宽度大于100m及以上时,耕地超过林地成为绿色廊道的最主要的用地类型,并逐渐增加占比。由于占用耕地(农田)面积的迅速增加,一方面降低了绿色廊道的整体质量,另一方面明显增加了绿色廊道的建设成本,因此,南昌市适于修建100m以内的廊道。
2.3.2 生态连通度安全评价
建设合理尺度的城市绿色廊道系统是以土地使用成本分析为依据,但仅仅依此确定城市绿色廊道规划和建设还是不够的。绿色廊道与所有源斑块的连接程度称作连接度,是廊道系统维护生态安全程度、有效和复杂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选择生态连接度作为绿色廊道系统结构与性能的安全分析评价指标。在一众评价指标中,为了简化评价过程,仅选择常用的连接度指数(闭合度α、点线率β、连接度γ)和成本比指数CR(Cost Ration)。
L表示系统中的绿色廊道总数,V表示源斑块数量,d表示廊道长度。成本比指数用来量化绿色廊道系统的建设成本,度量实际廊道的建设可行性与实践性。利用α指数、β指数、γ指数和成本比指数分析廊道系统的连接度、连通效率和生态安全。
从上表数据可知,由45条廊道构成的完整绿色廊道系统,α指数、β指数、γ指数均处于理想状态,连通度最佳、复杂程度最高,是南昌市绿色源斑块之间生物流最充分最有利的系统。但该系统数量大,占用最多的生态用地尤其是耕地,建设成本高。对比绿色廊道建设成本比最低,且具备相对连通性。但系统中回路数量非常有限,景观流动性最差,尤其是城市建成区。相对而言,优化绿色廊道的各项指标数据较高,成本比适中,形成较充分的系统网络结构,有利于生态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有效流通。因此,绿色廊道系统以完整绿色廊道系统优于对比绿色廊道系统,优化生态廊道系统为最佳建设选项。

图10 不同廊道宽度的用地比例变化

表4 不同廊道宽度内景观利用率(单位:%)

表5 绿色廊道系统生态安全指标数据
综上分析,在绿色廊道宽度基础上,结果认为构建的南昌市绿地廊道系统结构合理,是维护南昌城市生态安全的有效途径。
3 结论与讨论
文章以南昌市为例,在土地景观类型分析基础上,“源-汇”理论可以科学判定对生态过程有关键作用的生境要素,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和改进的吸引力模型识别潜在绿色廊道并进行合理优化,分析确定的100m廊道宽度为南昌城市生态安全建设提供了实际的、可行的理论与尺度数据支持。通过对其进行生态安全评价数据表明,规划的绿色廊道系统维护城市生态安全是合理和有效的。需注意的是,绿色廊道构建与生态安全维持是基于关键“源”斑块和整体生境的品质,尤其是城区及城郊,对城市生态安全意义更显著,而这些生境也因城市发展正面临最直接的侵蚀与破坏,因此须对其进行重点关注、修复或保护。
研究中还存在一些局限。首先,在对基础数据分析整理中,仅选择较大面积的林地斑块,类型单一,数量较少,其代表性尚显不足,应增加“源”地数量、丰富“源”地类型(如湿地等),有利于城市绿色廊道系统规划的合理性。其二是景观利用类型过于概括,缺乏对相近景观类型差异的进一步细化。如水体的阻力赋值并没有体现各类水体的差异,水体中坑塘、水沟、湿地、湖泊、江河等对生物流动阻力的差异,应进一步区别。三是主城区的绿色廊道不完善。由于建设用地的景观阻力最大,生物迁移的成本高,使得规划生成绿色廊道几乎回避了整个建成城区。这对于维护和提升主城区生态安全极其不利。因此,加强中心城区绿色廊道建设投入,应成为补充优化建设绿色廊道的重点,一方面应进行主城区生态源地的修复建设和生态品质提升;另一方面在规划过程中,对用地类型和阻力再细分,并形成独立的、不同于主城区外范围标准的绿色廊道系统,从而改善城区人居生态环境。这些都会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细化和深化。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