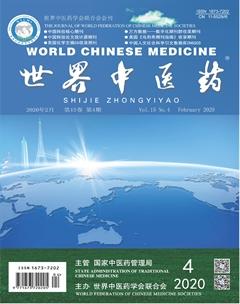冠心病合并中风中医文献研究
李艳娟 常大伟 王蕾 王丹
摘要 本文对冠心病合并中风中医文献进行了系统综述。本研究主要基于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文献研究,从病名认识、病因病机、辨证分型、治则治法等方面对冠心病合并中风的中医文献进行总结,期望为中医药有效防治冠心病合并中风提供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和临床实用价值。
关键词 冠心病合并中风;文献研究;传统医学;现代医学;病名认识;病因病机;辨证分型;治则治法
TCM Literature Research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ombined with Stroke
LI Yanjuan,CHANG Dawei,WANG Lei,WANG Dan
(The Second TCM Hospital of′ Shenyang,Shenyang 110101,China)
Abstract The litera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ombined with stroke was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modern medicine, the paper summarized the TCM literature o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ombined with stroke in terms of disease name recognition,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reatment principles and treatment methods. It is expected to support academic and clinical value for TCM in the treatment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ombined with stroke.
Keywords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ombined with stroke; Literature research; Traditional medicine; Modern medicine; Disease name recognition;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reatment principles and treatment methods
中圖分类号:R256.22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9/j.issn.1673-7202.2020.04.037
中医学将冠心病归属于“胸痹”“心痹”“心痛”“真心痛”等范畴,脑卒中归属“卒中”“中风”等范畴[1]。早在《黄帝内经》中对两病病因、病机及临床表现均有相关记载。然历代对胸痹心痛、中风的研究仅局限在各自的范畴内,少见二者并论同治。据《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4》统计数据显示,城乡居民死亡的首要原因是心血管病[2]。鉴于我国学者多年对心、脑血管病主要危险因素及流行规律的大量研究,提出将心脑血管事件中,最主要的缺血性心脏病和缺血性脑卒中,这两类事件统称为缺血性心血管病[3]。可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学术理念的不断更新,学科之间的横向联合将成为学者们未来研究的方向。目前,心脑血管疾病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特点,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严重影响生命质量,对人类健康已构成严重的威胁,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是公认的世界范围内公共卫生问题之一[4]。所以,根据缺血性心、脑血管病发生、发展的临床规律,中医药有效防治冠心病合并中风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和临床实用价值。
本文现结合近几年中医防治冠心病合并中风的有关文献,从病名认识、病因病机、辨证分型、治则治法等方面对冠心病合并中风的中医研究进展进行如下综述。
1 中医病名认识
古代医家虽未提出胸痹与中风两病合并,未见胸痹与中风合病之名,但对两病却有详细论述。如《素问·灵兰秘典论篇》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素问·脉要精微论篇》曰:“头者,精明之府”。明·李时珍明确提出:“脑为元神之府”。可见两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1 中医对胸痹病名认识 《灵枢·本脏》[5]中提出:“……肺大则多饮,善病胸痹、喉痹、逆气”。可见,胸痹病位在肺,病机为“痹”。后汉代《金匮要略》则正式提出了“胸痹”的病名[6]。其实“心痛”病名的出现早于“胸痹”,最早记载见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7],有较详细论述的则在《黄帝内经》中,如《素问·五常政大论》曰:“风行于地……心痛胃脘痛,厥逆膈不通”[8]。《灵枢·痹论篇》中记载:“脉痹不已,复感于邪,内会于心”。可见其他脏腑病变亦可传于心,引起心痹,如《灵枢·厥病》中还将心痛分为肺心痛、肝心痛、脾心痛、肾心痛等,显示了《黄帝内经》的整体观念。宋代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九痛叙论》中记载了九种心痛。明代王肯堂在《证治准绳》中对“心痛”病名有了更为确切描述,并提出心痛与胃脘痛之区别。清代至今,各派医家对胸痹认识基本达成一致,将心痛按程度、发病缓急分为“真心痛”“卒心痛”“厥心痛”等,与现代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含义基本一致。
1.2 中医对中风病名认识 张仲景首创“中风”病名,在《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治》中专论中风,“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痹,脉微而数,中风使然”[9]。“外风”导致中风的理论首见于《黄帝内经》,而“内风”则首见于《素问·风论》,“入房汗出中风,则为内风”。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将中风分为“中风、风癔、风口、风痱、风偏枯”。直至王履在《医经溯洄集》中,从病因学角度提出了“真中”和“类中”。“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因于火与气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也”[10]。明代楼英在《医学纲目》中首次使用“卒中”之名,曰:“中风,世俗之称也,其证卒然仆倒,口眼斜,半身不遂,或舌强不言,唇吻不收是也。然名各有不同,其卒然仆倒者,《黄帝内经》称为‘击仆,世又称‘卒中”[11]。李中梓在《医宗必读·卷六·真中风》中提出了“闭”“脱”的证候名称,论曰:“……如牙关紧闭,两手握固,即是闭证;……若口开心绝……声如鼾肺绝,即是脱证”[12]。
2 病因病机认识
冠心病合并中风的病因病机错综复杂,多见兼夹,且尚未有统一的标准。通过梳理阅读大量古今医籍和文献,发现古今医家对其各有论述,现详细总结如下。
2.1 古代医家认识
2.1.1 对胸痹病因病机认识 心者,为五脏六腑之大主,精神之所舍。若机体饮食有度、情志有节、营卫调和则脏腑功能正常,心脉通畅,则机体气血阴阳平衡、气机条达、血脉冲和。反之,就会出现脏腑功能紊乱、阴阳失衡,最终导致疾病的发生。情志失调能直接影响脏腑气机,肝郁气滞,运化失司,痰浊内生,阻碍气机,心脉痹阻,发为胸痹心痛。《杂病源流犀烛·心病源流》中云:“……七情失调可致气血耗逆,心脉失畅,痹阻不通而发心痛”。《素问·脉要精微论》提到:“夫脉者,血之府也……细则气少,涩则心痛”。说明年老体衰、脏腑气血亏虚,气、血、津液代谢障碍,气不布津,输布失调,水液运化失司,聚湿成痰,气虚无力推动血液运行,血行滞涩,停聚成瘀,痰瘀互阻,发为本病。《素问·评热病论》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灵枢·百病始生》:“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杂病源流犀烛》“心主诸阳,又主阴,……阳虚而邪胜者亦痛,……阴虚而邪胜者亦痛”[13]。脏腑功能虚弱,机体易感受外来致病因素的重要原因。寒邪内侵,寒凝气滞,胸阳不展,则血行不畅,心脉受阻,发为胸痹心痛。
可见,胸痹心痛发病因素包括情志失调、寒邪内侵、饮食不节、劳倦内伤、年迈体虚等,或多重刺激因素共同作用,导致气血阴阳失衡,痰浊、血瘀、气滞、阴寒之邪等病理产物留滞体内促发心脉痹阻不通,从而出现胸闷、胸痛、喘息、心慌、气短等一系列不适症状。在疾病过程中,病机可相互转化,有因虚致实,也有因实致虚。早期以标实为主,后期以本虚为主,标实为辅。痰饮、寒邪踞于心胸,胸阳痹阻,病延日久,每可耗气伤阳,向心气不足或心阳虚衰、阴阳并损证转化,最终发生血行滞涩,瘀阻脉络,瘀血日久,心气痹阻,心阳不振。可见,胸痹心痛病机为本虚标实,虚实夹杂。本虚有气虚、阳虚、阴虚,标实有血瘀、寒凝、痰浊、气滞,并可相兼为病,如气虚血瘀、气阴两虚、寒凝气滞、痰瘀互结等。
2.1.2 对中风病因病机认识 《素问·风论》:“风之伤人也,……或为偏枯,……风中五藏之府之俞,亦为脏腑之风”[14]。风邪侵入俞穴,偏重于脏腑经络,引起半身不遂的病症。《灵枢·九宫八风》:“其有三虚而偏中于邪风,则为击仆偏枯矣”[15]。说明体虚之人逢岁气不足之虚年,再逢虚风,导致卒然击仆晕倒,甚至遗留半身不遂的偏枯证候。《素问·至真要大论》:“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肝为风木之脏,体阴而用阳,主升主动。若肝阴暗耗,肝阳偏亢,化風内动,则为掉眩,甚至肝阳暴亢,血随气逆,蒙蔽清窍,则发为中风。张志聪于《黄帝内经素问集注·风论篇第四十二》又指出:“入房则阴精内竭,汗出则阳气外驰,是以中风则风气直入于内,而为内风矣”。精为肾所藏,筋为肝所主,肝与肾同源。肾精伤则水亏,水少不能涵木,则肝气内变,阳动而化风。此为后世发展“内风”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张锡纯提出本病“症系肢体痪废”而实由“脑部贫血也”,这是对偏瘫病因最接近现代的认识。
综上可见,古代医家认为冠心病与中风的发生与五脏虚弱、饮食不节、情志不调、劳逸失度等因素相关,同时与瘀血、痰浊关系密切。
2.2 现代医家认识
2.2.1 现代医家对胸痹的认识 崔源源[16]等秉承张仲景的“阳微阴弦”理论,心为阳脏,年老体衰、久病失养,或病邪克伐,心气(阳)将不能发挥推动、温煦作用。心功能失调,精微物质不能转化为血液,聚于脉道,形成“痰浊”;心气亏虚,不能推动血液运行,“营养物质”不能正常输布,积滞脉道形成痰浊,痰浊阻滞脉道,血行不畅,壅塞成瘀。且根据脏腑的病理生理特点,结合现代医学研究进展,得出“气虚痰瘀互结”是胸痹的主要病因病机,且因患病个体与疾病发展阶段的不同,三者可有偏重。初期心阳气虚为主,痰瘀阻滞轻微;中后期多见心气(阳)耗损,痰瘀互结,血脉瘀阻。邓铁涛[17]认为,冠心病心阴心阳亏损为本,痰与瘀为标。痰与瘀在辨证上属实,故冠心病是标实而本虚之证。本病病位虽在心,但与肝、肾、脾、胃诸脏腑关系密切,认为“五脏相通,心脾相关”。路志正[18]认为:如若脾胃衰弱,气血亏虚,血脉不充,脉络滞涩不通,久则血脉阻滞发为胸痹;脾虚不运,痰湿内生,湿浊上遏胸中,胸阳不展,久则心脉壅塞发为胸痹;脾胃功能失常,气机紊乱,气机郁滞,血脉失和,久则气滞血瘀发为胸痹。此观点是对“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传统医学理论的继承和发扬。王行宽[19]认为心病多本因气营亏虚而发病,结合临床实践,对“损其心者,调其营卫”继承与发展,提出“肝心共主血脉”理论,认为肝的生理功能异常,亦会导致血脉不得通调、营卫不和而发心系诸疾。张泽[20]认为“心肾相交,气化相通”是心病治肾的生理基础,提出“溯本求源,补中寓通”为心病治肾的大法。通过温阳调节脏腑功能,使痰瘀无所生,启门驱贼,标本兼治,补虚且不留邪,攻邪而不伤正。吴伟教授[21]根据多年临床经验,认为冠心病基本病机为血瘀、痰浊、邪毒、正虚,结合现代医学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研究的新进展,提出了“热毒血瘀”动脉粥样硬化易损斑块的中医病因病机学说。
可见,冠心病多因年老体虚,五脏之阳失于温煦,水湿内停,聚而为痰,痰阻气机,心脉痹阻;饮食不节,脾胃受损,酿湿生痰,痰瘀交阻,痹阻心脉;情志失调,忧思伤脾,脾失健运,水湿停滞,聚而为痰,痰阻气机,心脉痹阻;或郁怒伤肝,肝郁气滞,气滞痰阻,痹阻心脉;骤遇寒凉,寒邪内侵,素体阳虚,胸阳不振,寒凝气滞,血行不畅,瘀阻心脉。
2.2.2 现代医家对中风的认识 董少龙[22]教授认为:中风病以内因为主,气候变化往往是其发病的诱因。肝肾阴虚所致的阳亢风动,气升血逆而形成的下虚上实是本病的根本原因。陈绍宏教授[23]总结历代医家经验,提出元气亏虚、痰瘀互阻、风火相煽为本病病机。元气虚为本,痰、瘀、风、火为标,其中痰、瘀为中间病理产物,风、火为最终致病因素。风是由脏腑阴阳失调导致阳气亢逆的一种病理状态。多因情志失调,年老体虚,操劳过度,耗伤肝肾之阴,阴虚阳亢,水不涵木,阴不制阳,亢而化风,并进一步耗竭阴液,生痰生瘀,痹阻脑脉。李澎涛、王永炎等[24]提出中风病之所以具有高致残率,是因为中风病康复有一定的困难性。而脑络瘀阻导致营卫失和,卫气滞塞,化生火毒,进一步损伤脑络是其病机关键。从病理学基础角度看,缺血所致的自由基代谢毒性物质及毒性氨基酸等,对微血管内皮细胞和神经细胞造成了损伤,故辨证论治时以解毒通络,调和营卫为原则。
2.2.3 现代学者对冠心病合并中风的认识 颜德馨[25]教授提出“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胎”的观点,倡导“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理论。颜老认为心脑疾病的发生、发展与气血紧密相关。自创“衡法”论治心脑血管疾病,以气血通畅条达为要。张国伦[26]教授认为老年心脑血管病临床表现为脏腑亏虚、气血不足、痰瘀同病、经络瘀滞,属于本虚标实之证,肾虚血瘀是老年病的基本病机。气机条达,才能保证气血的畅行,气血失于健运是痰瘀产生的重要原因,故在心脑血管病治疗上,强调痰瘀同治,重视气血。徐木林[27]认为痰是心脑血管病主要病机之一,根据张景岳提出“五脏之病,俱能生痰”的理论,五脏皆可以生痰,尤以脾、肾二脏为主,素有“脾为生痰之源”之说,故在防治心脑血管病时,应着眼于痰与五脏系统的关系。韩宁[28]认为冠心病合并中风共同的病机特点为气血亏虚、痰阻血瘀。二者病位皆在血脉,气血亏虚、血脉失养是其基本病理因素,痰、瘀互阻是其病理基础。王佳馨[29]认为,冠心病与中风共同的病机特点为气虚、血瘀、痰浊。气虚血脉失养为始动因素,血脉痰浊瘀阻为病理基础。心络失养则发生为胸痹,脑络失养则发生为中风。
综上所述,二者病因多与饮食不节、情志失调、气候变化、劳倦过度、年老体虚等有关,其病机属本虚标实之证,气、血、阴、阳之虚为本,血瘀、寒邪、痰浊、气滞等病理产物为标,痹阻脉络为病机关键,各脏腑功能互为影响,多与肝、肾、脾胃三脏功能失调关系密切。因此,在临床辨治过程中应整体调治,补其不足,泄其有余,同时调理他脏功能,方能获得良效。
3 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治疾病的“灵魂”,为进一步指导疾病诊治提供了重要依据。冠心病合并中风的辨证论治针对性研究较少,且无统一的标准,因此探讨本病的辨证论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血脉为冠心病合并中风的共同病变部位,共同病理基础为血脉瘀阻,二者致病因素具有高度一致性,与肝脾肾脏腑功能失调密切相关。脏腑功能失调是本,痰浊瘀血内停是标,血脉痹阻使心脑产生器质性损害,形成心脑合病。冠心病合并中风虽然发病的部位、先后不同,但二者病因、病位、病理基础及病机演变高度一致。因此,对冠心病合并中风的治疗应针对疾病发展不同阶段,抓住主要病因病机,分清其标本虚实,辨证施治,治疗措施与药物相互借鉴,方可取得良好效果。
3.1 治病求本,调理气血阴阳 杨关林[30]教授认为痰瘀留滞日久,常可导致气血阴阳的亏虚。因此,对于冠心病合并中风的治疗应以调理气血阴阳为主。气虚证者,加用黄芪、党参、白术、绞股蓝等益气健脾化痰之品;阳虚证者,加用红参、淫羊藿、巴戟天、附子、肉桂等益气温阳之品;气阴两虚证者,加用西洋参、麦冬、五味子、玄参、山药、山茱萸等益气养阴之品;肝肾阴虚证者,加用生地黄、白芍、玄参、枸杞子、牡蛎、鳖甲等补益肝肾之品。张明雪[31]教授认为,脾气充足则气血生化有源,气血旺盛才能维持脏腑正常的气化、推动血液运行功能;同时脾气充足、运化有权,痰湿自消且不易复生。以此为依据,将“瓜蒌薤白半夏汤”“补阳还五汤”“二陈汤”三方组合化裁,组成了以人参、黄芪、半夏、瓜蒌、薤白、陈皮、当归、红花、川芎、炙甘草、地龙、天麻为主治疗冠心病合并中风的基本方。方中黄芪、人参、炙甘草补益脾气;半夏、瓜蒌、陈皮、薤白、行气化痰通络;当归、红花、川芎、活血化瘀;地龙、天麻通络祛风。本方寒温得当,攻补兼施,随证化裁,疗效颇佳。兼有阳虚证者,合回阳升陷汤加减治疗,是为补脾温阳、祛瘀化痰之法;兼有寒凝血脉者,合四逆汤加减治疗,是为补脾散寒、祛瘀化痰之法;兼有肾精亏虚者,合六味地黄丸加减治疗,采用補脾益肾、祛瘀化痰之法。
3.2 分清主次,活血祛瘀 杨教授[32]认为冠心病合并中风的病理基础为血脉瘀阻,痰瘀为主要致病因素。对于主证见胸闷、胸痛、半身不遂,舌强语謇、口眼歪斜、兼有头晕目眩,痰多而黏,食少纳呆,舌暗苔腻,脉弦或滑或涩等症状的冠心病合并中风患者,采用化痰祛瘀法,效果颇佳。常用桃仁、水蛭、赤芍、瓜蒌、半夏、丹参、薤白、当归、川芎、红花等,亦应根据痰浊、瘀血轻重的不同分别论治。痰重者加陈皮、苏子、白蔻仁等理气之品,以助化痰之力;瘀重者加柴胡、枳壳等调畅气机,取“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之意。
3.3 五脏相关,整体调理 杨关林[33]教授认为,冠心病合并中风病变根本在于肝脾肾三脏功能失调,故治疗上主张“健脾调肝补肾法”,方药上主要以茯苓、党参、黄芪、郁金、绞股蓝、菖蒲、远志、半夏及丹参为主,方中茯苓性味平淡,淡渗利湿,健脾安神;如兼气滞者可以加用柴胡、枳壳、佛手等疏肝理气药物;如年老肾虚者则加用鹿茸,紫河车,肉苁蓉,淫羊藿等滋补肾精的药物。如此则脾健肝疏肾壮,机体精气的升降出入正常,精微物质得以正常输布,痰浊无以化生。此外,杨教授临证时发现,心病更偏重心脾的调理,脑病则注重肝肾的调护,每每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冠心病合并中风属本虚标实、虚实夹杂之证,气、血、阴、阳之虚为本,血瘀、寒邪、痰浊、气滞等病理产物为标,痹阻脉络为病机关键,各脏腑功能互为影响。灵活运用中医学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思想,根据临床辨证分型确立相应的治则治法,体现了中医药治疗本病的独特优势及显著的临床疗效。
参考文献
[1] 张昌源,脑血管病[M].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465-472.
[2]陈伟伟,隋辉,王文.《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4》要点介绍[J].中华高血压杂志2015,23(7):627-629.
[3]曾哲淳,吴兆苏,陈伟伟,等.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中国人缺血性心血管病发病风险模型研究与评估工具的开发[J].心肺血管病杂志,2016,35(1):1-5.
[4]Nielen M M,van Sijl A M,Peters M J,et al.Cardiovascular disease prevalence in patients with inflamm atoryarthritis,diabetes mellitus and osteoarthritis: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primaiy care[J].BMC Musculoskelet Disord,2012,13(2):150.
[5]郭霭春.灵枢经校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489.
[6]张玉.冠心病胸痹发病相关因素与五脏关系初探[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6.
[7]周一谋,萧佐桃.马王堆医书考注[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10.
[8]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语译[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414.
[9]洁丽.张根明教授防治缺血性中风经验[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6.
[10] 王履.医经溯洞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96.
[11]楼英.医学纲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68.
[12]李中梓.医宗必读[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173.
[13]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78.
[14]周凤梧,王万杰,徐国仟.黄帝内经素问白话解[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230.
[15]陈璧琉,郑卓人.灵枢经白话解[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2:524,537.
[16]崔源源,高铸烨,史大卓.冠心病(胸痹)气虚痰瘀互结病机辨析[J].北京中医药,2014,33(2):117-119.
[17]赵益业,林晓忠,张敏州,等.邓铁涛教授以心脾相关学说诊治冠心病经验介绍[J].新中医,2007,39(4):5-6.
[18]路志正.国医大师路志正教授从脾胃论治胸痹(冠心病)[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35(7):1-4.
[19]卿俊,雍苏南,张稳,等.王行宽依据“损其心者,调其营卫”理论治疗心系疾病验案举隅[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6,22(1):131.
[20]张泽.从肾论治冠心病[J].世界中医药,2011,6(3):250-251.
[21]蔡俊杰.胸痹心痛证治文献整理研究[D].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14.
[22]窦维华.董少龙教授治疗中风病学术经验及临床研究[D].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11.
[23]郭建文,张晓云,兰万成,等.陈绍宏教授“中风核心病机论”[J].天津中医药,2006,23(1):79.
[24]李澎涛,王永炎,黄启福.“毒损脑络”病机假说的形成及其理论与实践意义[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1,24(1):1.
[25]顏德馨.从“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胎”论治心脑病[J].天津中医药,2009,26(6):441-442.
[26]孙刚.张国伦辨治老年心脑血管病经验[J].辽宁中医杂志,2006,33(7):786-787.
[27]徐木林.痰与心脑血管病[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0,34(2):20-22.
[28]韩宁.中风病与冠心病异病同源论[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10(1):20.
[29]王佳馨.中风与胸痹病机特点诊释[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11,25(2):34,44.
[30]肖蕾,张哲,陈岩,等.杨关林教授从痰瘀论治血脉病心脑合病拾萃[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09,23(6):20-21.
[31]杨舒.张明雪教授从“脾虚痰瘀”论治冠心病合并中风经验总结[D].沈阳:辽宁中医药大学,2015.
[32]肖蕾,张哲,陈岩,等.杨关林教授从痰瘀论治血脉病心脑合病拾萃[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09,23(6):20-21.
[33]张东伟,罗智博,杨关林.调脂宜从肝脾入手[J].中华中医药学刊,2007,25(4):726-727.
(2019-04-01收稿 责任编辑:王明)
基金项目:中医脏象理论及应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zyzx1609);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170540612);辽宁省教育厅青年项目(L201717);沈阳市科技局计划项目(18-013-0-11)作者简介:李艳娟(1981.02—),女,博士,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方向,E-mail:582902286@qq.com通信作者:常大伟(1967.11—),男,研究生,主任医师,研究方向:脑血管方向,E-mail:cdw19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