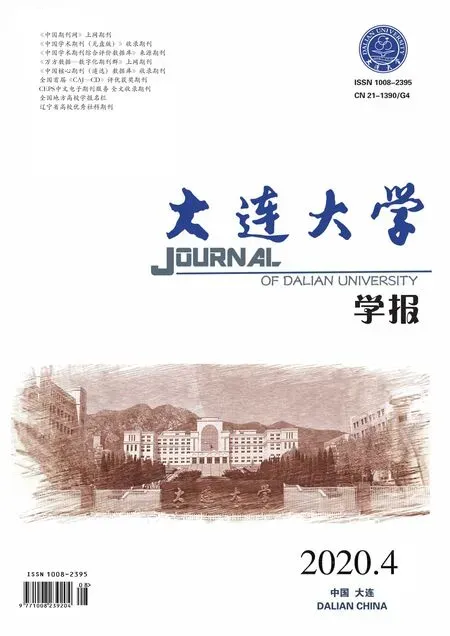试论东北地区出土的战国瓦当
王俊铮
(阿穆尔国立大学 宗教学与历史教研室,俄罗斯 布拉戈维申斯克 117027)
随着战国时期燕国进占辽东并设置郡县,东北地区南部因郡县管辖而逐渐出现了城镇。在目前所发现的东北秦汉古城中,有相当一定数量的古城始建于战国时期。如辽西地区的葫芦岛市邰集屯古城[1][2]、凌源安杖子古城[3]、建平扎马寨子古城[4]等,辽东地区的旅顺牧羊城[5]、普兰店张店汉城[6][7]、瓦房店陈屯汉城[6][7]、大连开发区大岭屯汉城[8][9]、梨树二龙湖古城[10][11]等,在上述古城内都不同程度发现了战国时期燕国的货币、房址、陶器、建筑构件等。城址内官衙建筑普遍使用了瓦类建材,因此古城内普遍发现了不同风格和形制的瓦当遗存。东北地区南部因其地理区位条件,不断受到燕文化东渐和齐文化北渐的渗透,瓦当纹饰风格表现出了燕、齐文化瓦当的特点。
本文依据东北地区战国时期遗址出土的瓦当考古材料,借助于类型学原理,以主题纹饰的布局特征作为瓦当分类的命名标准,以主题纹饰之主体搭配图案的显著差异作为区分“亚型”的标准。同一主题纹饰的不同形态或其细部“间饰”的差异,则作为区分式的标准。需要说明的是,每种主体纹饰未必完全遵循“型——亚型——式”的区分体系,如类型之下瓦当纹饰的差异程度符合“式”的标准,则直接区分为不同式。
东北地区出土战国时期瓦当基本均为半瓦当,主要有饕餮纹、树木云纹、树木兽纹、兽面云纹、山形纹、重环纹等纹饰。除兽面云纹外,其余纹饰在同时期的燕国、齐国遗址中均能找到源头,足见其深受燕、齐文化的影响。
一、饕餮纹瓦当
东北地区燕饕餮纹瓦当均见于凌源安杖子古城遗址。该瓦当为半瓦当,当面主体饰以饕餮怪兽图案,双眼呈圆形,怒目、獠牙、大嘴,宽鼻梁,常用数道竖线表示。兽耳耸立,位于双眼斜上方。宽当轮,当轮内填充以龙身变体的繁缛纹饰。值得注意的是,饕餮五官外区域饰以双龙纹。双龙首置于兽面鼻梁上方、双眼之间,背向朝外,双身顺势向上游动弯曲,前爪向上张开,龙身继而沿当轮与兽面之间向下伸展,尾部止于兽面嘴部两侧。安杖子古城出土饕餮纹瓦当共计7件。该类瓦当有大、中、小之分,当面直径为17-10厘米。F3:58保存较好,质地较为粗糙,表层施一层灰白粉,瓦面表层施粗绳纹,背面抹平(图1,1)[3]。
燕饕餮纹瓦当在易县燕下都遗址中多有出土,同时,在北京广安门外燕上都、良乡南黑古台燕中都等燕文化遗址中均有出土。燕下都65LJ:0102(图1,2)与安杖子F3:58饕餮纹形态几乎完全一致,唯有眼部形状稍有不同,燕下都65LJ:0102呈菱形,安杖子F3:58呈圆形。北京宣武区韩家潭图书馆院内出土之饕餮纹瓦当也与之高度相似,该瓦当表面灰黑色,底径15厘米(图1,4)[12]。燕下都老爷庙台V号地下夯土建筑出土双龙饕餮纹半圆形瓦当LYVT2③:18,与上述饕餮纹瓦纹身布局大致相同,细部略有不同。瓦当质地为泥质灰陶,底径20厘米,高9.8厘米(图1,3)[13]44。44兽面双眼呈菱形,龙身有阴刻线,有窄当轮。
凌源安杖子古城饕餮纹瓦当特征与燕文化核心地区同类型瓦当高度相似,具有明显的文化一致性。其年代为战国晚期,这与燕国在该地区设置郡县管辖的时间相吻合。

图1 饕餮纹瓦当
二、树木纹瓦当
树木纹瓦当 树木纹瓦当是纹饰组合和搭配较为复杂的一种瓦当。该类瓦当当面纹饰均以树木纹为主体,其旁与云纹、几何纹、动物纹等纹饰搭配,形成以树木纹为核心的复合型纹饰。树木纹中树干与枝叶的形态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一般多为多条树枝以树干对称伸展,也有将枝叶直接简化为一个三角形,树枝则有直枝、曲枝之别。根据树木纹及其组合纹饰,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两个类型。
A型 树木云纹。该类瓦当以树木纹和云纹为基本组合图案,又可进一步分为以下两式。
I式 凌源安杖子古城共出土该类树木云纹半瓦当11件。该类瓦当纹饰混合以云纹和树木纹,一棵简化的小树图案居于半瓦当中央,以树干为轴,各有树杈2-3枝,在小树两侧饰以数量不等的云纹,云纹均呈近似椭圆形,线条两端向内卷曲,如H4:35饰以五朵云纹,当面直径16.4厘米(图2,1);H4:34饰以三朵云纹,直径16.7厘米(图2,2);H4:32饰以两朵云纹,方向向上,直径14.8厘米(图2,3);H4:12饰以两朵云纹,方向向下,直径15厘米(图 2,4)[3]。
山东临淄齐国故城遗址树木云纹出土甚多。1958年出土于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出土一方树木云纹半瓦当,当面中央为一树纹,五对枝杈,枝杈下、树干两侧各有一朵卷云纹,两朵卷云纹线条开口处各有一小乳丁。当面直径14.4厘米,高7.5厘米(图2,6)[14]63。该瓦当与凌源安杖子古城出土树木云纹瓦当纹饰风格基本一致,但该瓦当制作更加规整,纹饰清晰精致,反映了齐国王都地区较高的工艺水准。除此之外,如1965年出土于山东临淄崖付庄H1树木云纹半瓦当,当面中央有一树木纹,四对枝叶,最下方一对枝头向下内卷,作曲枝态,并各与线条勾勒的羊角状云纹,共同构成两朵组合卷云纹。半瓦当直径18厘米。高9厘米(图2,7)[14]49。该类树木云纹当系另一形态的树木云纹,主要表现在其曲枝和羊角状云纹形态,不同于直枝、圆圈云纹的树木云纹瓦当。
II式 建平扎寨营子古城亦出土了带有圆圈云纹的残瓦当(图2,5)[4],云纹图案简易,但线条未如安杖子古城云纹瓦当般向内卷曲,而是直接衔接。自战国至汉代,瓦当中未见该简易圆圈云纹单独作为纹饰,而往往与树木纹搭配。云纹旁双线可能为树木纹局部,故而该云纹瓦当亦应归入树木云纹。树木纹呈现双线特点,与一般树木纹有别。扎寨营子古城曾出土燕国刀币、布币,可知燕国时期已存在,该云纹残瓦当可能为战国时期燕国树木云纹瓦当。
B型 树木兽纹。安杖子古城出土4件树木兽纹瓦当,仅西T4③:70一件完整。该类瓦当当面中央饰以三角形小树纹,两侧饰以对称的动物各一。西T4③:70树纹两侧各一鹿纹,树纹上方有一双角四足怪兽,形似蜥蜴。当面直径19.5厘米。(图2,8)H4:43虽残,但可辨三角形树纹两侧各有一鹿纹,树纹上部残缺(图2,9)[3]。大连牧羊城亦曾出土给类型动物纹残瓦当,当面仍可见树木纹上部呈三角形,其旁有一动物作奔跑状。王珍仁、苏慧慧著《瑰宝·大连文物》作“双马纹”(图2,10)[15]42,亦属于树木兽纹瓦当。另见日本东方考古学会编《牧羊城——南满洲老铁山麓汉及汉以前遗迹》一书记述,牧羊城曾出土树木纹半瓦当残片:“呈灰色,极其细小的残片,为简化的树形前端残存,在树形的中央显现,推测在其左右有文字或动物纹分布在半瓦当的一部。”[16]
山东齐国临淄古城曾出土不少树木兽纹瓦当,研究者一般均将动物形象视为马纹。1976年临淄齐故城桓公台工地附近采集到一面树木兽纹瓦当(图2,12)。当面中央有一树木纹,树冠呈规整的三角形,似伞状,与安杖子西T4③:70、H4:43及牧羊城所见树木纹瓦当的三角形树冠十分相似,但不如该瓦当三角形规整。树干两侧各拴一只马匹,马匹面向树干,均作前腿曲腿半跪状。瓦当直径16.5厘米,高8.1厘米[14]30。齐故城树木兽纹瓦当76LHT72⑤B:6,1976年出土于临淄齐故城桓公台遗址第72方5B层。当面中央有一树木纹,五对枝杈,树干两侧各有一匹马,左马前腿呈跪卧状,两马后腿微曲。直径16.8厘米,高8.8厘米(图2,11)[14]22。
以上树木兽纹瓦当,除齐故城76LHT72⑤B:6外,树木纹纹样均未表现出枝杈,而是直接简化为三角形,呈伞状置于树干上部。特别是东北地区所见三枚树木兽纹瓦当皆系此类。

图2 树木纹瓦当
三、其他纹饰瓦当
山形纹瓦当 该类瓦当为多道线条弯曲重叠,形成阶梯状山形纹饰。纹饰外围尚有抽象简化的云纹,似火焰呈放射状。
凌源安杖子T2③:2瓦当仅存残块,残径6厘米(图3,1)[3]。瓦当应系半瓦当,当面中央饰以三道山形纹。目前在东北地区汉代古城中仅见此一例,但在易县燕下都遗址多有发现,显然是受到了燕文化的影响。燕下都高陌村2号遗址出土半瓦当G2T6③H56:2(图3,2),当面中部为三道山形纹,层层相套,最外层山形纹与当轮之间用简易线条饰以形态不同的卷云纹和勾云纹。申云艳阐述为“两侧各饰一个羊角涡纹和多个单角涡纹”[17]48。该瓦当所饰之所谓涡纹,实际上就是极度抽象简化的云纹。G2T6③H56:2瓦当直径17.5厘米,高8.5厘米[13]635。临淄齐国故城也出土了该类山形纹瓦当。如,1965年出土于临淄崖付庄H1,当面纹饰为五层阶梯状山形纹图案,除最内层山形纹山峰较为高耸凸出外,其余四层至山峰顶部位已较为舒缓。当轮内又饰凸弦纹三道。该瓦当当面图案饱满,几乎未有留白。直径19厘米,高9.5厘米(图3,3)[14]102。

图3 山形纹瓦当

图4 重环纹瓦当
重环纹瓦当 重环纹瓦当系以多道圆圈纹环套。辽宁铁岭邱台遗址出土半瓦当1件T3③:48,瓦当为泥质黄褐陶,半瓦当当面饰以四道半环纹,上部有施钉的圆孔。半瓦当直径16厘米,高8厘米[18]。(图4,1)吉林梨树二龙湖古城出土两件:T0518③:22(图4,2)、T0618③:34(图4,3),均为泥质灰陶[19]。T0518③:22环纹呈三组,每组弦纹间留白。该类纹饰在河北、山东等地也有发现(图4,4、5、6)。由于纹饰特别,尚无法确定何地最先出现了该类纹饰。

图5 安杖子出土兽面云纹
兽面云纹瓦当 安杖子古城出土兽面云纹半瓦当计12件。H4:36当面中央饰以简易云纹,云纹由线条勾勒,两端向内卷曲。云纹外似有两只眼睛,当轮与凸弦纹构成眼睛轮廓,酷似简化饕餮纹的进一步抽象。瓦当当面直径15.5厘米、厚1厘米(图5)[3]。该类型瓦当在燕都地区流行的瓦当中未找到相似的纹饰布局,云纹则与燕地树木云纹中的云纹形态一致,应系一种带有地方特色的瓦当类型。
四、余论
东北地区南部受辖于燕国郡县,与中原、山东、松嫩平原发生了密切的文化互动与交往。因此,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瓦当无疑带有上述时代和地区的文化烙印。同时,也因汉地移民与世居族群的互动而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
首先,东北地区战国时期瓦当受到了燕、齐文化的强势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瓦当在各诸侯国城邑中渐次普及,燕国治下的东北地区南部也出现了最早的一批瓦当。随着“秦开却东胡”,东北作为燕国新开拓的疆域,在郡县制的管辖下受到了燕文化的强势辐射,表现出对燕文化全面吸收和复制的特点。这突出表现在燕饕餮纹瓦当特征与燕文化核心地区同类型瓦当高度相似,具有明显的文化一致性。同时,齐文化与燕文化也产生了互动与共生,作为齐文化典型特征的树木纹瓦当元素也进入了燕文化之中。
其次,重环纹瓦当在东北地区的出土地点具有一鲜明共性,即均出土于燕国疆域和燕文化北渐的边界沿线。铁岭邱台与梨树二龙湖遗址均地处东辽河流域,系辽东郡县直辖地区与松嫩平原濊、夫余等世居古族分布区的交错地带。在辽东半岛及辽西地区均未发现类似纹饰的瓦当。这即是说,在燕国北方边界的东辽河流域与燕国内地之间,存在较大的重环纹瓦当真空区。从遗址本身来说,铁岭邱台遗址在考古学文化上表现出浓厚的中原战国-汉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交往与融合的特点[20]。梨树二龙湖古城则表现为城内出土大量汉式陶器,类似西团山文化器物出土于城址东南[10]。这似乎与古城内外民族杂处的分野格局有关。二龙湖古城的性质在学术界一直争论颇大。有学者即认为该城址楔入夹粗砂陶文化腹地,周围无相似遗存,城址可能与“秦开为质于胡”的索居之地有关[21]。总之,重环纹瓦当同时出现在两处文化环境与民族格局相似的燕国边疆城邑,是否反映了其文化产生的地域特性呢?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无疑上述论断为我们探索其文化渊源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
除此之外,瓦当作为城址内官衙的建筑材料,为考索东北地区战国城邑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参考。如出土了较多战国瓦当的凌源安杖子古城(图6),该城位于凌源县西南4公里,大凌河南岸九头上下的平坦台地之上。城址城垣基本保存完好,城址呈不甚规整的南北向长方形,南北长150-328米,东西宽200-230米。古城东北角另有一座梯形小城,小城南北长128米,东西宽80-116米。小城西墙与东墙北段重合,但二者间有一缺口。城墙为夯土版筑,在北墙外的断崖下,发现有夯土和石子路面的断层。古城文化遗存丰富,地表堆积着丰富的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板瓦、筒瓦及陶器残片。古城战国至汉代文化层下还叠压着夏家店上层文化[3]。安杖子古城内出土了树木纹云纹、树木兽纹、山形纹、兽面云纹等丰富类型的战国时期,加之汉代“千秋万岁”文字瓦当等的出土,表明其在当时具备至少县一级行政建制级别。

图6 凌源安杖子古城平面图
结语:战国时期燕国的郡县管辖,使东北地区南部出现了第一批具有汉文化特征的郡县城邑群。城址的出现伴随着瓦当等各式建材的使用。战国时期燕饕餮纹、树木纹、山形纹等纹饰均受到了燕、齐文化的强势影响,体现出了多元文化汇聚的鲜明特点。至秦汉时期,随着国家大一统格局的出现,饕餮纹、树木纹、山形纹等瓦当纹饰渐次式微,直至被云纹、吉语文字瓦当等所取代,并与中原地区基本保持了瓦当纹饰风格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