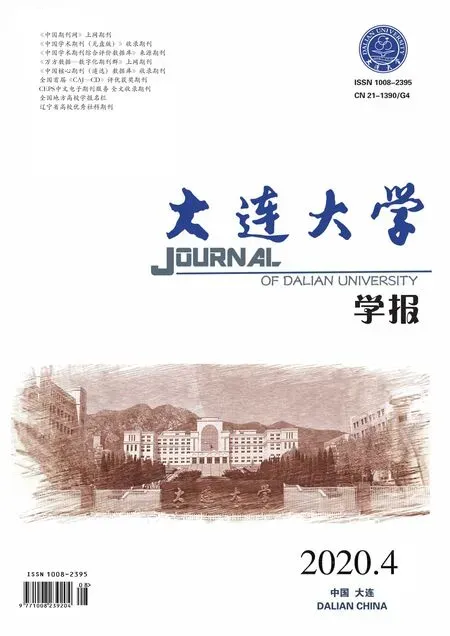“离去”与“归来”
——论《天黑前的夏天》叙事艺术
童颖瑶,杜明业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235000)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被誉为是“当代最杰出的女作家”[1]1,《天黑前的夏天》(The Summer Before the Dark)是她于197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女性文学百科全书》认为“其作品涉及性别角色、种族问题、社会巨变即人类未来”[2]326。莱辛在创作《天黑前的夏天》时,正值英国激进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潮。她以女性作家敏锐的感受描写了处于时代变动中女性个体的生命体验,通过表现凯特在家庭与社会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表达了对男权社会下女性命运的哀叹;同时也表达出对激进女权主义的反对态度。
对于莱辛作品的研究“尚不能脱离文本表层内容的解释和呈现”[3]。该小说将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紧密结合。在表层结构上,由“离去”与“归来”之间的对立选择打破了叙事过程中序列平衡;另外,在叙述频率上呈现出反复的单一叙事模式;紧接着又通过情节反转的结构设置拉近凯特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离去——归来”结构的反复出现显示出不同的叙事功能,从而勾勒出凯特在家庭与社会之间夹缝而生的处境及其矛盾、纠结的心理动态图景。据此,可将“离去”与“归来”表层结构背后的文化意义进行解码,即“离去”表达了莱辛希望女性能够摆脱男权枷锁重获个体生命的自由;而“归来”表达的是其“呼唤女性气质回归”的立场。这既是男权、女权在时代留下的“斗争”痕迹,同时也是莱辛本人心之所向的主题表达。
一、“离去”与“归来”结构下的叙事序列
罗钢认为,从句法分析的角度可以把叙述内容简化为一系列基本句型,最小单句叫做叙述句[4]113。《天黑前的夏天》的表层结构呈逆向平行模式,即“离去—归来”的结构模式。将单独的句子构成叙事内容的思想运用于提炼《天黑前的夏天》中的叙述句,严格意义上来说能够得到六个叙述句,即三个凯特离开了;三个凯特归来了。此外,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序列关系是由“离去”与“归来”交错展开,顺带使得情节与情节也呈现反复变化的特点,同时这六句话结构了全文的主要内容,区别就在于每一次的“离去”与“归来”在情节中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其功能不外乎有三种:打破平衡;努力恢复平衡;恢复平衡。(详见表1)

表1
凯特最初的“离去”就是一种看似主动实则被动的行为,该行为将女性在家庭中之于孩子、之于丈夫的被动地位不动声色的勾描尽显。当时,蒂姆在饭桌上对凯特“大吼大叫,说快被她窒息死了”[5]113,这一声吼叫是不懂事也好,是专属孩子的任性之气也罢,总之蒂姆的行为深深伤害了凯特的心。之于此情此景,凯特决定离开家去看望老朋友,借逃避、不见面的方式来规避与蒂姆之间的不愉快,同时也想要达到平静自己情绪的目的。可是早市将问题掩饰,暂时将问题放置于阴暗面并不会促使问题的解决,相反只会激化矛盾。
为了展现凯特在社会与家庭之中两难的处境,小说在叙事手法上也与这样的情感表达相互应和。小说常常通过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展现凯特曾经在家中的生活,曾经的情景在时光的涤纶中汇聚了如下凯特的新的感悟。凯特的婚后生活一直都是围着孩子和丈夫,在无形之下放弃了自我,她在家庭中“好像总是随时待命,总是听候传唤,总是遭受指责,总是榨干自己喂养这几个——魔头”[5]116。这也是凯特婚后在家庭的境遇表现,蒂姆的一声吼叫打破了原本看似平静却矛盾重重的“幸福之家”,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凯特的离开,又或者说是凯特“本我”的苏醒。而这次“离开”的行为在整个叙事结构上起到的是打破平衡的作用,同时也推动了凯特归来的情节发展。正如其“离去”的抉择一样,凯特的归来也不是她自愿选择的结果,而是因为原本可以帮助她打理家务的女儿有事要外出。
因此这次的归来就叙事内容来说只是起到一个努力恢复平衡的作用,也就是凯特的回归能够让家庭正常的运转,即便并非心之所愿也要维系外在的平衡,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激发家庭矛盾,从侧面来看,这也是凯特牺牲自我成全他人的例证,这时候的凯特用“超我”将“本我”的精神觉醒压抑住。
随后凯特再一次离开家,这次同样也不是自己主动想要离开的,而是丈夫在凯特不同意的情况之下将房子租出去了;在凯特不答应甚至已经明确拒绝的情况下帮凯特接了一份翻译的工作,第二次的“离去”较之第一次来说将凯特囿于家庭的困境再一次升华。
凯特这一次的离开在叙事序列中仍然起到打破叙事平衡的作用,同时在“离开”结构的背后还隐含着女性在男权社会的被动处境。当凯特离开家之后,不情愿的接受了丈夫为她接下的在“国际食品”组织的工作,在工作中结识了杰弗里,他们相约一同去西班牙旅行。凯特这一路的行程可以用颠沛流离来形容,既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也没有舒适的住所,另外杰弗在行程中身体有所不适还需要凯特的照顾。因此,经历了这一路的颠簸体验凯特非常想回家,“她很想家,很想家中的日子”[5]163,“她想念丈夫”[5]163,此时凯特“归来”的想法是一种心理上的冲动,同时也是凯特第一次主动想要“归来”。从“归来”的叙事中所起到的作用来看,虽然她后来回伦敦了,但还是由于房子期限(凯特离开之后,她们的房子外租出去)等问题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中,因此这里的“归来”起的仍然是一种努力恢复平衡的作用。
最后,凯特在内心深处又生发出了“离开”的想法,因为她目睹了莫林因拒绝菲利普求婚“双眼通红,脸颊肿胀”[5]269的样子,看见此时意志消沉的莫林,凯特就想起了曾经在家中“服从和适应他人”[5]25的自己,也想起了那个任劳任怨却反被怨择的自己,此时的凯特在莫林身上找到了一份共情之感:在情感中处于夹缝而生的处境,无论是服从还是不服从都不能获得心灵的安适,从而在心中凝固一种郁结之情。面对此景之后,凯特果断“回到电话机旁边,取消预约,告诉邻居计划有变”[5]274,这次离开的想法与行为属同步关系,具体表现为凯特就这次的“离开”付出了切实的行动——打电话,因此这次的“离开”在叙事意义上起的仍是打破平衡的作用,将原先想回家的想法再一次否定掉。
紧接着,情节又呈现峰回路转之态,随之而来又生发了“归来”的想法,这一情节的设置一定程度上是有些突兀的,具体而言就是最后的选择与之前的五次选择是不一样的,之前的“离去”与“归来”都有具体的原因,而这次的“归来”没有具体原因,仅仅只是“因海豹之梦结束,她的旅程也到此结束”作为其“归来”的理由,如果要追溯其内部原因的话那就是凯特自我意识的觉醒,即“本我”意识的觉醒,但是到底是在哪个时间点,源于哪件事却没有具体的反映,因此这次“归来”体现出的人为(特指叙述者本人)的建构意识较为强烈。究其外部原因,还要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出发,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社会,正是激进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开展的时期,这一派别的“基本倾向是与男性为敌的女性独立意识,采取的是与现代文明完全完全对抗的态度”[6],这样的思想倾向将“男性/女性”置于二元对立的立场之上,同时这也是女权主义的激进所在。
基于这一点,该派别主张在生理上消解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企图构建真正的两性平等。由此产生了一些激进的行为,例如她们想要在生理上消除两性的差异,即反对异性恋主张同性恋等,这些主张都已违背了日常的伦理。而莱辛就是通过建构凯特“归来”的结局,表达了她反对激进女性主义的立场。不论该结局的人为建构色彩是否浓郁,凯特最后的归来在“离去—归来”表层结构中起到的是恢复平衡的作用。
由上图可知“离去”与“归来”在《天黑前的夏天》中的结构模式中呈现出严整的对应关系,其主要作用之一就在于前一个情节能够合理的推动着后一个情节的发展,从而使得情节与情节之间呈现紧密相连、环环相扣之态。另外,看似三组“离去”与“归来”的结构是三条叙事线索,但是将每一组都放置于整个结构来看,实际上只有一条完整的叙事线索,即第一次离去(打破平衡)——最后一次归来(恢复平衡)。由此可见,“归来”结局的设定实际上使得整个叙事序列的结构得以完整,其背后肯定的正是莱辛主张女性回归家庭的立场。
二、“离去”与“归来”结构下的单一叙事
热奈特认为,叙述频率即叙事与故事间的频率关系(简言之重复关系)。根据叙事的具体“重复”能力,又可以将其划分为单一叙事以及重复叙事[7]73。“离去”与“归来”的结构模式类似于四种潜在类型中的一种,即n次发生过n次的事,这属于单一叙事。在《叙事话语》中,热奈特引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类型的例句:“星期一我睡得很早,星期二我睡得很早,星期三我睡得很早,等等”[7]74。《天黑前的夏天》中所呈现的“离去”与“归来”的结构模式仍然体现了这种反复叙事的单一叙事类型的特征,即反复叙述同一行为,具体表述为:第一次凯特离开了家;第二次凯特回到了家;第三次凯特被迫离开了家;第四次凯特想要回家;第五次凯特想要离开家;第六次凯特回到了家。将其细致划分就是两种单一叙事模式,即凯特离开家以及凯特回到家。
虽然三次“离去”与三次“归来”是在叙述同一件事,但是每一次“离去”或者是“归来”的行动背景已有所不同,由此导致每次行为背后的意义也不尽相同。总之,“离去”与“归来”的表层结构背后面临的是深层结构的解码问题。凯特的第一次“离去”意在刻画出凯特处于被动的位置,逃避仍是她解决问题的首要的方法,一个小孩子的任性之语竟能够成为凯特离开家的“武器”,这一行为也折射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女性面对孩子时的心理困境,即孩子的行为是符合其天性的,但是作为母亲却未能调整好自己的心理情绪;凯特第二次“离去”展现了她被丈夫安排的命运:被迫离开家、被迫工作,这些情节的设置集中体现了激进女权主义的矛盾焦点,即“对女性的压迫来自于父权制,从而父权制是万恶之源”[8];最后一次“离去”是因为看见凯特看见莫林因恋爱问题苦恼的样子而做出的选择,莫林激活了沉睡数年的凯特,促使她内心的“本我”开始复苏,也只有这一次的决定是凯特自我意识觉醒之后产生的。
与三次离开相对应的的是三次归来:最初的“归来”是迫于家庭的压力,这份压力是因其双重身份(妻子、母亲)给她带来的压迫感,这番现象也印证了维奥莱.马卡姆在《帝国的真正根基》中的那句“妻子为孩子工作,女人是家庭的守护者”[9],在家庭中的凯特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房子里的安琪儿”[10]21。随后的“归来”之举意在表明社会动荡不安的现状给凯特造成了来自精神与肉体上安全感的缺失,这使得她的心又牵挂起了家“她很想家,很想家中的日子”[5]163,“一到达伦敦满心想念的都是自己屋里的床铺”[5]174,“她想念丈夫,想念那份知根知底的感觉”[5]185等等,众多的语言词句不尽相同的话语,却深切的表达出在外漂泊几久的凯特,此刻对安全感的渴望、对家的渴望,可是矛盾之处就在于“房屋(家)可以是一个人的栖身之所,也可以是囚禁他心灵的牢笼”[10]25。这无不突出了凯特在社会与家庭之间夹缝而生的两难处境,对于凯特来说如果连肉身都没有安居之处,那么心灵的安全与丰盈将变为次要。由此可见,这里所采用的进行反复的单一叙事起到的作用显而易见,即不断强调某种思想情感,在这里强调的就是凯特在外漂泊久了之后对家的思念越发浓稠。最后凯特的归来,可以认为这是女性觉醒之后的自主选择,也可以认为是作者莱辛人为建构的结局(上文以详细赘述),总归它延续且发展了上一次的离去情节。
“离去”与“归来”在这里呈现出反复叙事模式下单一叙事的特点,不同的情境之下也会引起凯特不同的心里想法与行为,这种想法和行为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同步的,正是这种不同步才体现出“离去”与“归来”的选择在心理和行为上存在着错位的关系,在三组“离去”与“归来”的结构模式下,只有第一次的选择与最后一组的选择是心理与行动相一致的,其他三次的选择背后其心理与行动却相背而驰。(详见表2)

表2
由上图可得到“离去”与“归来”的深层结构内涵:其一,凯特每一次的决定都是由心理想法和实际行动共同促就的,凯特需要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反复针对同一问题做出选择也能反应她内心纠结、涌动的情绪。“离去”与“归来”的叙事结构为凯特的选择营造了六种不同的行为语境,凯特要在无一雷同的情境之下做出“离去”亦或是“归来”的选择,这既丰富了叙事内容,也使得凯特的形象更为饱满、立体。因此,该结构为凯特营造的生存困境延带透视了凯特丰富的性格特征。
不论出于何种心里想法,凯特的心理始终都要做出一个决定。如果说是“行动+心理”的模式,那么无可厚非,这是凯特心甘情愿的决定;重要的是“行动-心理”或者是“心理-行动”模式,这种结构模式体现的是凯特纠结、不情愿、犹豫不决的心境,影射的是一种无可奈何又不得不去做的心情,其重要意义在于彰显了凯特最后“归来”之选的重要意义,这是否定了前三次“离去”之后的谨慎决定,仍然起到建构莱辛主张女性回归家庭的立场。
三、“离去”与“归来”结构下的情节反转
亚里士多德认为,情节是指事件的有序安排[11]17,反转是事物从一个状态转向相反的方面[11]30。这一叙事理念最早被用于解释戏剧,如今随着经典叙事学以及后经典叙事学的相继发展与各种叙事学理论之间叠换交错,再加上各种文体的繁盛多元,使得该理论成为一种通行理论(各种叙事文体均可以用这一理论予以合理化的解释)。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无论是“情节”还是“反转”,这其中都含有变动之意,其更加强调的是由好到坏变动趋势背后的二元对立关系,在悲剧中讲这样的理念能够更加黑白分明的展现出来,例如众所周知的俄狄浦斯王就是由一个人人爱戴的国王变成一个弑父娶母的凶手。
虽然《天黑前的夏天》是小说,与悲剧不是同一题材,但是从叙事角度来说它们都有共同的要素——“情节”,而“离去”与“归来”结构呈现的逆向平行模式,也就形成了二元对立的关系,这一对立关系背后所反映出来的即是情节上的“反转”,也就是扭转了事态发展的方向。莱辛作为女性,《天黑前的夏天》也深深的打下了女性叙事的痕迹,正如女性主义叙事学家苏珊·S·兰瑟(SusanSniaderLanser)说的那样:“小说封面标有女性作家的姓名,这已足够表明小说有着女性的叙述声音,虽然在文本中毫无标记可言”[12]167,所以在情节反转的背后是“隐含作者”以不动声色的方式在牵引读者的情感价值取向。
在《天黑前的夏天》中,从“离去”到“归来”之间反复且不同的选择是由情节反转来实现的,这种反转一共出现了五次,每一次的反转都是在特定情境的推动之下发生的,也就是说相应的情境推动相应的情节反转。多次反转呈现的是情节变化的特点,在加上小说的叙事视角将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与全知叙事视角交错运行,眼花缭乱的同时又能够把握住整体的情节,这种多变的叙事情节设置正应了安·布莱克(AnnBlake)的那句话,“阅读莱辛的作品就像走进了一个变化多端的世界”[13]116。《天黑前的夏天》五次反转中最后三次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因此这里例举最后三次的“归来—离去—归来”说明情节的反转是如何拉近读者与凯特之间的距离。
以读者的期待视野来看,当凯特在家受了很多委屈之后,凯特终于可以离开家,也终于能够摆脱家庭的束缚,那么凯特在离开家的日子应该是非常快乐了。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在“国际食品”组织工作的经历以及与杰弗里同游西班牙体验到的颠沛流离之感,让凯特万分留恋家庭的温暖。显然,外出的经历就是情节反转的线索,这种情节反转与读者的期待视野背道而驰,因此读者也会随着情节的出乎意料而陷入沉思:凯特到底应不应该有回家的念头?这时读者也要设身处地思考凯特的想法是否正确,因此这种情节反转一定程度上拉近了读者与凯特之间的距离。接下来迎合读者期待视野的情节应该是,凯特想要回家的想法应该不会再变了,毕竟体验到了在外漂泊的滋味,这番滋味可不好少,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都不能够得到满足,甚至还要活在担惊受怕、惶惶不安之中。可是再次让人出乎意料,凯特再一次有了想要离开家的想法,情节又发生了反转,这里体现情节反转的线索就是:凯特看见莫林因在爱情中受到困扰而双眼红肿的模样。直到最后,凯特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回家了,此时面临的问题是:凯特是否应该回家。最后的选择将读者与凯特的距离再一次拉近,凯特选择回家的决定,也使得读者随着情节的发展做出相应的价值判断。
总之,“离去”与“归来”的表层结构在拉近读者与凯特之间的距离上起着明显的两个作用:第一,将故事内的人物(凯特)与故事外的人物(读者)紧密联系,读者要依据自己的价值观来衡量凯特的情感选择,而这正是读者参与小说的重要表现。具体而言就是读者的价值观时刻要根据“离去”与“归来”走向而做出判断。“离去”与“归来”是一种结构模式,同时其背后隐含的却是一种价值选择,所以到底是选择离去还是归来,这既是凯特要做的选择也是读者根据自己的境况而要做出的思考,读者到底做出怎样的选择不仅取决于使人能够产生共情情感的凯特,更取决于每一个读者本身身处的环境所赋予其的价值取向;第二,“离去”与“归来”的结构模式也有利于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当读者认为凯特应该反抗的时候,凯特却选择逆来顺受;当读者认为凯特应该安于现状的时候,凯特有生发出一波三折的变动。凡此种种都会激发读者的兴趣。其中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凯特的第二次离去完全是被迈克尔强迫的,读者这时候可以划分为两类:支持的或者反对的,支持凯特离开的就是顺应文本故事线走向的,而反对的读者就会认为凯特为什么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这就违背了后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期待视野,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进一步激发了这一类读者的阅读兴味。因此这种结构有利于拉近读者与凯特之间的距离。
四、结语
福楼拜说:“形式是外衣,不。形式是观念的血肉,犹如观念是形式的灵魂、生命”。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是形式与内容的高度契合,也就是说文学作品所选择的艺术技巧能够完美传达该作品所要表达的主旨思想。这一点对我们探讨莱辛这部《天黑前的夏天》中“离去”与“归来”的结构同样有效,在形式上该结构呈现的是一种不确定,正是这种不确定才肯定了最后“归来”决定的重要;内容上《天黑前的夏天》所反映主旨不止一种,每一次的“离去”或者“归来”的决定背后都表达了一种主题思想,但是最重要的是最后一次选择背后的内涵,即莱辛主张女性回归家庭,以此反对激进女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