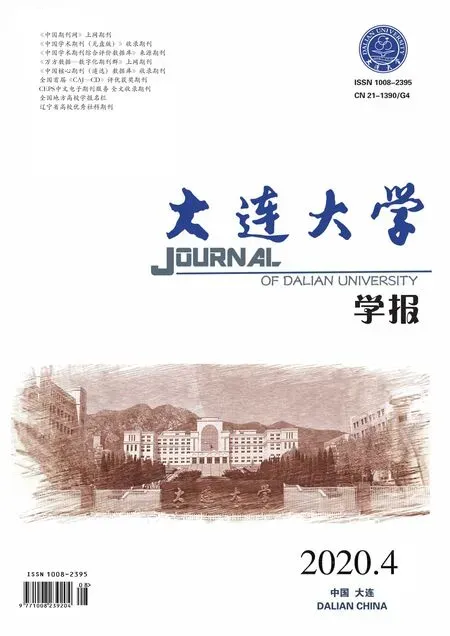徝、德及相关字字际关系考辨
俞绍宏
(郑州大学 汉字文明传承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01)
一、隶楷阶段相关字形梳理
在隶楷阶段汉字系统中,恩德、德行含义的“德”字存在多种异形写法,大致可分为两个系列:“德”“徳”“”“”等字形为一个系列,本文称为德系;“㥁”“”“悳”“惪”“”“”“”等字形为一个系列,本文称为惪系。汉字中还有一个与“德”字关系密切的“徝”字,西周时期用来书写词语“德”(本文以下凡词语均加{ })。
德系字均为“德”字异形写法。汉字中“彳”“亻”旁相混现象不仅隶楷阶段存在,古文字阶段已经出现①可参笔者《敦煌写本<诗经>异文中的隶定古文探源(之二)》,《励耘语言学刊》2015年第2期。,“”“”可分别视为“德”“徳”之“彳”旁讹为“亻”而形成的字形(为了称述方便,本文有时会将德系字中的“德”“徳”两类字形分别称为德类与徳类)。
惪系字形均为“惪”字异形写法。惪系字中带有“乚”形构件的“㥁”“”“悳”“惪”“”本文称为类。类中的“”即篆文“悳”之隶变字(见下引张涌泉说):一方面诸字形中的“直”旁所从的“十”讹写作“亠”,另一方面“乚”形构件省讹作一短竖画。当然,《说文》“惪”字古文作“”,而古文字中“”形构件在隶楷阶段可以转写成“亠”②可参俞绍宏、李索《敦煌写本<诗经>异文中的隶定古文释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5年第3期。,因此“”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的一种隶定形式。不带有“乚”形构件的“”“”本文称为“”类。汉字中的字形“恴”也属于这一系列,其即“”所从之“目”省简为“日”而成的字形,“日”增繁为“目”以及“目”简省为“日”而致使“日”“目”偏旁相混的现象在古文字中就较为多见,在敦煌写本等今文字中也较为常见,本文不再赘述。
惪系字形还存在其他变异写法,本文不再一一列举。
依据《说文》对“德”“惪”“直”“乚”的分析,按照研究现代汉字学研究者的说法,“乚”是“德”字的三级构字部件。
检《说文》,以“乚”为一级构字部件的字除“直”字外,尚有卷八“”部“真,僊人变形而登天也。从从目从乚;八,所乘载也”,卷12“亡”部“亡,逃也。从人从乚”,卷十二“匸”部“匸,衺徯,有所侠藏也。从乚,上有一覆之”,卷14“了”部“孑,无右臂也。从了,乚象形”。
二、基于出土的古文字以及汉唐文字材料的考察
检《新甲骨文编》[4],“乚”“匸”“惪”“德”“真”“孑”诸字未见录。
《新甲骨文编》[4]730-731直”下录有甲骨文“”“”等字形,从“十”从“目”,不从“乚”。《新甲骨文编》[4]108-109“徝”下录有甲骨文“”“”等字形,所从的“直”由“十”“目”构成,不带有“乚”形构件。
《新甲骨文编》[4]731-732“亡”下录有甲骨文“”“”等字形,虽带有类似于“乚”形的笔画,但其显然是同别的笔画连在一起的非独立的构字部件。秦汉时期隶书“人”或作“”,“亡”或作“”,[5]545、903“人”与“亡”字所谓“乚”旁之外的部分具有相似性,《说文》分析“亡”字从“乚”“人”或源于此。
《新甲骨文编》[4]734-735未见录独立的“匸”字。收录了《说文》“匸”部“区”字甲骨文“”“”“”“”“”等字形,“匿”字甲骨文“ ”“ ”等字形,“医”字甲骨文“”“”“”等字形,以及不见于《说文》的“”(作“”“”“”)、“”(作“”)二字。
《新金文编》[6]未录独立的“乚”“匸”“孑”字,录有“德(徝/惪)”“真”“直”“亡”字。
《新金文编》[6]201-204、1483-1484、1483“德”下收录有“”“”“”等共6例“徝”字,均为西周早期铜器铭文;“”“”“”“”等共37例德系字形,均属于徳类字形;从“辶”的“德”字异体“”“”“”“”4例,从“言”的“德”异体字形“”1例,前2例属西周晚期,后3例均属春秋晚期,諸形所从之“惪”均属于类字形;“”“”“”“”“”“ ”6例惪系字形。金文中的“徝”有的用作人名,是不是用作{德}不易确定。西周早期的曆方鼎(集成2614)铭文辞例“曆肇对元徝”,将其与集成238-242号铭文“穆穆秉元明德”比对,“元徝”显然就是“元德”,其“徝”字所记为{德}无疑。而其他非人名用字的“徝”字读{德},铭文文意也均能讲通。“徝”从“直”得声,“直”古音属定纽职部,“德”古音均属端纽职部,二者音近可通。37例德系字形中,西周时期31例,包括西周早期4例,中期8例,中期偏晚3例,晚期15例,另有1例未注明具体分期;春秋时期4例,其中春秋早期2例,中期偏晚以及分期未注明的各1例;战国早、晚期各1例,分别属于齐系铭文与秦系铭文。据相关铭文辞例可知,先秦金文中“德”字除了作人名外基本上是记录{德}。6例“惪”系字形中,西周中期1例,春秋晚期1例,战国中期1例,战国晚期3例。同时《新金文编》还列有“惪”字条,收录字形9例,其中有5例与“德”字条下惪系字形中除春秋晚期司马楙编镈“”外的其余5例字形重出,另收有西周中期字形“”“”2例,战国早期字形“ ”1例、战国晚期字形“ ”1例。[6]其中“”见于西周季嬴霝德盘(集成10076),作“/”,左下所从偏旁虽小,但明显是“彳”旁,为“徳”字无疑。《新金文编》辨析处理字形有误,将其误置于“惪”字条下。[6]《新金文编》所录的“”(集成3585嬴霝德簋),虽形体怪异,但将其与“/”比对,其即“/”字除去“彳”旁之外的部分,释“惪”可以信从。所录“”见于西周中期的惪盘(集成10110),将其与《新金文编》所录西周中期偏晚的燹公盨作“”“”形之“徳”相比较,“”显然是“徳”,只是右侧的反书的“彳”(即“亍”)有所残损。因此《新金文编》“惪”字条收录的惪系字形其实只有7例。7例中除用作人名1例外,其余均可以根据铭文确定其记录{德}。惪系字中只有晋系文字(即前录令狐君嗣子壶“”、中山王圆壶“”、中山王鼎“ ”、中山王方壶“ ”)属于类字形,其他都属于类字形。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战国楚简中“惪”字多见,其基本用法是记录{德},绝大多数属于系字,但郭店《语丛三》简24、26、50、54的“惪”字属于类字形,与晋系文字同。学者多以为《语丛三》有齐系文字特征,可能是以齐系文本为底本③可参冯胜君《郭店简与上博简对比研究》(国别篇章节),线装书局,2007年。。而《新金文编》“德”字条下收录的战国晚期齐系陈侯因敦铭文中的“惪”属于类字形。据此或可推测,《语丛三》可能与晋系底本也存在某种联系。
《新金文编》[6]1118“真”字条下收录3例字形,属于西周早期的“”(集成870伯真甗)从“”“贝”,“丁”声,“”(集成10091真盘)从“”“贝”“丌”;属于西周中期或晚期的“”(集成531季真鬲)从“”“鼎”。3例均不从“乚”。
《新金文编》[6]1741“直”字条下收录有字形“”(集成4199恒簋盖)1例,属于西周中期,字从“乚”。
《新金文编》[6]1741-1744“亡”字条下收录“”“”等字形几十例,与甲骨文类似,不从“乚”。
《新金文编》[6]1758-1762“匸”部“区”下收有战国时期子禾子釜铭文“”1例。“匿”下收有“”“”“”等字形,共10例,9例属于商代,1例属于西周早期,3例从“乚”(这3例均属商代),7例从“匸”。“匽”字下“”“”“”“”“”“”等字形,共38例,包括商代1例,西周早期19例,西周晚期2例,春秋时期15例,战国时期1例,其中属于商代与西周早期的字形绝大多数从“乚”,属于春秋时期的字形均从“匸”。“匹”字下“”“”“”等字形17例,分属于西周早中晚期,均不从“匸”“乚”。
《字编》[7]114“德”字条下录有秦系陶文德系字“”1例。录有楚系王子午鼎、王孙诰钟铭文各1例,均易“彳”为“辶”(字形已见前引参考文献[6])。录有齐系陈曼簠“”1例。另收有郭店简《老子》“”、晋系侯马盟书“”等惪系字各1例,晋系侯马盟书作“”形之“徝”字1例,晋系诸字均为人名。诸字形中除了晋系文字“直”(旁)带有构件“乚”,其他均不带有“乚”。
《字编》[7]700-701另列有“惪”字条,收录的字形除了见于郭店简《语丛三》之“”“”“”,侯马盟书之“”,以及令狐君壶、中山王鼎、中山王壶(后3器文字已见于前文所引参考文献[6])等晋系字形带有“乚”形构件,属于类外,其他如郭店简《老子甲》“”、郭店简《老子乙》“”、包山简“”等字形均不带“乚”形构件,属于类字形。
《字编》[7]568“真”字条下所录“ ”“ ”“”“”4例字形下部从“丌”,均不从“乚”。
《字编》[7]824-825“直”字条下录有的11例字形,其中有侯马盟书“”“”“”“”4例,郭店简《唐虞之道》“”“”2例,秦陶文“”“”2例,睡虎地秦简“”1例,均带有“乚”形构件。有楚系鸟虫书带钩铭文“”1例,似带有“乚”形构件。有古玺文“”1例,不带有“乚”形构件。
关于楚系鸟虫书带钩铭文“直”字带有的类似“乚”形构件需作补充说明。鸟虫书随意赘加笔画为饰的现象多见,其字形中类似“乚”的构件也有可能本不是“直”字形中的一部分。同样的现象也见于《字编》[7]366“植”字条下所录楚系鸟虫书带钩铭文“”,而郭店简《老子》“”、《缁衣》“”均不带“乚”形构件,侯马盟书“”则带“乚”形构件。笔者查核上博楚简,除了第一册《性情论》简32“直”因字残带不带“乚”形构件不能确定外,其他“直”字均不带“乚”形构件,如第六册《天子建州》简4、5的3例“直”字。另外第一册《缁衣》简2、《性情论》简28,第五册《弟子问》简3、20,第六册《孔子见季桓子》简25,第八册《李颂》简1的“植”字;第五册《姑成家父》简7从“木”“惪”声之字,第六册《孔子见季桓子》简21从“人”“惪”声之字,均不带“乚”形构件④从“人”“惪”声之字也见于春秋时期的王孙遗巤钟,战国时期的鄂君启车节、包山简84与85等,字形可参参考文献[6]1117、[7]567,也均不带“乚”形构件。。清华简中出现的“直”旁也均不带“乚”形构件,如第八册《摄命》简17、18从“辶”“惪”的“德”字异体,《治邦之道》简25从“臣”“直”声之字,《邦家之政》简5、12之“植”,以及见于《摄命》、《邦家之政》篇中多例“惪”字。因此,纯粹的楚系文字中“直”可能是不带有乚形构件的。学者或以为《唐虞之道》源于齐系底本⑤可参冯胜君:《郭店简与上博简对比研究》(国别篇章节),线装书局,2007年。,笔者以为其与晋系底本或也存在某种联系,所以其“直”字带有“乚”形构件而具有晋系文字特征。
《字编》[7]未见录有“孑”字。
《字形表》[5]120“德”字条下收录秦泰山石刻篆文“”(又见于下引《类编》《文编》)1例,两诏椭量中带有秦隶风格的字形“”(又见于下引《类编》《汇编》)1例,西汉时期“”“”“”等篆文与古隶(即秦隶。下同)字形9例, “直”旁均不带有“乚”形构件,即均属于徳类字形。带有“乚”形构件的德类字形东汉时期始现,且“乚”形构件讹作“一”形,如东汉孔宙碑“”。
《字形表》[5]743“惪”字条下收有西汉早期马王堆汉墓《老子》“”“”2例,均不带“乚”,属于类字形;带有“乚”形构件的“惪”(即带有“乚”形构件的类字形)出现于东汉时期,如“”“”,且“乚”形构件讹作“一”形。
《字形表》[5]580-581“真”字条下所录秦汉魏晋字形均不从“乚”,其下均从“丌”,如睡虎地秦简“”,马王堆《老子》“”,新莽时期新嘉量“”,东汉礼器碑“”,晋辟雍碑“”。
《字形表》[5]902、903“直”字条下录有秦峄山碑“”、睡虎地秦简“”各1例,以及银雀山汉简“”、居延汉简“”、新嘉量“”等西汉、新莽时期字形多例,均从“乚”;东汉时期“乚”形构件讹作“一”形,如孔彪碑“”、熹平石经“”、礼器碑“”等。
检《字表》[11]40-41,“直”字条下收录秦汉至唐代字形80多例,均从“乚”,只是后期字形“乚”讹与“一”形混同。
《字表》[11]134-135“真”字条下所录秦汉至隋唐字形50余例,除了唐代小篆字形带有“乚”外,其他从西汉早期到唐代诸形均不从“乚”形构件。
《字表》[11]380-382“德”字条下收录的西汉至唐代德系字与惪系字近150例,凡西汉时期的均不带有“乚”。德类出现于东汉时期,但只占极少数;魏晋至隋唐时期使用频次渐增,所带有的“乚”形构件或讹作“一”形,但占优势的依然是徳类字。汉唐这段时期德系字使用频率高于惪系字。
学者对“德”“惪”“徝”“直”等字形字义多有讨论。
《诂林》[12]554-555、570-57“8直”字条下按语以为“直”与“省”有渊源关系;“省”字下条按语说“直”为“眚(省)”初形,金文中的“眚”为“直”字之讹变。而甲骨文“直”用作“值”“植”“殖”“埴”[13]307。
《诂林》[12]570-578、2250-2256甲骨文“徝”字录有释“德”“省”“循”“”,以及“直”字初文等说。按语中从释“”说,解为巡视之“省”,指出其在卜辞中表察视义,也表祭名;又释为“循”,读“巡”。
何琳仪以为甲骨文“直”字从“目”“十”声,金文恒簋“直”字加“”其义不明。[15]67
宋华强以为卜辞“徝降”应即文献中的“陟降”,宾组卜辞说到对敌国用兵,或言“征某方”,或言“伐某方”,或言“徝某方”,或言“徝伐某方”,又常见省去方国名而言“伐方”或“徝伐方”,“征、伐、徝”三字用法接近,“徝方”也就是征伐方国的意思”,而《书·尧典》“陟方乃死”就是卜辞的“徝方”,也就是征伐敌对方国(三苗)的意思。[16]31-32
杨泽生以为甲骨文“徝伐”“徝方”“徝某方”之“徝”当进兵征伐讲,甲骨文“徝征”应即进兵征伐的意思;表祭祀义的用法的“徝”读“登”。[17]107-109
《古文字谱系疏证》以为“直”字从“目”,从一横画,会正见之意,金文(恒簋)于“目”旁加“”。或以为从“十”声。“直”甲骨文用作祭名,金文恒簋读“值”。“直”孳乳派衍出“徝”“德”“”诸字。“徝”为“直”字繁文,“德”之初文;古通“陟”。“惪”从“心”“直”,会内心正直之意,“直”亦声。“直”“惪”“德”古本一字。“德”之初文“徝”追加“心”旁而成“德”,“德”金文多用表道德、德行、恩德等义。[18]151-154
李学勤以为“德”从“彳”“直”声,甲骨文“德”从“彳”“直”声,金文多在“直”下加“心”,“德”遂以“”为声;“”从“直”“心”,也是古“德”字;“德”字本义为登、升,也常用指道德、品德。又指出“惪”从“心”“直”,“直”亦声。甲骨文“直”从“目”“丨”,会以目测量材料、使之不弯曲之意。[20]136、925、1114
李爱民所附笔画检索表、拼音检索表中仍从《诂林》释甲骨文“徝”字为“循”。[21]681、693
牛海茹以为“徝”在甲骨文中主要用于军事和祭祀两种活动当中,理解为“循”。表军事活动时理解为对军事防备或军事力量的巡查,表祭祀时与“直”相同,含义待考。[22]101-108
王冠英以为甲骨文“徝”一是用作祭祀方式,二是该字从“彳”“直”,亦取其身行目视、且行且视之意,故可训为循行、巡行;刘桓则读“待”。[23]559-560
郭沂以为甲骨文“徝”有“巡”“德”两读,即文字学家所说的同形词(笔者按,应为同形字)。前者义为“巡视”;后者为得失之“得”,是“德”的本义。“悳”为“德”的异体字。[24]88-94
可见学者对相关字之分析存在分歧。
三、陋见浅陈
第一,关于“直”字及其所从的“乚”
通过上述考察可知,“直”本不从“乚”。就现有出土文字材料来看,从“乚”形构件的“直”最早出现于西周中期,后为晋、秦二系文字所继承,秦系文字又为汉代文字所继承。
《说文》训“直”为“正见也”,训“乚”为“匿也”,而“正见”与“匿”似无关联。从词义角度看,“直”的基本义为正直,此义与匿义也无关联。因此说“直”从《说文》训为“匿也”的“乚”可疑。
在出土的商周秦汉文字材料中,独立的“乚”字未见,《说文》中所录以“乚”为一级构字部件诸字中只见到“直”字带有“乚”形构件。《说文》中带有“乚”形构件的“真”字极有可能是东汉时期的人基于他们对“真”字的理解(即《说文》所谓“仙人变形而登天也”,有遁隐义),对其字形进行改造而形成的字形。前文已述,“德”“惪”“直”字形中的“乚”形构件东汉时期讹作“一”字形,“真”字《说文》篆文中的“乚”形构件可能源自其古文字字形所从的“丌”形构件之横画,是这一横画的变异写法,其过程与“德”“惪”“直”字形中的“乚”形构件讹作“一”形正相反。而从“匸”部之“区”“匿”“匽”古文字字形来看,早期多从“乚”形,且从“乚”形与从“匸”形互作,晚期一般从“匸”形,《说文》训“匿”的“乚”与训“有所侠藏”的“匸”可能是同一个偏旁的不同写法。
前文所述西周金文中“直”带有的“乚”形构件,其可能并不是《说文》训“匿也”的“乚”。《新甲骨文编》[4]115“建”下录有甲骨文“ ”;《新金文编》[6]215、218“廷”下录有金文“”(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西周中期)等字形,“建”下录有金文“”(商代)、“”(西周早期)、“”(西周中期)、“”(春秋晚期)等字形;《字形表》[5]126峄山石刻作“”,泰山石刻作“”;石鼓文《田車》之“騝”作“”[5]466。疑“直”所从的所谓“乚”与上列“廷”“建”带有的“”形构件同⑥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简7有“”,原简字形作“”,文例为“世無德”,整理者指出“”从“乚”声,通“隐”(可参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59页)。从通读文意角度看,“”分析为从“乚”声是适合的。不过上博藏楚简中的“隐”数见,均用“”声字,如第一册《孔子诗论》简1“诗无(隐)志,乐无(隐)情,文无(隐)意”,简20“其(隐)志必有以俞也”,《性情论》简29-30“凡悦人勿(隐)〔也〕”(郭店简《性自命出》简59与《性情论》对应的字作“”);第二册《内礼》简6“(隐)而任”。同时“”若真是从“乚”得声,这可能是出土文字材料中“乚”旁出现的唯一例子,属于孤证。因此“”字也有可能存在别的考释意见。。裘锡圭以为“建”字本从“”,《说文》讹作“廴”;古书多训立,甲骨金文中“建”字某些字形正像持物立于“”内之形[25]353-356。
“直”字《说文》“正见”之训引申出一般的正、不弯曲、不歪斜等义。“建”有立义;又有建筑、建造义,如《逸周书·作雒》“乃建大社于国中”⑦“国中”原书作“周中”,为“国中”之误,可参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修订本),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37页。。无论是立还是建筑,均应正而不歪斜。《说文》“廷,朝中也”,古籍中由其构成的“庭”“挺”字均有直之训,如《诗·小雅·大田》“既庭且硕”,《诗·周颂·闵予小子》“陟降庭止”,毛传“庭,直也”;《周礼·考工记·弓人》“于挺臂中有柎焉,故剽”,郑玄注“挺,直也”。《说文》“庭,宫中也”,段注说“庭者,正直之处也”。疑“庭”“挺”可能是“廷”字的孳乳分化字,则“廷”字理当也有直义。如此则“廷”“直”“建”诸字字义均有关联。疑古文字中“直”“廷”“建”等字带有的“”形构件可能与测定垂直度的器具,或者古代测日影以定时节等的圭臬、圭表有关。《周礼·考工记·匠人》“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视以景”,说的是建都城时如何测定地面的水平度、槷(即臬,古代测日影的木柱)的垂直度。圭表形状与古文字中“直”“廷”“建”带有的“”形构件相似,可参文后所附1965年在江苏仪征汉墓出土的铜圭表图片。这件铜圭表高为汉制八寸(19.2厘米),属于缩微版便携式圭表,表高度为《三辅黄图》所载、造于西汉太初四年的长安灵台铜表的十分之一[26]407-408。而要使圭表测日影、定时令准确,放置时自然要正而不能歪斜。可见“直”“廷”“建”等字若用圭表之形“”作为表意部件是具有构形理据的。可能是受到“直”常用作正、直义的影响,西周时期出现了在甲骨文从“十”“目”基础上增益“”旁的“直”字。商及西周早期文字“建”字似为以“”测量他物的垂直度,也有可能是以他物来测定所立之“”是否垂直。
检《汇编》[10]57“建”字条下所录字形,带有“”形构件的“建”字只有元康雁足灯(元康元年,即公元前65年)“”1例;而长安下领宫高灯(神爵元年,即公元前61年)“”、林光宫行灯(建昭元年,即公元前38年)“”、建昭行灯(建昭三年,即公元前36年)“”与建昭雁足灯(建昭三年,即公元前36年)“”均从“廴”,可以据此推测从“廴”的“建”可能最早出现于西汉晚期。楚简“建”字多从“止”。
第二,战国时期惪系两类字的使用大致具有地域互补性
“惪”最早出现于西周中期,本不带“乚”形构件。带有“乚”形构件的“惪”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出土文字材料为晋系侯马盟书,也见于可能与晋系文字存在某种渊源的郭店《语丛三》,其应是受古文字(西周金文、侯马盟书等)中“直”字从“乚”旁影响,将类字形中不带“乚”形构件的“直”旁替换为带有“乚”形构件的“直”旁而成的字形。战国时期带有“乚”形构件的类字形与不带有“乚”形构件的类字形似乎具有地域互补性,即三晋系用类字形,非三晋系用类字形。
第三,关于德系两类字正俗关系及其构形
《说文》“德”字篆文之“惪”旁带有构件“乚”,两周时期德系字均不带“乚”形构件而作徳类字形,带有“乚”形构件的德类字形东汉时期始现。因此出土的两周时期文字材料中的德系字实际上应隶作“徳”,学者以为徳类字形为德类字形的省简体,此说不当。
《类编》[8]130-131“德”字条下录有秦公钟“”、秦公镈“”、秦公簋“”、两诏椭量三“”、两诏椭量四“”、墓志瓦文“”、琅琊石刻“”、泰山石刻“”各1例,均不带有“乚”形构件。
《文编》[9]100“德”字条下录有“德”系篆文字形6例,其中秦国诅楚文“”1例,以及上引《类编》秦代泰山石刻、琅琊石刻篆文字形各1例,均为不带“乚”形构件的徳类字形;所录三国曹魏正始年间的三体石经“”、品式石经“”各1例,孙吴禅国山碑“”字1例,均为带有“乚”形构件的德类字形。录有“惪”系篆文2例,为曹魏三体石经“”、品式石经残字“”,均带有“乚”形构件,于所录三体石经“惪”字形下注云“古文不从彳”。
《汇编》[10]55“德”字条下所录的秦旬邑权“”、大騩权“”、两诏椭量一“”、两诏椭量二“”、两诏椭量三“”、元年诏版三“”,西汉宣帝甘露四年池阳宫行灯“”,新莽时期新嘉量“”“”“”,共10例字形,均不带有“乚”形构件。两诏椭量二、旬邑权、大騩权上面的字形均带有古隶风格,出自两诏椭量二上面的字形与《类编》中出自两诏椭量四的文字,以及《字形表》所录两诏椭量字形一样,均带有古隶风格。
据上可知,带有构件“乚”的德类字形显然不是源自秦篆,其或是东汉时期的人们受当时“直”字从“乚”形构件的影响,将不带有“乚”形构件的“”增繁为带有“乚”形构件的“”而成的“徳”字增繁体。也有可能是东汉人受晋系文字(汉代人称述当时发现的六国文字为“古文”)“惪”字带有“乚”形构件的影响,将“德”字中不带“乚”形构件的“”替换为带有“乚”形构件的“”而成的字形。
综合对《类编》《文编》,《汇编》三书,以及对商周甲金文字材料、《字形表》《字表》的考察,可知两周至西汉,德系字只有徳类字形,被后世学者尊为正字的德类字并不存在,因此两周至西汉,徳类字形才是正字;东汉时期徳类字形的使用仍然占绝对优势。检《字表》[11]380-382所录三国至唐时期的德系字,不带有“乚”形构件的徳类字形40余例,带有乚形构件的德类字形30余例。我们曾对敦煌先秦写本文献德系字进行过初步考察,发现徳类字形数量远多于德类字形。从历史传承角度看,结合使用频率,我们以为东汉至唐时期,处于正字地位的应是徳类字形。据《字表》[11]382,开成石经用字形“德”,如作“”“”“”。前引李索书指出今《四部丛刊》影印宋本儒学十三经中除《论语》基本用徳系字形外,其余以用德系字形为主。这是刻本兴起后的用字情况,并为后世所承续,这可能与开成石经的刊刻及其强大的正字作用有关。
“徝”“德”“惪”均可记词语{德},据前文,“徝”字产生早于德系字,德系字产生早于惪系字,也就是说德系字产生时,惪系字尚未产生。从汉字发展史角度看,德系字应当是在“徝”基础上增益形符“心”而成的形声字,构形上应分析为从“心”,“徝”声,《说文》说“德”从“惪”声不可信。从“心”,“徝”声的“德”在构形上与《说文》“升也”之训关联性不强,“升”之训应当是假借用法(说见后文)。
第四,“德”“惪”之关系——古文字中大致具有时代与地域互补性
一方面,两周时期德系字、惪系字均可用作人名,且人名用法之外均记录{德},用法相同。另一方面,从时代上看,{德}西周早期用“徝”与德系字,中晚期用德系字;春秋时期多用德系字,偶见用惪系字,战国时期多用惪系字(秦系文字除外);另外在齐系铭文中,战国早期还有使用德系字的,晚期使用惪系字。从地域上看,战国时期,秦系文字用“徳”,其他地域以“惪”为主。可见徳、惪二系字的使用在时代与地域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以上两方面似乎表明德、惪二系字存在着异体关系。再从构形角度看,“惪”固然存在从“心”“直(声)”的可能,但我以为其更可能是来源于对“德”字的省简,古文字中此类简省现象多见,即省简掉“彳”而成的字。前文说“徳”省简为“惪”发生在西周中期,因此在西周中期以后的古文字材料中出现了用“惪”作偏旁构成的字形,如前文所述西周晚期散氏盘“”、降弔豆“”,春秋晚期王孙钟“”、王子午鼎“”,从“辶”“惪”;春秋晚期蔡侯钟“”,从“言”“惪”;沪简《孔子见季桓子》简21的 “”,从“人(亻)”“惪”。当然“”之类字形视为“彳”旁更换为“辶”旁,“”可视为“彳”旁更换或省简为“人(亻)”旁,也可备一说——前文已经指出“人(亻)”“彳”互换是古、今文字中均存在的现象。段注以为在表示德行、恩德义时“惪”为本字,“德”为俗字、假借字,此说不足信。
第五,“徝”“陟”“德”的字际关系
关于“徝”字,《汉语大字典》有两解,一是引《玉篇》训“施”,二是同“陟”,引《集韵》训“登”,引《字汇》训“升”与“进”。[27]827关于“陟”,《汉语大词典》第一个义项是“由低处向高处走”、“与‘降’相对”,文例有《诗·周南·卷耳》“陟彼崔嵬,我马虺隤”;第二个义项是“远行,长途跋涉”,文例有《书·太甲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第八个义项是“祭祀山岳”,文例有《诗·周颂·般》“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郑玄笺“则登其高山而祭之”,马瑞辰通释“……是升为祭山之名……升为祭名,陟即为升,亦祭名矣。周时祭山曰升,或曰陟,犹秦汉时曰登封,或曰登礼,或曰登假”。[28]982
《新甲骨文编》[4]789-790、791-792“陟”下录有甲骨文“”“”等,“降”录有甲骨文“”“”等,从甲骨文字构形来看,“陟”本应与“降”意思相反,指登高,也即上引《汉语大词典》“陟(zhì)”的第一个义项,这也是其在文献中常用的基本义训。从词义引申角度看,“陟”造字本义为登高,其与“祭祀山岳”固然存在关联性,但据郑笺“则登其高山而祭之”,则“陟”为登高之祭,不只是祭山岳;据《诂林》[12]1255,甲骨文中的陟祭就有祭先祖的。其与“远行,长途跋涉”关联性较弱,“远行,长途跋涉”应当是其假借用法,这一用法的本字极有可能是甲骨文中的“徝”⑧。“陟”古音属端纽职部,与从定纽职部的“直”得声的“徝”音近可通。学者所论甲骨文“徝”为“德”(义为“获得”)、“巡”二者本字之说不可信。一方面,甲骨文中已有“得”字,如“”“”“”“”等[4]105-106。另一方面,据西周早期金文,“徝”可表德行、恩德之{德},此为假借用法。甲骨文“徝”应分析为从“彳”“直”,“直”亦声。“直”《说文》训“正见”,“彳”表行走,“徝”正好完备地表达了巡视义。
《汉语大词典》收有“陟方”一词,解为“犹巡狩,天子外出巡视”,文例为《书·舜典》“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孔传“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苍梧之野而葬”,孔颖达疏“升道,谓乘道而行也,天子之行,必是巡其所守之国,故通以巡守为名”。[28]982“陟方”若解为“升道”,若不增字为解,“陟方乃死”字面意思即登上路就死了,显然不足信:文献记载舜死于苍梧之野,苍梧之野属于南部方国⑨。《汉语大字典》“方”字条下列有“殷、周称邦国之辞”这一义项,文例为《易·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书·多方》“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方者,殷、周称邦国之辞……故干宝云:‘方,国也。’是也”。[29]2172《汉语大词典》“方”下列有“上古指邦国,亦指古行政区的州”义项,文例有《诗·大雅·常武》“如雷如霆,徐方震驚”高亨注。[30]1550“陟方”的“方”也应解为方国,“陟方”就是巡视、巡行、巡守方国,“陟”即巡视、巡行、巡守义,与上引《汉语大字典》“方”字条下所引《易·观》“省方”之“省”相对应,与“陟”之“远行,长途跋涉”义相关。“陟”之巡行、远行义训的本字应当是甲骨文中的“徝”。至于学者所论甲骨文“徝”有征伐义,主要依据的是甲骨文中的“徝伐”“徝正(征)”文例。一方面,甲骨文“徝伐”“徝征”可以理解为巡守、征伐;另一方面,正如牛海茹引《礼记·王制》中对“巡守”有关表述,古代的巡守包含讨伐叛乱者[22]103。我以为这两种理解文意均可通。可能甲骨文中的“徝”在西周时期主要用来记{德},到东周时期只有晋系文字还在沿用,随着晋系文字的湮灭,字形“徝”秦汉时期消失,因而其不见于《说文》,传世先秦秦汉文献也难寻其用例。《玉篇》训“施”、《集韵》训“登”、《字汇》训“升”与“进”的“徝”字应当是一个后起字形,其与甲骨文“徝”字或只是同形字关系。
古音“德”“陟”声纽韵部同,与“徝”音近可通,训升的“德”其本字或应为“陟”。前引《诂林》[12]578、2250-2256之按语中指出“徝”在卜辞中可表察视义、巡视,也表祭名,这应当是其在甲骨文中的主要用法。查检甲骨文相关文例,尽管许多文例中的“徝”字因辞残,或文辞简约、文辞古奥难懂而不明其用法,但“徝方”“徝某方”文例多见,其中的“徝”解为巡视、巡守,文意均通。据《诂林》[12]1255,甲骨文“陟”字也有表祭名之例,应是本字用法。甲骨文“徝”字表祭名时,其本字可能也是“陟”字——同词异字现象在包括甲骨文在内的古文字材料中多见,例不赘举。当然,所谓用作祭名的“徝”也有可能读作“德”,请看下列《诂林》[12]578所引用作祭名的两条文例:
其实这两条文例中的“徝”若读作“德”,文意也通,“德”有感恩戴德的意思,如《左传·成公三年》“然则德我乎”,上列两条文例中的“德”也可作此解,可能是指感恩之祭,与报祭类似,《尔雅·释诂下》“侑,报也”,即报恩、报答的意思,“德”“侑”含义相近。甲骨文中类似的文例还有,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再看下面一例:
“害”与“不徝”因果关系明显,卜辞文意是説父乙施害,因而不对父乙进行徝(德)祭,即这里的“徝”理解为感恩之祭,与文例十分切合。若以上文例中的“徝”的确可以读作“德”,那么无疑将出土文献中的{德}出现的时间提前到了商代,而目前确知的出土文献{德}出现的最早时间为西周早期。
四、小结
德行、恩德为“德”字本字用法,《说文》训“升也”的“德”本字或为“陟”,文献中表巡行、巡守义的“陟”其本字或即甲骨文“徝”字。“陟”字的祭名这一用法甲骨文中或用本字,或借用“徝/直”字;当然,所谓表祭名的“徝/直”也有可能读“德”,则徝(直)祭与报祭类似。从西周至西汉,德系字只有徳类形体,东汉始见的德类形体乃徳类字形之增繁讹变体,德系字本从“心”“徝”声。“惪”为“德”省“彳”而成的省简异体字形。“直”本不从《说文》之“乚”。战国时期类字形与类字形似具有地域互补性,先秦时期“德”与“惪”大致上也存在着时代与地域互补性。西周中期始见从“”的“直”,其所从的“”所指待考,疑其与古文字中“建”“廷”所从的“”一样,可能与古代测垂直度的器具或者臬、圭表之类器具有关。

图1.江苏仪征出土的汉代铜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