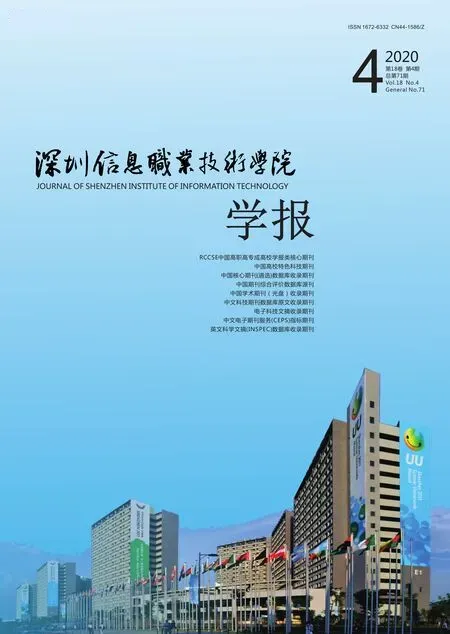《诗经·溱洧》“赠之以勺药”小考
程慧荣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溱洧》是《诗经》中以“淫诗”著称的《郑风》的最后一篇,学界基本公认该诗所描写的是郑国男女在春季聚会于溱水、洧水之畔的场景。但自汉代四家诗以来,古今学者便对《溱洧》篇末“赠之以勺药”的“勺药”究竟为何物以及“赠之以勺药”行为的涵义存有一定的争议,这些争议直接影响了后人对于《溱洧》主旨的理解,因此,“赠之以勺药”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在下文中,我们将通过梳理并分析周秦以来与勺药有关的文献,推断出“勺药”的具体所指,进而对“赠之以勺药”行为内涵进行新探,以期对《溱洧》的主旨有更为明确的理解,敬祈方家不吝指正。
1 “勺药”名物考
1.1 “勺药”含义集释
“勺药”一词始见于《溱洧》,《诗经》中仅此一见,这使“勺药”的名物考据相对比较困难,“勺药”究竟为何物,自汉代四家诗开始便无定论,素来有两大类说法:“植物”说和“调和”说。“植物”说可以再分出两小类:一是认为古今异物,即《溱洧》中的“勺药”是一种不知今之何物的香草;另一个则是认为古今同物,即此“勺药”与今之“芍药”是同一物。此外,“调和”说亦可再分出三小类,一是调料,名词,指具体的调味品;二是均调,泛指分布均匀、五味调和;三是调味,动词,指调味的行为。其中,作为“调料”的勺药还可细分出两种说法,一是与植物芍药有关的调料,另一个则是与植物芍药无关的调料。要之,前人有关“勺药”的考释,总共有两大类、六小类说法,参见下表。

表1 “勺药”含义归纳
1.1.1 “植物”说
《毛传》:“勺药,香草。”[1]毛公始注“勺药”为“香草”,解“勺药”为一种带有香气的植物,这给后代许多学者的注疏奠定了基础,古今学者大都认可“勺药”是一种草本植物。但正是这不够清晰的“香草”二字,又造成了后世的聚讼不已,后世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溱洧》中的“勺药”是否是今之“芍药”上。
“古今异物”说。勺是芍的同源字,二者无别,目前基本上没有学者因为“勺药”与“芍药”的字形不同而认为二者有差别,这些认为古之“勺药”并非今之“芍药”的学者,大多数是因为拘泥于《毛诗》所注“香草”二字。陆玑便持此观点,《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云:“勺药,今药草芍药无香气,非是也,未审今何草。”[2]在陆玑所处的三国时代应当存在一种名叫“芍药”的植物,但是此时的芍药似乎没有明显香气,不符合毛诗中“香草”的描述,所以陆玑认为《诗经》中的“勺药”并不是他那个时候习见的药草“芍药”。此外,《韩诗》认为“勺药”为离草,崔豹《古今注》认为“勺药”为可离,清马瑞辰认为“勺药”是蘼芜之类,均认为古之“勺药”并非今之“芍药”。
“古今同物”说。尽管有许多前人由“香草”二字否认《溱洧》中的“勺药”就是后世的“芍药”,仍有不少学者认为即使今之芍药茎叶不香,但芍药花无疑有香气,所以今之“芍药”亦可归为“香草”,因此古今芍药乃是一物。较早提出“古今芍药无异”这一观点的应当是宋代的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曰:“勺药即今之勺药,陆玑必指为他物,盖泥毛公香草之言,必欲求香于柯叶,置其花而不论尔。”[3]许多清代学者亦是持此观点,比如陈鳣《简庄疏记》曰:“今芍药甚香,《陆疏》云‘无香气’,岂当时尚未识其华耶?”[4]其观点跟吕祖谦一致,都认为陆玑忽视了芍药的花,古之“勺药”就是今之“芍药”。王念孙、陈奂等亦持此说。
1.1.2 “调和”说
“勺药”除了是植物名,亦可解为“调和”。《鲁诗》解“赠之以勺药”的“勺药”为“勺药之和”[5],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曰:“勺药又为调和之名”[6]。“调和”大致可以解为调料、均调或者动词调味。
“调料”说。陈子展《诗三百解题》:“勺药是调味之物,汉人相承语如此。”[7]尽管先秦时期的“勺药”含义不明,但至少从汉代开始,“勺药”就固定有了调味品、调料的意思。首先,“勺药”在作“调料”解释的时候,可以与先前的“植物说”不矛盾。因为芍药本身就是一味药材,可以食用,所以颜师古、俞正燮等均认为芍药这种植物本身就是一种调料。[8]马瑞辰亦认为勺药或许跟兰桂一样可以调食,“调和”之说可备异说。[9]其次,有学者认为“勺药”在作“调料”义时,这种调料与草本植物“芍药”无关,比如宋代的王观国发现“勺药”有两个读音,作调味品时的读音与作植物芍药时的读音有异,而且这个调味品是肉酱,跟植物芍药无关,《学林》云:“《子虚》《南都》二赋言勺药者,勺音酌,药音略,乃以鱼肉等物为醢酱食物也,与《溱洧》诗所言勺药异矣。《诗》之勺药乃草类也,今勺药花是已。《广韵》曰:‘勺,市若切,又张略切。药,以灼切,又良约切。’二字各有二音。”[10]黄侃认为勺药就是“作料”一词之正字,今湖南省方言,谓调味之物为香料,香或读去声,亦或谓指佐料。[11]
“均调”说。王念孙考古人饮食,未闻有用勺药者,自然也没有用芍药作调料的理由,所以他认为颜师古等解“勺药之和”为“以勺药调食”是不可信的,《广雅疏证》云:“勺药之言适历也,适亦调也。《说文》 字从厤,云:‘,调也,与历同。’又云:‘,希疏适历也,读若历。’《周官·遂师》注云:‘ 者,适历;执绋者,名也。’《疏》云:‘分布希疏得所,名为适历也。’然则均调谓之适历,声转则为勺药。”[12]王念孙考证出均调、适历、勺药三个词音近意通,认为“勺药”是“均调”的意思,即五味调和,十分均匀和谐。
“调味”说。“勺药”在作“调和”解的时候,还可以引申为动词调味,即调味的行为动作。许嘉璐先生认为东汉王充《论衡·谴告》篇“时或咸、苦、酸、淡不应口者,由人勺药失其和也”中的“勺药”所表达的正是此意。[13]
要之,“勺药”作“植物”的时候共有两种说法,一是“古今异物”的香草,二是“古今同物”的芍药花;“勺药”作“调和”的时候共有四种解释,一是与植物芍药有关的调料,二是与植物芍药无关的调料,三是均调,四是动词调味。
1.2 “勺药”名物考辨新探
在上文中,我们对前人有关“勺药”的名物解说进行了集释,总结出了两大类、六小类的说法。我们认为其中“均调”或者动词“调味”这两种说法应当首先被排除,因为“均调”指的是一种分布均匀、五味和谐的状态,“调味”则是一个动词,而《溱洧》“赠之以勺药”的“勺药”是一个物品,显然是名词,所以从词性语法角度而言“均调”和“调味”都是不合适的。因此,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只有“古今同物”的草本植物、“古今异物”的草本植物以及调料这三种说法(注:与芍药有关的调料跟与芍药无关的调料两小类合并,不做区别)。不过,即使有关“勺药”的这三种说法皆可通,我们依旧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1.2.1 “勺药”并非“古今异物”的香草
通过上文的整理,我们知道陆玑、崔豹、马瑞辰等均认为《溱洧》中的“勺药”是一种与芍药花无关的香草,但是他们的观点存在一定的问题。
首先,以《毛诗》所注“香草”二字否认“古今同物”说应当不妥。持“古今异物”观点的学者往往以“香草”为依据否定“古今同物说”,但是我们发现,古时解释名物的书,向来不单列“花”类,因此《毛诗》所注“香草”,未必就不是芍药花。古时解释名物的书,往往将“花”归入“草”类,比如三国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就没有专门解释“花”;现在流传下来的《尔雅》分19篇,分别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器、释宫、释光、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木、释草、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其中并未单列“花”类;作为《尔雅》的增补,《广雅》的分类依循《尔雅》旧目,分为19篇,其中亦没有“花”类。而且古人注疏中也少见“香花”而多见“香草”,我们认为,这或许与大多数草本植物都会开花的现象有关。
其次,如果《溱洧》中的“勺药”是一味罕见的香草,毛公应当不会以“香草”二字简单注之。“芍药”在汉代已经很常见,是一味常见药材,武威汉代医简中“勺乐”“芍乐”“勺药”均有一处,“芍药”凡两处,以及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也多有芍药,作为药材使用的芍药古今应当无别。[14]毛公身处汉代,亦应熟知芍药。古人作注的目的是阐明经义、避免歧义、便于后学理解,既然芍药常见,那么毛公自然不必为一常见之物详细作注。换言之,如果毛公认为《溱洧》中的“勺药”与药草“芍药”有异,他不应当用如此简略的“香草”二字草草了事,平白增添了这些歧义,反而违背了为经作注的目的。所以《毛诗》注“香草”二字,应当是为了与“调和”之义相区别,而非与芍药花相区别,因此,勺药应当就是芍药。
再次,芍药不是江离。不少学者认为“勺药”就是“江离”,江离又名可离、离草,是古书中另一种常见的香草,是离别之际的相赠之物,《韩诗》“勺药,离草也,言将离别赠此草也”[15]便是代表。但是我们认为该观点存在一定的问题。《广雅·释草》云:“挛夷,芍药也”,王念孙《广雅疏证》曰“挛夷,即留夷,留夷声之转也”[16],可见芍药就是留夷;再结合司马相如《上林赋》“被以江离,糅以蘼芜,杂以留夷”一句中“留夷”与“江离”并举的现象,我们认为留夷与江离应当不是一物,所以芍药不是江离。
最后,芍药不是蘼芜。《毛诗传笺通释》云:“古之勺药非今之芍药,盖蘼芜之类,故《传》以为香草”[17],马瑞辰认为《溱洧》中“勺药”是蘼芜之类的香草。但是我们认为勺药应当不是蘼芜,因为在《山海经》等文献中,芍药经常与蘼芜并举,如《山海经·中山经》“其草多葌、芍药、蘼芜、芎藭”[18],显然,芍药与蘼芜不是一物。而且唐朝诗人乔知之在《下山逢故夫》一诗中也有“庭前厌芍药,山上采蘼芜”的诗句,芍药与蘼芜亦是并举,表明至少在唐代人的认知里,芍药与蘼芜也不是一物。
1.2.2 “勺药”并非调料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总结出“调料”既有可能以植物芍药为原料,也有可能与芍药无关,但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跟“芍药花”比起来,可能性都不大。
假设所赠之调味品就是芍药,由于芍药采摘后无法直接食用,需要将芍药根进行诸如曝晒等加工之后才可食用,所以士与女必须提前准备好加工后的芍药并随身携带方可完成这一步;假设调味品不是芍药而是肉酱,流程亦是如此,甚至更加繁琐,总之这个过程十分复杂,可操作性较低。
春秋末年郑国大乱,社会并不太平,为了解决因战乱而锐减的人口问题,郑国男女才会于仲春之月来到溱洧相会,求偶求子,这是一件十分紧迫的事情。在这种焦急的心态下,我们不认为郑国男女会费尽心思以“调料”这一并无什么特殊寓意的物品作礼物来求偶。更何况先秦时期人们的物质生活并不丰富,依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我们并没有发现过有什么密封性强而且十分便携的器皿能够方便地把调料带出门,而且在士与女相谑游玩之后还能够完好如初地递交给对方。总之,跟直接在水边采一株芍药花相比,赠调料之举实在是迂曲复杂得多,因此所赠之“勺药”是调料的可能性不大。
1.2.3 “勺药”即芍药花
“芍药”与《溱洧》中“方秉蕳兮”的“蕳”生长习性相似,士与女具有在溱洧之地秉兰赠勺的可能性。《山海经·北山经》中有记载:“其草多芍药、芎藭,洧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19]可见洧水之地自古便出产植物芍药。《中山经》又有记载:“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银铁,其木多柤、梨、橘、櫾,其草多葌、芍药、蘼芜、芎藭。”[20]《中山经》此言表明芍药与葌可以生长在一起,“葌”与“蕳”相同,都是兰的意思,这说明芍药跟兰具有相似的生长习性,具有在溱洧之地共存的可能性。既然这些植物有可能生长在一起,那么士与女就有同时采摘兰和勺药并佩戴、赠送它们的可能性。
诚然,古今芍药之间或许有性状上的细微差别,但这种差别即使存在也只是一种自然演变的结果,而非本质上的区别。崔豹《古今注》云:“有草芍药,有木芍药。木有花,大而色深,俗呼为牡丹,非也。”[21]我们认为古之勺药类似于崔豹《古今注》中所言的“草芍药”,是一种野生的花,花小、观赏性不强,但药用价值高;而今之芍药应当为崔豹《古今注》中所言的“木芍药”,多为人工栽培,花大而艳丽,观赏价值更高。古人在论及古之勺药的时候,往往侧重于其根部的药用价值,而鲜少关注其并不明显的花;后人在谈论芍药花的时候,往往更加关注其芳香艳丽的花朵。我们认为这种关注点的转移也是造成古今学者对“勺药”一词聚讼不已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对《溱洧》中的“勺药”进行了名物考辨新探,认为“勺药”是一种草本植物,而且此“勺药”就是“古今同物”的芍药花,而非一种跟今之芍药花毫无关系的、不知是何物的“香草”或者调料。
2 “赠之以勺药”涵义新探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已经明确了“勺药”即芍药花。士与女以芍药花相赠,而不是以其他植物相赠,这种馈赠行为应当具有一定的寓意。有关“赠之以芍药”这一行为的内涵,学界历来众说纷纭,未有定论。学者杨文娟曾撰文分析过“赠之以勺药”的行为涵义,认为前人对此共有七种典型说法,其中最为传统也最为合理的观点是“结情”说。[22]我们对此表示赞同,但我们同时认为“赠之以勺药”的行为内涵还可以从读音的角度做进一步分析。
持“结情”说的前人对“赠之以勺药”有一种公认的看法,即“勺”“药”都与“约”读音相近,音近义通,二者可以通假,“勺药”就是“结约”的意思,马瑞辰主此说。[23]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有类似的观点,比如钱玉趾先生认为“药”与“约”同音,“勺药”的谐音就是“勺约”,《汉书·艺文志》有“勺椒浆”的记载,勺是动词,是舀的意思,约即约定、盟约、誓约的意思,所以“勺约”即“获得盟约”。[24]
但是我们认为“勺药”谐音“勺约”这一观点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勺药”在上古时期是一个叠韵连绵词,而叠韵连绵词属于连绵词,是只有一个语素的单纯复音词,虽有两个音节却不能拆开来解释,所以“勺”跟“药”二字不应拆开来理解,故而“勺药”的谐音也应当是一个字,而不是两个字“勺约”。
我们认为“勺药”所谐音的字应当与《溱洧》全诗所发生的背景有关。前人对“溱洧之会”所发生的背景聚讼不已,大致有求偶欢会、上巳祓禊、祭祀高禖神、祭祀社神这几种说法。尽管这几种说法都具有合理性,但是单纯从《溱洧》文本来看,我们只能直接看到一对男女在溱洧之畔嬉笑玩乐的场景,而不能直接看出上巳洗濯、祭祀高禖、祭祀社神等深层次信息,因此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溱洧之会”所发生的背景就是求偶聚会,这应当是最为稳妥的观点。
既然《溱洧》所描绘的是仲春之月郑国男女聚于溱洧之畔求偶欢会的场景,那么“赠之以勺药”的行为涵义应当与“求偶”主题相符合,“勺药”的谐音也应当与婚姻、求偶有关。我们认为,“勺药”谐音“妁”,理由如下:
首先,“勺”“药”“妁”三字的上古音极近,具有通假或者谐音的可能性。妁、勺,禅母药部;药,喻母药部。“勺”“药”“妁”三字韵部相同,声纽接近,故而可通。
其次,“妁”可以反映出全诗求偶的主旨。“妁”字有结婚的寓意,《说文解字》曰:“妁,酌也,斟酌两姓者也。”段玉裁注:“斟者,酌也。酌者,盛酒行觞也。斟酌二姓者,如挹彼注兹,欲其调适也。”[25]可见“妁”字就是考量两个家族之间是否可以联姻。“媒,谋也,谋和两姓者也”[26],婚姻就是结两姓之好,“媒妁”表示的便是说合婚姻的人。因为“勺药”谐音“妁”,“媒妁”有媒人的意思,所以这朵芍药花就像是一个媒人,让士与女明白了对方的心意,故而“赠之以勺药”的行为涵义就是士与女相约结为夫妇的意思。
再次,古人运用谐音双关的手法来传情达意十分常见。“折杨柳”之举便是典例,“柳”谐音“留”,“折柳”寓意“久留”,将柳条赠送给即将远行之人,希望对方能够留下来,借此表达内心的不舍之情。诸如此类的例证不胜枚举,比如古人在结婚之时撒于床上的大枣、花生、桂圆、莲子,便是”早生贵子“的谐音;雕梁画栋上的蝙蝠纹样,亦是”福“的谐音等。因此,以谐音为“妁”的芍药花作为礼物赠予心上人来传情达意,具有民俗学方面的基础。
最后,即使“勺药”亦与“约”上古音极近,我们并不认为“勺药”谐音是“约”。因为“约”在先秦时期的用法十分正式,多用于国家间的盟约,而很少有“婚约”的意思,如《战国策·秦策》:“故先使苏秦以币帛约乎诸侯。”[27]高诱注“约,谋约也。”《吕氏春秋·淫辞》:“秦与赵相与约。”[28]高诱注:“约,盟也。”《溱洧》所描绘的只是士与女聚会的场景,用“约”字过于正式,没有“妁”字合适。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勺药”谐音“妁”,“媒妁”即媒人,所以这朵芍药花就像是一个媒人,让士与女明白了对方的心意,故而“赠之以勺药”的行为涵义就是士与女相约结为夫妇。
3 《溱洧》主旨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认为“勺药”就是生长于溱洧之畔的一朵芍药花,“赠之以勺药”的行为内涵就是愿与对方结为夫妇。鉴于此,我们明确《溱洧》是一首爱情诗,描绘了仲春之月郑国男女聚会于溱洧之畔求偶欢会的热闹场景。
有关《溱洧》的主旨,除了《韩诗》提出《溱洧》描写的是“招魂续魄,拂除不祥”[29]的上巳节活动以外,大多数古人都认为这是一首淫诗,主旨是“刺乱”,即通过郑国男女在溱洧之畔的聚会来讽刺社会上的混乱现状,比如《毛诗》:“《溱洧》,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30]《鲁诗》:“郑国淫辟,男女私会于溱洧之上,有洵訏之乐,勺药之和。”[31]。朱熹在《诗集传》中称之为“淫奔者自叙之词”[32],同样认为《溱洧》是一首淫诗。清代已经有一些学者反对“淫诗”之说,比如姚际恒就认为《溱洧》是“刺淫者,非淫诗”[33]。近代以后的学者大多脱离传统道德礼仪观念束缚,否定“淫诗”之说,认为《溱洧》是一首纪实诗或者爱情诗,比如陈子展先生认为这是一首实写士与女春日郊游之作,钱玉趾先生认为该诗是叙述男女在河边恋爱欢会的情诗,这都是十分合理的。但是他们与此同时也否认了“刺乱”的说法,我们对此有不同意见,我们认为爱情诗与“刺乱”或者“刺淫”的主旨之间并不矛盾,理由如下:
首先,“昏礼”在古时十分重要。根据《礼记·昏义》的说法,“昏礼者,礼之本也”[34],“昏礼”是所有“礼”的根本。“昏礼者,将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35]今人谈到“婚礼”或许想到的都是一对恋人之间的爱情,但古人心中的昏礼并非如此,昏礼是两个家族之间的大事,关乎祭祀宗庙与延续后嗣。
其次,《溱洧》的男性抒情主人公违背了昏礼。《仪礼·士昏礼》首句是“下达”,下达就是男方家遣媒人到女方家里去提亲,但是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已经明确,士与女在溱洧之畔就已经“赠之以勺药”,那朵谐音“妁”的芍药花就如同一个媒人,让双方明白了彼此的心意,显然,士人违背了“下达”,他已经失礼。此外,按照“士昏礼”的要求,在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六礼”完成之前,女子不应当与士人见面或者有过多接触,不过很显然,《溱洧》中的士与女不仅见面了,而且“伊其相谑”,他们举止亲昵甚至已经私定了终身,所以士人无疑再次失礼。“昏礼者,礼之本也”,士人违礼至此,自然是会受到后世儒者的谴责,原本质朴的爱情故事也就具有了讽刺社会礼崩乐坏的功用。
最后,《溱洧》属于《郑风》,郑是姬姓国,理应捍卫周礼,但是郑国却在溱洧之畔举行违背礼教的大型求偶聚会,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即使全诗反映的是质朴爱情,它依旧是礼崩乐坏最典型的写照。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溱洧》是一首反映男女爱情的情诗,诗中的士与女在溱洧之畔求偶聚会有违昏礼,所以这首诗才具备了“刺乱”的教化意义,爱情诗与主旨“刺乱”之间并不矛盾。
4 结语
《溱洧》篇末“赠之以勺药”一句蕴含了丰富的信息,通过对“勺药”的名物考辨,可知“勺药”应当是生长于溱洧之畔的一种野生芍药花,而不是一种不知名的香草,更不是调料。士与女在临别之际以芍药花相赠,谐音是“妁”的芍药花就如同一个媒人一样向对方传达了求偶的愿望,因而“赠之以勺药”的行为内涵就是愿与对方结为夫妇。通过“勺药”的名物考释以及“赠之以勺药”的涵义新探,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溱洧》一诗的主旨,赠勺之举看似只是质朴爱情的体现,其实他们的行为已经违背了昏礼,是礼崩乐坏的写照,因此《溱洧》一诗的主旨应当是借溱洧之会来讽刺郑国之乱,即“刺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