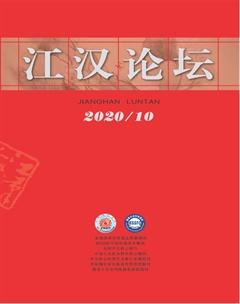从资本主义到协同共享
刘儒 张艺伟
摘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近年来,杰里米·里夫金提出的“协同共享经济范式”理念,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未来要共同进入共享经济时代,使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一科学论断遭到挑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自我调整、变革和不断完善被认为是制度性质的改变,导致各种有关两制“趋同”的论调纷至沓来,严重影响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正确理解和判断。目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确实出现了如里夫金所描述的协同共享经济现象,但这一现象远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更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协同共享经济范式是“趋同论”在当代的新翻版,协同共享经济范式无法取代资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是社会主义。
关键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协同共享经济范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趋同论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背景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研究”(18JZD01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生成逻辑和创新路径研究”(17AKS008)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10-0005-07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未来发展趋势作出的科学判断。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上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发展前景成为了经济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热点话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自我调整、变革和不断完善被认为是制度性质的改变,导致各种有关两制“趋同”的论调纷至沓来,严重影响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正确理解和判断。进入新世纪后,“趋同论”思潮随着以物联网和新能源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而沉渣泛起。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所主张的“超越市场资本主义的协同共享经济范式”这一观点日益流行且影响广泛,这对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唯物史观带来了极大挑战。
一、协同共享经济范式的意蕴
杰里米·里夫金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社会批判家和畅销书作家,长期从事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产生的影响研究。2012年,他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把人类社会进程划分为三次工业革命,认为当下我们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最后阶段。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构想,里夫金描绘了未来社会发展基于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相结合的合作性机制蓝图,在“能源互联网”基础上进入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后碳时代。里夫金强调,当新的能源与技术结合的时候,第三次工业革命就到来了。2014年,里夫金以《第三次工业革命》为基础架构出版了《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书,对未来社会新经济模式扁平化持续发展的概念作了进一步论述和深化。里夫金认为,未来将是一个由通信互联网、能源互联网和物流互联网组成的全球化超级智能物联网分享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生产者与消费者不再具有明显的边界区分,被统称为产销者①。这些来自世界范围内的产销者将会以近乎零边际成本的方式生产并分享绿色能源、商品和服务。至此,极致生产力将主宰人类社会进入协同共享经济范式,商品不再需要购买,产权也可以共享,靠吸食资本血液的资本主义将走到尽头,逐步被协同共享经济范式所取代。
那么,协同共享如何取代资本主义?里夫金在全书的开篇就给出了答案。“资本主义的没落并非由‘势均力敌所致,资本主义大厦的门前没有蓄势待发的狼群摧城拔寨。恰恰相反,瓦解资本主义的正是昔日将其推向顶峰的运行理念。”② 也就是说,尽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伴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通信/能源矩阵基础上形成的垂直整合型的商业模式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后,资本主义各种矛盾也随之显露。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带入经济领域,资本的趋利性非但无法使资本主义实现其自身的良性发展,而且会导致经济危机频发、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尖锐、生态环境恶化、生产关系滞后于生产力等问题。对此,里夫金断言,资本主义正在向“坟墓”走去,而“掘墓人”就是昔日将它推向顶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资本主义的生命值完全归零时,人类将开启由协同共享引领的超脱市场的全新经济生活。“资本主义市场将不再是经济生活的主宰者。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部分超越市场的世界,在这里,我们正在学习如何在一个相互依存越来越强的全球协同共享中共同生活。”③
(一)協同共享所具有的“零边际成本生产方式”超越了资本主义传统经济模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刻画了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即雇佣劳动——赚取剩余价值——积累资本——扩大再生产——赚取更多剩余价值。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衡量资本家赚取利润的标尺,无法满足所有资本家的野心。为了获得相对剩余价值,尤其是超额剩余价值,资本家千方百计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能力,以降低个别劳动时间。然而,里夫金认为,新技术革命足以颠覆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传统经济模式,带领人类社会进入协同共享经济范式。在未来,新兴物联网推动社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每额外生产一件产品或服务的成本几乎为零,当购买大部分产品都不需要再额外花钱的时候,以获取利润为主导的整个资本主义经营理念将变得毫无意义,到那时,资本利润枯竭,资产交易市场倒闭,资本主义制度也将消亡④ 。慕课是里夫金列举的零边际成本教育的典范事例。生产力高度发展变革了传统教学模式,教育的目的从培养善于劳作的产业工人转变为培养善于探索的协作者。慕课最大的特点就是兼具规模性、灵活性、开放性和平等性为一体,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在慕课中观看来自世界各地名牌大学教师的授课,这种全新的教学方式将取代传统高校教育。除了零边际成本教育是一大变革,社会的劳动方式也将得到变革。如今,已经出现的自动化工厂就是机器智能代替人工劳动的结果。里夫金预测,在未来,无论是物流领域还是服务行业,劳动都将被人工智能取代,并且人工智能能够突破语言障碍和科学技术限制,取代包括知识型劳动者在内的一切劳动,生产力将从雇佣劳动中解放出来,雇佣劳动虽然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未来将是几乎没有工人的世界,人工智能对于有偿劳动力的解放变革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发展历史。
(二)协同共享所具有的共享使用权形式超越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有权概念
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区别于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标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通过掌握生产资料来控制社会分配,以确保社会财富汇集在少数资本家手中。私有制的存在划清了个体之间的产权边界,强调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在无形中产生了狭隘的自私倾向。里夫金所推崇的协同共享,其核心概念是“所有权和排他权正在向使用权和纳入权转变”⑤,这个转变带来的是无尽的共享空间被激活,社会消费在实现了共享性的同时也兼具了环境资源的可持续性,人们的付出也不再以期待物质回报为前提,更多的是着眼于提高人类社会福祉。总之,协同共享所蕴含的消费理念就是一种提倡以分享或者租赁为主要内涵的可持续生活方式,私有产权和毫无节制的消费将被取代。对此,里夫金列举了两个共享事例:一个是共享汽车,另一个是共享医疗。汽车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把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带入电气时代。基于汽車工业的不断发展,私家车的普及率成为了现代化程度的标志之一。然而,协同共享时代的兴起改变了曾经以私家车普及率作为现代化程度标志的事实,传统私家车正在逐渐被共享汽车服务所取代。里夫金认为,在当下,各个国家的年轻人更愿意用汽车的使用权代替所有权,因为共享汽车的优势不仅在于免去了购买汽车及使用汽车后期需要支付的维护费用,更重要的是共享汽车能够减少城市汽车的保有量,释放公共交通空间、减轻环境污染、节约社会资源⑥。目前,共享汽车在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逐步实现,除了汽车共享是协同共享社会的产物之一,医疗卫生服务系统的共享也是从资本主义制度衍生出来的新模式。共享医疗的核心优势在于颠覆了传统医疗生态体系,共享医疗以物联网平台为支撑,能够便捷高效地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流动,均衡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医疗水平,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且具有针对性的医疗服务。同时,共享医疗具有极强的筛查和定位能力,能够通过对病毒的数据分析,获取病毒爆发的精确时间、地点及严重程度等重要数据,并且还可以追踪反馈病毒的蔓延速度和波及范围,这一点是传统医疗模式无法企及的。里夫金认为,在做好隐私保护工作的前提下,大数据物联网只要被医疗机构所掌握,必将给医疗卫生行业带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那些传统的、信息不对称的、成本高的医疗卫生服务将成为历史⑦。
(三)协同共享所具有的可持续绿色消费模式超越了资本主义反生态本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城市化问题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时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使它集中在中心城市的人口优势越来越明显,因此,它一边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一边破坏着人类生活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⑧。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耗费的自然资源不能及时补给土地,从而破坏土地资源的循环利用。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时破坏了城市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劳动者的精神生活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本性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造成了不可修复的生态灾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获取巨额利润的来源已经不限于对劳动力的剥削与压榨,对公共资源的疯狂掠夺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启工业革命的进程后,其自身的发展就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大肆开发森林资源、砍伐木材、污染河流,导致全球大范围的森林面积萎缩、植被退化、水土流失、动物灭绝、水资源枯竭、气候异常等问题。在20世纪30—60年代期间,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八大公害”事件,导致大量无辜群众生病死亡,引起了社会恐慌和人民不满,这一切都是由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过度消费生态资源引起的。资本主义追求资本积累的劣根性验证了其设法通过自然的资本化实现环境保护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凡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现代性反思都是徒劳的,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那么,想要彻底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修复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裂痕。里夫金认为协同共享的生产方式是让物质消费主义转变为环境资源的可持续,从而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由物质主义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能够在未来30—50年内大大减少地球上富裕群体的活动,释放地球活力,帮助贫困人口脱贫⑩。
毋容讳言,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催生下,协同共享经济模式的确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但由此得出协同共享经济范式将超越市场资本主义并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普遍经济范式的结论,显然是武断的和别有用心的。
二、协同共享是“趋同论”在21世纪的沉渣泛起
“趋同论”产生于20世纪“一球两制”的背景下,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竞争、对峙的结果。鼓吹“趋同论”的学者否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和制度界线,将两种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正常的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当作是制度融合的典范机制。1961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荷兰经济学家简·丁伯根在《共产主义经济和自由主义经济是趋同的样板吗?》中指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正在向比原本单纯的资本主义和单纯的社会主义更加进步美好的全新制度发展,这是“趋同论”首次以“理论形态”公之于众。随后,1965年,丁伯根与林耐曼和普朗克合著名为《东西方经济制度的趋同》一书,标志着“趋同论”正式形成。
毫无疑问,20世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衡与掣肘为“趋同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随着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进,“趋同论”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最为猖獗,直到90年代苏联解体才逐渐冷却。但是进入21世纪后,伴随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数字化经济形态的兴起,里夫金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在被协同共享经济范式所取代的观点使“趋同论”死灰复燃。事实证明,里夫金所提出的协同共享经济范式正在逐步瓦解资本主义政治结构、终结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与“趋同论”宣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将被“第三种社会形态”取代的主旨如出一辙,具有内在一致性,是彻头彻尾的当代“趋同论”新翻版。
(一)协同共享经济范式在路径归属上误判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趋势
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认识一直是马克思研究的重点问题。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第1卷中按照唯物史观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相继更替的历史过程,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五种社会形态论”是马克思在探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以生产关系性质为标准得出的科学判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马克思还在《共产党宣言》中依据资本主义的剥削现实断定资本主义必然陷入自身的生产关系矛盾之中,强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阐释,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社会主义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然而,里夫金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中提出的协同共享经济范式将取代市场资本主义的观点并没有正确地反映社会历史发展方向,没有认清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而是把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协同消费经济现象上升到社会制度层面,认为协同共享经济范式是可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体制。在里夫金那里,协同共享经济范式的产生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基于资本主义的这一根本特质,必然要被一种蕴含共享理念的协同消费社会取代。为此,他预测在21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必然衰败,协同共享必然崛起,到那时,协同共享将取代资本主义引领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如同马克思论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一样,“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终有一天将其埋葬,资本主义必然被取代。但是,溃败后的资本主义绝不会自行进入协同共享经济范式,协同共享经济范式是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衍生出来的一种经济现象,不具备制度属性,更不具备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依据,未来取代资本主义的只能是社会主义。
(二)协同共享经济范式在逻辑起点上将社会发展动力归于“科学技术决定论”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推动了近代西方工业革命。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科学技术逐渐被西方资产阶级奉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1929年,凡伯伦在其著作《工程师与价格系统》中首次提出“科学技术决定论”概念,后被以埃吕尔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决定论学派继承和发展。“科学技术决定论”按照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起到作用的强弱被分为“强技术决定论”和“弱技术决定论”两大类。一般而言,我们认为“科学技术决定论”属于“强技术决定论”,强调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唯一力量。“科学技术决定论”不但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发展是由生产力决定的这一核心观点截然对立,而且还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进步发展是“科技通过生产关系推动”这一核心观点,认为单纯依靠技术进步就能决定或支配社会的发展趋势,致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趋同”,从而无限夸大了科学技术的作用。辛向阳认为“科学技术决定论”是“趋同论”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并指出加尔布雷思作为支持“趋同论”的学者,多次表达“现代科技”是促进相同经济制度产生的唯一重要因素。在里夫金看来,协同共享经济范式取代资本主义的信心同样源于技术变革带来的物联网革命。物联网革命是21世纪变革资本主义命运的关键一招,基于强大的物联网技术革命,人类经济社会结构将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全世界的人和物都被连接到集成网络世界之中。通过物联网特有的信息传感器等技术装置将网络世界中的人力、物力、技术、设备、物流、资源等一切消费要素串联起来,进行感知、统计和管理,最终反馈至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边际成本,形成具有颠覆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力量,逐渐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向协同共享经济范式“趋同”。然而,物联网作为21世纪兴起的颠覆性科技,具有联通世界万事万物的超强智慧能力,但是这种科技和能力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结果,并不是推动协同共享经济范式产生的根本动力,也不构成协同共享取代资本主义的现实依据。
(三)协同共享经济范式在认识层面将“趋同”现象本质化
“趋同论”的错误在于没有正确理解“趋同”的实质,把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各自发展阶段上的调整和借鉴看作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而走向融合,混淆了社会现象与制度本质之间的差别。同样地,里夫金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中错误地把资本主义社会在21世纪出现的协同消费经济现象上升到社会制度层面,竭力夸大这一现象在制度层面取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抹杀了资本主义制度与协同共享经济范式之间的原则边界,使资本主义终将步入协同共享经济范式这一观点成为当代“趋同论”的翻版。诚然,在进入21世纪后,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确出现了协同共享的消费现象,这些协同共享消费现象也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如里夫金所描述的3D打印革命。3D打印作为新兴技术,不仅具有“信息化制造”的特点,也具有“增材制造”的优势,能够节约除去软件开发过程中的全部人工成本,直接利用电脑数据生成打印结构,减少原材料浪费,降低生产成本,是极致生产力的一次标准示范。但是,这一协同消费现象本身是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衍生而出的,是资本主义对自身未来发展的一次转型。因为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而言,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使它为了追求剩余价值不顾牺牲一切,随着对剩余价值的索取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能承担化石能源时代带来的负面效应,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面对的经济衰退、资源日渐枯竭、生态环境被破坏不可逆转的矛盾和问题,资本主义借助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巨大能量,实现了可再生能源和互联网技术的完美结合,形成了分散式、扁平化的全新生产方式以及高效、便捷、可持续的绿色能源在线共享体系。这种模式为资本主义带来了一种趋近于零边际成本生产方式的改变,全新的智能技术改变了原始传统低效的人工劳动行为,全新的共享能源管理方式改变了原始的以命令控制体系为主的资本能源模式,全新的高效低碳出行方式改变了原始的耗时耗能耗财的单一固定出行选择。毋庸讳言,资本主义利用互联网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减少资源浪费的模式是资本主义对以往过度消费的反思,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实现的,绝对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更无法实现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
三、协同共享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
在当前全球兴起协同消费浪潮的大环境下,里夫金认为协同共享可以取代市场资本主义的观点并没有认清资本主义共享经济的本质,单纯地认为只要变革了资本主义形态,就可以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基本矛盾,实现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殊不知,协同共享仍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是大义凛然的赚钱工具,协同共享正在用“共享”的名义把自由市场经济的魔爪伸向我们曾经一度被保护的经济生活领域。
(一)协同共享没有否定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
如前所述,协同共享经济范式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兴起的交易行为,这种交易行为仅仅是商品和服务使用权的让渡或租赁,不涉及所有权概念,更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本质。哪怕是在极致生产力作用下,零边际成本消费方式依旧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生产力发展的表象。生产资料私有制作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标志,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而产生,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消亡而消亡的。恩格斯指出,只要私有制存在,“利益就必然是单个利益,利益的统治必然表现为财产的统治。” 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形成资本剥削和资本压迫的根本原因,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资本永远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即便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受到协同消费理念的冲击,经济市场的商品和服务交易行为也依旧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买卖行为。协同共享利用绿色、环保、可持续的消费观念制造产权让渡假象,但是只要生产资料还归资本家占有,就无法改变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利益关系,广大劳动者始终被迫在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受到操纵。总之,协同共享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是更为巧妙地使资本家在新的社会发展条件下名正言顺地攫取剩余价值。
(二)协同共享没有改变资本主义雇佣关系
里夫金以“最后一个站着的工人”为例,指出边际成本接近于零的规模化生产方式不仅影响着社会生产,也影响着人类劳动。里夫金认为,技术的更新迭代是造成劳动工人失业的根本原因,当人工智能技术达到了超越工人劳动质量和劳动效率的时候,价值的创造过程必然会摒弃工人劳动而选择人工智能。里夫金的这一观点无疑挑战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尽管人工智能时代的显著变化之一是机器逐渐取代工人更多地参与劳动过程,但这并不代表工人完全消失或者工人对资本家从属的程度减弱,反而会因此形成一种更加隐性的强化雇佣关系。在极致生产力的催化下,社会发展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工人也逐渐从表面劳动转为背后劳动,从体力劳动转为脑力劳动,其中包括为了提升机器自动化技术水平而进行的计算机算法开发、平台运营及维护、语言翻译系统制作、自动化设备检修等工作。这些不仅对工人的知识技术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且还受制于大数据的监管和量化考核,工人的工作强度和工作质量被监视,他们只有不停地延长工作时间,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才能免去随时被淘汰的可能。
(三)协同共享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盈利逻辑
对利润的索取是资本主义的永恒追求,协同共享经济范式也是如此。协同共享经济范式利用合作、互利、共赢的商业理念宣称要实现对资本主义的颠覆和取代,带领人们走进没有商品交换的富裕可持续生活时代。里夫金的这一理念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追捧和深信不疑。但是,协同共享经济范式相较于传统资本主义来说,并没有改变资本家对利润的贪婪追求,而是在“共享”外衣的庇护下更加从容自若地实现着资本盈利,维护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协同共享经济范式自产生以来,就以分布式、扁平化为基础架构实现在物联网平台搭建的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一一对应的商业关系,这种商业关系淘汰了传统垂直整合模式下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复杂冗余的中间环节,使资本剥削和资本盈利变得更为直接和暴力。也就是说,协同共享经济范式仅在资本盈利的模式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和转型,但是其盈利的意图和剥削本质丝毫未变。更有甚者,协同共享经济范式用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作为支撑,形成了遍布世界的“生产—消费”网络,吸纳着数以百万计的产销者加入到用共享消费理念构建的资本剥削陷阱之中。可以见得,任何在资本逻辑基础上行使的新型消费理念,哪怕是“共享”价值观念的渗入,改变的也仅仅是资本的运作方式,而资本的剥削逻辑和剥削体系始终未变。
四、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必然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
我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协同共享,实现真正的共享必须脱离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前提下才能从根本上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虚伪与贪婪和对人性的压迫与肆虐。
(一)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国家经济基础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是区分社会制度属性的根本特征,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归劳动者共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既是资本主义剥削的起点,又是资本主义腐朽堕落的根源,同样也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斗争的依据。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桎梏。马克思立足唯物史观,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同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相兼容,强调共产党人要“消灭私有制”,资本主义也必然要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走向破灭。也就是说,私有制制造了尖锐的社会矛盾,意图改变这一现实,就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实现协同共享的根本途径,那些用共享概念来掩盖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做法,根本无法彻底铲除资本主义的剥削属性,也不会实现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
(二)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按资分配方式是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本原因,资本家凭借对资本所有权的掌控,肆意占有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造成劳动者始终处于低收入的相对贫困状态,一旦资本主义爆发经济危机,劳动者还将面临失业的风险,直接陷入绝对贫困化状态。资本主义分配制度与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如影随行,使无产阶级与资本家之间形成不断深化的矛盾。马克思站在广大贫苦的劳动人民立场上,批判了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非正义性,指出社会主义应当实行以等量劳动换取等量价值的按劳分配基本原则,并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任何一个劳动者,在作了相应的社会扣除之后,得到的正好等于他付出的,劳动者付出的就是他自己的个人劳动量。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具有平等性,获得生活资料的前提是参加社会劳动,生产者付出多少劳动就可以得到相应价值的权利,这一过程是用劳动来计量的。资本主义协同消费形成的资本剥削,将劳动者收入向资本阶层转移,根本无法平等地分配给劳动者,只有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原则才是劳动者劳动平等的价值体现,从而保证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这是劳动者自由平等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实现共享发展的必要前提。
(三)社会主义生产具有组织性和计划性
社会的进步发展离不开社会规模化生产,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成就,指出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巨大生产力,推动了社会发展,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始终避免不了由于市场机制的缺陷以及资本家的利益至上致使其根据市场价格的高低起伏,肆意扩大或缩小生产规模,以至于出现生产失衡现象以及生产和消费间的矛盾问题。假若资本主义仍旧维持当前这种无组织、无计划、无意识的生产行为,那么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但不会消失,反而每一次新的经济危机都会比前一次经济危机更加普遍、更加严重。要想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必须打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让规模化的社会大生产适应整个社会的需求,实现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调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生产、流通和交换环节的稳定有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四)社会主义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终极价值目标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核心命题,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取代资本主义的现实依据,就是因为社会主义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看作是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价值旨归。社会主义彻底改变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遭受不平等待遇的悲惨境况,聚焦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恩格斯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为所有人创建健康、有益的劳动环境,为所有人创建充足的物质保障,为所有人创建自由的劳动时间和广泛的生活空间。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普遍阶级对立,劳苦大众无法躲避残酷压迫。对此,马克思给予了深刻揭示,指出劳动工人不但被资本家剥夺了人身自由,连精神和道德的正常发展也因长期受到压制而处于迟钝萎靡状态,不得不面对过早逝世的威胁。针对这一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未来共产主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刻内涵,指出“代替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条件。”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并不是指某一个“单个个体”自由全面的发展,而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每个人在劳动实践层面、社会能力层面和个人道德层面都能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实现人类社会关于共享的真正价值与意义。
综上所述,协同共享经济范式就是资本主义最后的挣扎,无论资本主义自身呈现出何种外在形式,也不可能掩盖其资本属性的内核。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必然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社会在其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未发挥出来之前,是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因此,我们要坚定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信心,也要坚信这一过程虽然漫长但一定能够实现。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⑩ [美]杰里米·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6、2、XXV—XXVI、79、266、266—268、294、339、18、12—13、102—103页。
⑧⑨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9、579、30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412、414、36、422页。
李硕:《技术决定论浅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辛向阳:《“趋同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加]汤姆·斯利:《共享经济没有告诉你的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5、363页。
王峰明:《经济关系与分配正义——〈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的“权利—正义观”辨析》,《哲学研究》2019年第8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52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页。
作者简介:刘儒,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西安,710049;张艺伟,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710049。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