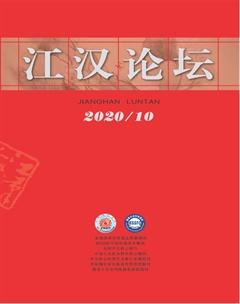国家认同何以形成?
曾水英 殷冬水
摘要:爱国主义是现代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政治资源。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其独特的“国家叙事”来构建国家身份,彰显国家精神,呈现国家形象,表达国家理想,论证国家对公民的意义和价值,建构公民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同。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叙事”中,国家首先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它界定公民身份,赋予公民归属感;提供秩序、自由与福利,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公民的幸福生活创造条件。同时,国家是一种神圣性的存在,其神圣性主要体现在国家创造了过去和现在的荣耀,并将在未来续写辉煌,公民为生活在其中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正是通过“国家叙事”,爱国主义教育建构、巩固和强化了公民对国家的认同。
关键词:现代国家;国家认同;爱国主义;国家叙事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吉林省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建构的有效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9B10)
中图分类号:D032;D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10-0046-07
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维度,强化公民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同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现代国家无不动用其拥有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意识形态资源、组织资源、技术资源来建构和巩固国家认同,通过国家认同来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有序,降低国家分裂的风险,提升国家的内聚力,“将一个政治消极、经济分裂的族裔共同体转变成了一个更具凝聚力、经济上更集中、成员更积极的政治共同体”①。实践表明,国家认同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国家主动建构的产物。在国家认同建构的过程中,国家发挥了关键作用。一般而言,现代国家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政治实体,其内部社会分化程度高、族群多样、人口高速流动,与其他主权国家保持信息、资源、技术等方面的交换。如何将现代国家打造成一个具有内聚力的政治共同体,如何通过政治社会化的方式实现异质人口的同质化,如何充分发挥公共教育体系的国家认同建构功能,降低地方主义、多元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等力量对国家统一的威胁,是现代国家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
众所周知,爱国主义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②。在政治生活中,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公民的“国家忠诚感、对国家象征的热爱、对国家优越性的特殊信仰”③。爱国主义是一种政治主张,这种政治主张倡导公民对其生活的国家持续的忠诚和对祖国持久的热爱;爱国主义是一种政治思想,这种政治思想倡导国家的神圣性、优先性、不可替代性;爱国主义是一种政治实践行为,公民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热爱其生活的国家,主要体现在公民的行为上,主要体现在公民对国家履行其义务的行动上,比如纳税、参军、捍卫国家利益、为国家而牺牲等等。
爱国主义是现代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一种重要政治资源,现代国家无一例外地通过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来“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④,建构公民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同。比如,在法国,爱国主义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爱国主义教育侧重对历史文化的珍惜和爱护。在美国,国家象征、政治仪式等在国家认同建构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小学每天都要例行开课仪式,学生在教师带领下面向国旗唱国歌,宣誓效忠于国旗和国旗所代表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学校的走廊和教室里,很容易看到美国国旗、美国地图,以及美国杰出人物和总统的画像。在波兰,学校十分重视利用各种纪念性的建筑物和纪念碑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等。
在现代国家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中,无不建构起一整套有关现代国家的“国家叙事”,依赖“国家叙事”来构建国家身份,彰显国家精神,呈现国家形象,表达国家理想,论证国家对公民的意义和价值,“鼓励公民支持政府政策”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叙事与‘政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产生如此广泛而密切的联系”⑥。
虽然爱国主义在现代国家认同建构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发现,目前学界对这种作用的学术研究尚显不足。现有的研究要么对爱国主义进行深入研究,要么集中研究国家认同,较少有研究将二者结合起来。在仅有的爱国主义与国家认同结合研究的文献中,有的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国家认同建构的意义,提出应通过包括爱国主义在内的政治文化的建设来强化国家认同⑦;有的梳理了社群主义的国家认同观,指出国家认同是爱国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是培养理性爱国者的必由之路⑧;有的发現在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强化了公民和国家之间的联系⑨;等等。
“叙事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用口语、书面语或辅之态势语、音像、图片等综合手段表述一件或一系列真实或虚构事件的行为过程”⑩。本文要讨论的是,在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爱国主义教育建构了什么样的“国家叙事”,如何依赖这套“国家叙事”来讲述国家的故事,塑造国家的记忆,增强公民对国家的归属感、依赖感、自豪感,培育公民对国家的认同与忠诚。
一、提供归属感的国家
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叙事”中,国家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独特存在,是人类发明出来的有效组织公共生活的一种制度安排。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国家存在的首要价值在于国家赋予我们每个人公民身份,提供了我们每个人归属的场域,确定了我们在世界之中的行动方向,使个人身份得到空间化的建构。依赖这种建构,我们每个人知道我们是哪个国家的公民,享受这个国家的保护,并履行相应的义务。与此同时,依赖这种建构,我们每个人也知道了自己不是哪些国家的公民,不需要对这些国家保持忠诚和履行义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对国家认同建构而言,爱国主义教育“国家叙事”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界定了公民的国家归属,赋予公民国家归属感。
众所周知,歌曲是现代国家实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重要媒介。在我国,流行着大量经久不衰的爱国主义歌曲。这些爱国主义歌曲界定了“中国”的国家身份,阐释了“中国人”国民身份的政治经济文化蕴涵。例如,《保卫黄河》用敌我政治观书写历史,将侵略者他者化,“敌人”成为建构中国国家认同的一种重要资源。《歌唱祖国》运用“五星红旗”、“毛泽东”等国家象征来象征国家,将国家身份化、符号化。《我的祖国》通过“美丽的祖国”、“英雄的祖国”、“强大的祖国”来呈现国家的伟大形象,将伟大的祖国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东方之珠》唤起了大国公民的优越感和自豪感,塑造了香港人的国家归属感。《我的中国心》通过“长江”、“长城”、“黄山”、“黄河”等地理文化符号具象化了祖国,建构了中国的“国家身份”。《龙的传人》诉诸历史资源,通过回溯历史源头来建构中国的“国家身份”。《中国人》通过“中国”与“世界”两个概念,在“世界”中定位了“中国”。
对我们每个人而言,身份归属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资源,这种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身份归属是人类社会组织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人类社会有效组织的基础。唯有确定不同的人的身份归属,将不同的人纳入不同的组织之中,人类社会的组织才能建立起来,并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奋斗。其次,身份归属是人类社会秩序建构的基础。人类社会唯有解决了个人身份归属问题,才能清晰地确定组织的边界,界定各种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和转移权。如果不能有效解决个人身份归属问题,稀缺资源的分配和产权的界定就难以推进,人类就会陷入夺取稀缺资源的无休止的纷争之中。最后,身份归属可为我们每个人的行动提供方向感。人是一种社会存在,任何人都需要依赖他人而生存,通过与他人合作来为幸福生活创造条件。界定了身份归属,每个人才能依赖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合作机制来发展自身的才能,实现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并为他人的幸福生活而努力工作。有了身份感,我们每个人才知道与谁合作,享有哪些权利,承担何种义务,“尝试在不同的情况下决定什么是好的或有价值的,或者什么应当做,或者我应赞同或反对什么”。
实践表明,人类社会存在诸多机制,提供了诸多身份来解决我们个人的身份归属问题。家庭、宗教团体、社会组织等,都是解决我们每个人身份归属问题的重要方式。对这些不同组织,我们保持了不同的忠诚。“首先靠近她的是忠诚于家庭的圈子,更远的是忠诚于特殊群体的圈子,二者之间的某个地方则是爱国式的忠诚的国家圈子。”
与这些解决个人归属问题的方式不同,爱国主义以公民身份为基础,倡导用国家这种政治共同体的方式来解决个人归属问题,并强调了国家这种解决方式存在的正当性、重要性和优先性。爱国主义捍卫国家存在的正当性,并不像无政府主义那样通过解构国家的方式来解决人类公共生活中的难题,尤其是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冲突问题。爱国主义并不认为国家是一种“恶”,也不认为国家是一种“不必要的恶”,恰恰相反,爱国主义认为国家是人类文明生活的必要条件,是衡量人类文明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国家并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存在,而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存在。對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必然要生活在民族国家之中,是民族国家的公民,受到民族国家的保护。与个人利益相比,爱国主义强调国家利益的优先性。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服从国家利益的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归属于不同的团体,对不同的团体保持忠诚。然而,在所有这些忠诚对象中,对国家的忠诚具有至高无上的位置。当不同忠诚发生冲突时,其他任何形式的忠诚都应让位于对国家的忠诚。这是因为,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为家庭、俱乐部、宗教团体等共同体提供了保护。如果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崩溃瓦解,其他共同体就难以生存。如果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受到外部力量的奴役,那么,生活于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中的每个人的自由就会荡然无存。因而,相对于个人善而言,国家整体的善无疑具有优先性。
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爱国主义教育“国家叙事”的首要价值在于它解决了我们每个人的归属感问题,将我们每个人与特定的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叙事”之所以能解决我们每个人的归属感问题,首先是因为它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建立起了国与国之间的界限感。这里的界限感既可能是物理空间意义上的,也可能是心理象征意义上的。正是这种界限感,为公民国家归属感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其次,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叙事”还要建构国家之间的差异感,这种差异感是公民国家归属感形成的重要条件。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叙事”中,国家之间不仅在空间上是隔离的,彼此之间界限分明,而且在历史传统、政治遗产、人口规模结构、资源占有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充满了差异性。对国与国之间差异的认识,为公民爱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别的国家)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最后,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叙事”还要在公民与国家之间建立起制度化的联系,建构公民与特定民族国家的连接感,并依赖这种连接感来建立公民对国家的归属感。
爱国主义教育强调国家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存在,国家赋予个人身份感。国家是由公民构成的,是自由平等的公民组成的合作体系与互惠网络。正是有边界的国家赋予我们每个人公民身份,通过国家的努力,公民身份具有了实质内容。有了公民身份,我们每个人才能协调好我们与其他国家国民之间的关系。拥有了公民身份,我们每个人才知道自己在自己生活的国家处于何种位置,才能有效地协调和平衡包括公民身份在内的不同身份之间的关系。拥有了公民身份,国家才能对社会进行有效治理,不断提升治理社会的能力,并为社会服务。有了公民身份,公民才能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发展彼此之间的友谊。因而,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公民权是许多归属形式中的一种。经常地,它意味着归属于民族国家。” “我们走到一起,形成一个共同体,目的是为了应付我们独自无法应付的困难和危险。” 国家存在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解决了我们的归属问题,获得了国籍和公民身份就为获得其他社会善提供了先决条件。从正向角度看,获得了国籍,我们就属于某个民族国家,受到这个国家的保护。从负向角度看,“如果没有祖国,就意味着丧失了一切。” 丧失了国籍,我们就可能变成不受保护的人,生存就可能会遭受威胁,身份的认同建构可能就会变得困难。
二、形成依存感的国家
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叙事”中,“祖国是‘人类幸福的首要与先决条件。” “政府是人类智慧的发明,用于满足人类的需求。” 公民应热爱自己生活的国家,认同自己生活的国家,这不仅是因为国家界定和确认了公民的身份,回答了“我们是谁”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且也是因为国家为公民身份的实现创造了条件,为公民的幸福生活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叙事”充满了对国家形象的展示和国民美好生活的赞美。例如,在《我的祖国》中,祖国有辽阔的土地,“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儿心胸多宽广”,“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眼光”,“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在《我们的田野》中,祖国辽阔、富庶、欣欣向荣,有“美丽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平静的湖中,开满了荷花,金色的鲤鱼,长得多么的肥大”。在《翻身农奴把歌唱》中,“太阳啊霞光万丈,雄鹰啊展翅飞翔,高原春光无限好”,“雪山啊闪银光,雅鲁藏布江翻波浪,驱散乌云见太阳”,“幸福的歌声传四方”。在《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中,生活在祖国中的每个人“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在《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冬麦,一片高粱,十里荷塘,十里果香。”在《大中国》中,“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还有珠穆朗玛峰,是最高山坡。”
从工具论的角度看,公民认同国家,主要是因为国家满足了公民的公共需要。“我们欠她的,所以我们对国家有道德义务。” 唯有国家为公民的幸福生活提供了秩序、自由和福利,国家才能获得公民内心的认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关系。公民忠诚于国家,为国家履行义务;作为回报,国家为公民的幸福生活提供坚实的保障。“如果国家被治理得很好,善的人们将理解,他们的善依赖于国家安全,进而全心全意地热爱祖国。”
首先,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叙事”中,国家是一种强制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建构公共秩序,为公民过上有秩序的生活提供了保障。
过上有序生活,是我们每个人的期待;享受公共安全,是我们每个人的追求。没有秩序,没有安全,要过上幸福生活就会变成一种奢望。实践表明,人类对秩序和安全有着普遍的追求。秩序和安全是重要的,但秩序和安全并不会自然形成。伦理学家强调了伦理道德对于社会秩序建构的意义,宗教学家论证了宗教信仰对于社会秩序建构的价值,经济学家强调了经济理性对于社会秩序形成的重要作用。然而,没有强有力的国家,人类社会就难以建立起一种稳定的、持续的和节约的秩序。在人的理性有限和资源匮乏的条件下,人类社会需要国家这种强制性的力量来建构秩序,为人们有序生活提供保障。作为一种强制性力量,国家以公共暴力为基础,以暴力威胁为运作逻辑,依赖暴力威胁来建构秩序。在建构秩序的过程中,国家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国家的运行以暴力为基础,而暴力对人的生命构成了威胁,国家成为人类建构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国家的暴力威胁之所以是有效的,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有死亡意识,都对死亡充满了恐惧。生命是有限的,生命只有一次,死亡是一件令人可怕的事情。正因为有了死亡意识和对死亡的恐惧,国家这只“利维坦”才变得不可替代。倘若没有国家这只“利维坦”,人类社会将如同霍布斯所预测的那样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
其次,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叙事”中,“公民的义务源于他因拥有祖国而拥有好的生活,他热爱祖国是因为那是它可以享受自由的地方。”
国家不仅要建构秩序,而且还应保障公民的权利。建构秩序是国家不容忽视的一项价值,对人类过上文明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建构秩序本身并不能涵盖国家对人类文明社会贡献的所有内容。对文明社会而言,国家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要建构一种“自由”的秩序,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人要过上幸福生活,有赖于各种权利的实现。“随着直接统治的深入,个人越来越依赖中央政府所提供的人身与财产保护、解决纠纷、提供教育和获取其他促进个人福利的公共产品。” 国家所要保护的,不仅包括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权利,也包括文化权利。公民要过上幸福生活,必须以其享有的政治权利为基础。拥有了政治权利,公民才有机会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发出他们的声音,贡献他们的智慧,捍卫其自身和团体的利益。与政治权利一样,经济权利也是至关重要的,是公民过上有尊严生活的重要条件。经济权利既包括劳动权、休息权、财产所有权,也包括生活保障权、物质帮助权等。对于公民而言,文化权利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人是一种文化存在,理应享受文化权利。这些文化权利既包括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也包括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享受个人进行文化艺术创造所产生的精神和物质利益的权利。国家是公民权利的保护者,要为这些权利的实现提供充分的物质保障,通过制定法律来实现权利,为权利受到侵犯的公民提供救济。在其权力没有受到约束的条件下,国家可能会异化为权利的侵犯者。但在国家权力被驯服的条件下,国家是保护公民权利的中坚力量。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叙事”,正是通过呈现国家作为公民权利的保护者这一形象,在公民内心建构起对国家的认同。
再次,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叙事”中,国家还有一项不容忽视的功能,那就是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为社会的富庶繁荣和公平正义承担责任。
国家不仅有政治职能,而且也有经济职能。国家有责任推动经济的发展,促进市场的繁荣,为公民的幸福生活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国家也有责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人类对社会的公平正义有着不懈的追求,公平正义对人类社会而言具有重要价值。对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而言,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社会的不公是诱发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社会团结的支撑力量,没有社会的公平正义,国家就可能面临分裂的危险。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国家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的不公将会使国家的持续发展失去应有的动力。虽然人类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是普遍的、迫切的、真诚的,但公平正义并不会自动实现。公平正义的实现需要国家承担责任。国家是公平正义的守护者,是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也是社会不公的矫正力量。国家是公共资源的分配者,“政治权力体现在国家中是维护、修订和捍卫所有分配领域的边界的必要工具”,而公共资源的分配状态是一个国家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国家掌握着税收、财政等再分配工具,通过运用这些工具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并不是一次完成的,需要持续努力,不断改进。作为组织化的公共权力,国家的存在为人类不断努力去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国家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保护神,生活在国家之中的每个人,都应该对国家保持尊敬。
三、滋生自豪感的国家
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叙事”中,国家不单单是一种满足人们世俗欲望的工具性的存在,国家还是一种让人产生自豪感的神圣的存在。单单从工具性的角度来理解和认识国家,无疑会降低国家的神圣性,进而会弱化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倘若国家只是满足我们每个人欲望、利益和需求的工具,只有国家满足了我们每个人的欲望、利益和需求,国家认同才会得到维系,那么,一旦国家无法满足我们每个人的欲望、利益和需求,國家认同就会解体。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叙事”中,虽然国家认同建构需要对国家进行工具论意义的理解,但这种理解是不完全的。建立在工具论意义上的国家认同必然也是脆弱的,因而必须超越工具论意义上的国家认同建构方式,着力建构公民对其生活的国家的自豪感。
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叙事”中,国家是一种神圣的存在。作为政治共同体,国家有着神圣的起源,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丰富的神话故事。作为政治共同体,国家是一个神圣的空间。所有的公民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对这一神圣空间之中的存在物充满了情感。作为政治共同体,国家也诞生于神圣的时间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爱国主义歌曲叙述了国家的神圣起源。例如,《中国人》从国家的神圣起源建构国家的同一性,并依赖这种同一性来建构国家认同。“五千年的风和雨啊,藏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八千里山川河岳,像是一首歌。不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經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爱国主义歌曲讲述了国家空间的神圣性。例如,在《边疆处处赛江南》中,边疆“朝霞染湖水,雪山倒影映蓝天”,“黄昏烟波里,战士归来鱼满船”,“牛羊肥来瓜果鲜,红花如火遍草原”。在《边疆的泉水清又纯》中,“清清泉水流不尽”,“锦绣河山万年春”。时间是国家认同建构的一个重要因素,爱国主义歌曲表达了国家诞生时间的神圣性。例如,在《歌唱祖国》中,“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在《我的祖国》中,“为了开辟新天地,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
实践表明,所有的国家都建构了公民身份,也都在一定程度上都满足了公民的欲望,实现了公民的利益,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国家都会得到公民内心的认同,也不意味着所有的国家都会得到公民同等程度的认同。实际上,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叙事”中,国家还是一种神圣的存在。公民对国家的认同,不仅来源于国家满足了公民的利益诉求,而且也来源于公民对国家的神圣性的体验。国家的神圣性主要体现在国家创造了过去和现在的荣耀,并将在未来续写辉煌。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我们每个人都会相信,“自己的国家和统治者无论是往昔还是现在都是光荣的,并将会带领人们走向光明的未来。” 正是国家创造了荣耀,从而为公民认同国家提供了持续的精神力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对祖国的热爱是一种道德的、政治的热爱,浓缩了对正义、自由与荣誉的热爱。”
首先,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叙事”中,国家是一种神圣的存在,在逝去的过去创造了荣耀。
众所周知,“现在的政治是过去政治的产物”。历史是爱国主义教育“国家叙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历史教育是塑造公民国家认同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每个国家都会“重新发现往昔时代的英雄主义、先祖文明的荣耀,还有他们伟大的民族英雄的光辉事迹,并常常对其进行夸大”。国家之所以让人产生认同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有着辉煌的过去。正因为国家有着辉煌的过去,国家才具有神圣性。也正是因为有了“对祖国悠久历史、深厚文化的理解和接受”,公民的爱国主义情感才能得到培育和发展。一般而言,爱国主义教育会围绕国家的荣耀展开有关国家过去的“国家叙事”。例如,在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中,必须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让公民认识到,“中华民族在创造灿烂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其内容博大精深,不仅包括了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成就,而且蕴含着崇高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和优良道德;不仅孕育了无数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艺家、科学家、教育家、军事家,而且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史迹、经典著作。” 这些“国家叙事”要呈现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在哪些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些领域既可能包括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也可能包括文化领域、科学技术领域。与此同时,要呈现这些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哪些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居于领先地位,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影响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提高了人类社会整体的生活质量。更为重要的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叙事”要呈现创造国家荣耀的重要人物,勾勒出清晰的英雄图谱,通过这些人物和英雄将国家的荣耀具象化、生活化。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公民,将通过这些人物和英雄的生平、事迹等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国家的荣耀。在呈现国家过去的荣耀的过程中,国家的伟大来自于其过去创造的诸多辉煌成就,也来自创造这些辉煌成就的伟大人物和人民,更与国家的行为密不可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赞美国家的辉煌成就,赞美创造这些辉煌成就的伟大人物和人民,往往与赞美国家政权之间具有高度的关联性。赞美的一个后果是培养了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提升了国家的认同度。
其次,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叙事”中,国家在当下续写了过去的辉煌,与过去相比,取得了更为伟大的成就。
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叙事”不仅关注国家的过去,而且也关注国家的现在。国家的神圣性不仅来源于国家过去创造了诸多荣耀,而且也来源于国家当下创造了诸多崭新的辉煌。从时间维度看,国家认同主要解决的是当下政治实践中的问题,关注的是当下公民对国家的认同,研究的是当下公民对其生活的国家的内心感受。正是国家认同问题的当下性,使得有关国家的“当下叙事”在国家认同建构中居于中心位置。国家认同建构依赖过去,也依赖现在。在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中,必须做到“用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说话,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说话,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说话,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说话,在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的对比中,引导人们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倍加珍惜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需要强调的是,在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仅仅呈现国家创造辉煌的意愿和能力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呈现诸多当下的业绩来证明国家确实创造了辉煌,证明当下要好于过去,证明祖国的生活要好于其他国家的生活。在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当下的辉煌会对国家认同建构形成支持,与之相对,当下治理的失败则可能会对国家认同建构构成约束和限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国家治理的有效性支撑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构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国家叙事”的核心内容。
再次,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叙事”中,还需要塑造一种对国家在未来续写辉煌的信心。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叙事”离不开对国家过去的赞美、对国家现状的褒扬,也离不开对国家美好未来的想象。
虽然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叙事”中当下性处于核心地位,但仅仅讲述当下的故事是不够的。我们每个人往往生活在过去,由过去的集体记忆所塑造,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现在。与此同时,我们不能止步于现在,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还生活于未来之中。正是未来赋予我们每个人方向感和改善现在的紧迫感。也正是未来的存在,使现在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现在影响着未来,我们这一代人对未来诸多代人承担着责任。因而,有关国家的“未来叙事”,是爱国主义教育中“国家叙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有关国家的“未来叙事”中,国家的未来是美好的,有关国家发展的未来蓝图是引人入胜且鼓舞人心的。因而,爱国主义主义教育总存在着对国家未来的承诺与期许,总会有国家未来的蓝图叙事,并依赖这种叙事来动员人民、组织行动,积累集体行动的力量,以此为基础建构国家认同。国家之所以应该被认同,不仅是因为当下的国家提供了幸福生活的条件,而且也因为未来的国家仍将为幸福生活创造条件。正是因为国家的存在,人类幸福生活能得到不断延续,人类未来生活才会变得更加美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国家值得公民信任、忠诚。
四、结语
毋庸置疑,“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是现代国家认同建构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一套有关国家的“国家叙事”,在规范和经验两个层面论证了国家的工具价值和国家的神圣本性,并依赖这些论证建构起公民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叙事”只包括这些内容,也并不意味着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叙事”在建构国家认同中都能获得成功,更不意味着爱国主义教育对国家只能一味赞美而缺乏理性反思。实际上,爱国主义强调的是“政治权力(而非生产方式)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但无疑也是最危险的善”。“对祖国的热爱可以是慷慨、同情和明智的,也可以是排他、封闭和盲目的”。在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过程中,有关国家的“国家叙事”可能是不完整的,面对这些“国家叙事”,不同公民具有不同程度的独立判断能力。在既定条件下,国家认同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取得成功,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来检验和评判。
注释:
① [英]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131、159页。
②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3日,第2版。
③ Leonie Huddy and Nadia Khatib, American Patriot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7, 51(1), p.63.
④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人民日报》2019年11月13日,第6版。
⑤ Stephen Nathanson, In Defense of “Moderate Patriotism”, Ethics, 1989, 99(3), p.536.
⑥ 范永康:《走向叙事政治学——后现代叙事理论的政治转向研究》,《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9期。
⑦ 刘晨光:《爱国主义、国家认同与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⑧ 闫闯、郑航:《社群主义的国家认同与爱国主义教育》,《教育学报》2015年第6期。
⑨ Stanley A. Renshon, Dual Citizenship and American Democracy: Patriotism, National Attachment, and National Identity,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2004, 21(1), pp.100-120.
⑩ 祝克懿:《“叙事”概念的现代意义》,《复旦学报》(社會科学版)2007年第4期。
[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Simon Keller, Patriotism as Bad Faith, Ethics,2005, 115(3), p.566.
[美]卡洛琳·加拉尔等:《政治地理学核心概念》,王爱松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45页。
[美]迈克尔·沃尔泽:《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褚松燕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99、3、35、17页。
[美]毛里齐奥·维罗里:《关于爱国: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潘亚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25、8、62、28、50、3页。
[美]迈克尔·赫克特:《遏制民族主义》,韩召颖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
孙银光:《制造群众: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逻辑》,《中国教育学刊》2015年第1期。
《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人民教育》1994年第10期。
作者简介:曾水英,长春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吉林长春,130012;殷冬水,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长春,130012。
(责任编辑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