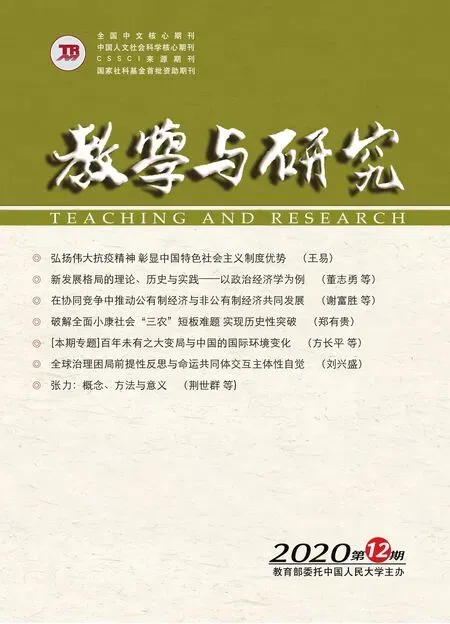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及中国的参与路径 *
刘 波
进入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更深。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领导人针对世界及我国自身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正在全面引领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性调整。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格局深度演变,中美两大国之间博弈日趋白热化,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更是增加世界的动荡性、复杂性和碎片性,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与高质量参与全球治理“融合发展”,探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道路”,实现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设定目标,既是当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关键方向,也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催生全球治理新变革
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以一系列国际制度、规则、规范为基础,解决全球问题的国际合作过程,(1)张宇燕、任琳:《全球治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3期。该理论最早是由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并倡导,经过30多年发展演变,现已成为国际关系领域重要的研究范式。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发表研究报告,认为全球治理是国内治理的延伸与再拓展,“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个人的——处理其共同事务的国际性总和。”(2)[瑞典]英瓦尔·卡尔松、什里达特·兰法尔:《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赵仲强、李正凌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第2页。全球治理委员会呼吁世界各国参与全球治理,在负责、透明、合作等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磋商,将参与者集体的意愿转化为全球各国通行的法律制度,推动全球问题的解决。可见,全球治理既作为一种调节利益冲突的规则机制,同时也成为国际社会协调解决全球问题的一项集体性实践活动。
2018年,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28页。在这一历史性大变局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整体实力呈相对下降趋势,受困于“能力不足”,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在逐渐消退,无法提供有效的全球公共物品,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正在陷入一场深刻的危机”,(4)常健:《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弱化了吗》,《人民论坛》2018年第16期。“美国领导”正在被“美国优先”“美国退群”所取代。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实力不断增加,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意愿不断增强。“百年变局中最为关键的变量在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5)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5期。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是当前国际体系最大的特征。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经济总量约为全球的60%,发展中国家约占40%,但发达经济体增速只有1.7%,发展中经济体增速为3.7%,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赶超趋势十分明显。国际体系力量对比变化,对全球治理产生深刻的影响,全球治理的领导力首先取决于国家实力。约瑟夫·奈在2017年提出,“在全球霸权国家既无意愿、又无能力提供必要的全球公共产品,而新兴大国也无力提供,那么会造成全球治理领域出现领导力的真空,使全球治理体系处于混乱状态”。(6)Joseph S. Nye, “The Kindleberger Trap”, Project Syndicate, January 9,2017,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kindleberger-trap.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并没有使得全球治理在公正合理机制建设方面同步更新,多领域全球治理框架存在代表性不足、合法性不足、有效性不足等问题。例如,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社会近百年来遭遇的最严重公共危机事件,见证了美国全球治理领导力的直线衰落,只顾“自扫门前雪”,国际抗疫团结面临撕裂的风险,反而是中国承担起全球抗疫联合阵线的团结人角色,持续向疫情严重的国家和地区捐助了一批又一批防疫物资,派去医疗专家组,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意识和国际联合抗疫的坚定信念。“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国际领导力测试赛中‘挂科’了,将不再被视为国际体系的领导者。”(7)钟声:《多边合作的绊脚石》,《人民日报》2020年7月3日。不难看出,目前国际格局正“处于旧的治理体系加速演变、新的治理体系孕育形成的关键当口”,国际力量从“东升西降”到“东西平衡”,催生全球治理多维度变革。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面临新挑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变是唯一的不变。在解决全球问题过程中,全球治理与全球失效治理共同存在,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衰退,全球化进程遭遇挫折,美国单边主义倾向愈发明显,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困难,全球治理面临理念上的矛盾性、规则上的合法性、领域上的复杂性等难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十年前,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就断言,21世纪的多边主义可能会比过去更具流动性和更混乱。(8)Richard Haass, “The Case for Messy Multilateralism”,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5, 2010.“国际社会正面临全球治理的僵局,国际关系体系中的空白没有得到填补”。(9)Thomas Hale, David Held and Kevin Young, Gridlock: Why Global Cooperation Is Failing When We Need It Most, Polity Press, 2013.
(一)全球治理体系松动
随着美欧日等原先世界领导力量衰弱,全球治理依凭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新兴国家为世界经济提供大量公共产品,但全球治理的话语权不足,这种张力日渐增大,全球治理体系框架出现松动迹象,进入治理“碎片化”阶段。
1.大国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
稳定的大国关系,是维系国际秩序的基础,更是全球治理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主要大国发展态势和实力对比显著变化,加剧新一轮大国博弈”。(10)王鸿刚:《中国如何认识与应对新一轮大国博弈》,《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年第5期。与历史上权力转移不同的是,新一轮大国权力博弈,不再是既有“中心国家”向“新崛起中心国家”转移,而是更加“两极多强”相对均匀的权力分配,塑造成去中心化的网络结构。中、美、俄、欧、日、印等大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中美在台湾、南海问题上的对抗,中印边界危机,俄美欧在乌克兰议题上的争执,日俄北方四岛争执,中日钓鱼岛争端等,地缘博弈色彩增强。在地缘政治竞争大背景下,大国相互渗透影响力,相对收益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动力不足。大国是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也是世界秩序的塑造者,在面对世界重大问题时,大国博弈加剧,必然导致全球治理出现松动和停滞不前。
2.国际社会信任受到侵蚀。
信任是国际关系最好的黏合剂,也是推动全球治理的精神动力。国家间本可通过多次信号传递和反馈进行重复博弈,表达战略意图,形成积极预期,实现相互信任。然而,近年来大国之间的误解、猜忌、隔阂、忌惮有所增加,不信任感造成全球治理国际合作的“信任赤字”。且在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中,不信任感随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引发一些国家国际政治战略研判的错误知觉,使得国际关系中的信任赤字结构化。一些国家为获得所谓的绝对安全,强化具有联盟性质的排他性区域组织,更进一步导致国际社会的信任受到侵蚀。在国际结构稳定的情势下,主要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变化幅度较小,理性行为体对安全状态有科学判断,当前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实力对比正发生巨大变化,国际行为体对行动目标和范畴的认知不确定性增加,彼此行为和意图的信任与理解困难显著增加。
3.逆全球化等保护主义增强。
逆全球化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孕育兴起,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增长受到巨大冲击,逆全球化再次兴起,英国“脱欧”、特朗普“美国优先”大打贸易战等各种逆全球化乱象丛生。逆全球化主要是由于原先发达国家全球经济利益大“蛋糕”被新兴发展中国家分割分享,“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国际分工体系发生新变化,导致传统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被打破”。(11)毛蕴诗、王婕、郑奇志:《重构全球价值链:中国管理研究的前沿领域——基于SSCI和CSSCI (2002—2015年)的文献研究》,《学术研究》2015年第11期。由于收入不平等加剧,失业率提高,发达国家的选民对传统精英执政的质疑普遍增加,民粹主义和政客上台,采取贸易制裁、提高关税、加强外资投资项目审查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导致逆全球化进一步增强。美国无视自己以往在全球治理所攫取的“存量利益”,重点关注其他国家的相对“增量利益”,对全球治理的规则不满情绪日渐高涨,滥用“301”条款,要求WTO改革现有规则,甚至“另起炉灶”,重新构建全球投资贸易规则,导致现行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崩溃的可能。从本质意义上来看,美国等西方国家并不是要彻底抛弃全球化,而是要塑造符合本国利益的全球化。
(二)全球治理赤字扩大
面对全球热点问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非传统安全带来的挑战,大国合作的意愿受到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影响日渐衰退,全球治理体系以及多边机制受到冲击,治理赤字明显扩大。
1.新冠肺炎疫情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存在规则真空。
二战后形成的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框架,越来越无法适应“突发性”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危机监测、预防和治理的需求。特别是在“美国优先”旗帜下的美国特朗普政府,扛起民粹主义大旗,这与全球治理所需要的多边主义南辕北辙,不仅对现行治理机制造成冲击,还导致在新冠肺炎疫情、难民危机、基因编辑技术、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新兴非传统安全领域日新月异的情势下,新生事物处于“治理盲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与不良的全球治理密不可分。”(12)Nikola Popovic,“The State and Globalization during Covid-19”,Modern Diplomacy,April 13,2020.新兴国家的全球治理能力在逐步形成,但面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可以借鉴的应对方案有限,在给全球治理带来新的希望的同时,日益面临全球治理能力不足与全球领导力缺失的尴尬。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新生事物带来的挑战,全球治理体系里面还没有建立起成熟的规则和标准,存在巨大的规则真空。此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规则真空也意味着为参与主体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同时也可能导致分摊公共产品的成本与收益不明确,一些国家倾向于采取“搭便车”的策略。
2.制度非中性“外溢”藩篱。
制度是规则体系,同一制度对不同的人或群体意味着不同的利益趋向。国际制度与全球治理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由于制度的非中性特征,“全球治理所遵循的各种机制给不同国家带来的收益或损失是不相同的,因此给全球治理打上非中性的烙印。”(13)徐秀军:《制度非中性与金砖国家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在网络、太空等全球治理赤字领域,发达国家在科技研发、融资支持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先天优势,在全球治理新领域容易再次成为新规则的主导者,享受制度非中性的先行优势”。(14)任琳:《中国全球治理观:时代背景与挑战》,《当代世界》2018年第4期。此外,制度非中性易引发“负面外溢效应”,参与治理、分摊公共产品的成本与收益模糊,引发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全球治理停滞不前甚至偏离正常轨道。时代与国际格局的变化,导致原先全球治理确立的概念已发生变化,内涵已不能适应当下的发展情境,需要集体探讨,达成共识。例如,市场经济竞争中性的规则概念,原先就是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情况,确保公共企业与私营企业平等竞争而提出,后逐步演变为国际贸易通行规则。然而,各国国情的不同,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并未有效参与竞争中性相关概念的规则讨论,竞争中性的理解存在偏差,存在升级真空。
3.治理“异化”效应凸显。
全球治理是一个高度复合体系和多元体系,各种非国家行为主体参与其中。全球治理需要所有参与者遵守共同规则和制度,在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时,实现利益共享责任共担。但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民众民粹主义或沙文主义上升,引发社会抗争,抗争的主题充满对全球化的发泄,对全球治理的共同集体失望。“全世界这种有毒的民族主义都试图利用由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结果所创造的政治空间。”(15)Deepak Nayyarm,“Failing Health of Globalization:Covid-19 Blow to a Stressed Order”,MINT,March 12, 2020.民粹主义情绪高涨,为全球经济合作设置障碍,削弱了政府承担国际责任的能力,在民众“要回国家主权”的口号下,发达国家利用现有全球治理机制,谋求利益补偿,遏制新兴国家,严重侵蚀全球治理的有效性, 治理异化突显,治理成本增加。伴随西方经济的长期性衰落,引发广泛的社会危机,反对全球化的人群从之前的社会底层和边缘人扩大到今天的精英阶层。尤其是在大选年,国内政治和全球治理之间的博弈明显。候选人为赢得选民的支持,不惜煽动民众情绪,将单边主义凌驾于多边主义之上,把国内经济匮乏归结于全球化以及全球治理,使得全球治理在发达国家被“污名化”,其改革面临“工具化”风险。
(三)全球治理多边合作机制弱化
全球治理得以有效实现主要是依赖于充分的国际合作,但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在发展目标的认知上缺乏足够共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全球治理机制,加强国际协调,促进共同利益,与现行国际组织主导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多边合作机制在重大问题上,越来越难以形成治理合力。
1.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权威效能减弱。
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国际体系中,联合国发挥的作用有限,使得一些主权国家对多边机构的治理能力丧失信心。联合国作为二战后维护世界和平的核心治理机制,是现存全球治理的重要支柱,但当前联合国的权威性和参与全球治理的效能有所减弱,机构臃肿,大国难协调等因素,致使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的作用减弱,治理失效的案例愈来愈多。由于联合国的核心治理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导致全球治理成果分配存在不合理、不平衡的问题,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压力,难以形成代际共享的治理成果机制。其他国际组织,如G20、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解决全球问题时,尤其是面对全球性的突发应急难题时,也表现得越来越无力。
2.美国等离场退群增加集体行动的难度。
世界卫生、气候变化、国际人权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等全球问题需要大国协商一致。大国尤其主导国美国的退出行为,严重破坏了契约精神,更破坏了全球治理的合作机制。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自认为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成本收益不对称,相继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多边机制。美国离场“退群”增加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在诸多议题领域,增加了国际社会集体行动的难度。例如,由于美国的不配合,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很难落地,导致2019年12月其上诉机构被迫停摆。2020年7月,特朗普政府向联合国正式递交申请,宣布美国将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这对亟需团结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社会是一个重大的伤害,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3.全球治理评估体系缺位。
科学的评估体系是推动全球治理不断调适发展的动力机制。尽管国际社会上关于治理的评估体系种类繁杂,例如世界治理指标、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评估体系等,这些评估体系主要由美欧等发达国家研制,很多内容基于西方的制度理念,对全球治理的分析和反馈,没有吸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内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诉求。全球治理评估体系还包括评估主体、具体对象、统计工具、指标体系等,这些要素既涵盖宏观指导,也要微观可评估,使得评估在操作性、效果性、兼容性等面临一系列困难。
(四)全球治理技术能力建设滞后
世界科技革命不断推进,各种科技应用日新月异,技术带来的全球性挑战超越了国家和区域的边界,然而全球治理体系却没有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一系列规则相对滞后,技术逻辑与权力目标相互冲突的情形时有发生。
1.新科技革命影响治理行为结构模式。
目前,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技术、区块链、云计算、跨境电商等新一轮技术变革方兴未艾。与之前历次科技革命比较,本次科技革命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度展开,对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新科技革命推动全球治理结构优化的同时,其所附带的颠覆性影响及风险巨大,也对传统治理提出挑战。例如,人工智能技术中的算法歧视、伦理道德、数据安全等对多方治理模式产生重要影响。新技术一方面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那些无法获得科技支撑的地区,与先进国家的鸿沟拉大,这也可能导致局部地区的动荡不安,增加建立公正合理、普惠均衡的全球治理体系的难度。此外,发达国家往往掌握高科技的主动权,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借口,不愿技术转移,增加发展中国家技术发展的难度,无形扩大数据鸿沟。
2.信息传播泛化,传统物理疆界虚化。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信息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传播不受传统国家物理边界的限制,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应用,使得即时信息可以自由进出每一个国家。在新媒体、融媒体以及全媒体的影响下,一国发生的事情,很快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虚假信息的传播通过现有的网络技术,可以快速且低廉向外传播。新冠肺炎疫情之中,关于病毒起源的阴谋论传播甚广,对各国民众产生广泛的负面作用,增加了全球治理的成本,不利于国际合作。特朗普通过推特,可以越过层层官僚机构,直接将信息传向世界各地,引导民众的国际认知,对全球合作造成冲击。而恐怖分子利用互联网传播信息,扩散恐怖已是他们的常用手段,难以追根溯源的网络空间为恐怖分子提供新的土壤。在网络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信息的生产者,同时也是信息的传播者,信息泛化成为全球治理的难题。
3.外太空、极地等全球新疆域治理滞后。
人们对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之外的深海、极地、网络空间和外太空等领域的开发利用日益频繁,由此带来新的全球治理问题与挑战。深海等新疆域能否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关乎人类共同的利益。新疆域是人类共有的财产,具有非排他性,但各国关于新疆域治理的全球供给产品严重不足,特别是发达国家,借助先进的技术,企图独占人类的“公地”,这导致在新疆域开发利用中产生“公地悲剧”。国际社会对新疆域理念也存在矛盾,在疆域属性认知、规则建立等方面存在分歧。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企图树立在新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不愿意为全球新疆域治理提供公共产品,而中国等新兴国家由于能力与经验等原因,不能给新疆域治理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拓展,新疆域活动增加与治理机制缺失矛盾日益凸显。同时,一些新疆域治理呈现碎片化、规则规制主导权竞争等复杂性问题。
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进路
一个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效能,既受全球治理体系发展影响,也取决于国际格局变化,更受自身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影响。当前,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面临的最突出挑战,中国在国内抗击疫情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疫情防控,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为全球抗疫提供公共物品,抗疫措施被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描述为控制疫情的新标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国智慧,也需要中国力所能及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中国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中国采取“一边倒”政策,这一时期重要的全球治理机制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都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建立,中国对这些全球治理机制采取抵制的态度。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缓和,尤其是改革开放国家大战略的实施,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融入世界,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军控、联合国维和、国际经济、气候变化等领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主要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开始接触。改革开放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日益密切,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既影响世界各国的发展,也关联我国经济建设进程。中国将自身的发展进步与世界的繁荣稳定密切联系,对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的态度开始从怀疑抵制转向接受融入,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自身定位也转变为现行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的参与者、支持者。(16)吴志成:《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转向》,《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3期。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越来越多地接受多边主义,参与相关国际机制安排。签署了此前不愿加入的多边协议。同时,中国在减少贫困、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国际人权保护等发展议题上参与讨论并发挥建设性作用。
第二阶段:积极参与。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意识到自身的发展获益于全球治理体系,自觉参与全球治理并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成为“负责任大国”的一项重要任务。2005年,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将中国称为国际体系中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17)Robert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September 21, 2005,https://www.ncuscr.org/sites/default/files/migration/Zoellick_remarks_notes06_winter_spring.pdf.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对全球治理实行多管齐下的战略,支持符合全球公益和规范的国际机构和协议,例如世界银行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作用日益增强,2006年,陈冯富珍被任命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支持推广中医药计划。在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参与协调亚洲宏观经济对策的工作,在帮助世界经济复苏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三阶段:深度融入。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和利益诉求也不断变化,中国把全球治理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致力于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中共中央政治局围绕全球治理议题召开2次集体学习,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目标更明确,全球治理成为中国推动全球事务改革完善的自信和自觉。习近平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35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50页。全球治理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2013年,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加深了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联系,推动了沿线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与各国的联系。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习近平主席主持下,会议围绕近30个领域取得100多项成果和共识,其中中方提出的倡议占到一半以上,中国的议程设置权得到明显提升。(19)《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精彩“三部曲”》,《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9月9日。在2016年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中国作为东道国,对G20这一全球治理的最重要平台议题设置,起到了牵引和主导的作用,达成了29项重要成果,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得到明显增强。中国以公平和正义的理念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在国际机构中发挥更大作用,在传统上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中赢得了影响力。例如,在2019年6月,中国农业和农村事务副部长屈冬玉轻易击败了美国支持的候选人,成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总干事。(20)《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屈冬玉当选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新华社,2019年6月23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6/23/c_1124660560.htm.2020年9月,《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显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各领域表现认可度均获提升,其中科技、经济和文化领域表现最为突出。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中,海外受访者最为认可的三个领域为:科技(66%)、经济(63%)和文化(57%)。经济与科技并肩成为海外受访者最期待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领域。(21)《智库报告显示中国“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形象备受期待》,中国新闻网,2020年9月15日,http://backend.chinanews.com/gn/2020/09-15/9291385.shtml.
(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进路
一国的经济综合实力会转化为战略影响力,影响力大小则取决于战略能力。法国国际关系专家伯特兰·巴迪亚就全球治理的实现提出三点:首先是全球共有的资产或者面临共同的威胁,需要通过国际社会的合作协调来治理;其次是超越过时的敌友关系,重塑“他者性”,通过促进伙伴利益的实现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最后是以相互依存的关系为基础,力所能及的提供全球治理所需的公共产品。(22)Bertrand Badie,“L’épidémie de Coronavirus(COVID-19):Un Catalyseurversl’acte II de la Mondialisation?”,The OECD Forum Network,April 3,2020.同样,中国参与完善全球治理,要坚持与时俱进,兼顾公平与效率,保持战略定力,增强世界团结粘性,力所能及提供公共物品,提升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信任。
1.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赋予全球治理新理念。
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的目标模式,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就是全球治理的最重要基石”。(23)高飞:《中国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人民论坛》2019年第30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优秀的中华文化,体现新时代中国倡导的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国际责任感,给予治理难度不断增加的全球性问题更多协调性整体关注。面对单一国家很难解决的诸多全球问题,需要各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全方位协作,整合碎片化社会为一体,发挥最大集成效应,实现解决全球问题的资源有效调配。“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就需要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理念性产品”。(24)任琳:《中国全球治理观:时代背景与挑战》,《当代世界》2018年第4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回答了中国以什么样的姿态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本质问题。积极发掘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处世之道与全球治理的共鸣点,坚持正确的义利观,赋予全球治理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新概念。一方面,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积极主动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敦促全球治理机构更好地代表新兴大国的需求,推动达成气候变化的国际解决方案,完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为在现有全球治理规范内运作的一个有效机构。另一方面,中国全球治理新理念根本目的是维护现有体系的稳定,并不是要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与美国争夺所谓的全球治理领导权,而是发挥全球团结力,通过改革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高效、快速应对各种新威胁新挑战,实现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此外,当前中美关系面临“脱钩”风险,中美双方未来协调合作的趋向,成为影响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关键变量。“中美应该将两国面临的分歧纳入全球治理体制中进行管控,平衡两国在全球治理体制中的共存和竞争”。(25)刘国柱:《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与中美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改变以往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存在结构矛盾观点,避免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创造条件增进战略互信,积极探讨全球治理的双方共同参与领域,引导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良性互动。在倡导“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同时,在全球经济、世界卫生、气候环境等全球议题方面,开展双边合作。面对特朗普给中美关系以及全球治理带来的不确定性,要保持战略定力,避免产生固化的“新冷战”思维。
2.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平台,增强公共产品有效供给能力。
全球治理需要平台作为治理行为载体。约瑟夫·奈在《美国与全球公共物品》一文中认为,美国参与全球治理在不同的三个层面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美国作为世界最主要力量,应发挥领导力,维护现行国际机制,协调全球集体行动;在追求自身利益同时,应将全球治理放在更高位置;必须充分利用自己主导地位,在解决国际问题时,充分发挥中间人或者领导者的作用,为国际社会提供全球治理所需的公共产品”。(26)Joseph S. Nye, “America and Global Public Goods”, Project Syndicate, September 11,2017,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merica-and-global-publicgoods?barrier=accesspaylog.近年来,原有一些全球治理平台难以容纳中国安全和发展需求,中国主动与其他国家一起搭建新的治理平台,例如“一带一路”、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等。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在理念和机制等很多方面与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和一致性,能够很好地提升全球治理的韧性。当然,国际公共产品的稳定供给需要巨大成本,中国要以“一带一路”已取得的成效为基础,在“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基础上,积极拓展保障供给领域。“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27)《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23日。平衡拓展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本国利益发展的融合交集,将中国的发展需求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结合在一起,同时充分动员其他发达国家、企业和民间组织的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这五个基本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不仅鼓励国家和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互联互通,而且还通过培训、规划和治理交流分享知识,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治理能力,形成发展的联动效应,塑造正面的外溢效应。
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团结合作,加强政策沟通,协调彼此的政策分歧,形成共同发声的合力,共同促进和改善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通过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中非合作论坛、中国-拉共体论坛、中国-中东欧“17+1”合作机制等平台和机制建设,推进务实合作,增强与发展中国家在应对重大国际问题、经济风险、气候变化、世界卫生等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改善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和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信托基金的使用,以便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推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与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逐步改变传统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发达国家主导的局面。
3.以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为挑战,提升全球治理议题国际协调能力。
结合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需求,加强国际医疗合作,主动号召合力构建新冠疫情后的全球治理新格局。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成就体现了中国之治,获得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评价。中国与联合国一起在中国境内建立全球性的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以确保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抗疫情医疗物资,充分展现了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责任。疫情可能会催生一个全球治理的新时代,其标志是对全球公益的共同责任、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多边行动以及对等的伙伴关系。同时,为了消除国际担忧,需要表现出对多边主义的承诺,继续加强与伙伴国家的团结,与国外利益相关者采取合作,利用软实力帮助世界摆脱这场非传统安全危机。
通过表达参与全球治理意愿与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推动建立完善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体系建设。重点对全球治理体系不完善甚至缺失的深海、极地、网络、太空等新疆域,提出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全球治理体系,充分发挥穿针引线的作用,破解全球“公地”治理的困局。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根据全球治理最新发展动态,做好“在场性知识”制订协调能力,引导其他国家参与,保障全球治理的成功。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的治理需要技术大国引领,更需要代表性大国协调保障公平。中国力求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领导者,并倡导“网络主权”的观念;中国公司还在第五代无线通信标准(5G)的专利和标准的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科技领跑者之一,要依靠自身的技术基础提出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同时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商议制定公平有效的治理规则,为新技术的科学引用、合理推广贡献中国智慧。采取措施来减少排放,减少化石燃料在其能源结构中的作用,巩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地位,与现有国际机构合作,成为气候变化领域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导者。
4.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注重发挥联合国等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
多边机制是推进全球治理的必然要求,协商对话是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要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原则基础上,构建一套促进多元参与、协调多方利益,推动多边合作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冠肺炎疫情充分表明现有解决国际危机的应急多边体系存在缺陷,需要加强国际组织在紧急情况中的领导作用。积极举办全球治理论坛,充分利用联合国等多边合作框架机制,共同探讨公平有效的全球治理方案,推动国际共识形成。由于各国利益的差异,不可能在所有全球治理的议题上达成一致,可在全球共同面临的诸如新冠肺炎疫情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积累多元主体参与全球治理的同向经验。很多全球治理的议题是无国界的,因此要坚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全球治理机制中发挥核心作用,(28)《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23日。还可以调动私营部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组织、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发挥它们在全球治理相关议程决策作用。推动相关国际组织完善全球治理评估体系,构建目标明确、操作科学,动态平衡的评估体系。
维护和加强多边机制,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将成为未来中国外交的主题。伴随经济持续增长,中国将更加有力地为全球治理设定条件,将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等历史悠久的组织中发挥更大的话语权。推动完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二十国集团行动计划,并为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以将二十国集团从短期应对机制转变为长期治理机制。
5.以完善全球治理人才培养体系为保障,讲好全球治理的中国故事。
打铁还需自身硬,国家治理是全球治理的基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引领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重要前提,正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29)刘雪莲、姚璐:《国家治理的全球治理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应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过程,重点在运用法治思维维护中国国际合法权益、国际人才培养、有效对外传播等方面完善自我。国际法是维护国际社会稳定的重要规则制度,也是保障国际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全球治理在法律规则下可以得到良性发展,实现善治目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要树立法治思维,积极主动运用国际法来解决国际争端,更好增进中国合法权益,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使命。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完善全球人才治理体系,打造人才网络,做好专业人才储备。根据我国全球治理参与的领域,重点培养国际金融、生态环境、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国际人才。针对全球治理的多领域知识融合趋势,逐步形成涵盖多学科交叉领域人才网络结构。注重参与全球治理的多元主体培育,支持我国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国际交往,与国外知名非政府组织加强国际合作。引导“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和境外留学人员,为我国推动全球治理提供更多助力。与此同时,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声音和力量,有的国家欢迎支持,有的国家疑虑误解,还有的国家可能排斥抵触。针对一些国家的“杂音”,要全面提升全球治理议题的研究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以中国治国理政的经验为重点,传播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在减贫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发展等方面治国理政的中国智慧。充分挖掘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资源,利用多种国内外媒体传播资源讲好中国故事,打造包括政府、传媒、学术、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内的全方位、立体化的对外传播格局,塑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良好国际形象。
结 语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两个根本全局战略环境。参与全球治理改革是随着中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必然结果,同时中国对参与全球治理有着清醒的自我认识,在办好自己的事情基础上,积极履行大国责任,力所能及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加了国际社会未来发展的诸多不确定性,全球治理也面临体系松动、赤字扩大、多边合作机制弱化、技术能力建设滞后等诸多挑战,客观上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效能,但同时现行体系仍具有一定稳定性和作用,中国通过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也为应对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一种思路框架。中国倡导开拓的全球治理体系是把世界看作一个利益交织的社会整体,体现了多元共生的文明观,顺应了当今全球治理转变处于历史转折点的发展趋势,必将对塑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