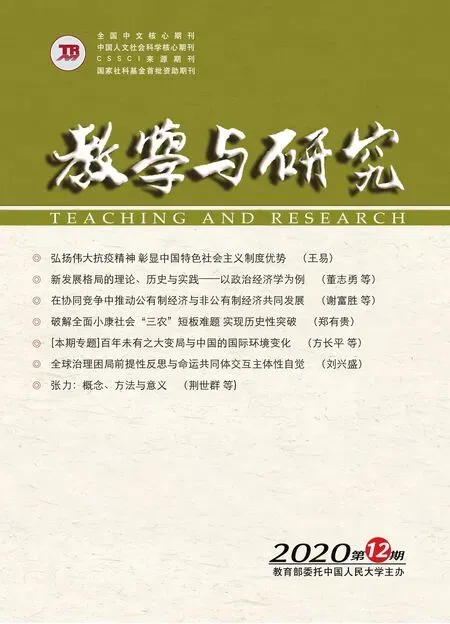全球治理困局前提性反思与命运共同体交互主体性自觉 *
刘兴盛
全球治理是满足人类世界普遍交往需要的途径和方式,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近年来国际交往领域凸显的种种“逆全球化”行为却使全球治理日益陷入窘境和困局,在此问题上,许多社会科学学科均对此进行探讨,以此立足自身视野为突破全球治理困局出谋划策。不过,在这些学科的视野之外尚存在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域,这就是理性或思维方式的维度,即是说,处于交往中的各个国家或民族不仅是利益主体、权力主体或权利主体,而且是由理性的人所构成的理性主体,因此对隐藏在种种“逆全球化”行为背后的理性之不自觉的前提进行批判尤为必要。换言之,克服和超越全球治理困局需要我们对引导相关国际主体采取“逆全球化”行为以此导致全球治理陷入困局的理性原则进行深入的追问。而作为思想中把握的时代和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对具有时代特征的理性或观念进行前提式的反思和批判,以此推动人们的思维方式转换,促进社会的发展。立足于此,本文从哲学视角对造成全球治理困局的深层思想原则做一追问和探讨,以期推动相关研究。
一、全球治理困局与实体主体性:现代性困境重大表征与深层“病灶”
现代性是全球化的“启动机”和内在动力,伴随现代性进程的展开,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跨越国度乃至跨越大洲的交往日益频繁。基于对现代性推动全球化的社会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马克思指出个人的全面发展不可能以狭隘的地域性的交往为基础,而必定同“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页。从而也就指明了世界普遍交往对人类实现自由个性的必要性。然而,在当今社会却出现了一种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逆全球化”倾向,这种倾向的典型表现是在全球性事务中拒不履行本应承担的国际义务,排斥甚至完全脱离国际合作框架,以单边主义取代多边主义等等。这种倾向和行为在目前的国际交往中频频出现,致使全球治理陷入窘境和困局,以此严重阻碍了世界普遍交往水平的跃升,给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梯带来“松动”和“裂隙”。
如前所述,全球化植根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成果和产物,这意味着求索全球化的悖反——“逆全球化”及全球治理困局的原因和破解之道亦须向现代性本身进行追溯。事实证明,现代性的深层思想原则恰恰是经不起追问的,正是这一思想原则的蜕变导致现代性走入困境,最终促使“逆全球化”倾向和全球治理困局的产生,而这一思想原则就是主体性。也就是说,作为现代性的深层思想原则,主体性一方面推动了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它的极端形式——实体化的主体性也阻碍了现代性的实现,使现代性走入困境,而“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困局不过是这一困境的表象。就此而言,从哲学层面反思主体性的极端形式——实体主体性对克服“逆全球化”倾向乃至破解全球治理困局具有前提性的意义。
所谓实体主体性意指一种将自我看作事物最高根据而将其他一切看作对象并加以利用或排斥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是伴随现代性进程的深化而逐渐形成的,是一种历史性的思想原则。具体而言,在前现代社会,人们匍匐于神、君主或抽象的共同体等外在权威面前,服从和服务于神、君主或抽象的共同体是其不予质疑的最高价值,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在此过程中,主体性开始萌生并崛起,并由此使得人们对价值的思考由向外转为向内,逐渐从自我出发看待世间的一切,也就是将自身确立为评判事物的尺度和根据。这种转向促使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而外在于人并凌驾于人之上的神圣形象——上帝、君主、抽象共同体等也在此过程中遭到解构。也就是说,正是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支撑了主体性的崛起,使得人们不再将自身看作宇宙和外部世界的附属品,而是移步于宇宙和整个世界的中心。这种自我与外部世界的位序转换鲜明地体现在宗教一体化力量的瓦解上:在前现代,无论是抽象的共同体还是君主,其统治性地位的稳固往往借助于宗教的解释力,从而作为整个社会的至高纽带,宗教发挥着绝对的一体化作用,宇宙秩序在宗教中获得最终解释,被认为是具有目的的整饬有序的一个整体, 即“包含着‘世界’作为一个‘宇宙秩序’的重要的宗教构想,要求这个宇宙必须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安排得‘有意义的’整体,它的各种现象要用这个要求来衡量和评价”;(2)[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08页。而在现代,宗教的一体性力量被解构,世界的中心转移到自我身上,世界的意义由人自己来赋予,自我成为了人们思考和行动的绝对阿基米德点。可以说,在将自我确立为思考和行动的出发点时,人们通过自己的理智而不是外在权威来赋予自身以自由和尊严。正是得益于这种洞识,康德对启蒙的本质做出这样的概括,即“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3)[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2页。也正是因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对主体性的崛起有着重大推动作用,所以不少学者认为,现代性在一定意义上始于这三大运动。事实上,将主体性视为现代性的深层支撑,可以在许多现当代哲学家那里找到根据。对此,黑格尔无疑是最早的代表,黑格尔指出:“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4)“主观自由的法,是划分古代和近代的转折点和中心点”。(5)[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30、145页。在黑格尔之后,哈贝马斯和鲍曼也均做过类似的论述,哈贝马斯说道:“在现代,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6)[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2页。鲍曼在给贝克的著作所作的序言中强调:“把社会成员铸造为个体,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7)[德]贝克:《个体化》,李荣山、范譞、张惠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页。
然而,近代以来崛起并支撑和推动现代性的主体性原则,随着自身的发展逐渐暴露了其内在缺陷,这就是其内含的唯我独尊的倾向,亦即实体化倾向。众所周知,在近代哲学中率先奠定主体性基础的是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他通过怀疑“我思”之外的一切奠定了自我的绝对地位,从而高扬了人的主体性。但是这种主体性的基础是一种知性原则,其特点是划分出自我与对象的差别,并以这种差别为前提进行思考,由此执着于 “不相容的对立”。对此,黑格尔曾指出:“那只能产生有限规定,并且只能在有限规定中活动的思维,便叫做知性(就知性二字严格的意思而言)。而且思维规定的有限性可以有两层看法。第一,认为思维规定只是主观的,永远有一客观的[对象]和它们对立。第二,认为各思维规定的内容是有限的,因此各规定间即彼此对立,而且更尤其和绝对对立。”(8)〔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93页。可见,在将自我高扬为绝对基础的同时,一条主客对立的屏障也俨然矗立起来,进而从自我出发“吞噬”或“消化”他者的实体化逻辑便不可避免。这里所说的主体实体化即是指将自我看作终极唯一的最高根据的思维倾向。对于这种“实体化”,联系海德格尔的相关论述来理解无疑是有裨益的,海德格尔指出,“把‘实体’的存在特征描画出来就是:无所需求。完全不需要其他存在者而存在的东西就在本真的意义上满足了实体观念——这种存在者就是完善者。”(9)[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2006年,第108页。这一论述表明,实体化意味着遗世独立和唯我独尊,而这种遗世独立、唯我独尊充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属性中:其一,单极性。“实体”是万事万物的终极的始因和归宿,是世界之永恒的基础,在它面前,所有事物都是无常的偶性和不固定的现象,是变动不居的。作为变动的“非本质”的现象,除“实体”外的所有事物都绝对地依系于“实体”,依靠“实体”获得存在意义并取得最终解释。其二,同质性。在时间和逻辑上的绝对先在性使“实体”被看作万事万物所从出的渊薮,成为衡量世间一切的尺度,这一绝对的尺度要求所有存在者都要返回或还原到“实体”之中,在后者的内在平面中进行价值排序。对于那些可同化吸收到自身之内的存在而言,它们被看作“实体”的派生,具有正统的合法性,除此之外的一切他者则被认定为不可理喻的异端邪魔,最终无法获得承认。在“实体”那里,“齐一万物”的法则被稳操于手。其三,封闭性。“实体”的单极属性和同质属性意味着它必然走向封闭。对于“实体”来说,一切事物已然被包含于自身之内,它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自因自足者,具有终极存在的意义,它并不借助任何他者就能独立自存。而无所需求的独立自存性表明,在“实体”的逻辑中没有与之相对等的他物,凡合理存在的事物在它看来皆出于它自身之内,由其所衍生。由此,“实体”拒绝接受任何与自身相左的事物,由此排斥差异性的“非我”进入。对于那些“非我”的存在者,“实体”不提供任何可供其进出的通道。也就是说,在“实体”同他者之间横跨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雷池。
由上述分析可知,实体化的主体性是一种单极的、同质的和封闭的主体性,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引导下,人们思考和处理问题时的视野将大受局限,犹如拘于泥沼难以自拔,以此掩蔽了自我同他者交流沟通的途径和渠道,正如阿多诺所形容的那样,锁闭在自我之中的主体只能“通过堡垒墙上的瞭望孔来注视夜空”。(10)正是这种理性形态和思维方式为现代性困境埋下了种子和祸根。即是说,现代性在本质上要求将个体塑造为主体,从而为人类自由解放奠定自觉自为的基础,然而伴随个体普遍采取实体化主体性的思想原则,自我与他者之间出现了分裂和对立,以此造成“伦理总体性”的瓦解和“社会生活统一性”的丧失,使现代性这一人的解放的谋划走入了自反。
事实上,个人间的交往与国际间的交往具有同构性,从实体化主体性出发导致的个人交往障碍和阻力必然表现于国际交往当中。这意味着,当国际交往中的个体采取“实体主义”思维方式时,也必然造成整个交往结构呈现出分裂对立局面,亦即形成中心—边缘的结构和格局。一些国际主体在实体化主体性的引导下,将自身作为考量事物的最终尺度,用以裁剪国际交往中的对象,而当他者同自身利益、话语等有所差异时必然被看作对立,由此不纳入自我所处的位置之中。因此,伴随自身被“实体化”为绝对的中心者的是他者被对象性地划归为边缘,由此塑造出中心—边缘相对的社会交往结构。也就是说,在采取实体化主体性的国际主体看来,只有自己才是“实体”,处在交往中心,而自我之外的他者则被一圈圈涤荡到边缘,逐渐同自我拉开差距。对于那些处于圆心之外的“边缘者”,等待他们的常常是来自“中心”的蔑视、冷漠甚至拒斥和排挤。对此,阿多诺形容道:“根、起源的范畴是一个统治性的范畴……它证明了本地人反对新来者、定居者反对迁移者”。(11)[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57、152-153页。
实际上,所谓的“根、起源”正是“实体”的同义语,将自身看作是“根”和“起源”也就是将自我摆在“实体”的位置,认为自我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和属性。这一地位与属性同他者是不相容的,后者之来临被视为“松动”和“裂隙”的开始,成了对自我的重大威胁。由此可见,从“根”或“起源”出发的实体化主体性必然阻断自我视域同他者视域的融合,从而对“边缘者”持蔑视、冷漠乃至拒斥和排挤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
二、交互主体性扬弃实体主体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的启示
如前所述,实体化主体性代表的是一种封闭的观念和逻辑,采取这种观念和逻辑必将使自身成为一种狭隘存在,从此出发难以做到同他者的及时沟通和有效互动,最终导致主体与主体间的分裂和对立,而这一点正是现代性走入困境的重要因素和根源。而在以实体化主体性为观念基础所建构出的国际交往格局中,各个国际主体之间无疑被一道竖起的无形墙壁阻隔开来,由此最终导致全球治理陷入困局。这就意味着,消解全球治理困局的前提是对这种不合理的思想原则和思维方式进行扬弃,即摒弃实体主体性的思维方式代之以更为合理的思想原则,这是有力推动全球治理水平跃升以及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思想前提。在此方面,交互主体性显现出了超越实体主体性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所谓交互主体性,意指一种以自我与他者间相互关系为立场和出发点的思想原则和思维方式,这一思想原则和思维方式的载体不再是单一孤立的独白自我,而是将自我诉求内在地同他者需要结合起来所构成的统一体,也就是以包容差异和多元共生为自觉的取向。以交互主体性为思考和行动的立脚点将切实实现不同主体的良性互动,从而为主体间的对话和沟通提供坚实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提升社会的团结与和谐。交互主体性的思维方式有着深刻的存在论根据,以此解构和扬弃了基于认识论或知性思维的实体主体性,是一种辩证地看待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理性原则,在此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其社会关系思想的深刻内涵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启示。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任何历史的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个人之所以能够按照属人的方式而不是动物的方式生存发展则在于其能够从事生产劳动实践。对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2)因此,从生存论的角度来说,生产劳动实践是人的存在的现实基础,但是这一活动之所以可能,除了需要满足自然方面的前提外还需要满足社会方面的前提,而其中最为本质的就是共同的活动,这种共同活动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和建立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3)“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14)由此可见,正是因为建立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社会关系,人类才能够互相交换其活动,从而产生出1+1大于2的实际力量,使得个体可以作为超越动物的真正的人而生存,以此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人的自由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由之奠立基础,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以此获得切实实现的可能。也是出于对社会关系在人的劳动实践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认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连用三个“只有在社会中”来表达社会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作用,即“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15)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532、724、187、505页。
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充分地揭示了一个道理,即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共在式的存在者,而不是孑然遗世独立的孤独个体,可以说,从始至终完全脱离同他人建立社会关系而能够单独存在的个人是不可想象的。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的那样,孤立的个人能够生产是罕见的事,这在已经具备了社会生产力的个人偶然落入荒野时才是可能的。(16)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页。现实个人的生存发展以同他人建立关系为前提启示人们,在人的生存发展尤其是公共生活领域中必须采取符合人的生存本性的思维方式,即确立交互主体性的思想原则。从交互主体性的思想原则出发,个体将不再仅仅局限于封闭性的自身去理解和对待他人,而是敞开心扉地同他者建立合理互动,以此在沟通和对话中促成合作。在此基础上共同推动自我利益诉求和他者需要的满足,而这样的状态的生成意味着实体主体性思维得以消解和超越。而交互主体性之所以能够消解和超越实体主体性,在根本上就源于其以对人的本质的深刻洞见为依托,这就是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经典论断,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⑥这一论断深刻地表明,社会关系作为人生存发展的重要前提,其性质和状态深刻地影响着处于交往中的每个个体的生存品性和生活境遇,因而以汇集到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这一论断为基点,要求我们采取交互主体性的思维方式,它凝结着对人的现实生命的真切关怀与价值眷注,适应人类对自由全面发展的向往和追求。
进而言之,确立交互主体性意味着主体性得到了彻底的重塑和转换,即孤立独白的主体性向交互对话的主体转变,这种转换将为构建理想的公共生活境遇搭建思维层面的平台和地基,从而成为实现社会和谐的精神支撑和思想保障。与交互主体性相反,实体主体性则在根本上背离了人的存在本性。就此而言,只有深入把握社会关系对人的生存发展的意义才能真正认识到人的生存发展的交互性,达到对人的现实本质的把握,即每个自我的存在都是在他人之中的存在,以他人的存在为前提条件。从此出发,人与人之间合理形态的相处之道便会向我们呈现和展开。总之,交互主体性蕴含着符合人的本性的合理观念,自觉确立这一思想原则将有力推动自我对待他者的态度和方式的转变,是一种自我向他人开放的活泼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交互主体性自觉及其对全球治理困局的破解
全球化和世界历史是人类通往自由全面发展阶段的桥梁和阶梯,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在这样的时代中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也就是说,只有以全球化过程中生成的普遍交往为基础,人类才有可能驾驭生产力的总体,以此消灭束缚人类的旧式分工,实现人类的进一步解放。就此而言,导致全球治理陷入困局的去全球化行为是极不可取的。与背离全球化的做法不同,正视时代趋势才能阻止全球治理颓势,从而以良好的治理水平和能力服务于整个人类。如前所述,全球治理困局折射出现代性困境的思想根源,以此警示应当努力弥补的观念短板,即消解不合理的思想原则和思维方式,这一思想原则和思维方式就是实体主体性,是导致现代性陷入瓶颈的因素,而全球治理困局则是这一困境的具体表现。因此,治理思维的合理化是提升全球治理水平、推动世界进步的重要条件。而这意味着,需要以交互主体性扬弃实体主体性,以此实现全球治理领域的思维形态转换。在此方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是构建交互主体性的重要方式,确立和践行这一理念将有力推动全球治理困局的破解,以此为人类走向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十九大则进一步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定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强调和追求,充分体现出从自我与他者、个体与共同体的主体间关系来思考和行动的本性,因而是以交互主体性为深层基础的。作为交互主体性自觉的当代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如下特征和属性。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多样性,反对单极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中,组成人类社会的主体不仅命运与共,而且复杂多元。正是这种丰富多样的属性构成了事物的本来特征,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18)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出发,人类实践谱写的画卷之所以宏伟壮丽就在于它由各种色彩所组成,正像马克思所形容的那样,每滴露水在太阳的照射下都显现出无穷无尽的色彩,而世界上的任何个体和事物决不仅仅只具有一种颜色。(1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页。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国际交往中的主体都拥有自由和独立的地位,其存在发展的权利是不容抹杀和遮蔽的。这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决拒斥任何形式的霸权和强权,尤其谴责和反对强国对弱国的欺凌以及对他国内政的干涉。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差异性,反对同质性。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不同国家的人民存在休戚与共的相互依存关系,而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又来自于差异和不同。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差异的存在才使得互补具备意义和被需要,而在互相补足的过程中,处于交往中的主体都将获得进步和成长。正所谓“同则不继、和实生物”(《国语·郑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中,差异是推动人类社会和世界永不停息向前发展的车轮,不同国家、种族、民族、宗教等相互间的差异绝不是成为使之受到蔑视、遗弃、屈辱和奴役的理由,而是彼此都应当将对方摆在与自身相同的位置,彼此充分尊重各自存在和发展的权利,尤其是尊重不同国家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那样:“‘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20)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开放性,反对封闭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目标中,开放包容被视作基本的行动原则和交往准则,即要求“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21)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实际上,开放包容原则的制定正是以对世界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洞见为依据,而与此同时,开放包容的原则也是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保障。也就是说,在国际社会当中,对于拥有不同利益、文明和价值观的他者,决不能采取视而不见甚至排挤拒斥的观念和心态,而是应当在承认其他国际主体利益、文明和价值观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在不损害他者利益的前提下满足自身的合理诉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他者的合理诉求表示关切,积极寻求实现共同利益和他者利益的渠道和途径。只有按照开放包容的原则行动,才能使自身和他者间的差异得到合理的对待。而在此过程中,不同的国际主体可取他者之长补自身之短,努力做到在推动他者需要实现的过程中满足自身需要,以此实现互利共赢,保障世界的多样,进而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社会秩序。
可见,作为交互主体性自觉的当代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其对多样性、差异性和开放性的强调超越了国际治理体系中的单极性、同质性和封闭性,因而是推动破解全球治理困局的重大力量。这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对世界各国人民所具有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存关系的表达,同时也饱含着团结合作、互惠共赢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从而充分彰显出它所内蕴的交互主体性思维方式,以后者为基础的成果和结晶。以交互主体性为立脚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落实,将使国际社会中存在的中心—边缘对立格局得到消解,代之以平等的主体—主体交往格局。在这一结构当中,每个国家都不再将自身推及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采取实体主体性的思维方式打压和遏制他国发展,而是充分认识到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并且自觉地维护平等互利、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国际社会秩序。而这也就表明,存在于全球治理领域中的种种“逆全球化”措施和“离心力”行为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和消除,全球治理效能也在“向心力”的凝聚中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台阶,由此有力地缓解乃至克服全球治理的困局。
综上所言,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体现出交互主体性的自觉,在其构建和确立过程中,全球治理思维将得到转换和升华,即通过交互主体性的现实化扬弃存在于全球治理中的实体主体性。而伴随实体主体性的消解,全球治理困局将得到有力破除,以此促进全球治理效能的巨大提升,从而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一言以蔽之,推动国际交往思维从实体主体性向交互主体性转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克服全球治理困局、提升全球治理效能的重要机制和环节,构成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重大意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