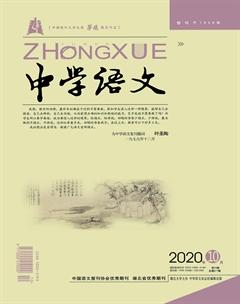由“木叶”说起
李清
林庚先生在《说〈木叶〉》一文中说到,自屈原写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这动人的诗句以后,“木叶”便成为诗者所钟爱的形象。“从概念上说,‘木叶就是‘树叶,原没有什么可以辩论之处。可是到了诗歌的形象思维之中,后者则无人过問,前者则不断发展。”究其原因,“这与‘木本身所具有的天然的干枯落叶的艺术特征有关。”那么,“木”何以有这种艺术特征呢?林庚先生说这“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按照林先生的说法,暗示性就是指“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或者用钱钟书先生的话说是“一种怀孕的静默”。那么语言形象为什么会产生“潜在的力量”,以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又何以能“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这些问题林先生只从“木叶”的艺术特征上作了阐释和解读,而对其发生的原因和机制却没有进行深入说明。因此,本文尝试从暗示性语言的符号功能、联想作用及其文化成因等三个结构层面来进行分析和阐述,以兹将问题说清楚,以便提供诗歌鉴赏一个新的解释路径。
一、暗示性语言的符号功能
暗示性是语言交际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具体表达上如形象、语境、修辞、表现手法,甚至语气、语调等都具有这种功能,但诗歌语言的暗示性则主要体现在其形象的符号意义上。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往往要借助特定的艺术介质,以传达特有的情感信息,这种特定的艺术形象就是意象。意象其实就是物象和景象等概念的文学符号。例如木叶和树叶,二者本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但在诗歌中木叶却具有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是“典型的清秋的形象”(林庚),而树叶则只是一种纯粹的事物概念。再如梅、兰、竹、菊本来是些客观事物,但经过无数文人墨客的氤氲孵化,便具有了文学上的意义,是高洁品格的象征。它们从单纯概念的意义到具有人格化的力量,这就是语言符号功能衍化的结果……无论是木叶的“清秋”形象,还是梅兰竹菊的君子形象,在诗歌艺术中都是固化了的意象,我们很容易根据这类意象的符号意义探寻其内在的意蕴。
诗歌形象的符号意义一般可分为潜在义和象征义两种情况。意象的潜在义在于概念本身所蕴含的某种事物的特征,例如“木叶”,其概念本身就隐含着深秋萧瑟的特点。又如“明月”“高楼”寄托着相思,“枯藤”“老树”蕴藏着悲凉,“梧桐”“细雨”暗含着感伤,等等。而意象的象征义则在于概念本身所赋予的特定人格或事理的特质,如梅兰竹菊所代表的君子形象,松柏橡樟所具有的英雄气质等。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任何形式的语言都具有符号意义。因此,符号意义是暗示作用的基础,但暗示性语言的符号意义未必全都直接指向所要表达的情感价值,尤其诗歌语言,其潜在义和象征义必须要通过对意象特点进行深思和玩味才能把握。也正因为如此,诗歌才意味深远,意蕴悠长,散发出无穷的魅力,给人以美的享受。
巴尔特认为语言符号内涵本身作为一个系统由三个部分组成,即能指,所指,以及把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意指过程。能指是指与实体相联系的符号意义,而所指就是指抽象的意识形态,如情感态度、价值判断、思想观念等,由能指到所指的过程则是意指。巴尔特这种将语言符号系统三分的观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对于诗歌欣赏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形象的能指上,而更要深入到其所指(暗示意义),那么这个过程就需要意指的联想功能。
二、暗示性语言的联想作用
以上我们谈到,对于诗歌语言只是单纯地理解其符号意义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发挥想象进行联想,将其潜在义或象征义与某种思想情感(所指)联系起来才更有意义。因为语言天然具有符号意义,这就回答了为什么会产生“潜在的力量”的问题。如果说意象就是一种文学符号,那么意境则是符号意义的综合,这种综合离不开联想。意象——意境——意图(主旨),这是诗歌鉴赏的基本步骤,而联想在其中起着统摄的作用。
所以,暗示性语言的主要功能特征就在于联想,朱光潜说:“语言有直指的意义,有联想的意义。”而“联想的意义是文字在历史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种种关系”。如果要很好地理解一首诗歌,就必须透过表面的文字,揣摩其背后的“种种关系”,然后筛选、整合各种有用信息,再进行合理想象,最后做出价值判断,这个过程就是联想。联想的过程一般是从具象信息到抽象信息,从表层含义到深层含义。例如一提到“木叶”我们就会想到秋意,想到萧瑟苍凉的气氛。如“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句,它给我们的直观感受是落叶纷飞,秋意正浓,从诗句中我们看到波浪涌起的洞庭湖面秋风飒飒,落叶飘荡,一派萧瑟的景象,这正是语言的符号意义使然。而此情此景“我们仿佛听见了离人的叹息,想起了游子的漂泊”。读者的思维一下子便从木叶的清秋气息跳跃到离人的愁情别绪,由具象信息到抽象信息,由感觉到感知,我们体会到了世事无常,人生不易,这就是联想的作用。
由此可知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写景抒情诗,如果剥离掉联想的意义,都将无法进行赏析。如李白《蜀道难》中“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只见蜀道悲鸟哀号,古木参天,雄飞雌从,林间盘桓,这是诗句所呈现的画面。但我们如果仅仅停留在诗句所呈现的画面上,那么就很难理解诗人所要表达的意图。再结合下句“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这几句诗歌描写了一派苍凉景象,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这里人迹罕至、极尽荒僻。此处写景目的在于渲染蜀道之艰之险,友人入如此艰险之地,实在让诗人担忧不已。读了这几句,我们仿佛听到诗人对坎坷人生的深切感叹,感受到他对前途命运的无尽担忧,体会到他对国势民生的倾心关切。如果不去想象,不去联想,我们会诧异于此处为何进行这样的景物描写。其实欣赏这几句诗歌,我们只抓住“悲鸟”“古木”“子规”“空山”等意象展开联想,就不难理解诗句的意境及其表达意图。王国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大概也正是基于联想的功能才有此说吧。
诗歌欣赏,起始点是意象,着眼点是意境,落脚点是意图,灵魂则在于联想,因此诗歌的审美价值取决于这种联想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的语言形象是“形”,它的暗示性是“神”,因此诗歌只有形神兼备,才会境界全出,才会产生美的效果。反过来说,我们只有抓住了诗歌的形和神,才能更深入地领略诗歌美的精神要义,从而触摸诗人的心灵世界,走进诗歌艺术的神圣殿堂。
“科学的文字愈限于直指的意义就愈精确,文学的文字有时却必须顾到联想的意义。”所以在诗歌语言形象中,如果抛却联想的内核,诗歌的意蕴美将会荡然无存,因此我们可以说联想是暗示作用的内驱力。那么,联想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或者说诗歌语言“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又为何能“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的呢?除了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符号特征能自然地传递某种特有的信息,从而引发人们进行想象外,我们还要考虑到共同的文化心理。比如“木叶”或“落木”给人萧瑟苍凉之感,“梧桐”“细雨”能引发人们沉郁悲切的情怀等,很多意象在长期的文化进程中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情感色彩,成为族群共同的文化表征,因此这些形象的文学符号才会引发群体的共鸣。
三、共同的文化意识
语言需要共通的心理基础,暗示性语言的联想意义更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作为支撑。言语属于个性化的语言范畴,而语言则属于社会性的符号体系。个性化的言语一旦被公众接受并使用,成为自然的语言习惯,它就具有了普遍的社会意义。而这种社会化的语言经过历史的沉淀,又会自然地形成语言投射的社会心理基础——共同的文化意识。很难想象如果缺少了共同的文化意识,语言的暗示意义还能为人所理解。因此,语言暗示性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共同的文化心理。文化的历史沉淀既凝聚着民族的共同情感,又蕴含着共同的审美意识。“木叶”或“落木”等形象原本属于异质性的个人言语,后为人们所接受而成为社会化的公共语言,它在意义衍变的同时,也在打磨着民族的文化心理。经过人们千百年的代代相承以及创造性地使用,其符号意义已经成为民族特性的文化因子。这些语言之所以被广泛认可并接受,其中不可或缺的介质就是康德所谓的“情感的共通性”(文化因子)。正是基于这种共通性,语言所蕴含的丰富意义才有可能被人理解和接受。“情感的共通性”促进了共同文化心理的形成,而同时共同的文化心理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纽带联系,二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共同塑造着民族文化的特性。
所以,共同的文化心理是语言暗示作用的前提条件。狄尔泰说:“人的生命体验和诗意表达不能借助逻辑思维,而只能由一个生命进入另一个生命体验之中,使生命之流融合在一起……只有通过符号和语言中介而感悟其所表现的生命本体。”狄尔泰所表达的思想是:人的审美体验来自人类的文化意识,而不是靠单纯的逻辑推理,因为只有引起心理共鸣才能产生主观感受。因此,人类文化形成的过程应该先是一种心理投射,而后形成文化共识,再然后成为人们的文化自觉,最后成为集体性质的审美意识。比如象征着高洁品质、高贵精神的梅兰竹菊,以其先在的独特气质为人所接受,从而成为人们的文化意识,最后成为一种集体的审美意象。而审美作为一种精神感受,恰恰又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体验,仅仅存在于个人化的感性知觉之中。而这种感性的知觉又无意识地受到共同心理的作用,内在地形成某种情感基础。所以没有感知者就没有美,没有共同的文化心理就不能深切地感受其美。例如自然物之所以美,是由于主体在其中获得了一种超自然理性的发现。而这种超自然理性的深层结构,却来自人类所拥有的文化意识。因此,如果缺乏共同的文化心理,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肯定会受到影响,比如与不懂汉语的外国人谈“木叶”,我想那肯定是一场鸡同鸭语的对话。
以上筆者从语言的符号功能、联想作用及其文化因素等三个结构层面,对诗歌语言的暗示性作了解读和分析,目的在于通过对暗示性语言发生和发展机制的探讨,揭示其产生作用的内在动因。符号功能、联想意义以及文化因素三者之间互为条件、有机结合,是构成暗示性语言审美框架的基本要件。因为要托物言志、要借景抒情,所以才会有诗歌的语言形象,而通过对这些形象所暗示的意义展开联想,我们才能够深入把握诗歌的意境和意图。因此,对诗歌语言暗示性的解读,不妨说是给我们理解和体验民族文化经典之美提供了一个尝试思考的视角。
[作者通联:安徽阜南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