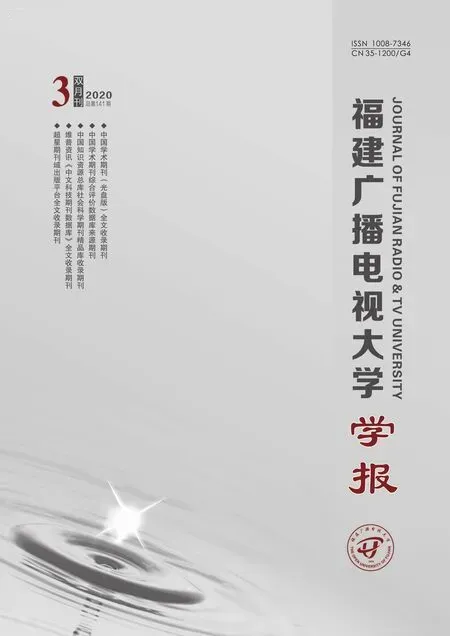福州近四百年印人述略
李永新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福建福州,350108)
近四百年来,福州印学与文人印的主流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福州远离文化中心的地理位置,给福州印人带来的影响至少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本土文化的传统得以沿袭;二是与中原、江南文化互动缺乏有时效的交流。当福州印人对赵孟頫、吾丘衍、文彭、何震尚处于想象,还停滞于对《三十五印举》具体篆刻技巧的揣摩以及对秦篆汉文的摹仿之时,福州有幸迎来周亮工、许容这样具有远见卓识与具体印风的优秀传承人,这些篆刻大家的专业素养、视野、文化包容力为福州印人开拓了由识篆、善篆进而深入到笔意的表现和以刀代笔、刀笔浑融的高妙之境。
1840年鸦片战争后,作为第一批开埠通商口岸的福州,城市近现代化的进程随西方工业文明的传入日益加速,城市文化也随之活跃。同治年间,福州印人受到赵之谦、魏稼孙等人引入浙、皖形式语言系统的影响,加之赵之谦“印外求印”“守拙胜巧”的理论也因针砭时弊而日趋流行,福州成为接纳浙皖风流遗韵之地。但福州光洁流畅的工艺大众审美也让篆刻家及受众选择相应的师法,以陈子奋为例,他生活于吴昌硕领军的时代,雄浑沉厚也自然成为陈子奋的艺术潜质,只不过他还是参入邓石如、吴让之的妩媚,让作品进入雅俗中庸之道。20世纪80年代初,艺术家个体意识增强,个人创造力成为篆刻创作摆脱简单模仿的内在源头。以石开为例,其夸张变形的入古出新方式不仅为篆刻图式拓宽了视域,也成为福州印人在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下自由创作的典范,这正吻合福州自开埠通商以来所形成的兼收、包容的文化生态。
谁是福州最初的印人代表?当代福州印人石开在2004年《吾闽篆刻歌》论述为:“篆刻斯小道,吾闽亦悠久。明清杂门派,宋比玉称首。八分始入印,虽俗名不朽。及至近现代,當推子奋叟。承续浙与皖,艳雅秀且厚。复见潘主兰,清逸同操守。居士谢义耕,古质意无苟。多产周哲文,印交天下友。现今力帆健,融合璜与缶。自立纵横相,结字其拿手。继起谢钦铭,新开黟山牖。还用傅永强,接力潘老后。愧我总异想,师传几尽否。邪正合一身,字间互掣肘。六十猶称小哥哥,束得长发京城走”。石开诗中“称首”之宋比玉(1576-1632年)原名珏,号荔枝仙,莆田人,流寓金陵。国子监生。工小诗,善八分书,规抚《夏承碑》,苍老雄健,骨法斩然。包世臣称其“分及榜书能品上”。善摹印,后人称为“莆田派”。诗云:“闻说莆田宋比玉,创将汉隶入图书”,宋比玉在书印史上影响深远,尤其在汉隶作书上有筚路蓝缕之功,为有清一代隶书中兴别开生面。
《广印人传》《明清篆刻流派印谱》记载魏植(1552-?),字楚山,又字伯建,莆田人。篆刻章法、刀法稳健。魏植稍早于宋比玉,将这两位置于福建篆刻史上言说,从所留存印蜕及后人评述中,可以暂定为具有专业印人资质的开始,算来迄今四百余年。莆田人林皋(1658-?),字鹤田,一字鹤颠,居常熟。印以小篆细朱文及汉白文为主,其篆刻堪称工整一路的极致,雅静秀润最为擅长,亦时见猛利之作。林皋印风,史称“林鹤田派”。以上三位均为莆田籍印人。而魏植、宋比玉、林皋的印风就是印学界所称之“闽派”的主要部分。而这三位莆田籍印人是福州文士极大关注的对象。
《闽中印人录》载侯官(今福州)人高瀫,明处士,善诗,画尤精墨兰,钩竹。篆隶、草书、八分、印章咸极其妙。《再续印人传》:林黼,字质夫,号石峰。闽县(今福州)人。通篆、籀。《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载其深于印学。同书另载侯官(今福州)人李根,字云谷,周亮工《印人传》云:字阿灵,工诗,小楷得晋、魏法,尤精篆、籀之学。尝注广《金石韵府》。周亮工为其付梓行世。镌图章直逼秦汉,有《云谷掌印谱》。
许容(1635-1696年),字实夫,号默公,又号遇道人,康熙廿二年任福州府检校。书法擅小篆,治印宗法汉人,为何震(1535-1604年)再传弟子,后人以占籍称为“如皋派”。何震二十岁至苏州,拜文彭为师,使他意识到“六书不精义入神,而能驱刀使笔,吾不信也”。彼时,正值《顾氏集古印谱》与《印薮》前后出版风行,何震师先秦古玺、仿汉玉印、拟汉满白,以至取元朱文印无所不有。何震成为仿汉热潮中一位集大成者。许容作为何震再传弟子,其善文辞,在总结师承理法上写下《说篆》一文,其中有:“夫刻印之道,有文法、章法、笔法、刀法。文须考订一本,不可秦篆杂汉、唐,如各朝之体,不可混杂其文,改更其篆。若他文杂厕,即不成文;异笔杂厕,即不成字。许容之后的福州清代印人,几乎没有逃脱这篇文字所框限的范围,甚至,在学习取舍汉印时以何震、许容的理念为先导。作为如皋派代表人物,许容可以说是江浙皖流派印进入福州的第一位宗主人物。而许容在印学上所总结出的经验理论必定在福州地域播下种子。
《广印人传》所载福州印人林霔却是一位颇具专业性的人物。林霔,字德澍,号雨苍,别号洞渔人,晚号晴坪老人。生活在乾隆嘉庆年间,印章典雅秀润,有《印商》二卷、《印说十则》传世。林霔篆刻与许容、林皋颇有相似之处,境界取向隐逸娴静。嘉庆年间出生的黄鹓(1798-1855年),字朗村,号雄飞、三余,福州闽县(今福州市区)人。父黄家积1820年辑自刻成《延古堂印谱》,朗村幼承家学,习六书学,研篆刻之技,一生辑刻印谱多种,其印风圆润流美。林霔、黄鹓两位印人成为许容篆刻观重要的薪传者。
1861年,赵之谦来到福州,这一年对于福州篆刻界而言至关重要,一批在福州的浙籍才子以及福州当地的金石雅好者与赵之谦频繁互动。赵氏在闽之时,颇多印事活动。赵氏艺友之中,众所周知以魏稼孙最为重要。在这大半年时间内至少有傅节子、傅栻父子,傅以绥,魏稼孙、魏本存父子,张国桢,丁文蔚,江弢叔、钱栻等新知旧友,同道中人相与切磋诗文金石。赵氏在这一阶段为朋友们刻下不少的印章,赵的言传身教,遂使浙皖派印学渐渗入闽。
杭州人魏锡曾字稼孙,号鹤庐、印奴。赵之谦在福州时,魏氏时任福建盐运使,因少好篆刻,嗜金石拓本,收藏甚富。据查,赵氏居福州为稼孙至少刻五印,即“魏锡曾收集模拓之记”“魏锡曾”“魏稼孙”“锡曾审定”“生后康成四日”。清同治二年(1863年),以魏氏为媒介,赵之谦和吴让之以印谱序跋为阵地进行了一场印学审美取向的讨论,即印学理论史上著名的“巧拙论辩”。赵氏篆刻艺术的特殊性归结为三方面:“入印文字取资广、范围大;刻印的随意性;感情的流露”。赵之谦居福州八个月,福州印坛来了一位思想导师。对于保守的福州印人而言,赵之谦篆刻的三点特殊性过于激烈。福州印坛在赵之谦入住前以“印从书出”为主,而他的到来把全新的视角“印外求印”引入。并且将“拙”的审美趣味及浙派后期以“拙”为表象的“巧”进行学术辩析。这些话题还应该会更全面、更彻底,也因此将福州印坛带入新维度。
浙江现代印学大家赵叔孺(1874-1945年)曾任福州、平潭海防同知,兴化府通判,福州、泉州华洋同知,前后居闽14年。其岳父林颖叔(1809-1885年),福州名士,家藏法书、名画、玺印、金石、古器甚富。叔孺居林家遍观所藏精品,目力递增,古物之真伪,常一语中的。其书擅四体,行楷出入赵子昂,魏碑篆书则拟赵之谦,又兼精篆刻。赵叔孺承浙江鄞县赵氏、福州林氏两家余烈,收藏极为丰富。沙孟海评述赵叔孺:“他的篆刻,继承汪关的传统,最擅长圆朱文及朱白文小玺。他的圆朱文,端严大方,基本上用元、明以来细朱旧法,偶然也参以邓石如、赵之谦的新体。用笔光整坚挺,精到之作,往往突过前人”。[1]周律之提出赵叔孺篆刻艺术四点总结:“一、刀笔端庄淳厚,神韵安详俊雅,章法优游从容;二、仿古玺、汉印,深得古人神髓。尤其是战国朱文小玺,古秀劲逸,错落自然;三、仿宋元圆朱文,真乃专精独到……神完韵足,珠圆玉润,雍容大方;四、观赵氏篆、楷书法,多导源于悲盦,故其篆刻受影响也很深”。[2]
赵叔孺在到福州前即模仿赵之谦,其边款亦有“仿吾家扌爲叔”可以证实。赵叔孺1897年入闽,已有《二弩精舍藏印》(1896年)问世,其时篆刻纯属浙派韵味,可见早期对西泠诸子心向往之,但从容含蓄不染锋芒毕露习气。离开福州时的赵叔孺正处于他艺术的中期阶段,《二弩精舍印赏》八卷1909年谱成。不论在仿秦拟汉,摹宋元方面都已形成自己静润稳健的特色。赵叔孺此时的印风所发出的渊穆雅洁似乎是对时流林兰沧、陈寿伯碎刀锋芒毕露的矫正。也恰恰是对许容、林皋的一次回首再出发。
林承弼(1866-1946年),字兰沧,署铁梅居士。福州人。《近代印人录》评价他:“能书草隶,能画花鸟。当时,吾闽印风,皆相沿林雨苍一派。逮赵扌爲叔、傅节子避地来居,始有人作浙派。嗣兰沧起,初摹完白,继则专抚徐三庚。以让头舒足为能事,名盛一时。又善作重台双钩,盖失之纤巧,至有人议。其后有《铁梅居士印谱》。”吴昌硕曾称为闽派之祖也。有《铁梅居士印存》三十二册及《砖瓦集锦》《陶庐剩墨》《铁梅题画》行世。观其印存,有浙派韵致,但多数印作含蓄不足,习气毕现。
陈宗烈(寿伯),一位不为世人熟知的福州近现代印人。陈寿伯生平资料不甚详尽,设石肆,善治印,宗浙派。自辑刻印而成《石湖渔隐篆刻》。王敦化《印谱知见传本书目》载《石湖渔隐印稿》为四册本。傅节子、丁文蔚游宦入闽时语以浙、皖印派,其乃变旧作,力追西泠诸老。一时画家周愈、何振岱、陈械等所用之印,多出其手刻。从印谱中可知陈氏钻研浙派刀法颇为自如,于铁线篆最有心得。他是福州人深研浙皖之典范,只是他的朱文略失纤巧。
陈寿伯、林兰沧印风偏重于铁线篆。赵叔孺系统偏重于圆朱文;小篆细朱文印,风格精工秀雅,宜用于鉴藏印、斋馆印、别号印、闲适句印等。赵叔孺早年学浙派碎刀法,通过赵之谦直追邓石如、吴让之,汪关,宋、元,秦汉,用刀也随之转化,只是渊雅和平、精谨蕴藉成为他一生的守则。陈寿伯、林兰沧传续浙派后劲徐三庚的布篆法,加上赵之谦碑帖融合的篆书样式,灵活运用碎刀斩斫。陈寿伯佳作秀挺绰约饶有古风;林兰沧精品坚挺劲逸不忘锋芒。此三位印人的美学倾向大致成为20世纪初叶福州印坛最有影响的力量。
1928年徐悲鸿写给陈子奋的信中,直抒其对陈子奋篆刻成就的肯定:“足下于印,固无所不可……当代印人,精巧若寿石工,奇岸若齐白石,典丽则乔大壮,文秀若铁瘦铁、丁佛言、汤临泽等,亦时有精作,而雄浑则无过于兄者。”[3]同处福州的书法家潘主兰为《陈子奋印谱》撰写的序中,从描述其篆刻成长的历程入手,着重突出其对篆刻印风的把控,强调陈子奋成与法、而不为法所困,并能开拓福建一带印风的中肯评述:“闽中言治印者,莫不知有陈子奋先生。陈子之治印,既通六书,更博览周、奏、汉、魏金石文字,至若皖、浙名家曾涉而猎之。生平尤心折让之、仓石,指腕流露,则让之之意为多。奏刀历数十年,无间寒暑。案头石累累,不旬日间,积稿辄盈寸。资之深,故成也大。闽之中,篆刻家或有未能出其右。顾前此风会未开,而陈子开之;后此时流屡变,而陈子亦无不变之。唯蕴于中原,发为纷华、为奇崛、为典重,皆随变所适。因知艺之至,初必以法,而底于无法,然非无法,法一而变多,遂臻幻境。暮年往往创新意,大胆用简体字刻烈士名言,人益以是争宝之。”[4]今天看来,这样的论断其实并未超越赵之谦“印外求印”的立论范畴。当然,陈子奋在个人风格上的左冲右突并未影响他的学术继承与判断。另外,陈子奋在边款行书体例上保存学习赵之谦的影子,且同样追随赵氏使用切刀,并能使刀如笔,从容圆转、意味隽永。陈子奋对文字结体及组构的敏锐程度颇高,也流露出对印学史上不同门派及高古印的涉猎尤勤,时常收集各家篆字以助创作之用,并能随心所欲制作各类布篆、边栏模式,其对印学资源的留心搜索可谓勤思敏求。
潘主兰诗、书、画、印四绝。其深刻之人文素养加之处世淡定的人生观给后学留下感人至深的精神财富。潘氏印篆边款一任简约平实,由此可知刀功亦如是;然而潘氏对文字学颇为精通,布篆上充分体现平和蕴蓄后又不失疏宕清逸。孙慰祖评价潘主兰:“既有黄牧甫质直宁静之基调,复介入灵动外拓之形神。乃能于平和中见生气,方劲中寓圆活,简洁中藏机敏,明快中蕴含蓄。印中颇有简化字,盖以为笔墨当随时代也。”[5]
谢义耕篆刻主张书从印入,印从篆出;有笔法则章法自然至;点画方圆,变化万千。刀法冲切兼用,随形下刃,以意领刀。谢氏篆书得力于《绎山》《纪功》诸秦汉石刻,印风追慕典雅朴茂之秦玺汉印,至老弥坚。
周哲文勤奋过人,表现在多字印的创作上,刻功的超级稳定为爽朗遒劲的印风提供保障。颜其居曰“百炼成钢之楼”。唐吟方认为周哲文真正名声大振的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依靠一系列专题性印章的创作广为印坛所知。奇怪的是,这位扎根于福州的老辈印人,是福州印坛上唯一对本地未构成任何实质性影响的一位。林公武先生却认为周哲文的篆刻样式保留了明清福州传统印风中某些特点,这一说法的深层含义在于周氏对说文篆和缪篆的秦汉印经典传承,特别是明清福州印人的秦汉印改造样式,一如林霔、黄鹓等人的篆刻路数。
林健自述:“余十五学印,喜吴昌硕、齐白石诸家。长者胡孟玺告之,应取法秦、汉,并承黄曾樾先生为借《十钟山房印举》,当时年幼不能会心。三十以后,稍稍有悟,以至今日。谈印亦谓,不学秦、汉者,则不登大雅之堂。信乎,长者之言不诬也。”林氏早期从事中医,深暗阴阳相反相生之理。其线条造型每以倾欹、粗细以破光洁平正,擅长曲线安排以洋溢率真、雄肆。其师陈子奋赠刻砚铭曰:“胆大如海,腕旋如天。一以贯之,亦圆亦妍。”林氏罗列钩摹三代两汉文字而编《补砚斋集篆刻文字类编》,可见其对篆刻文字造型的深刻思考。这种对篆字形态长年累月的收集是古往今来印人的案头功夫,甚至是秘笈所在,林氏有此工作,石开也有,他们这一习惯皆有赖贤师陈子奋的榜样所致。他与前贤同侪不同的特点还在于书法,印面文字、布篆,边款均能高度一致,这一特征在篆刻界尤其难得。
石开(1951-),福州人,篆刻师从谢义耕、陈子奋,遍学古玺、汉印及黄小松、吴让之、吴昌硕、黄牧甫诸家,于汉官印及封泥得力最多。1983年上海《书法》杂志开展的全国篆刻征稿比赛中,石开获一等奖。扬名之后的石开行迹幽古,往往于无声处听惊雷,大有开一代风气执牛耳的自信。其印八九十年代呈现诡异清灵、松散逍遥的作派。90年代后期以来的印面格调由清朗而入混沌,刀法上也由明快的冲刀改为披削浅行,唯求冲淡朴茂、平中寓奇、重在写心的样式不禁使人联想到赵之谦所斥之浙派后期那种“小巧”。印篆杂揉泥封、诏版、瓦当、将军急就章、陶文等非经典文字讯息,运用唐宋官印盘条的冗长曲度整合印面,而且石开不断在白文印文之外吸取吴昌硕铲底的方式,以创设苍茫的意象;朱文印则让线性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