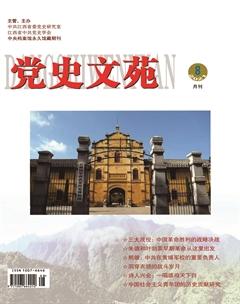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张太雷
徐安琪

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的张太雷,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做了大量工作。他不仅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形成,还以笔为枪撰文醒世,并敢于与蒋介石公开论战。他耕耘不辍、战斗不息,他的事迹值得后世铭记。
“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这句惊世骇俗的话,出自一位22岁青年的家书中。此时的他,正要前往苏联,成为中共派往共产国际的使者。信中他给妻子写道:“我们现在的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所以你不必以为是一件可忧的事。”这位青年名叫张太雷,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共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位使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先驱和青年运动的领导人,他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也是广州起义的组织者、领导者。他与瞿秋白、恽代英并称为中共“常州三杰”。
张太雷1898年6月17日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少年时代,他就对底层人民富有同情心。辛亥革命时,他带头剪掉了辫子,并阅读各种进步报刊。1915年秋他考入北京大学法科预科,同年冬转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法律系学习,半工半读。五四运动期间,他是天津地区爱国运动的骨干分子。1920年3月,他参加了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加入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战士之一。1921年,他成为中共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位使者,积极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他当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
张太雷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最早的推动者之一,他推动团结、宣传真理、鞭笞腐恶、关注青年、领导罢工……国共合作破裂后,危难关头,他被委以重任,参与领导发动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2日,在指挥战斗时遭敌伏击牺牲,时年29岁。
张太雷原名张曾让,字泰来,还用过春木、椿年等名,他最后改名为太雷,就是表达要把自己化作巨雷以冲破旧社会的反动统治的抱负。这是他作为一名党员的初心。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张太雷,确如他的名字所示,像一声惊雷,震慑着腐恶、催动着光明。
大力推动国共合作
1920年,共产国际就派维经斯基会见孙中山,双方进行了第一次接触。1921年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于广西桂林会见孙中山。双方探讨了国民党与俄国建立联盟及国共合作的可能性。担任翻译的张太雷,积极帮助马林与孙中山沟通,拉近他们的距离,成为他们得力的助手。孙中山还专门同张太雷讨论了如何动员青年的问题。
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离开广东。此时广东地区的共产党人陈公博、谭植棠等偏袒陈炯明。张太雷受命于中共中央,力争扭转陈公博等的立场,但未能成功。中共中央决定开除陈公博党籍,处分谭植棠。孙中山抵达上海后,更加感到了与中共合作的必要性,立即赞成国共合作。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在杭州西湖边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专门商讨与国民党联合的问题。除陈独秀、李大钊等5位中央委员参加外,马林和张太雷也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进行了激烈辩论。张太雷分享了陪同马林参加桂林会议的亲身体会,肯定了孙中山的表现,积极主张国共合作。经过讨论后,会议原则上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会后,张太雷加入了国民党,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干事。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张太雷仍担任马林的翻译。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和国民党合作,包括产业工人在内的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但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
此后,张太雷作为孙中山派出的国共合作代表之一,在莫斯科拜访了苏联党、政、军领导人,签署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党的援助协议。
中共决定与国民党合作,但又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在当时的历史关头,是非常正确的战略决策。张太雷以自己的角色,积极推动了这一决策的实现。
以笔为枪撰文醒世
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张太雷在《民国日报》《向导》《团刊》《中国青年》《人民周刊》《政治周报》《革命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他鞭笞军阀的腐恶,揭露帝国主义的罪孽,剖析国民党的问题,为工农运动呐喊,为革命前途探路。国共关系趋于紧张后,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部长的张太雷更是敢于亮剑、以笔为槍。
张太雷对北方军阀与各帝国主义势力的勾结有着清醒认识。他在1923年5月写的《奉直战争和日本与英美的利益冲突》指出:“中国所以不统一就因为列强的对华利益不统一,各要扶助一派以植自己的势力;而列强的利益终无统一之时,所以中国亦无统一之日。只有第三方面,就是中国平民自己起来把两种势力——军阀和列强——都推倒,方才能有统一。”在帝国主义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大城市市民的社会心理也发生着微妙变化。张太雷敏锐注意到这一点。他在《乞丐嘴里的上海社会资本主义化》中指出:“你在夜间在上海马路走,常常可以遇见乞丐来恭维你,他不说你‘生个儿子中状元’,他说‘先生,生个儿子做刚八度(洋行买办)’。乞丐这种话是要讨你好的,当然是要迎合对方面的心理;可见上海社会的心理已都是做刚八度的心理,上海社会的心理已早资本主义化了。”他的文风明白晓畅、深入浅出,常能针砭时弊。
张太雷对国民党的性质有着犀利而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政党的生命力在于民众,脱离民众,政党必然要垮台。在写于1923年6月的《羞见国民的中国国民党》中,他指出:“国民党应当是国民的党,是领导国民群众的政党。”“中国国民党辛亥革命以来十二年的奋斗一无所成,因为他完全和国民断绝关系,而只知道和军人政客交际。无怪乎国民不愿认国民党为他们的党,实际上国民党没有做他对于国民应做的事情,没有和国民接近,没有尽一点鼓起国民精神的责任。”“如果大家不相接近,愈离愈远,那末国民党将变成无国民的政党。”“如果国民党能把以前错误的政策改过来,注重于国民群众运动,注重于国民的宣传,国民非特如现时的怕惧国民党将欢迎之不暇。”
张太雷关心民众运动。知识分子出身的他,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中,感受到了工农的力量。1920年,他就在天津公开出版了面向工人的《劳报》。1925年,他积极参加并领导了省港大罢工。《“二七”之意义》发表于二七大罢工三周年的1926年2月7日。张太雷写道:“二七运动最先表示中国民族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为争人民的自由,京汉路工人是先锋。在这个运动当中,可看出工人阶级的团结力。”“在这运动中可看出工人阶级的牺牲精神。工人都有至死不屈的精神。”
关于农民运动,张太雷指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在写于1926年双十节的《今年纪念双十节之意义》中,他分析道:“辛亥革命没有解决或提出解决人民生活的问题;革命不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不是真正革命。辛亥革命唯一的口号就是排满,至于孙中山先生解决土地问题的口号完全被藏匿而未提出……人民在清朝之下受压迫,如果在清朝去掉后仍旧受压迫,那末,这革命对于人民有何关系呢?又如何能得人民的拥护呢?”他进一步指出:“在中国现在的人民生活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中国主要的生产者是农民,而中国的农民,无论他是自耕农,或佃农,每年由他劳力所生产的物品中,只有百分之五十以下是自己享受的,其余百分之五十以上是被地主,绅士,官僚,军阀,帝国主义共同瓜分了去……辛亥革命想在这封建制度上建筑一近代的民主共和,当然牛头不对马面。辛亥革命所以没有能产生一真正的共和而产生了一个军阀的专制。如果现在中国的土地问题不解决,就是说如果农民不得到解放,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他公开表达了共产党人的立场。
张太雷有着很强的宣传能力,也乐于接近群众。他曾说:“笔杆子和舌头是我们革命者政治斗争的武器,应该不断地运用,不写不讲是不对的!在这个时候,群众是多么希望我们写和讲啊!”
为青年事业而奋斗
作为中国青年运动的先驱,张太雷对青年问题情有独钟。1923年8月,他担任团中央创办的刊物《中国青年》的主编。10月,他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当选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会后又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1925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张太雷担任团中央总书记。但由于他后来又要赴广州担任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该职务便改由其他人担任了。大革命期间,张太雷多次就青年问题撰文。
1924年1月,列宁逝世。张太雷在《中国青年》发表《列宁与中国青年》一文,写道:“列宁同着俄国革命把中国青年革命的觉悟惊醒了……就是中国的青年学生,但他们抛弃了他们的先师孔子的时刻,他们正找着了列宁做他们思想上的指导者……列宁死了!但是在中国青年的心目中活着!”表达了中国青年对革命导师列宁的缅怀和继续战斗的意志。
1925年1月,他在《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的学生》一文中指出:青年学生“终归是智识阶级”,其中一部分是容易动摇的,如“二月革命后的俄国学生,和中国五四运动后的学生领袖;或因达到他们自身的目的而满足,或因防卫自身优越地位,而甘做反革命运动”。他还强调,青年运动的出路,在于与工农相结合。青年学生应当认识到,没有农民工人的参加,国民运动是没有希望的。
对于自己曾经参与的五四运动,1925年5月他曾撰文《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分析道:“由于中国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学生感受的压迫及大战后世界革命潮流的激荡而发生革命的要求”,是五四运动的动因之一。然而,“五四运动的主要成分是没有独立经济地位的学生,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太幼稚与软弱,没有维持这运动的力量,而中国劳动群众在那时参加的又甚少”。“五四运动没有组织,没有组织的意思就是没有政党领袖,一个群众运动没有有主义的政党领袖,他既不可能走入正轨,亦更不能继续发展。”他认为,青年运动具有必然性,但也具有软弱性,必须在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才能步入正轨。
在发表于1926年5月的《五卅运动之分析及纪念之意义》一文中,张太雷指出:“五卅运动开始的时候,全国学生是一致参加的,但是事后因为学生是反映社会各阶级的,五卅运动分化,因之学生中先后有退出此运动的,有继续与劳动群众坚持到底的。”“第一,学生的群众不能看他是一个整个的,所以对于学生的革命性不能有一律的评定。第二,学生群众是反映各阶级的,所以革命性是参差不齐的。”他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待青年学生,抓住了问题的症结。
今天的共青团员们不应该忘记这位青年运动的先驱。实际上,这位青年运动的领导者、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自己也是一位青年。这些富有思想力量的文字,都出自二十几岁的他!
与蒋介石针锋相对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此后国民党右派加紧了夺取革命领导权和反共的活动。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阴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意在排挤共产党人,打击国民党左派。面对暗潮涌动、日益紧张的国共关系,张太雷数次撰文分析时局、声明立场。
1926年6月10日,他发表了《到底要不要国民党》一文。文中尖锐指出:“中山先生这一种造党的决心自始就被党内反动派所反对,因为这是违反他们私人升官发财的利益,并且违反他们阶级利益,他们啸喊着三民主义,其实他们是反对民族主义的,因为帝国主义于他们是有利益,所以是他们所爱护的,他们是反对民权主义的,因为他们是要卖身与军阀,他们是反对民生主义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剥削民众重困民生的。”“共产分子表示并没有霸占国民党的心,如果国民党要共产分子退出,只要有正式的决议,我个人推想共产分子决没有硬赖着不肯走的道理。”
这篇文章戳中了蒋介石的要害,蒋怀恨在心。6月28日,蒋在黄埔军校的纪念周上对学生讲话时,声色俱厉地大肆攻击张太雷的文章,说“妨碍国共合作的话要少讲”,还威胁说“引起两党的恶感是不行的”。
8月12日,張太雷撰文《关于蒋介石同志对“要不要国民党”误会之解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应。他指出:“最先我要声明的就是:我做那篇文章的动机决没有要‘使两党生起恶来’,我做那篇文章的动机在那篇文章里说得很清楚:‘我们决不能看着国民党被人毁坏而一方面仍旧高喊国民党万岁。’”他还指出:“共产分子问题是政策问题,不是组织问题,不是一个党员人数的问题而是左派或右派在党内掌权的问题。这是我做那篇文章的观点。对于我这观点批评对与不对是可以的,如果介石同志加我以轻侮国民党的罪名我是绝对不敢承受的。”张太雷不畏强权、有理有据,展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品格。
8月20日,他撰写了《廖仲恺——国民党的左派模范》一文,高度评价了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先生的立场和贡献。文中指出:“如果要做一个真正的左派,你一定依照廖先生的言行,除掉你信仰孙文主义及打倒军阀帝国主义外,你必定要分辨反革命派与革命派,认清敌和友,一定要确实团结革命派以打倒反革命派,一定要把这革命派的团结建筑于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之上,一定要实际参加与帮助工农及一般群众运动。”
1926年年底,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为抗议蒋介石,给鲍罗廷举行了盛大欢迎会。会上,鲍罗廷揭露了蒋介石违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反动罪行。张太雷翻译时,说到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包括在江西屠杀农民、工人和共产党人时,声泪俱下。讲完话后,全场观众掌声雷动,完全为他翻译的内容所感动。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员倒在反革命枪口下。4月27日,中共在汉口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太雷在会议上坚决支持瞿秋白、毛泽东等提出的支持工农运动、与国民党右派斗争的主张,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在革命危急的关头,张太雷根据党的指示,担任广东省委书记,赴广州领导革命工作。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
尽管广州起义时正处于革命低潮,但这是中共英勇反击反动派的一次伟大尝试,它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道成为中共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新起点。张太雷用他可歌可泣的一生,践行着自己入党的初衷,耕耘不辍、战斗不息。
责任编辑 / 陈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