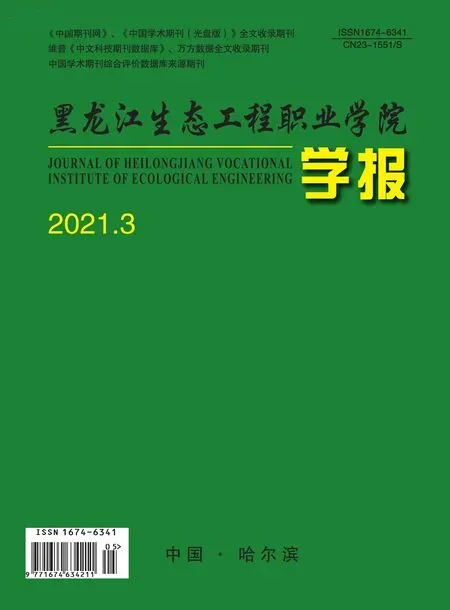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
李钢 王琪
(山东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山东 青岛 266590)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1956年起源于美国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暑期会议上,由约翰·麦卡锡首次提出。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发展,人工智能逐渐在新闻、音乐、绘画、诗作等方面大放异彩,表现出超出人类能力的强大功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具有不确定性,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法律关系、道德伦理、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新挑战。①出于人们对“数据世界”的需求已经发展到对“知识世界”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人工智能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大量的人工智能生成物被广泛运用,随之而来的是这些生成物的属性、归属等问题和争议。目前,一部分国家已经通过立法确认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一些国家也已开始着手保护人工智能创作的小说、音乐等知识产权。而我国目前并未对人工智能的相关法律问题作出相关规定。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来说,由于其是由人工智能产生而非“人”创作产生的特点,使得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内容属性和权利归属难以判断,明确其内容属性和权利归属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可版权性和著作权法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1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定性
目前人工智能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它是一种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新的技术科学。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需要结合其本身特点以及著作权法中作品的客观构成要件来探讨其内容属性。
人工智能生成物与纯由人类所创作的作品的区别主要在于:人工智能本身就是著作权法中的权利客体,而人工智能生成物从其产生过程来看则变成了客体的客体。在我国《著作权法》中,除特别规定,作者只能是自然人,作为本身属于权利客体的人工智能,其“创作”行为就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作者”的“创作”,于是人工智能生成物也将无法进行权利归属。因此有些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权利归属中的作者体系是与法理相违背的,是将私法体系中的权利客体和权利主体混为一谈,②人工智能生成物不能构成著作权法中的作品。然而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内容属性定性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归属其实是两个问题,是需要区别看待的。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内容定性是探讨其是否可以作为著作权法的著作权客体,也就是探讨其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继而再去讨论人工智能生成物权利归属的问题。
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③我国《著作权法》通过列举法列举了作品的具体类型,根据作品的一般定义和具体的列举条款,著作权的客体一般具备以下条件:(1)是通常意义上的作品,即“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的一种表达形式;(2)具有独创性;(3)能以有形形式复制。④如果人工智能生成物满足著作权客体的客观构成要件则应当认定人工智能生成物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可以被称为人工智能智力成果的。人工智能是对人的意思、思维的信息过程的模拟,它并不是人的智能,它是可以超过人的智能的。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的本质是应用“人”的“智能”,但是人工智能生成物不是作品。⑤本文认为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将人工智能认为是“人”的“智能”是不合理的,其实质是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等同了。人工智能不等于人类智能,对于人工智能应当从“人工”和“智能”两个方面理解,“人工”指的是人工系统,是指人类加工改造的自然系统或人类借助系统创造出的新系统,比如计算机系统。“智能”可以是意识、思维等,通常认为,自然人具备“智能”,而在科技迅速发展的现代,尤其我国著作权法已经规定了法人也可以创作作品,享有著作权利的现状下,仅仅认为“智能”是自然人的能力是不合理的,人工智能的“智能”已经是可以超出人类智能的了,是强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已经从早期仅能“推理”的弱人工智能时代逐渐发展到可以“深度学习”的强人工智能时代了,是可以脱离人的智能或者说通过人工智能本身自我开发智能。因此,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可以被称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智力成果的。
一件创作物是否构成作品最重要的就是判断其是否具有独创性。虽然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版权制度有很大不同,但是都将独创性作为认定作品的实质性要件。在我国的版权制度中,独创性这个概念并不明确,但对独创性的判断一般至少需要两个方面的要求:(1)独立创作;(2)创作的结果具有最低限度的创造性。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内容属性的判断也应当从这两个方面来考查。有学者认为,即使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与人类所创作的作品类似,但仍需要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生产过程来判断是否是作品。⑥然而,《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创作的表达,不保护创作者的思想以及创作者的创作过程。因此,以创作物的生产过程去判断是否构成作品的做法本身是不恰当和不合理的。《著作权法》只能依据展现在外的表达判断是否具有独创性,无法察知创作者的真实意图和想法,作者是如何把作品创作出来,更不是《著作权法》调整的范围。⑦《著作权法》保护的是结果,是作品的表达,对作品的判断并不需要参考其生产过程。判断创作物是否构成作品应当从作品的客观构成要件入手,而作品的客观构成要件并不包含创作物的生产过程,只要最终产生的结果符合作品的三个构成要件,具有独创性,就可以认定其为作品,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和调整。
由此,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属性的判断应当坚持客观标准,如符合《著作权法》中作品的客观构成要件,符合“独创性”,就应当判断其为作品,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国内也有许多学者持此观点。吴汉东教授认为,将人工智能作为拟制之人以享有法律主体资格,在法理上尚有斟榷之处,但是人工智能生成之内容,只要是由机器人独立完成,即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⑧易继明教授认为,应该坚持客观标准来判断人工智能的独创性,达到了具有“独创性”的标准,就是《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⑨
2 有关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权利归属的观点
人工智能逐渐渗入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工智能生成物也越来越多。美联社的机器人“作者”Wordsmith每季度可以写作300篇企业财报;腾讯财经的自动化新闻写作机器人Dreamwriter在财经、体育、证券、科技等多个领域进行实时播报和写作;轰动一时的微软小冰,2017 年出版了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2018 年又发布了新歌《我知我新》。如果人工智能生成物被认定为《著作权法》上的作品,那么明确其权利归属就显得尤为重要,否则,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无主作品”“孤儿作品”,不利于社会的创新发展。目前学术界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归属争议较大,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2.1 人工智能法律人格说
“人工智能法律人格说”认为人工智能具有法律人格,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新的法律主体,能够享有著作权利。然而目前并没有任何法律来支持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身份。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具有高度的智慧性与独立的行为决策能力,在现实条件下,人工智能是具有智慧工具性质又可作出独立意思表示的特殊主体。⑩因此,作为特殊主体的人工智能可以享有其创作的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著作权利。虽然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只是自然人可以享有著作权法,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作为拟制的法律人也是特殊的权利主体。而与拟制的法律人不同的是,人工智能本身是作为一种权利客体,是人工智能著作权人的作品,如果将其定义为具有法律人格的民事主体,那么将会违背我国民法中权利主客体之间禁止转换的原则,对我国的《著作权法》和民法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挑战,这是人工智能法律人格说的最难解决和最难回答的问题。
2.2 人工智能编程设计者说
“人工智能编程设计者说”主张人工智能的编程设计者对人工智能的模板、规则等作出了主要和决定性的贡献,因而其所产生的生成物构成作品也是由于编程的结果,体现了编程设计者的主要创造性的表达,因此应当由人工智能的编程设计者享有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权。虽然将著作权归于人工智能的编程设计者将会激励编程设计者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对于人工智能作品以著作权保护的意义并不是很大。将人工智能生成物定义为作品并以著作权法加以保护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创作和维护利益平衡,如果将其著作权归于人工智能的编程设计者,则忽略了人工智能本身可以进行“深度学习”独立进行创作。将权力归于编程设计者仅仅是保护了将人工智能作为辅助工具进行创作的编程设计者“人”的创作,而编程设计者预先设定的程序和模板规则并不能对其作品的产生起到决定和唯一的作用,也即两者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同时编程设计者已经就人工智能程序本身享有排他的著作权利,如果再将人工智能作品的权利归属于编程设计者,则会出现重复奖励,不利于我国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发展,也不利于实现利益平衡的立法目的,不利于激励创新和创作。
2.3 人工智能所有者说与人工智能操作者说
将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权归于所有者和将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权归于人工智能的操作者这两种观点是根据创作意志的体现来区分的。“所有者说”认为人工智能的创作是由于所有者早期对数据的选择和安排,体现了所有者的创作意志,应当将著作权归于所有者。机器人无法像自然人一样对其作品行使权利,因此,著作权应当归属于机器人的创造者或所有人。同时将其归于所有者有利于人工智能市场的发展和创新,并且符合民法保护所有人的理念和原则。而“操作者说”认为对人工智能的创作作出实质性的贡献的是操作者,人工智能的实际操作者在对输入人工智能的数据、信息等进行选择、优化、编排的过程中,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创造性。“所有者说”观点实际混淆了人工智能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在实际中,人工智能的使用者不一定是人工智能的所有者,而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产生一般是由使用者来操控人工智能系统,触发系统规则的运行,因此人工智能生成物应该更能体现使用者的创作意志。但是这两种学说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都将人工智能作为一种辅助工具,忽略了人工智能的“智能”,将创作意志仅仅归于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实际上也是混淆了“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通过是所有者还是使用者来操控这个工具创作的作品,从而确定作品体现的是哪方的意志,来判断其“作者”是谁,继而将著作权归于哪一方,忽略了在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的现代,人工智能将不会只是一个工具。同时,由于实际现实中所有者和使用者的不一致,将著作权归属于其中一方,都将是对于另一方贡献的忽视和不公平,利益分配的不公平实际就是权利分配的不公平。
2.4 社会公共领域说
著作权法寻求的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平衡,尤其是作者或著作权人的利益与作品使用者利益之间的平衡,著作权法在扩张著作权的保护的同时也在对公共领域、公共利益的扩张进行限制,比如对作品的保护期限的限制、合理使用制度等其他限制著作权的形式。而在人工智能时代难以确定权利主体时,将其归于社会公共领域将会解决这个问题。因此社会公共领域说主张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归于社会公共领域。这种观点的缺陷是如果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归于社会公共领域,那么就会造成“免费的午餐”现象,许多“作品”将被无限制地利用,不利于激励人工智能创作作品;不论是编程设计者、所有者还是使用者、投资者将失去人工智能创新创作的激情,人工智能的价值和意义就不能完全地实现,不利于社会创新。
3 人工智能生成作品权利归属的判断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除了特别规定,创作作品的自然人就是作品的著作权人。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权利归属难以确定就在于此,创作行为是由人工智能本身完成的,人工智能实际意义上并不能成为“自然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是无法将人工智能本身作为作者,从而也就无法自动产生著作权。但是如果认为人工智能具有法律人格,就可以直接认定人工智能本身是作者,这种做法实质上是扩大了民法的民事法律主体,不仅仅是对著作权法的挑战,也是对民法的挑战。在法律和道德伦理对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作出合理解释之前,只能在人工智能的编程设计者、使用者和所有者之间进行利益衡量,确定权利归属。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不同,表现出的能力不同,因此应当在不同的阶段分别确定权利归属。
按照人工智能法律人格说的观点,人工智能本身具有法律人格,可以作为著作权法中的作者,其所创作的作品便可权利归属于人工智能本身。对于这种观点许多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将人工智能作为权利主体赋予其法律人格是对我国著作权法和民法制度的冲击和挑战,不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同阶段的人工智能所体现的意志力和创造力是不同的,对于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法律人格需要重新审视。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是否可以作为作者与人工智能是否能够独立行使著作权利应该区分对待。
人工智能的发展逐渐从弱人工智能时代到强人工智能时代。在弱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只能根据系统的指令专注于完成特定的任务和目标,解决特定类的具体的问题和任务,是一个数据处理的辅助工具,不可能独立完成创作,因此不可能作为创作作品的作者,也就不能继续探讨其行使著作权利的问题。此时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作者便需要根据此作品创作过程中哪个主体作出了贡献以及贡献的大小来确定。在此过程中,编程的设计者、人工智能的使用者和人工智能的所有者都可能作出贡献,对于所创作的作品来说,某个主体的决定性贡献起着最主要和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判断作者主体时,要依据编程设计者、人工智能使用者和所有者的决定性贡献来决定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作者是谁。
在强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具备人类的认知能力和意志能力,有自觉和自我意识,其可利用自身足够的智能去解决所出现的问题。此时,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它本身便具有“思维”,可以独立创作作品,类比我国法律中“拟制的法律人”,强人工智能便可以具有拟制的法律人格,便可以作为作者身份存在。然而即便强人工智能存在拟制的法律人格,也可能无法像自然人一样行使自己的权利,著作权利的行使便需要另外讨论。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我国著作权法视为作者的规定,将人工智能视为作者,通过保护人工智能的所有者,由人工智能的所有者去享有著作权利,以此来保护人工智能作品。
因此,在判断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权利归属时,要对作者身份和权利行使区分讨论。对于人工智能是否可以作为作者,是对人工智能的性质下定义,即是否认为人工智能具有法律人格。如果认为人工智能具有法律人格,就可以直接认定人工智能本身是作者。其次,因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阶段不同,存在弱人工智能时代和强人工智能时代,在不同的阶段人工智能创作作品的能力不同,其确定权利归属的规则便不能一概而论。在弱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还不能完全自主意识完成创作,此时,人工智能仅仅是一种辅助工具,完全可以根据编程设计者、使用者和所有者在创作中所作出的贡献确定独立作者或者合作作者;如果是强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完全可以自主完成自我意志的创作作品,应当认为人工智能是作者,享有著作权利,但不能像自然人一样行使自己的权利,因此法律可以借鉴我国著作权法视为作者的规定,将人工智能视为作者,通过保护人工智能的所有者,由人工智能的所有者去享有著作权利,以此来保护人工智能作品。
4 结语
明确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内容属性和权利归属将有助于完善人工智能的法律制度,也有利于促进我国著作权法的完善。对人工智能生成物定性时,应当坚持客观标准,以《著作权法》中对作品的判断标准去定性;而对于人工智能生成作品权利归属的判断,也应当结合人工智能本身不同阶段的特性进行个别判断。人工智能技术还在快速发展的阶段,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也会逐渐被研究探讨,完善人工智能法律制度依旧是任重而道远。而不管是何问题,在研究时都应当坚持客观标准,将理论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结合人工智能本身的特点和实际应用来探讨其法律问题,继而完善人工智能的相关法律制度。
注释:
①腾讯研究院.网络法专报:全球互联网法律政策洞察[EB/OL].2019-3, https://www.sohu.com/a/312097934_455313,
(2020-10-13).
②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J].知识产权,2017(3).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
④崔国斌.著作权法原理与案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7.
⑤王迁.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J].法律科学,2017(5).
⑥同⑤.
⑦李伟民.人工智能智力成果在著作权法的正确定性:与王迁教授商榷[J].东方法学,2018(3).
⑧吴汉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5).
⑨易继明.人工智能创作物是作品吗? [J].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5).
⑩袁曾.人工智能有限法律人格审视[J].东方法学,20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