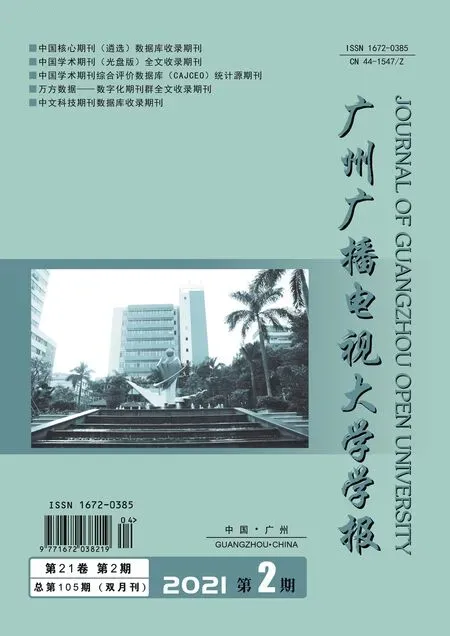《诗经》弃妇诗近十年研究综述
赵 鑫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弃妇是指婚后不受丈夫宠爱而被逐出家门的女性,她们被抛弃之后,无论是在母家,还是在社会中都处于一种不利地位,其命运结局多是悲苦不幸的,因此便创作诗歌以抒发忧郁悲伤的情绪,控诉丈夫的残暴无情。
有关《诗经》弃妇主题的研究著作颇多,研究者大多围绕诗中的人物形象展开论述,对弃妇被困的原因、弃妇诗的文学价值、流变与现实意义进行讨论。近十年来有关《诗经》弃妇主题的研究文章层出不穷,内容丰富且具体,体现了作者较高的研究水准,但是仍有开拓补充的空间。本文对近十年有关《诗经》弃妇诗的研究著作进行了综合性的分类探讨,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下一步深入研究作铺垫。
一、《诗经》弃妇诗分类考述
对《诗经》中的弃妇诗进行准确界定是进行科学研究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近十年来,学术界仅有尚永亮先生对《诗经》中的弃妇诗作了缜密严谨的分类考述。尚永亮《<诗经>弃妇诗分类考述》[1]对《诗经》中11首疑似弃妇诗的作品作了考述分析,并将其分为三类:一是《氓》《邶风·谷风》《中谷有蓷》《白华》《江有汜》,这五首作品中都有涉及夫妻关系以及妇人被弃的描写,可以确定为弃妇之作;二是《遵大路》《日月》《终风》《我行其野》《小雅·谷风》诸诗,从文本、后世评论和相关史实诸方面来看,都不尽符合已婚或离开夫家这两个构成弃妇的基本条件,故均不宜列入弃妇诗之列。三是《邶风·柏舟》,因“不得于其夫”和“仁而不遇”两种观点均来源甚早,且从史实和文本上也较难寻觅确证,因此可将其视为“是非得失未易决”的多义之作。
尚永亮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将古今学者对这11首诗歌的评析进行了分类整理,并以表格的形式呈现,使人一目了然,最后又分别对这11篇诗歌的文本内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以确证其上述观点。
《<诗经>弃妇诗分类考述》虽然是对《诗经》弃妇诗进行界定的孤篇之作,但它在此研究领域中却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只有对《诗经》弃妇诗的范围进行准确的界定,才能对弃妇诗作出科学合理的研究。尚先生的这篇大作,无疑为今后从事《诗经》弃妇诗的研究扫除了障碍,具有灯塔指明之作用。
二、《诗经》弃妇被困之因探究
《诗经》中的弃妇多是善良温婉、勤俭持家的形象,她们本身并无过错,之所以沦落到被丈夫休回母家的悲惨结局,其部分原因是受当时社会环境与男子见异思迁劣根性的影响。
马进宝《试论〈诗经〉中弃妇诗产生的原因》[2]一文专门对弃妇被困的原因作了分析,他指出:经济地位的变化是弃妇诗产生的根本原因;媵妾制婚姻是弃妇诗产生的直接原因;礼法制度的束缚是弃妇诗产生的主要原因;社会风气的日渐衰退是弃妇诗产生的重要原因;人性本身的弱点是弃妇诗产生的客观原因。具体阐释如下:第一,因为生产力水平的进步,男子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他们开始走向社会,接触更广阔的天地,而女性的活动范围则被局限在家庭之中,从事的多是辅助性劳动,成为男子的附属品。第二,媵妾制是西周乃至春秋时期盛行的一种婚姻形式,在这种不平等的婚姻形式中,多名女性共侍一夫的现象就决定了女性低于男子、不受尊重的地位。第三,当时女性的一系列行为举止都要受到礼仪制约,使她们无法做出超乎社会局限的行为,以摆脱这种不幸的陷阱。第四,西周末年礼崩乐坏,王公贵族贪图享乐,社会风气荒淫昏暗,使人心浮躁,因此喜新厌旧、忘恩负义已成为当时社会上男子的通病。第五,喜爱美色是当时男性的固有弱点,而当女子一旦容颜不再,失去固宠竞争力时,必然会被男子无情地抛开。丁晓俊《悲剧中的自我崛起——我看<诗经>弃妇诗中的女性自我意识》[3]还提到女性的知识缺乏这一原因,她们未曾思考过自身的价值,也未曾想学习一门技艺,一旦被丈夫抛弃之后就成为社会中的边缘人物。其他研究性文章也对弃妇被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但观点结论未超出以上六点。
三、《诗经》弃妇诗的文学价值
(一)人物形象
《诗经》包含十一首疑似弃妇诗的作品,其中呈现了不同风貌的弃妇形象。因其形象鲜明,且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故深受研究者的喜爱与关注。任娟、贺梅梅《<诗经>中弃妇的人格风貌初探》[4]、闫晓妮《论<诗经>中的弃妇形象》[5]、李千慧《析<诗经>中的弃妇形象及其产生原因》[6]、鲜小霞《论<诗经>中的“弃妇诗”》[7]等文章,以及陈文月的硕士论文《<诗经>弃妇诗研究》[8],都对《诗经》中的弃妇形象作了细致的分析,并将其作了归纳分类。
任娟、贺梅梅将《诗经》中的弃妇划分为三类:勇敢决绝、睿智刚强型;痴恋多情、性善心软型;忧生嗟叹、悲哀自悼型。闫晓妮将其分为四类:贤良勤勉、含辛茹苦型;悲伤哀怨、孤凄忿恨型;无限留恋、难以决裂型;以己为鉴、不屈果决型。李千慧的分类简明准确,将其划分为决绝型、哀怨型、矛盾型、无能型。鲜小霞将其分为两类:刚强睿智的弃妇形象、善良软弱的妇女形象。陈文月将其划分为三类:勤俭持家、温婉善良型;哀怨自伤、恋恋不舍型;刚烈愤慨、勇敢决绝型。通过比较分析可知,研究者是以弃妇对待爱情的性格态度作为划分标准的。
在上述分类中,笔者更推崇鲜小霞的观点,这种分类最为直观且简洁。在面对不幸的爱情婚姻生活时,《诗经》中的女性明显表现出两种态度:坚强勇敢或善良柔弱。如《氓》中的女主人公,当面临丈夫变心的境遇时,虽然也会悲怆,但令人佩服的是她能够保持清醒理性的头脑,认识到“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这种思想理念不仅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与深刻性,乃至在现代社会仍值得广大女性同胞思考,并作为爱情中的警句。与《氓》中的女主人公相反,《诗经》中的其他弃妇在面对丈夫喜新厌旧时,表现出的多是留恋不舍的情绪,她们仍然对过去的美好生活存有幻想,因此将自己描绘成一种孤苦可怜的人物形象。
(二)女性意识
虽然《诗经》中的弃妇都难逃脱被残酷丈夫驱逐回母家的命运,但是在这场不幸经历中,她们之中的有些人已经开始进行自我反思,显现出一定的自我意识。霍小芳《从<诗经>弃妇诗中浅析其时代背景》[9]以及丁晓俊、任娟、贺梅梅等人都曾对弃妇的自我意识提出赞扬。如《邶风.谷风》中的女子在丈夫移情别恋时,发出了“采葑采菲,无以下体”的劝告,提醒丈夫不能只重视美貌而无视心灵性情。《氓》中的女子在饱受丈夫摧残,遭受心理与身体双重折磨的同时,仍能清晰地认识到男女两性在情感上的差异,并给予广大女性善意的提醒。
(三)意象选择
哀怨悲凄是弃妇诗的感情基调,其中恰当的意象选择对这种悲情色彩的营造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作者多以植物、飞鸟起兴或以此为喻来表现自己的不幸命运。彭远利在《<诗经>中弃妇诗所选用的意象》[10]中将弃妇诗中的意象归纳总结为两大类:植物类与飞鸟类,而植物类又可细分为菜草类与树木类。这11首弃妇诗中用到的植物意象有:葑菲、桑、蓷、樗、蓫、葍、菅、白茅等。《邶风.谷风》涉及“葑菲”,《王风.中谷有蓷》中有“蓷”,《小雅.我行其野》有“蓫”与“葍”,《小雅.白华》中有“菅”“白茅”,这些都是菜草类植物。而在树木类意象中,桑的出现频率最高。彭远利指出:“桑树在中国古代是家家户户所种植的,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必要条件。它带有衣食之源的不可缺性,是百姓生存保障之一,被广大民众赋予了深厚的感情”,在《卫风.氓》《小雅.白华》中都有提及桑这类意象。“樗”是一种恶木,在《小雅.我行其野》中曾出现过,作者多以此恶木暗喻对方的卑劣行径。至于飞鸟意象,在这11首弃妇诗中出现了鸠、鹙、鹤、鸳鸯等。如在《小雅·白华》中用到了“鹙”“鹤”“鸳鸯”这几种意象,郑玄注:“鹙也鹤也,皆以鱼为美食,鹙之性贪恶而今在梁,鹤洁白而反在林,兴王养褒姒而馁申后。”在此诗歌中,作者以鹙、鹤等飞鸟不捕食鱼的行为,来比喻丈夫另有新欢;用鸳鸯偶居不离,来反比无德无情的丈夫不能和自己白头偕老的行为。
陈中林在文章《论<诗经>弃妇诗中的植物与动物意象》[11]中,根据作者的创作心理与情感的不同,将弃妇诗中的动物、植物意象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同病相怜”型意象,多为孤独柔弱、平淡质朴型的草木,或是遭到世界冷落的动物,象征着爱情不幸的弃妇;另一类是“物是人非”型意象,其给人一种物得其所,而自己却处于流离失所处境的矛盾感。
陈磊《论<诗经>弃妇诗中的水意象》[12]一文专门对弃妇诗中的水意象进行分析,观点十分新颖。他根据诗中水意象的不同特点,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作为比兴之水及其相关的水意象,代表作为《召南.江有汜》《邶风.柏舟》《邶风.谷风》《小雅.白华》。其中除《邶风.柏舟》是借柏舟起兴之外,其余3首都是借水喻人,表达人的情思与哀愁。第二类是情景交融的水意象,这在《卫风.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水不单是作为环境描写的要素出现,还是这场爱情故事的见证者,承载着女子心境的变化。最后,陈磊还对诗中水意象的审美意蕴作出分析,弃妇诗中水意象的选用不仅符合柔弱女子的身份,而且其清浊也能象征人物品德的好坏,此外,水的阻隔也象征着在爱情中被弃的命运。
(四)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诗经》是最早记载弃妇形象的一部文学作品,那些勤劳善良但却不得丈夫宠爱的女性形象,给后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并且对后世文学作品的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阳淑华《<诗经>中的“弃妇诗”及其主题嬗变》[13]一文以《诗经》中的弃妇诗为开端,对弃妇主题诗歌的发展脉络做了缜密的梳理工作。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弃妇形象的发展演变与性别角色的转换两方面。阳淑华将《诗经》时代的弃妇、汉乐府民歌中的弃妇、魏晋文人笔下的弃妇与唐诗中的弃妇进行了比较探讨。文章指出《诗经》弃妇诗中的女性“在性格上勤劳善良、情感专一、为爱付出;在性情上敢爱敢恨、无所掩饰、爱恨分明、不假雕饰,部分女性呈列出炽烈奔放的性格。”而汉乐府民歌中的弃妇,一方面失去了《诗经》中女性的那种活泼的生命力,而另一方面则出现了让人眼前一亮的新型弃妇形象,她们不甘沉默,勇于反抗。魏晋文学中的弃妇形象是一次巨变,她们多是生活在亭台楼阁中的大家闺秀,性情哀怨,时常担忧自己会被抛弃,缺少生命的活力与灵动。而唐代诗歌中的女性在被负心郎抛弃之后虽然也免不了伤心哀怨的情感,但大多数女性已经表现出独立自主的意识,能较快地从这种悲情中走出来,开始勇敢面对新生活,追求下一段幸福。这也是唐代弃妇性格中的进步与可取之处。有关不同时代弃妇形象比较的研究性文章,还有赵亚萍《汉乐府弃妇形象论析——兼与<诗经>弃妇形象比较》[14]、王淑玲《<诗经>弃妇诗与汉乐府弃妇诗之比较》[15],这些文章主要是将汉乐府民歌中的弃妇形象与《诗经》弃妇诗中的弃妇形象相比较。王淑玲得出《诗经》中夫妇离别,大多是因为女子年老色衰,或男子另有新欢,而汉乐府中的男女则是封建包办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的结论。赵亚萍认为这两部文学作品中的弃妇都是封建社会制度和人性弱点肆虐双重迫害下的悲剧形象,但是《诗经》中的弃妇更具备“温柔敦厚”的特征。李贝贝《<诗经>思妇诗与弃妇诗研究》[16]将《诗经》中的思妇与弃妇这两类女性形象进行了对比探讨,并对思妇诗与弃妇诗的内容与产生根源进行了细致讨论,体现了对女性问题的关注。
性别角色的转化是指作者描写弃妇形象不仅仅是出于写实的需要,他们开始以此为喻体隐晦地表达自己的心境。文章指出:“自曹植始,常以弃妇自喻,表面上是诗人们采用代言体,代弃妇言,实际上是诉说自己命运坎坷和难以言喻的苦衷。”代表作有《种葛篇》《浮萍篇》《七哀诗》等。总结来看,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弃妇形象开始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开始由被迫接受转向了勇敢反抗。
杨康《<诗经>弃妇诗两性关系模式的生成及其流变》[17]与尚永亮《<诗经>弃妇诗与逐臣诗的文化关联》[18]这两篇文章着重关注文学作品中弃妇形象的嬗变。因弃妇与逐臣之间存在文化关联,不少文人便以弃妇自喻,表现自己不受上层重用,无法发挥自身价值的惆怅失落之情。最为突出的便是屈原的《离骚》,他常以“香草美人”自喻,表达自己不同流合污的高洁志向。
四、总结
“弃妇”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描绘最多的人物形象之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在感受《诗经》中的弃妇的不幸命运、体会悲惨人物形象、学习诗歌艺术手法的同时,最应该关注它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如今这个离婚率居高不下的社会中,更应思考、探索婚姻家庭稳定幸福的策略,这将为《诗经》弃妇诗的研究注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