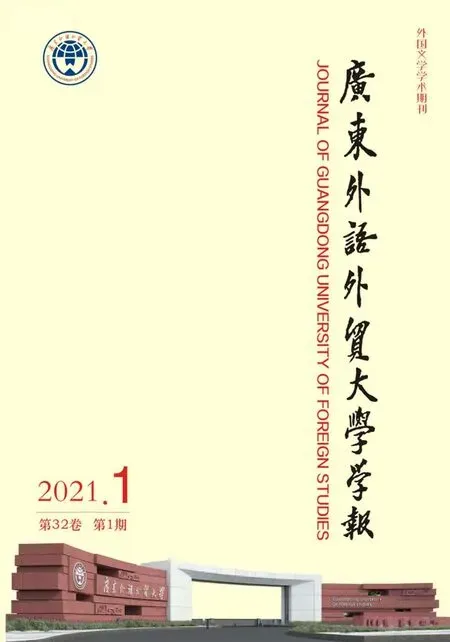对话与交融:西克苏关于绘画的“出位之思”与“跨界之行”
王迪
引 言
纵观西方文学艺术史,文学与艺术经历了无数次分分合合。“从18世纪末开始,各种不同的艺术相互分离……寻求自身的独立、自主、自足……整合艺术品彻底分崩离析”(泽德迈耶尔, 2014:62)。到了19世纪,崇尚整体性的浪漫主义开始“重组”艺术品,涌现出大量“图文一体”的美学作品。进入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后现代、去中心的解构主义思潮将文学和艺术再次带入反传统的泥淖,开始向传统“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宣战。法籍犹太裔女作家埃莱娜·西克苏(Hélène Cixous)是叱咤国际文坛的“思考的诗人、革命者”,以鼓励女性诗意、自在、反抗的“阴性书写”①而著称,又因其跨艺术思考和美学实践而独树一帜。西克苏曾这样定义文学文本:“文本仿佛一座城市,亦像是一座博物馆,勾勒一个季节:我们在里面散步,感受扑面而来的一切,尤其是与艺术相遇时的美妙”(Rossum-Guyon, 1997:210)。在西克苏那里,艺术是什么?当文学与艺术相遇,会擦出怎样美妙的火花?她有关文学与艺术的“出位之思”有何含义?这种思考在文学创作中有怎样的表现?
“出位之思”语出德国美学术语Andersstreben,意指一种艺术形式偏离或超越其自身的表达功能或局限,而追求另一种艺术形式所具有的表达长处或美学特色。钱锺书先生在《中国画与中国诗》中一语道名“出位之思”这个美学概念的真正本意,“艺术家总是想超过这种限制,不受材料的束缚,强使材料去表现它性质所不容许表现的境界……诗跟画各有跳出本位的企图”(龙迪勇,2015:89)。何以“跳出本位”? 文学如何在绘画艺术中寻得新的表现力,如何“赋予自己的词语以新鲜的面孔”?这是西克苏一直在孜孜探求的核心问题。由评价式反思到创造性构建活动,由简单的语图结合到文学虚拟作画,这反映了西克苏由表及里逐层深入、由思到行大胆创新的美学价值理想。
从“编织物”到艺术时空体:对绘画的“跨界”思考与摹仿式再创造
“文本”(texte)一词源自拉丁语“编织”(textere),文学写作实则是一种“编织行为”,在语言文字的能指层面进行。西克苏(1977: 20)认为,文学写作行为“与绘画是同步且同质的”,希望自己能够“用绘画的方式写作”。如此一来,具象思考并不是画家、设计师的专利。若想跨越文字符号的“线性特征”,把语词引入视觉空间,在话语叙事中加筑艺术空间的想象,借助光影、色彩、明暗等艺术元素对文字符号重新组合,为的是跨界中达到一种“出位之思”的美学效果。所以西克苏不仅注重小说情节、思想理论的陈述,而且强调从视觉艺术中获得资源和灵感,对创作素材进行艺术加工,从而使语词叙事处处体现别具一格的“开放性”和“展示性”。
西克苏坚持认为,语词叙事作品中包含着图画的自由质感,这份执念首先体现在她诸多文学评论性文本和创作性文本中。20世纪60年代,在西克苏还以埃莱娜·贝尔热(Hélène Berger)署名发表作品时,就已经开始对绘画中诸如审美、光线、辐射等主题做出富有思想性的分析,《事业的岔路口或前肖像》(L’Avant-PortraitoulaBifurcationd’uneVocation)一文就是最好的证明。在文中,西克苏借着评论爱尔兰作家乔伊斯(James Joyce)的自传体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Portraitd’unArtiste),在肯定乔伊斯美学思想的同时,明确自己对艺术审美的独到看法。她认为,这虽然是一部文学作品,但画面感强烈,很多片段“清晰如画”。在年轻的乔伊斯身上,西克苏觉察到:
耶稣显灵的日子,就是当时间被突然出现的美悬置起来,当审美乐趣辐射到主体时,就在这唯一的崇高的瞬息之间,这道光线是主体自身的光线。目光被吸引,迸射出欢愉,突然之间,一切皆有可能,包括崇高的自恋倾向。这是光芒四射的伊卡洛斯般的第一次飞翔。(Berger,1965)
的确,对美的观察和感知使观察者欣喜若狂,观察者因为自身也被照亮而成为美的源泉。在审美过程中,通过审美体验,观察者看到了自身,并发现了自身的潜力。文字同样具有瞬间取景的能力,将时间转换为空间,无限收缩为有限。与视觉艺术一样,自带线条、光亮的文学空间拥有一个始终不变的方向,即永远关注、思索和表现人类瞬间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况,都是艺术家用眼睛和心灵去捕捉的过程。
在文学叙事中或直接或隐含地援引著名艺术家及其知名画作,进而滋养、丰富和深化文学文本的内涵,这成为西克苏文学创作又一突出特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很多画家连同他们的画作——例如伦勃朗(Rembrandt)的《被解剖的公牛》(LeBoeufécorché)、《沐浴的贝莎蓓》(BethsabéeauBain)、戈雅(Goya)的《狗》(Chien), 再或者是葛饰北斋(Hokusaï)的《富岳三十六景》(LesTrente-SixVuesduMontFuji)、莫奈(Monet)的《鲁昂大教堂》(LaCathédraledeRouen)以及毕加索(Picasso)的《过路人》(L’EtudepourlaRepasseuse)……都相继进入西克苏的文学虚构世界。如果说西克苏的早期创作方式尚停留在邀请绘画作品走入文字世界,让文字浸润在艺术氛围中的话,随着思考的深入,女作家逐渐将写作与绘画并置,让它们彼此渗透,相互补充,逐渐形成了在文字中摹写、续写、重写绘画意向的写作策略。这样的例子散见其诸多文学文本。例如西克苏主动将自己的文学叙事与伦勃朗的《被解剖的公牛》联系起来,“女人的目光如刀锋般犀利,仿佛要把眼前的一切支分族解”(Cixous,2000: 39);戈雅的画作《狗》及其画面的虚空感、流动性反复出现在西克苏的多部叙事作品中:“狗向上望去,在期待什么?”(Cixous,1991: 61) “它身后的流沙似要吞噬女孩不愿看到的东西……”(Cixous,1995:76)。那些因色彩、明暗而著名的艺术形象不断丰富着女作家笔下的文学世界。于西克苏而言,这些艺术形象既表现(figurer)又损毁(défigurer),一直处在“正在进行的”状态中,拥有伦勃朗作品中的“无法捕捉的轮廓”。20世纪70年代是西克苏文学理论的重要形成期。她思考文学,开始构建“正在进行中的”“处于未完成态”的“阴性书写”观。这种介于理论和半理论之间的流动式的文学书写与画家笔下建构的无法名状的、无法捕捉的意象交相呼应,进而开启“一个不安的、不稳定的、不确定的时代”。正是借助这种未知性和不确定性,西克苏向读者展示了文学写作与艺术创作的渗透、融合以及相辅相成:“未知”既存在于亦虚亦实的绘画艺术里,也表现在开放的、非理性的“阴性书写”中。它们从本质上都表现出对“他者”的尊重。
“尊重他者”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上帝视角的阙如,意味着“同一”、线性逻辑的缺失,意味着西克苏所言的“面对面的”“开放的”艺术空间的诞生。西克苏提到的“他者”“面对面”无疑是对自己的精神导师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书写与差异》(L’EcritureetlaDifférance)中反复强调的“他异性”(altérité)和“外在性”(extériorité)的回应,亦是对视觉艺术作品的独特性——无限可塑性——的肯定。在诸多 “尊重他者”的绘画艺术手法中,西克苏尤爱自画像,认为自画像是实现“与他者相遇的最好的契机”(Cixous, 2010:47)。西克苏的阐释大胆而有趣,自画像本应是艺术家按照自己的模样所绘的肖像作品,而在西克苏眼中却变成了自己以外的其他事物、其他动物甚或是写作本身。比如西克苏评价《被解剖的公牛》 “正是伦勃朗最直白的自画像”,《狗》“正是戈雅的自画像”,而《玫瑰书写》(L’écritureRose)则是韩泰(Simon Hantaï)的自画像。西克苏定义的自画像是不同于肖像画和文学形象的他者存在,它摧毁了绘画艺术中描绘肖像的传统手法,正如她自己欲将文学中塑造形象的传统方式“土崩瓦解”一样:自画像既是一种反躬自省,更是一种可塑形式,具有敞开式的特点,它可以接受涂改、修正和失误。在这个意义上,作家的文学实践和画家的美学实践异曲同工:正是这些涂涂改改使得伦勃朗的“自我勾勒”在不断校正或修正中逐渐成形;正是一次次修改使得西克苏塑造的文学形象从“已经被书写”的思维定式中解脱出来,在不同文本之间穿梭跳跃,表现出可以永远重构的多面性和延展性。文学创作中的西克苏,仿若女性形象设计师,成竹在胸地、有预谋地为读者描绘出在生命不同时期的女性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状态:《内部》(Dedans, 1969)中的那个“父亲的女儿”尚徘徊在父爱和父权枷锁之间,几经修补,曾经的女儿摇身变成《新生女》(LaJeuneNée, 1975)中的渴望在历史中寻得一席之地的新生一代,经年之后,又带着岁月的沧桑卷土重来,在《伊拉》(Illa, 1980)中以挣脱牢笼、渴望自由的女子形象与读者见面。从单个作品出发,每一个女性形象都是女性生命体某个时段内的“自画像”,将众多作品勾连起来,所有女性形象仿佛被设计师用沾满“白色墨汁”的笔不断地涂涂抹抹、修修补补,形成了自成一体的艺术空间,与父权写作针锋相对,动态地再现女性生命体的跃动、复杂和自我更新,以及对这种复杂性的开放和接纳。
随着思考和创作的深入,西克苏不满足于只从“外围”对绘画艺术加以评论或再现,她开始尝试“为文插图”,有意识地将文本“编织物”打造成巴赫金所言的“时空艺术体”。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克苏充满美学设计和视觉效果的文本作品比比皆是。《面纱》(又译《帆》,Voiles,1998)是西克苏与德里达合著之作,他们借法语单词voile一词多义且一词多性的特点②,讨论阴/阳、男性/女性、男权中心/阴性气质等性别差异和双性同体问题。在正常的语词叙述中穿插出现了五幅黑白配图,图画线条飘逸、灵动,让人浮想联翩。既可以理解为让女性“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面纱,也可能是“海面上迎风招展”的船帆,作者将解读的权利交给了读者,邀请读者结合“具体的、可触摸的乃至忠实于现实的图画”理解自己提出的所谓“具有肉感的阴性书写”(Cixous, 1998:56)。
《坚持,致德里达》(Insister, àJacquesDerrida,2005)被看作是《面纱》的“姊妹篇”。西克苏再次联手德里达,探讨关于“犹太人”“他者”等身份困境问题。西克苏将自己的手稿嵌套在黑白素描背景内形成别具一格的插图,镶嵌在作品的开篇和正文内,形成一种“文与文、文与图的立体互文结构”。或许是唯恐读者忽略自己“为文作画”的良苦用心,西克苏在书后另加了一份《〈面纱〉原始手稿的描述性说明》,还原了这份完成于1995年南美旅途中的手稿的“原初状态”: 其中“五页纸由作者手写页码,尺寸均为长二十九厘米,宽二十一厘米,用蓝色墨水写成”;“另十页纸,尺寸同上,作者手编页码,正面为正文,反面为评注或增补”,“一个硬皮小本,尺寸长十三厘米,宽十厘米”,“一个三十页便签本,尺寸长十五点二厘米,宽十点五厘米”…… (Cixous, 2005:125)这份“描述性说明”有尺寸有厚度,为文字添加了视觉形象的外观,非常直观地再现了文本可诉诸视觉的空间性形式。
《超梦境》(Hyperrêve, 2006)则是一部语言优美、充满哲思的散文作品,围绕人生“向死而生”“向死而在”的核心话题展开。打开书页,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就是一副意境深远的彩色配图:近景处,高高的椅背上斜搭着一件白背心,明亮纯洁,深蓝色的背景里星光点点,孤寂中满是深邃与透彻。这幅图无可逆转地为全书定下了底色和基调,“我继续活着,继续失去,随时间渐渐消亡”(Cixous, 2006:24)。
个人长期形成的审美心理结构,是艺术独创性的深层心理素质 。作为一名具有独特审美体验的作家,西克苏胸有成竹,以观赏者和创造者的身份解读写作与绘画的交流模式。她曾淋漓尽致地描绘自己面对一幅绘画作品时的内心独白:
当我面对任何一幅画时,我从未觉得自己在写作:站在画前,我在反抗。我要么什么都听不见,麻木不仁,没有激情;要么截然相反,我被深深地感动,但不知其所以然。就是在这时,我的思想开始进入写作的轨道。站在画前,我感动了,我记录下当时的情感,再把这种情感放到一边……这幅让我动容的画作就这样在我的内心某个黑暗角落默默地发光,很久以后,当我动笔写作时,它再次被唤醒照亮我的文字,于是,我便开始思考:这份感动中还包含了什么?它源自何处?又将走向哪里?它在向我述说着什么?(Cixous, 2010:66)
西克苏坦然承认,自己并非传统意义的绘画爱好者,但作为一个对绘画有着深刻反思和独到体验的观赏者,她准备好了与那些同生命息息相关的经验“相遇”,这些经验既来自别人,当然也和观赏者本人密切关联。而我们任何一个个体面对一部作品,只有当这部作品所传达的与我们所接受的既相同又不同时,我们才能“被感动”,才能接受它。“这既是我又不是我。对于文学而言也一样,是我,又不是我”(Cixous, 2010:19)。换言之,这正是西克苏式的“写作-绘画”两栖创作理想,在坚守文学语词叙事魅力的同时,作家努力挖掘文学“出位”之可能:文字可以不受单纯信息的支配,接受其他艺术形式的感召并与之完美结合,其审美价值将在更大程度上得到实现。
《在那里》:实现“近视审美”和“跨界之行”的典型案例
互文性理论跨学科开放性的特征为文学和绘画之间的互文性阐释提供了合理、合法的依据(王芳, 2020: 51)。动用大量真实的画家及画作参与写作,在文学文本内实现了巧妙的互文、“互画”(interpictoral),这令西克苏的文学文本可读且可感,而且自然带有一种“透气性”,图像、色彩、明暗的再现,使话语空间得以空气流通,读者可以在文字与绘画之间恣意游走,自由呼吸,而不会因纯粹的文字或意象感到窒息。西克苏不仅“写画”,而且“作画”,借助艺术想象,在小说中虚构一幅画。
如何虚构一幅画?女作家用她的文学作品给出了答案。小说《在那里》(LA,1976)便是这种尝试的开端。这是一部关于“盲目”(l’aveuglement)或曰“近视审美”(la myopie) 的小说,德里达如是评价说。所谓“盲目审美”或“近视审美”重在强调目光的非确定性,就如一个盲人或视力不健全的人,其“目光是无法清晰看到客体的”。与正常视力捕捉清晰图像相比,“近视”是保证所观之物不尽完美、模棱两可、无限延异的重要条件。
小说《在那里》的第二章名为《一个陌生女人的视程》(Portéed’uneInconnue),描写的是小说女叙述者被一个陌生女人的肖像所吸引、驻足、近距离欣赏。她令女叙述者“瞬间感到眩晕”,继而心潮澎湃,而画中陌生女人纤细、轻灵的身姿令女叙述者自愧不如。陌生女人的出现让女叙述者一下子恍然大悟:“是时候拿起笔开始写作了”,潜藏在她内心深处的那个“神秘人写者”被唤醒,“你像一只鹰隼振翅高飞,你像一只野鹅高声鸣唱,你在发光发亮”(Cixous, 1976b:55-58)。这个光彩照人的陌生女人形象成为女叙述者奋笔疾书的契机,对于后者而言,画卷变成通向无限可能的窗口。此情此景与前文分析的乔伊斯的作品颇为相似,突然显现的美向女叙述者昭示了通往实现其自身可能性的路径,因为,就在这里,一个好似来自肖像的声音在召唤女叙述者,鼓励她拿起笔写点儿什么,“书写,为了不走向死亡”,同时也为了“显示这个陌生女人的视程”(Cixous, 1976b:59)。
这里的视程尤指审美能力所能企及的表达范围,是欣赏画作之后心愿达成的满足和喜悦,是对那些自己所不知的、失却的、被切断的生命根源的慨叹。生命的根源处, “她正是在那里开始学习阅读,学习被解读,在断断续续的字里行间,在每一丝光亮中尽情享受”(Cixous, 1976b:58)。由此,这幅肖像画带来的眩目、唤醒与享乐相联系,指向女叙述者的内心。对于作家而言,在注视他者时迷失自我必然会带来意外的喜悦和挥之不去的痛苦,那痛苦却并不令人恐惧,这种超凡的感受必将成为创作的生命之源。正如西克苏(1994:119)在《脚印》(PhotosdeRacines)中所说,如果“我们真的拥有忘我和遁世的力量,如果我们敢于拒绝承认身份特征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我们就可以“借助艺术之途深入人类真实存在的内核”,我们就可以“开放自我,为接纳他者留有一些空间”。而开放自我,超越自我,恰是绘画带给女作家的重大启示:因为自我往往是阻止飞翔的最后的“根”。
通过艺术的路径挣脱、释放,这是西克苏几经揣摩之后树立的文学创作信念。正是在这个坚贞信念的驱使下,西克苏在《在那里》这部书中有意识地提及了另外两幅画作:它们是富塞利(Füssli)的《梦魇》(LeCauchemar)和莫里兹·冯·施温德(Moritz von Schwind)的版画《囚犯的梦》(LeRêveduPrisonnier)。随着小说情节的深入,读者渐渐发现原来画面上那个陌生女人正在“沉睡”,在做噩梦,“一个恶魔让女子肝肠寸断”(Cixous, 1976b:33)。尽管画家富塞利的名字只是在小说行将结束时才被明确地提出,但上述描写还是很容易让读者与画家联系起来的,因为就是在1975年——《在那里》出版的前一年——巴黎小皇宫举办了富塞利的画展,画展宣传目录的封面恰巧就是《梦魇》这幅画。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西克苏仅仅是借用或模仿富塞利的画,那就失去了文学创作的意义,更远离了西克苏“以画寓话”的创作初衷。西克苏要告诉读者的是一个不一样的解画方式和“观看之道”。对于小说的女叙述者而言,她注意到画卷释放出来的光亮,而画面中平躺女人的梦境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力量”,梦境的魅力就来自于一次炫目的体验——女叙述者想象着她自己与画融为一体,化身为画中人:“当我从画的下方朝上看,沉睡的女子便逃离了原本桎梏她的樊篱,一种女性的成熟之美让她格外光彩照人,红色的翅膀将她略微托起,她微微动了一下,发出迷人的光。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她获得了重生”(Cixous, 1976b:34-35)。西克苏笔下的女叙述者既以她本应有的方式欣赏画卷,又以“另一种方式”对其进行解读,女叙述者被画中人散发出的光芒击中,但没有过多地沉溺于其中,而是看着看着,渐渐抽身出来,因为她惊奇地发现,一旦将画卷倒置,就可以为原本肝肠寸断的女子找到新的出路,这是从一次与艺术的相遇中窥探到的解放。倒置之后,画中人可以被想象成飞翔的姿态,或者被想象成逃亡的状态,而不仅仅是生命垂危的弥留之际。这便是女作家独特的“观看之道”,她创造性地摒弃历史性的性别期待,对女性身份进行诗性修正。事实上,西克苏在其同时期的其他著作中也表达了类似的“颠覆性的飞翔”的梦想,她认为,女性可以通过对艺术的占有和重组获得象征意义上的、甚或是真正意义上的新自由,以及用以表达她们各自欲望的声音——话语权。
让我们模仿西克苏笔下的女叙述者,将富塞利的《梦魇》这幅画倒置过来,从画中人的角度出发仔细看看,这完全颠倒了艺术传统。在传统视角里,那位女子被压抑、被注视、被监视,是个受害者;而倒置后,女子手臂上扬,超然、洒脱而自由。西克苏不失时机地将这个倒置后的形象再现于《呼吸》(Souffles, 1975)——另一本同时期的代表作——的封面。在一次采访中,她(1976a)坦言,自己想借此“昭示女性的飞翔。一直以来,人们只想着把女性安排在精神错乱的、痛苦的、被压榨的境地里。而这一次,我要肯定的是充满活力的、得意洋洋的、欢喜鼓舞的女性气质”。将画卷倒置,让女性飞翔,将女性从满是性暗示的噩梦中解放出来,这是西克苏梦想已久的逃亡,是一条突围之路。
逃亡与突围的想法将这个从富塞利那里借来的意向与另一幅艺术作品——施温德的《囚犯的梦》——联系起来。在《在那里》的最后一章,女叙述者终于清楚明白地道出上述两幅作品之间的互文关系:“是一股强大的直觉力量帮助艺术家找到了女性与囚徒之间最根本的相似性。他们的‘梦’中除了有逃亡和突围之外,不会有其他内容。逃亡自然可以通过窗子实现,因为那令人兴奋的光线正是透过窗子射进来的,唤醒了囚徒”(Cixous, 1976b:227)。有了窗,有了光亮,有了充满魔力的沉睡女子,西克苏将这些审美经验巧妙地揉进自己的文字创作中,让绘画与文学巧妙地相遇,可以让我们以别样的方式去思考和向往我们的世界。这种相遇也应验了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关于“艺术即救赎”的预言:“艺术家在转化中觅得愉悦,艺术创作在反抗各种灾难中觅得宁静,这些都不过是黑暗的苦海中天空云彩光亮的倒影而已”(沃特伯格,2011:99)。
正如西克苏在《在那里》中几次安排让写作与绘画相遇一样,我们可以借着遇见他者的这个时机,自我觉察,自我审视,或借用西克苏的话,“体现审美主体的多重性”。如此看来,德里达(2002:96)对西克苏的如下评价不无道理:西克苏的文字中 “没有稳定的叙述语调”,换言之,“总是带有多重主体意识因子”。西克苏所描绘的最为炫目的时刻事实上都是人们自我忘却的时刻,主体无限接近他者的真实。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如此这般的认知实在玄妙,是一种诗意的、理想的状态:我们真的能想象自己变成他者,抑或完全理解他者?这也是为什么在西克苏接下来的文本中有那么多看似不可能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肖像存在,比如“太阳的肖像”“一个盲人的自画像”,再或者“最后一幅画——上帝的肖像”③。回头看来,就算是《在那里》中的“一个陌生女人的肖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如何画一个我们不认识的女人,如何画一个陌生人呢?然而,换个角度思考,或许所有这些肖像画只是想通过其不可能性向读者展示无限接近真实的另一种方式。西克苏悖论式地强调一个事实:即便我们非常近距离地观察一张脸——就像艺术家画肖像画那样,我们也不能真正了解我们眼中所见的。写作和绘画如出一辙,都是在试图展示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事物,试图尝试各种不可能。
《在那里》一书中多次出现写作与绘画以及绘画作品之间的相遇,这使得西克苏的虚构作品超越了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成为一种更宽泛意义上的诗学之作、美学之作。一方面,这些相遇构成了不可能性的艺术审美;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向人类心灵中质朴又神秘的真实表达敬畏:
当我即将结束写作时,当我快要步入百岁时,我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尝试完成上帝的肖像……也就是说,完成对那些不为我们所知但却能够感受到的事物的勾勒。……我想说的是我们自己的神灵,虽然有些笨拙、扭曲或令人激动不已,但都是我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我们的秘密,我们的诗。(Cixous, 1986:175)
这里大写的“我们”使西克苏意义上的“创作者”身份混杂暧昧,多重叠加,“写作-绘画-阅读”无所不能。西克苏邀请他者参与她亦诗亦画的文本创作:“如果你不燃烧自己的热情,那么,我就把词集合起来,点燃一堆黄色的麦草。我的那团火没燃起来,我的词语就不会发出星星点点的黄色光亮,我的词语就仍是没有生命的死词” (Cixous, 1986:176)。在文字世界中,读者受邀于作家,一次又一次驻足、凝视、反思。这就是一部不朽作品的神奇之处,它让我们加深生命体会,让我们与那些曾经擦肩而过的人或事再次相遇。
结 语
如上所述,西克苏的艺术化书写创造性地实现了写作与绘画的跨界和巧妙融合,形成了独具个性的审美意识和文学实践。在文字中,她或对绘画作品直抒胸臆,或与图像互动,或将人物肖像重新演绎,将现实感悟深化为审美认知,期待在一次次整合和重塑之后对生命进行最古老、最深刻的阅读(la lecture la plus profonde, la plus antique)。西克苏充分肯定绘画艺术的可塑性、开放性、瞬间美等特征,将其与自己主张的“开放的、动态的、颠覆的阴性书写”展开对话和互证,继而在诸多文学作品中塑造出多元的人物形象,达成意境与主题的扩展和延伸,实现视觉再现和语言再现的交汇、叠生与转化。
从探索写作与绘画的互通共鸣及其表达形式起始,借助图像表现、反哺乃至重塑文学文本的艺术形象和价值理想,这是西克苏的出位之思和跨界之行带给我们的重大启示。可以说,西克苏为绘画艺术增加了文学性和诗学特征,她以画入文的写作策略极大地扩展了文学的表现空间。她借跨越写作与绘画的界限之机,所表现出的对人类心灵世界、精神诉求和生命体会的关注尤其可贵:相较于单纯的艺术美或文字美,跨界后的内省、敞开、尊重他者、探寻不可能之可能……这些镌刻着生命之美的态度和向度也尤为重要。
注释:
①关于“阴性书写”,笔者曾写过名为《女性话语的突围之路——论埃莱娜·西克苏“阴性书写”进行时》(载于《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年第1期)论文,专题讨论。
②法语中voile可以作阳性名词,意为“面纱”,也可以作阴性名词,译作“帆”或“帆船”。
③西克苏将自己的作画意识明白无余地凸现在作品题目中,如《太阳的肖像》(PortraitduSoleil, 1973)、《朵拉的肖像》(PortraitdeDora, 1976)、《最后一幅画——上帝的肖像》(LeDernierTableauoulePortraitdeDieu,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