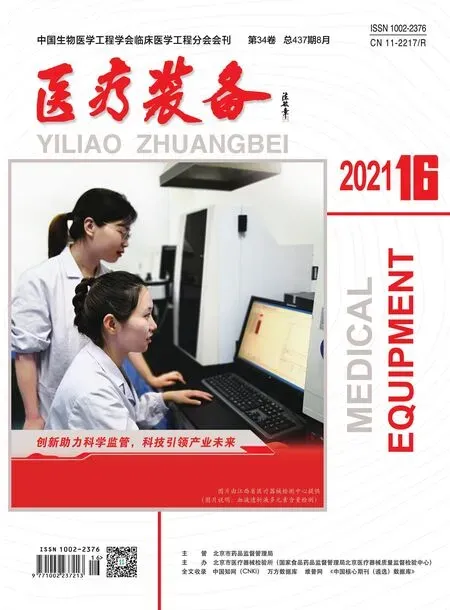新生儿脐血在恶性肿瘤疾病患者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潘春煦,刘鹏,崔洪艳(通信作者)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天津市人类发育与生殖调控重点实验室 (天津 300052)
自20世纪中期以来,恶性肿瘤患者的治疗方式主要为化学药物治疗,常用的化学治疗药物有铂类、蒽环类、抗生素类及抗代谢药物等,但化学药物治疗常会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临床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寻找新型的抗恶性肿瘤方案是目前临床治疗恶性肿瘤疾病患者亟待解决的问题。新生儿脐血(umbilical cord blood,UCB)是胎儿分娩后残留在胎盘和脐静脉中的血液,UCB组成成分在恶性肿瘤疾病患者的治疗中有广泛的用途,且UCB组成成分在肿瘤疾病患者治疗中的应用已经成为产科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对新生儿UCB在恶性肿瘤疾病患者治疗中的应用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UCB治疗恶性肿瘤研究提供思路和借鉴。
1 UCB的组成成分
UCB的组成成分有成熟的血细胞(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造血干细胞(hematopoietic stem cell,HSC)、免疫细胞[包括自然杀伤(nature killer,NK)细胞、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未成熟的T细胞,以及细胞因子介导杀伤细胞(cytokine induced killer,CIK)等]、未分化的成体干细胞、多潜能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 stem cell,MSC)、内皮/内皮祖细胞(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EPC)等[1-3]。UCB中所含多种细胞成分在恶性肿瘤疾病患者的治疗中发挥出多重作用。
2 UCB-HSC在恶性肿瘤疾病患者治疗中的作用
HSC移植是白血病、淋巴瘤、骨髓瘤等恶性血液系统肿瘤患者的重要治疗手段之一。目前,HSC的主要来源有外周血、骨髓和UCB。外周血和骨髓HSC移植都需要进行人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配型,但因移植物抗宿主病(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GVHD)较明显等限制了其进一步的应用。而UCB中含有的HSC(UCB-HSC)具有移植物抗宿主反应低、采集方便、易得等优势,UCB成为HSC研究和应用最理想的细胞来源。UCB-HSC的HLA配型允许部分错配,只要有6个位点匹配即可,而骨髓HSC移植要求10个位点匹配,且与骨髓移植相比,UCB-HSC移植发生GVHD的比例和程度都较低[4]。UCB-HSC独特的优势为HSC移植提供了优势途径[5]。
截至目前,全世界已经有40 000例UCB移植用于治疗各种恶性和非恶性疾病患者中,且疗效显著。其中,UCB-HSC移植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疾病患者治疗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UCB-HSC移植对成人高危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疗效显著,其无进展生存期,与成人供体移植相当[6];一项针对582例急性白血病或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骨髓移植,UCB-HSC移植后疾病的复发率更低[7];对于继发性急性髓系白血病,UCB-HSC移植显著降低了两年复发率和非复发病死率[8]。且除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之外,UCB-HSC也已在包括肝癌、脑瘤、乳腺癌、前列腺癌、肺癌以及结肠癌等其他恶性肿瘤疾病患者的治疗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取得了良好效果。2009年6月,北京儿童医院进行了首例自体UCB-HSC治疗患有神经母细胞瘤晚期的儿童患者,在化疗和手术治疗后进行了UCB-HSC移植,治疗效果显著,其造血功能恢复且肿瘤消失。2016年北京京都儿童医院成功完成了一例高危神经母细胞瘤患儿自体UCB-HSC移植手术,疗效显著。
然而,对于体质量超过40 kg的成人患者和儿童来说,从单份UCB中获得足够数量的UCB-HSC是难以成功的。因此如何提高UCB-HSC归巢植入效率和开发新的方法以提高UCB-HSC数量是目前临床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双份UCB移植为UCB-HSC在大龄儿童和成人中更广泛的使用提供了可能。临床分析发现,与单份UCB移植相比,双份UCB移植易导致急性GVHD发生率增高、成本和资源使用增加等问题,而在中性粒细胞移植率、疾病复发率、移植相关病死率和总体生存率等方面与单份UCB移植相比无明显差异[9-10]。UCB-HSC的体外细胞扩增是解决单份UCB数量不足的另一途径[11],目前的研究进展表明,细胞因子干细胞因子(stem cell factor,SCF)、促血小板生成素(thrombopoietin,TPO)、FMS样酪氨酸激酶3(Fms-like tyrosine kinase 3,Flt3)及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等在UCB-HSC数量扩增方面显示出独特的优势;小分子化合物如嘌呤衍生物stem regenin(SR1)、嘧啶基吲哚衍生物UM171等也表现出不俗的扩增效果[12]。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UCB-HSC会更广泛地应用于人类恶性肿瘤疾病的治疗中。
3 UCB-MSC在恶性肿瘤治疗中的作用
新生儿UCB-MSC是从新生儿UCB中分离培养所得到的一种具有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潜能的成体干细胞。UCB-MSC具有一般MSC的类似特点,具有向炎性部位、损伤部位、恶性肿瘤部位及转移灶部位归巢;抑制恶性肿瘤细胞生长;调节抗炎免疫和组织修复等功能。相较于脂肪和骨髓来源的MSC,UCB-MSC更加原始,增殖分化能力更强,潜伏性病毒和病原微生物的感染及传播率更低,对产妇和新生儿均无任何损伤和危害,且免疫原性较低,成为MSC研究中的重要工具细胞[13]。
UCB-MSC向恶性肿瘤或肿瘤转移灶部位归巢的特性使其可以作为重要的细胞载体,UCB-MSC能够特异地将化疗药物、细胞因子、纳米颗粒等递送到肿瘤部位,进而靶向治疗肿瘤,降低毒副作用。对于一些难治的恶性肿瘤,如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最具侵袭性的原发性脑肿瘤),UCB-MSC可通过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促进肿瘤细胞凋亡。通常静脉输注干细胞后,大多数细胞在肺或其他器官中积聚,仅有少量进入脑组织,这就极大地减弱了干细胞的疗效。而鼻内给药递送的UCB-MSC可以绕过血脑屏障,快速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并向脑肿瘤、脑转移肿瘤、缺血或创伤性脑损伤等的病变部位迁移,进而递送分子药物入脑并发挥其生物学效应[14-15]。因此,鼻内递送UCB-MSC很有希望成为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治疗的常用方法之一。在中晚期恶性肿瘤疾病患者的治疗过程中,肿瘤转移的发生为恶性肿瘤的治疗带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而UCB-MSC能够特定地靶向肿瘤转移灶,为进一步的药物递送提供了重要的途径,也为转移性肿瘤的治疗提供了重要方案。
恶性肿瘤的相关研究进展也表明,相较于脂肪来源的MSC,UCB-MSC能够更显著地抑制恶性肿瘤细胞生长,增加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tumor necrosis factor related apoptosis inducing ligand,TRAIL)介导的恶性肿瘤细胞凋亡[16]。将UCB-MSC作为细胞工具可将TRAIL基因特异性地递送到肿瘤部位,进行基因治疗时发现,相较于脂肪来源的MSC,UCB-MSC具有更明显的递送效果,能更显著地抑制肿瘤生长,延长肿瘤小鼠的生存期[17]。采用UCB-MSC为细胞工具递送改良型白细胞介素-12(modified interleukin-12,IL-12M)进行肿瘤治疗时发现:UCB-HSC能够更加显著地增加IL-12 M水平,调控干扰素-γ的分泌,介导T细胞浸润和抗血管生成[18]。上述研究表明,UCB-MSC在恶性肿瘤疾病患者的治疗中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而在选择临床应用的干细胞来源时必须考虑这些差异[16]。
UCB-MSC作为药物运输的载体已经在不同恶性肿瘤疾病患者的治疗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另外,UCB-MSC可以通过分泌细胞因子、辅助形成骨髓基质以及直接接触等方式促进UCB-HSC体外扩增和移植后的归巢,进而缩短移植后骨髓造血功能恢复的时间,为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疾病患者的治疗提供重要保障[19-20]。
4 UCB-EPC在恶性肿瘤疾病患者治疗中的作用
UCB中除含有丰富的UCB-HSC和UCB-MSC之外,还含有一定数量的UCB-EPC,且UCB中EPC的含量高于外周血[21]。EPC除了具备成熟内皮细胞的全部表型外,还表现出干/祖细胞的特征,其主要标记为CD34+/CD133+/VEGFR2+[22-23]。此外,UCB-EPC的端粒较长,端粒酶活性高,增殖能力强,且其GVHD水平和程度均较低[24-25],因此UCB来源的EPC相较于外周血EPC在临床应用和研究中具有更明显的优势。
肿瘤血管新生在恶性肿瘤的发生、演进和转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肿瘤血管新生中,EPC能够在肿瘤分泌的细胞因子如低氧诱导因子(hypoxia inducible factor,HI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和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stromal cell-derived factor-1,SDF-1)等的刺激下,动员入血,并定向归巢到肿瘤的新生血管处[26]。将标记后的EPC注射入乳腺癌小鼠体内时发现EPC能够被特异性地募集到肿瘤部位,参与肿瘤血管新生。EPC特异性地靶向肿瘤血管新生部位,使其成为又一个恶性肿瘤研究中的重要工具细胞。
基于EPC的基因治疗比传统的基于载体或病毒的基因治疗具有更显著的优势,这是因为,UCB-EPC不仅能够作为载体将治疗基因递送到特定的肿瘤部位,而且能够穿过血脑屏障,在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基因治疗中发挥更加独特的作用[27]。在药物递送方面,UCB-EPC能够特异地将抗血管新生药物、细胞因子或者前药等递送到肿瘤血管新生部位,达到靶向恶性肿瘤血管新生和治疗肿瘤的目的,减少因血液循环带来的药物损失,维持局部药物浓度,提高疗效[28]。
此外,采用特定的标签或染料对UCB-EPC进行直接或间接标记,可以作为成像中的探针和报告基因,应用于光学成像、核医学成像和MRI中[22,29]。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UCB-EPC能够安全有效地进行分离并广泛应用于恶性肿瘤疾病患者的治疗中[6,10,12,19,28],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UCB-EPC能够在肿瘤患者的治疗中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
5 UCB免疫细胞在恶性肿瘤疾病患者治疗中的作用
NK细胞在UCB中的比例和数量均显著高于外周血,且UCB-NK细胞能够通过分泌干扰素-γ和颗粒酶B等细胞因子促进肿瘤细胞的凋亡[30]。近期的研究进展表明,以CD19为靶点的UCB来源的嵌合抗原受体自然杀伤(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natural killer,CAR-NK)细胞疗法使患有复发性或难治性非霍奇金淋巴瘤和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患者出现临床缓解,且没有重大毒性反应,这些初步结果为将UCB开发成CAR-NK产品奠定了基础[31]。
UCB-CIK细胞来源于UCB,研究发现,UCB中CIK前体细胞含量较高且增殖能力较强,易扩增更多的CIK细胞;已有大量的实验证明,UCB-CIK细胞比外周血CIK细胞具有更强的增殖能力,且相比于外周血CIK细胞,UCB-CIK细胞对不同的恶性肿瘤细胞系均显示出较强的杀伤活性[32]。临床试验结果表明,UCB-CIK细胞过继免疫治疗后,中晚期肺癌患者的免疫功能有明显改善。在其他恶性肿瘤中的实验结果表明,UCB-CIK能够延长生存期,改善患者生命质量,且无不良反应[33]。UCB-CIK细胞为后续的细胞免疫疗法提供了细胞工具。
DC主要来源于骨髓、外周血和UCB。相较于骨髓和外周血,UCB来源的DC(UCB-DC)免疫功能较强,细胞增殖能力较强,且GVHD水平和程度均较低,因此,UCB-DC也可以广泛应用于肿瘤疾病患者的治疗中[34]。而单位UCB中可用的DC数量有限、扩增效果比较低等原因限制了其进一步的使用。因此,寻找新的能够有效扩增UCB-DC的细胞因子或小分子化合物值得进一步研究。
6 总结与展望
UCB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细胞来源,其不同组成成分均可应用于恶性肿瘤疾病患者的治疗中。目前,UCB的使用已经从仅限于儿童患者的造血移植发展到过继免疫细胞治疗。对UCB的研究克服了UCB和HSC应用的局限性,显著改善了造血和免疫功能的恢复。然而,UCB中HSC、EPC及免疫细胞等的含量仍然不足,在UCB衍生细胞的新时代,如何获得更高数量的目的细胞仍需继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