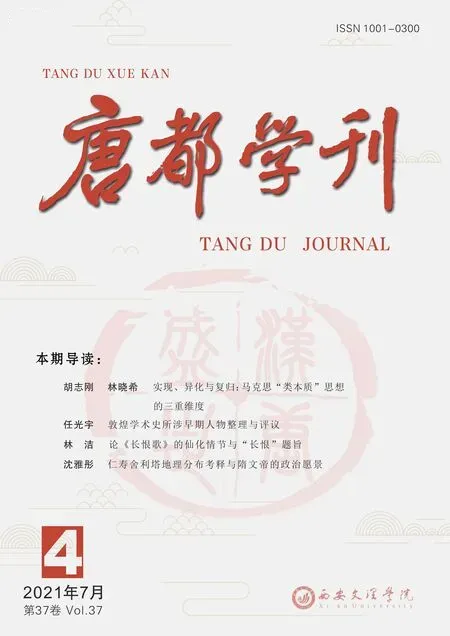明责·知耻·节制
——张锡勤先生论当代社会道德建设之关钥
桑东辉
(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国学院, 哈尔滨 150080)
先师张锡勤先生(1939—2016)是当代著名的中国伦理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专家,其专注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研究和中国近代哲学研究,深耕有年,斩获颇多,著作等身,影响甚广,在中国伦理学和中国哲学领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风格且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力。张锡勤先生不仅专注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和近代思想文化史方面的研究,而且十分关注社会现实,以古鉴今,推动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到了晚年,张锡勤先生更是针对突出的社会道德问题,一再撰文,意在纠偏除弊,以助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2016年,张锡勤先生遽归道山,于今已五年。这期间,有多位学者撰文缅怀先生,并阐述先生的学术思想。这些纪念论著大多围绕张锡勤先生的近代思想研究和传统伦理思想研究展开,如柴文华、关健英、魏义霞、张继军(1)柴文华、罗来玮《略论张锡勤先生对中国伦理道德史的研究》,载于《求是学刊》2017年第3期;关健英《简论张锡勤先生的传统文化观》,载于《求是学刊》2017第3期; 魏义霞、李洪杨《论张锡勤先生的梁启超思想研究》,载于《学术交流》2017年第5期;于跃、张继军《张锡勤先生对“五常”思想的阐释》,载于《求是学刊》2017年第3期。等学者围绕张锡勤先生的思想史研究从不同角度做了深入的分析和评价。笔者非常赞同和服膺上述学者对张锡勤先生学术的分析评价,也曾撰文对张锡勤先生伦理思想史研究的核心要义进行阐发(2)桑东辉《张锡勤先生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基本精神的发掘与提炼》,载于《知与行》2018年第2期。。笔者总感到,张锡勤先生的著述虽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思想史研究领域,但并非局限于对过去时代思想的梳理,更非不问世事地钻故纸堆,而是在皓首穷经的同时,极其重视学术研究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张先生不仅是一位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大家,更是一位深切关注现实道德建设的理论家和践行者。他在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中,不乏对当代社会道德状况的关注,其晚年在《人民日报》等媒体上发文,针对社会上的道德问题及道德建设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将明责、知耻、节制作为当代社会道德建设的关键和枢纽,一再加以强调。
一、责任与使命
在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张锡勤先生认为责任和使命对于实现这一民族复兴大业至关重要。在张锡勤先生看来,不仅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要带头担起复兴民族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自觉高扬传统的弘道精神,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而且主张民族兴亡、人人有责,每一位中国人都应肩负这一历史责任,为民族复兴大业贡献力量。
首先,张锡勤先生详细考证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出处和播衍,提出了“民族兴亡,人人有责”的时代最强音。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小考》一文中,张锡勤先生以深厚的史料功夫和考据功底,追溯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出处和流衍,指出在明末清初时期顾炎武提出的实际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1]。尽管顾氏这一提法实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先声和源头,但其原话远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样朗朗上口,缺乏战斗檄文的明快性和号召性。据张锡勤先生考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脍炙人口的名言乃近代维新思想家麦孟华等人首倡。近代维新运动期间,面对瓜分豆剖、列强环伺的民族危机,受顾炎武思想的影响,早在1899年,有识之士就提出“天下存亡,匹夫有责”的主张。1900年3月,麦孟华更是振聋发聩地喊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最强音。这句话后来经过梁启超、孙中山的多次引用,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变得家喻户晓。那么,张锡勤先生下大力气考证这句名言的出处其良苦用心何在呢?笔者认为,张先生详细考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名言的出处绝非仅仅出于好古敏求的史家精神,更体现了其关注现实、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赤子情怀。
遍读张锡勤先生著述不难发现,张先生对社会转型期的国家民族命运十分关注。张先生的研究领域虽然主要集中在近代思想文化和传统伦理思想方面,但他非常关注明末清初思想家对近代思想文化的影响。在他看来,明末清初是一个社会转型期,近代又是一次社会转型期,当代社会也处在社会转型阶段。每一个社会转型期都会面临纷繁复杂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讲,转型时期关乎国家民族的命运,关乎民生福祉。因此,张锡勤先生非常重视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文化建构,极其服膺自顾氏滥觞、至近代广为传扬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千古名言。在张先生看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仅在近代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极大地激发了国人爱国主义精神,唤起了国人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而且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对激发人们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激情,依然继续起着持久的激励作用”[2]437。基于此,张锡勤先生在2015年5月6日《人民日报》“大家手笔”栏目发表了《民族复兴,人人有责》一文。在该文中,张锡勤先生回顾了中华民族发展奋斗的历史,指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大力弘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并基于民族复兴的大业与每个国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每个人的个人利益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相一致的认识,提出了“民族复兴,人人有责”的主张。在张先生看来,民族复兴必须落实到每个中国人,这是每个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在这篇文章中,张锡勤先生反对的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普通群众的责任感缺失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置身局外、做旁观者的消极“看客”心态;提倡的是全民爱国奉献、人人爱岗敬业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概言之,张锡勤先生的“民族复兴,人人有责”观念的落脚点在于“强化全民的社会责任意识”[3]。
其次,张锡勤先生系统回顾了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为当代知识分子担纲起时代赋予的责任提供了传统精神基因。在《民族复兴,人人有责》一文中,张先生虽然重点在谈全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凸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人都应是参与者,人人肩上都须担负责任”[3]的思想主旨,但他对社会精英在民族复兴大业中的作用也特别关注,指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家国情怀,优秀士人则有一种先忧后乐、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责任感。这是中华民族历经内忧外患而百折不挠、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精神支柱”[3]。围绕时代精英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张锡勤先生曾以古代士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例,专门撰文阐述。张锡勤先生晚年学术论著中非常重要的一篇论文是发表于《道德与文明》2013年第5期的《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先生写成此篇文章后交由我进行打字校对,我对这篇宏文较为熟悉,也曾就这篇文章的创作主旨求教过先生。张先生告诉我,他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当代知识界的某些乱象,特别是某些知识分子丧失道德底线,唯利是图,缺乏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责任感。因此,先生这篇以古鉴今的文章是有感而发的,以期唤起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张先生看来,士人是社会的精英,是时代的良心。如果士人丧失了责任感,背离了志于道的使命,则必然对社会进步产生负面影响,阻碍社会的发展和思想文化的繁荣。在这篇文章中,张先生追溯了中国古代士的产生及其所应具有的明道、志道、传道、守道、殉道的责任和担当精神,将古代士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集中在对文化的传承、对社会的批判、致力道德教化和匡救等方面。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对古代士人与近代知识分子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辨析,进而指出在“志于道”这一亘古不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基础之上,由于所处时代和阶级地位的变迁,古代士人所志的道与近代知识分子所志的道是不同的。古代士人坚守的道是一种“等级责任”,强调的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近代知识分子则为挽救民族危亡,借鉴西方“主权在民”的民权观念,提出人人享有权利和义务。张先生这篇文章主体部分是在探讨古代士人的产生、使命感和责任感,兼及近代社会转型时期,近代知识分子对古代士人精神的扬弃,并无一字一句涉及当代社会。但透过这篇文章的表面字义,结合先生自述创作意图,不难读出其中的微言大义。概言之,张锡勤先生有感于当代知识分子中存在的使命感淡化、责任感缺失问题,呼吁广大知识分子要切实以国家振兴、民族复兴为己任,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同时要满怀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自觉对不良社会现象进行批判,谋划匡救,成为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中华民族之脊梁。张先生强调士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始终坚持唯物史观,主张与时俱进。一方面,当代知识分子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士人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和矢志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在具体践行中要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围绕推动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围绕增进人民福祉,殚精竭虑,勠力同心,贡献自己的才智和力量。
二、廉耻与荣辱
知耻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种基本属性和特征,亦是一个国家、民族文明程度的表征。张锡勤先生常常强调人要知耻,他对《管子》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主张和儒家的知耻而后勇以及义荣义辱等观点极其重视和服膺。在张锡勤先生看来,羞耻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自觉之一,教人知耻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首要任务。也就是说,树立人的知耻心是完善个人和构建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基础。
首先,张锡勤先生详细论证了廉与耻的要义,在他看来,廉主要是一种对官员的道德约束,是一种自律性的美德,所谓“廉者不求非其有”(3)参见刘向《说苑·卷十七杂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不仅追求非其所有违背廉的精义,而且即便对于介乎可取与可不取之间的,君子也不应取,取则背离廉的宗旨,所谓“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4]《孟子·离娄下》。通过不苟取,传统道德将廉洁观与义利观紧紧结合在一起,所谓“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然后取”。除此之外,张锡勤先生还论证了廉与耻的辩证关系,即廉者必知耻、知耻则能廉。也就是说,知耻是廉洁的前提,廉洁则是知耻的表现[5]209。何为耻,朱熹指出:“耻便是羞恶之心”[6]。用今天的话说,耻就是羞耻心、知耻心。张锡勤先生给耻也即羞耻心下了一个相对精准而严谨的定义,即“羞耻心是基于一定的是非观、善恶观、荣辱观而产生的一种自觉的求荣免辱之心,是人们珍惜、维护自身尊严而产生的情感意识”[5]210。进而,张锡勤先生将作为情感意识和社会心理的羞耻心发展到知耻的道德自觉和道德约束层面,所谓“知耻是促成道德行为的心理动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自觉”[5]210。张先生引经据典,梳理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廉耻内涵,特别是有关耻的内容,指出重耻是中国古代的重要道德规范,“人不可以无耻”是传统伦理的基本要求。如果说廉更多的是一种官员道德,作为“人道之端”“义之源”的耻则是一种全民性的普世道德自觉。诚如龚自珍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个人身份地位的不同,无耻的危害也各不相同,即所谓的“农工之人、肩荷背负之子则无耻,则辱其身而已;富而无耻者,辱其家而已;士无耻,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无耻,名之曰辱社稷”[7]31-32,但如果全民无耻,社会道德沦丧,则国将不国。因此,龚自珍大声疾呼国家民族复兴当“以教之耻为先”[7]31。张锡勤先生一再强调并认同于古圣先贤将知耻心作为培养、增进道德的前提和第一步,认为唯有知耻才能激发“人们对丑恶、堕落的憎恶和对美善、上进的向慕”[5]211,从而成为“人们为善去恶、积极向上的内在驱动力”[5]211。值得注意的是,张锡勤先生认为知耻心与荣辱观息息相关,指出知耻心这种激励人们为善向上的内在驱动力是“出于人们求荣免辱、维护尊严之心”[5]211,这也呼应了张锡勤先生在给羞耻心下定义时所强调的羞耻心基于荣辱观的理论预设。
其次,张锡勤先生系统阐释了传统的荣辱观,他指出:“荣辱观与是非观、善恶观以及人生价值论密不可分”[5]55。因此,中国传统的荣辱观也必然打上时代的、阶级的烙印。在强调礼、义、廉、耻的古代社会中,义不仅决定人禽之别,而且成为判断荣辱的标准,故有所谓的义荣义辱。也就是说,遵义则荣、悖义则辱。在古代思想家那里还有很多类似的论述,如“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8]《荀子·荣辱》,“辱莫大于不义”[9]《吕氏春秋·贵生》,“由义为荣,背义为辱。轻重荣辱,惟义与否”[10]。
当然,在传统道德体系中,义并非仅仅是一个德目,有时候还是对仁、义、礼、智、忠、孝等道德的概称,因此义荣义辱的范围也不仅仅局限于遵守义德与否,而是涵盖了对所有道德规范的遵守与否。孟子就曾说过:“仁则荣,不仁则辱”[4]339,但在等级社会中,那种完全摆脱等级地位影响的纯粹道德境界的荣辱是不可能真正存在的。对此,古代先哲也敏锐地察觉到,并将荣辱做了义(即道德精神)与势(即世俗物质)的区分,形成了义荣与势荣、义辱与势辱的分野。如《荀子·正论》中曾对此进行了较为详尽客观的分析,其曰:“有义荣者,有势荣者;有义辱者,有势辱者”。何谓义荣,即所谓“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何谓势荣,即所谓“爵列尊,贡禄厚,形势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卿相大夫”;何谓义辱,即所谓“流淫污僈,犯分乱理,骄暴贪利”;何谓势辱,即所谓“詈侮捽搏,捶笞膑脚,斩断枯磔,藉靡舌”。荀子区分义荣义辱与势荣势辱,目的在于强调君子与小人的道德选择不同,所谓“君子可以有势辱而不可以有义辱,小人可以有势荣而不可以有义荣”,凸显的是“义荣势荣,唯君子然后兼有之;义辱势辱,唯小人然后兼有之”[8]《荀子·正论》的义理。总的来看,在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受重义轻利思想影响,人们都把义荣、义辱放在首位,而不在乎地位高低、财富多寡所带来的世俗荣辱。所谓“位不足以为尊,而号不足以为荣”;“位下而义高者,虽卑,贵也。位高而义下者,虽贵必穷”[11],“贱而好德者尊,贫而有义者荣”[12]《新语·本行》。对于古人所分析的义荣义辱、势荣势辱现象,张锡勤先生认为在今天社会仍然同样存在。“因此,荀子等人的这些议论对于今人正确认识荣辱,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依然具有参考价值。”[5]58
在晚年,张锡勤先生痛切地感受到社会羞耻心的钝化和弱化,特别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有悖公序良俗的现象以及那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道德迷失心态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出于对社会荣辱观乱象的忧虑,张锡勤先生不满足于从纯学术研究角度来探究传统的廉耻观和荣辱观,而直接针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羞耻心缺失问题,写出了《警惕羞耻心的钝化》的宏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毋庸讳言,羞耻心逐渐淡化、弱化、钝化是当今社会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13]。在张锡勤先生看来,之所以会出现羞耻心钝化和知耻心淡化的问题,根源在于荣辱观的错位,即不知何者为真荣、何者为真辱,从而滋生爱慕虚荣的社会心理,甚至出现以崇高为迂腐、以卑劣为能耐的道德悖论。对此,张锡勤先生指出:“一个人皆知耻的民族是成熟的、有希望的民族,一个人皆知耻的社会是文明、健康、充满正能量的社会”[13]。今天,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警惕羞耻心钝化、弱化现象”,自觉“筑牢羞耻心这道心中的道德堤防”[13]。张锡勤先生对羞耻心和荣辱观的论述,不仅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而且是面对新时代的与时俱进,他所坚决反对的并不是时代发展下新的荣辱观,而是那些违背社会道德的荣辱观之倒错、羞耻心之迷失。具体而言,张锡勤先生非常反对社会上流行的浮躁心态、虚荣心理和审丑恶俗,以及一些人对失德悖俗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道德错位。
三、节制与适度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需要社会主义道德来调节。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个人欲望的实现、个人愿望的满足、个人利益的平衡等都面临着一个与国家、与集体、与社会相互协调的问题。张锡勤先生痛切感到当今社会“拜金主义抬头,一些人越来越自我膨胀,甚至丧失理性、失去节制,表现为任性、放纵、乖戾。这是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14]。基于此,他撰写了《节制是良好品德》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2015年11月16日的“大家手笔”栏目上,意在“提醒人们,要做一个懂节制、能节制的人”[14]。
(一)张锡勤先生将节制与理性紧密结合在一起
在张锡勤先生看来,“所谓节制,是指在理性的指导下,对利益、欲望、情感等进行控制、调节,使之合理、得当”[14]。也就是说,节制是服从于理性原则的,人的理性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古往今来,在平衡利益、欲望和情感方面的理性,大体离不开义利之辨、理欲之辨、公私之辨。张先生从传统文化的源头追溯了传统的义利观、理欲观和公私观,并使之成为节制的理性阈限,以此把控和平衡人的个体欲望和利益,使人自觉调节义与利、理与欲、公与私的冲突,达致节制和平衡。
第一,围绕节制与义利观的关系,张锡勤先生认为节制“首先表现为对利益取舍的节制”[14]。这就将节制的理性基础定位在义利观上,通过对传统义利观的辨析意在廓清长期以来人们对孔孟等先秦儒家排斥利、否定利的认识误区,指出不仅先秦时期人们普遍重视利,所谓“言义必及利”[15],而且孔、孟、荀等先秦儒家思想巨擘也都正视人的欲望,并不是简单否定利的存在。孔子就曾经肯定“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4]137。孟子更是肯定富与贵都是“人之所欲”[4]433。荀子也将义和利视为“人之所两有也”,即便是尧舜,也“不能去民之私利”[8]《荀子·大略》。即便是宋儒也不否认利是人生的基本需求。但总的来说,儒家伦理认为利(即物质需要)只是基础价值,并非最高价值。从根本上讲,人的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值。所谓“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4]98。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候,个人利益都必须要受制于一定的社会道德准则”,而“要想维护社会群体的整体大利,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欲望必须是、只能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义”[2]328。对利的适当追求、以义制利是一个人做到节制的道德理性基础。
第二,围绕节制与理欲观的关系,张锡勤先生认为节制也“表现为对欲望的合理调控”[14]。在张先生看来,理欲观与义利观一样,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范畴,对历史上的道德伦理的走向有着重要的作用。在锡勤先生看来,理欲观所要探讨的是“人的生理需求、物质欲望与道德理性、社会道德准则间的矛盾,及其解决方法”[5]36。张先生在比较儒释道对于欲望的不同界定和伦理要求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儒学思想史上有关人的欲望理论,重点辨析了宋明理学的天理与人欲关系学说,指出宋明理学的理欲观实际是一种导欲、节欲说,应属于一种“比较健全合理的伦理学说”[5]45。一方面,其承认欲望是人的自然本能,不可以禁绝;另一方面,其又揭示出欲望与社会道德准则之间的矛盾,以及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矛盾。基于此,其主旨在于既反对纵欲也反对禁欲,而是主张导欲、节欲,即主张通过道德理性、道德准则来调节个人欲望与社会道德准则之间的矛盾[5]45。张锡勤先生还通过对宋儒“存天理,灭人欲”这句名言的知识考古,进一步阐发了程朱维护等级统治的道德努力,廓清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以满足人们最基本生存需求为正当之天理、以超过基本需求为不正当之人欲的认识偏狭,纠正了对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误读[16]。说到底,张锡勤先生基于传统的以理导欲、以理节欲、以道制欲思想,并有鉴于历史上纵欲失德、纵欲败事、纵欲亡身等前车之鉴,主张将人的欲望控制在社会道德准则的范围内,而不能走向纵欲或禁欲的两个极端。在《节制是良好品德》一文中,张锡勤先生主要针对某种程度上出现的物欲横流、挥霍无度、侈靡浪费等社会现象进行针砭和警示,重在反对纵欲。
第三,围绕节制与公私观的关系,张锡勤先生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公私观对节制品德的作用,但从他对传统公私观和近代公私观的阐发来看,公私观与义利观、理欲观一样,都是调节个人与社会、个人利益和欲望与社会整体利益和道德准则之间关系的杠杆。张先生认为,尚公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并将尚公、重礼、贵和概括为中国传统道德的三大基本精神。在张先生看来,以尚公为主旨的传统公私观是对人的社会性的体悟,“它要求人们重视整体利益,尊重他人利益,不可损公肥私、损人利己,这对协调群己、公私关系无疑是必要的”[5]52。但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传统公私观也存在一些消极因素,特别是一些专制君主将“我之大私”视为“天下之大公”(4)参见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从而否定、漠视、压制、侵蚀人们的个人利益。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和近代思想家对传统公私观进行了大胆的反思和批判。特别是在近代道德革命中,针对传统公私观的弊病,提出了合理利己主义。一方面,他们反对以公覆私,充分肯定私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他们虽然高扬私的大纛,为私大唱赞歌,但他们并非主张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更坚决反对以私废公。“在中国近代,几代新学家之所以一再冲击、清算中国古代尚公的公私观,其实主要是为了寻找如何更好地处理公私关系的途径,而不是要废公。”[17]概括起来,大体途径有三:公私两利说、“绌身伸群”说、“以私成公”说。不管怎样,私往往与欲联系在一起,所谓私欲就体现的是个人愿望和利益追求。这种个人愿望和利益追求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能损害国家、民族、社会的利益。一言以蔽之,合理控制私心、私欲、私利就是所谓的节制。
(二)张锡勤先生将中庸精神注入节制理念中
在认同义利观、理欲观、公私观是节制品德的理性阈限的基础上,张锡勤先生指出:在合理限度内的私心、私欲、私利是被认可的,只有超出范围的,才会导致无节制的问题,进而强调中庸之道、从容中道的度无疑是节制品德的实操杠杆,其使得义与利、理与欲、公与私在“过犹不及”的中庸范围内取得动态平衡,既不过分强调崇义贱利、以理灭欲,也避免那种见利忘义、人欲横流、私而废公的无节制,而达致一种有节适度的社会和谐。在张先生看来,儒家所强调的中庸既是一种方法论,又是道德实践原则。“就伦理学而言,中庸主要是指实行道德、选择道德行为的方法原则。”[5]276作为哲学方法论和伦理原则,中庸有丰富而复杂的理论内涵,在做事方面,中庸强调的是中和、执中,主张恰到好处,反对过和不及。但中庸并非是僵死的执中,也绝非骑墙主义和乡愿,而是一种灵活的方法,是执中与行权的结合。基于这一理论,张锡勤先生强调的节制就是把握义与利、理与欲、公与私之间的度,针对社会上一些纵欲、侈靡现象,张先生更多地强调要节制私利和私欲。从中庸本义上讲,亦不可以义、理、公来过度压制和否定利、欲、私。因此,张锡勤先生特别指出:“节制并不是遏制、束缚个性。……也不是提倡做一个生活枯燥乏味、刻板拘谨的人,更不是让人无所欲求、走向禁欲。”[14]张先生所极力反对的是任性、放纵、无度、乖戾等没有节制和缺乏节制。
张锡勤先生所努力追求和大力弘扬的是“从容中道”和恰到好处。在他看来,节制的核心就是要求人要有节、有度。“惟有懂节制、能节制,才能使个性在社会准则许可的范围内得到正常、健康发展。”[14]节制在西方伦理思想范畴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道德规范,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对节制这一品德多有系统阐述。严格说来,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节制并不像仁、义、礼、智、信、忠、孝、恕等那样是一个传统道德德目,但节制的道德意蕴涵盖、渗透于各传统德目和中庸、慎独、修身等道德修养论中,特别贯穿于义利、理欲、公私等道德范畴中。张锡勤先生对节制品德一直非常重视,其关于节制的思想主张贯穿于其《中国传统道德举要》一书中,特别集中反映在义利、理欲、公私、荣辱、苦乐、勇、谦、让、宽厚、贵和、修身、慎独、自省、经权等具体条目中。说到底,要做到节制必须守节、有度、坚守底线,将中庸思想精髓活学活用到日常生活中。
节制是张锡勤先生针对社会上拜金主义抬头、纵欲侈靡之风渐起而提出的对治策略,旨在提倡社会成员懂节制、能节制,以此来遏制社会上甚嚣尘上的拜金、纵欲等不良倾向,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和谐社会。
综上所述,张锡勤先生始终致力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致力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精神与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相结合。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某些羞耻心钝化、责任感缺失、拜金纵欲倾向抬头等道德问题,他将责任感、羞耻心、节制品德作为当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和关键,通过强化全民的责任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复兴大业;通过明德知耻,在全社会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荣辱观;通过倡导节制品德,改变社会上那些纵欲、侈靡问题。通过明责、知耻、节制,来遏止和解决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道德问题,助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张锡勤先生是一位治学兼修身、奉行知行合一的长者,他所阐扬的优秀传统道德,也是他所时刻践行的道德操守。他曾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双知双淑斋”,不仅体现了他所倡导的明责、知耻、节制的道德主张,而且体现了他将伦理学研究与个人道德践履相结合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