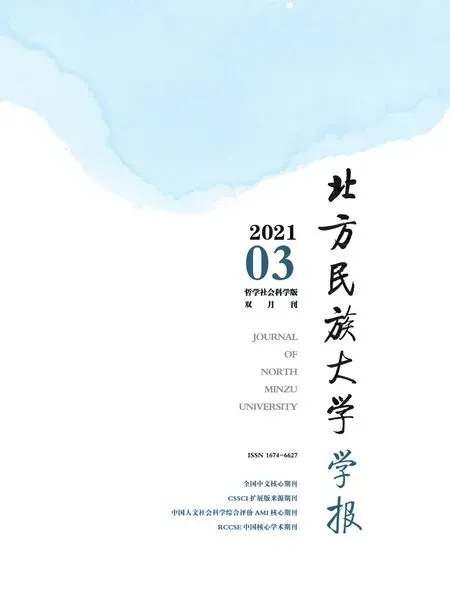舆论与社会:《盛京时报》所见1908年奉天商人抗“房捐”事件
彭 爽,曲晓范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
对近代奉天商人群体的相关研究,集中于商会的整体变迁、商会组织或商会与地方社会的整体关系,对商会与政府以及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商会与政府的合作互补,缺乏对奉天地方商人群体内部的研究,亦没有呈现地方与国家之间的紧张互动关系。本文通过考察《盛京时报》这一舆论空间所呈现的1908年奉天商人抗“房捐”事件发生的动因及经过,试图阐释清末奉天地方内部、地方与国家间的重层权力互动关系,从微观视角认识清末奉天商人群体,从而探讨舆论与城市社会转型及发展的内在关系。
一、抗“房捐”事件的社会动因
清末新政时期,东北三省屡遭兵燹,迟至1907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后,才开始实行改革。其改革过程调适和冲突并存,1908年发生的抗“房捐”事件正是改革推行过程中出现的冲突。
(一)清末奉天商会与警察制度之间的张力
奉天商会的最初形式可追溯到1862年成立的公议会,由省城工商业户自行组织设立于盛京长安寺。公议会成立之初,“东西各分四旗”[1(]69),以维护商人利益、调节商业纠纷为主要责任。此外,还代替政府对地方商业市场进行管理,如负责对每日的市场银钱、典当、粮食价格进行公议定价。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不断兴盛,奉天当局于1874年扩建公议会组织,将城关内外街道分为16会所,各分会按照各街道商铺的多寡,推选3~5人或7~8人不等,负责各分会相关事务,省城内各行业还选出代表1人,于每月朔望两日莅会议事。相较于最初的公议会,此时各会所还兼有“支办官差及庙会、水会”[2(]54),各街一应杂费均由各会首承办,并负责政府临时摊派的铺户捐纳。
随着城市商业的不断发展,人口和物资的大规模流动打破了原本相对封闭的区域经济模式,以地缘和乡缘为基础的公议会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1903年,清政府成立商部,颁布《商部奏劝办商会酌拟简明章程折》,筹划设立商会。在这一策令之下,盛京首先改商业公议会为商会,16街道各会头改称会董[1(]12)。次年颁布的《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明确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会垣、系城埠,宜设立商务总会,稍次之地设立分会。”[3(]22)此时,日俄战争爆发,奉天地区社会动荡,1906年年底,商会改组,同年,农工商局成立商务总会,公举孙百斛为总理,组织会务,订立注册章程[2(]57),并根据《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规定商会设总理、协理各1名。总理由会董推举,经地方长官呈报商部批准后产生,规定担任商务总理者,必须是“商号柜东或经理人,年贸易额为一方巨擘者”[1(]12),才具有资格[4(]54)。总理、协理的职责为“保商振商”,“凡商人不能申诉各事,该总协理宜体察属实,与该地方衙门代为秉公申诉”,“如不得直或权利有所不及,应即体察本部核办”[3(]22),并负责向商部如实报告地方商务情况。
清末警察制度的建立使地方城市绅商的社会功能逐渐弱化。近代奉天警察制度初建于1902年,增祺在任期间,设警察总局,下设文牍、承审等处,却是“有名无实、规则毫无”[5(]卷5:244)。赵尔巽主政东北后,在省城设总局1处,分局7处,但地方绅商依然在地方公共事务中有一定的活动空间。1907年,徐世昌全面改革东北官制,提出将“原户、礼、兵各司改并民政司,掌办理民政、巡警、缉捕等事”[5(]卷8:457)。巡警局下设总务、行政、司法、卫生、收捐5科,并设稽查处及警卫、消防、侦缉、清道4个队,分局8处[6(]卷143:3323),建立了奉天社会较为全面的警察制度。
如上所述,新政实施前,绅商直接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其活动空间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新政实行之后,随着商会和警察制度的逐步建立,地方绅商的活动空间逐渐遭到中央权力的挤压,被迫退出城市公共事务领域,而地方绅商并不甘心。奉天商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潜藏于新政的大流之下,抗“房捐”事件即是这一矛盾累积后的集中爆发。
(二)清末奉天经济秩序的紊乱
1901年,清政府发布上谕,实行新政改革,此时政府国库空虚,地方新政经费主要由地方筹措。东北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更需“举办新政,振兴庶务,收回主权”,但是“惟财政支绌,筹款维艰,颇形棘手”[7]。徐世昌考察奉天后指出:“现在举行各政,收税稍繁,统计奉省课税,有四十余种名目,民间颇以为苦,然用款繁多,无如何也。”[5(]卷5:242)在城市,这些课税基本加于商人身上,在农村则主要为土地税。自日俄战后,奉天地区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商业发展更是落后于其他省份,随着地方政府的治理,情况逐渐有所好转。然而因政策多变,市场情况极不稳定,每逢节日之后和青黄不接之时,便会出现商业不振气象,也会有商铺闭门歇业。1908年,奉省度支司规定商民缴纳官税一律使用大龙元,造成市场币制紊乱,原本脆弱的市场经济受到强烈冲击。奉省原以银为本位,且市场多流通铜圆,10枚铜圆可兑换1银圆,却只能兑换8角龙元,而在实际使用时,大龙元价值与小银圆相等,只能换取10枚铜圆。大龙元的使用使“钱法之杂乱已达极点”,普通民众深受其累,怨声载道,各商铺均受影响,“生意形极萧条”,省城商业颓废日剧,“咸有不支之势”[8]。9月伊始,已有8家商铺关闭[9],中秋节后又有3家商铺倒闭,外来货物也因币制市场紊乱,“多裹足不前”[8],“商务前途之不振,岌岌可危矣”[10]。政府既无法解决币制问题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又多次驳回商人请求免抽“房捐”的请求,致使商人反抗情绪愈加强烈,不仅阻碍了商业发展,也使底层民众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民众日渐倾向于支持商人,为抗“房捐”运动提供了民意基础。因此,币制市场紊乱诱发的商业危机是抗“房捐”事件爆发并不断加剧的催化剂。
1908年奉天巡警局加收“房捐”则是事件爆发的触发点。奉天警察制度设立于1902年,赵尔巽主政东北后,组织规模有所扩大,奉天省城警察人数增至630名[5(]卷5:244)。1907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全面推进东北官制改革,奉天省城警员人数达到1 265人,1909年则达到1 846人[11(]12)。随着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所需经费亦逐年增多,省城巡警局全年的经费支出白银为343 753两,占民政司总支出的一半以上[12(]卷六:943)。奉天省城巡警局的筹办经费主要来源于奉天省城官地房屋的租税,至于为何又要加收“房捐”,《盛京时报》做了如下报道。
省城各处空闲官地,商民建筑房屋已达上千余间,每月所入官租归巡警局作正开销。现因民政司以该司空虚,而办理一切在在需款,是以呈禀都宪,请将巡警所收地皮官租归该司经理,当蒙都宪允准,遂将此款拨归民政司,而巡警局因款项提出经费无着,遂禀明都宪加捐商民房捐,以资办理巡警经费,亦蒙都宪俯允。[13]
因官地租税拨归民政司,巡警局经费筹措无着,于是决定仿效天津巡警局,对在官地所建房屋征收租税的同时,加收“房捐”,美其名曰并非针对商户征收捐税,而是针对房主,但是这笔捐税最终依然加在商户的房租上。对于新政中的众多抽捐,商民本已有怨言,“房捐”再起,便成为矛盾爆发的导火索。矛盾爆发后,商人一再反对,甚至几度罢市,但政府因新政资金缺乏,“房捐”作为巡警局的资金来源,不可不抽取。于是“房捐”之事一时成为商人与政府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商人不断请求免捐与政府的屡次断然拒绝中,矛盾发酵升级。
二、舆论空间:《盛京时报》所见抗“房捐”经过
奉天政府为筹办警务而宣布抽取“房捐”,商人对“房捐”的不满最初表现为各会董、行业代表与商务总理之间的龃龉,随着矛盾加剧,不满情绪逐渐转向政府。为维护自身利益,商人代表多次向政府请求免捐被拒。于是,商人逐渐团结起来,向上请求中央权力的介入,向下动员民众,取得民间力量的支持,形成与奉天政府在力量上的抗衡。1908年8月初至10月末,《盛京时报》从商人的要求和行动、政府的举措、民间的反应,以及后续社会影响等多个维度对该事件进行了追踪报道。
(一)抗“房捐”事件的发生
1908年8月8日,《盛京时报》第五版“东三省新闻”一栏刊载了一则题为《商会全体与商务总理之大冲突》的新闻。据载,奉省为筹措创办巡警局的经费,将于1908年8月27日开始,对各商铺“酌定租价”,“征收房捐,补助警察经费”[14]。为此,省城商务总理赵国廷于1908年8月6日在长安寺召集省城内外各行商代表人,劝说商人缴纳“房捐”,与会会董及商人并不赞同,甚至发生肢体冲突[15]。为解决矛盾,奉省督宪徐世昌召见各商董面谈,谈话内容不得而知,但巡警局依旧催缴“房捐”,省城各关代表及各商铺执事也于9日上午11点在各关商务会召开会议,重申“绝不认捐”,如果政府“不体恤,勒令纳捐”,各商人也绝不示弱,“惟有一体闭息”[16],可见事情并未解决。此时,商人们只是有此决心,却未付诸实践,实际上,他们决定采取联名上书的形式请免“房捐”,签名者达2 000余人,希望总商会上呈联名书,以维护商人利益,却被总商会杨协理和沈君婉劝阻,言“将来必有办法,不可操切从事”[17]。
面对这一情况,一方面,政府贴出告示,申明加收的“房捐”为筹措办理巡警的经费,又强调巡警是为社会安定而设;另一方面,巡警总局饬令各分局“派巡警一名,收查各户”,于12日起,“一律崔赴总局纳捐”[18]。此时,作为政府与商界中间人的商务总理赵国廷称病闭门不出,甚至提出辞职,但未获准许。政府希望各商董能息事理解,劝解商人服从政府政策,巡警局申明殴打赵国廷者非商会绅董,而是散户商铺经营者,进一步劝说各绅董“不可稍存意见互相龃龉而涣商情”,“仍宜与总协理和衷共议,以济时艰”[19]。各关商会代表及各铺执事提出,如果政府执意收“房捐”,他们便罢市。面对政府的压力,商人们依旧寄希望于商务总会与政府的调和,各商董决定遵从训令,“前往公请”,挽留赵国廷继续任职商务总理,关于联名上书一事,希望总商会呈请劝业道转呈总督徐世昌,言明商人请求免“房捐”的要求[20]。
在政府的干预下,部分商人暂时妥协,“然终非甘心乐输”。为了缓和矛盾,政府受理了商人的上书,并言“商民等如有意见,尽可据实直陈,听候转请宪裁”[20]。然而,商人的上书虽被受理,政府抽取“房捐”的态度却没有任何转变,基于这一现状,商人决定公举代表进京请愿,省城各街公举1人,约43人,于16日搭乘京奉火车上请民政部,希冀中央政府予以解决[21]。此时,总商会接连下帖各商会代表,召开商务会议,希望能够和谈解决,但“全体商董均未到会”[22]。商人以此种形式显示了对总商会的不信任,也显示出此时商人由对政府施政已由不满发展为实施抗议。
(二)抗“房捐”事件持续发酵
面对商人的强烈诉求,政府依旧饬令巡警总局照常清查户口,为收取“房捐”做准备。为缓和商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不断有官员呈请“酌量免收”,但政府认为“当次立宪时代,凡官府黎民,无分贵贱,均在巡警保护之中,未便歧视”,并斥责呈请之官员应提倡捐纳,“以为众民之表率,何得禀恳免捐,致生阻力,姝属不和”,因此“批驳未准”[23]。政府虽然驳回了官员“酌量免收”的请求,但也希望能够缓和矛盾,同时又能保证新政经费的充足。奉天政府参考天津“房捐”成案,根据逐户调查后的具体情况划分商民等次,规定商铺抽取5%,民户抽取2%,于调查后第二天持票自行到巡警局缴纳[24]。与此同时,商会代表推举翰林出身的奉天官银号总办孙鼎臣为代表,上书巡警局,“请赐宽免”,巡警局再次拒绝。9月7日,进京上书的商人传来消息,民政部发来电报询问奉天具体情况,“不知奉省上宪如何电覆,所以近来各关户均怀观望”[25]。再加上受商户集聚议论演讲的影响,城内众多民户也加入其中,“民户多于商人,声多民愤”[26]。
事态的发展逐渐脱离政府的掌控,内外双重压力使奉天政府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9月9日,巡警局专为“房捐”一事发布《巡警道白话演说》,再次重申加收“房捐”的原因,并言上缴“房捐”是为公益,希望民众理解支持;12日,再次出示晓谕,鼓励民众配合缴纳“房捐”,然而效果并不明显。于是,巡警局“携《巡警道白话演说》挨户劝谕”[27],定于9月25日开始清查户口,催缴“房捐”。纵然如此,城内几万户商户仅有2 500余户上缴“房捐”,缴纳“房捐”的多为小商户,带头抵抗者又皆为“富商大贾之房主,率皆势力中人”,再加上京城传来好消息,更是增强了商人抵制“房捐”的信心,此时,作为地方政府代表的巡警局与作为商人团体势力的在京代表已形成“不相上下之势,正恐难以和平议结”[28]。至此,政府与商人的矛盾继续发酵升级。
(三)从抗“房捐”到集体罢市
在这场由“房捐”引发的官商抗衡中,政府逐渐失去威慑力,商人团体的力量及影响则逐渐增大。面对省内商民结成团体抵抗“房捐”的现实,以及进京商人请求民政部介入调查和民众对商人活动的支持,奉省政府不得不宣布暂缓缴纳“房捐”。抗“房捐”风潮发生近两个月,这是商民团体首次占据上风。但政府并未就此妥协,巡警局总办“又赴京运动”,待“总办回局,再行核夺”[29]。就在政府宣布暂缓缴纳“房捐”后的10月2日,巡警局再次催缴“房捐”,面对政府的举动,商会分会代表“飞帖传知各户,不令纳捐”,如果巡警局使用强迫手段,拘押反抗之商民,“则众商民惟有一律歇业关闭”[30]。商人们再次以集体罢市予以抗议,此次不同于第一次商会内部会议的提出,而是以“飞帖”将省城各商户团结起来。纵然如此,督宪徐世昌于10月5日继续发布抽取“房捐”告示,告示恩威并施,先是再度申明抽取“房捐”原因,接着说“奉省人民素明公义”,转而又严明政府态度,有“籍端生事,抗违功令”者,“无论官商绅民,一律惩治”,希望商民遵照告示,“迅速照缴,毋再违误”[31]。
就在商人与政府相持不下之时,京城传来消息,不仅“房捐”可免,其他税捐“亦须从末议减”,奉天商人得到这一消息后,“反抗愈烈,精神倍增”,“商权膨胀之大,将来于义务外,官权不得肆然压制云”[32]。面对政府施压,商人毫不畏惧“,沿街飞帖知会各商家”[33],坚决拒捐。面对商人第二次“飞帖”,政府态度依旧强硬。为进一步施压政府,各商董及商铺执事决定于10日起全体罢市,9日晚上知会各行街铺。10月10日上午6点,省城内外所有商店一律闭门罢市“,大清银行、商务书馆,及各官书局、银店、当行,以及东洋各商店,一时风起云应,闭门罢市”[34(]106)。劝业道两次出示劝谕开市,各商铺置之不理,双方僵持不下,罢市次日,省城贫民因“告籴无门”[35(]139)而掀起抢粮风潮。事态发展逐渐脱离当局政府的控制,奉天督署一面派官员镇压抢粮群众,一面向商民妥协,答应释放被捕者。12日,奉天府和承德县劝业道共赴商务总会,劝说各商行开市贸易,至于“房捐”一事,政府、商人各退一步,“酌量末减”,议定“房捐”分两等抽取:10间以上者为头等,按2%抽捐;10间以下者为二等,按1%抽捐,“零星房屋概行宽免”,如此结果“,始得众情,允洽照常开市贸易”[36]。
此次事件的爆发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而触发点是商户与商务总理发生暴力冲突。事件发生后,政府的强硬态度使商民与政府的矛盾不断升级,事件持续发酵,商民多次以罢市的形式予以抵抗。10月10日上午6点的集体罢市纵然是由于商民多次请免“房捐”而未获政府准许的必然结果,但是在这之前还有一个插曲加速了这一结果的到来,即就在商会代表与政府、商务总理矛盾加剧之际,各商会因商务办理公文,需要商务总理盖以关防,赵国廷因“房捐”一事避而不见,商董于是私用关防,赵国廷得知后将之控诉至审判厅,审判厅于10月8日拘传各商董到庭审讯并关押拘留。“众商民大为不服,迭议二日”,9日晚知会各商家于10日一律罢市[37]。这或许说明了历史事件“充满了张力与偶然性,并像现实生活一样无固定轨迹可循”[38(]8)。
三、传统与现代:抗“房捐”事件与清末奉天社会
抗“房捐”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根植于清末奉天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权力纠葛,即商人内部的权力争夺,商人与政府之间的力量较量,同时还蕴含着清末地方与国家之间紧张的权力制衡。它更不是简单的独立事件,通过舆论传播,这一事件成为社会公共事件,提高了市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意识,推进了近代奉天官制改革及城市社会治理。
(一)权力之争:抗“房捐”事件中的重层权力关系
清末新政实施过程中,打破了传统“皇权不下县”的制度模式,随着政府权力的扩张和巡警局的设立,地方精英的权利空间被挤压。奉天商人抗“房捐”事件所体现的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下,新政实施过程中,地方内部、地方与国家多层关系中蕴含的紧张复杂的重层权力关系。
根据1904年颁布的《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商务总会会长应由会董推举产生。事实上,商会本身就是清末新政中的政府行为,具有半官方性质,时任商务总会会长的赵国廷就是经赵尔巽干预而选拔出来的。商务总会与政府的关系过于密切或许会削弱商务总会会长在商人群体中的威信和公信,造成商人群体对商务总会会长的不信任。从舆论报道来看,此次抗“房捐”事件的爆发点是1908年8月6日商务总会会长赵国廷召集商会会董及代表召开会议,因赵国廷站在官方立场,导致与会商人不满,最后发生暴力冲突。当巡警局获批加收“房捐”以作经费后,赵国廷充当政府的说客,劝说商界缴纳“房捐”,参加会议的部分行商与其辩驳,认为货物本已有税捐、厘捐、铺捐、销场捐等,此时又正值奉天“商务困难之际”,又要增加“房捐”,“商力实难支持”,赵国廷却认为“区区之款,亦无大捐,若恐出捐,何不售房歇业以避之”,行商代表闻言,当场指责赵国廷作为商务总理,“不但不庇护众商户,反阿附官员家”,还“出言不逊”[15]。会场众人争吵不下,甚至“有小南关某木铺、大西关某铺等之执事人某等挥以老拳,将赵之鹏扇撕碎,被殴不堪,避于讲案之下”,经劝业道从中调停才暂时劝止[39]。商民指出商务总会会长赵国廷“阿附”于政府,而非为商人群体利益服务。事发之后,赵国廷既未完成政府的任务,也无法取得商人群体的信任,处于两难处境中,赵国廷选择闭门谢客,拒绝参加各商行代表所举行的任何会议,并请求辞职。面对赵国廷的举动,劝业道署总理声称“现未有接替之人,碍难尤准”[40]。在官方介入下,商会各会董表示愿意与赵国廷和解,亦通过商务总会向劝业道提交免“房捐”申请,但并不甘心,“房捐”并未免除,商人群体不得不越过商务总会和地方政府,直接公举代表进京陈情[21]。在事件不断发酵的同时,商人群体对商务总会逐渐失去信任,甚至当赵国廷邀请各商会会董开会商议“房捐”事件时,各商会会董均未到会,“大有不愿赵观察(赵国廷)为商务总代表之意”[22]。其背后或许有奉天官银号总办孙百斛的力量运作,孙百斛作为会董代表进京陈情,请求免捐[41],此次事件结束后,孙百斛便被推举为商务总会会董[42]。
在这场抗“房捐”事件中,商会代表着奉天地方社会,奉天政府则代表着国家政权。政府的步步紧逼使商民反抗愈烈,而政府的退让使商会自我力量不断得到确认。表面上看,冲突的发生缘于经济利益,暗含的却是地方与中央之间由来已久的紧张关系。
从《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可以看出,商会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传统集中式的绅权治理逐渐转向商会式的分权治理,在制度转换过程中,作为地方精英的各商会会董并不甘心就此被政治边缘化。1905年3月,日本军政署提议于次年改警察局为巡警局,负责街道管理,原本由商会负责的地方经济事务也一应交于巡警局办理。在巡警局设立之前,“凡地方商民公共事体,除由官府办理者外,均以公议会为代表,商民之信从商议会颇有积重难返之势”[2(]57)。当巡警局认为商会征收捐项不合规则,要求收回征税权,交由巡警局直接征收时,各街会“始则推延”。本应作为地方社会管理主体的巡警局反而有“登堂入室”之嫌,境遇十分尴尬。由于传统的引力及惯性,商会与政府的矛盾由来已久,并非体现在巡警局一处。如1906年总商会成立之时,原本由众商会会董公举孙百斛为商务总理,后因军督部堂赵尔巽禁止过码,孙百斛因反对而被撤职,各会董一再挽留,但赵尔巽认为孙百斛“始终骄纵,对于官局尚且如此,其对各行商人一味专制……可知未得公共团体之益,已露绅权把持之渐”[2(]57),因而执意撤掉孙百斛总理之职,推举赵国廷为继任总理。商务总理担负着维护商人利益,“使官商声息相通,免除隔膜之弊”[6(]卷115:2643)的责任。就此次抗“房捐”事件,舆论指出:
奉省向有铺捐,系专征商铺征为卫生费,此款本由公益会就各商铺经收,转解卫生局,去年卫生局改归巡警局,而此款亦改由巡警局自行抽收,时公议会绅以权限被削,心实不甘,此次巡警总局以警察费用浩大,款无着落,特禀请督宪添收房捐,适值商务萧条之际,故公议会中二三刁绅遂籍此房捐扰民累商为口实,乘机煽惑众商一律罢市。[43]
在清末新政以前,奉省地方事务多由地方绅士负责,尤“以公议会为代表”[2(]57),巡警局的设立显然要将商会边缘化。以商会为活动组织的地方绅士不会轻易让权于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既不能强制执行,又不便放弃责任”[2(]62)。在这一情境下,国家权力在地方不断遭遇挑战,地方政府亦不让步,传统权力关系在新的社会政治结构中继续存续并发挥影响。
(二)传统地方精英意识的延续与近代西方政治文化概念的传播
1908年,奉天学界发起国会请愿,并联合商界上书请愿[44]。商界本已因各种税捐对政府多有不满,“房捐”一事又使矛盾不断升级,此时,国会请愿运动的发起从侧面助长了这一矛盾。随着学界被饬退出国会请愿运动,商界成为主要社会力量,商会理所当然地成为中流砥柱。各商会代表于8月24日齐聚大南关,听教育总会会长曾有翼发表演说,“各商代表各携签名册本”[45]。“按铺户传发,愿入会者请自行注明年岁、姓名、籍贯、职业”[46],众商踊跃而起,签名者约万余人,更有商民借此希望政府在“房捐”事件上妥协,因此积极支持国会请愿运动。不难看出,商人之中不乏国会请愿运动者,而抗“房捐”事件的发生正好为国会请愿运动助长了声势。与此同时,各地革命运动迭起,更有革命党人从中策动。因此,各商行举代表进京上诉之运动也暗含着被操控的情况,“其代表为某内翰某观察,由商家共搓经费两万元,并持有某宅致某邸之函,以为运动之原动力,闻其目的又不专在宽免房捐而已”[47]。地方社会的动荡不安给奉天政府带来了压力。随着运动愈演愈烈,抗“房捐”逐渐融入社会改革及革命浪潮中,事件的发生及走向逐渐脱离政府的控制,最后,政府不得不以妥协来平息事件。
作为地方之代表,地方精英“倘若在其职位上无法表现出对于社区公共事业的热心,无法实现‘照顾集体面子’的集体愿望,就会失去地方社会的信任。反过来说,这种热心和能力,可以成为地方精英人士自我实现的手段”[48(]166)。《盛京时报》所载教育总会会长曾有翼在大南关的《请开国会之演说》鲜明地传达了地方“领头者”的心理活动。
南省请开国会者已接踵而起,而东三省吉、黑两省业已成就函至奉省学界,以冀三省共结团体,公举代表进京要,请速开国会,矧奉省乃国家发祥之地,又为东三省之首区,商学两界不减于他省,凡我同人当共结团体,请速开国会,以免他省笑我奉省商学两界风气之不开。[45]
当抗“房捐”事件遭遇近代西方政治文化概念的传播和舆论空间的扩张时,奉天政府不得不转变态度,转而寻求新的执政理念和模式。抗“房捐”事件发生后,巡警局多次刊登说明,《盛京时报》亦对此进行了公开报道。事件发生初期,巡警局对征收“房捐”的解释是:“房捐专抽房东与住户,无涉现在各商铺与各街”[49],并下令房主“不得籍口缴纳房捐增长租价”,若违令,“定将该房产由官酌定租价,以示惩儆”[50]。但是商人并不信任巡警局,认为最后依然会转移到自己身上。《奉天省商民会报》一文指出,商民之所以不缴纳“房捐”,是由于“巡警按月出入化销多不清白,并无列表张贴,俾民周知”[51]。舆论要求巡警局公开政务、财政透明,说明这一声音已经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在此文刊登前几日,巡警局刊登了巡警局的支出用度,可以认为是对民意的回应[52]。巡警局的官方说辞从最初的强调征收原因,转而从权利与义务的角度进行解释,指出:“警察为保卫人民而设,而人民即各有承担经费之责,如东西各国通商大埠,所有警察经费无不筹于民间”[53]。舆论对此亦表示认同,“国家有保护民之责任,斯人民有纳税之义务,此固环球之公例,而凡为国民者,皆所宜共认者也”[54],但也认为应该根据人们的经济情况酌情征收。
“房捐”事件平息后,《盛京时报》第五版“杂录”栏分别在10月11日、13日、15日、16日、19日、20日、22日连载《奉天房捐风潮记》一文,该文作者根据报刊报道、坊间传闻,以小说的形式勾勒了事件始末。作者认为此次事件爆发的原因是官商沟通不畅,商人之所以取得胜利,“虽是商权伸张之力,究竟是立宪新政之便宜商民也”[55]。该文反复强调清末新政实施以来国民意识逐渐形成,并直书国民、国家、权利、义务等近代西方政治文化概念在此次事件中的呈现及运用。作者认为抗“房捐”事件的根源是西方政治文化概念的引进与传统中国社会之间的冲突,并指出二者应该互相调适。从舆论来看,知识分子所关心的并非单纯的商人内部或商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而是意在借此事件在公共舆论领域表达自身的意见,媒体亦乐于刊登此类文章。而以小说的形式叙述此次事件原委,既有可读性,又能将作者所关注的近代思想概念传输给普通民众。
四、余 论
清末新政改革总体呈现出调适和冲突并存的状况,奉省在推行新政过程中亦呈现出这一特征,但也有其特殊性。首先,其发生背景具有地域特性。不同于内陆各省,东北因累遭兵燹,迟至1907年徐世昌任总督后,才开始全面推进改革,改革经费主要由地方承担。奉天商业也因社会动荡而一度低迷,加上1908年的币制改革,市场秩序紊乱。当巡警局仿照京津地区加收“房捐”时,便引起商人的极度不满。同年8月6日,各会董、商人代表与商务总理赵国廷之间的冲突直接引发了商人群体抗“房捐”,进而演化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公共事件,直至最后集体罢市。其次,该事件得以进入公众视野,是近代奉天舆论空间发展背景下,《盛京时报》对此次事件进行了为时两个多月的追踪报道。商人由最初的试探性挑战到后来直接对抗,政府由最初的强硬姿态逐渐自降身段,到最后与商人协商各退一步。整个过程所昭示的是清末政府权力逐渐为社会力量所消解,民间商人团体试图借群体力量影响国家政策,以维护自身利益,更是国家政策在地方遭遇的挫折。虽然此次抗“房捐”事件是以商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呈现的,实际上推进了近代奉天新政改革的力度,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转变社会治理方式。经过舆论报道,该事件更成为公共事件,提高了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后续舆论的关注则主要聚焦于此次事件所呈现的近代西方政治文化概念,原本抽象的概念与具体事件结合,更具有直观性。媒体人以小说的形式对此次事件的回顾,增加了可读性和趣味性,既丰富了奉天民众的阅读生活,也推动了西方政治文化概念在东北地区的传播。